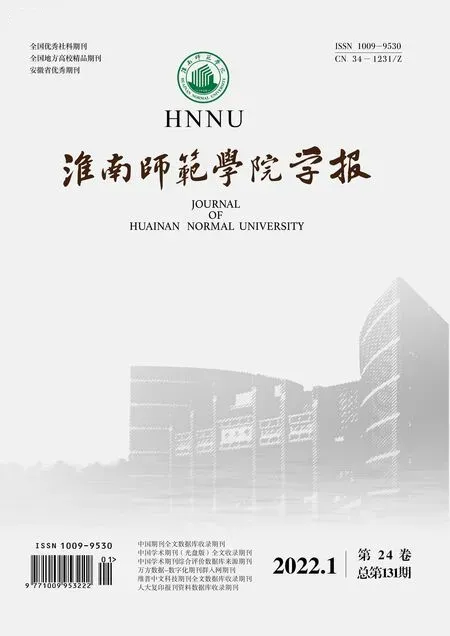超越生死与悲乐的生命范式
——《兰亭集序》的生命意蕴刍议
席思博,潘天英
(1.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公共教学部,安徽 合肥 230013;2.淮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魏晋时代生命意识的觉醒投影于文学的自觉,主要表现为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反思生命本质乃至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母题。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即是一篇追问生命之作。全文情感从“极视听之娱”到“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之痛,再到“临文嗟悼”之悲,情感跌宕起伏,辗转变迁。 文章前扬后抑,感慨万千, 透过文字不难品读到王羲之充满伤感的心灵,以及潜藏在心灵深处复杂矛盾的人生感悟。
一、由乐而悲:情感的两次升华
《兰亭集序》记录的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 年)上巳日的兰亭雅集。 全文由眼前会稽山水折入人之性情静躁有别,继而由“情随事迁”的共同感慨引出死生之论。 简淡之笔蕴含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情感变化过程。
(一)山水娱情之“乐”
开篇以极其简练的语言抒写兰亭修禊的快乐心情,这里的“乐”包含四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自然之乐。“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山高水秀,草木苍郁,修竹挺拔,是自然界赋予人的一种美的享受,更是一个放飞心性的环境。再加上“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美好的天气令人心旷神怡,实在是纵情山水的最佳去处。游览山水,享受自然美景,这是对自然的一种亲近,更是人类融入自然的一种生命追求。二是祈求生命安康。 选择“暮春之初”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美好时令去修禊事,本身寓意着对生命的热爱和敬重,即追求生命的安康。 单从季节特征来说,春天是生命重生的吉祥时节。 在这个时节又是去做“禊事”,吉祥之意更加突出。因为“修禊事”本身就是祈求吉祥幸福的活动。《艺文类聚》记载:“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1](P62)三月之初修禊事就是为了消灾祈福,暮春时节就是吉祥之日,充满吉祥的时令与表达祝愿的修禊事活动结合在一起,表达的是对生命意义的尊重。 三是雅集之乐。 修禊事虽然只是一种风俗习惯,但已不仅仅是祛除疾病、祈愿幸福的生活期盼,而更多的是借助修禊事来进行文学创作、 书法品鉴等高雅活动,以此减轻在官场上挤压的心灵劳累。这样一种放飞心性的文人雅集,对人格的修养、品德的提升,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探寻,都是一种极富雅趣的事情。 与王羲之同去修禊事的多是品行高尚、有才学、志趣相投的文士。史书记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于此焉。 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 ”[2](P2098-2099)谢安、孙绰之辈,既是东晋的贵族,又是品行清高的文人,与王羲之有着志同道合之趣,他们借助修禊事来陶冶情操,修养心性。
(二)人生倦怠之痛
在描绘了美好景色、抒写欢乐之情之后,“作者笔锋一转,由叙事变为抒情、议论,由写欣赏良辰美景、流觞畅饮,转而引发出对乐与忧,生与死的感慨。”[3]这就形成了一种情感的突变。在对生与死的思考之中,传递出作者对人生现实的尴尬和生命价值的复杂的思辨。
怎样对待生活,历来文人多有思考。“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苏轼对豁达乐观的人生理想追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文天祥对生命张力的追求。而王羲之则在追求生活的顺心快然,“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既有达观通达的人生观,也在追求现实生活的诗意境界。 而在追求诗意人生的过程中,作者更感受到人生理想与现实困境的矛盾,王羲之更从平静的现实生活中感悟到其中隐藏的伤痛:“不知老之将至”, 生命在平静的生活之中不知不觉地消耗了,时光易逝,感慨由此而生。 这一伤痛使得文章情感得到了升华。
(三)生命追问之悲
从人生倦怠之感出发,王羲之再进一步深思的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 ”读古人的文章,与古人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但却又感到古人文章寓意深奥,难以诉诸语言表达,这是一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痛苦。 作者追古及己, 由此引发“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生命思考,于是悲从中来,“进而探求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难免流露出感伤的情绪,历史在发展,由盛转衰,由生到死都是必然,正因人生无常,时不我待,才要著此文章,以示后来者”[3]。 从痛到悲,这又是一次情感的升华。
二、超越悲乐:生命价值的追问和思考
多数论者都在肯定《兰亭集序》抒发了王羲之寄情山水、无意功名的高尚情操,也高度肯定了《兰亭集序》最突出的主旨在于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阐释。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种观点认为,寄情山水、放浪形骸是王羲之根本的性格特征。这是肯定王羲之对待生命的一种态度:豁达自由。 顾农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忘却或淡化实际的功利的考虑,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生活,王羲之采取这样一种积极而达观的人生态度。 ”[4]而且,无论人生长短,不论生命质量高低,生命总是要走到尽头的,与其痛苦生活,不如尽情享受生活之美,“王羲之不赞成混同生死寿夭的所谓‘齐物论’,但他又很欣赏庄子反复提倡过的对待生活的审美态度”[4]。 其实,这样的生活价值追求是一种自由率真的生命观念。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羲之的生命观是一种生命自觉。 魏晋时期知识分子都在追求生命自觉,而且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下的一种生命自觉。表现为“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是颓废、悲观和消极的感叹,但实际上暗藏的应该是对生命、对人生的追求和留恋,亦是独立人格的觉醒”[3]。 更有人认为,王羲之的痛是对经世治国功名的失望,因而导致他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境之中。 “《兰亭集序》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由山水感发而悟玄理的信手拈来,不仅仅是纯然的‘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的生命恋歌,也不仅是‘情随事迁’‘修短随化’的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把‘死生亦大矣’放到时间长河中而产生的幽深浩叹,更是把个人际遇与家国情仇多重叠加的人生悲痛。 ”[5]两种观点都指向同一种理性思考,那就是《兰亭集序》最高的价值在于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思考。
从《兰亭集序》文本自身来看,文章的情感变迁带给读者一些矛盾的思考。 首先,作者与朋友修禊事是一种追求生命美感的仪式,兴奋和舒畅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所之既倦”的伤痛情感呢? 这是一种矛盾。 其次,作者既然“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与古人有心有灵犀的暗合,但为何又反对庄子一死生、齐彭殇的观点呢? 这又是一种矛盾。 最后,作者自己由乐而痛,再由痛到悲,对人生意义参悟深刻,但为什么期盼“后人览之,亦有感于斯文”?仅仅是想告诉后人这一人生道理吗?
对王羲之所写的生命之悲,有论者认为并不一定是悲,“这里情绪虽然明显地低沉下来,但并不完全是悲,尤非突然武断之悲,毫无道理之悲”[4]。 这实际是指出了王羲之的生命之“悲”意义的复杂性。
如果仅从表面来分析,《兰亭集序》情感变化是有一定的现实逻辑性的,但是,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些情感背后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恰恰就是作者内心的一种生命价值观的冲突,是作者对待生命和现实之间关系的一种矛盾心理。这种超越悲乐生命观使得作者的生命观显得深奥复杂。
三、寻求生命的合理范式
王羲之既深感人生短暂、 追求生命的现实意义, 又强力保持知识分子远离尘俗的高洁品质,在这种矛盾的生命观念之间,如何能够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王羲之不自觉地进入了寻求生命另一种存在形式的思考之中。如果从王羲之所处时代及文化背景来分析,或可探寻王羲之生命观的独特之处。
(一)玄学思想下“以无为用”的生命自觉
王羲之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玄学盛行的时代。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学以王弼玄学理论最为精华。 王弼提出过“体外无用”“用外无体”体用为一的哲学观点:“演天地至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6](P5)体用为一作为玄学对生命的思考,可以理解为无论生命的形式是放浪形骸、寄情山水,还是经国济世、追求功名,都只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没有高贵低俗和对错之分。 “此种由释大衍义而阐发的体用一如论(玄学本体论)或形上学主张体用相机不离,用者依真体而起,故体外无用,体者非于用后别为一物,故亦可言用外无体。 ”[6](P5)
玄学思想对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思考生命的价值产生了深刻影响。汤用彤说:“魏晋乃罕有之乱世,哲人们一方面立言玄远,希冀在形而上的思辨王国中逃避现实之苦难,以精神之自由弥补行动之不自由甚且难全其身的困苦。 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逃避铁与血的现实关系之网,因而对何为自足或至足之人格不能不有深切之思考。”[6](P8)很多的文士不再关心江山社稷兴衰,而是关心自己怎么生活得更潇洒,追求平静的生命状态。 当然,这种对生命价值的思考, 从哲理上说来既是对玄远世界的追求,也是在试图逃离现实,探得另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
作为魏晋时期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文士,王羲之追求一种矛盾的处世哲学,“谦以自处, 卑以自持,一方面避祸,一方面以无为用”[6](P130)。“以无为用”是对老庄哲学的继承,消极避世的无为处事方法也是一种有为,是一种抗争性的作为。 但是在当时政治斗争极为复杂的形势下,怎么能够做到在无为之中达到有为呢?这实际就是王羲之的一种矛盾的人生哲学。 在这种哲学理念支配下,他的内心充满无限的困苦。放浪形骸之外,只是一种无为的反抗,是一种对抗性的外在表现,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自觉追问和追求。 因而也就有了由乐转痛,再到悲的心路变迁。
(二)在寄情山水中寻求心灵慰藉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由“谈玄避世”进而转为在山水中寻求慰藉是这一时代的突出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 辞必穷力而追新, 此近世之所竞也。 ”[7](P65)实际是概括了魏晋以后的文坛风格变化,从玄言诗走向山水诗,在山水中寻找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
文风的变化则折射出魏晋之后文人的生命价值追求。“如果说‘庄老告退’喻示着‘理’的稀释,那么‘山水方滋’便体现出‘情’的深浓。 ”[8]玄学只是对人生意义的一种抽象的思考,而寄情山水则是对生命意义的另一种思考。 山水的兴起,实际是摆脱玄学的远离尘俗而转向寄情现实中的山水之趣,在山水之趣中寻求一种新的生命存在形式。
魏晋时期文人墨士大多是在动荡的社会变迁之中从中原逃亡到江东,他们对国家兴衰似乎已经不再萦怀,但又受老庄思想和玄学影响,在对生命价值追问的过程中形成了寄情山水、修身养性的人生观念。 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寄情山水也是对当时政治的一种躲避和抗争形式,“思想宗主发生挪移,而佛学又‘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此造成士人语言、文字表达的滞碍。 君臣大义无须讲论,正始玄学亦告衰歇, 此时惟有自然景物才能够安顿士人心灵。士人遂投注情感于山林皋壤,‘山水诗’ 之出现,亦势所必然。 ”[9]
王羲之也不例外, 而且表现得比其他人尤甚,“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2](P2098)。 从《兰亭集序》文本自身来分析,“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抒发的正是对隐居山林的极度认同和兴奋。在这里可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小小的山水世界可以让作者肆意思考世界奥秘和人生真义,可以“游目骋怀”,尽情享受自由快乐的人生志趣。
(三)超越尘俗的生命追求
修禊事既是一种追求生命健康的风俗,也是一种守护生命本真的仪式。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用一种风俗仪式表现出来,既是个体的修养,更是避免政治挤压的一种智慧,是避开现实矛盾,以超越尘俗寄情山水来变相表达对现实抗争的一种生命价值追求。
修禊事正是这种兼有两重优势的风俗活动。《艺文类聚》中有对修禊事的介绍,“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宿垢,为太洁”[1](P62-63)。 这里寓含着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说,修禊事是官民共享乐趣的事情,风气盛行;第二层在于解释修禊事的生活审美意义, 修禊事是为了去除污浊求得洁净,从除病这一通俗的卫生习惯,上升到个人修养的精神层面,已经是一种精神活动;第三层则进一步上升到玄学的意义: 修禊事可以得到神灵的保护,这不再是一种世俗的生命意识,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思考。
晋人孙绰的《三日兰亭诗序》曰:“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耶。 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潦落之志兴……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1](P71-72)这是阐述曲水流觞的寓意,人们借水喻性,借助修禊事抒发心中苦闷郁结之情,寄情山水,消解心中不快。 这一兼有世俗和崇高两重意义的活动,正契合了王羲之的心理追求,王羲之曾说过:“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纳吾,誓不许之。 ”[2](P2094)不愿在朝中做官,即使是丞相招纳也坚决不应,清醒的意识和坚定的态度由此可知。
任何一种心理状态和心性选择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远离庸俗官场、寄情山水美景也不是王羲之与生俱来的天然本性。 特殊的社会环境、政治背景以及人生经历, 使得王羲之心中充满苦闷和伤痛。文章开头所写山水之美其实只是一个反衬,是一种反衬性铺垫,是为下文抒发心中伤痛之情和悲叹做出的铺垫。
享受自然之乐与逃避现实,二者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在这种矛盾之中,王羲之并没有陷入痛苦而不能自拔,而是在“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反思中找到自己独立的生存方式: 既寄情山水、放浪形骸,又坚守生命的现世存在,保持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这就形成了王羲之独特的生命存在形式。 王羲之没有像竹林七贤那样纵情狂放、荒诞不羁,也没有堕落到庸俗的官场得意。超越尘俗、寄情山水只是王羲之保持自己高洁品质的一种精神自救方式,集高雅与处世于一体,成为王羲之生命观的高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