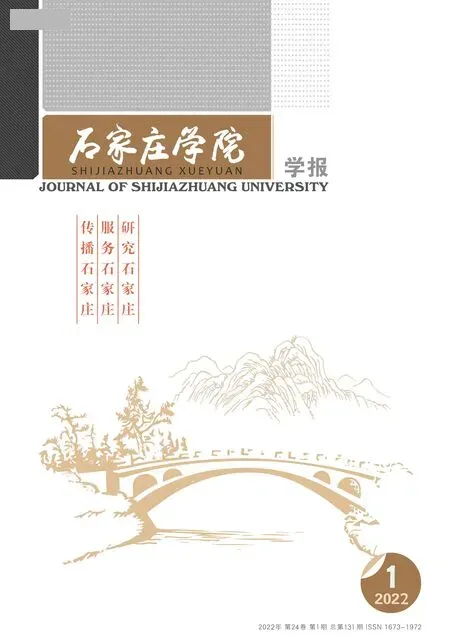孙犁小说的史笔与创作方法
张占杰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孙犁曾说:“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的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1]464在众多的孙犁小说选中,由资深孙犁研究专家刘宗武先生选编、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荷花淀——孙犁中短篇小说选》别具特色,诠释了孙犁的夫子自道。此书分为六辑,总体上由两部分构成,以1949 年为界,前半部分以孙犁的革命足迹为线索,将表现抗战生活的作品分别编选,计有《光荣》《荷花淀》《山地回忆》三辑;孙犁1949 年12 月进入天津,工作于《天津日报》,直至去世再没有离开过,因此后半部分以时间为线编为三辑,即《村歌》《铁木前传》两部中篇小说以及《芸斋小说》。此书还附录了编者2013 年发现的孙犁育德中学时期的小说《麦田中》,读者可以一窥孙犁早年的文学创作和思想活动。六辑小说基本涵盖了孙犁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代表性作品,编者从孙犁60 年创作历程中观其小说创作,或许别有一番滋味。
一、心灵书写的史笔
小说最初记录的是街谈巷议、贩夫走卒的小事,却被当作时代风习的重要见证,由此成为史传文学的源流之一。后世小说家重视这一传统,彰显了作家的历史意识和小说作为文学体裁难以抹去的文化印痕。在追随现代艺术潮流之余,现代小说作家骨子里更看重小说所蕴含的实录精神,以平实、庄重的笔触描述大到历史事件小到百姓琐事,作品艺术水平虽有高低,却以历史描写的不可替代性诠释着现代文学经典的复杂意义。当代读者要想深刻理解那个时代的生活、文化、历史气息,这样的作品不可不读。
孙犁是解放区作家的典型代表,他的小说多借用史传体裁命名,如“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铁木前传”“风云初记”,“芸斋小说”也被特地说明是“纪事”,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尽管孙犁这样强调作品的史传性质,但毕竟不同于古代的“史传”,所以我们依然将其归入现代小说之列。孙犁的小说重视叙述的历史真实性,着眼于心灵、人性的探索,不同时期,其观察、感受的重点也不同。
1937 年,抗战爆发,家乡的农民站在滹沱河岸边,看着败退下来的士兵,不无忧郁地想到,难道中国要亡了吗?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状,农民们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这源于守土有责的民间伦理,与党派及其观念无关。孙犁无论是在学校当学生,还是去北平做公务员,再后来到同口镇教小学,身边都不乏共产党员的同学、朋友,但他谨记父亲的叮嘱,不参加任何党派。但国难当头,在共产党的部队及其共产党员的同学陈乔、李之琏等相约抗日时,他没有犹豫就参加了,所遵循的就是这一伦理。直到1942 年8 月,经过王林等朋友的动员,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最终经田间、陈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队伍中,他没有太多正面战场的经历,大部分时间是在边区编杂志、搞宣传,接触的大都是最朴实的农民,对这一抗战主体有着切实的认识。他认为,正面战斗固然能显示我们抗战军民的英勇,但边区农民的日常生活也是这个大时代的一部分,也要随着抗战的脉搏跳动,准确再现边区日常生活中的风习、百姓真实的思想和情感,是抗战史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孙犁的抗战小说展示的是边区军民抗战的日常生活,在对生活琐事的细致描述中,将乡村普通百姓最淳朴的思想、行为一一呈现。如:战士受伤回到村里,不甘心当一名普通农民,仍坐在担架上指挥伏击战,依然是一名“战士”;一个贫苦的农民邢兰,为了抗战,可以为战士腾出最好的房子,拿出过冬的柴草……正是这些每天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在村里组织互助团,帮助抗属,支撑着抗战后方的一片天。五四新文化运动,使许多城市的知识女性意识到“我是我自己的”;抗战,则使千万农村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视野开阔了,精神升华了,她们自立、乐观,意识到自己与男人是一样的。在抗战洪流中,她们识大体、顾大局,与国家命运与共。有了这些以女人为主角的日常风俗描写,小说才有了张弛有度的节奏和血色中的浪漫,一部真正的抗战心灵史才是完整的。
孙犁的“史笔”一直延续到新时期。“芸斋小说”描写文革世相,取材身边之人,有朋友、同事、邻居、甚至领导,延续了抗战以来的“纪事”方式,“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2]238。如当年《阿Q 正传》发表时那样,小说之真,引起了原型及其家属的不满,风波延续至今,令人难以释怀。但是,普通读者不会认为这是孙犁对朋友的扭曲、丑化。在小说中,孙犁以鲁迅式典型人物的塑造方法——几句对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便勾勒出精神世界的复杂,浸透了对人性的深邃观察。孙犁曾说:“我如不写,别人是不会知道这些细节。为后世计,我还是写一点吧。”[3]184正是基于这种使命感,“芸斋小说”才会有不同的思想意蕴,远远超出了个人恩怨。许多人看到的是孙犁的“一个也不宽恕”,却没有看到他对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无力感与命运的悲悯,这可能是“芸斋小说”被误解的根本原因。
孙犁的小说,也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作为1930 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尽管有着左翼青年的热血与激情,甚至偏执到“非左翼不读”的境地,但育德中学的教育并不是左翼教育,它更多执着于“五四”的启蒙,无论是每周六的名家讲座,还是日常课程上的熏陶,抑或作文训练,多是“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前者培养了孙犁对个人的信念,后者使他的家国情怀深入骨髓,两相结合,“个人性”在艺术表现上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孙犁的描写是“实录”,但不妨碍我们在其小说的背后,强烈感到“我”的存在,他在记录历史,也在审视历史、审视自我,细致地展示着思想情感甚至某些情绪变化的过程,对自己的“真情实感”也秉持着“实录”精神。《琴和箫》中,叙述了朋友夫妻的壮烈,欲言又止,但终究掩饰不了“我”不合时宜的哀伤。《钟》写的是一对小夫妻的爱情经历,结局的圆满与叙述语调的低沉相互映衬,叙事者在悲叹什么呢?《铁木前传》写的是合作化运动给农民带来的变化,但变化的结果并不是“翻身农民把歌唱”的大欢喜,却是朋友、爱人关系再也回不去的一声叹息。“芸斋小说”叙述了一群在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翻滚的各色小人物,在特殊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人性和命运,叙事者“我”对人情世故的顿悟和感慨,那份突出的“人情味”与“沧桑感”构成了这组小说的“灵魂”。从抗战小说到“芸斋小说”,有人说孙犁经历了从“审美”到“审丑”的变化,但我们看到的是小说背后那双审视的眼睛,那颗“人道主义”的悲悯之心,它们一脉相承,从未变化。孙犁小说创作60年,“我”在小说中对所见所闻也观察、审视了60 年,带有明显的知识者的身份、情感以及思想,其中细腻的情绪、情感和思想的变化过程,构成了60 年沧桑变化中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解放区经典作家中,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像孙犁这样固执地在作品中凸显自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身份”,这个“身份是各种“改造”难以撼动的“主体”。这种坚守,抗战时期一些批评者意识到了,给孙犁扣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新时期被批评家们看到了,孙犁成了坚守知识分子立场的典范,只是有些人认为他是在“向后看”,却没有看到其积极意义,即独立精神。
二、“我”与“我们”
孙犁在安国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小说,在育德中学读书时期写了《自杀》《孝吗?》《弃儿》《麦田中》四篇现代小说,其中《麦田中》最为成熟。可以说,通过阅读和创作,他已经对现代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相当熟悉。参加抗战之后,孙犁的创作与抗战需求紧密相连。1942 年之前,他的小说多是特写或人物通讯性质,如:《一天的工作》是他第一次当记者,到雁北地区采访后的通讯作品;而《丈夫》《战士》《芦苇》等发表时都标注为“小品”或“散文”,后被收入《孙犁文集》小说卷,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小说;同时期写的《识字班》《投宿》则作为散文收入《孙犁文集》。从内容看,归属散文的作品,更像是边区生活的“速写”“扫描”,以鼓舞士气为宗旨,重群体情绪的渲染,与晚年那种个性散文有质的不同。后来划归小说的,情节较为完整,对人物有较为细致的表现,作品中的女人多多少少有孙犁妻子的影子。远离家乡,他知道家乡的妻儿也同样挂念他,妻子对自己参加抗战要有一个心理适应与理解的过程,有不满也有荣耀,有思念也有坚强。思念亲人,情绪色彩浓烈,作品便有了抒情性。总体来看,这些作品可以称为小说,但作为“特写”可能更恰当一些。
自《爹娘留下琴和箫》开始,孙犁的小说创作意识凸显出来,我们很难再将这些小说同“特写”混淆。即使像《荷花淀》,尽管他自己说故事是听来的,不便称为小说,“是报道性质”,但已经没有人把它当作“通讯报道”。从文体上说,它和同时期写的《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解放区生活报道》《游击区生活一星期》有着明显的界限,区别在于叙述视角的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情感特点的不同。散文重在写“我们”,小说则更多是以“我”的视角写。孙犁在边区生活,从不缺少写作素材,在成为“作品”的过程中,“我们”或“我”的视角选择,决定了文本最后的形式。面对一则素材,当有太多的“个人”情感需要喷吐的时候,孙犁的想象力会左右故事的走向和人物刻画,当故事、人物和作家的情感有机融合在一起,便形成了独特的孙犁小说文体。
在《村歌》和《铁木前传》中,孙犁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再一次直面现实。收在《农村速写》中的那些特写作品,着眼点在翻身农民的喜悦和精神变化以及对新社会的认同感。以这些特写为基础创作的两部小说《村歌》和《铁木前传》,在创作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村歌》中的双眉,不同于水生嫂们,她已经“走出”了家,有着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作品展示了她在遭受歧视与迷茫时,迎难而上、冲破幕障,最终被男人世界接受的过程。一曲村歌,是双眉胜利的宣示,也显示了孙犁在那个乐观的时代对这种胜利过于乐观的情绪。一旦沉静下来,孙犁的乐观便会一点点消失,变得忧郁。因此,在《铁木前传》中,他描绘了小满儿身上旺盛的生命力,也描绘了觉醒的小满儿站在集体的门口,羡慕又有所顾忌,最后选择逃避的结局。孙犁受鲁迅影响,钟情于俄苏小说。1946 年他主编的《平原杂志》上连载的《米家庄》,就是他请诗人商展思根据《被开垦的处女地》改写的。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对《静静的顿河》以及高尔基、契诃夫、托尔斯泰的作品都有过认真深入的讨论。《铁木前传》有着《静静的顿河》的忧郁与宽广,所以在小满儿身上看到了阿克妮西亚的身影也就不足为奇了。
孙犁抗战时期的小说,确实存在着小说、散文界限模糊的问题。因为他有着丰富的素材,也有着独特而细腻的情感,一般性的报告、通讯等新闻文体难以兼顾,所以在写作实践中他逐步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文体”。虽然这在主流叙事中显得另类,但它本于“我”,即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独特观察与思想追求,以抒情性为其文体表征。孙犁接续了育德时期的小说创作,又不断充实、强化小说的内涵,不称职的“记者”最终成就了抒情的“小说家”。
“芸斋小说”是孙犁写“我”之思的极致,对文革期间的种种世相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不同的是,他以对“抗战”与“文革”两个历史事件的亲身体验和思考为基础,从中国文化精神现代转型的高度提炼出它们内在精神上的“两个极致”:抗日战争中农民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是一种“美好的极致”,而十年动乱,则是“邪恶的极致”。前者代表的是这个民族在危难时刻每个个体的家国情怀,他们团结一致,舍小家为大家,有着共同御敌的昂扬向上的精神,是五四启蒙中强调精神个体的觉醒、独立的同时沉淀下来的民族精神财富,理应成为新的国民精神的组成部分;后者代表的是特定环境中的人性丑恶,是“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这十年,也是孙犁深入理解鲁迅,与其达到精神上契合的十年。1981 年至1991 年,孙犁用了十年的时间,一边咀嚼,一边写作“芸斋小说”。不同于新时期主流的“文革”叙事,它超越了政治层面的控诉、批判与反思,与鲁迅小说的“改造国民性”命题连在一起,“不再借用已经被美化的历史传统语句来表达以前的自己无法忍受的龌龊、丑陋和愤怒,而是用特别而又平静、凝练的语言来表达对历史、对现在、对过去、对将来、对自己、对别人的见解、感受与思索”[4]。“芸斋小说”由此形成了“文革”十年表现上的个人话语方式。
三、传统影响下的小说形态
五四文学源于启蒙,大众的接受与参与左右着它的发展。1930 年代的“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便是将大众从五四文学的接受者转换到参与者的理论探索。1934 年,孙犁高中毕业一年后在北平市工部局工作,关注并参与了这场讨论,为此他写了杂文《北平的地台戏》。正如鲁迅所言,大众文艺运动的实践有赖于政治的推动。抗战的到来,为文艺大众化的推进提供了物质基础。晋察冀边区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使作家的关注点聚焦于民间文艺和传统小说,尤其是相关作品的形式、创作方式和内容,加之抗战发动群众的需要,传统艺术的理论研究以及对民间艺术形式的模仿、改造、创新形成了齐头并进之势。
孙犁自1939 年进入到晋察冀边区文艺界,一直在创作和批评两个领域参与这场运动,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推进着文艺大众化,为此尝试过多种文艺形式。他最早以诗人闻名,写过《白洋淀之曲》《儿童团长》《梨花湾的故事》这样的叙事诗,写过《咏水》①《咏水》,发表在孙犁主编《平原杂志》第1 期,署名:土豹,1946 年7 月7 日出版,是孙犁佚诗。土豹,是孙犁的笔名。之类的科普诗,还写过许多文艺大众化的批评文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研究,其中《说书》②《说书》最初在孙犁主编的《平原杂志》上发表时,题名为《讲评词》。是其代表作。他认为:宋人话本故事的特点是,叙述的是现实生活里的故事,为群众爱好;编得很快,编好就讲;用群众语言,非常流畅;故事通俗,有关风化。他进一步总结了中国小说的传统:“一个故事一定是越说越圆满、越精彩。因为它不断生发,添长枝叶,增加情趣,切合现实。而师傅传给徒弟,或者是叫同行的人学了去又说、又修改,这就成了多人的集体创作,有很多人的心血、才智放在里边,作品自然就更精彩动人。”[5]
《爹娘留下琴和箫》之后,孙犁更多尝试描写正面战场的小说。小说的素材多来自真实的事件、人物,经过加工、生发,形成小说。有时对一个故事重写、改写,就会形成源于一个故事的多个小说版本。在这一过程中,孙犁会将一些新的传说故事融入其中,使不同版本的小说既相互关联,又同中有异,如《“藏”》《第一个洞》,《爹娘留下琴和箫》《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芦花荡》《夜渡》等。对孙犁作品的改写、重写现象,一些学者予以高度关注,但多是考查其改写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但如果注意到孙犁《说书》中所谈到的古代小说的形成方式,这些改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孙犁对古代小说创作方式的一种借鉴呢?就小说内容而言,尽管孙犁战场生活有限,更多是在日常生活叙事中让读者感受浓厚的抗战气氛,但他不再满足于一个人物、一段故事的素描,而是讲求人物性格的发展、故事情节的起伏与完整,在故事的铺陈中借鉴传统小说挽扣与解扣的写法,讲求小说情节内在的逻辑性与紧张性。他甚至想写一组正面描写对敌斗争的章回小说,尽管最终这组小说“抽了烟”,但从中演化而来的那几篇“五柳庄纪事”③“五柳庄纪事”包括《杀楼》《村落战》《麦收》等作品。的叙事特征充分印证了他对故事写作的追求。我们重视孙犁小说的“抒情性”,但也不应忽略他对“故事性”的追求。同样是“挖地洞”的故事,1943 年5月写的《第一个洞》相对于1946 年的《“藏”》,人物的心理过程描写要少得多。《第一个洞》的叙述集中于杨开泰挖地洞的过程,从他老婆的怀疑切入,先是感到杨开泰对自己态度的变化,进而怀疑他外面有人,再到半夜追踪,直到解开谜团,夫妻二人和好如初。妻子的疑惑、焦虑成为追踪的心理动因,以妻子的视角叙述故事,把读者带入到妻子的情绪之中,做到了读者与小说中人物情绪共振的效果。《第一个洞》中的男主人公杨开泰,在《“藏”》中变成了女主人公浅花。小说的描写重点集中于浅花的心理过程,加入了对新卯家庭背景、新婚后日常生活的描写,将其之前的安详甜蜜与后面的夫妻关系紧张形成对比,再加入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进一步加深这种紧张感,使浅花想要解开新卯去向的动机越发强烈。疑团解开后,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加入了一段夫妻共同维护地洞的情节,紧张的气氛舒缓下来,形成一个完美的团圆结局。两篇小说的故事框架、叙事策略没有大的变化,后者注重人物性格的衬托、变化,因此更加丰满,对人物行为心理动机的有序展开使故事更具张力。以女人为主人公的大部分小说,最后往往写到矛盾解决后的甜蜜与安静,小说节奏发生了变化,抒情因此变得越发浓郁。包括《荷花淀》《嘱咐》在内的小说叙事,基本上保持了这样的特征,对传统小说叙事方式的借鉴显而易见。
孙犁抗战小说从古代白话小说传统中借鉴了其中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手段,“芸斋小说”则从史传文学传统中吸收了更多的养分,形成“芸斋体小说”。文言小说源于史传,其精神实质在于“实录”,包括内容的真实和思想感情的真实。内容的真实在于可查,有别于文学创作中的“艺术真实”。“芸斋小说”的写作本于“实录”,取其郑重之意,人物、情节也大致有据可查,但这些作品又不同于历史。孙犁着眼于真实的历史氛围、独特的历史细节,追求的是事实基础上的“艺术真实”。这些小说也借鉴了史传文学及《聊斋志异》的体裁及其写法,如《杨墨》《杨墨续篇》《王婉》的“列传”式样,《高跷能手》《女相士》的“志异”写法。在这组小说中,孙犁还创造性地引入了“太史公曰”“异史氏曰”形式,以“芸斋主人曰”的方式为小说添加一点“闲笔”。这些闲笔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用笔舒展,精神放松,显示出叙述者的真实意态。它们与小说主体相互映衬,又旁逸斜出,在“旧瓶装新酒”中拓展了小说艺术空间。
四、民间故事母题的互文
美国叙事学家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认为,互文性是指:“在某一文本与其引用、重写、吸收、延长或者一般意义上转换另一些文本之间的关系。该文本中出现的引用、重写等清晰可见。”[6]106-107民俗学故事母题流变是互文的结果,对经典作家创作留下的母题的互文也广泛存在,后世作家能从各种类型的母题中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在互文过程中创造出既连接传统又注入自己精神与艺术追求的新文本。孙犁在早年的乡村生活中对传统戏曲耳濡目染,其一部分抗战小说与古代“寒窑”母题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互文性便顺理成章。
“寒窑”母题来源于传统的戏剧、小说。吕蒙正、刘知远、薛仁贵、薛平贵等人的故事都涵盖了这一母题,故事的主人公不同,但都有一个基本情节:丈夫出门在外,妻子在家苦守,终得团圆,尽享荣华富贵。这些故事中,以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最为典型:相府千斤王宝钏彩楼抛绣球选中薛平贵,相爷不允,父女反目。王宝钏由相府入住寒窑,苦守18 载,盼得丈夫得天下,最后成一国之母。王宝钏倾心薛平贵,顺从的是心灵的抉择,付出的是真挚的感情,守护的是一个家,期待的是未来的重聚。这些母题故事中,“寒窑”是中心意象。由于故事主人公的身份及形象的细微变化,“寒窑”的蕴意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它寄寓着广大下层民众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迫切愿望,包含着对忠贞爱情的期许,蕴含着对贞洁名义的珍视。[7]
在一般读者看来,孙犁最好的抗战小说是《荷花淀》《嘱咐》,《爹娘留下琴和箫》被发现后,也被列入其中,喻之为“天籁乐章”[8]。但孙犁说,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是《光荣》,这与读者的阅读感受产生了差异。当我们把《荷花淀》《丈夫》《光荣》《嘱咐》放在一起阅读时,会突然发现,这也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是“寒窑”故事的现代版。在《荷花淀》中,水生嫂们尽管依依不舍,还是将丈夫送到前线;《丈夫》《光荣》写的是丈夫(男友)走后女人的思念,对寂寞和不理解者嘲讽的忍受,以自强自立的姿态调整、充实自己;《光荣》写了水生们光荣归来,水生嫂们的喜悦与满足;《嘱咐》则展示了新时代水生嫂们的精神境界,为了过安稳的日子,她们再一次将丈夫送上战场,使“寒窑”故事有了新的内涵。在《第一个洞》《“藏”》《女人们》《蒿儿梁》《山里的春天》中,尽管不像上面几篇那样突出,“寒窑”意象也是包含在其中的。
孙犁在对“寒窑”母题的互文中,寄托了对乡亲、父母、妻儿的深情,赋予水生嫂们的传统性格以新的内涵,使她们作为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屹立于现代小说形象谱系中。“寒窑”母题中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与丈夫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经济上的表现是一方面,在精神上,她们的自我价值只有通过丈夫或者夫妻正常的关系才能实现,对丈夫的忠贞,对痛苦生活的忍耐,甚至对背叛的刚烈反应,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因为丈夫是她们生活的全部。无论后世如何粉饰这种关系,赋予他们天涯海角、生死相恋的浪漫气息,仍改变不了王宝钏们“贞节烈女”的本质。在孙犁的小说中,水生嫂们的性格有着传统的忠贞、坚韧,但她们的精神世界中,丈夫并不是全部,这是与王宝钏们的区别。
孙犁小说中的女性是独立的。抗战既是一场救亡运动,也是一场启蒙运动。边区的救亡宣传队既是抗战鼓动队,也是妇女启蒙宣传队。宣传队通过办夜校,宣传新的婚姻法,倡导破除封建婚姻,启发妇女的自我意识,让她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能力,鼓励她们为了幸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样,才有了“走出以后”的王振中。当她们真正走出家庭那一方小天地,融入抗战的洪流中,才能在广阔的天地间真正成为一名新女性,才能在男人走后组织妇女游击队,做好抗战后勤工作,并为自己感到自豪。
在这些小说中,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温柔坚韧型,一类则是泼辣能干型。前者以水生嫂为代表,温柔贤惠,对丈夫的选择没有任何怨言,丈夫走后,承担家务,照顾老人,还参加了水上游击队。后者以《光荣》中的秀梅为代表,秀梅与原生青梅竹马,在原生妻子小五离开家之后,主动承担起照顾原生一家的责任,日复一日,等待着原生的归来。她们置身于抗战救国的大潮中,与男人们有着同样深沉的家国情怀,形成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光荣意识”,使她们能够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上看待丈夫们的选择。抗战这一特殊环境以及广大边区的启蒙运动,唤醒了传统妇女的自我意识,使她们真正摆脱了对男人的依附,走向独立,参与历史的创造。她们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正是一种新的精神面貌的表现。孙犁以“五四”人道主义视角看到了这场战争带来的传统伦理道德现代性转化,将其纳入到新国民性格的塑造之中,延续着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与构建“新国民精神”的命题相呼应。以水生嫂、秀梅为代表的妇女形象,不是浪漫幻想的产物,而是在现实大地上的发现,并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完成的形象,是屹立于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四新文学的经典形象。
五、结语
孙犁把小说当历史叙述,其创作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这得益于他对所处时代理解上的“历史感”以及中国传统史传文学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启蒙了他的创作,但在其创作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古代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创作原则与创作方式对他的影响也至关重要,越到晚年越是明显。我们还必须重视孙犁小说的抒情性特征,因为它是五四启蒙带给他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体现,是五四新文学将个性表现视作文学的生命的体现,孙犁的小说也因此成为现代抒情小说谱系的重要代表。尽管1930 年代孙犁就已经开始关注文艺大众化问题,但真正吸引他重视古代白话小说的是解放区“民族形式”的讨论,从此开启了他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研究和借鉴历程,突出表现为在自己的创作中尝试运用白话小说的创作方法与叙事方式,对传统“寒窑”母题的互文则是他一直以来受民间文学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晚年的“芸斋小说”是他解放后学习鲁迅,沉潜古籍,对传统深刻认识与观照,延续早年“民族形式”问题的思考,意图使现代小说创作有效接续中国古代传统的结果。
孙犁的小说,从古代传统与民间文艺中汲取营养,丰富了现代小说艺术的表现手段,历史意识与对民族形式的追求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