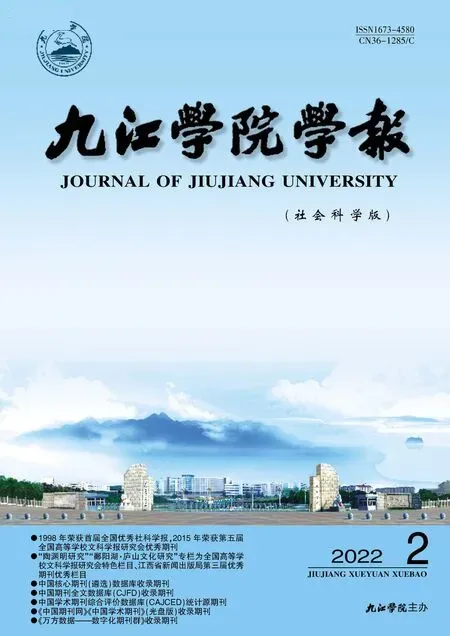六朝湓口关、湓城的历史及其方位考
吴国富
(九江学院学报编辑部 江西九江 332005)
据《晋书·地理志》,柴桑县有湓口关,简称“湓口”,其得名与水有关,附近的河流叫“湓水”,附近的湖泊叫“湓浦”,关上的城池叫“湓城”。因为“湓”与“盆”混用,所以上述名称也写作“盆口”“盆水”“盆浦”“盆城”。自唐朝至今,人们皆以为上述地方在唐代的浔阳城,即明清时期的九江府城,现在的九江市浔阳区;考诸史实,东晋南朝的“湓口”“湓城”应该在浔阳区西北七十多里处的城子镇(属今九江市柴桑区),与唐代浔阳城中的“湓口”“湓城”完全不是一个地方。
一、两晋南朝史料描述的湓口关
湓口关是长江九江段的水上关隘,在两晋南朝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军事地位。清代王谟《江西考古录》卷二:“晋时于湓口置关,其地最为要害。”“湓口又踞寻阳西偏,为荆楚咽喉,故其地在必争。”“凡寻阳有事,则湓口必先戒严,攻者不得不攻,守者不得不守。”如晋元帝称制江东,江州刺史华轶不从命,部属武昌太守冯逸等人与周访“大战于湓口”,周访大败之,事见《晋书·周访传》。晋成帝咸和三年(328),苏峻、祖约反叛,祖约部将祖焕欲袭湓口,陶侃遣部将毛宝击败之,事见《晋书·桓宣传》。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刘裕等人率义军讨桓玄,桓玄落败而西走,其部将何澹之等人守湓口,下到桑落洲迎战义军,一战即败,义军乘胜克复寻阳,事见《晋书·何无忌传》。南朝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1),侯景之乱方殷,王僧辩克郢州,乘流而下,遂克湓城。陈霸先自赣江入长江,与东下的王僧辩会师于桑落洲之西的白茅湾,事见《陈书·高祖本纪》。
东晋南朝时期有关湓口关的史料很多,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湓口”“湓城”的具体情况。
第一类史料反映湓口关与东晋南朝寻阳城不在一处。
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赐晋安王刘子勋死,长史邓琬奉刘子勋起兵反抗,继而称帝,雍州刺史袁顗从之,泰始二年(466)兵败被杀。《宋书·刘子勋传》:“沈攸之诸军至寻阳,诛子勋及其母,同逆皆夷灭。”《宋书·袁顗传》:“顗子戬为伪黄门侍郎,加辅国将军,戍盆城。寻阳败,戬弃城走,讨禽伏诛。”此事反映“盆城”不是“寻阳”。假如两者为一地,则袁戬必遭擒杀,无法再弃城而走了。南齐隆昌元年(494),萧鸾擅行废立,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懋谋伐之。萧鸾秘密派遣裴叔业等人偷袭寻阳,裴叔业先声言西上郢州任司马,至夜回袭湓城,遂下之。于是萧子懋“帅府州兵力据城自守”,事见《南齐书·萧子懋传》。湓城陷落之时,寻阳城(遗址在今九江市八里湖新区)尚在萧子懋的掌握之中,这也表明寻阳城与湓城不是一个地方。南齐末年,萧衍起兵于荆州,永元三年(501)八月命邓元起攻寻阳。镇守江州的冠军将军陈伯之退出寻阳城,让儿子陈虎牙据守盆城,事见《梁书·武帝本纪》。这又反映寻阳城与湓城不是一个地方。南朝梁太清二年(549),侯景发动叛乱,江州刺史萧大心移镇湓城,准备东下入援。第二年,萧大心将湓城让给鄱阳王萧范镇守,自己仍旧返回寻阳城,见《梁书·萧大心传》。不久两人互相猜忌,而萧范随后去世,萧大心派人夜袭湓城而不克,见《梁书·裴之横传》。此事亦足以反映寻阳城、湓城不在一处。
第二类史料反映湓城位于六朝寻阳城之西的上游地带。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殷仲堪、杨佺期、桓玄在荆州举兵,下至湓口,江州刺史王愉仓皇出逃。《晋书·殷仲堪传》云:“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临川,玄遣偏军追获之。”殷仲堪等人从荆州下来,假如已经到了寻阳城外或到了寻阳城以东,王愉就没法逃走了。如果湓口与寻阳城相距太近,王愉也是没办法逃脱的。以此而论,湓口在寻阳城西边的更上游地区,且与寻阳城相距有一定的距离。
梁朝著名诗人何逊《与沈助教同宿湓口夜别》曰:“我为浔阳客,戒旦乃西游。君随春水驶,鸡鸣亦动舟。共泛湓之浦,旅泊次城楼。华烛已消半,更人数唱筹。行人从此别,去去不淹留。”何逊与沈助教从寻阳出发,“戒旦”“鸡鸣”都表明黎明开始登船,而“西游”又表明是溯江而上。到湓口差不多一日途程,所以两人夜宿于湓口。假如“湓口”距离浔阳城很近,则完全没有必要在此住宿;假如“湓口”在寻阳城以东,就不能叫做“西游”。其中的“湓之浦”,又恰好表明当时湓口关旁边的湖泊叫做“湓浦”。何逊又有《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诗》曰:“的的帆向浦,团团月映洲。”反映湓城旁边有“浦”,对面有洲。
第三类史料反映湓口关位于江边,但地势较高,无法直接饮用江水,必须凿井而饮。
宋顺帝升明元年(477),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叛,萧赜(即后来的齐武帝)驻守盆城,布防得当,沈攸之遂不敢东下。据《南齐书·周山图传》,萧赜据守湓城之时,“众议以盆城城小难固”,周山图曰:“城隍小事,不足难也。”遂断取行旅船板以造楼橹,建立水栅,“旬日皆办”。又《南齐书·胡谐之传》:“世祖顿盆城,使谐之守寻阳城,及为江州,复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四:“时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镇寻阳,赜以为寻阳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镇湓口。”这些都反映寻阳城、盆城不是一处。《南齐书·祥瑞志》:“世祖顿盆城,城内无水,欲凿引江流,试掘井,得伏泉九处,皆涌出。”又反映盆城地势较高,城内缺水,“凿引江流”殊为不易,必须挖掘水井。南朝诗人何逊有《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诗》曰:“湓城带湓水,湓水萦如带。日夕望高城,耿耿青云外。”也明确描述了“湓城”地势很高的情况。
第四类史料反映“湓口关”附近有天然的大湖泊,便于停留战船,屯聚商旅,以是而成为当时的漕运中心和囤粮之所。
苏峻作乱,温峤命刘胤等守湓口。乱平,温峤奏以刘胤为江州刺史。刘胤借运漕而大做生意,《晋书·刘胤传》:“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江州运漕”应该就在湓口。
宋孝武帝即位之后,臧质任江州刺史,擅用盆口、钩圻米,导致朝廷不满。《宋书·臧质传》:“及至寻阳,刑政庆赏,不复谘禀朝廷。盆口、钩圻米,辄散用之,台符屡加检诘,质渐猜惧。”《资治通鉴》作“湓口、钩圻米”。胡三省注:“湓口米,荆、湘、郢三州之运所积也;钩圻米,南江之运所积也。”按“钩圻”即“钓圻邸阁”,在都昌;“湓口米”来自于江汉地区及洞庭湖地区,积累于湓口。
元徽二年(474),江州刺史刘休范于寻阳反叛,《南齐书·高帝本纪》:“元徽二年五月,举兵于寻阳,收略官民,数日得士众二万人,骑五百匹。发盆口,悉乘商旅船舰。”士众二万人皆以湓口的“商旅船舰”为战具,足见此处商旅之盛。宋顺帝升明元年(477),萧赜驻守“盆城”,周山图奉命加固城防,“断取行旅船板,以造楼橹,立水栅,旬日皆办”(《南齐书·周山图传》)亦反映盆城商旅云集,船只众多。
第五类史料记载了湓口关的开辟及浪井、陶公垒、南楼等故事。
东晋至南朝宋初张僧鉴《寻阳记》说:“湓城,灌婴所筑。建安中,孙权经此城,自标井地,令人掘之,正得故井。有石铭云:‘汉六年,颍阴侯所开。卜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满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权见铭欣悦,以为己瑞,时咸异之。井甚深,大江有风浪,此井辄动。土人呼为浪井。”(元代陶宗仪《说郛》卷六十一)《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九引用这个故事,稍显简略。宋代陈舜俞《庐山记》卷一记载这个故事,作“湓口城”。又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十:“灌婴筑盆口城,《十道四蕃志》:在汉高帝六年。”[1]《十道四蕃志》为唐代梁载言撰,所叙盆口城的历史当出自《寻阳记》。宋顺帝升明元年,萧赜命人在湓城掘井,得伏泉九处,喷涌而出,与孙权掘井的情况颇为相似。综合起来,《寻阳记》所说的“湓城”或“湓口城”就是两晋时期的“湓口关”,最初建造于西汉初的灌婴,东汉前期废弃,孙权时期重新设立,“浪井”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在六朝时期,“浪井”是王者的祥瑞之兆。左思《魏都赋》:“温泉毖涌而自浪,华清荡邪而难老。”《文选注》引鱼豢《典略》曰:“浪井者,弗凿而成。”[2]《南齐书·祥瑞志》:“谨案《瑞应图》:浪井不凿自成,王者清静,则仙人主之。”南朝陈徐陵《孝义寺碑》:“嘉禾自秀,浪井恒清。”
《南齐书·祥瑞志》:“世祖治盆城,得五尺刀一十口,永明年历之数。”“泰始中,世祖……治盆城,又得一大钱,文曰‘太平百岁’。”按《乐府诗集》中的《琅琊王歌》,有“新买五尺刀,剧于十五女”之语,“五尺刀”当流行于五胡乱华时期。“太平百岁”钱应即“大平百钱”,蜀国后主刘禅在位时期大量发行[3],在四川有大量出土,齐梁时代已称之为“古钱”[4]。这些南朝出土的文物,或能表明三国后期的湓口关已成为商旅往来之地。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八记载湓口城除了孙权的浪井故事之外,还有陶侃的“陶公垒”:“晋咸和四年,后将军郭默杀平南将军刘胤,叛于此城,陶侃讨默筑垒以攻之,默仍以布囊盛米为垒以应陶,今称云陶公垒。”
《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十二引《豫章书》说陶公垒在九江府城东北,“亦名郭默城”。事实上,“郭默城”有多处,或云在蕲水县(今浠水县),或云在黄梅县,或云在寿阳县,与“陶公垒”不是一回事。《晋书·郭默传》:“诏庾亮助侃讨默。默欲南据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筑土山以临之。诸军大集,围之数重。”参考《晋书·陶侃传》《晋书·庾亮传》,咸和四年十二月,郭默杀江州刺史刘胤,太尉陶侃令宋夏、陈修先行率兵至湓口以讨之,郭默则抢先占据了湓口关,宋夏、陈修攻之不克,只好“筑土山以临之”,此即“陶公垒”的由来。次年三月,庾亮率大军来到,但仍未能取胜。到了五月,陶侃又亲率大军赶到,郭默部下惊惧,遂缚郭默父子而出降。
唐代浔阳城有庾亮的“南楼”,通称“庾亮楼”。《世说新语》:“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据此记载,后人皆以为“南楼”在武昌。事实上,湓口自有“南楼”。《文选》卷二十有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李善注引《集序》曰:“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就明显记载了“湓口”有“南楼”。宋代陈舜俞《庐山记》卷一记载陈散骑常侍张正见湓城诗云:“匡山暧远壑,灌垒属中流。城花飞照水,江月上明楼。”诗中的“灌垒”当即“陶公垒”,“明楼”当即“南楼”。唐代白居易《初到江州》诗云:“浔阳欲到思无穷,庾亮楼南湓口东。”歌咏的虽然是唐代浔阳城的“南楼”,但却能反映湓口也有“南楼”。
二、湓口关不等于唐代的浔阳城
从中唐时期开始,人们皆以为湓口关、湓城在唐朝的浔阳城(亦即明清时期的九江府城、现在的九江市浔阳区);“湓水”指城西的龙开河,“湓浦”指城南的甘棠湖,“湓口”指龙开河的入江处,“湓城”指唐代的浔阳城。事实上并非如此。
其一,“湓水”发源于青盆山,流到长江边而入湖,这个湖泊就称为“湓浦”;“湓浦”与长江相通处称为“湓口”,建于此地的“湓口关”“湓城”,其名皆因“湓水”而来。但唐代的浔阳城与“湓水”无关。
按“湓”最初应该作“盆”。唐代徐坚《初学记》卷八引《浔阳记》曰:“盆水出青盆山,因以为名。带山双流,而右灌浔阳,东北流入江。”青盆山位于瑞昌、德安、九江县三县交界处,明清以来一般称为“秦山”。《乾隆瑞昌县志》卷二十三:“金盆寺,县南三十里。寺踞秦山巅,乔松修竹,匡庐长江,望之如在目前。寺前一泓莹净,因号金盆。相传秦时有王冢瘞山中,棺起穴存,后遂成池,寺旁犹存金吾将军故址。”青盆山得名于秦朝王冢的传说,发源于此山的“盆水”亦因此而得名。关于“盆水”的得名,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引《郡国志》曰:“湓浦水,有人于此处洗铜盆,忽水暴涨,乃失盆,遂投水取之,即见一龙衔盆,遂奋而出,故曰盆水也。”《明一统志》卷五十二引用这个故事,“遂奋而出”作“夺之而出”,语意更为明晰。
青盆山在总体上呈“西南——东北”走向,西北麓为山左,有狭长的山间平地,属于瑞昌市;东南麓为山右,亦有狭长的山间平地,属于九江县(今柴桑区)。《初学记》所引《浔阳记》,应即东晋张僧鉴的《寻阳记》,其中说盆水“带山双流”,分为左右两支,因此可以将两者称为“盆水左支”“盆水右支”。“盆水左支”沿着西北麓东流,过瑞昌城南而入赤湖,然后注入长江。唐代元结《瀼溪铭序》:“乾元戊戌,浪生元结始浪家瀼溪之滨。瀼溪盖湓水,分称瀼水。”清代地理学家齐召南《水道提纲》卷十:“湓口水,即瑞昌县东南杨林湖。”《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三:“赤湖,在瑞昌县东北二十里,周围百余里,汇县东北诸水成湖,自新、旧二口入江,中有石沃山、狮子山、金鸡嘴、破蛇洲,其水复分为车马湖、浴湓湖、遥泊湖及长港,旧皆掌于赤湖河泊所。”其中“浴湓湖”犹存“湓水”旧名,或因“湓浦”演变而来。
张僧鉴撰写《寻阳记》之时,唐朝的“浔阳城”(在今浔阳区)尚未出现。因此,“右灌浔阳,东北流入江”的“盆水右支”,就应该从青盆山东南麓东流,灌注到东晋南朝时期的寻阳城,而后在东北方向注入长江。东晋南朝寻阳城遗址现已经淹没在八里湖中,在遗址完全暴露出来且距离水面有一定高程的情况下,八里湖实际上是一条河流,这就是《寻阳记》所说的“湓水右支”。“湓水右支”与今浔阳区的甘棠湖相隔十来里路(直线距离),所处的地势比甘棠湖一带要低一些,在自然状态下是不可能流向唐代浔阳城(今浔阳区)的。1998年长江爆发大洪水,因堤坝决口,洪水涌入九江城西,靠近八里湖一带的地区被淹没,但甘棠湖并未被淹没,足以反映地势的高低。八里湖水原本直接排入长江,现代建造了闸门,提高了湖水水位,近二三十年来九江市试图将八里湖水引到甘棠湖,终因落差太小而未能成功。假如八里湖没有闸门,湖水直接排入长江,那么八里湖的水位会更低,更不可能直接流入甘棠湖。这也就是说,“湓水右支”与今浔阳区本来没有关联。又《南史·张孝秀传》:“遇刺史陈伯之叛,孝秀与州中士大夫谋袭之,事觉,逃于盆水侧。有商人置诸褚中,展转入东林。”这个“盆水”显然距离东晋南朝寻阳城较远,若在今八里湖或浔阳区一带,张孝秀是没法在“盆水侧”避难的。这一记载也反映南朝之时的“盆水”通常指瑞昌市境内的“盆水左支”,很少有人用来指称现代的八里湖。
《资治通鉴》卷十九四胡三省注:“湓口在浔阳,今德化县西一里有湓浦。”[5]《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三:“(湓水)绕城而东会诸水,水入德化县界,东经府城下,又名湓浦港。”“北入大江,其入江处即古之湓口也。”“按府志,城西一里有龙开河,长百五十里,源发瑞昌县清湓乡,东流入大江,盖此即湓水。”按照这种描述,湓水流到赤湖之后,又东下赛湖,再流到八里湖,再流到九江府城,因而龙开河就是盆水。事实上,这种叙述完全不符合当地的水文地理。
其二,唐代浔阳城是在东晋南朝寻阳城、湓口关被废弃之后出现的,与湓口关出现的地点、时代均不相同,两者并无直接关联。
按《隋书·地理志》:“立寻阳县,十八年改曰彭蠡。”《旧唐书·地理志》说隋朝的彭蠡县“取州东南五十二里有彭蠡湖为名”。从东晋南朝寻阳城(在今八里湖新区)到湖口的鄱阳湖大桥附近,大约就是五十二里,据此可知隋朝的寻阳县以及改名之后的彭蠡县,其县治依然设在东晋南朝寻阳城。
《明一统志》卷五十二:“浔阳城,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本汉浔阳县。其城晋孟怀玉所筑,隋因水患,移入城为附郭。”根据这一记载,到了隋朝,东晋南朝的寻阳城(在今八里湖新区)因为水患而被废弃。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说湓口城“自昔为戍守处”,“隋江州亦治此,既而寻阳县亦徙治焉。大业初,改曰湓城县。”按《旧唐书·地理志》,隋炀帝改彭蠡县为湓城,“取县界湓水为名”。因为水患,隋朝将位于八里湖寻阳城的彭蠡县治(原寻阳县治)迁徙到了湓城(湓口关),而县名也随之改为湓城。按《隋书·地理志》,湓城县包括巢湖、彭蠡湖、庐山、望夫山在内,几乎囊括了现在瑞昌市、德安县、星子县(庐山市)、九江县、九江市区的全部辖境,大致相当于两汉时期的“大柴桑县”。
据《旧唐书·地理志》,唐朝初年将隋朝的湓城县一分为三,武德四年分设浔阳县,武德五年分设楚城县;之后又合三为一,武德八年将湓城县并入浔阳县,贞观八年将楚城县并入浔阳县。很显然,湓城县的治所在湓城(湓口关),该县撤并之后,县治改为湓城戍。宋代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十三:“《唐志》:江州有湓城戍,寻阳县本湓城郡。”[6]楚城县的治所为东晋南朝的柴桑城,该县撤并之后,县治改为“楚城驿”。
据《旧唐书·地理志》,在武德五年的时候,有湓城、浔阳、楚城三个县。楚城县的核心区域在今九江市柴桑区南部。隋朝的湓城县因“县界湓水”而得名,唐朝因袭不变。浔阳县以“浔水至此入江”为名,“浔水”不等于“湓水”,在两县并存之时,“湓城县”也不等于“浔阳县”。换言之,唐初的浔阳县,既不会与当时犹存的湓城县并治湓口关,也不会设立在已经被水淹没的东晋南朝寻阳城,故而以“浔水至此入江”为名,在今浔阳区一带草创浔阳城以为治所。总结起来,唐代的“浔阳城”是在东晋南朝寻阳城被废弃以及湓城县降为“湓城戍”之后出现的城邑,这三个地方不能混同为一。
其三,六朝史料描述的“湓口关”或“湓城”,其特征与唐代浔阳城迥然不同。“湓口关”在东晋南朝时期是长江九江段的水上军事要塞,战舰云集,商旅杂沓,又成为荆州地区向朝廷输送粮食的转运中心。“湓口关”与东晋南朝寻阳城相距有一定的距离,是寻阳城的重要军事屏障,军情紧急的时候,江州刺史往往会临时驻扎在湓口。位于今浔阳区的浔阳城,唐代才开始出现,六朝文献中丝毫不见其影踪;本来也用不着与“湓口关”进行比较。但唐代的浔阳城出现之后,湓口关的许多地名被挪移到了这里,因此对两者进行一些比较仍然是必要的。
东晋南朝时期的寻阳县与柴桑县,分界很不明晰;但距离当时寻阳城咫尺之遥的今浔阳区一带地方,显然属于寻阳县,不属于柴桑县。相形之下,“湓口关”却一直属于柴桑县。唐初将湓城县并入浔阳县之后,湓城戍依然存在,也反映它与浔阳县治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另外,“湓口关”在东晋南朝寻阳城西边,唐朝浔阳城在东晋南朝寻阳城东边,方位也完全不同。东晋至南朝地位显赫的湓口关,留下的文物定然不少。然而现在浔阳区一带的考古发掘,又根本不足以说明这一点。正如吴圣林《湓城故址的考证与调查》一文指出,“湓城”作为一个城址,存续时间较长,地下必定有一定的文化遗存。然而现代的九江市浔阳区搞了不少的市政建设和人防工程,但迄今尚未发现湓城时代的只砖片瓦。在市区附近,就连这一时期的墓葬也极少发现[7]。
“湓口关”的城池建设在高地上,城内缺水,附近却有大湖可以屯留数以千计的战船、商船。今浔阳区一带,地势较低,常因长江涨水而遭受水患,地下水位很高,很容易挖掘到饮用水,不存在缺水的情况。城东的171医院一带、城南的南湖公园一带有低矮的丘陵,地势较高,但这些地方并没有任何古城遗址。城西南的甘棠湖、南湖,水面太小,根本无法容纳大量的船只。唐代李渤建筑的李公堤,表明自唐朝到现在两湖的水文变化不大。因此,“湓口关”的地形地貌与唐朝的浔阳城差异很大。
南朝时期,陈霸先称帝,湘州刺史王琳不服,引兵而下,屯于湓城白水浦,带甲十万。《陈书·侯安都传》:“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北齐书·王琳传》:“琳乃移湘州军府就郢城,带甲十万,练兵于白水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白水港在府西,亦曰白水浦。梁王琳破陈侯安,都于沌口,引兵下至湓城,屯于白水浦,是也。今亦曰白水湖,水溢成湖,水落为港。”说“白水浦”就是九江城东北的“白水湖”,也是错误的。白水湖与甘棠湖、南湖两个湖的面积大约相当,而且“水溢成湖,水落为港”,枯水季节水面更小,如何容纳“带甲十万”、数以千计的战船?事实上,这个“白水浦”就是湓口关边上的赤湖。
其四,城子镇的考古发现,足以反映这里是“湓口关”遗址。
九江县(今柴桑区)城子镇的火龙村,位于九江市区西北32公里处的长江边上,与瑞昌市交界,1988年在这里发现古城遗址,有人认为是东吴至西晋时期的“半洲城”,但据《元和郡县志》《同治九江府志》等记载,半洲城在九江府城西九十里,即瑞昌市码头镇一带,显然不在城子镇。城子镇古城遗址内有大量的六朝砖瓦,文物堆积层厚处达70厘米,附近还有六朝古墓群,毫无疑问是六朝的城邑遗址[8]。
城子镇的整体地形像一个向长江突出的三角形半岛,周长约20公里,江流为此拐了一个130多度的大弯。古城南负烟墩山(《乾隆瑞昌县志》称为“火炉山”),北临长江。烟墩山突兀孤立,高出江岸20余米,无疑是江防的制高点,可以从西、北、东三个方向俯瞰江面。烟墩山后面三四里处是白马湖,为赤湖的一部分;赤湖总面积有7.5万亩。在古代,赤湖与长江是相通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口被填塞,筑成防洪堤。
城子镇古城遗址与六朝的“盆城”有很多吻合之处。这里位于长江边,距离东晋南朝寻阳城六十来里。古城突出江中,地势较高,便于防守。孤立江边的小山容易缺水,但也容易挖到地下水。古城边上有与长江相通的巨大湖泊,便于屯聚大量船只并随时进入长江,形成天然的港湾。据《乾隆德化县志》记载,明清时期这里设有军事据点,建有营房、烟墩、瞭楼、牌坊栅栏等。这与唐朝设立“湓城戍”的情况相似。根据这些情况,可以判断城子镇就是六朝时期的“湓口”或“湓城”。
六朝时期的长江九江段有“大江”“小江”之分。《后汉书·郡国志》曰:“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南朝梁刘昭注引慧远《庐山记》曰:“山在寻阳南,南滨宫亭湖,北对小江,山去小江三十余里。”[9]综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六朝时代,长江从城子镇一带开始一分为二,北支即“大江”,为长江的主泓道;南支即“小江”,水流较小。“大江”流向今黄梅县蔡山镇,六七十里之后过黄梅县小池口,从桑落洲之西流出。[10]《光绪黄梅县志》卷四:“蔡山,县南七十里,相传古大江经其下,石崖缆迹犹存。”“大江自广济龙坪入黄梅界,旧绕蔡山,故蔡山有古江心寺。后长鸿脑洲,大江流过洲外,蔡山之江渐淤。后又长新洲,而江遂三分,至封郭洲复合为一。”[11]其中鸿脑洲与城子镇隔江相望,封郭洲则在黄梅县小池口,与桑落洲隔江相望。“小江”从城子镇下到今浔阳区一带,再下到桑落洲之西,与“大江”汇合。以此可知,六朝时期在唐代浔阳城一带设置据点,离大江、小江的合流之处尚有二十来里,只能控制“小江”,不便于控制“大江”;而在城子镇一带设置据点,则非常有利于控制“大江”“小江”开始分流的地方。到了隋朝,“大江”淤塞,“小江”变成了“大江”,导致江水上涨,淹没了六朝寻阳城;而后唐代浔阳城设置在今浔阳区一带,就可以控制合二为一的长江主泓道,而“湓城”的作用也就被唐代浔阳城取代了。同理,六朝时期的八里湖尚为一条河流,不是湖泊,当时的寻阳城位于河边而不是湖底;而甘棠湖、白水湖在六朝时期的水面应当比现代更小,不能作为大型的水军基地。
隋唐时期,天下一统,荆州、扬州互相攻杀的形势不复存在;因长江河道的变迁,“湓城”的地位也被唐代浔阳城取代。可以想象,在唐代的湓城县被并入浔阳县之时,原有的湓城县官吏大多变成了浔阳县的官吏,他们也就把原本归属于湓口关的“湓水”“湓口”“湓浦”“湓城”等地名,“浪井”“庾楼”“陶公垒”等建筑移植到了唐朝的浔阳城。对于新崛起的唐代浔阳城来说,接受这种文化移植并无什么障碍。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说及众多诗人的歌咏,这种被移植到今浔阳区的“湓城”文化产生了新的价值,但它们与东晋南朝时期的“湓城”文化显然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