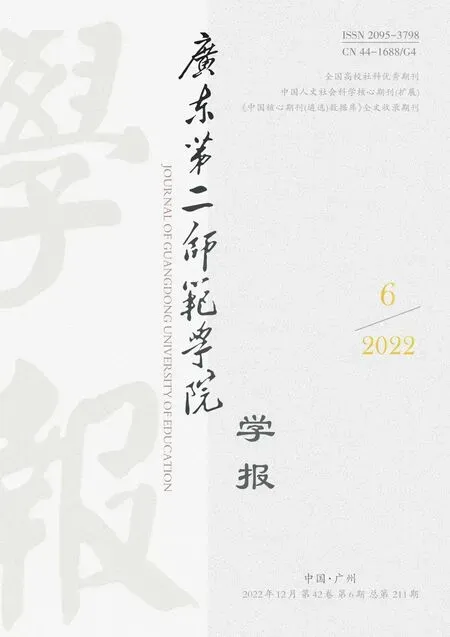中国心学教育传统与岭南心学的智慧
刘良华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上海 200062)
由孔子开创的原始儒学已经隐含了道家、法家和学问家(相当于“言语科”)等不同的方向。颜回倾向于道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与颜回境界类似的是曾点气象:“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颜回与曾点所代表的道家方向后来成为心学的基本追求,有人将颜回与孟子并列[1],王阳明则自比于曾点,“点也虽狂得我情”,而且明示:“以前尚有乡愿的意思,今得狂者的胸次。”(《传习录·下》)与颜回不同,子路倾向于法家,其理想是治理国家:“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论语·先进》)只要三年,就可以使民众勇敢善战且懂得礼仪。子贡与子夏比较重视博闻强记之“道问学”。子贡以言语科著称,擅长外交、商业。子夏长于经艺,传《诗》和《春秋》。清代一度有人认为,“颜子殁而圣人之学亡。后世所传是子贡多闻多见一派学问,非圣学也。”[2]颜回学与子贡学、子路学的分歧后来发展为孟子和荀子之争,在宋明时代则演化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争。朱陆之争是孟荀之争的延续。陆九渊直接引用孟子,“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象山语录》);而朱熹更接近荀子①朱熹直接汲取二程(尤其是程颐)及二程的弟子杨时的思想,属“道南学派”。杨时师从二程,学成南归,程颢目送曰:“吾道南矣。”道南学派的基本谱系是: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李侗传朱熹。详见: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M]∥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428-429.,有人甚至认为“朱熹是荀学。”[3]
孟荀之争、朱陆之争以及由岭南心学大师陈白沙挑起的“陈郑之争”(陈白沙与郑玄之争)的基本分歧聚焦于三个关系:一是情理关系(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二是学与思的关系;三是知与行的关系。
一、情理关系:情感对求知的兴发
情理关系主要通过三次争论呈现。首先是孟子与荀子之间的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争论,然后是宋代的朱熹与陆九渊的争论,最后是明代的陈白沙与程朱理学之间的争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湛甘泉和王阳明两个人,开创岭南学派。《明史·志第五十一》云:“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吕柟)与罗钦顺。”可见在陈白沙影响下,心学在明代已成为主流。
(一)孟荀之争
孟子以“人皆有不忍之心”讨论“性善”。《孟子·公孙丑上》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既然性本善,教育就不需要学习太多外部知识,而只需要“求其放心”而“自得之”。《孟子·尽心上》的说法是:“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走的是“由内而外”的路线。
荀子以“好利恶害”展开其“性恶”论。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对孟子学说直接提出批判: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荀子认为子思、孟子之罪在于误解孔子学说。荀子由“性恶论”而强调改造人性、“化性起伪”:以“人为之教”的手段来“改造”“雕琢”“控制”人的本性,使人“改过迁善”,强调“隆礼重法”,以此限制欲望的膨胀。《荀子·修身》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在《荀子》中频繁出现,达339 处之多。
表面上看,荀子对人性的描述比孟子对人性的解释显得更“实事求是”。比如荀子说,人总是“好利恶害”。这是普遍的事实。也因此需要以礼教和法治来限制人的情感欲望。孟子并不否认“好利恶害”的人性,以孟子的智慧,他也不可能看不到“好利恶害”的人性,也并不拒绝限制人欲的思路。
但孟子的智慧在于,他看到了人性中的善的本能。孟子与荀子对人性善恶的理解,直接影响其教育思想和管理观念。孟荀之争实质就是“内外之争”。荀子主张外铄论,孟子主张内发论或自发论。荀子倾向于性恶和外塑,故强调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重视教育以及法治对人的改造与约束。孟子倾向于性善和自发,故强调民本、民权、民主,谴责“民贼”“独夫”;重视让孩子自然生长,反对“揠苗助长”;重视对人性的保护,承认人的情感欲望正面的、积极的价值而不是压制人的情感、遏制人的欲望。荀子重视礼教、法治以及读书的外部力量的改造,而孟子重视发挥人的内在的主体性,让人主动发展。
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立足于性善论,孟子强调发挥个人的先验良知,有助于个人发挥其主体主义之自我修行精神。立足于性恶论,荀子不免重视外在法规的约束与惩戒。孟子浪漫,荀子理性。浪漫主义适宜作为理想的旗帜,而理性主义更适合作为现实的工具。也因此,后来有人提议“举孟旗,行荀学。”[3]
(二)朱陆之争
孟荀之争所隐含的内发论和外铄论在宋代“朱陆之争”中直接呈现为“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对立。据《陆九渊集》记载:朱熹主张多读书,“令人泛观博览”。而陆九渊主张“欲先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认为陆九渊的教育方法“太简单”,陆九渊认为朱熹的教育方法太重视整体,显得支离破碎。
按照朱熹的说法,“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熹的门人依其“语录”,整理成“朱子读书法”[4]。“朱子读书法”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在朱熹这里,读书是教育的基本途径。
与朱熹不同,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圣人之言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天理的标准。据《陆九渊集·语录上》卷三十四载,有人曾讥笑陆九渊:“除了先立乎大者一句,全无伎俩。”陆九渊听后连忙点头说:“诚然!”陆九渊的思路是:“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六经当注我,我何注六经!”当朱熹反复强调读圣人之书时,陆九渊反驳:“尧舜之前何书可读?”(《陆九渊集·年谱》卷三十六)
“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个质问便是陆九渊建构其心学教育的支点。陆九渊心学教育的立论与反驳,几乎都与这个质问相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陆九渊拒绝读书,他本人倒是对经典之书如《孟子》了如指掌。陆九渊主张一切从“发明本心”开端,“先立乎其大者”,而后才使之博览。在陆九渊看来,一旦“先立其大者”,则“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人可以成为“天地之心”的“主宰者”,可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陆九渊集·语录下》卷三十五载:“我无事时,只似一个全无知无能的人。及事至方出来,又却似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又曰:“志大,坚强有力,沉重善思。”这种“天地之心”的“主宰者”可以“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或曰“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陆九渊所立之“大者”,接近孟子的“大丈夫”以及“浩然之气”。
至明代王阳明那里,“先立乎其大者”被转化为“致良知”:“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王阳明集·续编一·寄正宪男手墨二卷》卷二十六)或曰:“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王阳明全集·答季明德》卷六)
由孟荀之争发端而由朱陆之争发展出来的“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之问,成为中国心学教育的首要课题。朱熹看重道问学,接近现代教育学之知识教育学派;而陆九渊看重尊德性,接近现代教育学之人格教育学。所谓“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也就是“情理关系”之争。
为了回应陆九渊的批评,朱熹后来做了反思。朱熹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陆九渊)所说尊德性,而某平日所闻,却是道问学上多。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道理全不仔细。而熹自觉于义理上不乱说,却于紧要事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一边耳。”即便如此,陆九渊并不买账。他认为:“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5]494
陆九渊的提醒或许是对的。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总有一个优先性的问题。尊德性虽不如道问学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尊德性却是提供安身立命的方向。失去了方向,无论如何道问学,都难免失之支离破碎。当然,无论陆九渊还是朱熹,两者都重视尊德性。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相对而言,陆九渊比朱熹更重视尊德性,正如孟子比荀子更重视尊德性。
(三)岭南学派
从原始儒学到宋代理学转变过程中的核心人物是朱熹。而在从宋代理学到明代心学的转变过程中,陈白沙起了关键作用。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6]。陈白沙被视为“明代心学的先驱”[7]。陈白沙倡导“以自然为宗”[8]19和“主静”[9]147,269的自得之学。
陈白沙倡导的“以自然为宗”和“主静”既有颜回、曾点等人的“道家”倾向,又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前提。“以自然为宗”和“主静”意味着人性本善,只是受外部世界的污染而变得晦暗不明。只要“精修”和“静养”,回归自然而“不假外求”,人就可以“浩然自得”。
主“静”原本是原始儒家的传统心法。至少在孟子那里,“养吾浩然之气”及其“求其放心”的静修方法已经明白地提出来。陈白沙推崇的“静坐”实际上就是孟子的“发明本心”和“求其放心”。陈白沙明确反对汉代郑玄(郑康成)那样的学问方法,认为郑玄虽著作等身,但失去了学问的大方向。所以陈白沙说:“莫笑老慵无著述,真儒不是郑康成”[8]880。
这样看来,陈白沙的“宗自然”与“主静”的思路,也可以理解为“先尊德性,后道问学”。这是心学教育的基本纲领。
二、学思关系:批判性思维对求知的兴发
孔子原本是“学”“思”并重的。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直为后人所称道①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接近康德所谓“知性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详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71.也有人译为:“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详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但是,孔子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后人:“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句话实际上使“思”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教育名言中落空。此后,学思关系在孟荀之争、朱陆之争以及岭南学派的理论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一)关于学思关系的孟荀之争
人们往往记住了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殊不知孔子尚有“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的另一种说法。荀子对孔子的这句话似乎心领神会,并将其转换成简洁明了的“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的话使“思”的含量进一步减轻,“学”的含量进一步增加。《劝学》置于《荀子》的首篇,看来并非偶然。所谓“劝学”者,意在劝“学”而不在劝“思”。在《劝学》中,荀子提出一系列“为学”的忠告:“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之学,重在《书》《诗》《礼》《乐》《春秋》等“五经”①荀子在《劝学》中提出五经,但在《儒效》中未提《春秋》。荀子“五经”虽不包括《易》,但荀子本人将之纳入自己的教学。。汉代开始提倡“经学”,荀子贡献最大[9]171。在荀子看来,“学”(读书)能让人借助前人的文化与道德成果而提升自己,少走弯路。“读书”之于荀子,犹如英国人牛顿所谓“巨人的肩膀”。荀子讲“高地”“风”“马”“舟”,牛顿讲“肩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荀子不承认思考的重要。与孟子一样,荀子也承认“心”的思考功能。《荀子·正名》曰:“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荀子·解蔽》则曰:“人何以知道? 曰:心。心何以知道? 曰:虚壹而静。”在荀子看来,人的心具有天然的认知功能,它是认识世界辨别是非的“天官”。人凭借耳目可以感知现象,然后凭借心辨别真伪。辨别真伪的办法是一心一意地专注于对象,不让原有的偏见或其他事物干扰认识。
如果说荀子选择了孔子的“思而不学则殆”与“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句话,那么,孟子似乎更愿意接受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的训示。孟子首先看重的是“思”而不是“学”,而且以“心之官则思”来证明“思”不仅重要而且可能。《孟子·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所谓“思”,就是“自求自得”“求其放心”,是将“流放”、丢失了的“良心”寻找回来。只需要停止放纵和破坏,就能够成为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自得”。《孟子·离娄上》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以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在这点上,孟子不同于孔子。孔子虽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原则,但总体上倾向于“诲人不倦”,不倦地为学生提供教学与教训。孟子不仅不好为人师,“甚至还反对教学”[9]168。
(二)关于学思关系的朱陆之争
朱熹与陆九渊有关学思关系的争论主要显示为“易简”与“支离”的分歧。有学者甚至认为,朱陆有关“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辩”只是表象,其争论的核心是教育方法的易简与支离之争[10]。也有人认为:“陆主演绎,执简驭繁;朱主归纳,由博返约。”[11]
陆九渊不满于朱熹所倡导的“字求其训,句索其旨”和“句句而论,字字而议”等学习方式,他由此而质问:“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血脉不明,沉溺词章何益?”(《陆九渊集·语录下》卷三十五)在陆九渊看来,“疲精神,劳思虑,皓首穷年,以求通经学古,而内无益于身,外无益于人”。(《陆九渊集·取二三策而已矣》卷三十二)
陆九渊强调“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卓然不为流俗所移,乃为有立”。陆九渊常告诫求学者:“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陆九渊集·语录上》卷三十四)陆九渊对自己的教学方法很自信:“某平时未尝立学规,但常就本上理会,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会,非惟无益。”他给学生讲课,往往“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陆九渊的说法是:“吾与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故人之听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为也。”(《陆九渊集·语录上》卷三十四)
求学不仅须自立自得,还要有“血脉”意识、“大纲”意识。“有一段血气,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却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为学的血脉也就是为学的大纲:“大纲提掇来,细细理会去,如鱼龙游于江海之中,沛然无碍。”(《陆九渊集·语录下》卷三十五)
据《陆九渊集》记载:“某读书只看古注,圣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须得传注? 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陆九渊集·语录下》卷三十五)
朱熹主张:“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积习既多,然后聪然有贯通处耳。”又说:“铢积寸累,工夫到后,自然贯通。”(《朱子语类》卷九)而陆九渊告诉弟子,其实,“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心明理,就可以把握一切。“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5]395。更豪迈的说法是:“六经当注我,我何注六经?”[5]522他觉得很多士人把精力耗费在经典知识的学习上,而朱熹一派更是把圣人之言看成是体验真理的途径。这样实在是增加思想的精神负担。所以他说:“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又曰:“今之论学者只务添人底,自家只是减他底。”(《陆九渊集·语录上》卷三十四)后来王阳明讲“吾辈为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明显受陆九渊、湛甘泉等人的影响。王阳明主张少读书,多思考,多行动。王阳明在《传习录》中的说法是:“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
(三)岭南学派关于学思关系的主张
陈白沙反对朱子理学读书穷理的求道路径,反对“支离”的章句之学。“今之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无可告语者。”[8]193
陈白沙并非完全否认读书,他反对的是朱子理学的读书方法。他认为,如果学习者读《六经》,只是读其支离破碎的章句字词,诵言忘味,断章取义,而不去理解其内涵意蕴,或者只是人云亦云,则《六经》也只是使人玩物丧志的糟粕而已。“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陈白沙由此提出“学贵自得”的原则:“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8]20
如何做到“学贵自得”? 陈白沙倡导两个方法:一是“以我观书”;二是“质疑”。
陈白沙的“以我观书”类似陆九渊的“六经注我”。陈白沙的说法是:“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矣。”[8]20又说:“千卷万卷书,全功归在我。吾心内自得,糟粕安用那”[8]288。可见,“以我观书”就是以自己的思考来带动阅读而不满足于支离章句,更不能人云亦云,使书本知识牵着“我”走。
如何做到“以我观书”? 陈白沙紧接着提出“学贵知疑”的方法。他的说法是:“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章初学时,亦是如此,更无别法也。”[8]165又说:“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皆由我,于子何有焉。”[8]287也就是说,读书要敢于怀疑,独立思考,有批判精神。如果读书只记住修辞章句,不带任何疑问或质疑,那就只能做圣贤和书籍的奴隶。
三、知行关系:行动对求知的兴发
知行关系的讨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尚书·说命中》的说法:“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是“知易行难”的较早议论。究竟“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一直成为悬而未决的议题。后来孙中山出于革命的需要而重提“知难行易”的说法[12]。除了“知行”的“难易”问题,争论更多的是“知行”的“先后”问题。由于“知行”的“先后”问题涉及知识的来源与标准,因而它显得比知行的“难易”问题更为重要。这个问题后来以“理论与实践”的名义不断被重新讨论。
(一)关于知行关系的孟荀之争
孔子比较看重“行”。《论语·里仁》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季氏》则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孟子延续孔子的“生而知之”的思路。《孟子·尽心上》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其实孟子所谓“良能”“良知”,主要是人与生俱来之“德”性或“善”端。《孟子·尽心上》的说法是:“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所谓“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已经接近“知行合一”的意味,虽然还不能说孟子已经是“知行合一”论者。
荀子将学习分为闻、见、知、行四个阶段。《荀子·儒效》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则百举而百陷也。”就“学至于行而止矣”来看,荀子虽重视“行”,但仍然只是先“知”而后“行”。近似于《中庸》所倡导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其实,先秦诸子在讨论“知行”关系时,只是浅尝辄止,并不深刻。“知行”关系到了宋明新儒家那里,才成为争论的中心议题之一。
(二)关于知行关系的朱陆之争
陆九渊的知行观已经接近“知行合一”。陆九渊重视在“日用”生活行动中发明本心。他提出:“圣人教人,只是就日用处开端。”①这与“顿悟”说有相通之处,“顿悟”说往往倡导在日用生活中领悟。所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人在形而下的世间生活中可以直接顿悟形而上的东西。参见:朱志良.禅门“青青翠竹总是法身”辨义[J].江西社会科学,2005(4):35-44.这条思路后来在王阳明那里得到发挥。
朱熹对陆九渊的批评是:“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陆九渊集·答张南轩》卷三一)他认为陆九渊虽然“气象甚好”,但过于看重实践而不重视读书。
朱熹承认“知与行常相须”,但明确提出“知先行后”:“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因为坚持“知为先”,所以对于求学者而言,还是以博“学”和读“书”为首要任务。
在王阳明那里,“知与行常相须”的命题才正式转换为知行合一:“知行合一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王阳明全集·与道通书》)也正是在这点上,王阳明对陆九渊的学说做了重要的“补充说明”。
陆九渊、王阳明所倡导的“知行合一”接近近现代教学论所谓“做中学”“教学做合一”“教育即生活”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陆九渊之所以抱怨朱熹治学“支离”,不仅针对朱熹过于看重考据、训诂,而且针对朱熹的过于看重知识(书本知识)而轻视实践。鉴于朱熹学说在明代已成为官方正统,王阳明尽量弥合朱陆的分歧,将朱熹学说心学化,从朱熹书信中选编“朱子晚年定论”[13],认为朱熹晚年“已大悟旧说之非”且“思改正而未及”。有人注意到:“在明代,朱陆早异晚同之说乃是合同朱陆的一个较巧的说法,也是朱学成为官方正统哲学情况下心学的护身符。”而朱学则强调朱陆早同晚异,“所谓冰炭之相反”[14]。
(三)岭南学派关于知行关系的主张
孔子之后,儒学逐渐分化为法家倾向的博学派和道家倾向的心学派。心学源自颜回,孟子发扬光大。孟子之后,心学一度淹没,成为“绝学”,唐代岭南人惠能则以南派禅宗“曲折”而“间接”地延续心学。宋代陆九渊等人视程朱理学为繁琐之学,重续孟子“绝学”血脉。陆九渊之后,心学断断续续,至明代岭南人陈白沙、湛若水,心学复兴,影响当世之王阳明和后世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诸贤。
岭南心学在心学发展史上地位甚高,气质独特,始终以“实践”为其核心精神。惠能开创第一代岭南心学,惠能之学貌似禅宗,实则儒家心学。唐代禅宗分南北两派:禅宗北派的领袖是神秀,走外求的道路,接近后来的程朱理学。禅宗南派的领袖是惠能,走内求的道路,接近后来的陆王心学。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陈白沙、湛若水寻找儒家、道家与佛家之内在关联,融汇而成第二代岭南心学(简称“陈湛学派”)。白沙心学是介于六祖惠能和康梁哲学之间的第二个阶段。陈白沙教育哲学上承六祖惠能心学,下启康梁教育哲学。白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传奇人物。他所开创的岭南心学通过湛甘泉和王阳明的发挥,让心学与程朱理学平分天下。有人注意到,陈白沙有两位师父:一位是惠能;一位是吴康斋。两位师父均认为劳动优先于读书[15]。六祖惠能教他在伦常日用和担水砍柴中修行。吴康斋令其耕作,辅之以经典。陈白沙由此走上与程朱理学相反的道路:重视劳动,不屑于与书呆子为伍,甚至认为读书太多太琐碎,容易成为书呆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白沙说:“莫笑老慵无著述,真儒不是郑康成”;又说,“他年倘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白沙先生行状》)也有人注意到,陈白沙有两位学生:一般人只知道陈白沙的著名弟子是湛甘泉,殊不知除了湛甘泉,还有王阳明。湛甘泉是陈形式上的衣钵传人,王阳明是真正的衣钵传人[16]。朱维铮则认为广东是王学的策源地;陈献章是王守仁学说的真正教父[17]。作为陈白沙的学生,湛甘泉教育哲学的核心是:随处体认天理。所谓“随处体认天理”,重点在“随处”二字。随处即随时随地的日常生活。学习的重点是生活与做事而不只是读书,在日常做事的过程中随处体认天理。王阳明与湛甘泉一样重视“伦常日用”。
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远续孟学(孟子儒学),近取惠能与陈湛学派资源,发展出第三代岭南心学。康有为尊孟,认为孟子“乃孔门之龙树、保罗”[18]。梁启超也一度以“絀荀申孟”为己任,发动“排荀运动”[19]。三代岭南心学虽有各自时代特色,却一以贯之地坚持“力行”。孙中山倡导“知难行易”,其良苦用心也在于倡导“力行”,并由此重视“意志力”训练。
一般人以为意志力的训练就是让学生坚持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在自己不感兴趣的方向持久地努力。在心学尤其岭南心学看来,这是搞错了方向。意志固然需要坚持,但意志力的动力主要来自爱好与自信而非来自简单机械的强迫与努力。当意志力形成之后,努力很重要,但是,当意志力尚未形成时,兴趣比努力更重要。
在意志力训练这点上,心学尤其岭南心学有其独特的贡献。现代教育有种种优势,但在意志力训练方面捉襟见肘,这是现代教育的死穴,而心学则以意志力训练为现代教育提供强心剂和解毒剂。
不仅如此,心学为意志力训练开发了有效的方法和策略。心学末流固然可能走火入魔而陷入狂禅、狂儒的极端,但心学正宗并不因此而改变鼓励和保卫学生自信心的初衷。就此而言,心学精神始于自信,终于意志。或者说,心学的核心精神是经由培育学生的自信心而发展学生超强的意志力,并由意志力走向“实践”,强调实践与实学,提倡“有行动的实学”。
有行动的实学不仅重视练习和训练之类的行动,更重视直接开展生活的“在事上磨炼”和“随处体认天理”的实践精神。传统教学重视书本知识,尤其重视四书五经等经典文本的学习,而心学更重视在日常做事过程中的自我体验和自我修炼。岭南心学为何珍视“随处体认天理”? 其秘密正在于“在事上磨炼”而不在书本磨炼。书本知识自有书本知识的重要性,但心学经由岭南哲人淘洗之后,书本世界之外的生活世界骤然成为一个不仅具有重要性而且凸显紧迫性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