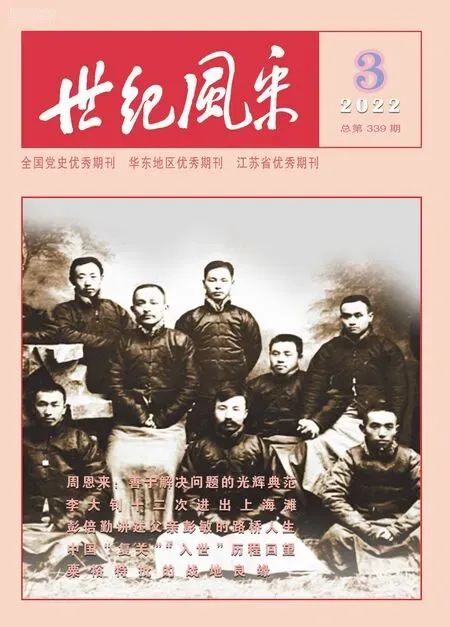李大钊十二次进出上海滩
徐光寿 徐超颖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对外交往和西学东渐的窗口,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主要传播地,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中央机关的长期驻地和民主革命的出发地。从戊戌变法、五四、建党乃至大革命时期,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无一不与上海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从留日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起,就曾踏上过上海的土地。在李大钊的革命生涯中,确切可考的记载就有12次进出上海滩,跨越了反袁反张斗争、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等近代中国重大事件。可以说,上海既是李大钊革命生涯的避难地,也是其除北京以外的革命事业的中心地。
一、留日期间两度来沪——为救国上下求索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逐步开始倒行逆施。至1915年5月,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体爱国人士的抗议。12月12日,袁世凯竟然宣布承受帝制,旋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更是激起反袁斗争之高涨。此间,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李大钊积极投身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并发起组织乙卯学会(后与中华学会合并为神州学会),展开反对袁世凯卖国、复辟的斗争。
为推动国内反袁斗争,1916年1月,李大钊离开日本到达上海,历时两周又回到东京继续留学。这是李大钊第一次进出上海滩。此时的他无心于上海的繁华市景,而是“心绪恶劣”,反袁复辟和忧心民国才是其心之所系。正如他在赴沪途中所作《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所言:“浩渺水东流,客心空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此次居沪两周,李大钊的具体行踪已无文字可查,但就其诗句“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来看,他是为反袁斗争而来,且对国内反袁斗争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此次两周沪上之行后,李大钊回到东京,竟因长期缺课被早稻田大学开除。为了国内反袁斗争,李大钊也不以为意。1916年5月初,他“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毅然决定离日归国,中旬抵达上海。时隔3月再来上海,李大钊住进孙洪伊的上海寓所,此间活动大致可分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孙洪伊、汤化龙的随从,追随孙、汤二人积极从事反袁的策划工作,站到了国内政治斗争的最前沿。李大钊回国后,主要担负汤化龙的对外联络工作,联系各方代表合力讨袁。还参加孙洪伊组织的“研究会”,讨论时局。
二是继续支持东京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的工作,并向东京友人介绍国内政治形势。1916年5月15日,《民彝》杂志作为东京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在东京创刊,李大钊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民彝与政治》,探求“为治之道”,论证“民彝”之神圣性与基础性,深刻阐述惟民主义思想。此外,李大钊致信远在东京的友人霍侣白,介绍抵沪后所了解的国内政治形势:“此间自溥泉(张继)公来,各派意见消融无间,裨益大局匪浅鲜也……”
三是与国内友人会面叙谈,参与些许饮馔观剧活动。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的同窗好友,留日期间二人就常以书信往来,此后一直过从甚密。此次李大钊来到上海,恰逢白坚武赴上海投奔孙洪伊。期间,二人时常会面,并相约出行。据《白坚武日记》所载,在李大钊此次暂留上海期间,二人相约多达十余次。甚至在李大钊7月11日离沪北上时,白坚武亦要同行,但因孙洪伊之“坚约同行”而作罢。
第一二次沪上之行,是李大钊毕生革命斗争的伟大开端和初步实践。第一次来沪使其对当时国内政治局势作了更真实考察,推动其从东京辍学归国之抉择;第二次来沪追随孙、汤二人参与反袁斗争,站在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最前沿,对其思想成长和斗争经验的积累,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二、避居上海百日——为反张复辟“仓皇南下”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北京局势顿时紧张。一向崇尚进步反对复辟的《晨报》编辑李大钊,被迫在7月初“仓皇南下,侨寓沪上”,仍然寄居孙洪伊寓所,再次开展反对复辟的斗争。这是李大钊第三次进入上海滩。
由于事发突然,加之行踪隐蔽,李大钊此次避居上海并无确切的文献记载。北京大学档案馆杨琥在《李大钊年谱》中推测,李大钊“在反袁斗争结束后,不仅与国民党人逐渐接近,而且继续追随处在当时国内政治核心漩涡中的孙洪伊,参与了一系列反对北洋势力的政治活动。因之,张勋复辟发生,不得不离京南下避难”。只是从与白坚武频繁往来的信件中,李大钊的心绪才可略见一斑。8月6日致白坚武的信中,李大钊赋诗表明此时心迹:“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白坚武说此诗“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可见李大钊此时内心苦闷和失意之重。8月中旬,李大钊致函在北京之友人李泰棻,虽然去信中有对李泰棻与李剑农关于“共和”“民主”两词的翻译之相关评议,但也无不透露其苦闷情绪:“南来栖迟沪渎,百无聊赖,幸有投止之所,不至漂泊旅馆,暇惟以读书自遣,尚足告慰耳。”又言:“至于发表言论,今已全非其时,即有所欲言,亦无正当之言论机关,供吾发表。”此类言语皆显李内心之失望与无奈,甚至自感怀疑,认为自身“年少性率,修养未善,诚信中孚,未足格物,有所论列,徒召恶感,不足诲人,诚不如缄默自守,徐俟劫尽之期,听其自忏之为愈也”,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些许悲观。

从7月初离京抵沪至10月18日离沪赴宁,李大钊此次逗留上海长达百日。虽倍感苦闷惆怅,但终究难以忘却自己对国家的责任。他以笔为器,先后于《太平洋》杂志发表《辟伪调和》和《暴力与政治》两文,针砭时弊,阐述思想。在《辟伪调和》中,李大钊对梁启超等人的新旧调和的怪论及其依附北洋军阀的行径进行了批判,言“今日伪调和之流行,几于遍国中而皆是”,“观于自命政团者,而宣言以无真是真非停止活动;身居要位者,而专意于自私自利一味模棱。人人相与以虚伪,事事相尚以颟顸……”言辞锋利,对时局一针见血。而10月15日发表的《暴力与政治》则是《辟伪调和》的续篇,文中李大钊重申了自己的非暴力主张和民彝政治观,反映了其对民主主义的执着追求。这两篇文章是李大钊第三次避居上海时思想和心绪的公开表达,显现了其避居上海期间对时局的思考。
经白坚武介绍,李大钊于10月18日离开上海前往南京与江苏督军李纯会面,接洽赴日事件,于一周后再次来到上海,又留10余日。期间,他继续与白坚武保持联系,直至11月9日,再次赶赴南京同李纯见面。此次留沪期间李大钊行踪如何,目前尚未发现资料记载,只知其致函白坚武信件一份,寄送《太平洋》杂志一册。就先前李大钊赴南京会见李纯是接洽赴日事件可知其有去日本打算,但因章士钊的介绍,准备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一职而放弃日本之行,因此在北上前再次至南京同白坚武和李纯告别。由此可大致推测李大钊此次在上海先是继续与白坚武联系准备赴日事宜,后接章士钊信邀决心北上,为返京后接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正式进入新文化运动阵营做准备。此次离沪北上,李大钊即将迎来其政治生涯的新阶段。
三、频繁出入上海——全力推动国共合作
中共二大闭幕后,李大钊于1922年8月下旬时隔5年再次踏入上海滩。本次南下,是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中共中央之命,前来讨论国共党内合作等重大问题。这是李大钊第四次来沪。
在沪期间李大钊活动频繁。8月26日,“与溥泉(张继)、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与反动派决裂。”8月27日,与马林、张国焘和孙洪伊讨论党的工作,并同胡适联系,告知南下商谈结果:“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并劝胡适“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在与各方会谈中,李大钊对孙中山和吴佩孚的政治态度已然明了,随即于28日前往杭州参加西湖会议,继续商讨国共合作问题。此次已是李大钊第五次来沪,此后短短3年间,他七入七出上海,皆为国共合作事宜奔走,步入来沪的高频期。
西湖会议结束后,李大钊于8月底再次来到上海,至9月8日离沪。李与孙中山进行了数次会晤,共商合作革命事宜,并经由张继介绍率先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9月4日,根据中共同孙中山协商的国共合作原则,李大钊参加了国民党改组委员会讨论改组问题,并重新就经费和出版刊物事向张太雷发电报。会后同孙中山会谈,决定赶赴洛阳与吴佩孚进行商讨。
在此期间,除了同国民党人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外,李大钊还公开发表演讲,进行青年团体动员。据《学生杂志》第9卷第11期刊载记录,9月3日,李大钊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的“国际少年日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号召青年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言语犀利地指出:“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是我们的仇敌。”就政治与教育的关系而言,李大钊对以往“教育与政治是两件事”的误解进行了批判,强调“我们绝不能把政治离开不顾”而空谈教育,“须要急起相持,非争到我们手里不止”。
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发生,北洋政府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向北京巡阅使王怀庆发出《令侦查李大钊活动以便依法惩办》的密电,以禁止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革命活动。为避免被捕,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的李大钊于2月上旬从武汉转抵上海,匿居孙洪伊家,后为避免与直系军阀关系密切的误会(此时孙洪伊和直系军阀关系密切)而搬离孙家,以示决绝。据3月5日《时事新报》刊登《北京大学旅沪同学会启事》通知可知,搬离孙家后的李大钊留下的联系方式是法租界环龙路44号张春木转,直至4月底离沪返京。

此次在沪停留近三月,活动大致有:一是总结罢工问题,讨论善后办法。2月12日李大钊赴寰球中国学生会,参加北大旅沪同学会的活动,讨论善后办法;2月22日再次赴寰球中国学生会,讨论学潮之事;3月30日,同马林、张太雷、邓中夏、蔡和森等讨论和总结二七大罢工后湖北新的罢工问题。
二是密切与上海职工和高校联系,频繁发表演讲。如3月11日,在上海职工俱乐部发表《马克思经济学说》演讲,向工人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4月5日,应邀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史学与哲学》,《申报》载文言“李君将史学与哲学之关系,解释极为透彻”,各报先后进行了转载,影响甚众;4月15日,应邀在上海大学发表演说,讲《演化与进步》,《申报》与《民国日报》均于4月16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此外,李大钊还参与了上海大学的改革事宜,与于右任、邵力子共商校务,推荐邓中夏任总务长,并建议开设社会学系,由瞿秋白任主任,恽代英、张太雷、蔡和森等到校任教,将上海大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共培养干部的基地。
三是促进国共合作事宜,为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2月,李大钊就同朱希祖拜访孙中山,“略谈北方事”。3月27日,经国民党本部宣传部长叶楚伧提名,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宣传部名誉干事。4月18日,李大钊以“T.C.L.”名义在《向导》第21期上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强调“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作为“反抗军阀的大本营”,并对国民党的历史和实际状况进行分析,指出国民党必须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改造成为一个能够领导全国人民结成革命联合战线的政党。4月,又与邵力子一起介绍杨钟健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吸收新青年,推动国共合作。
6月初,李大钊离京南下,经上海转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这是他第八次来到上海。据徐梅坤回忆,6月初,他与于树德、王振一、金佛庄4人,乘英轮“怡和”号从上海出发集体前往广州,在船上巧遇李大钊、陈潭秋、邓培等人,并同李大钊交谈。6月下旬,李大钊参加完党的三大后离开广州,7月初到达上海并作短暂停留。在沪期间,他“根据南方各地形势的变化,亲自观察了上海总商会对时局的态度和全国救国大会的情况”,这也为其到京后在《北京周报》上对时局发表独到的根本性评价做了准备。在7月10日离沪赴苏州参加蔡元培婚礼前,李大钊早在上海就已拜访了蔡,劝其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于7月9日出席了上海大学美术科学生毕业式并发表演讲,强调美术没有阶级,要反映现实社会的困苦悲哀,以图社会全部之改造。
1923年10月下旬,李大钊再次赴沪,同孙中山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据《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中记载,此次李大钊来沪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解决国民党内部关于共产党人加入的意见分歧问题,并于11月底至12月初与廖仲恺等国民党人会面并开会,具体讨论国民党改组以及次年一月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相关问题。
此外,李大钊本次来沪还以中共三大中央局成员身份出席了三届一次中央委员代表会议,并在会上汇报了京津地区党的工作情况,着重讨论了国民革命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宣传教育工作等,并确认将代表中共中央出席次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众所周知,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大学,一批共产党人在此任教,一大批进步青年在此学习。此次在沪期间,李大钊数次应邀出席上海大学的教学活动并发表演讲。11月7日,他出席上海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会”成立大会,发表题为《社会主义释疑》的演讲,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李大钊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能使社会破产,使经济恐慌和贫乏”,而“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认为在本质上,“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11月中旬再次在上海大学作《史学概论》的演讲,介绍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重点强调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说明改作、重作历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2月4日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的《劳动问题的祸源》亦是这一时期李大钊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劳动问题讲座上的演讲记录。在此次演讲中,李大钊对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贫困的根源。此外,李大钊还于11月21日和23日先后在中国公学中学和中国公学商科大学发表演讲,分别讲授《历史观》和《华茶贸易与蒙藏关系》,听者甚众。《华茶贸易与蒙藏关系》一文还连续两日发表于由日本人中岛真雄所创办的《盛京时报》的《实业栏》内,影响极大。

此次在沪期间,恰逢《晨报》创刊5周年,李大钊特作《时》一文作为纪念,于12月1日发表在《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文章对“时”的观念谈了种种感想,认为“时是无始无终的大自然,时是无疆无垠的大实在”,“时是伟大的创造者,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历史的楼台,是他的创造的工程。历史的废墟,是他的破坏的遗迹。世界的生灭成毁,人间的成败兴衰,都是时的幻身游戏”,感慨“今日之日,不可延留,昨日之日,不能呼返”,强调要珍惜现在,面向未来。
四、第十二次来沪——为国民革命而奋斗
1924年1月4日,李大钊、张国焘等6人当选为国民党北京支部代表,次日南下赴粤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据张国焘《我的回忆》,此次赴粤途中,李大钊一行在上海做了短暂停留,并出席了中共中央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国民党改组和中共代表在广州应该采取的态度,“李大钊先生在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声言北京中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1月10日上午9时,李大钊等北京代表乘苏州轮离沪赴粤。

离沪前夕,李大钊给爱国华侨徐瑞麟、吴亚男夫妇留下便条。便条全文是:“瑞麟、亚男先生:昨承枉驾,并馈食品,谢谢。‘苏州’将于今午12时启行,宠约不克如命矣。由粤归来,再趋访谈。匆匆,不尽白。弟李大钊敬白。”徐瑞麟是爱国华侨,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斗争。吴亚男则是章士钊夫人吴弱男的妹妹,也是最早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四位女性成员之一,二人都是李大钊的好友,当李大钊从北京乘火车来到上海时,徐、吴夫妇不仅前往探望,还馈赠了礼品,并诚邀其赴约。1月10日,李大钊因急于去粤而爽约,特留便条说明。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说是10日中午12点起航,实则上午9点离沪。3个小时的时间差,可能考虑了安全的因素。
一个月后,参加完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李大钊结束广州之行,于2月9日抵达上海。这是李大钊第十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上海。据黄日葵《给邓中夏和团中央的报告第六号(2月21日)》:“闻守翁有信给高、范、张、何,言‘闻京地各团体与我们发生冲突,宜让步’云云,全无其事。既无冲突,更无让不让之可言。现在除对外传播‘内部一致’,‘可以合作,不愿包办’之空气,及加以相当的准备外,余均待守翁回来,才能决定。”可见,2月21日前李大钊可能还在上海。而在此期间,李大钊于上海行踪如何尚未可知,但可猜测,李势必要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汇报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的相关情况。
关于李大钊是否出席了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这一问题,学界说法不一。朱文通在《李大钊年谱长编》中指出:“这次大会于11日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项英、李大钊、周恩来等二十人……”但这一史料是以按语形式列出的,真实性待考。杨琥在《李大钊年谱》中关于党的四大的史料记录并未提到李大钊,且同样以按语形式表明:“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0名,其中有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林育南、瞿秋白等。”许毓峰在其《李大钊年谱》中对此事件并未提及,但朱志敏在其《李大钊传》中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录又比较明确:“1925年1月,中共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出席大会的李大钊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显然,多数学者认为李大钊并未来沪出席中共四大,但确实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也未确认李大钊出席中共四大。所以,本文所谈李大钊12次进出上海滩,并不包括党的四大。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后,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党内同志和国际友人,都对李大钊的牺牲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在上海的鲁迅先生率先作出了评价:“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表达了对李大钊的深切怀念。
李大钊一生12次出入上海滩。上海既是他思想沉淀和播撒之地,也是他同各方进行广泛联系的媒介之所。自留日期间初次入沪,到国民党一大结束返京途中最后一次莅临上海,李大钊的上海之行皆处在其人生履历的关键时期,对其思想转变和政治选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严格说来,李大钊与上海的关系远不止这12次亲赴上海的经历,无论是从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与《新青年》的密切互动,还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程,亦或是大革命期间李大钊始终与驻扎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以及其数次在上海的多家报刊发表文章,与上海思想文化界保持频繁的交流,无一不展现了李大钊与上海这座城市间的密不可分。可见,北京之外,上海也是李大钊的主要革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