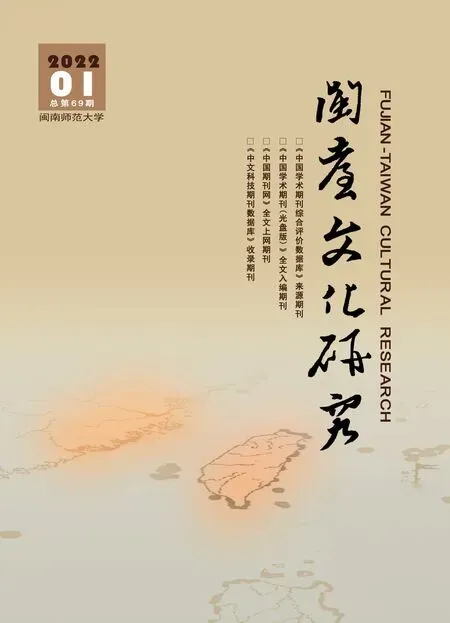论清代嘉义县城隍庙的经费、赐封及有关善堂
谢贵文
(高雄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系,台湾高雄)
城隍信仰虽起源甚早,但自明代方将其整体纳入国家祭祀制度,并且延续至清代。洪武二年新制,给予天下城隍神封爵及位阶化,视其为与现世地方官相对应的冥界管理者。洪武三年改制,则取消城隍的封号与封爵,以木主取代神像,庙宇建筑完全仿照各级地方官署,以作为官方的教化场所,且祭祀礼仪及庙宇管理皆有严格规定。[1]但自明代中叶以后,其仪式、神格与庙宇功能都发生重大变化,如祭祀仪式的世俗化,官方每年三次迎请城隍主祭厉坛的仪式,演变为民间热闹的“三巡会”;恢复城隍神的塑像及神诞致祭,其原为“冥界行政官”的形象,逐渐转变为阴间司法审判官;城隍庙则成为地方乡绅、生员与官员议论公众事务的重要场所。[2]此外,随着民间力量逐渐介入,城隍庙的修缮与管理越来越仰赖地方社会,官方以之作为信息播散与官民沟通的场所,士民亦利用该庙来进行立誓、慈善与招魂等,形成一种官民共享的空间。[3]
清代台湾虽孤悬海外,但仍依制度在各行政层级兴建城隍庙,成为本地最重要的官祀空间。透过这些庙宇及其活动,一方面可从官员、士绅、百姓的互动中,看见整体城隍信仰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与人文环境下,观察城隍制度在地方的实际运作与特殊表现。本文即以嘉义县城隍庙为对象,藉由文献史料及碑匾文物的分析,探讨其经费来源、皇帝赐封及有关的两间善堂。嘉义县原称诸罗县,乾隆五十二年(1787)因嘉许义民在林爽文事件的忠勇表现而改名。该县城隍庙建成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仅较台湾府、县为晚,且与澎湖县同为全台仅有两间获皇帝封号及赐匾的城隍庙,不仅在文献史料中多所记载,庙内亦保存多件碑记、匾额等重要文物,实为探究清代台湾城隍信仰的最佳案例,亦可与大陆的城隍庙相比较,扩展整体城隍研究的内涵与视野。
一、经费来源
城隍庙的经费主要用于两部分,一是庙宇的创建、重建、扩建与维修;二是日常运作所需的人事、香灯及固定的行香、祭祀等。明清两代虽将城隍神纳入祀典,但仅规定京都城隍庙的祭祀,各地城隍神则与山川、风云雷雨之神同坛而祭,另在每年三次的厉坛祭祀,须迎请该神前往主祀。而有关城隍庙的兴建与祭祀,则交由地方官员自行处理,道光十五年(1835)柯培元《噶玛兰志略》即明载礼部的态度:“部议以城隍神位既应附祀于神祇坛,即不必另为建庙。该督称噶玛兰地方建造天后、城隍二庙,应由该督自行筹办,不必动帑兴修,亦毋庸报销祭品银两,庶于礼典益昭画一。”[4]该部认为城隍神既已附祀于神祇坛(风云雷雨山川坛),自然不准以公费报销城隍庙的祭品,甚至连建城隍庙亦无必要;若地方仍要兴建,亦应由官员自行筹款,不必动支公帑。
另在乾隆十七年(1752)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中,记载台湾府的存留经费:“府县学、崇圣祠、文庙、社稷、山川等坛祠春秋二祭,并上中下元厉祭,共银一百九十六两二银钱……关帝庙祭银二十四两……祈晴、祷雨、谢神,共银三两。修理府县二学、文庙、城隍等坛祠,共银四十两。”[5]可见能动用公费祭祀者,有府县学、崇圣祠、文庙、社稷坛、山川坛、厉坛、关帝庙等,这些皆列入国家祀典;而城隍神已附祀于山川坛,故并未另编祭祀费用,只有修理城隍庙的经费,但仅区区四十两,还须与其他坛祠共享,显然只能做例行性维护。
在此一经费规定下,清代台湾城隍庙的创建、重建或修建,皆是由官员捐俸为之,或是向地方人士募捐,嘉义县亦然。根据《诸罗县志》记载其城隍庙:“在县署之左。康熙五十四年,知县周钟瑄捐俸建,规制颇宏敞。参将阮蔡文捐银四十两为助。”[6]又在周钟瑄《诸罗县城隍庙碑记》中,仅言“糜白金五百六十有奇”,并未载有地方绅民捐输或参与。这些说明该庙除参将阮蔡文赞助四十两外,主要即由周令捐建而成,此亦凸显城隍神在其心中的重要地位,故自愿承担大笔经费为之建庙。
不过,随着台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士绅阶层逐渐形成,也在公共事务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在现今嘉义县城隍庙内,尚保存一方乾隆三十年(1765)诸罗知县张所受所立“重建城隍庙碑”,碑文记载该庙创建后,曾经历两次修建,皆是采常见的“官倡绅继,官绅合捐”方式进行。[7]一是“雍正十年,前宰冯讳尽善、商绅陈君陆,旧贯重修。”此次为原样重修,主要出资者除知县冯尽善外,尚有商绅陈君陆,已可看见官方之外的民间力量。二是“甲申之蒲,余奉调斯土……爰捐廉俸,谋诸缙绅林振魁等,董事重建。幸都人士输诚乐助,计金二千有奇。召工营缮,秀石花砌,堂庑聿新;丹槛锦栋,灿然改观。”此次则为知县张所受到任后进行的重建,因是大规模的营缮工程,经费高达两千多两,除张令捐俸发起外,主要靠县城人士的踊跃捐输,甚至整个重建工作亦由士绅负责,展现民间力量的主导性。
城隍庙的修建经费虽然庞大,但毕竟数十年才有一次,并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反倒是人事、香灯、祭祀等例行性费用,才是官方须时时面对的问题。究竟这些例行性费用有哪些?大约多少银元?在《新竹县制度考》中收录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城隍庙住持僧所呈报的出息条款,从中可略窥一二。在全年开支部分,包括有住持僧、奉佛僧、差遣、烧火煮饭菜、打扫佛堂各一名的辛工银,及伙食米、伙柴、伙炭、伙食油、点火油、煤油、伙食菜、茶烟、檀柴香烛等费用,总计银三百七十二元。[8]
这笔费用即约占新竹县应支存留各款银一千三百多两的四成,且不能从存留经费中支应,必须由地方官员自行筹措,确实是不小的负担。所幸新竹县城隍庙有多笔民间献充的土地及瓦店,每年所收租银即甚为可观,加上普渡赈孤的纸枷钱,及善男信女所捐的香油钱,大概可负担这笔支出费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收入中尚有一笔淡水厅从渡船经费内提拨的献充银,[9]亦即官府将其在港口或溪流经营的渡船收入,提拨部分作为城隍庙的经费。这种作法也见于嘉义县城隍庙,如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记载诸罗县的桥梁,曰:“榕树王渡:在大槺榔保,县西南□十里。康熙六十一年,知县汪□□批允城隍庙僧人设渡济人,所收渡税充为本庙香灯。”[10]由于港口、溪流属公共财,设渡须经官府批准,地方官员即藉此为城隍庙开辟财源,也是一种职权范围内的弹性作法。
这种官员运用职权的弹性作法,确实是地方筹措官祀坛庙经费的重要手段。蔡东洲、张亮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考察州县武庙的收支问题,即指出地方官员会将百姓违法的罚款银两,及卖粮食过斗时所交之“斗息”税收,用于支应武庙所需经费。此外,官府也可以在调解民众经济纠纷时,诱导其将涉案金钱充作武庙经费,以摆脱官司麻烦,此即为“畏累充公”。[11]岁有生在讨论清代州县的祭祀经费时,亦指出由于地方经费拮据,官员往往会假借行政之名,向民间榨取额外的收入,此即为“陋规收入”。例如以供应杂差为名,强迫各村承担差徭,并折征银钱,再以此解决祭祀经费的问题。[12]这种作法或属于官员的行政裁量权,或游走于法令的灰色地带,但只要不中饱私囊,亦为朝廷所默许。
在清代嘉义县城隍庙的经费来源中,也可以看见地方官利用职权从民间巧取者。现今该庙内尚有一方道光十八年(1838)嘉义知县范学恒所立的《阿拔泉社番租充为香灯示告碑记》,即可从中解读出官员的取巧手法,曰:
据阿里山正、副通事番宇旺、尹和禀称:“本城内城隍庙,自昔我创建崇祀显佑伯尊神,声灵赫濯,庇佑四方,番民感戴,德泽无疆。适旺蒙宪恩饬充阿里山通事,进社安抚,沾沐神光普照,番民平安。爰是,细查邑庙香灯莫供,祇因出息无几,无以壮观瞻而报神庥。荣欲捐资供俸,抑恐住持花销有名无实,徒费微忱。惟思酌答恩光,必顺创业以垂久远,崇奉以诚取敬。兹旺愿将承受阿拔泉社所管界内每年产出什籽,除供应番食外,年余租税统共愿捐庙中,以作神前油香之资……”等情。据此,除批准存案给示勒石外,合行谕知,为此示仰该住持僧福海知悉,所有阿拔泉社内每年产出什籽,抽收壹九抽分早冬龙眼什籽等物,余息永远充入城隍庙以助香灯之资。
台湾于十五、十六世纪外人未入侵前,即居住着南岛语民族,古时泛称为“番”,今称“原住民”。清代的“番”分为“生番”与“熟番”两种,前者指住在山上未服汉族教化者,又分已、未归化两种;后者则指住在平地遵法服役、输饷者,又称平埔番。除未归化的生番外,其余各番社皆设置有通事,作为官府与番社的中间人,其必通番语、识书算,负责收管社租、纳课、发给口粮及派差役等工作。清朝统治台湾初期,通事多由汉人担任,亦扮演地方官派驻各番社的耳目与职役,权力甚至凌驾番社土官之上,且逐渐成为招垦番地的中介与支配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之后,因通汉语的番人渐多,且通事屡有滥权图利之事,故改以番人担任此一职务,偏远的归化生番因无通汉语者,则以汉人任副通事,但仍是实际处理贌社、输饷事务者。[13]在此碑记中的阿里山社,即属于归化生番,设置正、副通事,分别由番人宇旺、汉人尹和担任。
据该正、副通事禀称,因番民感戴嘉义县城隍的神威显赫,庇佑番社平安,故愿将阿拔泉社所管界内每年产出什籽之余息,捐给该庙作为香灯之资。这看似一桩感念神恩而喜献之美事,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因阿里山番人有自身的信仰,且与该城隍庙相隔遥远,不可能千里跋涉去求神庇佑,更不可能对汉人的神明有所感应,而愿将占地甚广的山林作物余租税捐献。如同台湾学者吴育臻的分析,最可能的原因即在“适旺蒙宪恩饬充阿里山通事”,嘉义知县范学恒任命头目宇旺担任通事一职,再与汉人副通事联合怂恿其捐出山林作为香灯之资,年轻不谙世事的宇旺出于感恩回报,也就不加算计地同意此一捐献。[14]
事实上,清代台湾成立香灯租的土地不少,包括有部落公地之给出、不征正供的田园之认捐、购置或受献的荒埔之给出、自己所有土地上设定香灯租、官衙拨出的香灯租及喜献等类型,[15]多属于汉人或官方土地,且主要出于信仰之目的;但仍有部分属于番人土地,背后都不脱官员或通事的操弄。除上述嘉义县外,凤山县(左营)城隍庙亦有类似情形,该庙内保存一方乾隆三十八年(1773)知县刘亨基所立的《城隍庙碑记》,内曰:“照得放索社土目麻□卓戈嘪加、留万大、卑力贤宗等,有埔园三十□甲,在观云庄尾,于乾隆二十六年舍入城隍为香资僧粮……付僧意端掌管收租,年纳社课□十石。”放索社属平埔番,又远在现今屏东林边地区,如何会舍其田产作为与其信仰无关,且相距遥远的左营城隍庙之香灯资?想来亦当是官员利用职权而向番人巧取的“不乐之捐”。这种作法虽出于公务的需要,亦解决城隍庙在内的官祀坛庙之经费问题,但却也造成番地的流失,凸显清代台湾番民的无奈处境。
二、皇帝赐封
自北宋中期以来,朝廷为因应民间祠庙快速增加,乃透过授予庙额、封号之方式,以区别正祀与淫祠,达到一元化的管理与统治。这种赐封制度至南宋已深入民间,民众认为神明显灵需要获得世人的肯定,透过赐予封号、爵位及匾额,可以鼓励神明持续的显灵。在这种信仰观念下,社会精英会积极为本地神明争取赐封,以提升其灵力与地位。由于只有地方官员有权向上呈请赐封,故这些精英必须寻求其协助;而地方官员亦需要借助他们来推动公共事务,故也会认同并支持本地的神明。两者即在此一制度下,维持一种非正式的合作关系。[16]
城隍庙在宋代也获得大量赐封,据赵与时《宾退录》所载有数十庙之多,即使未获赐封者,也会为自身编造封号,“朝家或锡庙额,或颁封爵;未命者,或袭邻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17]不过,这些赐封都是个别进行,至明洪武二年新制,皇帝方下令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其中府城隍封为威灵公、州城隍封为灵佑侯、县城隍封为显佑伯。虽然洪武三年改制,又去除其所有的封爵称号,仅称为某府州县城隍之神,但这些爵号仍深植人心,各地方也会持续向朝廷争取赐封,明清两代获赐额、封号者亦不乏其例。尤其清末面临内忧外患,各地城隍屡显护国佑民的神迹,朝廷也藉由赐封来安定民心、兴复王权,仅就《清实录》与《大清会典》统计,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加封号者即有110 余次,赐额则至少有180 余次,[18]显示该神受重视的程度,从中也可看见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权力互动。
清末台湾也同样战乱频传,尤其发生于同治元年(1862)的戴潮春事件,与朱一贵、林爽文事件合称为台湾三大民变,其历时之久、为害之大、官员死难之惨烈,较后二者犹有过之。吴德功在《戴施两案纪略》自序即言:“戴万生作乱三年,台湾道、镇皆殉难,知府洪毓琛亦积劳病故。尔时,北至大甲,南至嘉义,地方盗贼蜂起,官军南、北、中三路进剿,始克荡平。其害较烈于林爽文。”[19]在这起重大民变中,嘉义、淡水、大甲皆有城隍显灵事迹,嘉义县城隍神还因此获皇帝赐予封号,为台湾本岛所仅有,不仅是地方的荣耀,也呈现当地官员与士绅的合作关系。
有关嘉义县城隍神在这场民变的显灵事迹,《戴施两案纪略》有载:“时嘉义地方人心鼎沸,柳仔林、黄猪羔、黄万基等竖旗……贼攻城急甚,城上矢石如雨下,贼犹不退,后以火药掷之始溃,遍处抢掠而去。百姓见贼横行,绅士陈熙年等会百姓至城隍庙焚香,誓同心拒贼,并联络近城各庄应之。”[20]另在该庙内尚高悬同治三年(1864)署嘉义知县白鸾卿所献“至诚前知”匾额,款云:“壬戌(元年)三月,彰邑倡乱,我邑民心莫定,因率在城绅商祷于神,蒙赐签诗云:‘有祸不成殃’,嗣果被围至七月之久,卒获保全,益信神灵前知,其默佑为不爽也。”这些都说明该神在民变初起时,即发挥安定民心的关键作用。
清代台湾由于民情浮动,分类意识强烈,加上吏治不良,时有民怨,故每当一地发生民变,各地皆有响应者,常致一发不可收拾。同样的,戴潮春事件虽发生于中部地区,但嘉义县城邻近各庄亦有竖旗附和者,因攻城甚急,导致城内民心惶惶,不仅可能全面溃散,甚至会倒戈附贼,局面甚为紧张。所幸城内官员率绅商向城隍神祈祷,并获神示“有祸不成殃”之签诗,这不仅凝聚地方领袖同心抗敌的意志,也带给百姓有城隍庇佑的信心与安定感,而愿意追随官绅共同守城,最终得以度过难关。
类似的显灵事迹也发生在淡水厅。在戴潮春事件发生之前,士绅林占梅即洞烛先机,在淡水厅治设局团练,加强防务。当乱事爆发,淡水抚民同知秋曰觐南下驰援而殉职,一时城中无主,居民搬徙不定。绅商有主张贿贼以缓其来,或出城避贼者,但林氏独排众议,强调应守城抗敌,并捐助军饷,共推候补通判张世英权理同知职,且“率众至城隍庙,誓同心拒贼”,终能确保淡水厅城之安全。[21]林氏不仅守城有功,且在平定乱事上出力颇多,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林豪《东瀛纪事》即记载:“或于淡水城隍庙问彰化何时收复,得一签语,有‘若遇清江贵公子’之句,后果竹堑林雪村观察往剿始克。清江为观察小名,亦一奇验也。”[22]此亦城隍神藉由签诗预示乱事终将平定,且林氏将扮演关键之角色。
这种城隍神在社会动乱中的显灵事迹,乃清末各地常见的现象。有学者统计清朝官方资料中神祇显灵事迹,发现城隍神在咸丰之前并无任何记载,至咸丰方有11 次,同治有34 次,光绪更高达104次,高居各神祇之首,其中除降雨解旱外,即以平定匪乱最多。[23]这说明自明代以来城隍的官方化至为成功,祂不仅被视为与各级地方官对应的冥界行政官,甚至还成为国家的重要象征,当有危及政权的动乱发生,该庙即成为官绅宣誓效忠之所,也发挥安定民心、团结抗敌的作用。另外,清末各地城隍庙已普遍有灵签、扶乩,[24]透过这些与民间信仰相同的神示方式,使百姓更能接受城隍神背后所代表的官方意志,也有助于凝聚众人保家卫国的信念。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上奏《请敕封嘉义城隍折》,曰:
窃据前署嘉义县、现任台湾县知县白鸾卿详称:“嘉义县旧祀城隍尊神,祷雨祈晴,久昭灵应。其最著者同治元年彰化戴逆倡乱,围扑嘉城,绅士等恭请神位于城楼,虔诚吁祷,五月十一夜,地忽大震,雉堞倾颓而城垣无恙,兵民得以保全,咸称神佑。九月间,戴逆复扑嘉城,众心惊慌,告庙敬占休咎,蒙神默示平安,人心遂定,兵民竭力誓守,复保危城。”此皆该令署事任内所目击者。兹据绅民陈熙年等佥禀前来,伏恳奏请敕加封号,以答垂庥等因;并经台湾道夏献纶核详无异……[25]
联名上奏者尚有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26]光绪元年(1875)正月初十日,皇帝准其所奏:“以保卫城池,敕封台湾嘉义县城隍神封号曰‘绥靖’。”[27]
由此可知,在戴潮春党众围攻嘉义县城期间,城内士绅曾迎请城隍神位于城楼中供奉,以祈求守护城池。后来发生地震,城墙雉堞倾塌,但整座城垣却安然无恙,避免敌军趁机攻入,兵民皆视为该神的庇佑,也是官员特别强调的显灵事迹。“城隍”的原始意义为城墙与护城河,最早的显灵事迹也是在护佑城池,《北齐书》即记载慕容俨镇守郢城时,遭南朝梁军围城,并以荻洪截断水路供应,全城危在旦夕,“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所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欻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28]虽然其后该神职能日益扩大,但守护城池仍是最受倚赖者,当各地遭遇敌军围城,亦多会请神登城坐镇,如太平天国之乱时,湖南长沙府城、安徽怀宁县城皆然。[29]
此外,戴潮春党众亦曾围攻淡水厅的大甲城,同样发生城隍神显灵守城的事迹,如林豪《围城雨》一诗所言:“美贞孝林氏之善祷也……所居大甲土城,城内无井,居民汲溪水以炊。同治壬戌,彰化戴潮春作乱,屡围大甲,绝我汲道。民心皇皇,共请林氏祷于城隍庙,天乃雨;反风,贼之迫附濠边放火者皆反烧,贼军遂大溃,围乃解。”[30]大甲城及其城隍庙皆民间所建,但当面临围城危机时,绅民仍会祈求城隍的庇佑,并将危机化解归功其显灵所致。这些都说明城隍乃官方与民间共同的信仰,尤其当发生重大动乱,该神往往能凝聚官民抗敌的意志,确保王朝政权的稳定,这也是清末皇帝对其大量赐封的原因所在。
虽然嘉义、淡水、大甲都有城隍显灵事迹,但唯有前者获得赐封,一方面是因该庙为官祀,且当地被围城七个月之久,能在城隍庇佑下坚守不失,进而确保台湾府城的安全,确实是厥功甚伟;另一方面则是当地士绅锲而不舍地争取,加上国家政策与官员配合,终能成就此一荣耀。如同庞毅的研究指出,善城隍在太平军攻打长沙时因守城有功,而在地方士绅所请下获得赐封,背后原因乃城内商民在此战役中出力甚多,但却未获奖励,故藉由争取赐封来提升该神地位,以为酬神并获其庇佑,且可因神灵香火旺盛而得到经济的利益,此亦有表彰商民之效果。[31]同样的,嘉义县城在长期被围攻下,城内商民亦多所付出,藉由士绅陈熙年等人的呈请赐封,不仅是在荣耀其城隍神,也可为该庙及其周边城区带来香火与繁荣,此亦达到奖励商民的目的。
不过,即便地方绅民如何努力争取,若无官员的配合呈报,仍难以获得皇帝赐封。所幸在围城期间见证神迹并敬献匾额的署嘉义知县白鸾卿,后来再任台湾县知县,且在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桢来台时仍在任中,故能经台湾道夏献纶查核后呈报此事。而当时发生日本攻台的牡丹社事件,让清廷治台态度转为积极,沈氏奉命来此筹备防务,自然也乐于为地方神祇奏请赐封,以与本地绅民建立合作关系。又加上清末面临内忧外患,朝廷亦有意藉由赐封来兴复王权,以致各地官员积极呈报显灵事迹,获得赐封者亦大幅增加。就在这些官员与政策的配合下,嘉义县城隍神终于在乱事平定十年后获赐“绥靖”封号。
除了赐予封号外,嘉义县城隍庙还获光绪皇帝颁赐“台洋显佑”匾,迄今仍高悬正殿之中。在《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仅记载:“(光绪十三年春二月)十七日(乙亥),以神灵显应,颁福建台湾嘉义县城隍庙扁额曰‘台洋显佑’、龙神庙扁额曰‘海屿昭灵’、天后宫扁额曰‘慈云洒润’。”[32]详细赐匾理由则见于《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同年二月十四日条所载:
谕旨刘铭传奏神灵显应,恳颁匾额一折,福建嘉义县城隍庙、龙神庙及笨港天后宫均着灵应。上年,该县地方自春徂夏雨泽愆期田禾枯槁,经该官绅诣庙虔祷,甘霖立沛,岁获有秋,实深寅感。着南书房翰林,恭书扁额各一方,交刘铭传,祇领饬属,分诣悬挂,以答神庥。[33]
可知此一匾额乃因城隍显灵降雨而来。祈求雨泽亦为城隍重要职能,福建祀典规定:“凡祭坛雨日,委官雨缨素服,诣城隍庙、龙王庙读祝文、行香。(山川、社稷)两坛祭毕后,各官每日同诣城隍庙、龙王庙行香,第七日为止。”[34]凡地方遇亢旱,官员即需依此定制祈雨,如能顺利降雨,亦常归功城隍显灵,这也造成各地呈报以此类事迹居多。
皇帝赐封虽是莫大的荣耀,但地方的认知却未必正确。如嘉义城隍是获敕封为“福建台湾嘉义县绥靖城隍之神”[35],但地方却把封号当成爵号,宣称从“显佑伯”晋封为“绥靖侯”。又如“台洋显佑”匾乃因城隍显灵降雨而来,但地方却传说是清法战争期间,法军曾攻打嘉义东石港,战况紧急之际,突然狂风大作,法军受制于飓风,无法作战,乃转攻基隆。根据戍守东石将士所述,起风时有神仙显化佑助,观其冠袍似为嘉义城隍神;后来此事上奏朝廷而获赐匾。[36]这些或对制度有所误解,或有意夸大神迹,但都无损于皇帝赐封的正统性,迄今仍被庙方视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源。
三、有关善堂
从事慈善救济的善堂出现甚早,除宗教团体、家族所设者外,宋代开始有官方成立的居养院、安济坊、养济院、慈幼局等。明末则有民间的善会兴起,成立药局、育婴社等救济贫病。清初除官方所设的养济院外,民间的善堂也渐普及,且朝制度化发展。雍正二年(1724)皇帝谕令地方官员劝募好善之人设立育婴、普济两堂,以收容弃儿及老疾无依者,更使这两类善堂大量增加,且官方积极介入其管理与财务,协助整顿堂务与增加资金,而形成“官僚化”的现象。乾隆中期以后,又出现大量崇文敬字的惜字会与救济寡妇的清节堂,强调道德教化的功能。嘉庆以后,善堂则朝小社区发展,乡镇出现配合家庭制度的保婴会,施棺助葬会及收容流民的栖留所亦甚普及。[37]
城隍庙由于是依照各级衙门形制而建,为城市中规模宏伟的祭祀空间,也是官方进行教化及与民间沟通的重要场所,故与当地善堂亦常有连结。例如有些善堂鉴于城隍神作为阴间司法审判官的形象,而会将财务收支的征信录送到该庙焚化,以示绝无循私舞弊之情事。[38]又由于城隍庙与善堂皆具有教化功能,有些善会组织即设在该庙内,如江苏高淳、武进的惜字会皆是。另因清代慈善组织“官僚化”的发展,许多善堂皆设在官地上,[39]尤其城隍庙因占地宽广,有些善堂即建于其庙旁,如台湾府城内的普济堂“在县城隍庙侧(乾隆十二年建,御史六十七、范咸为文倡捐焉……屋舍二十间。嘉庆十二年,知县薛志亮拓城隍庙建两廊,乃徙普济堂屋舍于庙后)。”[40]
清代嘉义县城隍庙左侧亦有两间善堂,一是奉祀外江人士客死而无主者之英灵堂,二是代养贫民所生女婴的育婴堂。现今庙内尚保存一方道光二十二年(1842)嘉义知县王德润所立碑记,即记载有英灵堂设立缘由,曰:
据城隍庙僧会司僧福海禀称:“缘道光二十二年间,海倡捐□□□□祖开建城隍庙左畔圹地,创建英灵堂一座,供祀外江各处游幕士官、商民及跟官人等。在嘉义□□□并捐银起盖庙口右畔瓦店二间,收税祀祭。海经禀请易前主出示在案,但是香灯无几,所收不□□□。现海再倡捐鸠金,于上年十二月间,凭中郑黄明买嘉义保江滚、江来、江龙、江忠等田园一宗……年收税谷除完大租外,以为英灵堂清明、中元、冬至祀祭,语□□□无依之人病故,给为棺殓埋葬之资……禀缴伏乞恩□存案、出示立石,以垂永远。幽明均沾大德,合邑讴歌。切叩。”等情……为此,示仰合邑城庙内外士庶军民人等知悉,尔等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碑末载有捐款人,包括山东、温州、福州、汀州、常州、广东、苏州、福清、宁波等外地人士,安徽人僧福海亦捐银拾伍元。其后复勒一行文:“住持福海禀官……一所,自备工料兴筑阴灵堂,又捐银并起盖妈祖宫口左右九房二间,收税以为奉祀本……道光贰拾柒年贰月□日。”
清代从内地来台者,大部分是在此落地生根的闽粤移民,其后事多由家人办理,无后者则由地方代为处理。少部分是来此任职的文武官员及轮调戍守的班兵,其皆有固定任期,即使在任时亡故,亦有官方处理后事的机制。另还有少数的“外江各处游幕士官、商民及跟官人等”,他们仅短期来台工作或经商,亦非任正式公职,如不幸在此亡故,即使内地有家人亦难渡海处理,无依者更可能乏人安葬及祭祀,而沦为流落异乡的孤魂。这座由城隍庙住持僧人福海所募建英(阴)灵堂,即在解决这些外江人士的后事问题,兼具施棺助葬会与义冢的部分功能,乃本地甚为少见又具特色的善堂。
“游幕士官”即地方印官所延聘的幕友,在各级衙门皆有之。由于地方印官出身科举,不习吏事,尤其裁判、征粮税等主要职务又非所学,虽有佐杂但权限不大,且非其所辟举,自不能全予信任。加之清代回避制度,地方印官不得于本籍任职,所管地方常语言不通、人地两疏,而衙内虽有吏差,但学识有限,且皆系土著,常互通声息,挟制印官。这些都使印官必须延聘擅长吏务、明晓律例,且可信任的幕友辅佐治务,并代长官监督吏差。“跟官人”则称家丁或长随,乃地方官所自雇,主要随侍在官员左右,或协助衙务杂事,因多为官员亲信,亦会协助控制或监督吏差。[41]这两种人皆地方官所聘雇,理当随其同进退,但有的因主官在任内亡故,有的因故遭辞退,因返回内地困难,大多只能流落此地,也衍生出后事问题。
这种流落异乡而无法落叶归根的处境,安徽人僧福海当有更深感受,也促使他出面募建英灵堂。福海并非普通僧人,而是僧会司,根据《大清会典》记载:“凡僧官、道官皆注于籍。京师僧官曰僧录司……直省僧官,府曰僧纲,州曰僧正,县曰僧会……府州县各一人,由地方官拣选,具结详报督抚。”[42]可见他是嘉义县的僧官,由官方选派而来,同时担任城隍庙的住持,故能在该庙右侧空地兴建英灵堂,且能在庙口右畔起盖瓦店二间,收税祀祭,这些显然都有地方官的助力。福海的僧官身分,也让他募款顺利,故能购置田园及起建多间店铺,以收税作为维持该堂的费用。在碑文中所列的捐款人,亦皆为来自内地各处的外江人士,显示当时在县城任职或经商的外来客不少,出于对相同身分者的怜悯与照顾,也都能慷慨解囊,让这座英灵堂顺利建成。
福海选择在城隍庙旁兴建英灵堂,尚有两层特殊意义。一是自明代将城隍信仰制度化后,城隍庙就犹如衙门一般,不仅城隍神如地方印官高坐正堂,有时两侧还有下属各司、文武判官,甚至差役的塑像。因此,该庙不仅是官员祭祀及辅助施政的空间,衙门吏役也与之关系密切,既是庙内神判仪式的表演者,也是城隍赛会的组织者,甚至是庙务的实际管理者。[43]而这些游幕士官与跟官人虽非正式的官吏与差役,但亦为衙门中的重要成员,也必然常在城隍庙活动,并对该神有所信仰。福海身为城隍庙的住持,自然与他们多所互动,也对其处境知之甚详,故选择在庙旁兴建英灵堂,既可满足其生前的信仰情感,也是其死后灵魂最熟悉而妥适的归宿。
二是城隍神作为冥界的管理者,民间相信人死后魂魄被带离人间,要向该神挂号后,方正式成为冥界一员;福海在城隍庙旁建英灵堂,即有让这些客死亡魂顺利进入冥间,而勿流连人间之意。再者,在传统落叶归根的观念下,多盼异乡亡魂能回归故土,但台湾与内地有一海之隔,其渡海返乡亦须倚赖城隍神相助。道光八年(1828)台湾知府邓传安祭祀海难孤魂时,即有《牒台湾府城隍文》曰:“顾故土之思,人鬼同情……仰惟威灵公爵秩尊显,如一路之福星。海岛商民内渡,必官给照乃行;想幽明事同一体,为此牒呈神鉴。伏冀俯念无主游魂,陷于险远,思归不得,默赐引导,护还故乡,得享族类烟祀。”[44]清代商民渡海来台,须经官府核准给照;而今孤魂渡海回归故土,亦须经冥界行政官城隍神的同意与引导。因此,福海在城隍庙旁建英灵堂,亦有请该神护送客死亡魂返回故里,接受家族香火祭祀之意。
除照顾外江人士后事的英灵堂外,嘉义县城隍庙左边尚有一间由绅商所捐建的育婴堂,关怀对象则是本地贫民所无力抚养的女婴。《台湾私法物权编》有载:
从前嘉义四方贫民者多,而养育时家贫,生产女儿不舍抚养,由小儿自己抱埋。当时众绅商人等目击心伤,邑绅出为劝捐置业,大举行善,建设公堂一所,在本城隍庙左边,名曰育婴堂。告示达知四方贫民,如遇生产无力抚养者,抱送来堂,由堂管事转倩乳媪代养至十六岁。查贫民家无力娶妻,将婴女许配,或三、四岁,五、六岁,该乳媪自要为女为媳,先行通知管事,查实妥人许之。嘉庆初设起,历至道光、咸丰。于同治年间,因损款不敷费用,蒙嘉义城内绅士陈熙年出首重振,禀官再兴,加捐置业,有千余租,为永远义举者。[45]
传统社会贫民生育子女,常因无力抚养而有溺婴与弃婴的行为,且在父权制度下多为女婴受害。宋元的法律明文禁止溺杀婴儿,明清法律虽对此不甚明确,但地方官均不时谴责此一习俗。育婴堂即在解救这些可能遭溺杀的婴儿,同时也宣扬好生之德的理念,发挥宗教性净化的作用。而清初的育婴堂明显带有完美主义,又具有社会道德示范作用,[46]故为雍正皇帝大加赞赏,而谕令各地官员广为劝募设立。嘉义绅商选择在城隍庙旁建育婴堂,当亦考虑该庙为宗教与道德教化的空间,且此举符合朝廷的慈善政策,亦能获地方官员的支持。
这间育婴堂与内地一般,除代养贫民的女婴外,也关怀其长大后的出路,而订有嫁人与收养之规定。此外,清初育婴堂采集中弃婴与乳妇于一堂的方式,但由于花费过大、管理困难,嘉庆以后渐转为补助本妇自乳的保婴会;从该堂的经费中有“乳媪每月每名一元”“自养每月乳媪六十钱”两项来看,[47]当是采乳妇代养与本妇自乳并行。不同于英灵堂是由安徽籍的僧官福海为外江人士所募建,育婴堂则是由嘉义绅商所捐建,所照顾者亦为该县贫民的女婴,本地色彩甚为明显。又从其创建于嘉庆年间,多少可看出清代中叶台湾士绅阶层已在公共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同治年间捐资重振该堂的陈熙年,正是在戴潮春事件中带领百姓保家卫国,并积极争取赐封城隍神的关键人物,亦可见清末士绅的力量已不再局限于地方,而扩及国家层次的事务。
四、结语
本文透过文献史料与碑匾文物之分析,探讨清代嘉义县城隍庙的经费、赐封及有关善堂。研究发现清代城隍庙的经费大多无法从公帑支应,创建与兴修多由官员捐俸或向地方人士募捐而来,例行支出则赖民间所献的庙产租银,地方官亦会利用职权来开辟财源。嘉义县城隍庙的创建来自官员捐俸,但后来的修建则有士绅捐助,甚至由其主导。另当地官员为筹措该庙营运费用,也利用任命番通事的职权,与汉人副通事串通怂恿番人捐献山林作为香灯租;这种作法亦见于其他城隍庙,虽可解决其经费问题,但也造成番地的流失。
清末由于面临内忧外患,各地城隍屡有护国佑民的神迹,朝廷也藉由赐封来安定民心、兴复王权。同治年间台湾发生戴潮春事件,嘉义、淡水、大甲城隍皆有显灵事迹,尤其嘉义县城隍神不仅在地震中保护城垣无恙,且以签诗凝聚绅民守城抗敌的意志,终能化解危机。在地方士绅锲而不舍的争取下,加上各级官员的配合与国家政策的支持,终获光绪皇帝赐予“绥靖”封号。此外,该庙尚因显灵降雨的神迹,而获颁“台洋显佑”匾额。虽然地方对这些赐封有不同认知,但都无损其正统性,迄今仍是庙方最为重视的文化资源。
城隍庙由于是城市中规模宏伟的祭祀空间,又是官员辅助施政与教化的场所,故也与从事慈善救济的善堂有所连结。清代嘉义县城隍庙左侧即设立有英灵堂与育婴堂,英灵堂由安徽籍僧官兼该庙住持福海募建,主要在解决内地来台的游幕士官、商民及跟官人等的后事问题,捐款者亦皆为外江人士。福海选择在城隍庙旁建英灵堂,亦有考虑该庙是这些幕友与家丁的信仰及活动空间,且该神亦能引导其亡魂渡海返回故里。育婴堂则是本地绅商所建,所照顾者亦为当地贫民无力抚养的女婴,建在该庙旁有宗教性与教化性的考虑,且亦有地方官的支持。
总之,就整个大清帝国来看,嘉义县城隍庙虽微不足道,但却清楚呈现城隍神作为冥界行政官的形象、护佑城池与降雨解旱的职能、国家象征与团结民心的作用、显灵与赐封的方式,及城隍祭祀制度在地方运作的实况,也提供观察台湾社会中的绅权扩张、官民互动、番地流失、外江人士与慈善组织等视角,仍是深具价值。
注释:
[1][日]滨岛敦俊著:《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4~129页。
[2]巫仁恕:《节庆、信仰与抗争——明清城隍信仰与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行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0年第34期,第145~210页。
[3][38]王健:《官民共享空间的形成:明清江南的城隍庙与城市社会》,《史学月刊》2011年第7期。
[4]柯培元:《噶玛兰志略》,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第59~60页。
[5]王必昌编纂:《重修台湾县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第129页。
[6]周钟瑄纂辑:《诸罗县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第64页。
[7][12]岁有生:《清代州县的祭祀经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
[8]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新竹县制度考》,台北:编者,1961年,第107~108页。
[9]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新竹县制度考》,第29页、第106~107页。
[10]余文仪纂辑:《续修台湾府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第98页。
[11]蔡东洲、张亮以:《晚清地方州县武庙的经费收支问题——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的考察》,《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3][14]吴育臻:《清代嘉义沿山地区阿里山社番租流失——以通事角色为中心》,《白沙历史地理学报》2017年第18期。
[15]戴炎辉:《香灯租——关于支分所有权、物的负担之若干考察》,载《人文科学论丛》,台北:台湾光复文化财团,1949年,第23~29页。
[16]有关宋代的赐封制度及其在地方社会的运作,可参看松元浩一:《宋代の赐额、赐号について——主として《宋会要辑稿》にみえて史料から》,野口铁郎编:《中国史中央政治地方社会》1985 年度科研费报告,1986 年。韩森(Valerie Hansen)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17]赵与时:《宾退录》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点校本,第103页。
[18]张传勇:《明清城隍封爵考》,《史林》2017年第5期。
[19][20]吴德功:《戴施两案纪略》,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第1页,第11页。
[21][22]林豪:《东瀛纪事》,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年,第16~18页,第54页。
[23]庄德仁:《显灵:清代灵异文化之研究——以档案资料为中心》,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4年,第34~89页。
[24][43]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著,孙琢译:《城隍庙中变化的权力平衡(1800~1937)》,吕敏、陆康编:《香火新缘: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寺庙与市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49~50页,第36~38页。
[25]沈葆桢:《福建台湾奏折》,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第19页。
[26]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台北:编者,1968年,第502页。
[27]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清德宗实录选辑》,台北:编者,1964年,第2页。
[28]李百药:《北齐书》卷20,台北:艺文印书馆,1956年,第134~135页。
[29]吴兆熙等:《光绪善化县志》卷33,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702页。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三辑,台北:编者,1973年,第157~158页。
[30]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诗钞》,台北:编者,1970年,第102页。
[31]庞毅:《城隍如何守城:善城隍与晚清湖南地方政治》,《史林》2017年第2期。
[32]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清德宗实录选辑》,台北:编者,1964年,第221页。
[33]徐致祥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年复印本,第15564~15565页。
[34]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福建通志台湾府》,台北:编者,1960年,第231页。
[35]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清会典台湾事例》,台北:编者,1966年,第102页。
[36]王吉清等编:《嘉邑城隍庙附设慈善会22周年特刊》,嘉义:嘉义市城隍庙附设慈善会,2003 年,第71页,第109页。
[37][39][46]有关传统善堂的发展历程,详见梁其姿:《慈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
[40]谢金銮、郑兼才合纂:《续修台湾县志》,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第91页。
[41]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697~700页。
[42]昆冈等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依光绪二十五年刊本,1976年,第378页。
[44]丁曰健编:《治台必告录》,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第122页。
[45][47]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私法物权编》,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第1477页,第1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