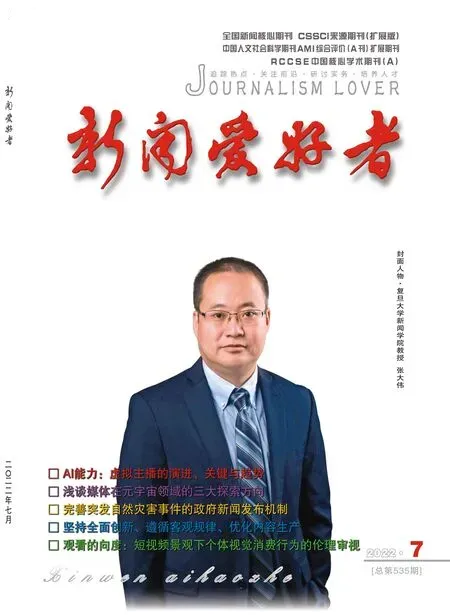红色民歌的传播路径研究
——以鄂豫皖革命民歌《八月桂花遍地开》为例
□朱全稳
《八月桂花遍地开》(以下简称《桂花》)是中国革命历程中较为典型的音乐文本,它以红军和人民群众为传播对象,成为政治认同和情感动员的中介音乐。作为媒介的红色民歌从革命时期传播至今,其音乐叙事及其表现形式的流变暗含着其宣传角色的改变。作为红色民歌代表,《桂花》 等典型红色民歌是传递思想、记录事实、鼓舞人心的媒介形式,是一种传递思想的“装置”,那么这一“装置”是如何诞生、改写与传递的? 其传递的形式及特征是怎样的? 本研究并非简单的历史脉络梳理,而是试图以《桂花》为个案思考红色民歌的叙事变迁及其在政治宣传中的中介作用,这也是对政治传播与音乐媒介关系的积极探索。
一、“相遇”革命:与群众沟通的媒介首次登场
《桂花》 的登场源于一次重要的革命事件——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①通过考察其诞生的经过可以发现,这首民歌的曲调由传统民歌《八段锦》的曲调变体而来,其歌词为叙述革命事件而专门创作,并经由当地民众的传唱而作为政治媒介首次登场。
民歌是民众记录生活、表达情感的工具,以生活叙事为主,革命民歌选取传唱度较高,比较有特点且利于传播的民间歌曲,为革命时期的政治宣传和动员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理想的“传递装置”;同时,在民间曲调的借用过程中由生活叙事转向了革命叙事。
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当中,口头传播是音乐传播最主要的方式,即使在文字出现后,口头传播依然是音乐传播的重要路径。民歌在最初的传播过程中主要是民间的自发传播,其传播主体及受众主体是普通大众及流浪艺人,革命歌曲的传播也契合这样的传播规律。据《解放军报》刊载的文章《桂花》所记载,“由于这支歌子的曲调大家熟悉,又是采用当地民歌的唱法,歌词也简单,人们一听就会。会上唱完了,会后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也就学会了”。[1]
熟悉的曲调、简单的歌词,大大降低了歌曲的传播门槛。当时民众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具备印刷文本的生产与传递条件,这首民歌无疑是记录和传播革命事件效果的最佳方式。“传递”是一种积累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接力,而是需要再思考、再描述、再转化[2],正是由于歌词的替换,《八段锦》与《桂花》之间媒介逻辑发生了置换,完成了日常生活到革命话语的政治化、情感化转变,作为与群众沟通的媒介首次登场,并通过口语方式进行传播,这也成为此时政治宣传的重要方式。此曲经传播后,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各个革命区域的观摩代表纷纷记录传抄,把它带回自己干革命的地方,进而鼓舞群众、团结群众,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
二、军旅传唱:以政治动员为目的的组织传播
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举办以后,《桂花》逐渐传唱开来,并且以书本、口语传唱为传播方式,以军队的组织为控制力量,经由红军的足迹,向全国多地传播。1931年夏,原红三十二师副师长漆德伟等人,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调到中央根据地工作,这支歌就由他们带到了中央根据地并迅速流传。其例证在文献资料对该作品归属论证中多有体现:在《中国传统民歌400 首》(柳正明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南卷》(河南编辑委员会,中国ISBN 中心,1987年)中,编者将之认定为河南新县民歌;《中国民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将之认定为安徽金寨民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歌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则将其标注为“江西民歌,焕之曲”;《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全国编辑委员会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将它作为湖北民歌(鄂东北红安县);1932年12月,这支歌又随红四方面军来到四川②。《桂花》这首歌就这样伴随着红军的足迹,不断扩大影响范围。
“政治动员作为政党政治传播的主要功能之一,需要有其适切的宣传工具和传播媒介。”[3]《桂花》是红四方面军在征兵动员期间唱得非常响亮的革命歌曲,也是部队征兵时的有力动员载体[4]。德布雷提出“传递”涉及三个系统:由不同外观符号所构成的象征形式;不同地域、民族、性别、阶级的人群的集体组织;以技术制式作为区分的各种传播技术系统。[5]曲调、歌词作为歌曲的组成元素构成了传递系统象征形式,以各类传播技术搭建的传播渠道建构了各类传播技术系统(如口语传播、大众传播),以征兵为中心的制度化安排即是传递系统中的集体组织,与其技术系统、象征形式一起形成了《桂花》的传递系统,将其从地方传播至全国,大大延续了这首歌曲的生命力。直到全国解放后,征兵期间很多征兵站还在用录音机播放这支红军时期的革命歌曲。[6]
征兵动员时传唱的歌词“红军队伍真威风,百战百胜最英勇……一杆红旗飘在空中,红军队伍要扩充”,突出了革命的动员和鼓舞的词汇,起到了传播革命意识形态、宣教以及娱乐的功能。这支革命歌曲的魅力、影响力和感染力难以用语言表述,它已然成了人民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洪学智上将曾经这样评价这支歌,“战争年代,这支歌就好像是战斗的动员令”。徐光友、徐兴华和史群英等许多红军老战士在谈到自己革命经历的时候,也提到他们忘不掉的就是唱《桂花》,认为这支红军歌曲给他们带来革命斗志和力量[7],这也成为电视剧《桂花》《上将洪学智》中的经典画面。
经过改造后的《桂花》在征兵以及战场上组织化的宣传动员,成为红军坚定理想信念、凝聚共识的中介,与延安的新秧歌剧类似,成功实现了“抽象思想”向“物质力量”的转化,即一个观念通过《桂花》这样一首歌曲转化为了革命胜利的物质性力量,为革命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集体记忆: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再造
集体记忆理论的开创者哈布瓦赫认为 “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8]他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雕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群体共享的东西”。[9]
经历了诞生之初的口语传播、军旅传唱的组织传播后,《桂花》在新中国成立后迈入大众传播阶段。经由大众媒介进行的传承,主要包括音乐书籍、舞台表演、电视剧、纪录片等多种方式,这首歌的功能已经从实用的动员转向了记忆建构的象征符号。
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家充分调动文艺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民歌收集整理工作以及后续对民歌的整理编撰工作等,对民歌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红色歌谣《桂花》在这一阶段的民歌搜集采编过程中一如其歌名遍地开花(上文为体现该作品的广泛传播所列例证可见一斑)。除官方收录外,专业化、艺术化的传播方式,延续抑或再造了其革命叙事,这种“国家在场”的媒介传播无疑推动了红色歌谣的经典化、大众化。如,2007年7月,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 周年,《桂花》 被改编为民歌剧并在第八届安徽省艺术节戏剧调演上演出。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第一篇章中该曲出现,并被首次认定为鄂豫皖革命民歌,成为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标识”……
戏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等艺术形式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持续“传播”着这首民歌。这一时期,《桂花》的传播主体由军队传播向专业文艺工作者转变,专业文艺工作者既是传播主体,也是创作主体,出现了歌剧、舞剧、文学作品等专业化、艺术化传播方式,而普通大众由最初的传播者转换为受众。
除国家在场的精神传承与再造外,以该音乐为题的电影、书籍、电视剧、纪录片也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桂花》逐渐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革命年代的符号象征。如,2006年,河南影视制作集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 周年推出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桂花》,讲述了主人公王霁初爱戏、唱戏、收集民歌、创作革命歌曲、参加战场演出、最后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故事,《桂花》的音乐贯穿全剧,推动剧情发展;河南省首部大型原创民族歌剧《八月桂花开》也是以红色歌谣《桂花》为特性音乐编创,选取了淮河文化、楚文化等豫南特色的音乐元素,第一次将信阳民歌与西方交响音乐融为一体,艺术化地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大别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红色历程;由湖北省演艺集团、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民族歌剧《桂花》也将该民歌作为特征音乐使用,延续了民歌的革命叙事,体现了音乐戏剧化的创作思路。
四、文化符号:集体庆典的符号象征与意义建构
“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10]共同记忆的唤起催生了仪式与仪式化符号的创造,而国家对于一个集体的文化认同、共同记忆的唤起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新生政权而言,一系列的国家仪式与仪式化的国家象征符号,对于国家认同的凝聚与建构、国家信仰的确立与强化、国家记忆的塑造与延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价值。[11]2021年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官方和民间以不同的形式围绕建党百年的话题策划制作了大量的内容,种种媒介实践可被看作是一次“集体庆典”,以仪式性内容强化公众对于革命年代的集体记忆。《桂花》在国家主导的官方话语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集体回忆的文化符号,并且被赋予了新的符号象征和意义。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音乐专辑《百年》推出百首建党百年经典歌曲。其中,年轻演员周雨彤演唱了民歌《桂花》,以歌曲的方式将党史讲给年轻人听,以旋律为中介建构起年轻人的集体记忆。2021年1月,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纪录片《桂花》,该片以安徽金寨县59 位开国将军为主体人物,用人的故事讲党的道理,为今天的年轻观众打造了一部有声有色的纪录片式“思政课”。其中,在纪录片《桂花》 第二集的第12 分钟,主人公就唱起了这首《桂花》,饱含对过往历史的追忆。
从歌曲本身到由歌曲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这首作品从插曲逐渐演变为一段历史的象征,成为一个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2021年的“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 将关键历史节点串联成宏大历史叙事,这种回顾更是一种国家共同记忆的激活和唤醒,是国家认同的再次强化。在这次“集体庆典”中,《桂花》再次成为创作元素,并首次在国家舞台被认定为鄂豫皖革命民歌,相较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伟大征程》赋予了歌曲新的内涵。音乐与情景表演的结合在舞台声光电的烘托下,革命火种的燎原之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蓬勃景象。歌词文本中删除地方属性,将范围扩展到鄂豫皖,将鄂豫皖的集体记忆上升到了党的集体记忆,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在这类国家重大庆典仪式活动中,《桂花》 的歌词版本及其文化政治意义随着时代主题与政治需求的更迭发生变动,其所凝结的国家记忆也随之受到改写与重构。这种重构使用了象征手法,以意象化的表达体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疑赋予了作品新的内涵和意义。
五、结语
通过对《桂花》的媒介学考察,可以发现其在不同时代的叙事变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是在传播上,早期的传播过程中的改写和流变是无意识的自然变迁,传播方式为口语传播;而在革命传播中,这种改编改写甚至重构则出于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理性思考,旨在满足政治宣传诉求和艺术表现需要,以征兵及战争中的组织传播为主要传播方式。在“国家在场”的背景下,专业化文艺作品通过传播延续了红色歌谣的革命叙事。二是在传播过程中音乐的呈现形式上,表演场所从田野等相对自由开阔的随性演唱向仪式性、专业性的舞台呈现转变;音乐本身则体现出了从单旋律的民歌自由演唱—集体性的群众歌咏—舞台化的人声与器乐综合—音、歌、舞、声、光、电等现代化综合性艺术呈现的时代性变迁。三是《桂花》的传播过程经历了民歌原叙事(生活、生产反映)—革命历史叙事(革命斗争需要)—国家宏大叙事建构及革命叙事延续(情景再现、国家认同)的叙事变迁。经过不断地改编和传唱,这一典型革命民歌经历了跨时代、跨地域传播并成为革命象征符号,成为被大众媒介传播的文本,这样的传播路径也为研究红色民歌的传播与传承提供了一定参考。
注 释:
①学界对该作品源于何政治事件多有论述,综各家之言,以及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庆典晚会《伟大征程》中首次对其“鄂豫皖革命民歌”的定性,在没有新的史料情况下,定位其源于庆祝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有一定的说服力。
②四川有关此歌的最早记载是四川旺仓史家的史群英在《八月的桂花》一文中回忆了当时她第一次听到女红军战士唱起了《八月桂花遍地开》,原文刊于《星火燎原》(季刊)1982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