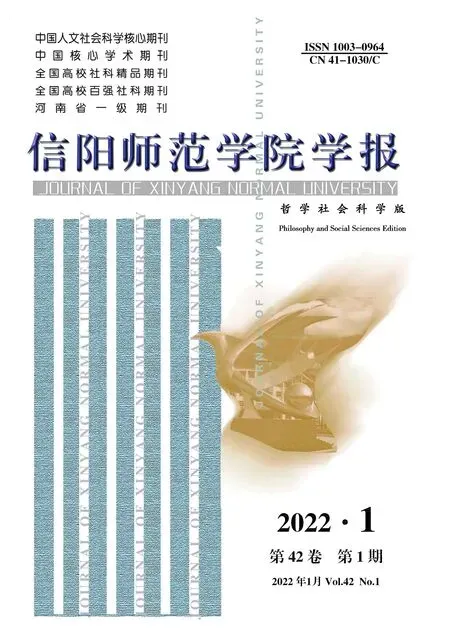功百侯公 纳策鸿沟:以《项羽本纪》“侯公”事管窥刘邦与项羽
曲景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中文系,新加坡 639818)
《史记》中有所谓“累积型”人物与“闪现型”人物。秦汉之际的侯公,无疑属于后者。关于侯公,历史上的叙述与评论甚少。秦汉之际有两位侯公:一为秦朝方士①,一为楚汉之际著名的辩士。二者皆如流星一般,一闪而过,就连其具体何名,亦难详考。
司马迁以项羽为本纪入汉的第一篇文章,列于汉诸帝之前,无所顾忌,以显示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理念,这也是太史公一生立言追求所在。前人关于楚汉相争的论述颇多,对刘邦、项羽二人的比较也众说纷纭,本文拟以《史记·项羽本纪》所载“侯公”事管窥楚汉之际的历史风云。
一、司马迁笔下的“侯公”:《项羽本纪》“侯公”事句解
侯公的鸿沟议和之功,划定楚河汉界,堪比先秦苏秦、张仪,秦汉郦生(食其)、陆贾,不遑多让。然而,关于侯公的生平事迹的记述,只有《史记·项羽本纪》一段:
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见。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1]416
按理说,侯公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项羽与刘邦达成和解条约,并且将刘邦的父母妻子解救回来,这是莫大的功勋。西晋陆机在《汉高祖功臣颂》中将侯公列为刘邦的开国功臣之一,并评曰:“侯公伏轼,皇媪来归。是谓平国,宠命有辉。”[2]109宋代史家周紫芝曾将侯公与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并称,“使子房为谋臣,侯公为辩士,犹未足以决胜负而定安危也”[3]卷一二四。两则评论均指侯公说服项羽,使归刘邦家眷之功。刘邦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也因此而能最后夺取天下,手下著名的文臣武将不论,观其对辕生、董公、陈恢、随何、武涉等一众“次要”谋士的纳谏亦可见一斑[4]2-8。但在对侯公的处理上,却颇令人不解。本文尝试对这段文字逐一句解,同时,借助西方接受美学的“文本的召唤结构”理论,对这段文本中存在的空白、空缺和否定性疑问进行分析②,并在此基础上解读刘邦与项羽在楚汉之争中的性格特征。
(1)“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是时”,乃汉之四年(前203)八月,楚汉之争已在不知不觉中客主易位,此消彼长,形势发生了转化,由楚强汉弱变为楚弱汉强(客观地说,彭越在后方作乱、韩信破齐自立,均使得楚国腹背受敌)。这里的“兵盛食多”与“兵罢食绝”形成鲜明对比。项羽何以落到“兵罢食绝”的境地?试详细分解之。
“兵罢”,指项羽自起兵之日(前209)至今(前203)已6年,长年征战,士兵疲惫,颇“苦军旅”。这实际上是双方共同面临的问题,只不过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食绝”,很有讽刺意味,曾经的项羽锐不可当,深谙“甬道”(运输粮食的通道)的重要性,在巨鹿破釜沉舟,绝秦军甬道,大破秦军主力,一战成名,勇冠诸侯;汉初三年(前202),项羽取得彭城大捷之后,数次侵夺刘邦的甬道于荥阳,迫使刘邦请和。但在楚汉相争的最后一年(前202),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因粮食问题为汉军所困。此前一年(前203)刘邦即“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③,这次在广武又再次陷入同样的粮食困境,被彭越“绝楚粮食”。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司马迁用同样的句子两次形容项羽的这种窘境:“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楚兵,绝其粮食。”[1]469、472耐人寻味,最后项羽在垓下因兵少食尽而败亡。
(2)“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在这个危急时刻,刘邦派去劝说项羽的第一人是陆贾,不是侯公。
陆贾(前240-前170),汉初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他有口才,善辩论,司马迁将之与郦食其合于一处列传。他早年即追随刘邦,因能言善辩常出使诸侯,刘邦安定天下后,陆贾曾向刘邦谏言:“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5]396著文12篇,总结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刘邦无不称善,名其书为《新语》。
陆贾本是楚人,或许其与项羽的同乡之谊也是刘邦派遣他的原因之一,但能言善辩的陆贾并没有说服项羽放回太公,这是为什么?他当时向项羽开出的议和条件是什么?这些是司马迁没有交代的文本空缺。
(3)“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鸿沟,在荥阳(属今郑州)成皋一带,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至今,荥阳广武山有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两城中间有一条宽约800米,深达200米的大沟,即鸿沟。鸿沟划界,奇功一桩。自古以长江限南北,鸿沟判东西,侯公说项羽与刘邦中分天下,对中国地理的界限是有卓越贡献的。
这一句的标点值得商榷,“往说项王”之后的“项王乃与汉约”之间,是否应为“句号”?说服需要一个过程,后来的约定是谈判的结果,中间应以“句号”区隔以示这个过程。相应地,“项王乃与汉约”这句之后,是约定的内容,所以用“冒号”更为适宜。
读至此处,读者不禁存有几个疑问:刘邦再次派侯公去项羽军前,有过怎样的谈话?性暴气刚的项羽是如何在陆贾劝说不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次被侯公说服?双方为达成合约有没有暗中的条件?难道此前陆贾第一次去,仅仅愚蠢地要求项羽归还太公,而没有什么相应的对项羽的允诺?可惜,司马迁对这些文本空白只字未提。
后世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依据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文心绣笔曾尝试补白。比如,宋代文豪苏轼以小说笔法记叙的《代侯公说项羽辞》;明代万历间的甄伟据以敷衍为小说《指鸿沟割地讲和》④;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有《设侯公说项羽书》一文⑤。这些对侯公故事的敷衍构成了一个虚拟的“侯公”,可以与本文的解读相得益彰。限于篇幅,将另文申论。
(4)“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此处文本跳过说服的过程与内幕,直接说出了结果:侯公成功说服项羽,即刻归还了被他扣在军中为人质已长达28个月的“汉王父母妻子”,军士都高呼万岁。
这里的人质——“父母妻子”何解,是有争议的。《史记·项羽本纪》前文已有交待,两年前(前205),项羽与刘邦战于睢水(又名濉河,在今河南),汉军大败,刘邦的家属为楚军所俘:“(刘邦)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因此,刘邦的父亲太公和妻子吕后是人质无疑。梁玉绳据《秦楚之际月表》和《王陵传》皆称“太公、吕后”,所以此处亦应如是。但是,《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高祖本纪》皆称“父母妻子”,陆机《汉高祖功臣颂》称“侯公伏轼,皇媪来归”,明言人质中有刘邦之母⑥。
事实上,刘邦应该有子在项羽军中为质,此虽无直接的文献证据,但在《史记会注考证》中有一段考证颇可卒读:“高祖母虽已前死,而楚元王为高祖异母子,则高祖尚有庶母也,孝惠尚有庶兄肥,后封齐为悼惠王。高祖道遇孝惠,与孝惠偕行者,但有鲁元公主,则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别无投归高祖之事,则必与太公吕后为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项军也。则《史记》所谓‘父母妻子’,乃无一字虚说,而《汉书》改云太公吕后转疏漏也。”[6]48
值得玩味的是,刘邦第一次派陆贾说项羽,只请“太公”,而第二次派侯公说项羽,却迎回了“父母妻子”,“太公”应不是“父母妻子”的简语,那中间的差别作何理解?
(5)“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见”。刘邦“乃封侯公为平国君”之后的话,颇令人费解。上下文不连贯,或有文本空缺⑦。“匿弗肯复见”是说侯公“匿”, 还是刘邦“匿”,甚或是侯公“被匿”?可以有多重解读。
第一,《史记正义》此处引《楚汉春秋》作注:“上欲封之,乃肯见。曰:‘此天下之辨(辩)士,所居倾国,故号平国君。’”[1]415如是,则是刘邦想要封侯公,侯公才肯出来复见刘邦。所引《楚汉春秋》的文字在别处更为明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复见。曰:‘此天下之辨(辩)士,所居倾国,故号平国君。’”这是说侯公立功之后“匿”,不复见刘邦,刘邦才有“平国君”之语。并且“平国君”的封号并未出现在“匿弗肯复见”之前。
第二,前人认为此句是司马迁引用陆贾《楚汉春秋》的佐证。但是,从不同版本的《楚汉春秋》引文的异文来看,文意截然不同:一是侯公因刘邦要赏封,才见了刘邦;一是侯公藏起来,不肯再见刘邦。到底侯公有没有复见刘邦,仍然存疑。
第三,此句的“匿”与“弗肯复见”之间,或许应该有停顿或标点。王叔岷《史记校证》云:“上文‘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犹言‘汉王将封侯公为平国君。’因侯公‘匿,弗肯复见。’无从封之,故仅‘号曰平国君’也。”[6]284想封侯公为“平国君”而无法复见,所以只是给了他一个“平国君”的封号。
第四,有无可能是刘邦将侯公“匿”,或者刘邦让侯公“匿”,刘邦不愿再看到侯公呢?这又是为什么?对此,下文有解释。
(6)“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关于“平国君”这个封号本身及这个封号的意义,颇令人寻味。《史记会注考证》云:“按:说归太公、吕后,能和平郡国。”[7]65《汉书·高帝纪》载颜师古对“平国”的解释:“以其善说,能平和邦国。”[8]47“和平郡国”“平和邦国”都应该是表面上的奖励之意,真正的意思乃由刘邦自己道出,这样的辩士,使用起来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倾国”乃倾覆国家之意,这种辩士所居的国家都有倾覆的危险,所以刘邦不愿再见此人(“弗肯复见”)。日本学者中井积德认为:“故号为平国君,取其反称也。”[7]65“反称”如果是说从反面称呼,那么“平国”恰恰是不能使国家和平、平和。事实上,这句话在其他文献中也有不同的记载,意义也有别:“汉王乃封公为平国君,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号为平国。”[9]卷四六三刘邦称侯公为“天下辩士”,或者是寓贬于褒。
另外,清人梁玉绳引《金石录》中欧阳修《金乡守长侯君碑》云:“汉之兴也,侯公纳策,济太上皇于鸿沟之厄,谥曰安国。”这里说侯公的谥号为“安国”。宋人赵明诚就此提出了疑问:“高祖纪侯公封平国君,此碑言安国既不同,而平国君乃生时称号,如娄敬为奉春君之类(按:娄敬因建议刘邦迁都关中有功,赐姓刘,号“奉春君”),碑以为谥,恐非。余疑‘谥’当作‘号’。”并认为,“谥者号也,不作谥法解”[10]210。他并在《史记·孟尝君列传》的“志疑”中对此类现象举数个例证[10]1277-1278。然则,“安国”与“平国”又有何分别?在后世人眼中,侯公解了刘邦“鸿沟之厄”,汉之所以兴,刘邦之所以平天下,侯公厥功甚伟,所以有“安国”之美誉,比起“平国”之封号更为显赫。
二、以“侯公”事管窥刘邦与项羽:从侯公结局的臆测谈起
关于侯公的故事仅限于《史记·项羽本纪》所载的寥寥百余字。像这样闪现式的风云人物,读者不禁会有这样的追问:侯公的结局是怎样?历史未有明载,留下文本空白。而刘邦和项羽对于侯公的鸿沟和议如何想?这当中体现了二人怎样的性格特征?本文尝试作如下解读。
首先,让我们回到两位辩士的比较上来。为何陆贾第一次没有说服项羽,侯公再去却能说服,在谈判过程中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样的结局是否会引起刘邦的猜疑?同为说客、辩士,一向能言善辩的陆贾失败,而侯公却能成功。“事光陆贾,功百侯公”[11]卷九一七。陆贾的无功与侯公的大功形成强烈的对比,甚至后人在述及鸿沟之议时,根本不谈陆贾,只谈侯公。然而,一则失败,一则成功,成功者侯公从此在历史的视野中消失,而失败者陆贾却一直为刘邦所重用,这难道不让世人起疑吗?什么才是刘邦的帝王心?侯公似乎仅仅作为刘邦的政治工具,目的一旦达成,便弃之不用,这显示出其为人的狠心。有人或许会说刘邦的所有过往丑事都被侯公知晓,所以不愿再重用他。笔者认为没有这样,也并非如此。史书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侯公的最终结局,但可以约略推见,他被刘邦“匿”或者自己隐“匿”之后,即没有什么作为了。
进一步说,笔者想着重分析的是,侯公成功说服项羽,或许并非是刘邦的心意。这首先可由《史记·项羽本纪》在楚汉达成约定后的文字中窥见:
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1]415-416
项羽如约解兵,刘邦则负约,继续向项羽进兵。次年即公元前202年,垓下之围,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回到鸿沟议和的当下,张良、陈平所说的“太半”具体指什么?据韦昭的解释:“凡数三分有二为太半,一为少半。”[1]416手握天下三分之二的刘邦,此时心里或许并不在意是否能够将“父母妻子”赎回,他从来不是一个对家人有孝心、爱心的人,这在《史记·项羽本纪》及其他传记中都有记载。在他心目中,统一天下的雄心和成为天下帝王的决心绝对胜于家庭的安宁与和睦。“中分天下”绝不是他的目标,他要的是天下,是彻底地打败项羽。在汉强楚弱的情况下,刘邦是并不想达成和约的。南宋人杨造《乞罢和议劄子》曾这样引述“侯公”事:
昔汉太上皇、吕后为项王所得,置俎上欲烹之。夫高帝岂恝然亡之哉?而未尝为之屈,盖势不可尔。然项王卒不敢加害。盖以高祖之□,害之无益,而存之则可以为重资,故割鸿沟之后,卒从侯公之言而归之。今国家若能励兵秣马,稍振中国之威,且勿与之通,则彼莫能测其虚实,必不敢动。吾已复中原,然后遣辨(辩)士若侯公者,往说焉,彼亦且奉二圣以来归矣。故二圣虽在彼,于中国用兵之势无有害也。[3]卷一六八
杨造的文章对刘邦的行为多所回护,不言自明。然而,从以上文字中仍然透露出政治角力过程中的残酷与虚伪。此段“高祖之”后有缺字,也许即是“狠”字。项羽与刘邦争霸天下多年,最了解自己的对手,项羽很了解刘邦的性格以及狠辣,他绝不会因为父母妻儿已为人质,受要挟而束手,或如杨造笔下“势不可尔”。项羽在公元前205年已经试过一次: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1]412
作为一代政治枭雄,刘邦从不因私情而受胁迫;作为人子人夫人父,刘邦殊少人情。观其彭城败后,楚骑追急,连续三次“推墮孝惠、鲁元车下”的惊人举动,此处“幸分我一杯羹”的雷人之语,置人伦父子亲情不顾,为后世所不耻。唯务得天下,此刘邦之所以为刘邦,《史记·项羽本纪》乃刘邦品性的绝佳记录。
相反,项羽在与刘邦对峙的过程中,却数次犯下“封建”贵族软弱病。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仁义之人,他曾屠杀降卒,曾焚宫屠城,曾烹杀说者,弑杀成性,残暴不仁。所可恃者,能战也,“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自矜功伐”而卒由战败。司马迁详细记述了项羽对刘邦及其家人一次次的妇人之仁,极尽画态:鸿门宴如此,烹太公如此,鸿沟议和亦复如此。杨造文中称项羽“卒不敢加害”于太公、吕后,故然有留之作为人质牌的考量,诚如杨造所言,于“用兵之势无有害”,但其实这再次暴露了项羽的贵族软弱病,或者说他还有作为人的基本底线,所以会姑息与优柔。后人对于项羽当初在鸿门宴上不听范增之言而杀刘邦有所回护:“项梁不肯听田荣以杀田假,项羽不肯听范增以杀沛公,皆有大度,勿以成败论英雄也。”[12]24对项羽与刘邦的关系也有这样的解读:“项羽之待汉王,犹夫差之待勾践,夫差之仇怨也恕,勾践之仇怨也酷,项羽之负约也小,汉王之负约也大。”[13]60-61“大度”也好,“负约”也罢,但终究项羽败、刘邦胜,诚如后人所评论:“项王非特暴虐,人心不归,亦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志迹,其既灭咸阳而都彭城,既复彭城而割荥阳,既割鸿沟而思东归,殊欲按甲休兵,宛然图伯筹画耳。岂知高祖规模宏远,天下不归于一不止哉!”[13]61项羽一次次贪图荣归故里,时念“东归”,不知深谋远虑,“无统一天下之志”,错失良机,比起刘邦来说,确实气局志向有差。“不止”二字,道出刘邦不达一统天下的目的,绝不罢休。
最终,谈判劣势方项羽释放“人质”与刘邦达成和议,这本是基于对等原则的谈判结果,如果双方都是有身份的贵族,或许会遵守协议,但刘邦不是贵族,他是地痞流氓,没有道德束缚,成王败寇是其基本价值观,只要成功,只要胜利,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北宋王禹偁有《过鸿沟》诗云:“侯公缓颊太公归,项籍何曾会战机。只见源沟分两处,不知垓下有重围。”诗中讥讽项羽何曾了解战机,鸿沟之议看似楚河汉界,中分天下,从此“按甲休兵”,但失去了最后的“重资”的项羽随即遭到刘邦的继续围剿,遂有垓下之败。刘邦用侯公将父母妻子迎回(“缓颊”的功效),进而完成了对项羽的决胜,正所谓成者为王败者寇,楚汉之争就此落幕。
注释:
①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此侯公,亦称侯生,韩国人,在秦为客卿。侯生曾与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修订本《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19、324-325页)两人于是逃亡。秦始皇以为厚待诸生的后果是诸生反过来诽谤自己,所以命令告发诽谤皇帝的博士诸生,被告发的士人全部被坑杀,此即“坑儒”。据《说苑》附会,侯生后来被捕,秦始皇与他当面对质。要将他车裂,问他有何面目来见自己背叛的皇帝。侯生指出秦始皇奢靡无度,将要败亡。秦始皇默然良久,问他为什么不早说。侯生说皇帝自负,自己不敢言而逃亡,现在必死,才敢进谏。始皇最终没有杀他。
② “文本的召唤结构”(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 of text)是德国文学批评家、接受美学创始人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 1926-2007)在1969年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接受美学概念,其中包括三个要素:空白(blank)、空缺(vacancy)和否定性(negation)。这个理论后来在氏著《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originally in German in 1976) 中得到详细阐释,他认为文本(text)在产生后会形成“一个召唤结构网”(a network of 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s), 驱使读者参与文本的解读。情节线索的突然中断形成的“空白”,或者片段间的不连贯形成的“空缺”,或者文本自身的“否定性”,都是文本对读者发出的具体化的召唤。
③ 按:实际上,破坏项羽后方的功劳不只属于刘贾,太尉卢绾亦“绝籍粮饷”(《太史公自序》)有功,并且这支军队是以卢绾为主,刘贾为辅,事见《高祖本纪》《荆燕世家》。另,此事纪在汉四年,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六在“汉之四年”(西楚霸王四年,即公元前204年10月至前203年9月)之下有案语:“此以下所叙之事,前后倒置,不但与《汉书》异,并与《高纪》不同,恐系错简,细校如左。”(第207页)
④ 明·甄伟:《西汉演义》第七十五回,有明万历年间金陵周氏大业堂刊本。
⑤ 明·谈迁:《北游录·纪文》卷二十八,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⑥ 参见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又,赵氏著《陔余丛考》卷五亦云:“羽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为质。及鸿沟之约,羽又归汉王父母妻子。虽父母妻子者不过家属泛词,然果无母,则何必曰父母乎?”按:刘邦生母起兵时死在陈留小黄,此处或为庶母。
⑦ 按:查《汉书·高帝纪》在“归太公、吕后,军皆称万岁”之后,仅云“乃封侯公为平国君”,无有他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七引张文虎曰:“匿弗肯复见,与上下文不接。《汉书·高纪》无,疑匿以下二十一字,后人依《楚汉春秋》窜入,而注中‘乃肯见’三字,又即匿肯复见之误。”(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