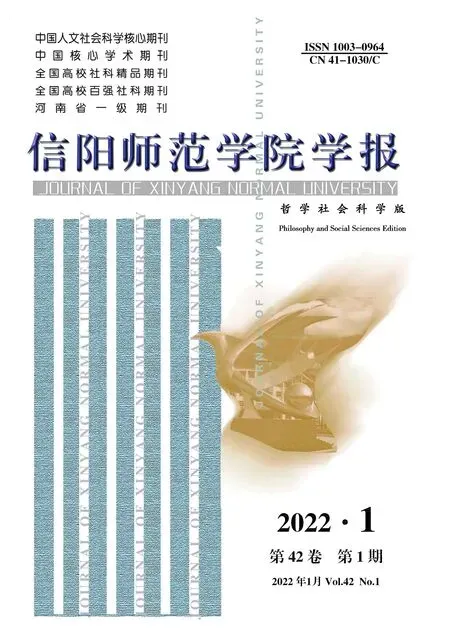“汉承秦制”格局下高帝、高后对秦法路线的调整
林聪舜
(台湾清华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新竹 30013)
商鞅变法后,秦国力量显著上升,逐步蚕食诸侯,终至一匡六合,将法家影响力推向高峰。但秦帝国短短15年即覆亡,却也让法家承担罪责,成为被打击的对象,使汉代法家在思想竞逐中遭遇论述上的困难,法家的理想论述不再能说服人,即便在“汉承秦制”的政治格局中,法家的精神与制度被承袭下来,汉代法家也很难再引领风骚,其角色必须做出重大的调整。
汉帝国建立后仍承袭秦制,特别是实施以秦律为基础的汉律,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且代秦而起的汉帝国的统治正当性经常建立在与“暴秦”“孤秦”的对比之上,《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曰:“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烈,今汉独收孤秦之弊。”[1]364因此,汉初一方面维持“汉承秦制”的政治格局;另一方面则在惩秦之弊以及反秦以形塑政权正当性的政治号召下,对秦法家路线做了符合现实需求的务实调整。
高帝、高后时期对法家路线的调整,取得很大的成效,使帝国稳定下来,避免成为第二个短命帝国。政治路线调整的大方向是在“逆取顺守”的原则下进行的,所以在“汉承秦制”的政治格局中,具有扩张性格的法家依然无法继续担任台面上的统治思想。汉帝国虽承袭体现法家精神与制度的秦制,但主要是工具性地使用法家,很难直接宣扬法家理想并执行法家主导的帝国路线。以下具体谈谈高帝、高后时期对法家路线调整的几个重要方向。
一、关东地区建置王国,暂缓“一用汉法”
关东地区是异于秦地的文化风俗区域,秦帝国强调公平齐一的理念,“一用秦法”,将秦法推行于全帝国,企图清除各地在原有价值体系上存在的风俗习惯,完成军事、政治征服后的思想、文化征服与统一。但文化低度发展的秦国,对文化高度发展的关东地区进行思想与社会规范的整齐化统治,激起广泛的不适应与仇怨,此一强势的价值洗濯,无法妥善处理王国扩张为帝国的转型工程,结果秦法秦政与关东地区文化风俗严重冲突,使秦帝国无法得到关东地区人民的支持,凝聚成亡秦怒火①。
在秦末的反秦起义运动中,陈涉义旗一举,关东地区瞬间星火燎原,数月之间尽复六国旧观。《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2]3106但在秦帝国本部的关中地区,则统治牢固,不见任何动乱,秦本部的吏民对风雨飘摇的帝国死心塌地服从,“关中卒”甚至构成镇压起义军的主力,一批批的关中子弟被送往章邯军大营而无怨无悔,与王离统率的防备匈奴的边防军结合成镇压关东起义的精锐骨干,直到巨鹿之战后,“关中卒”才被章邯胁迫投降,投降的“关中卒”在项羽入关前夕仍对投降表现出焦虑不安的情绪,遭到项羽击杀而覆灭。关中子弟对秦帝国的效忠,几乎坚持到帝国的覆亡。由秦末反秦起义运动中,秦本部吏民仍支持帝国政权,关东地区则人人以亡秦为念,可以看出帝国的关东统治出了大问题。
刘邦在楚汉战争期间,开始在关东地区建置王国,其原因固然出于结盟灭项的需求,必须裂土拉拢各地军头,诸如韩信、英布、彭越、张耳、臧荼、吴芮等,满足他们封王的愿望,形成反楚势力。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牵涉稳定关东治理的问题。只有在关东地区推行王国分封,放弃“一用汉法”,让关东地区处于半自主状态,故国意识强烈的关东吏民才乐意加入反项阵营;后来异姓王屠戮殆尽后,关东地区依然维持王国分封,改为大封同姓,仍是为了稳定东方统治。刘邦选择在关东地区推行秦统一前的王国建置,且不强求“一用汉法”,以尊重关东地区文化习俗,稳定关东治理,是在当时形势下不得不然的选择。
刘邦对分封同姓,造成尾大不掉之势,不是没有疑虑。消灭黥布后,立刘濞为吴王,两人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对话,《史记·吴王濞列传》载:
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2]3395-3396
“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是当时人对帝国东南隅离心力的观察而来的流言,刘邦对刘濞的告诫,不能全由神秘性预言的角度解读,这段对话若由理性角度解释,反映刘邦对分封同姓为“莫大诸侯”, 特别是对分封在楚地的王国仍感到不安。吴楚之地民风剽悍,风俗文化自成一格,《史记·高祖本纪》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2]440。秦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目的地即是东南方向的楚地。不辞万里之遥到楚地展示权威,威慑楚民,代表始皇帝对楚地分离意识的焦虑。刘邦对分封旧楚之吴地给刘濞,从分封初始即感到不安,此一不安不只是针对刘濞,他与始皇帝的忧虑一样,是对帝国东南隅离心力的忧虑。在此一心理背景下,刘邦仍在关东地区大封同姓,必然有其不得不然的考虑。其关键很可能就是面对关东地区的离心力采取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认为在关东地区建置王国,可以尊重当地文化习俗,缓和矛盾,稳定关东治理,预防激起民变。
刘邦建立帝业,承秦之制,袭秦之法,帝国直辖郡县也大多在旧秦之地,这时关东、关西地区仍未融合,如何稳定关东治理,避免蹈上亡秦激起关东民变的覆辙,会是很重要的考虑。在关东地区建置王国,实施郡国并行的一国两制,在帝国直辖郡县则实施承秦法而来的汉法,由于这些直辖郡县大多在旧秦之地,人民已经熟悉秦法以及承秦法而来的汉法的统治,只需依循旧章,不会造成适应不良而导致的反弹与动荡。至于关东王国地区则保留某些法制上的差异与弹性,降低人民对新帝国统治的不适应,用以稳定关东地区的统治。
在高帝、高后时期,诸侯王地位非常崇高,在王国内地位几乎等同皇帝,等级、势力、衣服、号令等区分贵贱尊卑者几乎无别,在皇权已强化的文帝时,贾谊在《新书·等齐》中仍感叹:
曰一用汉法,事诸侯王乃事皇帝也。谁是则诸侯之王乃将至尊也。然则天子之与诸侯,臣之与下,宜撰然齐等若是乎?[3]46
在王国内,事诸侯王采用中央事皇帝的汉法,与至尊无异。与贾谊感叹的文帝时期相较,高帝、高后时期,诸侯王地位只会更高,他们在王国内拥有相当高的自治权,形同半独立状态,特别是在汉朝法律外,各王国还有自己的法律,不必“一用汉法”。贾谊《新书·亲疏危乱》云:
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非立,汉令非行也。[3]120
“汉法非立,汉令非行也”,反映的是文帝时期已要求王国“一用汉法”,但遭到王国消极抵制。由于文帝在政治现实上要同时面对军功集团与诸侯王两大集团的势力,无法强硬摊牌,只能暂时容忍,这才引起贾谊的感叹与忧虑。高帝、高后时期,“汉法非立,汉令非行”是王国拥有的权利,是关东地区王国拥有相当高的自治权,形同半独立状态的正常现象。
推动郡国并行制,在关东地区广置王国,放弃“一用汉法”, 尊重旧俗,是“汉承秦制”政治格局下对法家整齐划一路线的调整。从稳定关东地区统治的角度看,高帝、高后时期,“一用汉法”的条件尚未成熟,在关东地区不同风俗文化圈大行封建,建置王国,可以因俗制宜,在汉法基础上调整出适合各地风土民情的法律,尊重各地在原有价值体系上存在的风俗习惯。因而秦帝国时期关东地区对中央极权统治带来的紧张性大为缓和,汉帝国也因此做一调整,暂时稳定了东方治理。
二、对法禁做局部修正,缓解承袭秦律而来的严酷
汉律承袭秦律,目前几乎已是学界共识,出土的材料也印证此一论断,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奏谳书》中出现的,代表高祖六年(前201)至十二年(前195)的法律案例,与秦律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包括刑名大体相同、审判程序基本一致、量刑标准与秦律极相似、刑徒也与秦刑徒一样是无期的[4],即早期汉律对秦律更多的是直接继承。萧何所定汉律,已推翻了三章之法的宽容精神,《汉书·刑法志》载:“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1]1096张家山出土汉简印证了此段传世文献记载的正确性。
帝国实施继承秦律的汉律,但在特殊风俗文化圈的关东地区建置王国,可以因俗制宜,弹性制定适合各地风土民情的法律,缓和了关东治理的紧张性。另外,朝廷在体认“逆取顺守”的政治路线下,对法禁做了局部修正,缓解汉律的严酷。
高帝、高后时期对法禁做局部修正,以缓解承袭秦律的汉律的严酷,史传颇多记载,《汉书·食货志》载:“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1]1127《汉书·高帝纪》载十一年二月(前196),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1]70这两条记载都是在“约法省禁”的原则指导下,放宽律令限制,从轻制定各项税收标准,减轻百姓负担。《汉书·惠帝纪》载:“(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1]90这是减省妨吏民的法令,除挟书律则是放宽思想、文化管制,争取读书人支持。《汉书·高后纪》载元年春正月(前187),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辠、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1]96此诏书执行了惠帝议而未决的除三族罪、妖言令。虽然除三族罪屡次废而复行,根据《汉书·刑法志》,文帝时,“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1]1104的刑法仍在,但汉初确实对法禁做了局部修正,缓解承袭秦律的汉律的严酷。
在法禁的执行方面,刘邦也经常从轻处理,并多次颁布大赦令,如《汉书·高帝纪》载六年十二月,执楚王韩信后,诏曰:“天下既安,豪杰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1]59刘邦同情刚复原的军民,因不熟习法令而触法,颁布“赦天下”之诏。惠帝、高太后效之,亦曾“赦天下”“大赦天下”。
高帝、高后时期屡屡颁布赦令,是与法家主张背离的,法家主张信赏必罚,施刑无赦,避免官员与民众存有侥幸心理,《商君书·赏刑》曰:“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5]138又曰:“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5]142又曰:“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5]143《韩非子·五蠹》曰:“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力矣。”[6]1100《商君书》与《韩非子》都反对法外施恩,赦免犯刑者,是要建立刑法至高无上的权威,不让吏民有丝毫侥幸的心理,使吏民不敢轻易犯法。
《韩非子·奸劫弒臣》比较商鞅变法前后,秦国对法的态度不同,成效遂不可同日而语。变法前,“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秦民习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6]283。“废法而服私” 是以私恩私德干扰法秩序的运作,造成“有罪可以得免”,导致人民“轻犯新法”,法之成效不彰。法家的法治观念反对以私恩私德干扰法秩序的运作,法外施恩,赦免犯刑者,也属于私恩私德。变法后,“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私(告)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6]283。
在法家的主张中,法的施行是冷冰冰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是独立运作不受任何干扰的,高帝、高后时期屡次“赦天下”“大赦天下”,都干扰了法的运作,是与法家主张背离的。但在“汉承秦制”的政治格局中,在汉律承袭秦律的严酷性的政治现实中,高帝、高后时期屡颁赦令,其作用与对法禁做局部修正相同,都是缓解承袭秦律的汉律的严酷性的一环。
三、在“以顺守之”的政治路线指导下,推动黄老无为政治
刘邦即皇帝位后不久,就接受叔孙通“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2]3278之说,征鲁诸儒生30人,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叔孙通弟子百余人共起朝仪,刘邦大悦,体认到原来鄙视的儒者的重要功能,守成的儒生开始大量进入朝廷。接着又接受陆贾建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2]3252刘邦领悟“逆取顺守”的道理,知道取天下靠武力,治天下必须靠文治,取与守不同术,从此“以顺守之”成为刚建立的帝国的政治指导原则。
儒学的仁义、礼乐、先圣、《诗》《书》可以达成“以顺守之”的目标,汉初推动的黄老无为政治也可以达成“以顺守之”的目标,而以汉初残破局面的情况衡量,此时推动黄老政治更符合时代需求。推动黄老政治的重要人物是曹参,《史记·曹相国世家》载其治齐,“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2]2450。采用黄老之术治齐,除休养生息的普遍需要外,曹参看到齐国是特殊的政经文化风俗区域,须有尊重差异性的治理方式,所以他为齐相,第一要务即是“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2]2450。黄老术清静不扰表现的兼容作风,可以降低帝国统治此一关东重要王国造成的紧张性。“安集百姓如齐故俗”既是实行尊重齐地风俗民情的放任政策,又能表现对本土思想的尊重,以此方式安集百姓,是“以齐治齐”的策略与智慧的高度发挥。
曹参后来继萧何为汉相,除了在军功集团的资历声望外,他以黄老之术治齐,舒缓关东、关西对抗的经验与治绩,对帝国东方政策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可能是重要原因。《汉书·曹相国世家》载惠帝怪相国不治事,曹参答曰:“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2]2451-2452为汉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2]2452这是在萧何依循秦律的法治基础上,以宽缓的方式做了修正,亦即在“汉承秦制”架构下对严酷的法家路线的调整。
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强调道与法的结合,在理论上可以调和汉承秦制的政治格局下,汉律承袭秦律,帝国却又急需休养生息的政治现实。汉初普遍流传的《黄帝四经》是黄老思想的重要著作,《黄帝四经》的《经法·道法》强调“道生法”,由此,“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7]48的“法”,取得由“道”而来的形而上的根据与正当性。《经法·道法》继云:“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7]48那么在“法”的运作过程中,执道者弗敢犯、弗敢废的无为态度,遂可以与“法”的运作相配合,成为最协调、最完美的运作方式。《黄帝四经》另有刑德相辅相成的主张,如《十大经·观》强调先德后刑,“夫并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7]282。这是主张效法自然规律春夏德养在前,秋冬刑杀在后,先行德教后施刑罚。《十大经·姓争》强调刑德相养,“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视其央。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缪天刑,非德必顷。刑德相养,逆顺若成”[7]325。这是主张刑德的互补关系,犹如日月相望,不可一无,若缺其一,刑德都无法单独实行。这些主张,与汉初黄老政治调整承袭秦律的汉律成为较温和的法治主义,刚好相呼应。
在“汉承秦制”的政治格局下,刘邦确立了“以顺守之”的帝国路线,高后时期则在曹参推动下,具体化为结合清静不扰与依循秦律的黄老无为政治。这些转向,都是对严酷的承袭秦制的法家路线做了宽缓的调整,并取得极大的成功,稳定了帝国的统治。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思想,则为黄老无为政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也让后人更清楚地看清汉初黄老政治的真相。
四、结语
汉初沿袭秦制,沿袭秦法,但在惩秦之弊以及借反秦以形塑政权正当性的政治号召下,做了统治方向的调整。汉高帝、高后时期,帝国一方面维持“汉承秦制”的政治格局,作为统治的基本架构;另一方面透过在关东地区建置王国、在法禁上做缓解严酷的局部修正以及推动黄老无为政治等方式,对秦法家严酷统治路线做了调整,走上“以顺守之”的政治方向。这些调整兼顾思想引导与现实需要,从结果看,是很成功的调整。
注释:
① 陈苏镇认为,根据各地反秦之激烈程度的差异和《语书》透露的信息,说秦之“法律令”与关东文化存在距离,特别是与楚“俗”之间存在距离,当无大错。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