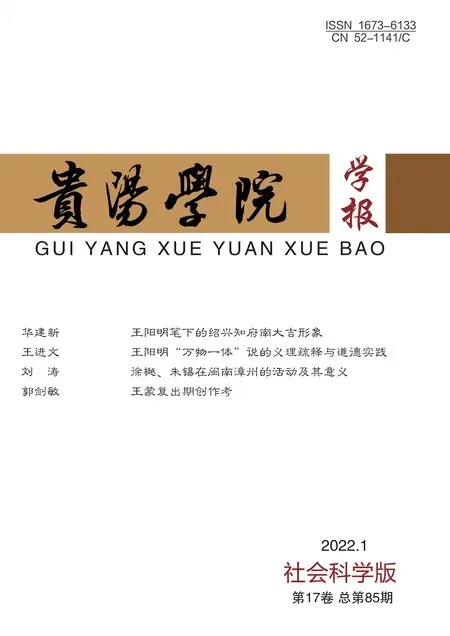王阳明“万物一体”说的义理疏释与道德实践
——致良知视角下的本体论、工夫论与境界论
王进文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相较于西方哲学以知解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儒家哲学以实践道德理想为目标,注重在对生命的自省和参与宇宙万物的化育交感中养成完善人格,具有明显的实践品性与强烈的生命关怀。其中,阳明学说尤其强调“行”的重要性。众所周知,阳明之成学历程异常曲折,有所谓“三变”与“五溺”之说①钱绪山撰《刻文录叙说》云:“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参见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下册,第1306页。湛甘泉为王阳明所写的墓志铭中则提到,阳明一生“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同前,第1149 页。。经过恶劣的环境考验,尤其是数端濒死经历与心智磨炼,阳明最后终体会到“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圣人之道,圣人之学即良知之发明,“致良知”遂将其体用一源之特色呈现无遗。自三十四岁在京师与湛若水讲学论道,宗程明道“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1]1149之说,到晚年“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万物一体”之说成为阳明一以贯之的重要论述之一。阳明“万物一体”之说由致良知开展,通过发挥先秦以降儒家内圣外王之人格修养,证成由人的内在道德心的觉醒,体之于身、验之于心,在亲亲、仁民、爱物的同体关怀中与万物无隔,与大化同流,达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理想境界。“万物一体”既是阳明对个人生命历程不断反思与体悟的结果,也是其成己、成人、成物道德实践的全幅展现。
一、阳明“万物一体”说的建构与展开
众所周知,对阳明思想进行系统性的表述是非常困难的,这既与阳明本人对书写传统保持怀疑与谨慎的态度有关,也与语录体的文本形式相关[2]18。阳明一生将成圣贤为第一等事作为目标,此一目标则是通过其思想的心即理、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次第达成,而以致良知为主轴。他继承先秦以降儒家“一体之仁”的思想,认为良知作为宇宙本体,因生生之理流行下贯而为人性,可以通过人的明觉是非判断而肯认其心体即天理。通过心的发用,天地万物俱可亦俱能被收摄其中,世界便可从本然层面转化为意义层面。因此,如能体悟“心即理”并扩而充之,便可谓之仁。此即阳明所言之“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3]89。
(一)良知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仁是儒学的核心关怀。先秦儒家以仁为天地万物内在的生命本质,主张天道性命相贯通,通过下学上达的内圣而成己,经由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体物不遗的外王而成物。内圣之学属于纵向的提升,是“通天人”而与天地合德;外王之学则是横向的开展,是“通物我”而与万物为一体。不过,明确将万物一体与仁相联系并予以阐述的则是宋明儒者。钱穆认为,宋朝理学是围绕本体论的“万物一体”与工夫修养论的“变化气质”两部分展开热烈讨论的[4]。这一论述相传延续至明代,阳明思想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孕育滋长的。阳明原是遵循朱子格物致知之旨,始终未能对格物致知有所体悟。直到谪居龙场,方悟心即理、心外无理,并由此展开对良知的阐发。
阳明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即孟子所谓的性善或四端②这样的说法可从《传习录》中随处看见:“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性善也。”“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参见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8 条(第40 页)第155 条(第175 页)第288 条(第277 页)。。心作为万物的本质存在而为本体,而心即是理,天地万物又都秉受此理,故心即万物之本体。接续孟子的理路,阳明主张良知本来自明,之所以不明则是因为吾人之心受到私欲障蔽。人心发动为意念时则有善恶,但因本心是至善,只是其发为意念时会有所偏倚,才有恶的出现[5]。
问:“先生尝谓善恶只是一物,善恶两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谓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3]247
良知是人心本体,但人的善端有时会被欲望所遮蔽,未能在事事物物上体现,便为恶。换言之,恶是偏离中庸而变成过与不及的状态。既然良知常为私欲所蔽,故要有克治省察之工夫来让良知觉醒。
良知人人皆具,不以愚智而有所不同,这便意味着人人皆可成圣贤,其原因就在于良知与天道是一,而人受了天道而成为人之性,此即孟子尽心知性而知天的理路。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1]214
在上述文字中,阳明已将良知学提升到“心即理”的层面,并蕴含了“万物一体”的观念。理为天理,亦即万事万物之理,然而万事万物之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阳明通过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路论证人心与天理是一体的,这就实现了形而上境界与伦理意识的结合,使得自然秩序转化为人文秩序。
(二)良知的内在与超越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则会发现阳明之良知论具有内在与超越两个层面的意涵。就前者而言,如孟子之即心言性,阳明认为:“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1]802在他看来,良知就是天命之性,先天内在于我而为心体。性体、心体是“未发之中”,当意念发用应物时,此心体上即自然地呈现善与不善、是与非之明觉。阳明一再说明良知是“心自然会知”“良知自知之”,四句教中有“知善知恶是良知”,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他所言之良知乃是一个能为一切已发的意念给出是非善恶评判的准则,这就关系到意念之发是否合于天理,亦即“心即理”的问题。“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3]194良知发用之思做出价值性的评断而知是知非,知是知非故必然知合乎天理与否。换言之,良知能明觉天理,良知即是天理。
就后者而言,阳明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3]263他将良知视为绝对的存在,是形而上的宇宙本体,是天地万物之源。而天地万物的本质即天命之性,性体即道体,可以流行下贯。故而,“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3]269。虽然人与万物均有良知,但唯有人得天独厚发窍最精而具有一点灵明,这是人的特殊之处。横渠以“太虚”命名道体,阳明则以良知即太虚,在道体未发用流行之际论说良知之虚、之无。“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起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3]267由此可见,阳明已将超越的良知与内在的良知通而为一,毫无隔膜。
(三)成己成物以践行一体之仁
在儒家看来,“仁者,人也”[6]375。仁是人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依据,体现了宇宙的生生之理。仁心良知作为“天植灵根”乃能生生不息,人作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便应当具有普遍的仁爱与同情感。
根据《阳明年谱》记载,阳明晚年居越讲学,环座而听者三百人,而阳明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其良知。又做《大学问》及《拔本塞源论》二文,充分发挥万物一体说之精义。在《大学问》中,阳明抉发《礼运》“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之义蕴,认为“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1]798。
“万物一体”之大同理想境界非凭空臆想,而在于人人可以为尧舜之主体性的仁心良知之自觉。阳明所谓“一体之仁”即“明明德”之“明德”;以“致良知”来说,“一体之仁”即是“良知”。合而言之,“明明德,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7]。良知的呈现,便是天理的具体实现,而天理创生万物,那么,良知的呈现便要及于天地宇宙间一切存在之物,体物而不可遗。良知使天地万物为一体,则我们对于生民之困苦荼毒,如吾身之疾痛,这种同情心可以使人超越我者与他者之分,走向人我之间的统一。在此意义上,仁爱恻隐之心即构成了联通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心理情感基础。阳明确信,如果每一个体都能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将恻隐之情普遍地运用于天下之人,便可逐渐遂其万物一体之念。
《拔本塞源论》,真切地流露出阳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并转化为成就圣贤人格道德实践的动力。阳明论述道: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3]155-157
圣人出于其心之不容已,自然而然推广其“浑然与天地万物为同体”之念。出于忧患人心私蔽以致狭隘失其本心,圣人不容已之心自然推己及人而施教养,这便是“知行合一”的展现;使天下人自行恢复心体之同然,则是“致良知”自觉复性的要义所在。对阳明来说,如果一味专注于辞章、训诂、技艺,成就的只是工具层面的理性而已,精纯的内在修养工夫、临事上的磨炼体验及人伦生活中的道德人文教养,才是体道成德的正途。只有深造于道,才能形成主体内在德性,才能化良知为自我不可须臾相离的真实存在。不仅如此,在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与《中庸》“尽物之性”的基础上,阳明更进一步地主张由“物我同一”发展到“成己成物”。圣人体察天道运行而知万物本一体,良知充分致用,由尽性而知天地化育,无人己之分,无物我之别。从人的具体道德情感的普遍性意义着眼,人性与人伦互相成就,成己便意味着成人,成人便意味着成物,则人若能循天理而行,物我合一,便可顺畅无碍,故而成己即成物,这便是儒家在通过自我认同的实践后所完成的理想境界[8]。至此,我们可以说,在阳明的论域中,“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3]274。
二、“万物一体”说之本体观
阳明“万物一体”说立基于儒家心学“心即理”的传统,四句教中“为善去恶是格物”更直接提示了心与物的联结。可见,心物关系是阳明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么,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阳明之“万物一体”呈现出怎样的姿态呢?
(一)摄物以归心:心外无物
众所周知,阳明一生思想之精义在于“良知”。“良知”二字原出自孟子,心学传统中“心即理”之“心”,不仅是道德主体,也是可以通于“性”“天”而为宇宙化生之本体;理也不仅是道德法则,而是可通于性理、天理而为宇宙万物的存在之理。阳明以良知释心,既综括了心之仁、义、礼、智四端,又深入地探讨和发掘了良知是非之心和明觉天理之义,将其涵摄于“天地一体之仁”的思想中。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3]263
阳明言“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3]29,宇宙生化的仁德天理就是良知,良知的发用流行不限于“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也表现在“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的宇宙生化。因此,就良知心体的无限性来说,人的仁心中所显出的道德秩序即宇宙秩序,仁心即是天道,因此,本体论与宇宙论是合一的。所以,人的修德成圣便是人的存在价值,这既是个人人格的完成,也是天道生化的完成。而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恢复良知,超越有形的躯体的限制,达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与物无对的一体境界。
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3]269
天地万物之所以能成为有意义的存在,是由于人的良知灵明之作用,否则只是物质性的存在而已。良知遍及一切,为万物所共有,只是人可自觉地呈现,而物则否。物虽不能自觉地呈现其良知,但当人的良知呈现时,必然生发出遍及一切与万物为一体的意义,一切存在都在人的良知朗润之下。当良知呈现而与万物为一体时,天地万物皆与我无分别,良知之发于我,亦即发于物。无疑,这一主张与横渠所言之“我体物未尝遗,物体我知其不遗也”[9]及明道所言之“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10]等具有相同的意涵。
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3]308
在良知的明觉感应之下,物我是同体的。通过心的活动,可使以彰显天道生化的意义。而如果没有人的实践感通活动,天道的意义也就无法彰显。因此,“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这一仁心的感通,是天地万物的真实存在与本心良知的一体呈现。天地万物皆因良知而成为有意义的真实的存在,而在一这存在关系中,物不是现象、对象中的物,而是“在其自己”之物,存在也是在良知的显发明通中存在。良知是宇宙万物的存在根基,良知的完全扩充发挥也就意味着道德实践达到了极处,只有在良知心体没有一丝障蔽时,才能达到这一境界,从而,一切工夫便需要收归于“致良知”之上。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3]29
既然心之所发为意,意之所在为物,因此,物即是事。阳明在此强调的是人的各种现实活动均离不开意念的贯注,意念之发若为善,则此行为便是善,反之则为恶。阳明认为,人之身体所以能视听言动,乃是由于“心”的主宰,否则,便成麻木之身。然而,“心”又不是独立自存的实体,“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所以“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心是身之“灵”,所以能觉天地之性、觉一体之仁;也因为心之“灵”,所以它能为一身之“主宰”、能知是知非,是为性行于身的一个机窍,所以心与身体交融无间、身心一如。心正意诚,则生活行为自必归于正。阳明释“格物”为“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心之本体无所不正,但常人之心已不是心之本体,格物就是纠正人心的不正,以恢复本体的正。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即是事事物物皆得其正、皆得其成。
综上,摄物以归心,心以宰物以成物,此便是道德之创生。所谓“心与理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都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获得解释,这也就是“心即理”“良知即天理”最中心的义蕴[11]132-133。
(二)心体即天理:心外无理
阳明尝言:“圣人之学,心学也。”具有传奇色彩的龙场悟道是阳明日后论学之本。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1]1007。此“心外无理”之悟,发现人不仅能成圣,且内在地具备成圣的根据。仁义必求于心,吾心即物理,这便是“心即理”之内在逻辑,亦为阳明学说之基础。
孟子主张,“心之官则思”,不仅赋予心为身之主宰的意义,更将其视为良知、良能等先验的道德主体。阳明在承继孟子论述的基础上,对“心”进行了更加细致与深化的阐释与建构,使之不但是道德实践的根据,也是道德法则的根源,此即“心外无理”之义:
所谓汝心了,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3]115
阳明反对朱子格物穷理之说,在他看来:“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3]22就道德行为发生的过程而言,外在事物的存在只是一个客观事实,本身并不足以决定道德的价值;只有当由道德主体根据客观事实作出相应的判断之后,才有种种道德之理的产生。所以,常人见孺子入井而援之以手,并非是由客观对象而是我们以自己的良知本心为主作出因时因地制宜的决定。故而,“理”必由“心”发,不由“物”得。他扭转朱子向外求理之论,力陈人之穷理求至善,只须在自己心上去发觉、寻找,其工夫便在心上去人欲之蔽,以恢复心体原来的客观普遍性。
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3]23
故而,“心外无理”之实质便是“心体即天理”。不过,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理”并不是在否认外在物理的重要性,而是指唯有具备纯乎天理的本心,将其发用于事物上,便有事物之理,自然会真诚地去追求纯全的德行。质言之,纯乎天理的良知本心是一切的根本,我们只要有此真诚的心体,必然会去寻求恰当合理的表达方式。
在“心外无理”的前提下,阳明所论之心为道德本心之心,道德本心自然知恻隐、是非、辞让、羞恶四端,四端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道德本心就是此知仁知义。不但如此,他进一步认为,源自孟子的良知四端可归结为“是非之心”: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3]277
阳明将“良知”说成“是非之心”,凸显的是良知代表了人的内在道德判断的标准。因此,如果将良知之“知”仅仅作为认知意义的知,无疑是错误的。良知的昭明灵觉,能使人不容自已地好善恶恶、为善去恶,故“良知即是天植灵根”[3]255。人起私意,良知便知是私意;人为恶时,良知能觉是恶。“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3]239在这样亲切浅显的表达下,道德实践便成至简至易之事,自然人人可付诸行动。
综上,阳明关于天人关系的展开,主要是通过“理”或“天理”观念将“人”与“天”、“人心”与“天心”相结合。“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1]181作为人道德实践的凭据,心是主体与主宰,是无私欲之蔽的超越本心,只要无私欲之蔽,便能表现为忠、孝、信、仁等德性。既然天理是人人本具的良知,其本身真诚恻怛之感通,依其轻重厚薄而显其事亲之孝、从兄之弟、事君之忠等的等差性,达到“天然自有之中”。
(三)人心与物同体: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
阳明在《答聂文蔚》中云:“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3]208圣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此一本体即贯彻天地人的共同本体,为天地万物与人之存在的终极意义。事实上,自明道揭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培养和追求人的精神境界,并落实到内心生活中,便成为儒学精神性的表达。不但如此,儒者还需将其落实到社会关怀和生民忧患之上,是为儒家外王之诉求。
阳明认为,就心的本来面目而言,每个人与圣人一样,人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这种一体主要表现为相互之间的诚爱无私。“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其元气充周、血气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3]157他将天地万物、生民困苦荼毒之“疾痛”视为切于吾身的“饥痛”,由此,天地万物在“我”这里便成为一个“血脉贯通”的“大身体”,这个“大身体”的痛痒、饥溺便是我的痛痒、饥溺,这个大身体的“知”痛痒、饥溺便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体知”,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知识意义上的“知道”。当我“体验”到天地万物这个“大身体”的痛痒时,便对这个“大身体”的“痛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1]798-799
“人心与物同体”不仅具有物质实体的意义,就本质来说,以万物为一体一方面指的是心之本体原本是以万物为一体的,另一方面则是万物本来就处于“一气流通”的一体联系之中,同时包含着把宇宙看成一个有机系统的意义,强调万物与人息息相关的不可分割性[12]。“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3]269由此,人心的一点灵明固然是属于“人”的,但亦应该说是属于“天”的,是“天地之心”发窍之最精处的一个“结果”。天地万物的意义便是从这个发窍的最精处透显出来[2]64-65。
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还表现在人之良知的运作亦与天地万物的运作同步、共鸣:
夜来天地浑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无所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凝一时。天地既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闻,众窍俱辟,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可见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3]265-266
“吾”与万物皆“混处于天地之中”,本身就嵌在大化流行的一气之中,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环节,而“万物同体”系吾人有了“自觉”所得到的“体验”,即所谓的“感应之机”[2]69。阳明认为外物的存在,乃在人心的感应之下才有意义,这便是其所言之“心外无物”。
众所周知,朱子主张穷格事物之理,“理”是外在人心的客观存在。阳明则认为,朱子有将心与理分而为二的支离之病,而主张“心即理”,强调“心在物为理”。在心与物的感通下,人与万物的距离得以消弭,物不再只是客观存在,万物同体也因而建立起来。天地万物共此一个良知,人之良知本心无私不隔之感通中,即得体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综上,阳明一体之学是“实学”,其“实”就在于体之于身、验之于心,在亲亲、仁民、爱物这一推己及人的无限过程之中落实、体证一体之仁[2]103。阳明的心、身、性、理乃一通贯的整体,与孟子“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①《孟子·尽心上》的践形观是一脉相承的。人之心能验得此万物一体之仁,人之身能体证此万物一体之仁,本身也是天之所命,在大化流行之中,人有幸禀得天地之“灵气”,此气至灵、至正,充塞身心,活动不已,是为良知、良能。因为充塞于周身,所以是体知,所以能“践形”。致良知是“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即是“推其万物一体之仁”“遂其万物一体之念”“负其万物一体之责”。
三、“万物一体”说之工夫论
在阳明“万物一体”说之下,人道、天道本是一体,但人唯有反己内证,了悟天理内在本心,以勤勉的工夫修养来完成“变化气质”,经其良知充分致用后方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才能达成参赞化育的目的。由此,“致良知”之重点便在工夫论的展开。
(一)致良知的重要性
阳明肯定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至于圣贤愚凡之分别,则不是受教育的高低与知识的多寡,而是能否致其良知。
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3]145
在阳明看来,人人本具先天圆成的良知,虽在圣不增,在凡不减,而圣愚之分,只因凡人顺躯壳起念,被私欲妄念遮蔽,良知遂隐而不显。此中关键就在于人伦日用中不断地克服私欲,而后良知才能保持着清明的状态,落实于道德实践,成就完满的人格。
至于致良知的重要,我们可以从王阳明《书魏师孟卷》中看出端倪:
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是故良知之外,无学矣。[1]236
能致良知才能具体实现人皆可成圣贤的命题,故而,阳明才说:“此致知二字,真是个千古圣传之秘,见到这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3]239《年谱》中亦记载在写给邹守益的信中提道:“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②《年谱》,“(正德)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岁,在江西”,《王阳明全集》,下册,第1050 页。可见,阳明在经过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学后至五十岁提出致良之教的这十四年当中,经历过了“百死千难”的历程,通过了自己最真实的生命体验,终于体悟到原来圣人教人的道理如此简易,就是“致良知”而已。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若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3]193
阳明的致良知教可说是儒家“成德之教”的圆满结穴。“良知”乃先天的道德本心,它不是来自于经验的见闻之知,而是德性之知。但阳明并未排斥见闻之知,其所强调的是只有以良知为主,见闻之知才能真正彰显其价值[7]165-167。
(二)克治省察与格致诚正的工夫路径
如果说阳明的良知二字重本体意义,则致良知无疑具有工夫意义。在肯认良知即天理后,如何扩充良知本体?在此,本文以阳明思想形成过程为切入点,考察其工夫论的进路。
首先是立志。儒家自先秦以降,即以人作为研究对象,以讨论人生问题为着眼点。阳明在幼年即立志学做圣贤,自始脱离世俗人生路线,而欲得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究竟圆满解答③据《年谱》记载,阳明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阳明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参见《年谱一》“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岁,寓京师”,载《王阳明全集》,下册,第1001 页。。立志学圣可以说是他一生追求的志业。阳明之所以如此恳切地要人立志,或是源自其经历过廷杖之后的深刻自省,故而,他才谆谆告诫:
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3]307
在龙场教学所立的教条中,他更明白地将立志列为其中: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1]804
其次是省察克治。凡人立志并具体实践成圣成贤,必须要有方法。阳明认为,“立志用功,如种树然”,即要循序渐进,先固其根,然后时时加以培养灌溉,除去杂草,方能渐进其干、枝、叶,然后才能开花结实。这个立志的根,就是良知心体,而用功就是要能使良知一体朗现,这就要从“省察克治”着手,亦即阳明所说的“去人欲、存天理”。
阳明认为,人心本然之体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但现实的人心因受物欲之蔽而产生私,把自我与他人及万物分隔开来。因此,恢复心之本体与实现万物一体的至仁之境的根本途径便是去除私欲:
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 耳。[1]799
私是指“有我之私”,欲是指“物欲之蔽”,本然的明德是“未动于欲,未蔽于私”。如果间于私、隔于蔽,明德就丧失了本然之明,所以圣人之学的基本原则就是:“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3]15在此意义上,德性修养的根本原则是“克己”。阳明把儒者成圣之学归结为“为己之学”,这里的己指人的真正自我,克己的己则是指私己之我。在与弟子论为学工夫时,阳明说道:
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需教他省察克治。[3]60
克治是克己,即克吾心之私欲,而克治时,一定要真真切切,等到达无私可克,即良知与天理一体展现之时,便达到为天地育万物之境界了。所以,克己就要除恶务尽。那么,如何克己呢?“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3]115“克己”即“复礼”,人必须“非礼勿视听言动”,才真是“为得个躯壳的己”。“克己”是克躯壳的己,躯壳的己即是“身”;“为己”是为“真己”,真己即是“心”。“真己”与“躯壳的己”是主从关系,“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有真己作主宰,躯壳便不只是躯壳,而是真己的具体显现,即视听言动,依循于礼。而“身”与“心”并非截然分开而相对立之二物,所谓“克己”并非不让耳目口鼻四肢去视听言动,而是不可“随躯壳起念”。如此,“克己”便是“为己”。阳明以《大学》“诚意”“正心”为例,指陈如果离开了诚意正心,就无修身工夫可得;如果能够“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而慎独存诚,便是有“为己之心”,便能“克己”,也就能“成己”了[11]95。
再次是集义。克己既显示阳明成圣心志之坚定,也意味着天理下贯而为人之心体。心体“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是日日克己复礼而成,孟子将之视为“集义”。阳明说:“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3]85集义便是为学用功之处,按照阳明的话,便是须在“事上磨炼”[3]50。何为事上磨炼?阳明回答:
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谓“必有事焉”者也。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余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3]165
阳明良知学讲求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事当然不是说完全忽略良知以外的事物,即“见闻之知”,因为万事万物无不是天理之表现,只要人心能把握(或者复归)本体良知并时时加以省察以使其不被蒙蔽,时时加以培养以使其得以扩充至极,便能顺天理而应事,本良知而行事。学问思辨之穷理是穷究外在事物之理,这是实然的知识之学。而良知所知者乃是道德上的是非善恶,是“应事接物”之理。对阳明而言,在具体的道德生活中,良知与见闻之知是体用关系。基于良知在实践上的优先性,阳明以良知为“体”,闻见之知为“用”,良知为主,闻见之知从之,以此才能开示出人文化成的价值意义世界[7]167。
最后则是格致诚正。所谓良知即是天理,天理不外良知,是就事事物物的“应然之理”而言的。面对具体的人事物,良知之呈显发用固是自作主宰,不假外求,但这仅表示良知是一切事理的最高决断原则,并不意味着其已蕴含一切客观事物的实然及其所以然之理: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3]246
可见,一切事业其实都是本乎良知天理之决定而步步做成的,人经由学问思辨以穷理求知,本乎良知之要求而发愤致力。故而,“致良知”工夫是要推扩良知于事事物物之上,不离日用感应,这便是格致诚正的意义。
(三)以知行合一悟得存省良知
致良知是将良知心体本所具有的天理扩充通贯到具体的道德实践中,使人秉具良知天理行事,使事事物物皆在良知天理之感通朗润之下各得其正、各得其成。因此,我们可以说,致良知之目的就在于在良知的通显感应中使万物各得其宜,致良知之效用则必然通向外王层面的事功。
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3]153
内圣之学为本,外王事业为末。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就圣人内心之纯德而言的,在此意义上,成圣是人人可为的,是人人能力可及的。对阳明而言,良知作为天地万物的本体及创生原理,它本身并非静态不活动的超越之理,而是在良知本体的感应活动中显示出其作为最高的存在。宇宙论层面所言之良知本体,即是“太极生生之理”。而良知本体之“体”,是就太极生生之理的“常体不易”而言的;良知本体之“用”,是就太极生生之理的“妙用无息”而论的。在此意义上,“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3]103。
悟得良知本体之后,便需要存省良知。“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3]132要达到良知明觉感应而与万物为一体,则需要亲身体会的实践工夫,即“知行合一”。阳明认为,心诚而无妄,行直而无曲,良知充分显露,便是复得知行本体,便是“知行合一”。而现实中则往往因为不能致良知,导致知善知恶的良知被情识妄念所动而不能具体落实于日常行为中,即知行被分为二。就良知而言,知行是通而为一,落实于“去人欲、存天理”之中,因此,行并非只是已形于外的行为,凡善恶之几,起乎一念之微,此意念发动处良知自然知之,故而意念一有萌动便是行,知行本是一而非二的。《传习录》载:
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问学,只因知行分做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3]246
由良知心体上指点工夫着力处,一念发动时之不善必须彻底去除之,而一念好善之心必须实现于生命历程中,这才符合知行合一的宗旨。可见,阳明所持知行合一之论,是要在日常人伦中处处存省克治,时时以致良知为念,将私欲不善一齐去尽,使得本体恢复,所思所虑无非天理流行,如此,便可臻于万物一体之境界。
四、阳明“万物一体”说之境界论
在阳明那里,“万物一体”不仅仅是一个认知的世界,也是人通过长期修养获得的一种超越个体限制,达到与天地万物圆融和谐的心灵境地。那么,“万物一体”的境界论呈现出怎样的图景呢?笔者试论如下:
(一)至诚至真的“狂者胸次”
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①《孟子·离娄上》阳明承接孟子之“诚”论,认为“诚是心之本体”[3]114,与天道为一,既是宇宙本体,又是心性原则。这就将诚的主体性、自主性扩展至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极致。
诚是本心良知自做主宰,不为世俗媚心所左右,表现出阳明所激赏的“狂者胸次”:
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3]288
阳明在追求至诚至真的圣境中,由衷地欣赏“狂者胸次”。“狂者胸次”以良知本心作主宰,出乎本心之真诚,自能明辨是非善恶,不受外物扰乱,不为世俗媚心所左右,其或出或处,能卓尔自立,执中而行。而“狂者胸次”正是真己、真我的表现,能信手行去,甚至特立独行,是一种真正自觉自信的境界,是“常快活”的。人因受人欲迁蔽,执着于躯壳之我,产生了“有我之私”,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真状态被人们迷弃了,这便需要“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3]156。克其私、去其蔽才能显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真我”。此即追求心灵与精神上的自在和幸福的“常快活”。在他看来:“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尔。……心尽而后,吾之心始自以为快也。”[1]762君子之学之行,从善而非有意为善,不求于人知而只求自快吾心,面对富贵贫贱、忧戚患难时才能“无入而不自得”,可谓洒脱率真之表现。
在阳明看来:“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3]316虽然他并不认为狂者是理想人格的最高标准,却远远超越常人和俗人境界,“一克念,即圣人矣”。一旦克念入圣,由“明”以至于“诚”,自能圆应无方而善成之,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
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工夫。[3]278
阳明认为,情是人所本有的,顺其自然地发用,本身无善恶可言,我们对其存在也不应带任何价值判断,但对人因私意而有着,便不是自然之发用,亦不是正常之发用,便影响到良知之展现,是为“欲”,即良知的障蔽,故成恶。狂者胸次始终保持良知本体的明觉,使七情免失于正。阳明强调,应就人人本有之良知明觉而去蔽复体。面对诬谗困境时,阳明蹇以反身,困以遂志,自从居夷处困,动心忍性,或“反身而知止”,或“致命以遂志”,身处逆境,却神明在躬,天清地宁,“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1]574,即是其一生真性情的写照,也是“万物在我心”的超然境界的体现。
(二)至仁至善的社会关切与生命关怀
儒家认为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体现为真诚恻怛的至善道德境界。阳明在肯定道德实践主体层面的自安自足的同时,更强调人伦日用、道德事业的客观层面的明德亲民,实现“万物一体”至仁至善的境界。
阳明早年在阳明洞修道时,曾一度有遁世的想法,只因难以割舍对祖母、父亲的思念之情而放弃。这种思亲之念是植根于人的天性,是人最根本的情感,“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1]1004。由此可见他对人伦亲情的看重①据《年谱》记载,阳明曾以儒家的人伦亲情唤醒了坐关三年沉沦于禅境之僧。参见《年谱一》,载《王阳明全集》,下册,第1004—1005 页。。他一再强调,“圣人之学,心学也”[1]206。儒者所言之求尽其心,是由主体自觉地履行道德义务而达到的自慊自快的状态,“其间权量轻重,稍有私意于良知便不自安”[1]181。基于儒家对天下有所担当的外王事功这一价值取向,他批评佛氏虽然追求的也是明德良知,却逃避君臣父子之义,外弃人伦,“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不管,不可以治天下”[3]98。
阳明认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3]208万物一体之仁是人心的本来状态,本心如果不受各种私欲的遮蔽与外诱的浸染,自然会做到视人犹己,视天下犹一家,视中国犹一人。这就是“大人者”的至仁至善境界。而以万物为一体之仁心,则是始从孝悌层面由对亲情人伦的眷念和责任,向内“修己”成就自我,向外则由“修己”推扩到“安人”与“安百姓”,使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这一向外推扩的过程,就是儒者救世济民之责任,也是与万物同体的至仁至善情怀之展现。就此而论,践行万物一体之仁不仅要克己成己,而且要成人成物,不但克小己之私、去小我之蔽以成就个体之人格,而且要融小我于大我,化个体于群体以成就家国天下。唯有如此,才能融天地万物为一体,进入“与物无对”“天人一体”的境界。
与万物一体的仁心既是“明德”,也是“良知”。大人与小人之别,便在于能否体认万物一体。大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便能随所见之孺子、鸟兽、草木、瓦石而有所感应,生出怵惕、恻隐、不忍、顾惜之心,而小人则否。但是,大人与小人的不同并不是本质上的,不论大人或小人,皆具有万物一体的仁心,只是后者为私欲所扰动遮蔽,导致良知隐而不彰。由此,“大人之学”就是要使人良知朗现,复归万物一体之仁心。在阳明看来,人只要去其自私物欲之病,恢复本然“与物无对”的良知,去除人我与万物的隔阂,以复其本有之明德,自能恢复万物一体之仁。他以《大学》的“明德”为本,阐发儒者“万物一体”之仁民爱物胸怀:
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1]799
大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明德”必须兼顾天下苍生,以“亲民”为要;“明德”既明,而后一体之仁始能呈现;而“明明德”的工夫,不是由外力所加,是本然具有的,只要本乎“仁爱恻怛之诚”,便恢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本然之仁心善性,便可免于沦为功利权谋而亲其民,而后一体之仁始才能由内施于外。因此,“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1]204-205。换言之,明德与亲民是体用的关系,立体达用,本末是一,欲达明德之体,必得落实于万物一体之用;“明明德”必须落在亲民的实践上,才可实现“止于至善”。
当然,阳明“万物一体”思想是首先确立无差别的“仁”之本体,然后落实到有差别的外在工夫,最后再回溯到无差别的“仁”之本体。在回答“大人与物同体”的质疑时,阳明阐释道:
惟是道理自有厚薄……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如此条理,便谓之智;始终是这条理,便谓之信。[3]270
由上可知,在阳明那里,“万物一体”思想带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对人的爱高于草木瓦石的爱,这种等级上的差别,根源于伦理实践主体对于对象不同的现实感受性。人只要诉诸内心情感,这些厚薄差等是良知的自然条理,即良知的诚爱恻怛对不同的对象自然呈现为不同的程度。他所说的无差别的爱只是从“仁”的本体来说的,而现实世界中爱的差别则是由本体至工夫的必然结果,“义”“礼”“智”“信”则是工夫的具体内容。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的万物一体之仁的渐次发展,这是缘于人与万物之间的自然厚薄,也是仁的自然条理。但是,天地万物息息贯通,没有间隔,我们应以“莫非己也”的态度直面当下,以遂万物一体之念。每念斯民之陷溺,而思以此救之,这种切身疾痛和强烈的使命感,要求我们无论境况顺逆,均不能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社会责任。可以说,阳明所言之“万物一体”不仅是亲亲仁民爱物的至仁道德境界,更是处人伦、接物理,应物而不为物所累、顺情而不被情所挠、入世而不被世所困的至善生命境界。
(三)至乐至美的人心本然状态
陈立胜认为,人是天地的“心”,是“万物之灵”,这是儒家对人的总体定位。此心不只是也不主要是认知心,而是恻隐心;此心不是超离万物自足的主体心,而是内在于一体之中的;此心不是和身完全割裂的意识心而是与身纠缠在一起的。“吾”与万物皆“混处于天地之中”[2]69。阳明“万物一体”之说认为先儒所追求的孔颜真乐,就是人心的本然状态。他在《答陆原静书》中说: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3]189
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乐是心之本体,这个本体就是万物的生生之理,就是人生命本真的怡然自由状态。人之生理本无不乐,良知即乐之本体。良知不是对情的压抑、排斥,而是情顺其自然而行,是为“真乐”。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七情有着,则俱为良知之蔽,便非心之本体。常人“为客气物欲搅此和畅之气,始有间断不乐”[1]165,但此乐仍根于心,通过致良知之修为复其本心,反身而诚,则怡悦自得的孔颜真乐就可显现。至于体悟良知以达至乐至美境界的具体工夫则在于对本心的持守:
夫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增,乃反为洒落之累耶?[1]161-162
“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1]162,“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存于“戒慎恐惧之无间”,而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即是“慎独”,慎独即是“敬畏”,“敬畏”则是无时或已、不容间断的工夫。阳明心学所持守的敬畏,并非畏惧害怕,而是一种浑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浑然与万物同体”的状态,是一种朝夕惕励、不间断地存省良知,达到自律,更是一种“无善无恶心之体”的道德化境[2]200,也就是真洒落;洒落亦非放肆妄为,而是超越小我局限、私意遮蔽,进而顺应无滞。在阳明看来,圣贤之乐是根据至仁真诚而发的道德觉情,常人之乐是感于所爱之物而发的激情。只要“一念开明”,良知明觉便能感通无碍,便能致良知,“反身而诚”,便能不顺人欲迁流,彰显良知本性的纯粹真实。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3]291这是阳明居越后期的四句教。四句教以良知为本体,以致良知为工夫,既要本体明觉无滞,又须在工夫上落实良知发用——心之体虚灵明觉是至善的道德本心,只是人在现实中不能免除随躯壳起念的干扰,一起念而有善恶之分;心体则能察知属于经验层面的意是善或恶,而良知之天理不仅是是非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具有“真诚恻怛”的力量,对意之所在的事物,能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可以说,四句教的重点不在空谈本体,而是明示德性实践的内在理,也就是为善去恶的致良知的工夫,它既不着于“无”亦不偏于有,却又同时兼融“有”“无”二境,而成一“彻上彻下”的圆实之教,实现了境界的有无合一[13]。能够与万物同体而得洒落之真乐趣的良知,恰恰是“有”与“无”的统一。不过,一般人在理解阳明致良知说的时候,往往只是关注良知“知善知恶”的能力,而忽略其“无思无虑”的特质,故而在致良知的工夫上不免多着了一分意思。阳明提示道:
圣人只是还他良知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3]267
良知之“虚”之“无”,这是从本体意义上肯定良知虚寂无执,自然流行;至于说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则是从工夫意义上强调不须后天人为地执着。由此可见,良知之“无”贯通于本体和工夫,不仅无碍于良知之“有”的呈现,也更能彰显本体与工夫的本来面貌。
“乐”作为自我生命的本性所在,成就“真乐”就是要在自我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中感悟和把握人存在的根本,复得良知的意蕴,体悟到“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的人与人、人与万物生意不息、生意相通的至美体验。这是一种人的心灵超越物我人己之界限而与宇宙万物合为一体的生命状态。四句教中的“有善有恶”是意义世界的诚境,“知善知恶”和“为善去恶”是道德世界的仁境,而“无善无恶”则是审美世界的乐境,是德行工夫成就过程中的无执无着以及工夫成就后无偏无私的至美化境。如果说仁境与诚境体现着“与物无对”,即物我无隔,是人实现理想的自在境界之内在根据,这也意味着尚需主观努力,那么,乐境便是融合于诚、仁二境之中自由愉悦的至美体验,只需顺良知本心便能适意自得[14]。阳明以“本体工夫,一悟尽透”的顿悟式体认来呈现本体之乐,不过,“乐”虽然偏重于直观体验,仍须有道德实践的心为主导,是在人伦日用中体认与磨炼的结果。圣人之学主于经世应物,应物乃成就圣功之所需,所谓“于尘劳烦恼中作道场”也。因此,凡圣之别的关键端就在于人是否肯努力作修养工夫,使此心纯乎天理,复得良知体。
综上,阳明“万物一体”的境界,无论是至诚至真的真理境界(即诚境),还是至仁至善的道德境界(即仁境),都离不开至乐至美的人心本然状态(即乐境)。在乐境中,良知即本心,本心即良知,顺天则而自慊,是非无须执着去知,善恶无须刻意去辨,自然可以超越有无之分、物我之隔,进入“与物无对”超越自得的境地。可以说,乐境既是一种超越的境界,又内在地融合于诚、仁之境的体验中,真正达到本体与境界的合一。
五、结论
阳明由致良知所开展的“万物一体”之说,是在传承儒家从先秦“天人合一”到宋明“一体之仁”思想精华的基础上,通过对自身生命历程的反思与体悟,揭示心即是理,赋予良知既内在又超越的理论意义与“成己成物”的道德实践面向,极大地深化和扩展了儒家一体观的意涵。阳明肯定“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而言“心外无理”,良知明觉之绝对普遍性,此即“心外无理、心外无物”。
就本体观而言,阳明“万物一体”的良知不仅是道德主体,同时可以通于性天而为宇宙生化的本体与天地万物的存在之理;就工夫论而言,欲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唯有反己内证,悟天理内在本心,知天德在己,顺其良知之发用,才能达成与万物同体之理想。阳明致良知的道德实践便在于体之于身、验之于心,通过立志、克己、集义与格致诚正,在亲亲、仁民、爱物这一推己及人的无限过程之中落实和体证一体之仁。就境界论而言,阳明“万物一体”的至诚至真、至仁至善与至乐至美是三位一体的,诚境与仁境以乐境为依归,而乐境既超越又融合于诚境、仁境的体验中,超越有无之分、物我之隔,化解了有无之间的紧张与物我之间的对立,是为“本体即境界,境界即本体”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