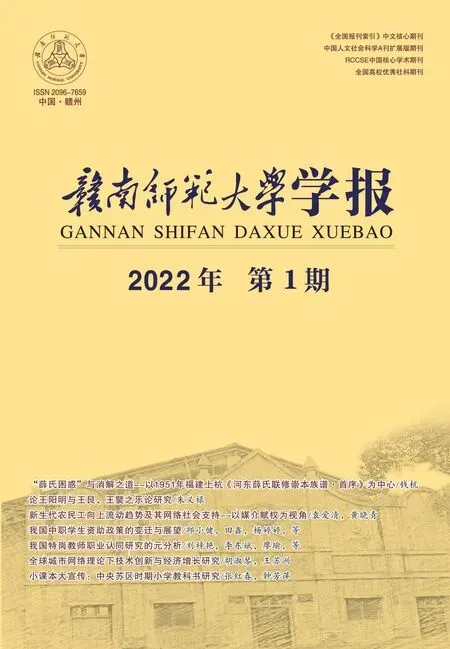马克思社会理论:以消费为核心的解读*
吴玉彬,倪明宇
(赣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全球化浪潮把消费实践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边缘角色”变成了“时代的主角”。同时,中国社会也面临着消费转型和消费升级的现实性问题,是“一场静悄悄的消费革命”。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一些主要观点已不再重要。重新梳理马克思消费的社会理论并探索其当代实践意义,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进消费革命”等相关论述。由此,在面临新时代、新问题,拓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领域的研究不仅是理论继承发展的问题,更关涉中国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实现美好生活的现实问题。
一、返回生产与生活的消费研究
现代和后现代理论有一个共识:消费处于当代资本主义和文化中的中心位置。消费主义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背后主要的推动力量,消费作为符号机制重构后现代社会结构。同时面对多元主体性重构,消费主义是对身份认同危机的反映,随着多元化的群体、价值观和知识在后现代社会的出现,消费主义是重建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 鲍曼[1]认为,消费主义是自我建构与身份建构得以围绕其旋转的中轴、是自由选择的社会、是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物的社会。在消费主义中“当一个人的出身、历史在社会中不再那么重要的时候,身份就更是一种流动的资本,消费也就变的更加重要了。”[2]用贝克的话说在现代社会中“一切事物都围绕着个体利益和个体生活而运转……基本上接近于决策的生活机遇所占的比例在减少,开放的而且必须由个体建构的活动所占的比例则在上升。”[3]换句话说,消费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本身就是要打破基于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对立和基于社会结构上的身份认同机制。消费社会所践行的不仅是一种资本增值的逻辑,更是一种统治的策略、一种流动的认同机制,这种机制建立在“朝生暮死的”商品上。
起初,消费主义是社会精英的事情,具体表现为奢侈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但随着时间推移和下层人民收入的提高,这种生活模式被假定可以被下层人民模仿。涌现出消费“民主化” 的同时,消费主义的理念从少数特权人物变成普通大众触手可及的现实。斯特恩斯[4]把“消费主义”定义为物质商品的诱惑,这种消费主义形式首先出现在18世纪的西欧,关注于衣着打扮与家用的小物品。然后在19世纪晚期传播到世界各地,以商品与闲暇为核心的消费主义迅速占领大众日常生活。但是消费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有不同的表现模式,并非单指西方的消费主义并将其移植到世界其他地方,重要的是要融合地方模式和传统价值观念并形成独特的消费主义类型,包括:俄国消费主义、东亚消费主义、拉丁美洲的消费主义等。随着对“现代性”不同的评估和理解,消费社会的图景也不断变化,呈现“现代消费者”“传统消费者”和“后现代消费者”的理想类型。
如果把焦点放在消费主义的“贪婪”“物质主义”“被购买商品的欲望控制”时,同时,忽视了消费的现实功能,例如消费者身份已经与市民参与、文化认同、社会和全球正义等问题中。Ben Fine[5]174认为,要回到生产来理解消费和消费主义,如果把消费主义等同于富裕社会,这不仅忽视了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边缘的群体,更无视那些第三世界的人民——消费水平仅维持在果腹之欲的人群,更不用提那些正在经历饥饿、疾病或无家可归的人。无疑,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正是发达国家的贫困者、第三世界国家的牺牲,加上近代出现的富余生活产生了超越生存的消费形式。同时,Ben Fine[5]174指出,需求长期对经济的发展决定性的作用经不起推敲。消费主义的路径假定底层阶级的消费会模仿上层阶级的层级传递的模式(上层的需求会刺激下层的需要)。预设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被普及所有的人口,这种观点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证实。事实上消费在人群中的扩张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因为消费前提是要付得起钱。
Terhi-Anna Wilska[6]在研究芬兰的消费主义和生活风格时指出,尽管存在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但大多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是适度消费。同时,储蓄和投资对大多数消费者是最重要的。更为突出的是,例如性别、年龄、社会阶层和收入对大多数的生活方式有重要的影响。由此,研究消费主义不仅要关注消费主体,更要探究生产主体,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下形成独特的消费主义模式。不仅要从欲望策略、物质主义、符号等方面来研究消费主义,更要从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阶层地位、收入水平、地方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来研究消费主义。
二、马克思消费的社会理论研究脉络
在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已有解读中,“生产”被视为关注的中心和重心。[7]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消费”绝不是“失语”,相反,在《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和资本》等文献中对消费领域的相关问题有重要论述。这些关于消费的社会理论论述,虽然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有重要区别,但也深刻分析了消费对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推动了身份地位、文化认同与生活方式的转型。之后,哈维、列斐伏尔、詹姆逊、布迪厄等诸多社会理论家从马克思主义的消费思想中获致学术灵感和思想渊源,从不同视角融汇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路,部分回应了马克思关于消费的思想和理论。 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关于消费理论的研究呈现多元化态势。
首先,批评马克思消费思想的时代性和局限性。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已经不再能够充分解释以商品增值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只有借助于符号学理论才能解释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物品的消费已不再因其物质特性,而是因其符号特征,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这种关系已延伸和弥漫到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8]同时,国内学者[9]对此进行转述、阐发、评价。
其次,被动继承转述马克思消费思想。全面地概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本质、商品拜物教、异化的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消费观的拓展和延伸。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异化消费、消费主义和生态危机的反思和批判,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10]
再次,积极肯定马克思消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张一兵[11]在分析了历史上的消费和消费主义后,认为要返回生产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消费文化和机制。Slater[12]在消费文化研究中重新求助于基本问题和现代性概念,引用马克思的论述,对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消费需求等展开进一步分析。Miller[13]重新尝试把黑格尔的客体化理论应用于他命名的“物质文化”,并认为马克思的消费研究曾经占据主导地位。Renton[14]把马克思论劳动异化、马克思论金钱的魔力、马克思论面包的生产作为马克思讨论商品与消费主义的三部分。Korkotsides[15]对消费的资本主义文献做批评性评估时,以“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消费”为小标题,论述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消费问题上的政治经济学贡献。
最后,拓展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领域。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新的经济社会情境下分析和探讨其中的消费问题。余晓敏和潘毅[16]把消费视为是资本的逻辑和工厂体制与政治力量合谋的结果。王宁[17]分析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如何促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Magagna[18]把阶级分析应用在消费领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消费的不平等,即享有消费特权的人群和普通的消费大众之间的不平等。
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纳入消费的视角,展开消费文化研究或消费的社会理论研究。同时建构一个突破西方消费话语体系,完善补充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理论体系。理论研究的终极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为正确认识消费主义的传播和制定合理消费的具体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在对消费实践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制定相关的解决方案,提出应对策略。
三、马克思消费的社会理论二重性
马克思关于消费的社会理论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有形的物品消费,其二是无形的闲暇消费,这两者都对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有重要影响。在工人日常活动中,闲暇时间被消费因素(消费的欲望、商品的购买等)所充斥,缺失了工人自己的活动方式,呈现异化的状态。工人试图通过消费来改变身份认同的幻想最终会破灭,因为他们所践行的只不过是资本的逻辑,也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工人自身的认同、目标、活动也逐渐遗失了。
(一)消费的有形之物象征意义
1.消费——文化意义的解读
以物作为媒介来探究人与人之间关系并彰显社会的结构,这是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物就是指具体的事物,而文化则是通过这个物折射出来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在消费活动中,人与人关系通过物的形式表现出来。把消费视为物质文化的具体表现时,物的消费所承载的就是它的社会意义,而不是它有什么样的实际功能、什么样的外观和形式等。 同时,消费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仪式,其“主要功能是让一系列进行中的事件产生意义”。[19]消费的内容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有形的物品消费,另一种是无形的闲暇消费。
起初,对消费一词的解释是:“毁掉,用尽,吞掉,吃光或喝光”。事实上人类在消费时不仅仅是对物品本身的消耗,“如果一个人主要是像这样从吃喝上获得满足和快乐的话,那他就很可悲,因为这表明他要么过于贫困,要么过于贪婪;表明他是穷人”,[20]更重要的是对附着在物品上的意义彰显,这种意义是对社会结构及不平等的复制,它体现在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商品可以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或者说商品体现社会地位,传递了人际间的相互影响。”[21]13凡勃伦也认为消费是一种实践活动,消费者试图通过商品来确证自己的身份。消费展示的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22]32可见,消费在建构个人身份和地位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萨林斯甚至借用图腾的概念来描绘这个现象,他认为原始的部落都有对山川花鸟虫鱼等万物的崇拜,这些事物后来成为区分不同部落群体的图腾。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崇拜的客体只不过用生产出的商品置换了自然事物。换句话说被生产的人工制品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图腾,不同消费群体相当于原始社会中的部落。这样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服饰、住所、交通工具等来区分个人所属群体,人成了挂在消费之网上的动物。
鲍德里亚把物的符号意义的自我运行推向极致,他认为物的符号意义替代了真实之物,符号在相互指认的结构中形成一个完美体系。这个符号体系通过不断地分裂、组合和自我再造,生产和再生产了社会结构。[23]我们只能根据这个符号系统的变换来找寻自我的归宿,虽然我们不了解这个抽象的符号体系,却在他的引诱下不断前行。人类自以为在历史中创造着一件件物品,并用它们作为交流、指意、表述、建构的工具,实际上,如今人类却受制于它,按照它的旨意行事。总之,我们的身份已经成为消费模式的同义词,而消费模式是由我们以外的东西(符号系统的自我运行)所决定,这里“意义的逻辑代替了生产的逻辑。我们已经从以商品形式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进入到符号形式为主的阶段,这样消费不应理解为和使用价值有关的物质用途,而是作为意义,主要和符号价值相关。”[21]63
2.消费的身份置换了身份的消费
现代性的消费方式打破了基于等级制形成的传统社会消费方式。在传统社会中,身份和地位是消费的基础,权力等级的高低决定了日常消费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不能随意消费超出自己所属群体等级的物品。比如古代欧洲,整个社会由僧侣、贵族和平民三个“等级”构成。基于这三个等级序列的人群通过各自的消费品来展示自己的身份,表现在住所、服饰、食品等生活的各方面。[24]同样,我国古代社会的等级地位也是根据消费品区分的,这种现象在儒家的“礼”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儒家鼓吹的理性封建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要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礼具有鲜明的层级性和差别性。礼即赋予差别性、因人而异的行为规范,所以‘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他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去选择相当于其身份的礼,符合这条件的为有礼,否则就是非礼。”[25]在这种等级观念的基础上,对不同群体的衣食住行用,甚至人的生老病死等消费的细节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对住所消费的规定:“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李靓《礼记·中庸》)。关于服饰的消费,《礼记》中对衣着等级作为了明文规定:“天子龙衮,诸候如黼,大夫黼,士玄衣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候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以此人为责也。”甚至对于衣服的颜色都有明确规定,在清朝,官服除以蟒数区分官位以外,对于黄色亦有禁例。如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而下属各王等官职不经赏赐绝不能服黄。
随着大众消费的来临,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流动性频繁的陌生人社会,所以基于传统“乡土社会中”的情感、稳定的身份认知与人进行交往变得举步维艰。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大都根据一个人的消费方式来确定他的身份序列。这里最主要是由于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品在建构身份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建构不是基于明确的等级序列,而是基于消费品的意义逻辑来建构个人的身份认同。姚建平把消费分为三个重要特征:第一,消费方式建构身份的过程中不再强调等级差异,而是强调消费品位的差异。等级社会中的身份认同是在阶梯结构中选择自己的位置,而大众消费社会中的身份认同是在网状结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第二,自我感或群体疏离感。强调个性化和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第三,消费社会中的身份体系有较强的不稳定性。[26]
(二)消费中的无形之物——闲暇时间的象征意义
把无形的闲暇时间拉入消费文化的视野,就会发现闲暇也是一种社会区分的指标,更能折射出社会结构的现状和变迁。也就是说,人们不仅使用有形的物来区分不同的群体,无形的时间也是造成社会区分的一种重要方式。当然这里所指的不是纯粹物理意义上的时间观,而是富有社会文化意蕴的时间观。
恩格斯把人们的生活分为生存、享受和发展三部分,为生存所需的时间为劳动时间,而用于享乐和发展的时间为闲暇。马克思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区分,阐释了商品、资本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并争取把剩余劳动时间归还给工人,使人摆脱异化最终实现人的复归。马克思认为“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就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27]605阿伦特[28]178对此持否定态度,她区分了劳动、工作、行动三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阐释,最后指出即使人有了闲暇时间也不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闲暇的出现虽然标志着人类脱离了劳动必需性的压制,但同时走向了另一个必需性的漩涡——消费。人类从追求生活必需品转移到追求多余的奢侈品,最终世界会被消费吞噬而毁灭。所以阿伦特提出行动的理念——超脱人谋生的动物性,用行动和言行来彰显人的德行,以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实现人的自由。[28]178为了更好地对闲暇时间进行认知,需要进一步梳理闲暇时间的研究脉络。
对闲暇的理解和认知贯穿整个人类文明,从柏拉图对正义和理想国的探索到亚里士多德[29]的“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以及到后来的斯多哥学派、犬儒主义和伊壁鸠鲁派都有一个共同点是崇尚自然闲暇的生活。他们深信良好的秩序是上天安排好的并能通过良善意愿达到,提倡肉体的欲望要受控于人的理智,以追求一种内心的宁静。[30]但由于受当时生产力的限制,这种闲暇属于上层人士的特权,他们过着一种“政治生活”“善的生活”。可见闲暇在古希腊时期是公民身份的、自由人的象征。
随着社会步入近代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大大地推动了人们对奢侈品的追求。人们拒绝了古典观点——把对个人欲望的追求与“怯懦”“柔弱”连在一起。[31]民众开始追寻世俗生活和对自由的向往,而人自由发展的一个条件是闲暇时间的出现。同时,人们对闲暇的追求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工人对限制工作日的斗争,他认为工作日“取决于两点,第一,劳动力的身体界限。第二,工作日的延长受到道德界限。工作日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27]269
凡勃伦认为,从古希腊哲人时代起直到今天,那些思想丰富的人一直认为要享受有价值的、优美的或者是可以过得去的人类生活,首先必须享有相当的余闲,避免跟那些为直接供应人类生活日常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工作相接触。[22]32这里凡勃伦把生产劳动污名化,视为低人一等、劣势地位等。他把奴仆、家居的布置与烦琐的礼仪制度视为有闲的标志,也是自我炫耀的方式。所以凡勃伦说“有闲”这个字眼,指的并不是懒惰或清静无为,而是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这样,闲暇就从作为追求卓越的条件降到彰显世俗身份地位的方式,仅仅是对自己身份的一种确证。闲暇时间的充裕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它和有形的物一同建构了这个社会的结构和人与人的关系。
近代随着时间概念的发展,出现了休闲学说,这种学说区分了空闲和休闲的不同意义。皮珀从哲学的高度重新阐释了盈余时间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并声称休闲是文化的基础,人之所以受物的奴役而不能自拔,主要源于人与世界的功利主义思想——工作的伦理。人之为人不能仅满足于工作的迫力,更重要的是享受内心的平静并达致人的完满,这需要休闲的哲学,对人心的、人性的陶冶。他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来取代已经日显破坏力的工作文化,这就是闲暇文化,认为“工作只是手段,闲暇才是目的,有了闲暇,我们才能够完成更高层次的人生理想,也才能够创造更丰富完美的文化果实。”[32]
古德尔和戈比区分了空闲和休闲的概念(1)一方面,因为空闲是用小时、天、周等时间单位来度量的,所以时间就显的很重要;另一方面,空闲时间标志着一种与工作相脱离的状态,所以工作也被人们当成一个重要的时间概念。工作是空闲时间的反义词,但不能作为休闲的反义词。休闲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人生状态和理想。,认为空闲是一种空洞的时间概念,而休闲不是一种纯粹的时间概念,更不是一种摆脱外在限制的自由,因为这样都反映出人的内在贫困。休闲是在休闲哲学指引下,关注人内在的自由和宁静的生活方式,包括空闲时间和精神状态两方面内容。[33]
凡勃伦的有闲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是一种文化制度的压力,在蔑视劳动的前提下形成一种有闲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一个拥有财富和权力的群体认同具有重要作用。皮珀、古德尔和戈比事实上从哲学的角度解析休闲的内涵,并将其与空洞的时间(空闲)区分开来。当他从古希腊到清教徒再到近代思想史中探求休闲的原则时,实际上是和劳动者的闲暇是无缘的。不论是凡勃伦书写的有闲,还是古德尔哲学意义上的休闲,都不能更好地解释普通劳动者群体的闲暇的真实状况,以及他们闲暇时间的作用。
闲暇的不平等分配和有形物的不平等分配是同一个社会区分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的产品分配的不平等,在消费过程中的无形时间分配上也表现出明显的断裂。这种断裂不仅表现为时间数量上的多少,更重要的表现在时间所包含的意义和所要传达的社会内容。
四、结论
目前学术界大多研究都集中在文化批判和后现代哲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消费进行研究。借助于客观主义研究方式,将所有工业消费品归到文化统治观念之下,推导过程仅仅是一笔带过地谈论商品消费的罪恶。相关的研究大都停留在理论探讨、分析或相关的调查报告上,缺少相关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创新。
更为重要的是,搜集整理现代和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消费论述的中文和外文文献,阐述其继承、发展关系。需要进一步系统地梳理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理论的研究,同时选取对世界和中国现实问题有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消费理论进行重点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的社会理论置于历史视野和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进行讨论,否认消费社会的单一模式。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消费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差异性,对传统消费、现代消费和后现代消费进行探讨,分析生产、消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消遣经济是费孝通在《禄村农田》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最初用来针对那些雇工自营和把田地租给别人经营的人,这些人倾向于脱离劳动,而不是参加劳动使土地产出最大化的理性主义行为。“那辈脱离了农田劳动的人,在我看来,在农做中省下来的劳力,并没有在别的生产事业中加以利用,很可说大部分是浪费在烟榻上,赌桌边,街头巷尾的闲谈中,城里的茶馆里。”[34]张敦福[35]指出面临当下中国公共生活的缺失、社会整合度低的现状,急需重建传统乡土社会的休闲、消遣观念和生活态度予以平衡。消遣经济分为几个命题:消遣经济指的是传统农村社会的经济态度,其核心是少劳作,少消费,有空闲;空闲时间被消耗于茶坊、酒肆,一起抽烟、说长说短,甚至“鬼混”,其中不少是参与公共生活,即“仪式投资”;全村自给自足的程度很高,自足自得的消遣经济生活比较普遍。
而在当代社会缺少了大把的闲暇时间,更不用说这种悠然的生活方式了。社会大众即使有了闲暇时间也被现代消费的欲望所占据,在消费欲望的支配下陷入了不停地工作、消费的怪圈,缺少了传统的公共交流活动。在闲暇时间,民众不是彼此交流、进行仪式投资等,而是逛街、看看光怪陆离的商品、嗅一嗅梦想中的物品、谈赚钱做老板等,造成了彼此的隔离和疏远。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重构消遣经济是很有必要的。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归传统的消遣经济,因为消费主义的盛行已不可避免。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增加闲暇时间的“消遣性”和公共性,增进人际间的情感交流。其次,要使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同步增长,这样才不至于使主观消费欲望与客观的消费能力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最后,消费主义在演变成“欲望机器”时,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治理工具,普通民众要认清自己的需要,打破法兰克福学派的“虚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