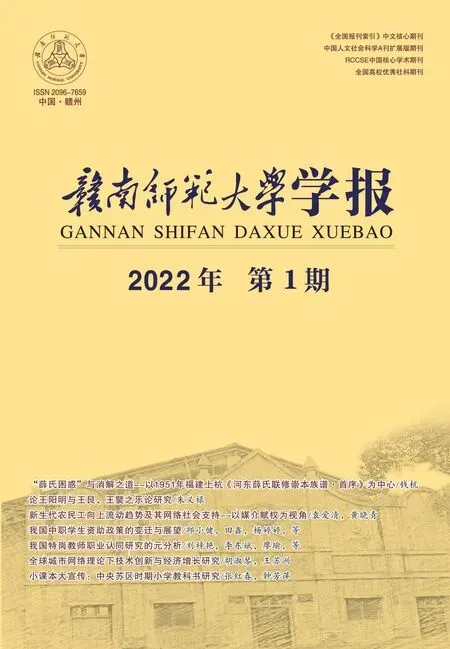“薛氏困惑”与消解之道
——以1951年福建上杭《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首序》为中心*
钱 杭
(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34)
上杭县是闽西南名镇,东接龙岩,西连武平,北倚长汀,东北毗连城,东南邻永定,西南与广东梅州接壤。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划龙岩的湖雷下堡(今永定县下湖雷)设上杭场,隶汀州;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升场为县。此后直至清末均隶汀州,民国时先后隶第六、第七督察专员公署。1949年8月27日,上杭县解放;9月17日,上杭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1950年1月13日,改称上杭县人民政府,[1]隶龙岩专署,现为龙岩市属县。
上海图书馆《中国家谱总目》[2]著录福建省上杭县家谱117种(含上杭籍台湾地区家谱2种),上杭县古田乡家谱10种,共127种。其中上杭薛氏家谱2种(528-0063《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528-0064《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据528-0063“提要”:
[福建上杭]《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二十八卷末一卷。薛史青等纂修。1950年铅印本,九册。书名据版心、书衣题。书名页题《薛氏族谱》。二修本。
始祖伯启,号三十六郎,宋代人。
(收藏)慈溪市环城南路励双杰。
全谱各册封面均标明“一九五零年庚寅岁修”,联修草谱亦刊印于1950年,但谱中某序的写定日期则为“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故该谱正式的问世时间应定为1951年,(1)超星数字图书馆收录2004年《福建上杭(河东郡)薛氏族谱》,第115页“六世祖”下“千二郎—万一郎—东一郎公”条,亦称该族有“1951年版族谱”。距第一次修谱的清雍正五年(1727)已时隔223年。
按笔者的“新谱”定义,凡在对旧谱(主要是民国谱)修改、增删基础上,于建国(或当地解放)后印制问世的谱牒,可视为“新谱”中的“新旧谱”或“半新谱”。《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倡议筹备于民国廿六年(1937)夏,至民国卅年(1941)大致完成,待避过兵燹、新中国成立后,在总纂薛史青主持下,按新标准对原稿因旧辑新、改谬补遗,(2)“如顷收新稿,凡树封建式,蓄官僚气,或含偏私炫耀性,能迷陷正确思想,导入浮俗歧途,有妨实际福利者,概行删削,或全篇割爱,恕不登刊。”《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凡例》第4页。以下凡引《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所收文字,均径引篇名及页码。1951年正式铅印问世。按此过程,将该谱归入“新旧谱”一类应无问题。
本文以上杭县《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首序《社会主义与修谱史略》为线索,参考首册所收各时期谱序及相关地方文献,分析和理解位于闽西南丘陵地区的一个古老宗族,在面临建国初一系列不确定前景时,一些代表人物的困惑、思索和对策,为当今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民间宗族在处理与国家—政府、社会公共事务间的关系及编谱者的自我要求,提供一个可资参照的案例。
一
《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首册为全谱卷一,封面目录中属谱序、凡例类文章共18篇,依次为:首序《社会主义与修谱史略》(1950)《凡例》(《闽杭河东薛氏八省联修崇本族谱·首先几个例子》)《家规遗训》(7条)《族箴》(17条)《闽派河东薛氏八省联修崇本族谱付刊·首先的一段话》(1951)《闽派河东薛氏八省联修崇本族谱新序》(民国三十一年,1942)《河东薛氏廉村族谱源流集》(元至正十一年,1351)《溪南薛氏族谱源流集》《杭川薛氏族谱源流序》(明正德十二年,1517)《杭川薛氏手册族谱序》(明万历元年,1573)《杭川薛氏编修崇本族谱序》(清顺治十六年,1659)《杭川薛氏续修崇本族谱序》(清雍正五年,1727)《泰和芬溪薛氏族谱序》(清咸丰元年,1851)《芬溪薛氏族谱序》(同上)《成盛户初修族谱原序》(清雍正三年,1725)《薛氏成盛户社背家谱序》(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薛氏成盛户社背家谱原序》《成盛户重修族谱序》(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等。
首序《社会主义与修谱史略》共390余字,图影及全文如下:
或谓社会主义不久要临到,族谱会消灭啦,曰,唯唯、然然。社会主义势必降临,但社会主义有领导的动机性和创造制度的事业,惟族谱一物则与历史同,仅记载过去事迹而已。其宗旨在追木本、溯水源、详迁移、考世系,敦宗睦族,长长亲亲,以孝思为则;其实质为国史的细胞,是民族实录的基础(人类的骨干社会中不可消灭的),国家信史的来源。故序族谱者咸曰“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史编则昭褒贬之荣辱,族谱修则知宗派之盛衰。采国风、编国史者,取舍之间,存乎其人。因此,于民国廿六年夏,开始逻辑[集]闽派启祖一脉厚、鼎、闰三房遗篇;卅一年,函征散居于川黔滇桂湘赣闽粤八省宗族齿录,陆续接到江西安远县肇、启二房合修刊本族谱(3)薛修玉:《薛氏联修崇本族谱》,1989年河东堂铅印本。,得以参考。又知荣通公叔祖一脉移居泰和,贵公叔祖一脉久年隔绝于赣大由乡,复得联属。至卅三年夏,倭寇侵犯茶陵,谱牒随之逃避,不毁的危机不绝如缕,至一九五〇年,始将草谱在原乡付刊,十余载编纂之工,于斯告竣。(以下落款者为总编纂史青、编辑者和校对者共11人,略)
收藏该谱的励双杰先生认为,该首序“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家谱论文”。[3]但“不错”处表现在哪里?励先生未能指明。
结合全谱细读序文后,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共即将在全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薛史青等对此不会有什么了解,但他们已经敏感意识到,这一制度与族谱反映了不同的价值体系,两者最终可能无法兼容。所谓“族谱会消灭啦”云云,既是“或谓者”(有人说)不明所以的传言,也是经历过革命运动、对中共纲领略有所知者的担忧。细品上下文语境,似乎在整体上还未进至“恐慌”的程度,故可称其为“薛氏困惑”。在1950年,由于新制的政治内含、覆盖范围、实现步骤、与传统间具体的理论分歧和功能区隔,即便在党和政府层面也处在探索摸索和有待逐步明确的阶段,对于生活在中央苏区的一个具有一定社科知识和相当政治敏感度的老乡绅(4)薛史青:《闽派河东薛氏八省联修崇本族谱付刊首先的一段话》自称:“二十三世嗣孙总纂校七一老人史青。”第4页。以下简称“薛氏《一段话》”。(可惜不知道领衔者薛史青的人生轨迹)来说,提出“薛氏困惑”,采取“唯唯、然然”,不置可否、不持定论的态度,不仅不奇怪,而且更合乎情理。当然,薛史青们复杂忐忑的心情,已经跃然纸上。
第二,“社会主义不久要临到”“社会主义势必降临”一类断言,显然不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农村居民普遍达到的认识。在导致薛史青等人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已有迫在眉睫之感的诸因素中,上杭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拥有的特殊地位,可能构成了一定的外部氛围,上杭县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乡古田村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位于上杭县西北部才溪区上才溪乡和下才溪乡,是毛泽东1933年11月下旬进行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之地。这一调查是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5)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高级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内部文件),1961年,第2-3页。进行的一系列农村调查之一,是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也是上杭县人民可以引以为傲的光荣。薛史青曾戏称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金圆券是“化学性的”货币,(6)薛氏《一段话》,第4页。也反映了他较高的政治觉悟。
第三,面对未来不确定的族谱生存环境,薛史青等虽感困惑,却不消极,更未坠入宿命。他们通过从理论上确定新制与传统之间不同的政治目标,营建出各司其职、各擅所长的互补局面。作为新制,社会主义有领导的动机性和创造制度的事业,不言而喻将居于掌控现实、设计未来的主流地位,而作为民族传统之一的族谱,“则与历史同,仅记载过去事迹而已”,它的存在,不仅与现实和未来绝无冲突,而且“其宗旨”“其实质”还是“国史的细胞,是民族实录的基础……国家信史的来源”,几乎可以与国家建立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所谓“昭褒贬之荣辱”)同构。以此化解“薛氏困惑”,其用心之良苦,可以理解。
薛史青等所说的国、族关系格局,源自宋代苏洵、明代方孝孺、清代章学诚等儒学理论家奠定的基本原则,清宣统三年(1911)程宗宜主修《绩溪仁里程世禄堂世系谱》的序言:“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史寓褒贬,而谱则以纪源流”(7)转引自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页。,更可视为首序的直接范本。但实际上,按照现代国家理论,如此阐释国史与家谱的关系是难以成立的。问题不在于“国”“族”分别代表的人群共同体之大小,而是支撑着这两个历史范畴的不同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8)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旧的氏族公社则是“由血缘关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6页。如果在“血缘关系”后加上“世系关系和婚姻关系”,将更符合中国传统宗族的历史规定际。正是这些迥异的原则和方式,决定了“国”“族”之间在大部分时空内不可能形成细胞、基础和来源的关系,虽然不存在前者“消灭”后者的问题,但经过限制生存范围、消解大部功能的过渡阶段,促使宗族演变为一种非强制性的同姓俱乐部形式,则是一般宗族可被预见到的最合理的命运。当然,这绝不影响民间知识人尤其是宗族文化信仰者对“国”“族”间形成和谐兼容格局始终抱有的想象和憧憬。
第四,除了为国—族寻找兼容互补的理论依据外,薛史青等还以“追木本、溯水源、详迁移、考世系”“知宗派之盛衰”等文辞,细致概括族谱的实践特征。(9)“族谱一书,为姓氏的血统记载,为世系的溯本追源,为迁徙的地址实录,实为民族精神感召的结晶。……姓氏为民族精神的源泉,为民族主义的基础,为民族团结的磐石。”参见薛氏《一段话》。这既是族谱体现的文本逻辑和框架,也是编谱遵循的操作路径和标准,更是族谱存在合理性的充分自证。换言之,族谱欲实现“其宗旨”“其实质”的前提和被国史兼容的资格,必须要按照上述逻辑、框架、路径、标准,把族谱编成一部可得旁证的信史,这已经不是一般性的学术要求,而是根本性的生存要求。对于迁徙无常且无系统资料积累的基层宗族来说,这显然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读者若据此来核查和评定薛史青的总纂成果,对薛氏族谱也将形成不小的考验。
二
首序涉及的上杭薛氏族史内容不多,非薛氏读者若要对首序在世系学上的努力作出评价,还需利用首册所收各时期谱序及相关地方文献。
(一)上杭薛氏世系
首序:“闽派启祖一脉厚、鼎、闰三房”,“闰”或为“闺”之误。“闽派启祖”,指薛氏迁闽始祖薛伯启(谱行三十六郎),南宋宁宗嘉定末年(1220年前后)偕弟薛伯肇,“由闽省宅漳州之钱塘……又舍钱塘移汀州之宁化,居不数年……兄弟离散,各自逃生。伯肇公逃往潮州府海阳县,吾祖伯启公避难奔上杭,游乡相宅,绍定庚寅秋始开乡名河坑。”(10)明正德十二年(1517)《杭川薛氏族谱源流序》,第4页。“漳州之钱塘”,指漳州府南靖县居仁里钱塘村,有钱塘陂、钱塘社等,见清乾隆八年(1743)《南靖县志》卷2《山川·水利附》、卷7《古迹·坊表》。“绍定庚寅”,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即被定为薛氏定居上杭之年,薛伯启则为上杭薛氏始迁祖(一世)。其后的世系传承是:四十三郎、四十四郎(二世);百三郎、百四郎、百五郎、百六郎(三世);千五、千六郎(四世);万七郎(五世);得贵、得华、汝贵、友梅(六世);五十(七世);荣华、荣通(八世);厚、盛、端、鼎、闺、鑑(九世)。(11)清顺治十六年(1659)《杭川薛氏编修崇本族谱序》,第7页。“盛、端、鑑三房传及十三世而失传,独厚、鼎、闺三房,丁粮殷盛,世世同房籍,共烝尝,和好无间。”(12)清雍正五年(1727)《杭川薛氏续修崇本族谱序》,第12页。上杭薛氏三房的直、旁系渊源皆在于此。
(二)迁杭始居地
首序中未涉及具体地名,前引明正德十二年《源流序》有“始开乡名河坑”;清顺治十六年《族谱序》续称“开乡河坑,今改名豪康”(13)清顺治十六年(1659)《杭川薛氏编修崇本族谱序》,第7页。,此后的有关文献均称薛氏始居地为“豪康”。如雍正五年《族谱序》称伯启公“卜居豪康”(14)清雍正五年(1727)《杭川薛氏续修崇本族谱序》,第11页。;晚清赣县教谕李孝澍《薛氏成盛户社背家谱原序》称薛氏“郡系河东,立基福建上杭豪康”(15)李孝澍:《薛氏成盛户社背家谱原序》,第17页。;民国二十八年(1939)《上杭县志》记录上杭县105个姓氏,(16)“旧志于氏族未别为编,今特广为谘访,集成此志,依字画多少为先后,得一百零三姓,其旧有而今无者二姓,并附载焉。”参见张汉修、丘复纂:民国二十八年(1939)《上杭县志》卷8《氏族志·序》(华其志纂),2004年唐鉴荣校点本,第170页。以下简称“民国《县志》”。其中河东郡薛氏,世居“县南豪康乡”(17)民国《县志》卷8《氏族志·薛氏》,2004年,第185页。;民国三十一年(1942)《闽派河东薛氏八省联修崇本族谱新序》称伯启公“立基豪康”(18)民国三十一年(1942)《闽派河东薛氏八省联修崇本族谱新序》,第4页。等。按清顺治十六年《族谱序》作者薛应吉(即良璧公)的解释:
河坑改名豪康者,非无因也。当明、清鼎革之交,四乡俱为张恩选所胁从,惟我一乡,智出人表,筑寨独先,创造制坚,地利人和,守御有方,矢不屈贼,反导上灭贼,能自豪强,全获安康。聚住九年,平寇归上,始筑围下山,因名之焉。(19)清雍正五年(1727)《杭川薛氏续修崇本族谱序》,第11页。民国《县志》卷9《人物志》:“薛应吉,字良璧,来苏里豪康乡人。邑庠生。明崇祯之季,山寇张恩选劫掠四乡,应吉父被执,奔赴赎回,乃矢志歼贼。”
将“河坑”改为“豪康”一事与英雄传说勾连,薛应吉等上杭薛姓人会信,而我等外地外姓人可能就不信。在上杭县的地名记录中,县治以南的“豪康”不仅称“河坑”,还称“豪坑”(20)该村清初属来苏里,见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上杭县志》卷1《区域志·里图》来苏里属村,爱如生数据库“中国方志库”,第23页。民国二十五年(1936)属第一区龙文乡,建国初属来苏区,1958年公社化时属下都公社,1965年并入中都公社联河生产大队,1968年划为中都公社“河坑”大队。1986年6月中都乡划出包括“豪康”在内的11个村增设下都乡,村名又称“豪坑”。参见《县志》卷1《建置》第二章《行政区划》,1993年,第73页。。之所以会在地名用字的选择上显出以上特点,既与上杭客家话“豪”谐音“河”、“康”谐音“坑”有关,又与客家话的特义字和谐音雅化字有关。这在上杭县表现得相当普遍。(21)“泮境公社大队自然村名称”:“院康”曾称“院坑”,“元康”曾称“严坑”;对“上早康”的标音为shàng zǎo kēng,或写作“上早坑”。《上杭县地名录》,福建省上杭县地名办公室,1980年,第33、56页。另外,稔田公社“南坑”大队被改为“南康”,理由是“与南阳公社南坑大队同名,改坑为康(谐音)。”参见《上杭县地名录》,福建省上杭县地名办公室,1980年,第139页。据上杭县地名办公室池粤松介绍,在上杭县客家话的特义字中,“坑”为山涧,读kāng,“康”(kāng)则是对“坑”的雅化;因此,“豪康”就是“河坑”的谐音雅化。(22)池粤松:《漫谈客家话地名》,《上杭县地名录》,福建省上杭县地名办公室,1980年,第213-215页。如此看来,“能自豪强,全获安康”的英雄传说未必真实,很难被作为“国史的细胞”。
(三)薛氏郡望及联宗基础
如《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谱名所示,该谱是以“河东”为郡望的一部薛氏联宗谱。河东郡是始置于秦朝的古郡,下辖安邑、猗氏、解、汾阴、闻喜等24县,(23)《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4年,第1550页。西汉以后泛指晋西、豫北、皖北部分区域。河东薛氏自南北朝以来一直是河东郡望族,也是薛氏的主干之一。(24)“薛……出河东、新蔡、沛国、高平四望。”参见陈彭年等:《广韵》卷5《入声·十七薛》。李学勤:《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第59册《韵书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薛氏迁闽始祖据称是南朝陈朝的光禄大夫薛贺(字履端),(25)“迨梁天监中,光禄公号贺,始迁于闽,闽之有薛氏自兹始。”参见元至正十一年《河东薛氏廉村族谱源流集》,第2页。入闽时间大约在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
民国《县志》称:“吾杭多聚族而居,谱牒世系井然秩然。又各建宗祠,绵亘街衢以百计。且有一姓支派、郡望不同,别立支祠多处者”(26)民国《县志》卷8《氏族志·序》,2004年,第170页。。“且有一姓支派、郡望不同”云云,即说明上杭宗族一旦进行联宗活动,其参与者的地域范围和世系认同很容易具有拟制性质,这一点正是明清以来华南宗族联宗的普遍特征之一。上杭薛氏的联宗是以薛伯启、薛伯肇兄弟的真实世系为依据,以上杭本县、福建本省为基础,兼及有文献记录的相邻诸省薛氏,亦如首序所称,该次联宗的范围是“散居于川黔滇桂湘赣闽粤八省宗族”,所以整体上的拟制程度并不显著(或存有个别拟制细节)。
“八省宗族”中参与联宗的薛氏族人大致有以下几支:
1.福建上杭县薛氏,源自上杭始迁祖薛伯启。主体为豪康薛氏第八世荣华公之子厚、鼎、闺三房,分别立基于上杭县胜运里、来苏里、古田里。(27)清雍正五年《杭川薛氏续修崇本族谱序》,第12页。“胜运里,县东南,宋胜运乡。明初编户十六图,后省五。成化十四年分二图隶永定,存图九。弘治五年增一。嘉靖十一年又增一。今存图十一。”安乡,清初胜运里属村。清白岭俗名石灰岭,清初古田里属村,“古田里,县东,宋古田里。明初编户七图,后省二。嘉靖十一年又省一,今存图四。”来苏里,“来苏里,县南,宋来苏团。明编户四图,今仍统图四。”高寨岭,清初胜运里属村,“高寨岭,在县东十五里,路通安乡、卢丰等处。”参见清康熙二十六年《上杭县志》卷1《区域志·里图》,第22、23、38、41页。
2.福建福安县薛氏,源自迁闽始祖薛贺。至其子薛许时,任陈州司户,定居福安县长溪廉村。(28)“贺公为中散大夫,徙于闽之晋安郡(今泉州),温麻西里孝义乡也。其子许公,署陈州司户,善明地理,相宅于长溪之廉村。”薛景腾:《溪南薛氏族谱源流集》序,第3页。关于长溪廉村,“廉村薛氏”:“梁天监中,光禄大夫薛贺始迁于闽。六世孙令之……避城山,即长溪之廉村也。其后子孙居廉村、高岑,与徙邑之黄澜者各建祠,祀令之为始祖。”参见光绪《福安县志》卷终《氏族》,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412页。又见上图《总目·河东郡廉水薛氏宗谱·提要》(1962年木活字本,王超秋等编纂)。万历《福安县志》(9卷)无《氏族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其后或居州域,或居宁德,或居福宁殷土……或居汀州之上杭”(29)元至正十一年《河东薛氏廉村族谱源流集》,第3页。。
3.江西安远县薛氏,分别源自薛伯启、薛伯肇兄弟。伯启公六世孙东一郎(讳旭日、号东陞),为安远开基始祖,(30)“定居于濂江乡等地的薛姓,望出河东(今山西省沁水县和霍山县一带),自福建省上杭县徙入安远县”,其流动形式为“倒迁型”。 参见江西安远县志编纂委员会:《安远县志》第三篇《人口》,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81页。“散处于虔安”(31)“隋开皇中(公元581年至600年),安远县并入雩都县。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南康郡为虔州。县境隶属虔州。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分雩都县南三乡并信丰县一里,再置安远县,属虔州。……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改虔州为赣州,县属赣州。”参见江西安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远县志》第一篇《建置》,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30-31页。。伯肇公后裔东六郎为安远开基始祖。首序称“接到江西安远县肇、启二房合修刊本族谱”,即因有此世系渊源。两支薛氏“共建薛祠,咸奉京公为上祖,立在薛祠上座,伯肇伯启居次座,各立始祖为一世,族谱亦是合修”(32)薛氏《一段话》,第2页。。京公,薛京,据说为唐末大学士,奉旨南征后,定居于福建漳州钱塘,被尊为薛氏入闽开基始祖。(33)http://www.zupulu.com/zupu.phpt=l&z=34515。另有记载则称其为南宋人。(34)“薛京,字宗汴,诏安人,与郑柔俱师事陈景肃。肃与秦桧忤,辞知台州,京亦乞归省。桧以其为景肃党,啣之。归与吴、郑、诸杨讲学渐山九侯间,赋诗自乐。终桧之世,屏迹不仕。”参见光绪《漳州府志》卷28《人物一·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77页。待考。
4.江西泰和县薛氏,为上杭薛氏始祖伯启第八世荣通公后裔。荣通子永安,永安长子薛福,居江西泰和县高行乡里南坑。闺房十三世,徙居泰和县木古凹村。首序所谓“又知荣通公叔祖一脉移居泰和”,即指此。
5.江西赣县薛氏,为上杭薛氏第八世荣通公子永安次子薛贵后裔,居江西赣县大由乡西水一都薛坝里。首序所谓“贵公叔祖一脉久年隔绝于赣大由乡,复得联属”,即指此。
6.江西南康县薛氏,为上杭薛氏第八世荣华公之子薛厚后裔,十五世薛耀、十七世薛克友后裔,居江西南康县潭口堡下坝甲村头坊兴隆坝。
7.广东信宜县薛氏,为上杭薛氏第八世荣华公之子薛闺后裔,十八世薛宏远后裔,居广东高州府信宜县新图马贵堡排钱洞心聚田村。二十世徙居信宜县白龙堡青云上乡,十八世徙居信宜县四区罗定罗镜分界墟木栏。散居于潮揭。(35)薛氏《一段话》,第3页。
8.广东韶州英德薛氏,为上杭始迁祖伯启公第六世得贵后裔。(36)顺治十六年《杭川薛氏编修崇本族谱序》,第7页。
9.惠州兴宁薛氏,为上杭始迁祖伯启公第六世汝贵后裔。(37)顺治十六年《杭川薛氏编修崇本族谱序》,第7页。
另有广东何猪村薛氏,为上杭始迁祖伯启公第三世百六后裔。(38)清雍正五年《杭川薛氏续修崇本族谱序》,第12页。
10.广西荔浦县修仁镇薛氏,为上杭薛氏第八世荣华公之子闺房后裔,二十三世扶光徙居广西荔浦县修仁镇、建陵镇。(39)薛氏《一段话》,第3页。
11.云南永昌薛氏,为唐代补阙公后裔。(40)元至正十一年《河东薛氏廉村族谱源流集》,第2页。云南永昌,不知何指。若指位于云南省西部始于东汉顺帝永和年间的古永昌郡(详见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下》第十章《益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41-942页),相隔时间及地理位置似又太远。待考。
以上为对福建上杭、福建福安、江西安远、江西泰和、江西赣县、江西南康、广东信宜、广东英德、广东兴宁、广西荔浦、云南永昌诸薛氏之间大致的世系勾连,其中尚存模糊之处,因资料所限,难以一一细辨。
首序及各序在指认薛氏联宗涉及的范围时存在一些问题,如:
1.首序指出参与联宗者包含了“川黔滇桂湘赣闽粤八省宗族”,而各序中并没有川、湘诸薛。
2.首序没有将《河东薛氏廉村族谱源流集》认真关注过的浙江诸薛(41)“其后……或徙温州莆田,或居平阳之南潮,或居永嘉之梯云,或居丽水之锦山。”元至正十一年《河东薛氏廉村族谱源流集》,第2页。“南潮”或为平阳县“南湖”乡之误。“始祖荣华,明代自福建漳州府迁居浙江平阳县北港四十一都南岙村(今属南湖乡)。”见《浙江家谱总目提要·廉水薛氏宗谱》(1926年木活字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纳入参与联宗者中。
3.首序及各序均未涉及原属福建、今属台湾地区的薛氏,这显然是因为1950年前后两岸已隔绝的缘故,但部分薛氏迁台的时间一般都可追溯至清代,至少是民国,如果联宗动员的覆盖面再大一些的话,应该是可以有所涉及的。如台湾桃园、新竹、台北县三重市薛氏的《薛氏族谱》(1974年薛武兴写本):“始祖,三十六郎号伯启,迁台:昌桂、英义(清)”;新竹湖口乡薛氏《湖口薛氏族谱》(1976年薛丁写本):“始祖,三十六郎号伯启,迁台:时赞(清)”;台中县沙鹿镇、新竹县湖口乡薛氏《薛家家谱》(1985年写本):“始祖,三十六郎伯启,迁台:昌通、昌柱等(清)”(42)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摄影:《台湾私藏家族及地方历史资料目录》,成文出版社,2007年,第866-867页。。至于上图《总目》著录的528-0062[福建金门]《金门薛氏族谱》(1991年铅印本),始祖令之(即前文提及的薛贺六世孙、唐代补阙公),始迁祖薛成济迁居金门的时间更是早至元代。
虽然尚存部分遗憾,但通过首序及首册各序表现出来的1951年福建上杭《河东薛氏联修崇本族谱》的整体质量,已经达到了民间书写某一族群历史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准。据此而言,薛史青等人希望实现的族谱存在合理性自证,应该说大体做到了。
三
然而,“合理性自证”的完成,不过表现了实现自我期许的主观能动,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消解“社会主义不久要临到,族谱会消灭啦”这一导致并深刻缠绕薛史青们的趋势性困惑。因为有机会打开这一涉及两端的困惑之锁的钥匙,一把在宗族手里,另一把则在“有领导的动机性和创造制度的事业”的“社会主义”手里。仅有一把钥匙,哪怕是一把“好钥匙”,也是不够的。
就一般的判断而言,在中国,汉人宗族以及其他一些具有血缘—世系性质的团体(如宗亲会等),在现代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与作用呈递减趋势这一点应该不会和世界其他地区出现根本的区别。笔者和谢维扬教授20多年前所作江西泰和农村调查的一个重要结论,则是确定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起点,即:“中国社会中传统宗族组织的发展历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应该说已经基本终结。在这之后存在的以及近年来恢复的宗族组织,无论是其结构还是功能,严格地说都已经不是旧宗族形态的简单重复和翻版,而应被看成传统宗族转型过程中一个阶段的产物。”[4]以新中国“开国大典”之日为新、旧族谱划界的主要理由也在于此。这比主要从“新政治与村落家族文化的关系”[5]角度进行的理论归纳,更富于历史感,也可使研究对象获得一个便于操作的鉴定标准。
但问题是,谱牒本身既非政治性文件,也非宣传类作品。作为宗族文化的文字表现形态,它是对基层社会中某一特定宗族的起源、世系、聚居、迁徙、人口、规则状况的记录,可归入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下的“亚文化”(sub-culture)范畴,(43)亚当·库珀:《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亚文化群》,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773页。新中国建国以来出现的宗族、族谱无疑是“亚文化群”现象,但整体上肯定不属于“反主流亚文化群”。与发生在社会主流层面上的国体变动和政权更替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因此不会,也没有必要以响应“时代背景”的变迁作为证明自身合法性或合历史性的要素;换言之,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问世的新谱,虽然一定会顾及鼎革剧变给整个文化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但不会立刻对尚在建立过程中、具有与传统价值不同的新型意识形态定位的新政权、新制度作出实质性的反应,存在一个或长或短的观望期、适应期和过渡期是合乎常理的。既然人们会选择性继承传统,新社会的到来又必然经历缓慢阵痛,新谱所具之各类“新”特征,因此也会有一个逐渐成型和积累的过程。
薛史青等人应该意识到新制度建立后宗族文化将居于“亚文化”地位,否则就不会以“或谓”的形式去传播这样一个深刻的、富有历史感的困惑,虽然总的态度是没有把握的“唯唯、然然”。这不仅是基于“五四”新文化的教育和社会革命理论的影响,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的外部环境使然。就在撰写首序的1951年,上杭县于1月10日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严厉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1月中旬开始,又分批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对保有土地革命果实的地区,按《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规定,进行必要的土地调整,确定地权,发展生产。(44)《县志·大事记》,1993年,第31-32页。从上杭县党政领导对工作的部署重点来看,显然还没有把提倡和实践编谱建祠一类传统宗族活动的人员看作必须实施专政的政治异己分子,但有一个结果却是可以预料到的,即他们在新制稳定后必将成为基层社会的“边缘人”。
对于这样的结果,薛史青们固然不会公开表示反对,但心中掀起波澜则是可以肯定的。宗族代表人物一向有很高的自我期许,坚信自己不是国家—政府—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的“外人”,更不是敌人、仇人,而是友人、同人、调人。在迎接新时代的日子里,他们赋予新编族谱的最高目标也是如此。有一段文字坦率和急切地表露了宗族成员希望作为一支有组织的重要力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愿望。《家规遗训》之七《诚追远》称:
宗祠祖庙,于岁初合族团聚时,集议全年生产计划,如何发展工业,赶上新时代的趋势。年终合族团聚时,检讨全年各业结束的得失,急图改正,以求生存。适合天择条件,走入人民政府行政大纲范围,免受淘汰。从前一切虚文虚礼,无补于事,一律铲除洗涤之。(45)《家规遗训》七条,第4页“人民政府行政大纲”,或指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尽管不是一部正式宪法,但内容上和法律效力上都具有国家宪法的特征,是建国初期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前进的政治基础和战斗纲领。
面对编谱者通过上述族内训诫的形式,向新社会领导者婉转表达的忠心,所有族外听者、族外读者会怎么想?除了嘲之为“你们总是不把自己当外人”,还能怎样?对于研究者而言,如果“外人”做出这样的表态,也不是新制度生产者和新社会组织者不领情,而是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可能为宗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留出这样的空间。如前文所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国”“族”间根本的区别并不是各自所代表的人群共同体的大小,而是支撑着这两个历史范畴的迥异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加上“宗祠祖庙”的经济基础和人群基础正经历着土地改革、区划调整、户口管制的猛烈冲击,在这之后将被“一律铲除洗涤”的,就绝不止“从前一切虚文虚礼”,而是“宗祠祖庙”及宗族本身,也就是说,“薛氏困惑”在一定条件下是会成为现实的。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合作化、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社教(四清)、“文革”等一系列深刻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以来,民间宗族被戴上坏人、恶人、敌人、仇人帽子的过程,人们早已熟知;即便在八九十年代,当宗族已经重归社会,逐渐增添了友人、好人、善人、能人的色彩后,宗族作为国家—政府—主流文化总体上的“外人”,仍是其基本的“底色”。比如1993年《县志》有关章节的作者就在总结县内宗族联宗的特点时,断言其目的只是“为了发展宗族势力”,或“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46)“为了发展宗族势力,常不顾地区界线,与县内外族众‘合族’,或者应邀参与县外同姓‘联宗’活动……‘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联宗活动又有所萌发,在一些乡镇,同宗本家又联合起来,共商修祖坟、扫墓、编修族谱以及协调处理族中纠纷等事。”《县志》卷31《风俗》,1993:831。在此10多年前的1982年2月上杭县政府曾发布《关于树新风破旧俗的布告》(杭政[1982]8号),其第四条明确规定:“严禁修祠建庙(包括建神坛、‘社公’)迎神打醮、联宗祭祖、聚众赌博等非法活动”参见《县志》附录二《文件辑录》,1993年,第1006页。,没有在准确理解联宗原理的基础上,肯定联宗发起者、参与者对历史渊源与文化根源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如有可能,最好删去《家规遗训》之七《诚追远》,免得麻烦。
在当代中国,国家与宗族、社会公共事务与宗族参与之间,至今没有、也不会在制度性和法理性层面发生前者对后者明确的兼容或承认,这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内的现代国家理论的基本逻辑,也是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于宗族文化的爱好者、坚守者而言,宗族与国家—政府“正式结构”的相处原则,最成功、最主动的选择,应该脱离对这两个层面不切实际的追求,改以非强制性同姓俱乐部成员的身份,在认同“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国民伦理的同时,遵循“毕竟是外人”的政治规训。乐观地说,经过70多年中国全社会正反经验的积累,党和政府已经在除政治、法律以外的众多领域为两者形成恰当的关系模式留下了必要的调适空间;换言之,在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只要宗族自觉遵守“外人”的限阈,就不会成为“反主流亚文化群”,而可以是,或更可能是友好的、守分际的“亚文化群”。如果这样,“薛氏困惑”应该就能够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