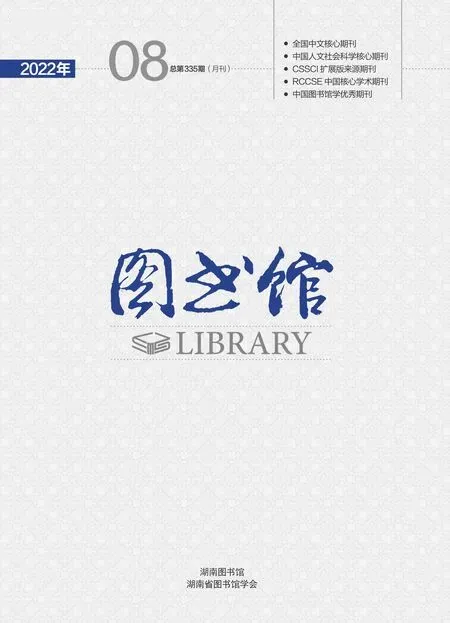试辨“目录之学昉乎史”
——古典目录学与史学的思想迥异及会通*
孙 墨
(1.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哈尔滨 150080;2.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哈尔滨 150080)
近代以降,许多中国传统学科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及学科价值受“西学东渐”之风影响而日趋衰微并渐有相互拆合之势。古典目录学业已从昔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1]之诸科求学门径必叩的“显学”,发展至如今面临难守自身畛域之危,盖因其对传统多类具体学科均具有考辨的学术史价值,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渊源甚深,而被一些学者将其学科意义及价值消弭混淆,甚至有意消亡古典目录学之学科,使之拆解为各专科目录学,如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文学文献目录学等,并分别划进其所归专业科目供专科学习旁参之用。此说法又以与古典目录学渊薮最深的史学为最,近代学者张尔田在讲述目录学起源时就有“目录之学何昉乎,昉乎史”[2]的结论。古典目录学的传统学术考辨特点与治史任务庶几相似,两千年来各朝代名家治史大都具有古典目录学的深厚功底,其将学术考辨方法运用于考史上,使得古典目录学的文化价值只显现其为史学提供学术文献的内容梗概与参考价值的“考辨”手段,而忽略了清人章学诚所谓的“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3]7的“考辨”真义与吸收、整序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道”学科理想。由于学科本身殊异,文章将对史学与古典目录学易纠缠混淆的学科思想范式、研究方法与学术目的进行比较析辨,旨在呈现两者的会通与迥异之处,从而在学科认知上突显古典目录学在传统文化的接受与表达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唯一性,以期打破古典目录学之史学范式研究视角,彰显古典目录学的价值意义并非只还原历史,而是更强调对文化意识的整序与重建,使之摆脱自身即将成为一门过时迂腐且自闭于学术文化之外的考证之学,及寄其他科目之下的旁参引目之学的衰败定位,让其能够在现代学术文化氛围中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并起到独特的学术助推作用,重获往日“学子所重,几埒国学”的学科地位。
1 古典目录学与史学之学术渊薮
古今中外的目录体系基础都是对一批相关文献进行著录及编排组织次序,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客体与起步工作也是对具体文献的描述与标引。自夏朝起便有人将国事、农耕、占卜、狩猎等政治行为记录成文字并汇总,这部分人既称史又称巫。自殷商后两者出现分工,史官的主要职责是编撰与管理文献,《礼记·曲礼》中有句“史载笔”[4],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六《释史》中提出“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即为掌书之官”[5],可知史官便是最早的对文献享有垄断权力的官员。《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6]”,说明外史在管理文献的同时有将文献分类并编写书名目录通告各地的职能,此即有古典目录学发源于史官甚而产生“诸子百家之学,莫不出乎史官”的历史观论断。而后因汉代书目类著作甚少,《七略》《汉书·艺文志》均不设目录类,东汉班固对《七略》删冗提要制成《艺文志》并将其列为《汉书》中的一卷,自此《艺文志》成为《汉书》的一部分。后世对于《汉书》的研究自然也包括对史志目录的研究,反之,目录学也成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方面。
《七略》将史类书籍置于《六艺略》的春秋类后,荀勖、李充虽设立史部,但均未见类名与细目,王俭的《七志》则又将史书附于经典志、小学之后。南朝萧梁时期,阮孝绪仿四部法而设列“纪传”类,刘知几在《史通》中释“纪传”为“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故阮孝绪以纪与传概括史书之体例,进一步将纪传录分为国史、注历等十二类,即史部于经典录之后列为第二。这是史学分类的创举,阮孝绪首次将“簿录”即包括《七略》在内的各种“名簿”和“官目”共计36 种列属于纪传录,此为《隋书·经籍志》设“簿录”于史部之先河。后《隋志》列“略录,以纪史策条目”入史部,其对类目的界定被收入《唐六典》卷十中,为开元年间编目人员所参,亦被收入《旧唐书·经籍志》总序,《旧唐志》分类体系以《隋志》为本,更“薄录”为“目录”也入史部,被北宋诸家目录如《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所采用,后世也多以此例绵延。宋人郑樵在《通志二十略》中以“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7]的通史观视域总结其目录学思想,清人章学诚也在《校雠通义》中阐释了其古典目录学的思想体系,已成为近代以前目录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校雠学本为史学之从属,章学诚论述“文史义例,校雠心法”的主要成果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皆为史学类著作,可见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思想理论在历史上长期隐于不断繁盛的史学名下,目录学的基本定位以及对于目录学科的接受视角也被惯性预设成一个前提:以史学为顶点向下发源。另如郑樵、刘知几、章学诚等既为史学理论名家又是古典目录学家,其重要作品所运用之治学手段如“考辨”“互著”等,常使后学之辈对两门学科的方法论产生混淆,进而放大古典目录学重分类与解题而轻编目与索引的特点,并将其等同于学术史,然而对两门学科的学科本质与学科方向上的独特价值都难以深究。
2 古典目录学与史学思想范式的迥异与会通
2.1 “通”之会通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有“学不专家”的治学传训,如郑樵、章学诚、马端临、黄永年等具有古典目录学与史学知识的通才名家,其成果的形成源自目录学思想范式与史学思想范式的相互交融与促进汇通,是因两种有着天然学术血缘基因的学科思维范式之间的规范制约和转换指导,才汇聚成独到且自成体系的思想见解与文献脉络。如马端临基于通史观点形成的史学思维范式,在其目录学杰作《文献通考·经籍考》中表达为“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8],其著作既包含水平线上共时性的静态融会,又具有古今维度的历时性动态关联的架构特点。郑樵曾极力抨击班固易《史记》纪传体的通史体例,反对割裂历史、断代独立而成的《汉书》,其上下融汇的“通史”史学观范式在其目录学名著《通志》中表现为通记历朝各代藏书,不仅对其“存续”注目,也详考其“亡佚”。马端临受郑氏“通史”观范式导引,觉察到《通志》中的纵通架构只局限于对图书形式的表述,郑氏基于对目录提要“文繁无用”的评价将其进行价值上的忽略舍弃,而马氏进一步将史学与目录学的思维范式交叉延伸到对图书内容的融通,他重视汇辑材料并加注按语组成提要以揭示所记书目的内容。可见与“断代”观相异的“通史”观史学范式明显对各史料间纵向上的渗透联系更为关注,而目录学的思维范式也正是被“通史”观史学范式影响才交叉生成新的目录形式,这样体现“通史”观史学思维范式的目录形式,其文献类例与内容具有历时性的上下相因、详明贯通之特点,能在文献与学术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从而从时间演化的角度规范文献背后纷繁交叉的学术门类,以揭示文献中隐含的学术历时性秩序,这也是目录学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的基本理念保证。
古典目录学与史学学科思维范式的相互交叉作用,使得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要思想更加凸显,以“辨、考”为宗旨的史学范式在目录学研究中得以拓展。“目录学”一词最早由清藏书家耿文光在其著作《目录学》中提出,该著作除在“序言”“凡例”部分论及编目方法外,内容尽是一部课读书目。梁启超晚年唯目录学是务,其撰写了《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与《中国图书学大辞典·簿录之部》两本颇具影响力的目录学巨著,前者总结佛经目录所遗文献以填补空白,后者以史志为主干引书目著作为词条,进而依次排列并详附考证为一部书目简史。之后承此清代考据遗风兼继学术考辨的价值观念,刘纪泽、余嘉锡、周贞亮等从古典书目的宗旨、体例、类例沿革等方面发微,进而确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根本思想。
2.2 “通”之迥异
史学思维范式之“会通”观可早溯至《礼记·经解》所载孔子云“疏通知远,《书》教也”,白寿彝将“疏通知远”解释为先秦人运用历史知识的一种表现形式,以“疏通”为方法论途径,“知远”为目的论指向。知史、著史若要做到原始察终、贯通古今则必须要有融会贯通的“通”式思维[9],此处的“通”即有通识思想的含义。后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的“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10]便是通识的理性自觉。刘知几在《史通·鉴识》中提出:“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11], 这里的“识有通塞”也是要求史家具备通识含义里的“通”观思维范式,只有做到此点才能“鉴有定识、铨核得中”。需要说明的是,史学思维范式的“通”并非一种单纯尊崇通史体例而轻忽断代为史的思维导向,而是重在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并贯穿严谨的连续构建逻辑。如颜师古评断代名著《汉书》的“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泛而言之,尽在《汉书》耳”,正是注重《汉书》的“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12]的史学“通”观思维范式。这一思维范式的反面是对史料“碎片化”的断章取义,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无法脱离历史环境与其他历史现象进行单独研究,这种割裂的研究无法达到学术认识的目的。史学思维范式的“通”就是强调将每一种历史现象都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中去考察认识,使史料能够在时空上相互贯通联系进而发挥以史明道的功用。
古典目录学的核心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余嘉锡言“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集、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13]。辨考的提出者章学诚在其核心作品《校雠通义》与《文史通义》中皆以“通”字点题,《文史通义·言公下》所云“昧者徒垂于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14]12及《校雠通义·汉志诸子》的“著录之书贵知原委,而又当善条其流别”[3]7,都可释古典目录学的“通”式思维范式重在书目源流于时间上的追溯与书目分类在空间上的正统。虽然古典目录学与史学的“通”式思维范式交叉表现在将文献内容在整体文化背景中以分类目录的形式予以映射,能够做到“观其类例,亦可知兵,况见其书乎”[15],然而古典目录学的“通”式思维更加侧重文献主体性内容间的起承分流 ,如《校雠通义》中的“至于卷次部目,篇第甲乙,虽按部就班,秩然不乱,实通关联之事,交济为功”[14]12,最终实现“辨、考”价值。《史记·自序》的序传,《七略》的叙录,《四库全书》的凡例、类序、按语等都旨在解决因书目分类而导致的知识被隔绝孤立,保证类别间的旁通关联,明晰整个知识文本的系统结构,以实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辨考”目的。
3 古典目录学与史学研究方法的迥异与会通
3.1 校勘之融通
古今学者对于校勘之学甚为重视并将其引为治史的基础研究方法,“校勘为读史先务, 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16],此之校勘古称校雠。刘向对校雠下过定义:“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17]而后这一概念迁延溯展至清朝又推进精化,戴震在《古经解钩沈序》中释校勘方法为“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又广览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18]。遂校雠之学有两大意义,一是订正沿袭讹误的求古意义,二是拾遗补阙改正误失的求是意义。校勘常被引为史学研究的基础方法是因为它能够对史料记载的谬误与不清之处匡得正确或接近正确的内容,如《后汉书·郑玄传》载玄著的《戒子书》中有句云“吾家旧贫,不为父母昆弟所容”,此句本身无甚谬误且文义疏解,然而郑玄于东汉末年以“敦品力学”闻名,何以闹到“不为父母昆弟所容”之地步?至清乾隆六十年,阮元赴高密郑玄故祠,以金代重刻唐史承节所撰碑文记引《戒子书》为勘材,才明原来《戒子书》中并无“不”字[19],陈鱣以黄丕烈处的元刊本《后汉书》为勘材,同证文中无“不”,于是史料疑窦清明。校勘对史料的旁证之功亦被史家所重视,清人吴光酉所辑《陆稼书先生年谱定本》的雍正刊本阙文数处,以它本为勘材相较发现所有缺文均与吕留良事迹相关,乃因文网周密而削去。阙文不补可见刊者深意,而清代文字狱之严酷史实也于此处得到佐证。
校勘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古典目录学的丰富与发展同样产生极深的影响,目录学著作在编制过程中可以根据校勘成果著录图书版本,惠泽后学,给予其求书问门的可靠依据。顾千里的《仪顾堂题跋》与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等目录学著作中,均大量出现运用校勘方法发现和纠正前人出现的谬误。如《四库全书总目》误信明人刻本,将王偁视为《东都事略》的作者而将原来的王称作伪,此后一切官私著作及刻书者均沿其谬误,以为著《东都事略》者为王偁。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以他人的成果作勘材,订正了提要的“以作称者为伪改”之误,用校勘方法体现了目录学著作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价值。
3.2 方法之分殊
校勘研究方法的正事实、通文字之作用确是对史料进行精深研究的必叩之门,也是史学治学的重要基础手段。校勘的核心内涵同古典目录学的终极旨求一样,都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于是便有学者将目录学作为校勘学的从属,以校勘为史学方法之源,故标举史学包含古典目录学,进而否定古典目录学单独存在的价值。校勘学在以考据学风为主流的清朝盛极一时,章学诚认为:“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20]张舜徽承郑、章诸说,主张以校雠大名而统目录小名,他说:“夫目录既由校雠而来,则称举大名,自足统其小号,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郑樵、章学诚深通斯旨,故郑氏为书以明群籍类例,章氏为书以辨学术流别,但以校雠标目,而不取目录立名,最为能见其大。”[21]然而郑、章此后诸说都旨在否定目录学之存在,各自学说中均是先为目录学赋予不完整的概念,后而自己加以驳论,实为混淆概念不足服人。
校雠之学主要是指校勘文字篇卷中的谬误,是整理史料文献工作的一道工序,不能涵盖整个过程。郑、章等学者强赋目录学以“书目之学”,“记其撰人之时代,分帙之簿翻”之特定界说,忽略目录治学整理篇次、校正文字、辨明学术、粗陈梗概、撰写书录的学术活动。诚然“书”是对全部治学活动的成果总结,不可因为史料通过校雠方法加工成为史学著作,便引校雠之学为史学的主要基础研究方法,如清代学者朱一新所言“校勘为读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尽于此”[22]。古典目录学作为具有多种研究方法及整套复杂工作程序的学科,必然在方法与程序上涉及若干相关学科,但不可因学科研究方法之融通而强下片面定义,混淆忽略学科间其他重要研究方法的殊别,进而否定学科的存在,何况中国古代目录工作大部分与校书工作和官修制度相关。因此对历朝有关校书的措施和所兴办事业的探讨与论述也是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方向之一,不可将其片面地限定于校勘之概念,应知校勘虽为目录学之先务,但目录之大端也不尽于此。
4 古典目录学与史学学术目的的迥异与会通
4.1 致用之同归
学术界在对史学学术目的的讨论中一直交织着对“为学问而学问”之求理目的与“经世致用”之求善目的的论辨。关于史学之治学目的,近代学人多承梁启超推崇的“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23]之求理目的,然而一味执着于考据、校雠与疑古辨伪等方法,便无法将史学放在历史环境中研究而体现其致用价值。只管求学而不问学问的经世价值,则会让史学研究丧失对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关照。不同于以物理客体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求理求真之学术目的,史学的研究目的不应止于钩沉辑佚地穷理求末,而应以经世致用为归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古典目录学曾在近代遭受到西方目录学的严重冲击,当时学者几乎都自觉将重精确、重形式的西方目录学作为古典目录学学术目的的最高参照范本。然而古典目录学的内涵与价值不能作为一种单纯的检索工具而被功能化的概念所涵盖,其学术目的也并非科学性的精确与效率。古典目录学在本质上处理了作为自为之物的人类社会文化秩序,其“道术精微,群言得失”的学术信仰与追求即是要在人生处事、社会伦常、政教文化等方面发挥价值。如自《庄子·天下篇》至《史记·自序》前,《易》在六经中的次序一直居于《春秋》之前的第五位,刘向父子将《易》作为“众经之源”与“道之源”,并在《七略》中将《易》提为六经之首。后南朝目录学家王俭作《七志》,将《孝经》居首而《易经》为次,这便是基于魏晋南北朝以孝悌治天下的社会政教风气所为,由此可见古典目录学的学术目的更着眼于其社会人文教化的功用。正如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在《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中指出的“于国史则熟研今日政教礼俗及其他各种现象之所由,明厥变迁而知其所以,识厥利害而知所兴革”[24],史学的学术目的应是在国家社会人伦教化中发挥“经世致用”的价值。古典目录学的学术目的亦是如此,直面为人、为学、为政之道并“致用”于整个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如“经、史、子、集”四分法便是一种社会政教策略,用来开示礼教上“尊经、重史、轻子、鄙集”的文化态度。
4.2 求真之分殊
古典目录学与史学在“致用”学术目的上的最大异趣便是主体性致用与求真性致用的分殊。史学的“致用”学术目的如果不加赋“求真”之限制,极其容易偏变为“滥用”。古今史学文献中某文某书通过滥用史料与违背史实真相的手段来实施个人政治或阶级目的的“今用”现象信手可拈,史学通过将既往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来论述过往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最终实现其“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而“致用”能够产生效用的前提是正确论述过往的历史进程。诚然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便是人类自身的社会活动与精神活动,无论是史料还是对史料的评述都无法脱离人的主观意识而将治史完全做到真实客观。不能忽视的是主观虽然可以使研究者违背真实的历史进程,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主观也能有意识地让研究更接近真实,所以史学“致用”学术目的的终极旨归是尽可能对当今社会发展产生最大价值的成果,同时保证著作成果最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况。古典目录学的“致用”学术目的是具有完全主体性而不加带 “求真”限制的,编纂目录的过程极为注重所辑文献主体的资治教化价值,如《隋书经籍志考证》所云:“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25]古典目录学的学术追求是通过书目分类体系来体现历代学术思想与政统教化的需求,进而建构学术理念观与人伦秩序观去指引求学问道的读书士子,如刘向父子的《七略》叙评《管子》言“务富国安民,道要言约,可以晓合经义”,论《晏子》言“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26],以管、晏刑名法术之学合于六经,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政教价值导向作用于读书士人进而致用于社会教化。古典目录学的“致用”学术目的殊然于史学对真实性与客观性的要求,它旨在通过目录学家的主观知识体系、分类规范与学术导向去塑造目录读者的文化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以实现《四库全书总目》序中所谓“钞录传观,用光文治”与“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的整体政教价值导向的社会效应。
5 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古典目录学近代境遇的本质是其从对古今天下文献进行时空覆盖的“要紧之学”转向为仅能面对近代之前经籍典献进行的“旁证之学”,古典目录学业已维持两千余年之久的中国文献秩序与其背后的学术规范,自此开始断裂崩塌。对此,多数学者归因有二:一是近代西学输入,四部之法已不能统筹世界多元文化学术;二是近代以降,中国从天下文明的中心转为世界文明的一隅,自身文明自然开始“新旧”断裂。然而自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以来,特别是章炳麟的“以经为史”观对近代史学做出了极富时代特色的创造性转化,构成了古典目录学在近代地位被消解的主因。
近代学人章炳麟在《国故论衡·原经》中提出:“经与史自为部,始晋荀勗为《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旧法。《七略》《太史公书》在‘《春秋》家’,其后东观、仁寿阁诸校书者,若班固、傅毅之伦,未有变革,讫汉世依以第录。”[27]可见章炳麟将古典目录学作为探求经学性质的起点,既然文献分类法始于《七略》而《艺文志》因袭,他便将《艺文志》中的《史记》附于《春秋》,且部类并无史部来证明汉代本无经史之分,并据此文献分类的客观事实得出结论:经即为史,史即是经。他延续此观点又进一步提出以“史学”的眼光与态度审视经部文献,这样一来不仅文以载道的“六经”成为“上世社会”的历史实录,甚至孔子亦破除了“圣人”光环而下阶成为了“历史人物”。不仅如此,孔子删削六经的历史功绩,也让其顺利完成了从文明立法的“圣人”到“史家”名相的转换。章炳麟的这一做法无疑直接导致了经学的溃亡,学术转型进入“以史为本”的时代。
众所周知,古典目录学一贯将经部置于整个书目体系的首位,史部、子部为之两翼,集部后之。每一类书或每一册书的具体整序过程都映射着“垂型千载,如日中天”的“经旨”政教人伦核心。经部居于首位所表现出的政教人伦权威经典的优越性,也是古典目录学成为“明道之要”与“学术之宗”的一大前提。反过来,经部的地位与意义发生根本性动摇与重构也会使古典目录学固有的精神纲领失去主体支撑。古典目录学对于包括经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吸纳与理解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可以说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就是认可古典目录学的现实意义。诚然,史学与古典目录学在思想范式与学术旨归上的渊薮极深,然而已形成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古典目录学要充分认识其自身畛域与作用,不能一味解构并抹杀其意义。
(来稿时间:2020 年9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