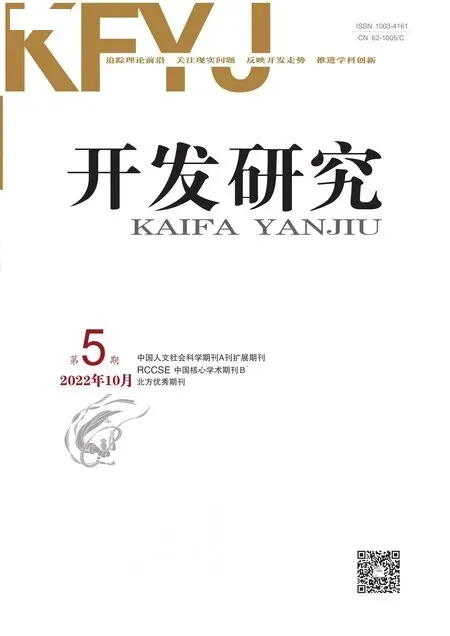中国产业与就业空间协调发展研究
赵 璐,刘释疑,2
(1.中国科学院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100190;2.中国科学院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9)
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其最终通过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来实现[1-2]。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制造业比农业、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这种收入差异促使劳动力由低收入部门向高收入部门转移[3]。1940年,英国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克拉克以配第的研究为基础,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产出资料进行了整理归纳,提出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再向第三产业转移[4]。1941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阐述了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各产业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认为在工业化后期特别是后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下降,服务部门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呈现上升趋势[5]。
我国正在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空间发展的产业与人口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我国的产业与就业结构协调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他们主要采用就业弹性、结构偏离度等方法探讨了全国或区域层面的产业与就业结构协调问题[1,6-9]。例如,孙晴等应用结构偏离度、就业弹性和比较劳动率等指标研究了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10];何景熙和何懿应用结构偏离度分析了1978—2010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及其与我国城市化率变动之间的关系[11];卫平等从协调性和冲击性视角对1978—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12];王阳等应用结构偏离度描述了1990—2020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失衡状况[13]。我国就业结构变动显著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虽然有学者开始关注区域产业与就业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例如牟宇峰运用重心方法和结构偏离度等方法从空间和结构两方面分析了1978—2009年长三角地区产业和就业演进及其耦合性[14];单良等基于省域层面运用协调系数刻画了1998—2015年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并用标准差椭圆方法分析了二者协调系数的动态演变[15],但是,目前尚未有研究基于城市层面从空间动态发展和空间格局协调性的视角全面分析我国产业空间与就业空间发展演化。而在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双重转型的关键时期[16],全面了解产业空间与就业空间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协调发展态势,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业资源合理配置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应用空间统计方法以及GIS空间分析方法,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结合全国维度产业和就业空间格局协调特征的宏观层面与城市维度产业和就业结构协同特征的微观层面,从空间发展的视角全面分析我国产业空间与就业空间发展过程及其空间协调发展演进态势,期望能为新时代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一、方法与数据
(一)基于标准差椭圆方法的空间格局协调性描述
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方法(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SDE)是标准差概念在二维空间上的拓展,其将地理空间上多点离散的要素定量描述为包括中心特征、空间聚集特征、空间分布主趋势方向特征等的椭圆空间[17-19],是刻画空间分布整体格局特征的有效方法。该方法由Lefever在1926年提出[20],初期主要用于人口空间分布测度[21-22],近些年陆续有学者将其引入经济空间刻画及优化发展[18-19]、资源空间格局及其差异[23]、警力空间优化配置[24]等研究领域。
本文主要采用加权SDE方法研究我国产业空间和就业空间发展以及二者的协调性。SDE方法不仅能够从全局、空间的角度多维定量刻画产业和就业空间发展的整体格局特征,并且通过产业空间格局椭圆与就业空间格局椭圆的空间关系可以定量描述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性及其动态演化。
基于SDE方法的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SDEI、SDEP分别为产业产值和就业的空间统计椭圆,Area为空间椭圆面积,SDH为产业产值和产业就业空间发展的空间格局协调度指数,值介于0和1之间,值越大,空间协调程度越高。
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基本参数计算公式如下[25-26]。

(2)

(3)
x轴标准差:
(4)
y轴标准差:
(5)

此外,产业空间中心与就业空间中心之间的距离变化是反映二者空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27]。因而,本文研究计算了产业-就业空间椭圆中心之间的距离,用以辅助前述的空间格局协调度全面分析二者空间发展的协调性。
(二)基于协同系数和偏离度的结构协同性描述
除了前述整体空间格局协调性之外,本文应用结构协同系数和偏离度测度城市维度上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协同性。其中,结构协同系数能够从整体上反映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结构偏离度能够定量描述三次产业中就业与产业结构的失衡状况。同时,对协同系数和偏离度进行空间可视化描述,能够进一步从微观层面探析我国产业空间与就业空间发展的协调性。计算公式如下[1]:
(6)
(7)
其中,Ci表示产业i产值占GDP的比重,Li表示产业i中的劳动力占总产业劳动力的比重。S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系数,值介于0和1之间,值越大,两种结构变动的协同性越好。Pi为产业i的结构偏离度,值为0时,说明该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值小于0时,说明就业比重大于产值比重;值大于0时,说明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绝对值越大,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越不协调。
(三)计算数据及来源
2003年,全国经济空间重心开始由向东部沿海方向向内陆方向转移,并且2010年之后全国经济东西向增长加快的转型态势更加显著[18-19]。因而,本文研究期限为2003—2019年,研究对象为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研究数据主要包括2003—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三次产业的全市产值和就业数据、城市区位数据、中国行政区划数据等。其中,产业产值及就业数据来源于2004—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区位数据来源于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国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本文空间计算均基于ArcGIS 10.2软件平台开展,空间参考为Albers投影坐标系(中央经线为105°E,标准纬线分别为25°N、47°N)。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地级及以上行政区划的调整,2003—2010年基于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展开,2011—2016年分别以288、288、289、289、290、291个城市计算(由于数据不可得,不含三沙、昌都、林芝、山南、吐鲁番、哈密),2018年以296个城市计算(由于数据不可得,不含三沙、林芝),2019年以295个城市计算(由于数据不可得,不含三沙、日喀则)。同时,因《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中不含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市三产产值数据,故未对2017年产业及就业进行分析。
二、我国产业-就业空间协调发展态势
我国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增大,第一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减小;第二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最大,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最低。同时,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空间中心距离减小,第一产业-就业空间中心距离增大;第二产业-就业空间中心距离最小且减小幅度最大,第一产业-就业空间中心距离最大(见表1)。我国城市维度的产业-就业结构协同系数增大(2003年结构协同系数平均值为0.907 0,2010年为0.912 0,2019年为0.954 0),表明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协同性提升;从空间分布来看,中西部地区产业-就业结构协同系数明显提升。
(一)第一产业-就业空间协调特征及演化
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就业“双重扩散”发展(即二者空间椭圆面积均增大),二者的空间格局协调度减小,空间中心之间的距离在大幅波动中整体增大(见表1)。从产业-就业整体空间格局差异来看,第一产业产值空间中心分布相对稳定,第一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差异主要存在于产值空间中心的北部,二者在东北地区空间格局差异明显,并且第一产业就业空间分布更为分散。
具体来说,2003年,第一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为0.602 4,二者空间中心之间的距离为231.32 km;其中,第一产业产值空间格局中心为114.95°E,32.86°N,长半轴为1 133.51 km,短半轴为595.72 km,方位角为23.48°;第一产业就业空间格局中心为114.68°E,34.99°N,长半轴为1 607.95 km,短半轴为593.15 km,方位角为24.25°。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为0.476 7,二者空间中心之间的距离为766.28 km;其中,第一产业产值空间格局中心为114.88°E,33.33°N,长半轴为1 144.69 km,短半轴为586.06 km,方位角为24.71°;第一产业就业空间格局中心为119.16°E,39.38°N,长半轴为1 585.46 km,短半轴为598.82 km,方位角为25.37°。2019年,第一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为0.470 3,二者空间中心之间的距离为781.96 km;其中,第一产业产值空间格局中心为114.06°E,32.56°N,长半轴为1 158.45 km,短半轴为625.41 km,方位角为26.56°;第一产业就业空间格局中心为118.60°E,38.48°N,长半轴为1 581.51 km,短半轴为650.49 km,方位角为27.13°。

表1 我国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与空间中心距离
我国城市维度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以正值为主且平均值整体增大,表明我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整体大于就业比重且二者差距不断增大,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协调性持续降低(见表2)。从城市维度结构偏离度空间格局来看,东北地区、黄河上中游地区、西南地区第一产业-就业偏离度绝对值一直较低,其第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相对来说更为协调。2003年,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绝对值较小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黄河上中游以及湖北、江西、江苏等地区,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绝对值较大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山东、河南、河北、广东以及成渝地区。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整体增大,绝对值较小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和黄河上中游地区,其绝对值较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河北、浙江、湖南及成渝等地区。2019年,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继续增大,绝对值较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山东、辽宁、湖南、四川等地区。
(二)第二产业-就业空间协调特征及演化
我国第二产业产值和就业“双重集聚”发展(即二者空间椭圆面积均减小),二者的空间格局协调度增大,空间中心之间的距离在波动中保持整体减小态势(见表1)。从产业-就业整体空间格局差异来看,2003—2012年第二产业就业空间范围一直大于产值空间范围且二者的差别保持大幅度减小态势(在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产值-就业空间范围之间的差别最小),2013—2015年第二产业就业空间范围小于产值空间范围,其中,2003年第二产业就业空间位于产值空间的西北方向,而在2010年和2019年第二产业就业空间位于产值空间的西南方向。

表2 我国城市维度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情况
具体来说,2003年,第二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为0.771 7,二者空间中心之间的距离为135.48 km;其中,第二产业产值空间格局中心为116.18°E,32.90°N,长半轴为1 036.48 km,短半轴为667.19 km,方位角为15.79°;第二产业就业空间格局中心为115.32°E,33.89°N,长半轴为1 103.07 km,短半轴为692.49 km,方位角为20.81°。2010年,第二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为0.918 0,二者空间中心之间的距离为64.06 km;其中,第二产业产值空间格局中心为115.69°E,33.06°N,长半轴为1 030.14 km,短半轴为679.62 km,方位角为16.22°;第二产业就业空间格局中心为115.48°E,32.52°N,长半轴为1 013.24 km,短半轴为695.70 km,方位角为17.25°。2019年,第二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为0.953 0,二者空间中心之间的距离为33.72 km;其中,第二产业产值空间格局中心为115.07°E,31.68°N,长半轴为919.44 km,短半轴为701.25 km,方位角为15.32°;第二产业就业空间格局中心为114.89°E,31.42°N,长半轴为938.48 km,短半轴为708.03 km,方位角为15.81°。
我国城市维度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平均值保持为正值,表明整体上我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第二产业具有一定的劳动力吸附优势。同时,我国城市维度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平均值整体减小,表明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协调性整体在增强,其中,2003—2010年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平均值增大,2010—2019年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平均值减小(见表2)。
从城市维度结构偏离度空间格局来看,2003—2019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结构正偏离的城市逐渐向中西部地区集中,负偏离的城市数量进一步增加,但由分散分布逐渐向胡焕庸线东南区域集中。2003年,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成渝地区、广东、广西等地,这些区域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大于产值比重,表明这些区域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存在劳动力转出的可能;正值结构偏离度较高的部分城市主要在陕西、甘肃、内蒙古、云南、广西等省(区)的崇左市、榆林市、乌兰察布市、庆阳市、玉溪市等,这些城市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显著大于就业比重,表明这些区域第二产业具有一定的劳动力吸附潜力。2010年,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即就业比重大于产值比重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及湖北等地,结构偏离度为正值即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的部分城市主要在陕西、甘肃、内蒙古、广西、四川及东北地区的安康市、庆阳市、乌兰察布市、白城市、吉安市、通辽市等。2019年,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及湖北、甘肃、河南等地,结构偏离度为正值的部分城市主要在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其中正值结构偏离度较高的城市主要在西部及西南地区,如西藏那曲市、林芝市、山南市和云南昭通市、丽江市。
(三)第三产业-就业空间协调特征及演化
我国第三产业呈现“产业集聚-就业扩散”的发展特征(即第三产业产值空间椭圆面积减小、就业空间椭圆面积增大),产值与就业的空间格局协调度增大、空间中心之间的距离在波动中减小(见表1)。从产业-就业整体空间格局差异来看,第三产业-就业空间差异主要在东—西方向上,第三产业产值空间比就业空间更靠近东部沿海地区,同时,就业空间范围大于产值空间范围并且二者差值持续增大。其中,2003年第三产业就业空间与产值空间的空间格局差异主要在西北—东南方向,2010年之后二者的主要空间格局差异逐渐演变为东—西方向。
具体来说,2003年,第三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为0.770 9,二者空间中心之间的距离为140.88 km;其中,第三产业产值空间格局中心为115.88°E,32.78°N,长半轴为1 067.22 km,短半轴为673.08 km,方位角为17.22°;第三产业就业空间格局中心为114.92°E,33.76°N,长半轴为1 097.50 km,短半轴为656.99 km,方位角为21.51°。2010年,第三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为0.811 1,二者空间中心之间的距离为106.32 km;其中,第三产业产值空间格局中心为115.84°E,32.88°N,长半轴为1 052.14 km,短半轴为658.22 km,方位角为14.59°;第三产业就业空间格局中心为114.86°E,33.39°N,长半轴为1 081.71 km,短半轴为668.30 km,方位角为19.76°。2019年,第三产业-就业空间格局协调度为0.825 5,二者空间中心之间的距离为97.12 km;其中,第三产业产值空间格局中心为115.11°E,32.10°N,长半轴为978.17 km,短半轴为701.18 km,方位角为16.98°;第三产业就业空间格局中心为114.26°E,32.59°N,长半轴为1 037.23 km,短半轴为745.98 km,方位角为21.01°。
我国城市维度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平均值保持为负值,表明整体上我国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第三产业整体劳动力不足,需要劳动力转入;同时,负值结构偏离度城市数目持续减少,正值结构偏离度城市数目持续增多,表明城市维度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低于就业比重的幅度正在减小。此外,我国城市维度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绝对值整体减小,表明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协调性整体在增强,其中,2003—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绝对值略有增加,2010—2019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绝对值减小(见表2)。
从城市维度结构偏离度空间格局来看,2003—2019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结构正偏离的城市逐渐聚集分布在沿海地区,负偏离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2003年,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即就业比重大于产值比重的城市数为261个,负偏离程度较大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内蒙古、河北、陕西、河南等地以及东北地区、山东、广西的部分城市,如贺州市、大庆市、菏泽市、玉溪市、乌兰察布市、延安市、榆林市、周口市、来宾市、驻马店市等;正值偏离度较高的城市分布比较分散,主要包括崇左市、伊春市、七台河市、厦门市、泉州市、新余市、珠海市、包头市、黑河市等。2010年,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的城市数有所减少,负偏离程度较大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陕西、河南、江西、广西等地以及成渝地区、东北地区的部分城市,如庆阳市、大庆市、延安市、周口市、南充市、许昌市、克拉玛依市、榆林市、漯河市、商丘市、百色市等;正值偏离度较高的城市分布比2003年更为集中,主要聚集在江苏南部至珠三角的沿海区域,如泉州市、绍兴市、厦门市、苏州市、珠海市、惠州市、温州市、嘉兴市、青岛市、宁波市、深圳市、无锡市等。2019年,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的城市数进一步减少,负偏离程度较大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陕西、内蒙古、云南、广西等地,如延安市、榆林市、安康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保山市、昭通市、贵港市、百色市等;正值偏离度较高的城市保持聚集在江苏南部至珠三角的沿海区域,如福州市、泉州市、杭州市、绍兴市、苏州市、南通市、威海市等。
三、结论与建议
从产业空间与就业空间格局及其空间协调性的动态演化定量分析结果来看,我国第一产业产值与就业“双重扩散”发展,空间格局协调度最低,且空间格局协调度和结构协调性均减小,东北地区、黄河上中游地区、西南地区等第一产业与就业发展相对更协调;第二产业产值与就业“双重集聚”发展,空间格局协调度最大,且空间格局协调度和结构协调性均整体增大,结构正偏离的城市逐渐向中西部地区集中,负偏离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表明目前中西部地区比沿海地区更具有第二产业从业劳动力转入的可能;第三产业“产业集聚-就业扩散”发展,产值与就业的空间差异主要存在于东—西方向,且空间格局协调度和结构协调性均增大,结构正偏离的城市逐渐聚集分布在沿海地区,负偏离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表明沿海地区具有更强的第三产业劳动力吸附优势,而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存在剩余劳动力。
我国产业空间与就业空间协调度的变化间接反映了资源要素空间布局的配置效率,会影响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程度。探索促进产业与就业空间的协调发展有助于促进两者高效的空间配置,进而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区域产业结构演进是区域政策变化的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存在进一步吸收劳动力、优化结构的可能性,并且中西部地区城市市场规模相对偏小[28]。建议在中西部地区加快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新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形成新的要素空间集聚点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撑点,继而拉动人口集聚。相对来说,我国沿海地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且就业仍处于空间分散发展,具有较强的就业集聚潜力,因而建议优化调整沿海地区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大力促进新兴服务业如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行业发展,最大限度发挥其对经济和就业的拉动作用。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东北三省时就深入推进东北振兴提出6个方面的要求,其中包括“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更好支持生态建设和粮食生产,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2003—2019年间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就业偏离度绝对值一直较低,产业和就业结构较为协调;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由2003—2016年的负偏离为主转变为2018—2019年的正偏离为主,就业比重大于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持续减小且负偏离度越来越大,就业比重越来越大于其产值比重,其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劳动力缺失和结构性失业是目前东北地区产业转型与升级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需要东北三省制定出台合理、有效、有力的吸引劳动力和各类人才的政策措施。同时,产业升级会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特别是某些行业的就业弹性因为劳动力进入壁垒而无法充分利用,因而政府部门要建立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使劳动者的素质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协调。
——对2018年广州市一道中考题的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