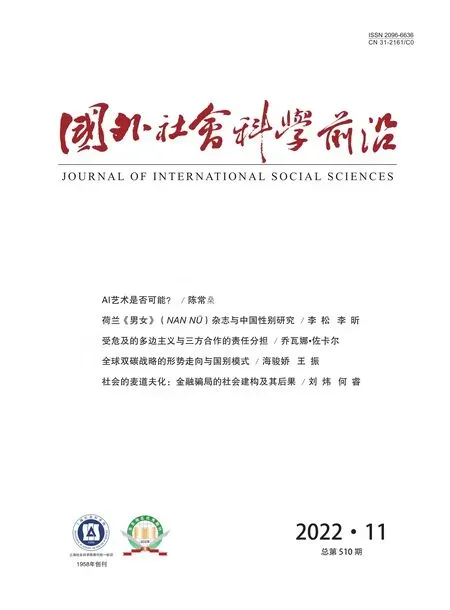当代亚太“旧金山体制”的困境及其超克*
森田明彦/文 吴国邦/编译
紧密互联逐渐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支配性特征。国家——这一传统国际范式(international paradigm)中的重要角色——与国家间也愈发变得彼此相依。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社会的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和信仰多样性征候逐渐强化,“民族国家神话”在其侵蚀与冲击下渐趋衰微,相应地,不同族群基于“民族国家”框架表现出的政治同质性也呈解构之态。在高度互联的世界格局中,伴随着诸种非传统化人权保护机制的建构与用以保障人民对治理决策过程更为广泛之参与的多种渠道的拓展,多层次治理体系应运而生。相应地,那些认为国家在相应法域内享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最高权威(sovereignty)的传统国际法理念,正面临着根本性挑战。然而,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似乎已经落后于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这多半是其历史境遇所致。在本文中,我将首先介绍泰勒的交互文化主义(interculturalism),并将其作为阐述亚太具体历史境况的可靠框架加以援用。其次,我将提出一种区域人权方案,其具备在持续性跨文化交流的境况中渐次培育区域人权保护机制的能效,并希望借此打破亚太——尤其是东亚——诸国间现存的人权地缘政治“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一、缘何重构“旧金山体制”:当代亚太面临的挑战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亚太地区的战后政治秩序是由《旧金山和平条约》所缔造的,1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政府对《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态度是:“‘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参见新华社:《中国绝不承认“旧金山合约”》,http://www.people.com.cn/24hour/n/2013/0531/c25408-21683864.html。)再者,朝鲜与韩国由于“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的代表权问题,也未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直至1965 年韩国方才与日本签订《日韩基本条约》解决相应问题。(参见管建强:《民间战争受害者权益救济的权利与义务主体研究——以韩国启动国内救济手段为视角》,《东方法学》2013 年第6 期。)从这个角度说,更加符合我国战略立场的观点应当是,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围绕“雅尔塔体系”建构起来。作者森田明彦教授“亚太地区的战后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是由《旧金山和平条约》所缔造的”这一论断,其实失之偏颇,系由日本单一视角出发所得结论,应当辩证、理性甄别和看待。学术观点背后深植的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译者虽选择将本文译出,但此举并不意味着,译者同意作者的全部观点;凡是不符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选择的表述和认知,译者均持否定态度。好在本文的意旨根本上还是对“旧金山体制”的批判和超克,本注释所对应的观点不过是作者森田明彦教授的“过程性论述”。——译者注该条约实际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多边条约,由于涉及日本与各同盟国间复杂且各异的政治、经济问题,其奠基于大量的双边条约与政府间协议,因此常常被描述为一种“复杂混合体”(complex amalgam)。肯特·柯德尔(Kent E. Calder)将以《旧金山和平条约》为基础建构的“旧金山体制”的显著特征描述如下:2Kent E. Calder, Securing Security through Prosperity: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1, 2004, pp. 138-139.
第一,美国和太平洋主要国家之间的正式安全联盟(主要呈双边性)的密集网络。
第二,从华盛顿辐射出去的双边关系的“轴辐”网络。除了《澳新美安全条约》(The Australia,New Zealand,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aty,简称“ANZUS”),3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于1951 年9 月1 日在旧金山缔结安全条约,该条约于1952 年4 月29 日生效。——作者注旧金山体制并未建立多边安全体系。
第三,在安全和经济维度呈现为一种高度非对称的结构。该体系向非美联邦成员提供军事保护和经济发展机会,而未能向它们强加类似的集体防御义务。
第四,就经济机会和安全保障义务而言,日本享有特殊的优先权。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是战败国。
第五,西太平洋国家非常有限的同意和参与。最终,只有两个表示无条件支持该条约本身的亚洲国家是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这两个国家均未实质性参与对日战争。
第六,尽管不是以大多数盟国最初期望的“日本直接赔款”这一形式展开,“旧金山体制”确实也为美国的安全盟国们带来广泛的经济利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经济利益部分通过双边通商通航条约实现。该种机制为亚洲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开放渠道;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通商通航过程中,互惠原则很少得到切实贯彻。
柯德尔将这种高度不对称体系的形成,归因于该地区20 世纪40 年代后期与50 年代不寻常的历史环境:
旧金山体制诞生于朝鲜战争初期,处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1950 年11 月下旬中国突然加入朝鲜战争的背景下。面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和军事打击,稳定亚洲的非共产主义地区,同时抑制中国对亚洲的经济吸引力,是美国的首要任务。1Kent E. Calder, Securing Security through Prosperity: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1, 2004, p. 143.
除上述六项因素之外,柯德尔还强调,“旧金山体制”所建构的区域地缘政治秩序是一种包容——或者说是默许——“领土边界的模糊性”的秩序,这构成其又一个显著特征。原贵美惠(Kimie Hara)基于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也论证了《旧金山和平条约》同西太平洋岛礁归属争端间的因果关系。她还指出,《旧金山和平条约》有意将此类问题搁置,以确保日本能够紧密地与西方集团绑定。2Kimie Hara,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86-188.
按照柯德尔的说法,“旧金山体制”主要由三个要素所组构:美国的强大(aラuence),对中国崛起的担忧(the specter of China)以及朝鲜战争高峰时期太平洋地区制度建设的催化过程。3Kent E. Calder, Securing Security through Prosperity: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1, 2004, p. 144, p. 140.
尽管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特别顾问、“旧金山体制”的主要设计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r)喜欢类似于欧洲的区域集团安全架构,4Kent E. Calder, Securing Security through Prosperity: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1, 2004, p. 144, p. 140.但历史环境造就了一个基于双边网络的不对称框架,最终既阻止了日本与邻国发展多边网络,也使其无法深入包括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更为全球化的网络,而只能寻求同美国的政治合作甚至依附于美国。不过,由于美国影响力的逐渐减弱、中国和韩国的崛起、日本的停滞和朝鲜的不可预测性,在经历了由美国主导的半个世纪的相对稳定后,当今亚太的地缘政治秩序正在经历根本性的转变。
尽管得到普遍同意的是,用以替代“旧金山体制”的新秩序应当建立在以发展平等伙伴关系、尊重和保障人权、法治等为要义的国际政治原则之上,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人成功地描绘出一幅能够为各方所共同接受的蓝图。相反,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亚太各国围绕各自地区领土和历史问题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加剧。目前亚太地区的政治局势完全可以借用博弈论上“囚徒困境”的经典模型和案例加以描述,这一点在亚太各国围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AIIB”)展开的相关谈判中得到了证明。
以TPP 谈判为例,假设“积极缔约”和“积极谈判”为“合作”,而“消极缔约”和“消极谈判”为“背叛”。在美国主导谈判的阶段,澳大利亚、智利、秘鲁、新加坡等已经同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以及墨西哥、加拿大等原本已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国家,能够借由TPP 获得的新利益(如原有自由贸易协定中没有完全放开或者迟延放开的商品的关税利益等)相对较少,加之需要就原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未达成一致的部分进行重新谈判(或要引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同TPP 的冲突处理机制),其“背叛”动机相对较强;马来西亚、越南、文莱、新西兰等没有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能够借由TPP 获得的新利益最多,但同时意味着所有自贸谈判必须从零开始,对冲后其“背叛”动机与“合作”动机相对均衡;日本出于加强日美经济同盟关系、打开亚太市场、扩大出口等目的,与美国借日本挖掘亚洲国家潜在市场容量的需求相耦合,具有较强的“合作”动机、较弱的“背叛”动机。1反映各缔约国决策逻辑的实证资料来源于刘中伟、沈家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研究前沿与架构》,《当代亚太》2012 年第1 期。——译者注不难发现,这三组决策单位各自同美国存在不同程度的“囚徒博弈”,尤其是第一组,双方的博弈输出停留在非合作结果的纳什均衡点的概率较大;而如果从TPP 整体的角度来看,第一组和第三组的决策逻辑本身可能构成一种二阶的对冲,使得自贸伙伴关系最终是否能够成型变得扑朔迷离。
在美国因国内分歧而正式宣布退出后,其他缔约国即陷入了“碎片化复杂自贸谈判的‘囚徒困境’”中,由于许多国家最初选择加入谈判的动因正是吸引、维持或进一步开拓美国投资,这一转折点使得它们各自利益考量与前一阶段迥异,“帕累托最优”(“复活”TPP)的达成更加艰难。这充分说明,由于“旧金山体制”的影响,亚太地区的主要政治行动者之间总是缺乏长期且稳定合作的愿景,这无疑阻碍了面向未来的政治对话的发生。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地缘政治秩序?或者说,我们应当援用何种理论框架以科学有效地支撑和指引这一重要的政治实践议程?正如查尔斯·泰勒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不仅需要具体的政策,还需要讲出清晰的“故事”以阐明我们正在为改变“旧金山体制”所做之事。在泰勒看来,能够触动或映射区域政治秩序的“故事”一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反映或者本身能够成为相应区域内不受争议的“共同叙事”(common narratives);第二,“共同叙事”的非争议与共同性主要借由相应区域内普遍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ies)得到实践承诺,即“共同叙事”具有形塑或者构成相应区域内普遍“社会想象”之背景的资格和能力;第三,保障“共同叙事”之非争议性与共同性的“社会想象”,同时具有塑造相应区域内“共同实践”(common practices)与获得广泛认同的合法性观念的资格和能力。1Charles Taylor, Intercult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38, no. 4-5, 2012, pp. 415-416.根据这样的标准进行检视,“旧金山体制”背后原有的“故事”与当代亚太的地缘政治形势并不相符,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故事”来发展一套崭新的区域政治秩序。泰勒的交互文化主义或许可以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抓手”。
二、以查尔斯·泰勒的亚太交互文化主义重构“旧金山体制”
晚近以来,交互文化主义正逐渐取代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而成为一种新型的政治意识形态。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于2008 年5 月7 日发表了旨在促进文化互动、减少文化冲突的“交互文化对话白皮书”《在尊严中平等共处》(Living Together as Equals in Dignity)2译者并未检索到该白皮书的官方中文译名,学界对其译法还有《在尊严中共同平等生存》(参见刘兴澍:《交互文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争——加拿大的案例分析》,《世界民族》2014 年第5 期)、《平等·尊重·共处》(参见宁伟:《跨文化教育视角下的外语教育》,《学习与科普》2019 年第13 期)等。前一种译法忽略了作为人权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之分,因而将“生存”与“生活”混淆;后一种译法错解了“共处”与“平等”“尊严”的逻辑关系,将它们翻译为具有并列关系的三个语词是不妥当的。——译者注3Council of Europe, White Paper on Intercultural Dialogue “Living Together as Equals in Dignity”, Strasbourg, Jun.2008.,其结论认为,用于认知和应对文化多样性的传统路径——如多元文化主义——已然无法圆融当下的情形。原因在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社会文化多样性问题,不再是一个“有”与“无”的存在性问题,而是一个“高”与“低”的程度区分问题。很显然,多元文化主义等传统范式,无法有效满足程度前所未有、谱系仍在裂变的多样文化及其治理需求。4Council of Europe, White Paper on Intercultural Dialogue “Living Together as Equals in Dignity”, Strasbourg, Jun.2008.
然而,正如纳萨尔·梅尔(Nasar Meer)和塔里克·莫多德(Tariq Modood)所研究和阐明的那样,5Nasar Meer and Tariq Modood, How Does Interculturalism Contrast with Multiculturalism?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vol. 33, no. 2, 2012, pp. 175-196, p. 413.交互文化主义的主要理念,即鼓励交流、承认动态身份、促进团结和批判非自由的文化实践。不过,这似乎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特征。从这一点上看,交互文化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二者并没有太大区别,它们在制度上都可以被具体化为一套对民族文化多样性具有整合与治理功能的政策。
那么,交互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区别究竟是什么呢?泰勒认为,交互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故事”。1Nasar Meer and Tariq Modood, How Does Interculturalism Contrast with Multiculturalism?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vol. 33, no. 2, 2012, pp. 175-196, p. 413.如前所述,“故事”是一种能够为生命提供意义和价值,能够形塑或构成“社会想象”的背景,并能够借由这种“社会想象”赋予特定社会的“共同实践”与在该社会中具有广泛认同基础的合法性观念以可能性的“共同叙事”。泰勒一再重申,我们不仅需要具体的政策,还需要清晰的“故事”,以标识我们正在为改变这个社会所作的努力。2Charles Taylor, Intercult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38, no. 4-5, 2012, pp. 415-416,.泰勒将魁北克的交互文化主义与英属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如下对比: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故事实际消解了传统“民族—历史”身份的中心性特征,同时拒斥其他任何身份类型替代其中心地位。这样的结果是,所有的“身份”在去中心化的社会文化格局中共存,且没有任何一种身份以“官方文化”的面貌出现。而关于交互文化主义的故事并未显现出去中心性的症候,它往往动议于某种历史身份的支配性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不平等的发生,因为在交互文化主义支撑起的社会文化格局中,无论何种身份的公民均能够自由地发出其声音,也没有任何一种身份的介入附带特权地位。3Charles Taylor, Intercult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38, no. 4-5, 2012, p. 418.
交互文化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治理文化和宗教多样性的可行路径。在既定社会情境中,它借由多民族宏大叙事的方法论,直面实质不平等,并确保社会各方均能够平等参与确立新型集体身份认同的过程。
那么,泰勒的交互文化方法何以能够圆融亚太地区的政治文化实践呢?笔者认为,以美国单极主导、多边安全结构薄弱为特征的“旧金山体制”与当代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不符,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故事”来构建地区政治新秩序。简单来说,“旧金山体制”背后的“故事”主要是,美国作为自由民主国家(states)之联合体——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领导者,被迫进行斗争,最终于1945 年战胜了包括日本在内的极权国家,并将所谓的“真正的自由民主”移植到了那里。美国随后与苏联、中国进行对抗,并宣称其利用自身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力量,维护了该地区所谓的“和平”与“繁荣”。
然而,如今的中国是全球一体化市场经济的第二大参与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情况并不相同。韩国和日本也都是亚太地区繁荣发达的经济体,拥有相对健全的自由民主制度。从根本上说,韩国和日本渴望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不再愿意受制于“山姆大叔”一直扮演的家长式角色;中国则自始至终拒绝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从这个意义上看,该地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及随之而来的历史和领土争端,正是这些国家及其人民的自然表现,也是这些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政治力量的明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日本不是从制度比较学的角度出发科学、客观地考察中国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社会与文化条件,而是仅出于意识形态分歧或对立,便以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同样是加剧局势恶化的重要因素。
那么,应该如何克服此困境?泰勒坚称,交互文化的故事也适用于许多欧洲国家,原因在于:第一,这些欧洲国家往往具有一种能够为大多数公民所共享的长期历史身份;第二,这些身份及其认同往往围绕一种民族化、国家化或区域化的语言中心点加以建构,由于语言(小语种)的地理不可通约性与文化非交互性,他们的身份认同总是面临着强大的“全球化”语言压力。1Charles Taylor, Intercult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38, no. 4-5, 2012, p. 420.很显然,面对此种境况,消解“小语种”国家全球化身份认同焦虑的好办法,便是具有语言优势的所谓“主流”国家,同代表少数语言文化认同者们的所谓“非主流”国家摈弃分歧、合作共赢,协同引导和构筑适用其间的交互文化场景。2Charles Taylor, Intercult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38, no. 4-5, 2012, p. 421.在亚太地区,这种基于交互文化主义“宏大叙事”的区域协作议程,同样有助于消解冲突,并推动构建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三、基于交互文化方法重构“旧金山体制”的政治实践方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适用于东亚各国的区域人权保护机制尚未建立,而在欧洲、南北美洲大陆、非洲和东南亚,却分别设立有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美洲人权委员会(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和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ASEAN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的构造与运行经验来看,亚太地区不仅在地理与政治上与南北美洲大陆和东南亚相交叠,更在多领域互动中分享“共同历史”(common history)。因此,理所当然地,与区域人权保护机制建构经验相对丰富且同亚太地区具有地理、政治与历史渊源的美洲人权委员会和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合作,发展亚太区域人权保护机制(如“区域个人申诉机制”等),或许是一条具备可行性与可信度的路径。
在这方面,秋子江岛(Akiko Ejima)3明治大学(Meiji University)国际人权教授。——作者注通过研究“区域个人申诉机制”[基于《欧洲人权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设立]对英国人权状况的影响发现,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个人申诉机制”积累的、以《公约》为裁判依据的“人权判例”,既有助于建立成员国互信、强化《公约》的合法性认同,更有利于《公约》内容向各成员国国内法的转化与适用。秋子江岛还提及,欧洲议会、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简称OSCE)的人权政策为有效执行《公约》奠定了基础。秋子江岛强调,只制定《亚洲区域人权公约》还不足以有效落实各项权利。4Akiko Ejima, A New Phas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Jinken Hoshou no Shinkyokumen), Nippon Hyouronsha, 2002(in Japanese).
在笔者曾经举办过的研究工作坊上,学者们的讨论也表明,“国际个人申诉机制”需要与“人权监察员”“人权委员会”等国家人权组织密切联系与合作。例如,当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简称CEDAW)等国际人权机构准备受理由幸存者和/或其代表提出的个人申诉时,有必要引入国家监察员及律师参与,也有必要与相应申诉人所在国家的妇女组织(如中国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展开合作,这既能够保证幸存者证词具有获得国家认可的政治理性与事实客观性,又能够提升相应证词的法律公信力。此外,向人权监察员和相关律师寻求专业的咨询意见,对于确认相关国际人权机构的合理受案范围十分重要。换言之,国内法意义上的“国家人权组织”与国际法意义上的“区域个人申诉机制”相辅相成,由国家人权组织和相关非政府组织[既包括“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政府主导的非政府组织(GONGO),也包括其他非政府主导的非政府组织]组建的区域内网络,能够成为亚太区域人权保护机制建构的坚实基础。1参见Akihiko Morita, Guidebook on 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a Communications Procedure (CRC/OP3), Houbun-Sha, 2013 (in Japanese)。——作者注
简而言之,建立区域人权保护机制客观上起到了补充和加强国家人权保障结构的作用,而为了提升人权保护效度,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须携手共进;或者说,有效人权保护的“基底”(foundation)不仅应植根于区域层面,还应深入作为“终端”的国家。所谓有效人权保护的“基底”,不仅意味着司法结构及其人力资源所能够贡献的制度力量,还意味着支持和拥护人权作为社会“根基性文化”(underlying culture)的公众心态。为了保育有效人权保护的“基底”,人权教育必须与交互文化教育相结合。2Association for Historical Dialogue and Research, Policy Paper: Rethinking Education in Cyprus, K&L Lithofit Ltd.,2013.因此,必须在构筑区域人权保护结构的同时,推动交互文化项目持续增量。
如果具象地作出项目规划,则值得亚太各国展开联合研究的可能口径是,针对亚太地区的“人权先锋”及其间为夯实亚太人权文化“基底”所展开的互动,作专门史或人物史研究。例如,日本人权先锋贺川丰彦(Toyohiko Kagawa,1888—1960)于1927 年提出九项儿童权利,其中包括选择父母和作为独立个体(individual person)被对待的权利。3在作为国际联盟大会(General Assembl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第一份关于儿童权利的官方文件《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Geneva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正式通过(1924 年9 月26 日)的三个月前,贺川丰彦已于1924 年6 月9 日便在东京深川提出了六项儿童权利。Toyohiko Kagawa, Kodomo no Kenri (children’s rights), The Dictation of His Lecture at the Seminar for Child Protection at Sarue-ura, Fukagawa, Tokyo in Jun. 9th, 1924. (attachment of“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Children’s Rights”, Toyohiko Kagawa Memorial/Matsuzawa Museum, 1993)——作者注有趣的是,“选择父母的权利”正是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的著作《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1900)第一章的标题。身处瑞典的爱伦·凯是“以儿童为中心”之教育和育儿方法的早期倡导者,该书于1906 年被翻译成日文,有迹象表明贺川丰彦读过凯的这本书,此种历史亲和与时空互动正是笔者所提联合研究计划的适恰切入点。
另一个发现是,“作为独立个体被对待的权利”与韩国作家、儿童权利积极倡导者邦正焕(Bang Jung Whan/Bang Jeong-hwan,1899—1931)发表的《对儿童承诺书》(Commitments for Children)所载第一条准则完全相同。事实上,1920 年至1922 年期间,邦正焕一直待在日本,由其所发起的儿童运动于1922 年5 月1 日宣布了设立“Eorini 日”的构想。“Eorini”是邦正焕创制的、用以代替原单词“aenom”与“esaekki”的韩语词,意指儿童或青少年。他首次使用该词的语境是,表明儿童乃像成年人一样享有充分人权的独立个体。贺川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从邦正焕那里借鉴了这一理念。
再者,十分有趣的是,日本牧师、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直史田村(Naofumi Tamura,1858—1934)于1911 年提出了“儿童是独立且适格的权利持有人”的观点,远远早于贺川。1Naofumi Tamura, Rights of the ChildKeiseisha-shoten, 1911. 据说该书被翻译为了韩语,参见Naofumi Tamura,Child-Centered Christianity, The Publishing Department of Taisho Kindergarten, 1926, p. 58。——作者注他通过观察和反思当时美国基督教群体围绕儿童阐发的诸种神学观点的逐渐变化,提出了这一革命性的想法。2Naofumi Tamura, Child-Centered Christianity, The Publishing Department of Taisho Kindergarten, 1926, pp. 82-85.
我坚信,我们越细致地审视和研究儿童权利先锋的历史,就会越充分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权概念不仅仅是一种“西方规范”,而且是通过超越国界的互动和相互学习发展起来的普遍价值。因此,发现隐匿于人权文化与政治史上的亚太地区人权先锋,并追溯其间展开互动的历史——当然也包括与美国的互动史——必将能够为夯实亚太地区有效人权保护机制的“基底”贡献应有力量。
我们需要发展一套新的“故事”以实现区域政治秩序的理性进步与有效转化,亚太地区的区域新秩序必须以人权和法治等普遍规范为基础。因此,潜在的新“故事”同样必须以该地区人权和法治的“共同故事”为基础。与文化交互并行的区域人权保护机制等实践议程,可以逐步并最终促成此种新“故事”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