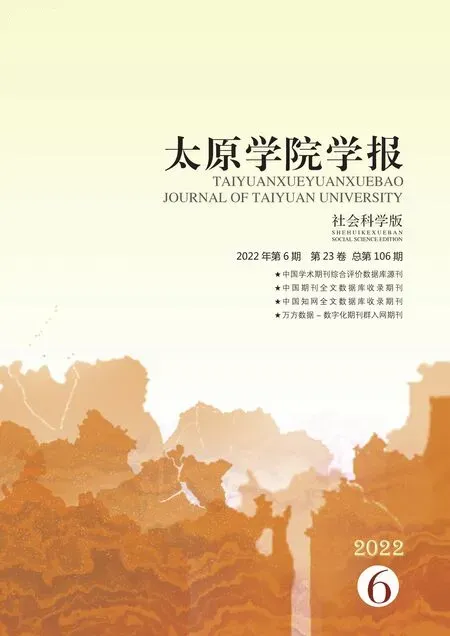要做清醒的教育者
刘庆昌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人精神中都有不可改变和可以改变的成分。其中,不可改变的成分,属于人的本性,对人的一切更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可以改变的部分,不过是表现本性的方式,即使改变了,也只是能帮助人把本性表现得更艺术一些,并不会使人的本性有一丝的变化。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特殊性,就像其他任何的事实一样,仅是个事实而已,但对教育却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或许对教育的方法没多大的影响,但对教育的立场应有修正作用,使教育者在束手无策时少一些自责,在得心应手时少一些自负。根本上是因为他们的束手无策很可能不是自己的心力不济所致,而是因为恰好遇到了某种不可改变的劣质本性;而他们的得心应手很可能并非他们自己有什么教育的制胜法宝,而是因为他们恰好遇到了不可改变的优质本性。在这一点上,我们没必要看似慈悲地坚持各种教育浪漫主义,正确的立场是:努力为可为和应为之事,绝不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任何一个对象。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因不该承担的失败而忧心忡忡,也才不会因不该贪占的成功而沾沾自喜。
很久以来,在我的意识中就萦绕着一个指示,即是教育在人的认知侧面是自然赐予中常人群的福利,有效的传授与引导,可以帮助个人把自己本有的智慧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好地发挥出来;但在人的人格以至德性侧面,教育则主要是借助必要的规则灌输和行为干预,帮助个人张扬该张扬的、自己本有的积极本性成分,同时自我抑制自己本有的消极本性成分。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对于个人的认知还是对于个人的人格乃至德性,教育的作用都存在着一个极限,这种极限也就是教育作用的边界。进而可以说,教育者的责任只能存在于教育作用的极限以内,他们一方面不必为教育作用极限以外的个体成败或喜或忧,另一方面也不必为个体认知天赋和人格本色带来的优劣或得意或自责。能这样想,并不是自认教育的无力,而是已然具有了教育的理性。从这里出发,教育者优先要做的是从一切科学中获得知识和方法,为教育的有效性而尽心竭力;行有余力之时,则须从一切非科学却同样理性的人类文化创造中汲取慈悲与诗意,以使教育具有鲜明的精神性。
整体地看,有效性与精神性之于教育可谓缺一不可。没有精神性的有效性,其背后隐藏的只是类似工匠的机巧;而没有有效性的精神性,只不过是某种理想主义的或贵族情结的艺术形式。但当两者能够完美结合的时候,教育便可兼具机智与希望,人类的创造在其中似乎均能有用武之地。而作为专门教育机构的学校,不仅传承着,而且储存着人类的智慧,虽非全能,也近乎完美了。但不管教育自身进化到什么程度,教育者也需要格外清醒,须知多么完美的教育也不可能超越教育作用的极限,近乎完美即便令人激动,也只能使教育自身的功能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清醒的意义远大于光明。当教育者普遍清醒时,教育的行为方式和分寸把握便不是问题,任何时尚也不会动摇他们对教育的理解,教育则会因此而朴素而优雅,而不至于成为“冒险家”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