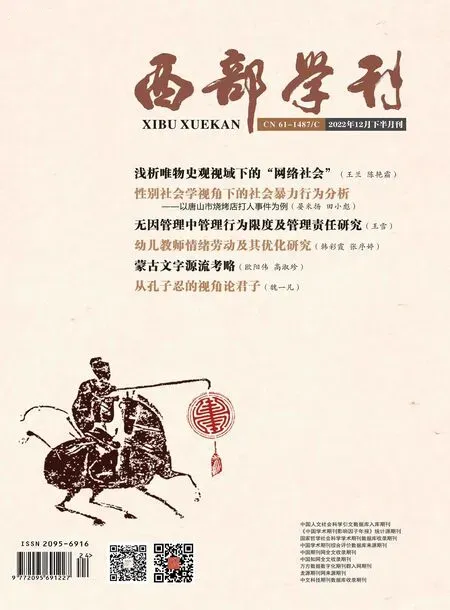余华长篇小说儿童形象研究
黄相露
余华的6部长篇小说中儿童形象数量颇丰。笔者以余华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意图探究余华小说中的儿童形象的共性与个性,同时也尝试挖掘作者寄寓在儿童形象上关于家庭、社会的深层体悟。
一、共通与变化的儿童形象
余华笔下的儿童形象绝非千篇一律的模式化人物,这些形象既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又因各自性格、遭际的不同而成为独特的个体存在。
(一)共性设定
一个人的思想具有连贯性,所以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相似之处。余华作品数量众多,他长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在家庭背景、生存状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共同点。更为独特的是,部分儿童的姓名也与他们的父辈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读者在阅读中足以体会到余华对于细节的考究。
1.姓名与父辈之间的联系
余华长篇小说中儿童的名字反映了父辈的经济状况、性格特点等方面的情况。《活着》当中,福贵的大女儿叫“凤霞”,凤霞出生之时正是福贵家财力旺盛之际,“凤”与“霞”二字正是福贵家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福贵的儿子有庆则是在福贵败光家产时出生,“庆”字有“祝贺”“可祝贺的事”之意,“有庆”二字折射出福贵一家渴望摆脱经济困境的心情。凤霞和有庆两人的姓名生动地反映了福贵家经济条件由好转坏的状况。
在余华的小说中,也出现了儿童名字与父亲名字相互呼应的情况。《许三观卖血记》的主人公名为许三观,“观”有观点、看法之意。恰巧许三观的三个儿子名为一乐、二乐、三乐,这三个儿子名字当中都含有“乐”字,“乐”正是许三观夫妇正向心理的投射。儿子们的姓名正好回应了父亲姓名的“观”字,可见余华塑造人物时十分注重细节。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儿童姓名也是父母性格的投射。《兄弟》里,李兰评价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宋钢和他父亲一样忠诚善良。”[1]这句话将宋钢和其父亲画上了等号,读者无形中接受了宋钢父子性格良好的设定。李光头原名李光,他的母亲称呼他为李光头,一切缘于李光头继承了父亲好色的秉性。李光头与其父亲因为在女厕所偷窥女性遭到了村里人的嘲笑,连带李兰也长期在村里抬不起头。牢狱犯在入狱时通常会被要求剃头,所以“光头”作为一种符号与犯人身份紧密相连,这表明了“光头”符号带有一定谴责性。这个称呼可看作是脾性软弱的李兰对亡夫的埋怨,同时这也是作者借用姓名来表达自己对于李光头父子偷窥行为的看法。
在余华长篇小说中,儿童姓名不仅是儿童的个人代号,儿童之名也是作者间接塑造父辈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段。儿童与父母亲的羁绊绝不仅限于血缘关系,在姓名、性格、社会地位等方面,双方的关联度非常高。
2.大多为工农家庭子女
在余华的6本长篇小说当中,儿童形象多达30余个。在这些作品里,农民家庭子女有12个,工人家庭子女多达13个。这种设定表明这些儿童的家庭并不富裕,他们的家庭环境使得温饱问题成为头等大事。当不同家庭背景的人碰头,社会阶层的层次感也由此扎根于儿童心中。例如,农民孙光平、孙光明看到苏医生家的饭菜时,惊喜地发现城里人也吃咸菜,但是城里人的菜里有香油。城里人和乡下人同样都吃咸菜,但城里人面对同一事物时借助添加物显示出城乡差距,越是平常的事物越能显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儿童只能无奈接受现实的冲击。这是生活间接暗示家庭出身的不同导致的待遇差别,当儿童普遍进入社会交往话语体系中时,他们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孙伟的父亲在“文革”前期光荣无比,当父亲被人指认成“资本家”后,他也沦为阶下囚。因父亲地位的改变,孙伟从耀武扬威、人人尊敬的小混混变为垂头丧气、低调做人的小孩,孙伟遭遇的落差显现出社会对于权力和财富的追捧。
在余华长篇小说中,许多儿童原生家庭处于社会底层,有限获取的社会资源注定让这些儿童经受一些磨难。
3.坎坷的童年经历
在余华的6部长篇小说里,许多儿童都拥有一段曲折的童年经历。在物质方面,社会生产力低下,家中人口众多,再加上家长收入有限,儿童们大多要经受饥饿的折磨或者是多人同时争抢有限的资源。许三观卖血以后带着家人们去饭馆吃面,鉴于卖血的钱有限,再加上一乐的特殊身份让许三观心生嫌隙,可怜的一乐只能独自啃红薯果腹。这只是物质上的困窘,一些儿童在精神上也遭遇了不幸。《文城》中的小美因家里快揭不开锅,被父母卖给沈家做童养媳。小美父母这样做一是缓解家里的经济负担,二是凭借与沈家的姻亲关系为自家增添颜面。年幼的小美寄人篱下,处处受到阿强母亲的管控规训,被压抑天性的小美如同她的被深藏衣柜的亮色嫁衣,无法展露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另外,有的儿童并未拥有完整的家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第七天》中的杨飞。母亲在火车的厕所里产下了杨飞,他意外地掉落在铁路上,杨飞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的关怀。养父也因杨飞终身不娶,杨飞童年时期的家庭结构始终残缺不全。也有因为父母亲的失责而饱受心灵煎熬的儿童形象。许一乐的亲生父亲是何小勇,当许三观得知真相后,将心中的怒气与怨气全部撒到一乐身上。一乐遭受了许三观言语上的辱骂、物质上的克扣、许玉兰的驱逐、何小勇的拒绝……一乐因自身身份的敏感,小小年纪就遭受家庭内部的情感冲击,而最亲近之人的回绝一次次地让他遭受重创。
余华笔下的儿童形象在姓名、家境、遭遇等方面存在共同之处,这是作者写作习惯的一种展示,也可看作是余华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整体性概括。社会生活往往是由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交织汇集而成,所以作者笔下那些颇具个性人物的生活经历也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
(二)个性十足的儿童形象
余华长篇小说中儿童形象数量较多,此处论述着重选取文本中叙述篇幅较大、个性特征较明显的儿童形象分析。比较突出的两类形象,一是私欲发泄者,二是成人化倾向追求者。
1.私欲发泄者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将一个人的人格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层,并且以性本能作为阐述此理论的出发点。换句话说,本我是人类遗传本能和基本欲望的体现者,儿童身上同样透露出人类本我的影子。李光头随时随地对着椅子、电线杆发泄情欲,人们惊讶李光头放浪行为的同时,部分人带着嘲讽的眼光打量着李光头的偷窥与自慰,部分人也对他“目中无人”的行为予以理解。在笔者看来,作者对李光头泄欲行为的设计更能引发人类对自身的关注与正视,人们对性问题的回避并不能掩盖人类自身的需求,作者借由李光头将此问题凸显放大引起人们的反思。
2.成人化倾向追求者
在余华长篇小说中,存在成人化倾向的儿童形象。成人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儿童过早地接受成人世界的生存法则,二是儿童的人格快速进化到“超我”阶段。《在细雨中呼喊》里的鲁鲁非常懂得收买人心,他在出发之前用自己的生活费购买了香烟,只为了让班车司机中途停车。他提前买烟贿赂司机的老练行为与他从小跟随母亲四处漂泊的经历有关。国庆年纪尚小却已开始挣钱养活自己。喜欢上一个女孩后,他满怀希望地到女孩家提亲,国庆的行为在女孩父母眼里是一场玩笑,但是在国庆看来,这是他作为一个“社会人士”的正常社交活动。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一部分儿童因现实条件的制约,被迫提前适应成人的交往秩序,同时他们也可能遭遇到成人的排斥和打压。他们模仿成人的行为也正是儿童话语权微弱的表现,儿童在社会交往中的弱势地位也更加明显。
根据弗洛伊德人格系统理论,人格最高级的阶段为超我阶段。“超我本质上代表人类从他人身上继承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种受到赞赏的、具有典范性的社会理想。”[2]因发烧救治不及时,失去听力的凤霞成为家里人的负担。有庆即将步入学堂之时,福贵夫妇欲把凤霞送给别人抚养,以此缩减家庭开支。凤霞的顺从并不意味着她完全拥护这个决定,一方面,体贴的她知晓父母养家的艰难,她愿意用自己的牺牲改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她懂得“在家从父”的纲常伦理,在父亲的强势主导下,她的怨言和不满只是徒劳。在旁人看来,凤霞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正是凤霞的人格成长到超我阶段的表现。
余华笔下的儿童形象除了迥异的成长背景外,其所生活的环境也同样建构出余华小说中的儿童“王国”。
二、不同场域中的儿童形象
儿童的生活空间主要分为作为家庭成员存在的家庭环境和作为社会成员存在的社会环境,以下我们将论述儿童形象在这两种环境中折射出的深意。
(一)儿童之于家庭
儿童成长期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父母承担了抚养儿童的责任,这种关系使得儿童依附父母生活。经济供给和血缘关系维系着儿童与父辈间的关系,某些特殊情况下,亲子关系可能因感情的紧密度被重新定义,父母压制孩子的局面也可能受到多重因素干扰而被颠覆。
1.儿童依附于父母
儿童未正式进入社会生产劳动活动前,都依附于父母而生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情况下,儿童在家庭生活中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以至于儿童必须服从父母的指令。《活着》中,有庆抗议将姐姐送给外人,遭到福贵暴打后,他向父亲求饶。双方力量悬殊过大的情况下,有庆不得不接受父亲的安排。这足以可见父母在家中利用暴力维护自身绝对权威。儿童大多会在自己犯错后或者有求于父母的时候讨好父母。《许三观卖血记》中,当许三观知晓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后,他对一乐的态度由喜爱变为厌恶,一乐企图讨好父亲来平缓父亲的怨气。儿童的讨好和乞求是儿童话语权在家庭关系中被成人话语权压制的表现,而讨好也是儿童方试图减轻双方隔阂的行为。成人在这种讨好声中获得了满足与虚弱,变相加深儿童受成人限制的程度。
2.亲子关系的重构
在《第七天》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杨飞和许一乐名义上的父亲都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然而他们在养父处获得了温暖、雄厚的父爱。杨飞的养父为了抚养杨飞,一生未娶,即使去世后也在冥界火葬场等待儿子的到来。虽然杨飞也曾短暂地与亲生父母重聚过,但他心中最信赖的人还是自己的养父。刀子嘴豆腐心的许三观经历一番挣扎后重新接纳了一乐,将一乐视如己出。即使是何小勇病危之时,许三观仍教导一乐要以生命为重。许三观和杨飞养父的行为解构了传统以血缘关系为判定标准的亲子关系,他们用行动证明了真情、真心才是建构亲子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许三观不计前嫌的善举和杨飞父亲倾尽全力地付出紧凑了家庭成员的关系,加固了家庭结构。
可在社会秩序混乱期,被管控的儿童也会反过来施压父母。《许三观卖血记》中,许玉兰惨遭游街示众,身心疲惫的她回到家也要遭到家人的批斗。在政治高压下,长幼有序的关系被解构,年长的父辈随时面临儿童的拷问指责,长期积累在儿童心中的怨气趁机喷薄而出。许三观主动交代自己的错误时,一乐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现在最恨的就是何小勇,第二恨的就是她……”[3]在政治话语强力干涉下,父母与儿童之间不平衡的天平倾向儿童一方。儿童对于父母的反攻并不是空穴来风,当社会上出现儿童反攻父辈的风气时,即使儿童不情愿也要被迫参与到畸形的斗争中来。另外,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大义灭亲”的文化心理。“大义灭亲”是指为了维护正义,亲属不包庇家属的罪行,使家属受到法律的惩罚。家人为了追求义理选择不包庇犯罪的亲属,而义理通常与社会绝对话语权的掌控者所规定的思想倾向相一致,家人的不包庇行为实则是为了迎合社会主流话语权,而这种迎合也使得社会秩序得以平稳地运行,“灭亲者”在背离亲属的同时也获得社会的认同与赞赏。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的亲子关系被重塑。
(二)儿童之于社会
儿童是社会人力资源的后备军。一方面,儿童在成长期不断适应社会生存法则,他们是社会秩序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儿童眼中的世界与成人眼中的世界大有不同。余华曾说:“舒尔茨用儿童的视角进行写作,他获得了纯洁的叙述方式,叙述者由此获得了成人视角无法具备的童真和同情,并在叙述中处处显露着儿童的天真。”[4]余华同样选用了儿童视角创作,透过儿童视角,我们可以对社会产生别样的思考。
1.对社会秩序的适应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们也逐步接受、适应社会的各种法则。在此过程中,家中长辈充当着引导者的角色。“乡土社会的教育理念是鼓励孩子模仿、实践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同时孩子被寄望于与父亲、祖先相似。”[5]这种教育模式带来的后果是父与子的处事模式带有极大的继承性,儿童的行径多少带有父辈的痕迹,父辈的经验为儿童的社交提供了借鉴。例如,宋钢继承了父亲刚毅正直的品德、孙光平继承了父亲精于算计的品性。
2.对恶与欲的揭露
余华儿童叙事视角的运用使叙述者保持着儿童原始、纯真的视角观察周边世界,或者以儿童的经历来展现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在这种纯洁视角下,人性丑陋的一面被暴露。
刘镇两大才子让偷窥的李光头游街示众,道貌岸然的他们私下同样想知晓林红的身材状况,油滑的李光头趁机敲诈了他们两碗阳春面。一群成人因为自己的偷窥欲而被儿童敲诈本就荒唐,才子对敲诈的顺从更是暴露了他们心中的怯弱与狡诈。换句话说,“儿童视角由于其边缘立场和‘不理解’的认知特征,在呈现现实形成具有张力的讽喻上有着成人视角不可替代的优越性。”[6]由于儿童有限的认知水平、故事创作是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这两个事实:故事情节中儿童对外界的认知其实是作者个人思想的投射,作者借助儿童在行动、心理等各方面的表现将成人的不雅行为放大了。
现实生活中,成人在儿童面前闭口不谈性话题,余华选用李光头以及孙光林等人对于欲望的好奇表现了人类追求欲望的本能。作者利用儿童的不谙世事,更能表现出人的欲望存在的客观性。李光头无视周遭环境,镇定自若地自慰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处理欲望的态度和方式。
3.对美好人性的呼唤
余华的6本长篇小说均创作于1990年后,余华对人性恶的揭发转向对人性爱的呼唤在儿童形象上也有所体现。孙光林自小遭受身边人的冷落,这段孤独的经历让他成年后仍然在回忆中舔舐着童年的疮疤。不过他的回忆中仍有朋友的欢笑、养父母的温情在其中游荡,孙光林的童年并不完全是晦涩的。这两方面的回忆是对他的抚慰,也帮助孙光林在童年的难堪中找寻到了值得珍藏的记忆。这种温和的感情处理方式大不同于余华写作初期的短篇小说里赤裸裸的冷血与残酷。刚步入生命初程的儿童被人们视为未来的希望,作者借用孙光林在苦闷童年之中仍找到抚慰的生活经历来表现自己对美好人生的呼唤,而这种写作也达到了重新审慎自我,展望未来的效果。
余华长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既有一些共性设定,也各具特色。儿童们的社会活动范围非常有限,读者依旧可以借助他们的生活轨迹窥探特定时代人们的生活状况,感受社会生活的复杂。在余华的笔下,我们重新审视了儿童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处境,也重新审视了人类自身,这或许就是余华小说中儿童写作的价值所在。
——读余华小说《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