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巨子”张季鸾
周利成

张季鸾
1941年9月6日,《大公报》主笔、报界宗师张季鸾在重庆病逝,重庆、陕西、天津、广西等地新闻界相继举行公祭,毛泽东、周恩来分致唁电,蒋介石亲往吊唁。此后数年中,香港、桂林、重庆、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东方日报》,重庆的《中央日报》《益世报》等报刊,发表于右任、陈布雷、张申府、胡政之、王芸生、许君远等数十名社会名流的百余篇文章,记述了张季鸾曲折而传奇的一生。
投身报业 两次被捕
1935年第12卷第1期《国闻周报》中张季鸾的《归乡记》、1941年9月8日《大公报》中于右任的《悼张季鸾先生》两文,详记其生平事迹。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以字行,陕西榆林人,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亡后,随母扶柩返关中,师从咸阳大儒刘古愚,就读于烟霞草堂,“故于国学朗然得条理,为文章亦如良史之绵密警策”。1905年秋,官费留学日本,为陕籍最年轻留学生。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再升第一高等学堂,攻读政治经济学,加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编辑《夏声》杂志,主编反满刊物《陕北》,为其从事新闻事业的起点。
1908年,张季鸾回国,在关中高等学堂任教两年。1910年10月,受老乡、同学于右任邀请来到沪上,担任《民立报》编辑兼记者。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于右任的举荐下,张季鸾出任临时政府秘书,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张季鸾从南京拍至上海《民立报》关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著名报人徐铸成曾评价:“中国报纸之自有新闻电,确以季鸾先生一电为嚆矢”。同年2月,孙中山辞职北上,张季鸾回沪与于右任等人创办民立图书公司。
1913年初,张季鸾与友人曹成甫在北京创办《民立报》,兼任上海《民立报》驻京通信。因发表文章揭露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和秘密大借款以镇压革命党人的罪行,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被逮捕后囚于军政执法处监狱三个月。后经友人康心孚等人多方活动,始于双十节后一日出狱,“北方天已寒冽,先生则衣纱大褂出狱,怡然还自己之天地间”。1938年10月11日为张出狱25周年纪念日,于右任与张在汉口置酒为祝,于作《双调·折桂令》为念:“危哉季子当年,洒泪桃源,不避艰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吊民立余香馥郁,谈袁家黑狱辛酸!到于今大战方酣,大笔增援。廿五周同君在此,纪念今天,庆祝明天。”
获释后,张季鸾潜回上海,撰写《铁窗百日记》,刊于《雅言》月刊。此后,应留日同学胡政之邀请,担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兼任翻译、编辑、采访、撰述等工作。1915年,他与友人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继续撰文抨击袁世凯的倒行逆施。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重回北京,主持政学系机关报《中华新报》,兼任上海《新闻报》驻京通信,撰文揭露段祺瑞以参加世界大战为名与日方秘密勾结的行径,再被执政府秘书长徐树铮下令逮捕,羁押半年,始获自由。
此后,张季鸾在上海、北京、天津各报社之间往来奔走,鬻文为生。直到1926年,在天津与胡政之、吴达诠接办《大公报》。
“三驾马车”接办《大公报》
1946年9月6日,胡政之在《大公报》发表《追念张季鸾先生》一文,回顾了他与张季鸾、吴达诠共同复刊《大公报》的过往。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创办人为晚清名宿英敛之,社址设于天津旧法租界。该报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宣傳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黑暗吏治和外来侵略,以“敢言”有声于时。辛亥革命后,英敛之积劳成疾,报务几近废弛。1916年,王郅隆收购该报,胡政之任主笔,稍加整顿,略有起色。1919年,胡政之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1921年回国后辞去报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遇难,继任者不得其人,《大公报》遂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胡政之
1926年夏,胡政之与张季鸾同旅津门。胡时办国闻通讯社,张适无事。二人常偕过日租界旭街《大公报》社址,忆及当年,颇多感喟,遂经与银行家吴达诠协商,共同盘收复刊。吴任社长,胡任经理,张任主笔,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终由张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为准。吴出资五万元,胡、张二人以劳力取得股权,签约三年内三人皆不得另有俸给之公职。议既定,胡向旧股东购得产权,由王佩之出面召集旧工友,着手复业。1926年9月1日,《大公报》正式复刊。
《大公报》前已停刊达10个月,一切无异于新创,尤以广告极少,最初半年逐月赔累。当时,各家电影院、戏院概不肯在该报刊登广告,不得已,报社每晚派人至各院门首抄记戏目,义务刊载,历时数月,始能收费少许。长期广告仅有一两家银行、银楼,亦碍于吴之情面,每月每家收费不过二三十元。出人意料的是,扭转艰难处境的竟是报纸销路的迅速扩充。吴、胡、张三人初时预测,销量能在天津销3000份,在北平销2000份,共计5000份于愿已足,但在半年后即已达6000份。
《大公报》创刊前五年,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多变,张季鸾除担任撰述外,并须随时出外采访。他撰写的社评根据版面可长可短,遇有重大事件而版面小时,更能文字凝练而又切中要害;遇有事件不大而版面有余时,他则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文字流畅,丝毫没有拖沓之感。在时局紧张时期,往往于深夜2时后才得北平电话随时抽换社评,另行撰稿。张季鸾虽体质虚弱,但能通宵工作,不厌不倦。依据北平电话,深夜捉笔疾书,排字工人立前待稿,每写数百字辄付排版,续稿毕,前文已排竣。他再“自校自改,通篇完成,各分段落,一气呵成”。在编辑报纸时,常为题目一字之改,绕室徘徊半小时,重要社评则反复检讨,一字不苟。待报纸出版后,如发现排错一字,他便顿足慨叹,终日不欢。

吴达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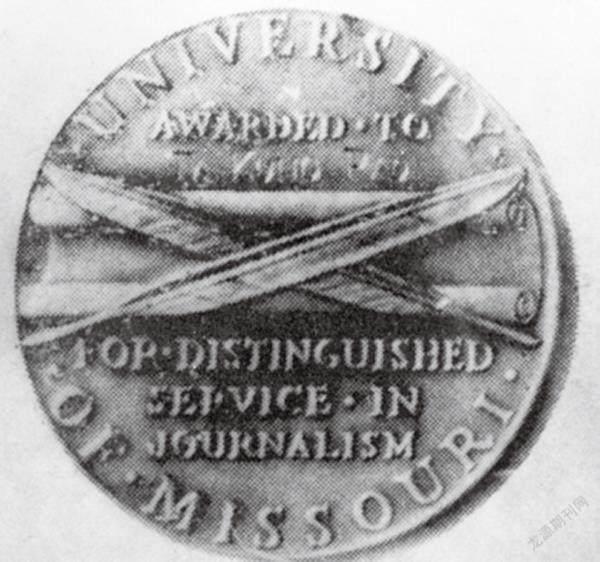
1941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的荣誉奖章
胡政之总结《大公报》的成功经验时称:“因由全体同人之努力,而吴张两与我精诚合作,尤有重大关系。”张季鸾的办报秘诀则是“不望成功,准备失败”,即不怕失败才能成功,从失败中获取成功,每个失败都是成功。
吳达诠、胡政之、张季鸾合称《大公报》的“三巨头”“三驾马车”,他们的通力合作正是《大公报》走向辉煌的重要因素。三人皆为文人,均有个性。因此,合作之初,许多朋友都认为未必能够长久,但事实表明,他们配合默契,精诚友爱。在工作中,他们都能尊重彼此个性,更能发挥自己个性:吴长于计划,报社每有重大兴革,胡、张二人一定要征求他的意见;胡负责经营,吴、张绝对信赖,让胡事权统一,放手做事;张长于交际,思想与文字皆佳,吴、胡便尽量发挥他的能力,文字方面尊重他的权威。因此,五年后,《大公报》销量已达5万份,1936年更突破10万份,从一份地方报纸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舆论重镇。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荣誉奖章”,该奖章被公认为新闻行业最具声望的国际奖项之一。
《大公报》素有“中国《泰晤士报》”之誉,常人心目中的大公报馆应该是巍巍洋房,屋宇轩昂。但《大公报》唯重精神、不重表面,天津馆址不过是一处普通楼房,会客室是一个用薄木板间隔、不满16平米的小房间,室内除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外,别无长物。这间不起眼的小屋却招待过众多中外社会名流,因此,张季鸾曾自豪地说道:“《大公报》的会客室虽然因陋就简,连一个地方报馆的会客室都不如,可是,许多有富丽堂皇会客室的报馆,恐怕成年不会有名人巨子到那里坐一坐呢!”报馆办公条件虽则一般,但编辑部的藏书却最丰富,国内绝无第二家报社能出其右。这完全是张季鸾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复刊首日,《大公报》即表明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刊主旨,成为中国报人独立意识觉醒的一个里程碑。由张季鸾、胡政之执笔的社评更是《大公报》的金字招牌,既透彻时事,文笔犀利,又稳健明达,不温不火,让读者如同听围炉夜话,娓娓动人,听而忘倦。
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说过“结婚有利于革命”的话,转天张季鸾即在《大公报》上撰写《蒋介石之人生观》一文,以嬉笑怒骂的文笔,对蒋讥讽嘲笑,给读者留下“《大公报》敢骂蒋介石”的深刻印象,一时传为佳话。
1936年冬,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史称“七君子案”。“七君子”被捕后解往苏州,由江苏省高等法院审理。此案拖了半年,法院捏造罪状,拼凑出一份《起诉书》,由中央社发各报刊登。为此,“七君子”针锋相对,也写了一篇义正词严的《答辩状》,但国民党当局不准各报发表。救国会派胡子婴找张季鸾要求在《大公报》上刊登。张季鸾此前听说“七君子”已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所谓《答辩状》不过做戏给大家看而已,所以一口回绝。胡子婴说:“国民党的诱降计谋,完全是痴心妄想,七君子不但不会‘悔过,而且正在狱中以不吃、不说、不写的‘三不对策与国民党抗争,《答辩状》如能发表,不正是给他们的迎头痛击吗?”张季鸾听罢此言,当即抄起电话通知编辑部:“《答辩状》明日见报,不必送审。”张季鸾违抗当局禁令的正义行动,换得了社会舆论对“七君子”的广泛支持。此后,张还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陈说利害,劝其三思。7月31日,迫于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把“七君子”无条件释放。
1941年9月15日《新闻报》所刊敬仲的《张季鸾先生轶事》一文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1931年夏间,北京大学考试,胡适之所出历史考题中有几处错舛,作者遂撰文指出。但当时北平各报均托词恐惹学生麻烦,不予登载。作者乃寄稿给张季鸾,第二天即全文刊于天津《大公报》,张且复函作者称:“学术愈辩愈明,何所顾忌而遗此大文不录?”1937年2月15日,《大公报》发表了记者范长江撰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这是一篇冲破国民党当局禁令的爆炸性报道,它像拨开重重迷雾的一道闪光,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即将团结奋起应战的希望。这篇报道轰动上海滩,传遍全中国。蒋介石看后勃然大怒,把张叫去狠骂了一顿。
1941年9月7日,《中央日报(重庆)》所刊许君远《敬悼张季鸾先生》一文称,张季鸾永远能走在大众的前面,不反对“左”倾,不反对共产主义,即使在“剿共”时期,《大公报》也从未以“匪”字头衔加于任何人或任何军的头上。1948年7月30日《东方日报》中风伯的《张季鸾遗事》一文亦称,当年,国人要明了国内政事的得失以及国际问题,均以《大公报》的言论为准绳。因此,张的文章也成为最高当局的关注点,蒋介石时阅报纸只有两份,一是《中央日报》,二是《大公报》,其言论往往可以左右政府的决策。而毛泽东曾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是《大公报》。
“外和易而内刚正”
“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与人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采访所得,常可达到问题之症结。尤其生活兴趣极为广泛,无论任何场合,皆能参加深入。然而,中有所主,却又决不轻于动摇,生活看起来似乎很随便,而实际负责认真,决没有文人一般毛病。”这是胡政之眼中的张季鸾。而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悼张季鸾先生》一文中则称:“季鸾先生为人和易可亲,潇洒自若,大公无争,淡泊有志,言论的委婉而不失为敢言,平实而常中肯綮。”
陈布雷在《中央日报》刊发的《追念张季鸾先生》一文,回忆了他们的初交情形。1921年,陈供职于《商报》,因某案与张主持的《中华日报》往复论辩七八次,陈的论据当时也没有压过张,但张却在报上刊了一篇短评道:“余在报界10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等讨论者正多,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彼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陈感佩张之雅度深情为中国新闻史上所仅见,与之成为挚友。
许君远的《敬悼张季鸾先生》一文,既介绍了张季鸾平易近人的一面,也展现了他爱憎分明的个性。与任何人在一起,张都会让对方感到舒服,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大公报》在香港出版时,许把一位同乡介绍给张,约好到同乡家吃饭。第一次见面,同乡觉得张名气很大,怕难伺候。但吃饭时,气氛极为融洽,张不住地赞美同乡太太厨艺好:“做得太多了,你太忙,叫我过意不去。”聊天中更是翕然自得,同乡太太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此后,张成了他家的常客,时去打牌、吃饭、聊天,积之既久,凡吃饭则非去他家不欢。但张绝不滥交,鉴别善恶的能力极强,疾恶如仇。一次,许在九龙饭店邂逅了从上海来的何某。当得知张也在时,何便希望与之见面。许把何之意转告张,却碰了一个很硬的钉子,张说:“何某?不见他,你就说我不在香港,就是在也没工夫!这个人在上海的行为一塌糊涂,靠不住,我不能见他!”早在北京时,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提出国语拉丁化,张季鸾首先表示反对,两个人辩论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最后张一麐又举日本文字为例,张季鸾立予驳斥说:“论中国旧学我不如您,论日本文字您且住口莫谈,您所说的全是外行话,无论您怎么说,我《大公报》绝不会登您提倡国语拉丁化的文章。”这样的疾言厉色,在张季鸾一生中极为少见。
风伯的《张季鸾遗事》一文,介绍了张季鸾不卑不亢的文人风骨:“张先生名士习气颇重,其衣领口之纽扣永不扣好,即谒见蒋介石时,亦复如此。”蒋介石视张为诤友,而论张的资望、能力和政治眼光,做个高官毫无问题。但张一生对当官、敛财毫无兴趣,身后一无长物。据说,他临终前身边只有十元钱。张季鸾老来得子,友人赠送孩子金银饰物为贺。当时《大公报》正在呼吁民众踊跃捐款,救济难民。他想把这些礼物捐献给受难同胞,太太则想留下两件作为纪念。他说:“你只想小儿可爱,不知比他更可爱的许多孩子,因为父母惨遭敌人杀害而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他们正企望着我们的救助呢!”太太听后心悦诚服地将礼物全部捐出。
张季鸾非常关心青年,尤其注重对新人的培养。1946年第42期《新上海》中丁玲的《张季鸾的衣钵》一文介绍称,张季鸾为了要使《大公报》能够永远以社评见长,有人继承他的衣钵,特地收了几个青年学子来训练。训练方法是以每日时事为题,令诸生练习撰写社评,张逐一详细批改。结果有两个门生让他最为满意,颇有其风范:一个是王芸生,另一个是徐铸成。张季鸾病逝后,社评便由王、徐二人执笔。
王蕓生在1944年第4卷第3—4期《新闻战线》刊发的《张季鸾先生的性格与文境》一文,表达了对恩师的深深怀念之情。“季鸾先生的性格,主要的特征是愉快、健谈而有人缘。凡他所在之处,一定送往迎来,会客不绝;凡他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与他厮混,无论是正经大道理,或是说笑玩闹,都必为他所吸引。”约于1933年春,王芸生与张季鸾同在北平,一个中午与胡适之一同吃小馆子,张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而王眼中的张则“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度”。吴达诠也曾赠张一首诗,前四句是:“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不忘,日见百回如新睹!”这“日见百回如新睹”七个字,恰当描绘出张的风格,即他随时都能给人以新印象,永远觉得他是一个崭新的人。
张季鸾在汪山养病时,王芸生每月至少两次上山看望。他们一起吃喝谈逛,对王芸生而言不仅是一种放松,更能在与张的谈天中获得启示和灵感。每次回馆后,王总可在谈资中发现几篇文章的素材。张季鸾对他的正面指示更是简劲而有力。1941年8月中旬,正是敌机疯狂轰炸重庆之时。王芸生上山时,张季鸾之病势已沉重危殆,二人不禁相顾戚然。但谈到敌机轰炸时,张季鸾说:“芸生,你尽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一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无精打采地说:“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张季鸾忽地拥被坐起,兴奋地说:“今天你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的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敌机尽管卖大气力,也只能威胁我们少数的城市,并不能奈何我广大的农村。况且,我少数城市所受的物质损害较之广大农村的割稻收获,数字悬殊,何啻霄壤?让敌机尽管来吧!让你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那天是8月18日,距他病逝仅三个星期。在他发烧喘汗之际,仍忧国恨敌,“运用活泼的脑力,给我这个新鲜活人启开了死脑筋”,令王芸生无比钦佩和感动,几至泣下。一会儿,张季鸾累了躺下身子又说:“芸生,你可筹备一篇提倡水利的文章。”接着,很有力地高声说道:“要打倒这亡国的粮价!”王芸生回馆就写了《我们在割稻子》的社评,提倡水利的文章则由工程师孔昭恺完成。

1937年2月20日大公报社举行同仁公宴,庆祝张季鸾50寿辰

王芸生
积劳成疾 病逝重庆
张季鸾和胡政之都曾赴日留学,回国后,出于职业的关系,同日本报界又有20多年的接触,所以,他们对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状况比较了解。九一八事变前后,《大公报》的社评对日本问题讨论最多,皆能抓到日方痒处,主战到底的观点,也颇能影响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因感到战事威胁日益扩大,华北行将不保,他们先于1936年将报馆分出一部分到上海,张季鸾主持报务。1937年7月天津沦陷后,天津版随即停刊。“八一三”战起,8月17日,张季鸾又以带病之身赴武汉,筹备汉口版。行前,他与胡政之彻夜长谈,一致认为,中国一定要坚持抗战,而抗战一定要牺牲毁灭,但毁灭之后一定能够复兴。《大公报》与国家休戚相共,汉口开馆就是准备复兴,而上海报必是毁灭。张季鸾在汉口负责领导复兴事业,吴达诠在上海处理毁灭事宜。
七七事变前不久,张季鸾的儿子士基刚刚出世。他异常兴奋,到汉口后给胡政之来信称,自己儿子已有了,以后更要全力在汉口办报。当时王芸生还未到汉口,汉口版的文章皆由他一人执笔,这一年是张季鸾自复刊《大公报》以来最辛苦的一年。1938年,香港版发刊,他又来到香港主持笔政。此时,他的身体已差,依赖服药才得休息,每月都要往来内地与香港之间数次,加重了他的病情。随着战事发展,武汉沦陷,汉口报馆撤退,重庆版《大公报》发刊。此时,他的精神更差,已不大執笔,但主笔王芸生遇有重要问题仍需请他发表意见,以为参考。每次从香港飞到重庆,张季鸾虽很疲乏,但仍坚持谈论国家大事和对时局的看法,胡政之欲阻止他让他好好休息,他也不听。1941年,张和胡料定日本必攻香港,香港也决不能守,就在桂林创刊《大公报》。见到桂林版《大公报》时,他精神倍增,不但访新闻、打专电,还用“老兵”的笔名撰写通讯。日敌时在重庆疯狂轰炸,天气又热,张的身体越发不支,但怕同人分心,在给胡政之的信中只字不提自己的病情,还说等病好了一定要到桂林看看报馆,期待他们再合作。
1941年8月3日,张突感呼吸困难,入医院治疗。虽经医治,但病势沉重,肺已衰竭。许君远的《敬悼张季鸾先生》一文记录了张季鸾的最后时刻。9月4日下午,许与《中央日报》社长陈博生来到歌乐山中央医院看望张。张的右鼻孔插着氧气管子,神志仍很清醒,见到他二人进来,便用手指点着凳子让他们坐,告诉他们:“热度已经退了,比前一天好。”但刚说了这么一句,便觉“倦得很”,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医生说:“希望他能挨过两个礼拜,挨过这个阶段就有办法。”一会儿,张又睁开眼睛,对伴在床边的太太说:“你告诉君远,我今天情形好,烧退了……”他想侧转身子,很吃力的样子,自嘲道:“没有这么狼狈过,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
5日午后,蒋介石亲往医院探视,与张季鸾握手。张季鸾临终前曾留遗言,于右任、陈布雷、萧振瀛等同作遗言证明人。6日凌晨4时,一代报界巨星搁笔长殒。7日,《申报》发表社评称:“张季鸾于昨晨4时病故。这消息的重要性,虽抵不过美日关系或德苏战事的电讯,但就中国立场,尤其是中国新闻界的立场而言,的确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新闻。因为张先生不仅是中国报业的先进,实在更是最能代表中国民意,最能宣达民族意志的一位人物……他对国族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四年来他赞助抗建大业的重大功绩:他主张奋战到底,他信仰奋战必成,他更随时随刻呼吁团结,他对于国际大局的认识极其深刻,他始终相信世界大势必能有利于中国。他的信念、他的判断,现在差不多已一一实现了。但是苍天不佑,竟不待这位老记者目睹胜利,生生把他夺回去了。这不仅是中国新闻界的莫大损失,同时更是中华国族的非常不幸。”
重庆、陕西、天津、广西等地社会各界相继进行公祭活动,蒋介石亲往吊唁。毛泽东认为张季鸾“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邓颖超致唁电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1942年9月,张季鸾的遗体从重庆运回陕西。6日,灵柩自兴善寺发引,送往少陵竹林寺安葬。灵车所到之处,沿途数万乡民夹道迎榇,绵延数十里。
(责任编辑 王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