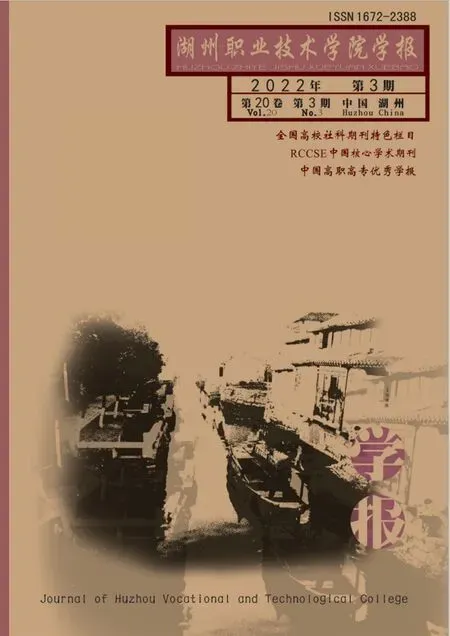“修己治人”:胡居仁理想人格的实现路径
毛心悦 , 路永照
(1.新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2.温州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浙江 温州 325035))
明代理学家胡居仁(1434-1484年)继承了“修己安人”“反求诸己”等儒家思想,以人性论为其仁道政治的出发点,在肯定人性情欲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人性固善,进而由天命之性的普遍善性推出仁政王道的合理性。“修己治人”作为胡居仁“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融合修身态度、路径、精神于一体,寓精神于方法之中,力求在“知”和“行”的汇合过程中实现儒家所倡导的“圣人之道”治国理想。胡居仁认为,无论在培养道德君子的“理想人格”方面,还是在以圣人治国求“理想社会”的追求上,“修己治人”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性善的普遍性
关于“性”的善恶问题的讨论始终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史。为此,张岱年先生曾说:“有许多学者,在别的哲学问题上并无贡献,而在人性论上颇有所见。”[1]300胡居仁明确表示人之性固善,并将人之性善观照于“理一气一”视野之下,由“理一气一”论善的普遍性,由善之普遍性论仁政的合理性。
“性”的探讨最早见于孔子的弟子世硕、公孙尼子、宓子贱等人的谈论中。他们对于“性”的看法是,性有善有恶,既可为善,又可为恶。《性自命出》认为“性自命出”,喜怒哀乐均为情,情即性。情的喜怒哀乐之变化决定着性善性恶的取向。《中庸》虽未明确性的善恶之分,但提出“率性之谓道”,反对笼统地认可喜怒哀乐为“性”,只认可喜怒哀乐中符合“中节”的部分为“性”。宋明儒学,尤其是周敦颐、程颐、张载和朱熹,则是以宇宙论推衍人性,以理论性,更重要的是从宇宙论中寻求人之善恶的根源。胡居仁关于“性”的见解虽然兼具了《中庸》以及“周程张朱”对于性的阐释,但是他称“故论性至周程张朱始备”[2]6,指出“惟伊川程子言:‘性即理也’,真实精切,发明孟子性善最尽。朱子又曰:‘性者,人心所禀之天理’,则又曲而详矣”[2]6,并通过对“周程张朱”所言之“性”的爬梳和反思,来展开以“喜怒哀乐之未发”论“性”的路径。胡居仁所言之“性”是理具于形气之中才有的,是就人而言的。人受天理以成性,从天理到人性的过程便是宇宙本体上升为道德本体的过程。基于此,胡居仁将“性”二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命之性作为人的本性乃情之必善之“性”,气质之性由于其所禀之气混杂不清,其善恶具有不确定性。
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却不论善恶;孟子言善,实指人之“四端”,并非现实的善,认为只有将其扩充,我们才能受用。孔子看到了“气禀”,所以讲性相近,但却没有意识到人禀理成性的一面。与此相反,孟子只看到了人性善,却没有看到人性恶的部分。所以,胡居仁在认识到孔孟及其后来儒学者人性论的不完备时,才对周敦颐、张载以及程朱的人性论进行归纳与剖析,试图采用与他们相同的方法,从宇宙本体出发寻找人性的善与恶。因此,从性即理的角度而言:“理无不善,所以发而为阴阳五行,以生人物者,气也,其交感错综,益参差不齐,而清浊偏正,于是焉分,而贤愚善恶出矣……愚者因其气之浊,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于恶矣……程子言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是兼理与气禀而言,如清者为水,而浊者亦为水,盖水之源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浊,理之源本善,禀于人便有善有恶,故论性至周程张朱始备。”[2]6胡居仁认为,理本善,而人性禀于天理,固无不善。但从文中可以发现,人性尽管存有本善之理,但因气的参差不齐,也会产生“清浊偏正”之状,无法避免产生“恶”。善、恶本为对立之物,人之本性不可能在善恶之间摇摆不定。那么,这一矛盾如何解决?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宋明儒学,其共同点之一就是不反对“情”,也就是胡居仁所说的“欲”。人在出生之际便有情。但依《性自命出》所言,“情”的变化决定着“性”的善恶。战国后的儒家学者意识到情的不确定性,将情分为“已发”和“未发”两种状态。胡居仁亦是如此。他以“喜怒哀乐之未发”论“性”,实际是指人生而就有向善的倾向,以此倾向“性”之本善,确保“情”之必善;他以喜怒哀乐之“已发”为欲,实际指人受浊气之后所具有的恶,禀浊气之后性即为恶,但经过后天的主敬工夫也可向善。因此,在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抉择上,胡居仁主张“善乃人性之固有,人之所当为”[2]7,认为善性是人与生俱来,并且处于乱世,人性之善“乘彝之不可泯处”。
在确立人性善之后,胡居仁又指出,性本善是普遍的。他的宇宙本体论以“理”为核心范畴,以“气”为万物生化之具,并且认为宇宙万物在接受“气”之所化时遵循“理”之规定,恪守“理一气一”之规约。胡居仁认为,尽管天地人万物迥然不同,但就其本质而言却是同“一理一气”的。所以,他指出:“人之有生,均气同体,固无物我彼此之间。”[3]1 260他认为,因为人的理气相同,所以善就成为人们的普遍共性。在解释人性善的普遍性时,胡居仁接受了朱熹关于“恻隐之心”普遍性的本体论解释路径。传统中国学者关于孟子“恻隐之心”的本体论解释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将恻隐之心看作是本体论层面的理本身,代表学者是牟宗三;另一个则是将恻隐之心看作是本体在人心上的表现,代表人物是朱熹。性即理,就其字面意思而言,可理解为胡居仁所言的性是本体论层面的本身。但从性与理的关系深究,性即理,理为万物的最高遵循,其深层内涵即理统筹万物,包括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性则是内含于人类的道德规则,性所表现的善是理的本源善。所以,人性善是宇宙本体的理在人性上的表现,即所谓“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4]238。
中国古代便有王道与霸道两种政治形式之分,最早由孟子提出。两种政治形式的区分点在是靠仁义德治还是靠强力计谋。在二者的抉择上,孟子据“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的性善论,确立以“仁心”行“仁政”的王道政治,而胡居仁则依其性善的普遍性,确立仁政的政治方向。他说:“故圣人所以真实恳恻,以仁民爱物,乃其心之自然,非强而为之也。其所以民安物阜,而上下与天地同流者,亦其效之自然,非有一毫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民之所以仰瞻感化者,亦其心之自然而不容遏,非有强也。”[2]8儒家学者所追求的目标是圣人治国,所以国家管理者必然要求是圣人君子,百官也必然是德才兼备的贤人。圣人贤人之所以能够治国,在于其天然之性至善至纯,其心纯粹醇然,不为利欲诱惑。正因如此,圣人能够以仁心对待万物,能够使“万物皆在吾生育之中”。既然统治者以及管理者是至善至纯之人,那么治人之法也必然遵循人性的普遍善性,所形成的社会也必然是“民安物阜”的理想社会。此时,胡居仁面对的现实问题便是,如果确立了某一个王朝的统治者不是圣人时该怎么办?圣人贤人治国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如果不能将设想的蓝图转变为现实存在,其主张就会变为空想。胡居仁肯定人性善的普遍性,也肯定性之恶向性之善转化的可能性,所以,平常人也具有向圣人贤人转化的可能性。为此,胡居仁提出“修己治人”的方法论,即统治者要实现其仁政王道,必须修身、爱民、任贤。
自古以来,性的善恶问题一直是极为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因此,对胡居仁人性善恶问题的解读是十分必要的。在处理人性的善恶取向问题时,胡居仁借鉴宋明理学家,尤其是周敦颐、二程、张载以及朱熹的人性论,以本体论确立性本善及其普遍性价值。人性善的取向和普遍性特征也决定了胡居仁政治主张的走向,即儒家始终提倡用仁政王道——“圣人之道”治国。由此可见,胡居仁在其政治理论的铺设之中,延续了儒家政治的基本主张,特别明确了其人性论意义的基础。
二、“修己”与“治人”
胡居仁圣人治国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其所提出的“修己治人”的方法论路径。“修己治人”作为王道政治主张中的核心内容,最早在儒家文献中以“克己复礼”“修己以安人”“反求诸己”出现,主要见于《论语》《孟子》,以及朱熹的《大学章句》。“修己治人”思想要旨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无甚变化,但对其的具体阐释却有差异。胡居仁以孔孟学派、朱熹等人对“修己治人”奠定的儒学基调为基础,阐释了对“修己”与“治人”的理解。
胡居仁所谓的“修己”,含有孔孟所言“反求诸己”“克己复礼”之意。为了充分理解“修己”一词,探讨“修”“己”二字的内涵是必要的。“修己”二字包含道德实施与道德主体两个方面,而实施方式则以对象为标准,所以,在探讨“修”的含义之前要先弄清“己”的内容。儒家学派所说的“己”,主要概括为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作为道德行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自身;二是德行尚未完善,亟须进一步改善的个体。
孔子在把“己”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的自身时,就为其道德修养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确立了基本原则,即主体性原则,也为后世儒家学者解释这一概念奠定了基础。孔子认为,“能近取譬”是仁之方法论,道德修养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为仁”作为个人的道德追求,其动力来自人,其对象是要求自己,强调人作为主体的自觉和主观努力。受主体性原则的影响,孟子在将人之四德——仁、义、礼、智作为本心本性的内在禀赋的前提之下,提出道德修养需要“反求诸己”。此处的“己”便是孔子所说的主体自身。“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5]805相比抱怨他人,孟子主张要“反求诸己”,指出道德修养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以拥有“养吾浩然之气”的崇高人格。虽然,孔孟一致认可主体自身,但其所属的是封建贵族范围,只有封建贵族范围内的主体才可养成理想人格。而胡居仁摆脱了先秦儒家的偏向,提出人人皆可成贤,将“人”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人。
主体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和所处的社会环境都会对个人产生影响。“就其井然不淆处识是礼,就其杂然拘蔽处识是己。”[6]407句中的“其”即“仁”,在儒学家不反对人的物质欲望的条件下,“己”的另一层面的含义就是“仁”被乍然遮蔽时的状态,蒙蔽仁心如贪财、好色,其实就是“私”意。“私”从何产生?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宋明儒学,其共同点之一就是不反对人对“欲”的向往,认可这是人的天然之性。胡居仁立足于心性论,在坚持“理一气一”后,由浊气、物欲分辨人心与道心。道心乃圣人之心。因为浊气的污染,以及物欲的诱惑,部分道心不坚定,就会产生私意,进而沦为人心,导致个体德行的不完善,无法达到“参天地化育”的程度。因此,个体长期生活在困惑与烦恼之中,就难以超脱世俗。针对个体的这种现状,先秦儒家早已以私意为克制对象,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道德实践。“克己复礼”,从“克”“复”来说,可判定“己”与“礼”是相对的,其意即指:“撤尽气拘物蔽之障,而复还先天继善之良。”[6]407个体受物欲所惑时,要牢记自身的道德责任,做到个体的道德自律。道德主体在此过程之中所采取的“克”“复”等修身的道德实践,即为“修”。“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乃儒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所提,“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寻求一个“为什么”,是对主体行为的要求;“正心”即修正被物蔽的本心本性,是对主体的内在本性的要求,是指个体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达到修心修身的效果。
以上论述可见,道德行为主体的克制、修养即为“修”,道德行为主体及其被拘蔽的状态即为“己”。胡居仁对儒家学者所提的“修己”内容兼收并蓄,从君子的内在德行和外在表现,心性工夫和行为举止出发,指出:“夫古之君子,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也。盖修己者,必能救民;救民者,必本于修己。”[3]1 260君子心性纯然、心无旁骛的天然本质决定了其专于修身工夫,对君子在“进”“退”之间的行为也作出了规约。在继承儒家“修己”思想时,胡居仁以其人性论为始点,归“修己”于心性纯粹的君子之要求,强调君子的道德自律意识,致力于追求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
“修己”乃是理想人格的品行要求。作为国家统治者不仅要要求自身,还要寻求治国之道,而治国的关键在治人。作为“治人”的理论来源,孔子所提的“安人”在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再次阐述后,被沿袭进了胡居仁的治人理论之中。自秦王朝开始,社会结构经历了由贵族为主体向平民为主体的转变。所以,胡居仁在“安人”之外,也将孔子所言“安百姓”纳入治人之内涵。
何谓“安人”?在先秦儒家理论中,有“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的表述,意为统治者只有树立榜样才可以对各级官吏进行管理。胡居仁主张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实施的主体不限于国家统治者,还涉及每一层的管理者,亦有所谓“一正君而国定”;更进一步说,除最高统治者之外,管理者是每一层的各级官吏,同时各级官吏也是被管理者。由此可见,“安”即为管理之意,“安百姓”就是对百姓的管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之言所体现的便是百姓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这也是儒家学者在其仁道政治主张中注重百姓治理的原因。
“修己”是个人内在道德修养,“治人”则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方法论。胡居仁将“修己”与“治人”合于一处,一同提出,却并没有指出二者有何联系。同其他儒者一样,他希望通过培养有道德理想的“君子”来使国家和社会走向文明与秩序。此时,便存在君子“修己”之后,是否可以“治人”的问题。“修己”是“治人”的充分必要条件吗?如果不是,“修己”和“治人”又是什么关系?“修己”作为个体的道德修养追求,实为一种道德能力;“治人”作为理想社会的实现方式,实为一种治理能力。但道德能力能否等同于治理能力?答案是否定的。道德原则也不能推之为政治原则。余英时曾指出,“修己”和“治人”之间的混淆,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其中“以理杀人”就是将士人及其以上者的自我修养要求,推之于普通群众,即将“修己”的高标准贯彻于“治人”的程序中,从而造成严苛的后果[7]150-151。“修己”作为“治人”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对“治人”者的内在品行进行规约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治人”者,不仅需要胡居仁所说的“修德”之能,还需要智识因素,以此消除其带来的社会危害。
吕妙芬在研究胡居仁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指出:“一个人的思想内容几乎就是对其生存的时代所进行的思索与反应,虽然个人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创造力,常常是促使人类文明变动的真正力量,也是创造历史的主因,然而时代和社会所组成的复杂机制,却具有主导和限制个人创造的力量。”[8]3虽然,胡居仁所提的“修己治人”来源于孔孟学派以及朱熹,但是,置此主张于明代官官相护的背景之下,却体现了胡居仁作为官吏阶层的一分子,依照道德的应然性编造的理想世界,并借此理想世界来关照、批判其所处的现实世界的道德关怀。
三、立大本、用贤才:“修己治人”之道
胡居仁以“修己治人”之义为出发点,试图通过对社会主体的规约,加上对社会治理者的规范,辅之以刑法的约束,实现“圣人之道”治国的理想追求,完成理想社会的构建。
在寻求君子“修己”的道路上,孔子力求通过“克己复礼”“能近取譬”的仁之方法达至君子修身;孟子深受孔子道德修养意识的影响,提出“存其心,养其性”的道德修养方法;胡居仁在继承孔孟修身之法的基础上,提出个人道德修养之大本——“正君心”。“正君心”源自《大学》中所说的八条目之一的“正心”。“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4]8在朱熹看来,一个人的意识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心正,则身之五官皆可为其驱使,主体的实践才可以合乎情理[9]535。因此,朱熹在认识到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乃人之皆有的喜怒哀乐之本性,并且皆可导致心不正时,提出以诚意通达“正其心”。“正”即正直、公正、正当、不偏不倚的意思,“君”自古便有君子与人君之分,但胡居仁通过“君者所以为天下主”来诠释其人君之意[3]1 260。作为宋明儒学家之一的胡居仁,处于对程朱之言亦步亦趋的文化环境中,虽继承了朱子正心的修己之法,但也有不同于朱熹之处。他力求通过“克己则公矣”来实现“正君心”的道德目标。胡居仁以宇宙论为依托,借气禀之浑浊确认人心的拘蔽性,指出:“公生明,私生昏,私则有蔽,有蔽便昏。公则无蔽,无蔽便明。”[2]23人心只有不被外物所惑,不被情绪所左右,才能达到朱熹所说的“空”的状态,即理智、清醒的状态。同时,作为具有道德本心概念的“心”,其是否公平正大,是修身的关键。人君如若无法做到心正,“修身”就无从谈起。为此,胡居仁回到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范畴寻求仁政的轨道之中,在不排斥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的前提下,强调正心是使心不为外物所动摇,不为外在所影响,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过与不及,时刻保持清醒状态,进而在实践过程中能够合理地认识事物。而“克己”作为“正君心”的途径,要求君主从内心认同社会道德伦理,修得“公平正大之心”[3]1 260。其外在的表现为能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使自己的行为逐渐趋向于圣人之行。
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包含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将其推至社会群体两个方面。胡居仁所提“正君心”的向度是向内的,属于个体道德修养的领域。将这种道德修养作用于社会他人,则是胡居仁所提的治人之道的第一个方面,即“新人”。“新人”并非胡居仁所提,而是延续了朱熹的治人之说。朱熹所言“新人”是期望主体在“自新”之后当推己及人,把主体之明明德向外推之于社会,使天下之人皆能恢复本体之明德。相较于朱熹注重治人之革新的一面,胡居仁则强调“新人”的效法功能和上升过程。他以“正君心”为前提,力图通过发挥君主的榜样作用,实现常人之心向贤人之心的转化。“使朝廷既正,百官莫不正,百官既正,万民莫不正。”[3]1 260在君主个体的道德修养得到完善的同时,万民、百官必然是上行下效,追求较高的道德修养,万民及其百官也必然处于由常人之心向贤人之心的上升过程之中。
儒家学者矢志不渝追求的是圣人治国的理想社会,一国亟须君子贤人治理,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胡居仁在“新人”之后提出君主用贤的治人之道。早在先秦时期,儒、墨、法三家就已经提出用贤。孔子言:“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9]107孟子讲“尊贤使能”,荀子主张尊贤、任贤。至于墨法两家,则提出唯贤是举。胡居仁之所以重视用贤,一方面是对其所处社会政治黑暗的间接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其人性论的表现。胡居仁“修己治人”理论的思想基础是:以人性论为基础,肯定了人从性恶向性善转化的可能性,明确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也意识到,虽然君主的榜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主体道德修养的完善,但是作为具有喜怒哀乐之情的人必然无法逃脱气禀的影响,所以,他强调,君主要用贤以“壮国家之元气也”[3]1 260。基于孔子提出的“政在人为”“人亡政息”论,胡居仁将任用贤人与国家兴衰相联系,提出了“壮国家之元气”“政可立而民可安”的思想[3]1 260,这是对“不信仁贤,则国空虚”以及“隆礼尊贤而王”的延续[4]366。
胡居仁将治人置于“有耻且格”的观照之下。胡居仁治人之道的标准是要求治人者德才兼备,但若把“德”与“才”置于一处比较,他更强调德之重要性,注重伦理道德,即所谓“德之胜者为君子,才之胜者为小人”[3]1 260。贤者之士的素质主要是靠道德品质来凸显的。他强调贤才的道德教化和榜样作用,要求用仁义道德来治国,使百姓得到自我完善,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强大。这也是自孔子开始,儒家学者治国之道的显著特点。
依据德与才之间的伦理关系,胡居仁指出,要达到“治人”,君臣之间须以道义相处。胡居仁对孟子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思想进行深化,提出君为天下之主,“位乎两间,养贤以养万民,以至庶物莫不得其所养者”[3]1 260;臣为“食君之禄以养其身,而各尽其职分所当为者”[3]1 260。从个体而言,在位者谋其职。君、臣所处的位置与环境决定了二者的任务和职责,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君主的职责就是修身养德、德化臣民、任用贤才、治理国家;臣的职责就是精选人才、进贤退不肖。从整体而言,二者密不可分,君要完成自己综理万事,养天下之民的天下之主的重任,就必须依赖于贤能大臣的辅佐,只有如此,才能取得丰功伟业。无论是对于先秦儒家而言,还是对于宋明新儒家来说,在以“仁”为其理论核心,注重伦理道德的背景下,君、臣的权利都是相对的;并且在对待“义”与“利”的态度上,儒家学者都是重义轻利的。因此,胡居仁强调,要实现儒家学者所描绘的文明且有秩序的世界蓝图,除了须有“好道之君”与“有道之臣”外,还要求在治人的过程中,将道义一以贯之。唯有如此,“道既行,则可以保天下之民,岂不能保其身乎?”[2]52胡居仁所言君臣以道义相处也是立足当下的。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哲学之后,明代理学者意识到只有精通程朱理学才可以为官。于是,新儒学逐渐流为训诂之学,从道德诉求变为外在装饰,贯穿君臣关系的也“只是利心相合,未尝以道合”[2]52。
孔子在《礼》中提出,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核心,以“齐之以刑”为辅助手段,进而实现“为政以德”。可见,孔子虽强调德行以及礼仪规范,但也不否认刑的作用。胡居仁汲取儒家学者的治国思想,强调为政最主要的手段是王道政治,靠明君贤相,靠百官良好的道德风范感化众生,但也离不开刑法,需要坚持德主刑辅原则,对于贤人采取道德教化,对于恶人小人则须用刑法加以惩罚,如此才能使其有所畏惧。他说:“感化者,圣王为治之本。刑赏者,圣王劝惩之具,驭众之柄也。天下之大,生人之众,虽远近贤愚不等,然莫不本于一理。圣人在上,尽此理于己,安有不感化者哉!然善者爵而赏之,恶者威而刑之,亦此一理中之散而万殊者,圣人岂有意为之哉!理之当然也。然刑当乎理,众莫不惩,赏当乎理,众莫不劝。故此又为驭众之柄也。”[2]69胡居仁认为,王道德治的感化是为治之本,刑赏法治则是另一重要的辅助措施,是驾驭天下众人的有效之法。二者虽有主次,但王道与法治应该相互配合,缺一不可。
唐凯麟先生认为,儒家思想把道德实践作为个体安身立命、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根基[10]84;儒家强调道德实践的作用,特别是把个体的道德修养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这是儒家思想的主流精神[10]86。个体的道德修养无论是对于个体的自身来说,还是对于社会整体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胡居仁以“圣人之道”治国为其“修己治人”之道的落脚点,在继承孔孟学派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哲学后,希冀在道德哲学向仁政王国的转化中,通过对君、臣、百姓的德化刑赏,使其理想人格有所归宿。
综上,作为一名儒学的实践者,胡居仁提出的“修己治人”仁政主张主要脱胎于儒家政治观念,其中也不乏闪光之处。作为一种政治目标,胡居仁所继承的“仁政”一直是儒家学者在国家构建中所致力于寻找的最终归宿,而“修己治人”作为一种目标抑或作为一种手段,都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虽然圣人治国难免有其空想性,但是处于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适当的修身养性仍有其普遍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