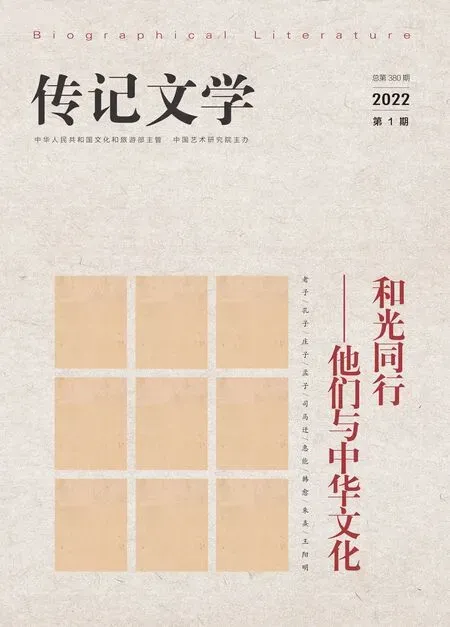司马迁:功追尼父,笔写千秋
宋亚莉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司马迁早年饱读诗书,在游历四方中追慕圣贤,将继承父志、效法孔子,做一代良史当作自己的平生事业。虽罹李陵之祸,仍忍辱发愤,继《春秋》,明王道,完成了史学巨著《史记》。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探求历史变化规律,批判现实社会和政治弊端,并融入时代审美风尚和个体情感体验,为我们留下了中华文明三千年发展波澜壮阔的史卷。司马迁也因此成为孔子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千百年来,以其高贵的灵魂、坚毅的心志、执着的精神,对无数仁人君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画像
效法古圣贤
司马迁生长在黄河之南的龙门山:“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传说大禹曾在此处开山治水,生于斯长于斯的司马迁,自幼开始诵读古文,饱览山河胜景,听闻历史传说,了解先贤圣迹。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司马迁开始南下游历天下,考察风俗人情。这应该是司马迁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游历名山大川、古迹名胜,追寻前人的行迹,与百姓交谈的游学活动,使司马迁对历史有了更加深切的体悟,这些最终都沉淀于《史记》之中。他行至会稽,探访禹迹,感受大禹治水的艰辛;登上箕山,寻绎许由的坟冢,追思其高义。他深深地理解屈原的殉国,亲自到屈原自沉之地,为之伤心哭泣。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孔子是司马迁最为仰慕的人物,他在《孔子世家》中曾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故而他到鲁国,久久不愿离开:“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他认为孔子一介布衣,为天下学者宗尚,“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诸篇之中,多引孔子言辞,如称赞田叔的贤义,引“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列传》);肯定万石、张叔的笃行,引“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万石张叔列传》);称张良状如妇人好女,不可以貌取人,引“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世家》);谈鲁国之乱,引“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龂龂如也”(《鲁周公世家》)。对孔子的敬仰之情,在《史记》随处可见。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和风格》一书中谈到司马迁“却已经把《论语》的成句,熔铸成自己的文章了”,“司马迁的精神,仿佛结晶在孔子的字里行间了,仿佛可以随意携取孔子的用语以为武器而十分当行了”。
司马迁尤其喜欢信陵君魏无忌。他曾到薛地寻探当地的风俗人情,发现民风彪悍,乡闾之间多是暴桀子弟,完全没有邹鲁之地的淳朴民风,询问百姓缘由,竟是“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由此认为“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史记·孟尝君列传》)。他还到大梁的废墟中去寻找夷门,感受当年信陵君魏无忌和门客侯嬴的交往事迹:“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史记·魏公子列传》)他与梁国遗民交谈,听到有人说“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便为魏无忌不平,认为魏国之亡不在魏无忌一人:“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记·魏世家》)公允地指出秦灭魏乃大势所趋,非魏无忌一人所能救,更将魏无忌的传记尊称为《魏公子列传》。战国四公子之中,黄歇、田文、赵胜则分别名列《春申君列传》《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中,可见司马迁对魏无忌的喜爱之情。
司马迁还亲自到过淮阴,与当地人聊起韩信,有人告诉他,韩信布衣时,就与众不同,家贫无以葬母,就选择“旁可置万家”的开阔之地。他亲访此地,“余视其母冢,良然”(《史记·淮阴侯列传》)。他到楚国故城,看到宫室盛大,感叹明智一世却败于李园的黄歇:“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史记·春申君列传》)
也许无数个夜晚,要成为怎样的史官,要记载怎样的历史,常常萦绕在司马迁的脑中。辗转反侧之际,仰慕、追寻与探求,种种情绪挥之不去。对司马迁而言,史官这个职业,是继承先祖遗留,是人生理想与追求,更是使命与责任。
《史记》中记载了诸多史官,折射了司马迁的对史官这个职业的敬仰和尊重。史官秉笔直书,不惧生死。齐国的太史兄弟二人,直书崔杼弑君而献身;晋国的太史董狐,乃“古之良史”,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晋世家》),使朝野知赵盾之事。史官能推举贤德之人,郑庄为太史,推荐天下贤达长者,“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汲郑列传》)。最重要的是,史官能预见王朝兴衰,为王朝发展指示方向。据《史记》所载,周太史伯阳读史,预见了周之将亡,或与褒姒、伯服有关。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周幽王爱褒姒,欲废王后和太子,周太史感叹道:“祸成矣,无可奈何!”(《周本纪》)周烈王二年(公元前374),周太史儋见秦献公,预见了秦国未来发展将不可估量,说:“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秦本纪》)《田敬仲完世家》中的周太史,占筮得到“观之否”卦,预见了陈完将来取代姜姓齐国而为田氏齐国。郑桓公询问太史伯,王室多变故,何处可安身?太史伯分析了地利与人和,认为“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郑世家》),指示了郑国的发展之地。
游历开拓了司马迁的眼界,考察了各地风俗人情,加深了对自身使命和责任的思考,历史上的诸多圣贤成为司马迁心中的典范。此时的司马迁,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向往,他在与好友伯陵的通信中说“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清楚地展示了他的人生理想。
发愤著《史记》
元丰三年(公元前110)四月,司马谈病故。三年后,司马迁继承父志成为太史令。家族的荣耀、父亲的期望、个人的责任和使命,使得司马迁非常重视自己的工作:“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戴盆望天,意思是头顶着盆子望天。如淳注:“头戴盆则不得望天,望天则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如履薄冰、尽职尽责由此可见。
天汉二年(公元前99),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李陵寡不敌众,兵败投降。汉武帝食不甘味,群臣忧惧。司马迁与李陵并非至交:“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与李陵一为文官,一为武将,“趣舍异路”,未有衔杯之交,但司马迁置性命身家于不顾,站出来为李陵说话,认为他奋勇为国,投降是权宜之计:“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司马迁说的是实情,但时机不对,更在言辞之间得罪了汉武帝宠姬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一怒之下将司马迁下狱。司马迁面临前所未有的困窘之境:
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汉书·司马迁传》)
危难之际,司马迁没有自赎的钱财,又没有人敢替他说话,连自辩的机会都没有,因而惨遭宫刑。为此,他痛苦万分:“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汉书·司马迁传》)甚至精神恍惚,不知如何自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汉书·司马迁传》)此情形之下,司马迁可能想过自杀。他在《悲士不遇赋》中写道:“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而之所以没有自杀,则是因为担心“志行之无闻”,人生的价值未得实现。对他而言,死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死得毫无意义:“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作为史官的司马迁,从历史上无数历经磨难而终成著述的人物中汲取力量,用于完成《史记》的撰写: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汉书·司马迁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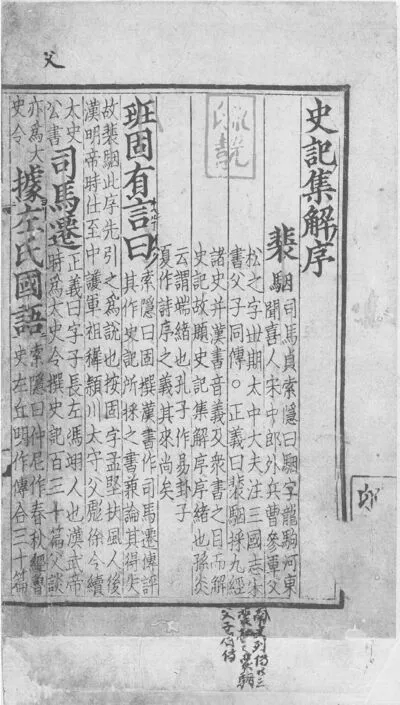
《史记·史记集解序》(部分)(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刊本)
这段言辞,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两次谈及,与其说是叙述历史,不如说在反复激励自己以前进。司马迁再次坚定了自己的方向,认定《史记》能够“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汉书·司马迁传》)
汉武帝并非昏聩的君主,之后有所醒悟。《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但司马迁已经不是之前的司马迁了,他开始与朝廷政治保持着距离,也与朋友保持着距离。任中书令后,他的朋友任安曾写信给他,“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任安希望他能够在汉武帝面前“推贤进能”,司马迁回以《报任安书》,拒绝了好友的请求。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可能是任安的求救信。征和二年(公元前91),巫蛊案起,戾太子发兵与丞相战于长安城,任安受太子节而按兵观望,太子后败,任安被武帝腰斩,理由是“持两端”。这封回信在征和二年十一月。汉代旧例,在腊月处决犯人,任安可能危在旦夕。司马迁也知道这点,故言“今少卿抱不测之罪”,但最终司马迁拒绝得非常坚决:
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
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 《汉书·司马迁传》)
意思是,以现在的情形,即使朝廷人才缺乏,我也无脸昂首品评政治,推荐贤德之人;倘若这样做,就是对国家和士人的羞辱,你的信中所求,实在无法实现。此时司马迁的拒绝,拒绝的不仅仅是任安,而是过去的自己。
司马迁在坎坷仕途中遭遇的惨痛而真切的人生经历,赋予了《史记》以内在的精神与情感张力。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这个“惭耻”,说的何尝不是那个深陷囹圄、救助无门,“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的自己呢?他写世态炎凉,见风使舵:“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平津侯主父列传》)“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他借翟公写在门上之言表达这种悲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列传》)也正因为自身的经历,加上对儒家思想的坚守,他并不喜欢法家人物,他批评商鞅为天资刻薄之人,他憎恶酷吏,认为刑罚并非制治清浊之源。
司马迁同情李广将军,为其遭遇不平:“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李将军列传》)他替“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的苏秦鸣不平,认为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苏秦列传》)。
也因为这些人生经历,他无数次为悲剧人物高歌,肯定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激赏他们的抗争之举。勾践卧薪尝胆,终得复国。伍子胥为父兄复仇,不惜鞭尸三百,恶言“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司马迁却看到了对命运的不屈反抗,认为他是铮铮烈丈夫:
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史记·伍子胥列传》)
而这种对昏庸君主的反抗,在《史记》中尤其突出。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谈到,司马迁喜欢书写对抗君主的故事,对个人的自由礼赞有加,“这恐怕是他因李陵事件遭难后最终到达的心境”。他让《陈涉世家》里卑贱的陈涉,说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豪言壮语,起义抗秦之际,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悲情与抗争交织,凝结成了《史记》独立山巅的崇高之美。我们看到,《史记》写的不仅是诸多人物的抗争,还是司马迁的个体的抗争,他在众多的历史人物身上,寄托了个人命运,《史记》因此而具备了鲜明的感性特征。

《史记·太史公自序》(部分)(南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刊本)
不与圣人同是非
元丰三年(公元前110),司马谈临终之际,深感自己没有完成太史的使命,叮嘱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此时,家族的荣耀感、使命感以及父亲的殷切期望,感动着司马迁:“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这部父亲殷切叮嘱的史书,从撰写之始,司马迁就明确表明此书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对《春秋》的效仿: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认为,周公之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之后到现在也是五百年,谁能继承孔子之遗志呢?这正是著书之契机,怎么能辞让呢?自序中还谈到,鲁哀公西狩获麟,孔子之《春秋》至此辍笔。“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提及微言大义、寓事于褒贬之中的春秋笔法,《匈奴列传》中说:“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襃,忌讳之辞也。”《儒林列传》中说:“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在司马迁与友人壶遂的一次讨论中,司马迁谈到史官的志向、职责,更论及《春秋》的社会功用,其中“《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几句,更将《春秋》推到无比尊崇的地位。司马迁对“五百年”的强调,对“获麟”的重视,对《春秋》的尊崇,处处彰显了司马迁欲效《孔子》著《春秋》而撰《史记》的人生理想。
当然,尊崇孔子及《春秋》,与汉武帝时代崇儒学、尊《春秋》的社会风尚密切相关。此时以汉武帝为首,汉代朝野上下对《春秋》极为重视,汉武帝甚至以“春秋之义”解读对匈奴作战:“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史记·匈奴列传》)此风气之下,司马迁效《春秋》而撰《史记》,应该也有借《春秋》之名以推崇自身之学说的考虑。不少学者也指出这点,如明代史学家柯维骐说:“隐约之士,意有所弗遂,故或詠之为诗,或著之为书,以传于来世,如文王、孔子是已……鲁郊呈祥,汉武再见,故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迁之自任,亦重矣。”说的也是此意。
司马迁的人生之中,虽然仕途坎坷,在现实政治中处处碰壁,身心俱疲,甚至想到过死,但始终没有放弃继《春秋》而著史书的信念,大约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后,司马迁以顽强意志完成了《太史公书》: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
此书在西汉以至东汉中期,都被称作《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简称《太史公》。韩兆琦认为,“史记”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始于东汉后期,而到三国时代,《史记》作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已经非常流行和普遍了。司马迁的此“一家之言”写成,又抄副本。全书首开纪传体例,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八书、十表,以人物为中心,以族谱为框架,本纪、世家分国编年叙事,宏通博伟;更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网疑,保存了众多史料。书中孔子之仁、项羽之勇、刘邦之智、陈平之谋、季布之诺,人物特色鲜明;大禹舍家治水、勾践卧薪尝胆、张良运筹帷幄、商鞅为国变法、屈原忧国沉江、扁鹊妙手回春、缇萦舍身救父,事迹生动。历史长河中诸多人物的生平事迹与人生抉择得到尽情展现:有人一生清贫,有人一世平顺;有人一战成名,有人难获封侯;有人一语成谶,有人因梦腾达;有人生于安乐,死于忧患;有人舍生取义,坚守傲骨;有人屈服权势,有人至死不甘……
这部“一家之言”,以《春秋》为绳墨,“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呈现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的史家风格。如在《平原君虞卿列传》里,司马迁激赏平原君赵胜乃翩翩公子,也毫不掩盖其贪图小利、引发长平之战的罪过:“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他肯定李斯在秦帝国统一六国中的贡献,“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也毫不掩饰其与赵高同谋,造成秦二世而亡的事实:
斯知六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史记·李斯列传》)
他为李斯深感到痛心,如若不是贪恋权力,不会导致身死国亡,李斯的功绩甚至可以与周公、召公并列。如孔子撰写《春秋》感于当时社会政治,司马迁在对历史的批判中也寄予了现实的忧患感。
《史记》继承了《春秋》笔法。《春秋》以一字言兴衰褒贬,而《史记》中的布局谋篇、列传安排就蕴含着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态度。司马迁将吕雉写入《吕太后本纪》,孔子入《孔子世家》,陈涉入《陈涉世家》,更尊魏无忌传记为《魏公子列传》。不仅如此,还以“互文足见”之法,本传之中多褒,他传之中多贬。刘邦彭城兵败逃跑,为保身家性命,多次将儿女丢弃,此事载于《项羽本纪》而未见《高祖本纪》。全书于全局中见褒贬,于特例之中见春秋笔法。
这部“一家之言”,尚勇尚奇。他在《鲁仲连邹阳列传》中视鲁仲连为奇士:“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他在《刺客列传》中评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他在《游侠列传》中激赏游侠之勇:“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他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赞赏蔺相如智勇兼具:“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这部“一家之言”,质疑天道、反叛旧说。在《伯夷列传》中,他提出质问: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这是司马迁尤为激烈的一段评赞,他连连发问,都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伯夷、叔齐仁义洁行,为何最终饿死于首阳山;孔子爱徒颜渊,安贫好学,竟然早逝;暴徒盗跖,杀人聚党,横行天下,却安得天年。这是报的何善?遵的何德?他重视经济与民生,直言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他写致富成名之人,如子贡、陶朱公、乌氏倮、寡妇清等,肯定他们的价值。他没有从男权的角度否定吕雉,而是充分肯定吕雉在建国之初恢复帝国经济发展中所作的贡献:“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这些内容备受批评,班固、扬雄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不与圣人同是非”,现在看来,正是《史记》不同于《春秋》而胜于《春秋》之处。
《史记》在司马迁生前少有人知,至汉宣帝时才逐渐流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司马迁传》)在后世,《史记》不仅是二十四史之首,也是历代正史的典范,如明灯般照亮了中国文学和史学的发展之路。书中的人物和事迹,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逐渐熔铸于我们的思想与灵魂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与精神,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说司马迁“功业追尼父”,可与孔子比肩,良非虚誉。
注释:
[1][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第10册),中华书局2014年8月版,第3998页。文中《史记》引用皆出自该版本。
[2]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和风格》,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0—51页。
[3][5][清]严可均编纂,陈延嘉等校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3页,第500页。
[4][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册),第2729页。文中《汉书》引用皆出自该版本。
[6][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解读〈史记〉》,中信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14页。
[7]周振甫:《〈史记〉集评》,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4页。
[8]韩兆琦:《史记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页。
[9]郭沫若:《题司马迁墓》,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编,张天恩、冯光波选注:《历代咏司马迁诗选》,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