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先生的为人和治学(一)
赵 明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公木先生逝世已经22年了,但在我的精神世界中,他始终没有离去。我做过他的学术助手,师从先生十年。其后,虽云山阻隔,仍有十年的书信往来。甚至,在他逝世半个月前,我们还有声息相通。在先生离世后,文艺界、学术界许多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因他真诚、宽厚情怀中的人性光辉而缅怀景仰、唏嘘感叹。我从游公木先生近20年,对于他的为人、治学都有近距离的观察和感受。不少了解此情的朋友和学生,曾建议我把这段历史写成文字,以使更多的人了解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显名于世的公木先生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邃的精神世界。我不能拒绝这个建议,我对公木先生的缅怀,不应默存于心里。“向前!向前!向前!”以军歌激越百万将士、提振雄威的公木,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其中就包括我师从公木先生多年,所历、所见、所闻的诸多故事。
公木(1910—1998),原名张永年、张松甫,又名张松如,直隶束鹿(今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后改为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青年时期赴延安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调入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任主任。1942年,他听到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参与讨论。1946年,他赴东北,曾任东北大学教育长、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长。“文革”结束后,历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吉林省作协主席等职。公木先生是“业余”诗人,一生都在从事教育管理和教学研究工作。他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是培育了几代学人、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但最重要的是,他追求真理,正直一生,躬尽辛劳,虽屡经坎坷而不改初心,成为无数后学心目中人伦师表的楷模。
一朝春暖
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从这个积雪消融的春天开始,我所在的农村,地处长春郊区的新立城,已陆陆续续有插队知青和下放干部返城。我在农村生活历时8年,早已牢固树立起扎根农村,生于斯、老于斯的念头。不是我不想回城,而是我没有任何人脉关系,没有什么骄人“资本”去寻找可接收我的单位。我的青年时代和而立之后长达十年的中年期都已结束。我蹉跎半世,与其返回城里,还不如过着远离喧嚣、较少人际纷扰的村居生活。在农村的日子,也让我有了另一种收获:从春雨、夏风、冬雪、朝霞、夕晖,到一年四季时序流转、草木荣枯、万象更变,我从不适应到适应。在这里远比在城市更能亲和自然,能够接受她的抚触和慰藉。比起城市,农村生活确实很艰苦,我住着两间草房,夏漏雨、冬透风,每年都要修葺;住在坡上,没有水井,一切生活用水,都要到坡下的一口井去汲,回来便要担着两桶水一路爬坡。这是当时我们基本的生活情况。但比起刚下乡时与插队知青同住的情况,已是大有改善。自我在农村和知青共住两年之后,在一块坡地上,我终于建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而我周边的几户村民,也都朴实、善良,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如草屋修葺等事),也都会热心帮忙。就在1977年的春天,我从几十里之外的山区买来一车柳树枝,把我这两间草屋、三分宅基围成了绿色庭院。我是真的准备后半生像陶渊明那样过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生活了。但是,当我筑起的“家园”的绿墙又经历了一个春秋的风雨栉沐,柳条围墙已成一道绿阴风景的时候,我才如梦初醒:眼前的田园生活和所谓“诗意般地栖居”,能为我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儿子长期接受吗?做医生的妻子想返回长春工作,并且已经收到商调函;在农村长大,刚刚上小学的儿子也需要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我的“陶潜梦”,到了应该清醒和立即决断何去何从的时刻了。我明白,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一个愿意接收我、同时我也愿意去的工作单位。
我把妻子接到单位商调函的信息和我求职的想法告诉了在吉林大学工作的兄嫂,他们分别在哲学系和中文系任教。嫂嫂李扶乾1961级吉大毕业后留校,对中文系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时已到了1978年的夏秋,1977级的学生即将升入大二,1978级同学又刚刚入学,1979级的课程安排和师资配备也进入了议程,兄嫂所在的系都已引进了不少教师。我的想法是哲学系或者中文系都可以,能进入吉大就好。嫂嫂建议我到中文系,并热心地承担了推荐和沟通的工作,但我心里还是很不踏实:荒废了学术青春,继之又僻居乡村多年,已届“不惑”之年而实“多惑”的我,到底能再做什么?事到临头,面对“大考”,我才发觉这确实是个躲不过的坎。
从程序上来说,要调入系里任教,首先要经由教研室做专业考核,再由系务会议讨论通过,然后上报人事处,等待学校批准。完成这个程序要很长的时间,其中一个环节受阻,我的“戏”就结束了。我的理想是进古典文学教研室。我的弱点是年龄偏大,而且还缺少考核需要的成果,也没有和年龄相配的学术职称。这些弱点,自然会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引进工作中触及并讨论。这时,担任系领导的程书记向我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已届古稀之年的公木先生时任吉大副校长兼中文系名誉主任,此外还兼任多项重要社会职务,亟须配备一名学术助手,目前尚未定人选。如我愿意,他即电话联系公木先生。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对他表示感谢。程书记当场打了电话之后,随手就在桌上撕下便笺,上面写着:
公木,东中华路33号201。上午,9点30。
东中华路33号的公木先生
长春市东中华路是条整洁而静谧的短街,它的东出口通向吉林大学鸣放宫,西出口则通向开阔的地质广场。这条不足千米的短街,竟然泰斗云集,大家荟萃,先后居住过众多大师级的学者,其中数理化学科的就有朱光亚、唐敖庆、余瑞璜、吴式枢、王湘浩、高鼎三等人;而文史哲方面则有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历史学家金景芳,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作家废名和哲学家高清海等。
那是9月中旬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公木先生约我到他家见面。他住在东中华路33号被人们习惯称作“十八家”的一幢小楼里。这幢建于20世纪50年代,灰瓦、黄墙、红院套的3层小楼,因为居住过不少名人,我在年轻时就有耳闻,心向往之,路过时也曾多次仰望,但惜乎难得一见大师们的仪容趋止。在赶赴东中华路“十八家”的路上,我的心情渐趋紧张,不停地猜想:即将出现在面前的公木先生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电影《英雄儿女》主题曲的歌词作者,该有一副怎样肃肃威严的仪容呢?他的歌词,连同他的笔名“公木”二字,都让我联想到“革命”“战斗”“坚强”……
想着,想着,我已走进了“十八家”的院内:两侧几株乔木在阳光下,“涂金”的叶片闪闪发光;树边的田垅里,还剩几行枯黄了的玉米秸依然挺直;几个橘红色的硕大南瓜横卧地表,晒着和煦的秋阳。看到院内这种农家景象,一瞬间,我的心情平缓下来,心理上的距离似乎缩短了。我穿过一条小径直抵一楼门洞,快步走上二楼,在201室门前稍停,看表上时针到了9:30,正好是约定时间,我轻触了门铃。一位父辈年纪的长者从室内迎出,我趋前问候,报上名字,老人直接把我引入卧室里间的房内。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位学者的书房。除了靠窗的南向,整个房间排满了书架,每个书架上又挤满了书。还有一些书和报刊,因为无处容身,暂时堆放在房间的角落里。南向窗前,有一张黑赭色的写字台和一把竹椅。面对写字台的方向,摆放着供单人坐的两只布沙发,也和桌椅一样,是老家具。我知道面前的人就是公木先生。他见我有些拘谨,便先示意我在沙发上坐下,回身又倒了一杯水给我,然后坐回到他的竹椅上与我相对。此刻,我的心情已放松下来,并迅速完成了对公木先生的“扫描”:我面前的长者中等身材,一身浅灰的便装,配着黑色的布鞋。说不上魁伟,却足够挺拔结实。方头宽额,鬓发虽已花白,眉宇间却仍透出一缕英气,端庄的仪容,半显坚毅,半露慈祥;而一双很有神采的眼睛,也会让人感受到非凡的睿智。这次对我来说可谓是重大机遇性的见面,并不像我事前想象得那么正规、严肃,而俨然如我和一位长者之间进行的一次亲切交谈。公木先生从询问我的个人经历和家庭情况开始,很自然地把话题引入到读书和志趣,然后便倾听我的读书心得,进而对我作出评价:他认为我对所读的书拥有个人的视角,特别是我对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学者王夫之撰写的《船山遗书》的通读,使我能够跟随王夫之的引领,理清从先秦以迄宋明这段时期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脉络和梗概,这不仅开阔了我的文、史、哲视域,同时也使我经历了一次很好的学术训练。王夫之不仅为“六经”“别开生面”,而且对以《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著作和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评述,也都令人耳目一新。此外,他在史学和文学领域也多有开新之论,如《读通鉴论》《宋论》《楚辞通释》及所著《诗话》的诗论等,也多发前人所未发,令人服膺。通读中的专注和思考,于我而言,收获是远大于听课和读教科书的。《船山遗书》是我二十几岁时下过功夫认真读过,并做了大量文献卡片和分类评语的一部大书。我之所以用时两年阅读此书,缘起于1961年年初,吉大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吴锦东老师邀我合作撰写一部有关王夫之的专著。他要求我先行通读全书,做好资料准备工作,然后再找他商量提纲拟定和分工撰写等事宜。我好不容易啃下了这个“大部头”,待到去找吴老师请领下一步工作任务时,却发现门锁高挂。到哲学系问询吴老师去向,有知情人告知他早已离职回印度尼西亚结婚(吴老师是华侨),后又到香港经商去了。我摘写的大量资料卡片和几本阅读笔记,就这样成了一堆废纸,但我并没有把它们扔掉,而是装进一个大纸箱中,作为纪念品保存了下来。同公木先生的见面,给我提供了一个自由选题、自由发挥、展示所长的机会,让我把多年用心做足的功课,集中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进行了概略陈述。因此,初次面见学识渊博的公木先生,我就得到了赏识。当然,这些都不是公木先生直接对我说的,而是事后中文系的领导私下告知我的。我在当时只是感觉公木先生在认真而耐心地听,间有几次插话提问,并无任何诘难。最后,当我辞别公木先生时,他起身后只简短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回去等待吧。”我退出书房,如释重负,心情完全轻松下来。返家的路上骑着自行车,50多里的距离,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妻子在家坐卧不宁,一直惦记着今天面试的结果,当我把最后那句话告知她时,我们这才相信8年的农村生活即将结束。晚上,躺在多年睡习惯了的土炕上,我总是睡不着,想着白天的事:东中华路33号,坐拥“书城”的公木先生,还有他那深邃而慈祥的目光、他倾听时的沉思……身旁的妻儿都已入睡。睡炕前的窗棂,浮动着徘徊荡漾的月光,透进草屋,有几缕映射到贴满旧报纸的土墙壁上。这一夜,我身如梦,又似梦非梦。时光的流逝、命运的起落、偶然的机缘,有时真让人辨不清真与幻、梦与觉的界限。
撰《老子校读》的公木先生
1978年10月初,国庆节刚过,我和妻儿告别乡居,举家返回长春。“文革”结束后,高校住房本已极紧缺,新调入的人员很少有得到学校安置住房的。好在,我临时在校外借到了一间小房,全家人总算有了落脚之处。芳华虽逝,但我的学术青春却由此展开。
在吉大中文系,公木先生主要从事古典文学专业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学工作。作为他的助手,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学习中协助,在协助中学习。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准时来到公木先生家中,准备听取他的工作交待。

公木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后排居中者为本文作者
但是,当我走进书房,向正在伏案写作的公木先生请领工作时,他先是抬头看了看因为搬迁而有些憔悴的我,然后又示意我坐下。我有些不解,公木先生认真地问起了我回城后生活如何安排等问题。他显然清楚,从乡下回城,住房肯定是一大困难。说心里话,工作伊始,能够听到公木先生这样的大学者问起自己生活中的冷暖困苦,已经很令人感动了;更意想不到的是,前一天傍晚,公木先生还利用饭后的时间,穿过东中华路东口,又过了条南北通向的大路,步行到鸣放宫所在的那个空旷的大院子里(现称“牡丹苑”),去看他和妻子吴翔老师曾经住过的两间仓库房。“文革”结束,这两间仓库房在他们搬出之后,便空置起来,被校后勤部门用来堆放杂物。公木先生看到仓库房未被他人使用,决定待我到来后即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如果愿意入住,他就找后勤部门疏通一下,以便我尽早把家安顿下来。我听后感谢之情难以言表,顿出哽咽之声,但为极力控制情感,不让眼泪流出,我没有迅即回应先生。他大概以为我在条件上有所考虑,不愿去住。于是又强调说:“这只是暂时的,眼下学校实在困难。我都能住,你有什么不能的!”
就是这句话,让我思索并回味了几十年:这里有公木先生的艰辛经历,有他无惧困苦的坚韧意志,但更多的是他对我现实困境感同身受的关怀。是的,长我近30岁的公木先生能住,我又有什么不能住呢?这个约有两间大小的仓库门房,并不比我在农村那两间草屋差,至少不用我每天爬坡挑水。对于短暂栖身来说,已经是够“档次”了。只是因为此前我已在朋友那里借到了一间居室,三口之家也还住得开,我不想让公务繁忙的先生再为我的家事操心费力。但这件事让我感受到的温暖,却永驻于心,终生难忘。半年后,在吉大工作的兄嫂调入北京工作,而公木先生也出面向学校总务部门提出了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入住理由,我因此搬入他们的两居室。自此,进入了“安居乐业”的状态。
我的助手工作,最早就是从公木先生的老庄研究介入的。在我到来之前,公木先生倾注了多年心力撰写的《老子校读》初稿已近尾声。我来后,先生把已竣稿的上编《道经》部分4本手稿交给我,让我先校阅一遍,校阅中有什么想法、建议可记录下来,随时向他提出。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主要注意力也因此投注到研读《老子》和《庄子》上。
公木先生对老子的兴趣和关注由来已久。他晚年撰著《老子校读》以及脱胎于此书的《老子说解》,曾令很多关心或熟悉他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们不解:“红色诗人”公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东方红》《英雄儿女》主题曲这些广泛传唱、深有影响的曲目的歌词作者公木,怎么会同撰著《老子校读》的张松如联系在一起呢?在别人看来,两者之间不仅横着一道难以相融的巨大情感障壁,而且它们文化色彩的反差亦甚鲜明。如果只是把公木看作以诗歌为战斗号角的“诗人”,我们就难以理解学者公木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甚至我们也无从理解革命岁月、战士经历和历尽坎坷之旅的公木是怎样成就了“战场奏军歌,人伦树师表”的人生。
首先,在到延安之前,青年时期的公木已涉猎了大量的原典、古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老庄对他的精神建构必然有所影响;其次,公木的中年和老年时期,老庄哲学对他不无纾困作用,提供一种精神力量和豁达情怀。而他晚年撰著《老子校读》,更因缘于两件事:第一件事是,1973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发掘出西汉初期长沙王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其中的大量精美丝织品和包括帛画、帛书在内的珍贵文物得以面世。其中帛书有《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与后世诸多通行本有异。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启发了公木先生以帛书本《老子》检验校正后代诸通行本误读错简的念头。第二件事是,1973年以后,大学的文科教学还缺乏规划。公木先生感到迷惘,“因想到老氏之旨,以清虚谦弱自持,或可医治我无补于时无济于世的忿戾偏激”(《老子校读》“后记”)。这时,公木先生开始了专注《老子》的著述之路。整整一段时间,他闭门索居,读帛书、校《老子》,没有谁知道他在搞什么,只有住在隔壁的古文字学大家于省吾先生与他相互过往,引为同调,时有摩研切磋,抑或公木先生于篆籀古文的释读有所请教。此外的知音人,就是逾世之交、同在长春而在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的杨公骥先生。公木先生与杨公骥先生二人相识于延安,又于50年代初期合作从事文史研究。待到1976年后,二者学术上的联系渐多,公木先生把《老子校读》竣稿的部分不时寄给杨公骥先生,二人亦借书札往来,论《庄》说《老》,析辨奥义。时间到了1978年春,公木先生担任了由校到省,直到国家的各种职务,会议接连不断,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实在是生活在忙乱中,晕头转脑,顾此失彼,不加强压力,自然便停摆了也”(《老子校读》“后记”)。是年4月26日,公木先生接到同样也是宾客盈门、文债如山的公骥先生的赠诗:
寒霜历尽又逢春,
枯木重华稀世珍。
座上不虚谈笑客,
案头未了应酬文。
悬口滔滔浮白日,
垂发皤皤挽黄昏。
欲追王弼穷奥旨,
怎奈无暇学老君。
诗中提及的王弼,是曹魏人,著名玄学家,以《老子注》闻名天下。1978年秋冬之际,《老子校读》的撰写已近尾声,而公木先生却诸事纷繁、多任在身的时刻,我来到了他的身边。我能协助先生的,多是抄抄写写、校对文字一类的事,而在这种协助的过程中,我倒是有机会认真踏实地习读《老子》诸多传世本,也算是穿越历史,在“老子学”中走了一遍,这对于我后来撰写《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以及有关道家与中国文学的系列论文奠定了基础。1979年冬,为周围同事、左右师友关注和期盼了6年之久的《老子校读》终于面世。但没有想到的是,对于我为此书所做的那份微不足道的工作,公木先生竟给予了热情洋溢的鼓励和不吝笔墨的肯定。他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直到去年冬赵明同志调来我校,助我一臂,才把劲儿上足,时钟再度发出滴答声,今年春天赴京参加诗歌座谈会归来,一鼓作气,命笔急就,又把《德经》四十四章赶了出来,全部杀青,是在五月。于此期间,还综合八十一章说解大意,写了一篇《论老子》,这篇东西,便更加是与赵明同志共同探讨,并得他协助才写成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赵明同志,此书或将功亏一篑,那是大有可能的。”整整40年过去了,今天看到先生的这段深情奖掖的文字,我只深感有负先生,愧对先生的奖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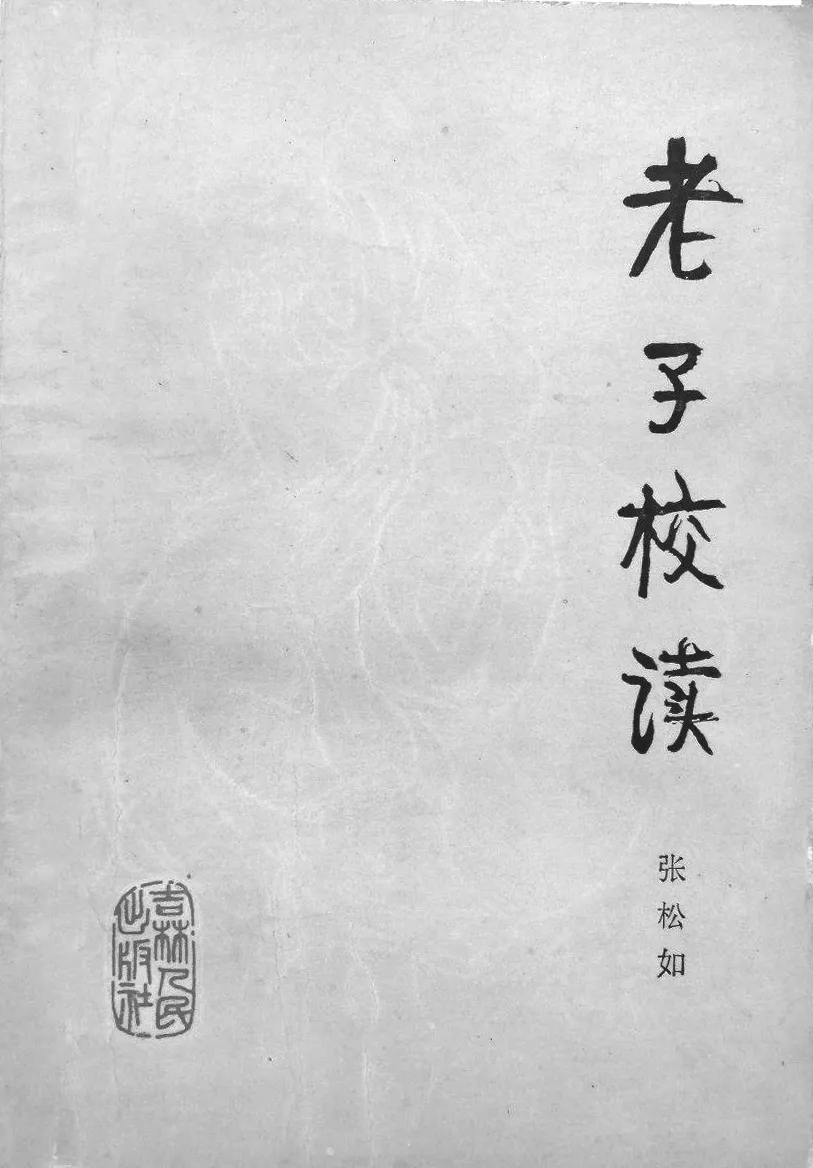
张松如(公木):《老子校读》
公木先生的庄子情怀
对于撰著《老子校读》,公木先生曾戏称自己是“初学”,说自己“是一个富有兴趣,敢凑热闹的人”。事实上,以诗为人所知的公木先生于经史、于古文字,都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公木先生在青年时代曾为高级中学讲授国文和文字学课程,他编著的《中国文字学概论》,由他的老师、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黎锦熙审订后出版。扎实的文字学和经史功底,在他的很多著述中都有所显示。他在晚年撰著《老子校读》,实亦渊源有自而非偶然。《老子校读》是在1993年湖北省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竹简《老子》之前,较早利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用以检校后世诸通行本《老子》的著作。这部专著不仅做到了“悉取古今诸本,检别疑谬,审义所安,择善而从”,写定“经文”并附以“校释”,而且全书81章每章都缀以“译语”和“说解”。《老子》是近于诗体的古文,公木先生又是学者兼诗人,所以每章的“译语”,都以生动、活泼的现代语言,让读者享受到奥义玄思中的深邃诗意或恍惚朦胧的老子诗美。这一点,只要将它和诸家译语略作对比,特色立判。最后的“说解”部分,既针对每章主旨作“原汁原味”的解读,又联系全书按老子思想的逻辑线索作引申和发挥,使读者读每章都得窥《老子》全貌。这样一部既完备又有特色的《老子》读解本,它的问世,必然会引起海内外学人的关注。果然,不久中国台湾旅美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以研究老庄哲学蜚声海内外的陈鼓应先生,在其所著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老子今注今译》中,即“嘤鸣友声”,不仅对公木先生的《老子校读》作出了公开的学术回应,而且他本人也不避远途,专程来吉大拜访公木先生以达仰慕敬重之意,遂由“相忘于道术”的默会而有了后来合著的《老庄论集》(198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面世。大约也是在此前后,又有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池田知久教授一行3人专程来访公木先生,就日本的《老子》研究和有关老子的诸多感悟与之交流讨论。池田知久教授等人为了更详尽地了解公木先生最新的老子研究,特意在吉大招待所驻留了3天。其间除有一次面见公木先生外,其余具体交流工作便由我代劳。池田知久教授回国不久,即在日本《海外东方学》杂志上著文介绍了公木先生其人和他的《老子校读》。此后,还有多位日本汉学家,以拜访或书信的形式,继续了有关《老子》的文化交流。公木先生在完成有关老子的著述后,曾有过接下来再写一部关于《庄子》的书的想法,他多次在与我的交谈中流露:他对兼具深邃哲思与悲悯诗情的《庄子》由衷喜爱和激赏,在情感和审美层面上,甚至超过了对《老子》的兴趣。我长期受公木先生情怀熏陶,对此亦深知之。实际上,具有浓郁诗人气质,想象力超拔瑰奇,行文漫无涯际的庄子,才是公木先生的神交和心仪对象,是他晚年祈望的一个能与前哲共舞遥契的心灵之约。很遗憾,他急于做和必须做的事情太多,不能推辞的会议也太多。他能放弃自己的热爱,却不能冷却诗人的热肠和对社会的责任。他对刚刚崛起的一代诗坛新人和初绽蓓蕾、尚待滋溉的文学青年,都担负着园丁般的责任。他抽出很多时间看诗坛新人寄来的诗刊或信件,给他们写评论,引导并呵护他们的成长,其中就包括舒婷、北岛和徐敬亚等“朦胧派”诗人。他还担任着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主管全校文科科研、职称评定等事务。叩门找他主持“公道”和向他倾诉的教师,有时一天中就要接待几个。这都因为他太热心,太平易近人,太主持正义。一向健康,很少患病的公木先生,在这样多头绪、多“战线”、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

1979年10月,公木(右二)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留影
1981年春,持续的心绞痛引发了心梗,公木先生住进了医院。对他来说,有限的精力还必须落在诗和诗学的领域,这是由他的“诗人”身份注定的,也是为了完成教育部列出的学科规划的任务要求:公木先生主编了由先秦至近现代九卷本的《中国诗歌史论》,跨度之长、体系之大,前所未有。这一浩大学术工程,使进入晚年的公木先生在完成对《老子》的解读后,未能得偿注《庄子》的夙愿,这是他的一大遗憾。有幸的是,在和他多次的谈老论庄中,我断断续续地记录了他对庄子覃思卓见的雨丝风片,其中每个论点,都足以延展发挥为一篇精彩的文章。比如:“诗骚”是中国诗歌的双源,“庄骚”则是中国文学璀璨的双珠。这一线索,贯穿了中国古代文学演进和发展之路;庄子是“哲之诗”,屈原是“诗之哲”,共同达到了“悲悯”高度,此后再无诗人可企;庄子文学性的特点是浪漫主义的浮想联翩和现实主义的犀利观察,是“冷眼热肠”;庄子借助大量寓言来表达深奥的哲理,在《庄子》一书的理论线索上,缀满了灿烂多彩的形象花结;庄子是最深情的“诗人”,他的情感极为丰富。他所谓的“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莫不属于情感的范畴。庄子谈人生,一则曰:“不亦悲乎?”再则曰:“可不哀邪!”这种哲思中的悲悯情怀,内含远比诗人更为丰富、更为深沉的人生体验和情感;庄子总是在“道”上渲染着浓厚的情感色彩和鲜明的审美意绪。著名的“庖丁解牛”,是一个“技”(艺)进乎“道”的过程,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创作活动。庖丁解牛之后的“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善刀而藏之”,表现出传神的审美愉悦情态,这些都需要极高的艺术经验和哲学睿智;读《庄子》可知:思与诗,哲学与艺术,必在最高的灵境或玄妙处有以相会,这需要进行更广泛而深入的对诗或艺术以及直觉、语言符号等的探索(公木先生晚年所著的《第三自然界概说》深入探讨了这些问题)。如此等等,不必更多罗列即可看出,若非对《庄子》有深刻的解读,怎能有如此不同凡响的立论?庄子是广义的诗人,或曰艺术家,但他的“诗”或“艺术”是什么?在何处?多年来,我看过不少学人论庄的文章或著作,但最终还是不知所云,更不得探知九渊蛟龙之“骊珠”究在何处。公木先生既是诗人又是哲人,学识渊博,人生阅历丰富。读他的论庄之言,让我恍惚有窥“骊”见“珠”之感、得情感共鸣之愉。我写过几篇有关《庄子》的文章,也曾被《新华文摘》及《报刊文摘》转载,但终因学识、阅历、情怀、才能以及诸多因素宥限,未能得发先生论庄意蕴于万一。先生之治学、为人,诚然令人钦敬追慕,激励后学精进,然如我之庸平碌碌,终难望其项背。

1980年,公木(右)与萧军在一起
也许中国诗人或作家的职业关注、情感认知、审美取向以及经历阅历等,都与老庄情结有着文化基因的血脉关联,随际遇变化而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得以表露。无独有偶,在公木先生著《老子说解》20年后,著名作家王蒙又以阅览感悟的方式,将自己的老庄情结连续在《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两部书中尽情释出,极“淋漓尽致”之兴。这两部以老、庄为话题的书,并非学术性著作,而全然是王蒙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历练说老解庄。王蒙要面对的并非学术界,而是文坛和中国的读书界。在青岛,我应邀参加了一次既有学术界也有文艺界朋友出席的讨论会,提交了文章并在大会宣读,文中充分肯定了王蒙解庄的特点和价值。其中核心的论点就是:作家王蒙是怎样把“正解”留给专家,而自己却把“谬解”变为“妙解”。是的,王蒙跌宕起伏、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确实可为不少“妙解”提供绝佳的注脚。而作为诗人与学者的公木先生,走的是以学术规范注“老”解“庄”的路子。在这条路上,他的经历、阅历、感性思维乃至悲欢激赏,都自觉受驭于理性、理智和思维,他的诗怀和激情,也都需要内敛、沉潜,直至“自我”退出,无踪可辨,无迹可求。这是公木完全不同于王蒙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