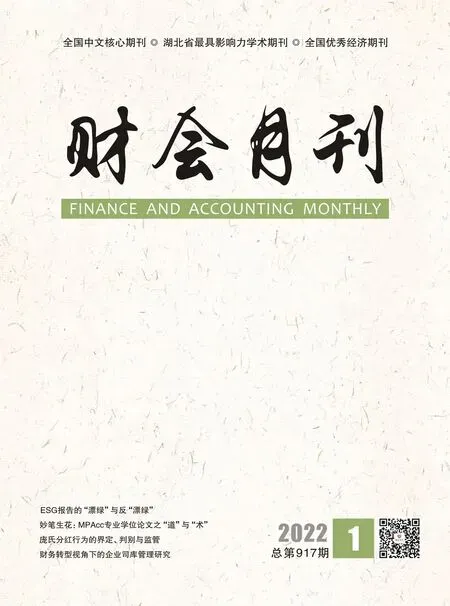谈《元祐会计录叙》中的财计思想
杨 修(副教授)
一、《元祐会计录叙》之缘起
中国历史上,对于中央财政会计制度及央地间的财政关系,进行过较长时间的探索,最终形成了一系列适合封建大一统王朝国家治理的财计制度。如果说发源于先秦、成熟于秦汉的上计制度标志着大一统国家在财政方面的形成[1],发源于唐、成熟于宋、流变于明清的会计录则是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又一里程碑,有力地回应了“中国古代没有数目字管理”之言论。
现存最早的会计录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的《元和国计簿》,由唐宪宗朝宰相李吉甫与史官共同编纂。元和承丧乱之后,国计凋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较之盛唐大幅度下降,加之藩镇跋扈和土地兼并,税源萎缩。为明确收支两条线,对症下药,由宰相亲自挂帅,编纂了《元和国计簿》。《元和国计簿》为唐王朝中央政府开源节流起到了导向作用,对元和中兴局面的形成也发挥了作用。《元和国计簿》标志着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财政管理和会计核算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
宋代可以说是会计录的成熟期。自真宗朝三司使丁谓编纂《景德会计录》始,几乎每朝都可见编纂会计录的记载。流传至今,较受学人关注的有真宗朝《景德会计录》《祥符会计录》、仁宗朝《庆历会计录》《皇祐会计录》、英宗朝《治平会计录》、神宗朝《熙宁会计录》、哲宗朝《元祐会计录》和南宋高宗时期的《绍兴会计录》[2]。宋哲宗元祐(元祐在元丰后)二年(公元1087年)初,时任户部尚书李常受命与户部侍郎苏辙编纂会计录即《元祐会计录》。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完成,后由户部尚书韩忠彦(李常已于元祐三年升御史中丞)与户部侍郎苏辙、韩宗道进览。一般认为,前后两任户部尚书李常与韩忠彦都是挂名主持,实际组织工作由苏辙具体负责[3]。除以文学家知名外,苏辙还曾位列执政大臣,有较丰富的实际行政经验,对于治国理政的实学也有独到见解。因此,可以认为,苏辙是编纂《元祐会计录》的核心人物。
在苏辙文集《栾城集》[4]中,关于《元祐会计录》的文章有三篇:《元祐会计录叙》《收支叙》《民赋叙》。高磊[2]认为,可能收支与民赋二篇均由苏辙撰写,因此作叙(叙同序)。此说有一定道理。按此推论,为《元祐会计录》全篇作叙,也是苏辙作为编纂工作实际负责人的旁证。这三篇叙文,集中体现了苏辙的财计思想,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分析其间的财计思想,不仅能够体味先贤谋国之艰,也能对当下研究会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起到借鉴作用。
二、《元祐会计录叙》的历史背景
1.学术背景。北宋初期,文坛流行辞藻华美、用典繁复的文风,代表为西昆体。经过数十年的沉淀,欧阳修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主持进士考试,推崇平实文风,提倡通达平易,坚持使用策论作为考试形式,拔擢了一批华实兼备的青年人才,其中有苏轼、苏辙、曾巩。二苏对欧阳修的主张极为赞同,写作简练易懂,排斥华而不实。在他们的引领下,许多士大夫转向质朴,追求“文章经世”。苏辙历官户部,对理财形成了一系列观点,也是这种文风的体现。
2.政治背景。宋神宗即位时,上距北宋开国已逾百年,承平日久,必然导致机构膨胀和不急之务占据财政空间,这也是封建社会中央帝国的通病。对此,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但是由于官僚体制本身的问题,许多利国利民的改革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反而给百姓增加了负担,比如苏辙对青苗法的批评,王安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其有道理。元祐二年,执政的高太后任用旧党,废除新法。新法虽然废除了,但是财政的紧缺状况仍然没有改变。摆在太后、皇帝和执政大臣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维持国家运转,并筹措军饷以应付在陕西与西夏的战事。正是在这一局面中,李常和苏辙受命编纂《元祐会计录》。
三、《元祐会计录叙》中的财计思想
1.会计的政治学意义。苏辙在《元祐会计录叙》开头,先是引经据典,论证“图籍”在大一统帝国治理中的重要意义。然后话锋一转,指出“其始无不具者,独患多而易忘”,即如果不对图籍进行妥善贮藏并加以整理,就会“人亡而书散,其不可考者多矣”。之后,苏辙[4]又简述了国计簿到会计录的历史沿革。考诸原文如下:
臣闻汉祖入关,萧何收秦图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汉祖赖之,以并天下。丙吉为相,匈奴尝入云中、代郡,吉使东曹考案边琐,条其兵食之有无,与将吏之才否,逡巡进对,指挥遂定。由此观之,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制胜千里之外者,图籍之功也。
该段原文后面叙述了国计簿到会计录的沿革部分,因前文已介绍,不复引。作为掌握天下财政的户部堂官之一,苏辙对于会计录的地位进行了准确、允当的概括,将会计录的编纂置于国家兴亡的高度。这种对于会计的政治学意义的真知灼见,不仅在当时具有先进性,即使放在今天,也让许多会计人精神为之一振,认识到会计真正的地位。本文拟对苏辙的这段表述加以演说,阐发《元祐会计录叙》在会计与政治关系方面的思想。
(1)作为国家权力和政权合法性象征的“图籍”。《元祐会计录叙》开篇第一句“臣闻汉祖入关,萧何收秦图籍”点明了“图籍”作为国家权力和政权合法性的象征作用。之所以苏辙仅用一句话开宗明义,没有展开论证,是因为这一观点在古代中国可谓常识,无需反复申说。但是在专业化程度极高、会计在大多数人眼中仅仅是应用性学科的今天,有必要花点篇幅加以阐明。
“萧何收秦图籍”这一历史事件见于《史记》:“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需注意的是,萧何收秦图籍的地点是丞相府,熟悉秦汉制度的人都知道,秦汉三公极贵,握有实权,丞相更是行政中枢。因此,萧何去丞相府接受秦的“图籍”,绝不能仅仅视作收集战略信息以进行“决策支持”的功利性行为,而是有明确接管政权的象征意义。作文无过论、废话,是唐宋八大家的共同特点之一。“臣闻汉祖入关,萧何收秦图籍”十二个字,就将“图籍”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介绍清楚,在文章的开头定调、定性。
如果追溯中国会计发展史,“图籍”一直具有国家权力和政权合法性的象征地位。比如《史记·夏本纪》对“禹会诸侯江南”的记载,禹确立天下共主地位的象征,是对诸侯“计功”。即使不能完全认定为信史,也可以表明曾经有一位部族领袖,对从属于他的其他部酋进行了“会稽”,而这种原始会计行为,是这位领袖政治权力的最好体现。因此,查阅、稽核账簿是权力的象征,诸侯/地方向天子/中央呈送账簿以示服从。后世史料也不断印证了这一点,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指责北凉沮渠牧犍“民籍地图,不登公府[5]”,以及明东莞伯何真表列郡县户口及兵马钱粮,归降明朝[6]。就连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标志也是“版籍奉还”,藩主绝不仅仅是只把账簿图册交给了中央政府,还将领地的所有权和行政权交给了中央政府,“版籍”则是政治权力的象征。
因此,可以认为,《元祐会计录叙》开头的十二个字反映了以苏辙为代表的当时政治人物之共识,即“图籍”是国家权力和政治合法性的象征。但时移世易,今日的会计人员甚至会计研究者却未必都有这个意识,反而会看轻会计。
(2)作为制定国家政策依据的会计信息。上述第一点,可以说是会计在政治哲学中的意义,此点将阐述会计录在实际行政中的意义。在“臣闻汉祖入关,萧何收秦图籍”之后,苏辙具体介绍了收秦图籍带来的实际功效,就是“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汉祖赖之,以并天下”。通过查阅较为原始的账簿图册,了解各地的收入、产出,以此为依据,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战略。萧何之所以力劝刘邦暂时隐忍,接受项羽使之王汉中的安排,“收用巴蜀”,徐图进取,与他对“图籍”的掌握是分不开的。正是通过对账簿图册中信息的分析,让刘邦集团确定了先王汉中而后“暗度陈仓”收取三秦,进而东出争天下的战略方针。而项羽对“图籍”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体现出政治眼光的缺乏,不掌握战略信息,数十万大军如没头苍蝇般左右奔突,可以说在萧何收秦图籍之时就决定了楚汉相争的结局。
在用刘邦、萧何的历史事实为会计录的地位定性,论证编纂会计录的正当性之后,苏辙又引用了汉宣帝朝丞相丙吉的事例。大家行文,以古喻今,用汉宣帝朝与宋哲宗朝的相似性,论证编纂会计录的必要性。汉宣帝朝是汉朝的转折期,与宋哲宗朝同样面临着收入下降、边境用兵的极盛而衰景象。苏辙隐隐以丙吉自况,暗喻宋哲宗如果能够运筹度支、对症下药,也能像汉宣帝一样实现中兴的局面。然后提纲挈领,给出结论:“由此观之,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制胜千里之外者,图籍之功也。”也就是说,“图籍”最主要的功用是为“运筹”即决策过程提供信息,收到制胜千里之效,简言之,编纂会计录可以为制定国家政策提供依据。
时至今日,学习过管理会计课程的学生都知道,会计信息是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而苏辙在近千年之前的宋代,已对会计信息的决策支持功能尤其是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决策支持功能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不禁让人心生敬意。
2.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在引经据典论证会计录编纂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之后,苏辙回归历史现实,直指编纂《元祐会计录》的最核心目的:通过“取元丰之八年”的会计事实,对神宗元丰年间的度支详情加以核算,并登记在册,总结元丰政事的利害得失,为元祐年的行政提供参考,避免“国用旷竭”的不利后果。为此,苏辙先分析了造成宋元祐朝财政枯竭情况的原因,以此为据提出了自己的理财方略(也是苏辙作为户部侍郎的本职工作),从中可以看出苏辙的部分理财思想。考诸原文如下:
故咸平、景德之间,号称太平。群臣称颂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请封泰山,祀汾阴,礼亳社。属车所至,费以钜万,而上清、昭应、崇禧、景灵之宫,相继而起,累世之积,糜耗多矣……加以宗子蕃衍,充韧宫邸;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赡,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观,几见日新之政,而大业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富国强兵之计。有司奉承,违失本旨。始为青苗助役,以病农民;继为市易、盐铁,以困商贾。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于是经人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继以南征交趾,西讨拓跋,用兵之费,一日千金。虽内帑别藏,时有以助之,而国亦惫矣。
苏辙认为,之所以元祐年间会出现中央度支左支右绌的局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中三个属于通病,另一个属于特性。三个通病中:首先是太平盛世导致群臣歌功颂德,宋真宗朝君臣都沉迷于盛世幻象之中,于是进行了许多对于国计民生没有实际作用的形象工程,比如“封泰山,祀汾阴,礼亳社”等仪式性活动,又因为宋真宗笃信道教,修建了许多宫观庙宇,导致“累世之积,糜耗多矣”(太祖太宗两朝的积累被大量浪费),影响了中央度支在真正大政方针上的决策。其次,由于天下底定,享受“铁杆庄稼”的皇子皇孙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生育率大幅度上升,虽然宋朝宗室待遇随血缘递减,远支庶族已与平民无二,但“吃财政饭”的近支宗室又造成了一定负担。最后,由于海内无事,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官僚机构大幅度膨胀。以上三个通病,属于古代封建帝国的通病,能否得到有效遏制,一方面有赖于掌握无限权力的帝王自律性,另一方面取决于政权是否有魄力对皇族及其他“吃财政饭”的既得利益集团加以限制。
同时,宋哲宗朝还面临着自己的特性问题。王安石变法本意是“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即为了增加财源,富国强兵。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遭到歪曲,加之封建官僚层层摊派的流弊,在短期内虽增加了收入,长期来看反而与民争利,有枯竭财源之嫌。再加上连连用兵,“用兵之费,一日千金”,即使皇帝动用内库私银助饷,也无能为力。
由于封建帝国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阶段的制约,除了田税、盐税、矿税、印花税,几乎没有其他开源手段。而上述财源既发展较为缓慢,又极度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再加上贵金属本位制使政府转移支付效率受到影响,比起开源,封建王朝更依赖节流。因此,苏辙暗喻,为了保证度支的稳健性,有必要裁撤糜耗,回归俭约,会计录编纂的主要作用就是找出糜耗的原因并加以杜绝。苏辙更希望宋哲宗像汉文帝一样“恭俭寡欲”,以身作则,带头节俭。从这方面看,苏辙遵奉的仍然是传统中国官厅会计的主流思想,即量入为出,在收入无法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控制支出,以此保持中央度支的稳健性,避免“国用枯竭”的恶果。而且苏辙也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一样,不赞成与民争利,对于损害百姓利益的敛财手段不以为然,甚至有一种变法就是贪利的过度道德洁癖。
3.中国古代王朝官厅会计职能与会计分析。在《元祐会计录叙》的最后部分,苏辙[4]表示:
凡会计之实,取元丰之八年,而其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储运,五曰经费。
这段话介绍了会计录内容的五个分类,实际上点明了中国古代王朝官厅会计的五项职能,分别是收支、民赋、课入、储运、经费。与《景德会计录》《皇祐会计录》相比,《元祐会计录》的结构有较明显的调整。《景德会计录》除杂记外分为五个部分:户赋、郡县、课入、岁用、禄食;《皇祐会计录》除杂记外也分为五个部分:户赋、课入、经费、储运和禄赐[2]。《元祐会计录》与后者较为接近,有四个部分重叠。
其中,户赋与民赋指当时国家赖以生存的赋税;课入则是工商收入,即俗称的农业税和商业税,是中国古代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储运是指财赋转输与储存,宋代虽已出现名为“交子”的纸币,但仍以实物货币为主。粮食、货币的存储与调配,事关国家大计,尤其是当突发事件出现时,能否及时调配资源并妥善应对涉及政权合法性。自安史之乱后,南粮北运的重要性日趋显著,在唐以后的历代王朝都有着显要地位,漕运本身也是中央政府的重要支出项,有在会计录中单列一项的必要。经费与禄赐或禄食都属于支出项,禄赐或禄食指近支宗室的“铁杆庄稼”和官员的俸禄,是国家支出的要项。但在元丰改制之后,裁撤冗官、抑制宗室的举措起到了一定的实际作用,其占比有所下降。但是自仁宗朝西北用兵始,边事成了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其重要性增加,因此与修筑宫殿、宫观的支出合在一起作为“经费”,取代禄赐或禄食。
从上文不难看出,从《景德会计录》到《皇祐会计录》再到《元祐会计录》,大体上近似,但在一脉相承之中也有着时移世易下的改弦更辙,体现出不同时期国家的战略重心。《元祐会计录》最主要的创举是增加收支一项,并放在首项,突出了收支核算的重要性,这在会计学上不得不说是长足的进步。通过对收支进行会计分析,横向(郡县)、纵向对比全国的财政资料,可使统治者清晰地把握国家收支状况,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苏辙在编纂《元祐会计录》时新增收支一项并放在首位,是为了让宋哲宗及两府大臣对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更加明确,以便贯彻传统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但也能够说明苏辙已经具备了较为原始的会计分析意识和数目字管理思想,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古代会计尤其是官厅会计的进步,这可以说是苏辙在会计史上的一大贡献。
4.小结:苏辙财计思想的局限性及《元祐会计录》的回响。在《元祐会计录叙》中,苏辙逐步分析论证了编纂会计录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同时在分析过程中也体现了苏辙的财计思想:一是会计工作和会计账册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学意义;二是在中央度支方面,应该遵循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三是中央政府有必要完善收支、民赋、课入、储运、经费五项官厅会计职能,并通过条列收支进行会计分析,提供决策依据。但是,由于时代因素,苏辙的财计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似乎对封建社会中央帝国管理成本必然随着生产规模上升这一点没有很深的认识,在纸币没有普及的宋代,也不可能掌握增发货币之类的财政手段。然而我们不应苛责古人,而是将苏辙置于历史长河之中,正确认识他在中国会计史上应有的地位。
《元祐会计录》编成之后,在短期内的确为中央度支部门量入为出提供了依据,缓解了宋朝财政的紧张状况。但这种好转只是暂时的,由于财源日趋枯竭,而支出无法大幅度裁撤,也就无法真正脱离财政困境。因此,宋哲宗亲政后,一反元祐更化时期旧党举措,重新启用新党,此即绍圣绍述,而苏辙的名字也在身后与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一起被刻上了元祐党人碑。
四、苏辙《元祐会计录叙》财计思想的启示
1.高度认识会计的政治学意义。上文已述,苏辙在《元祐会计录叙》的开篇,高度评价了“图籍”也就是古代会计账册的政治学意义。这一观点,对于今天的会计学研究和会计准则趋同实务,也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会计学界和业界的工作重心始终放在支援经济建设方面,更强调会计研究如何指导会计实践以及如何通过会计实践助推经济发展。经过几代会计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的会计研究和会计实践已达到几千年来的最高水平,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会计本身是应用性学科,注重实用肯定正确,但在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存在过于轻视理论的倾向。社会上也认为会计不属于“高端”学科,会计在我国高校专业“鄙视链”中的位置颇为尴尬,会计专业的硕士博士经常被人问及“会计读研能研究什么”。时过境迁,在国家硬实力较强的今天,如何通过提升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树立文化自信,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重点议题。在会计领域,这一方面的工作就是通过会计史研究,阐明会计行为体现国家权力和政权合法性、通过会计准则与方法构建并维系共同体认识、高度认识会计的政治学意义。这也是当前会计专业课程思政的要求,有助于树立和塑造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使命感。
其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中国与沿线各国的经贸交流不断深化,为降低交易成本,国家间的会计准则趋同势所必至。显然,在以准则趋同为主的国际会计交流之中存在着政治意义。因此,我国一方面应该在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过程中争取更多话语权,实现有条件的趋同;另一方面应该“和而不同”,兼顾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尊重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意愿。这些都需要我们高度认识会计的政治学意义。
2.在有效使用政策工具的同时保持稳健性。今天与宋代相比,经济学思想高度发达,中央政府通过有效使用政策工具因应经济周期,这是以苏辙为代表的古代理财家没有掌握的新方法。但是使用政策工具也要适度,否则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从而危及金融安全。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张连起所言:“我国经济恢复元气和活力需要一个过程,财政收支的平衡状态也将持续较长时间。”地方政府仍需要“过紧日子”,中央对此三令五申,叫停了一些债务压力较大城市的部分项目(如地铁等),并对一些在错误政绩观下产生的形象工程进行了通报。确保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与民生无甚关系的不急之务应停尽停,也是苏辙的财计思想给予今天的启示。
3.保有足量储备以应对外部风险。现代国家不再使用贵金属本位制,中央政府贮藏货币应对冲击的要求也没有古代严苛,再加上粮食大宗交易已成为较普遍的商业行为,储运的重要性似乎较宋朝低。但近年来,西方某些国家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进出口贸易往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成为境外反华势力的钳制手段。一旦粮油禽蛋肉类等日常生活必备品的价格持续波动,不仅会直接反映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对居民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也会让农业生产无所适从,损害农民利益。因此,仍需要保有足量的外汇储备、粮食储备、战略资源储备,以妥善应对外部风险。
五、结束语
宋代是会计录的成熟期,从真宗朝开始,每代皇帝在位时期均有编纂会计录的记载。苏辙实际负责编纂《元祐会计录》,不仅圆满完成了工作,在体例上进行了创新,还留下了一篇重要会计文献,即《元祐会计录叙》。本文通过对《元祐会计录叙》的文本进行分析,领略了这位大文学家的财计思想。虽然存在时代局限性,但苏辙的财计思想时至今日仍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与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