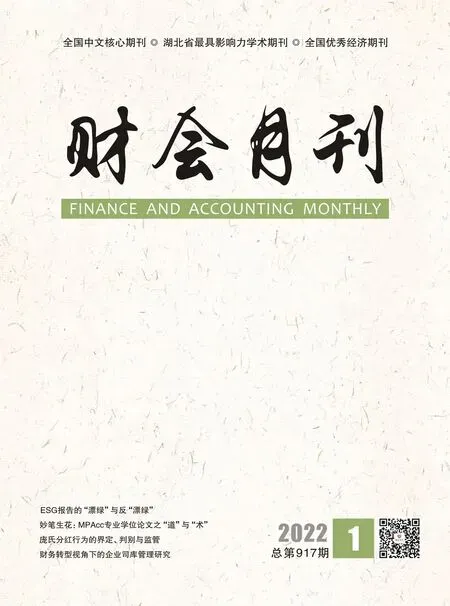论违反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的合同效力
陈圣利(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为维系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有限公司”)的人合性,避免因股东以外之人的任意加入而破坏原有股东之间的信任关系,大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对公司股权的对外转让均有所规制,一般要求需征求原有股东(或目标公司)的同意,并赋予原有股东优先购买权。我国《公司法》自制定初始,即规定了有限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①。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72条对旧《公司法》(1993年)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2013年修订的《公司法》在内容方面保持了2005年《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只是将条文序号调整为第71条。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之规定,虽然较1993年《公司法》有明显的进步,但仍存在“过粗”问题,由此导致该项制度的法律适用存在困难。
《公司法解释(四)》的出台,有效地弥补了《公司法》规定之不足,合理地解决了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适用中的部分疑难问题。然而,就违反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所订立之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曾试图解决,但由于争议太大,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规定。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就这一问题再次进行规定,并改变了《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的立场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虽然平息了审判层面的纷争,但前述问题(即违反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所订立之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无论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还是在学者著述中都存在重大争议,故而在学术上仍有研究的价值。
二、合同无效说及批驳
(一)合同无效说之见解
合同无效说认为,转让人违反《公司法》中的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与股东以外之人(即受让人)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2日公布的《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曾规定,优先购买权受侵害之股东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法院应予支持。但2017年8月25日公布的《公司法解释(四)》最终放弃了这一规定。
合同无效说的基本见解有二:第一种见解是,《公司法》第71条中的“应当”“应就”等措辞,表明了转让股东负有此项法定义务,并且彰显了该条规定系属强制性规定,有限公司股东未履行征求其他股东同意的程序,擅自将其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之人,违反了《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其与股东以外之人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属无效合同③。第二种见解是,转让人违反《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未履行征求同意手续,擅自将其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之人,侵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故而应认定该项股权转让合同无效④。
(二)合同无效说之批驳
合同无效,即已成立的合同因严重欠缺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而不发生当事人意思表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所谓无效,是指合同当然、自始、确定不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1]。鼓励交易为现代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由于“无效”的法律效果严重限制了私法自治原则,故而现代立法对“无效”范围多有限制。根据现行法规定之精神,合同(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一般情形,是因为“其欠缺的要件,属有关公益”[2]。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公序良俗等固然属于公益,但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未必都属于公益,故而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未必都是无效合同。判断某一规定是否属于“无效合同所违反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首先要看相关规定是否明确违反该项规定的合同无效,若无此规定,则应进一步研判违反相关规定的合同若为有效是否将有损公益。
关于合同无效说的第一种见解,笔者批驳如下:首先,征求其他股东同意,系转让股东的法定义务,合同相对人(即股权受让人)不负有此义务。未履行征求同意的程序,应由转让股东自负责任,而不能连带地“伤及无辜”,使受让人的合同利益落空并使其无法通过违约损害赔偿得到救济。其次,现行法并没有规定“违反《公司法》第71条规定的合同无效”,且若使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亦不会有损害公益的现象发生。《公司法》第71条所保护的股东优先购买权,仅限于有限公司领域内,目的在于维系公司的人合性。有限公司系属小型封闭性公司,公司规模小、股东人数少是其典型外在特征。若将少数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归入公益范畴,未免过于牵强。再次,虽然法律规定了有限公司的股东优先购买权,但该项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公司法》第71条第4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由此可见,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的征求同意义务并非绝对或必然存在,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也非固有或不可剥夺的。公司章程可以排除股东优先购买权这一“法定权利”,在此情形下,转让股东亦不负有征求其他股东同意这一“法定义务”。
关于合同无效说的第二种见解,笔者亦认为值得商榷。合同生效引起的直接法律后果是,在当事人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即一方(权利人)得请求另一方(义务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参见《民法典》第118条第2款)。在一般情形下,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参见《民法典》第465条第2款)。也就是说,当事人的缔约行为通常不会影响合同以外第三人的利益,而真正有可能伤及第三人利益的,应该是合同履行行为。正基于此,《民法典》一方面在物权编第311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标的物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另一方面在合同编第597条又确立了“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不影响合同有效性”规则。因此,转让股东未履行征求同意程序的情形真正侵犯了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应是合同履行行为(股权让与行为),而非合同订立行为。既然如此,只需否定合同履行的效力即可,而不应使“无辜”的基础契约(股权转让合同)“背黑锅”。
三、合同可撤销说及批驳
(一)合同可撤销说之见解
合同可撤销说认为,有限公司股东未征求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擅自将其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之人,侵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此种行为与公益无涉,但与其他股东的个人私益有关,故而应由其他股东自主决定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并由其决定是否申请撤销转让股东与股权购买者之间的合同。
合同可撤销说的基本见解有五:第一种见解是,此情形下的合同在转让人与受让人内部之间系属有效,但相对于公司和其他股东应属无效,由于该项合同侵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故而其他股东可诉请法院撤销之⑤。第二种见解是,此情形下的合同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故而并非无效,但其侵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故而其他股东可诉请撤销之⑥。第三种见解是,《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仅是股权转让的程序限制,而非实体上的禁止,不影响股东对其股权的处分权,但有限公司股东未履行该项程序,侵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故而其他股东可诉请撤销该项合同⑦。第四种见解是,《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属于任意性规定,并非对拟转让之股权的限制,但有限公司股东擅自将其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之人,未征求其他股东同意,侵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可因此诉请撤销该项合同⑧。第五种见解是,有限公司股东擅自将其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之人而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形,公司中的其他股东如果不同意该项交易,前述股权转让合同应属无效,其他股东有权诉请撤销该项合同⑨。
(二)合同可撤销说之批驳
上述关于合同可撤销说的五种见解,之所以认为其他股东有权诉请撤销转让股东与受让人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其理由可归结为一点:由于转让股东未征求其他股东意见而擅自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之人,侵犯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故而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的股东有权撤销这项股权转让合同。该观点的逻辑在于:优先购买权是《公司法》第71条明确赋予有限公司股东的一项法定权利→既然优先购买权是一项法定权利,法律自然应予保护,当其受到损害时,应得到法律的救济→优先购买权是股东的一项私权,无关公益,故而当该权利受侵害时,应由权利的主人(公司其他股东)决定是否行使→转让股东未征求其他股东同意、擅自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之人,侵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故而其他股东可诉请法院撤销该项股权转让合同。
前述论证似乎逻辑严密、严丝合缝,但笔者认为合同可撤销说仍存在可商榷之处,理由如下:
第一,前述论证未注意区分“股权转让(行为)”和“股权转让合同”,故而证成了其结论。在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所为的股权转让中,基础合同(股权转让合同)本质上属于负担行为,其直接法律效果是在转让双方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即转让股东因此负有向购买人转移股权的义务,但它并不直接引发股权变动。真正引起股权变动并可能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应是股权转让行为(股权处分行为)。如果认识到“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是股权转让行为(而非股权转让合同)”,那么前述用以证成可撤销说的逻辑基础将不复存在,其结论自然不攻自破。
第二,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目的有别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分别言之:(1)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追回的财产,仍应为所有债权人债权的担保,并非归行使撤销权之人独有,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并不能因该项权利的行使而获得优先受偿权[3]。简言之,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保护一般债权人的整体利益,而非个别债权人的个别利益[4]。(2)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目的在于优先取得被转让的股权,该项权利行使的法律后果是该特定股东因此取得被转让的股权,权利行使所取得的利益完全归特定股东个人独有。简言之,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设置并非在于保护一般债权人的整体利益,而是满足优先购买权人(转让股东以外的股东)的个人利益。
第三,优先购买权股东不具有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条件。具体而言:(1)债权人得以行使撤销权所保全的债权,原则上应发生在债务人的诈害行为之前。撤销权行使的目的在于保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而所谓“责任财产”应指债权成立时的责任财产,在此前债务人既已处分之财产,不应列入该项债权的责任财产范围内。如果债务人减少财产的行为发生在先、债权人的债权发生在后,则难谓债务人的行为损害到了债权人的债权。“盖债权之发生,莫不以当时债务人之资力为其信用基础,因而于债务人行为时,尚未发生之债权,则无因该行为而受害之可言”[5]。(2)公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系以转让股东与受让人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成立为前提条件,从而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法律效果为:在优先购买权股东与转让股东之间形成一个(与转让股东和第三人间合同)“同等条件”的合同。简言之,转让股东和受让人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在先,而优先购买权人与转让股东间的合同“形成”在后。由于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其合同债权发生在他人合同之后,故而不得根据撤销权制度撤销转让股东和受让人间的股权转让合同。
四、合同效力待定说及批驳
(一)合同效力待定说之见解
合同效力待定说认为,有限公司股东违反《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未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擅自将其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之人而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在效力上系属待定;合同有效与否,取决于公司其他股东的意思;其他股东若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则合同有效,否则合同无效。
合同效力待定说的基本见解主要有二:第一种见解认为,有限公司股东擅自将其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之人,侵害了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得撤销转让股东与受让人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在被撤销之前,该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待定⑩。第二种见解认为,《公司法》优先购买权规定对有限公司股权对外转让设置了双重程序限制,既要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同时还需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若股东未履行此两道程序,擅自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之人,其订立之股权转让合同不立即生效,在征得其他股东同意之前,合同在效力上系属待定⑪。
(二)合同效力待定说之批驳
前述第一种见解的论证逻辑值得商榷。“可撤销合同”与“效力待定合同”系属两个并列的概念,一项合同不可能同时既是可撤销又是效力待定的。现行民法中的“可撤销合同”与“效力待定合同”有其特定的含义。可撤销合同自成立始至被撤销前是有效的,只有被撤销后合同才归于无效。而效力待定合同在效力上既非有效也非无效,如果第三人追认了,合同确定有效,如果第三人拒绝追认,则合同确定无效。因此,如果认定某一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就不应该将其归入效力待定合同序列。前述见解以“其他股东可诉请撤销该项合同”为由,认定“该项合同效力待定”,其论证逻辑存在瑕疵。
对于前述第二种见解,笔者批驳如下:依据《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之基本文义,有限公司的股东将其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之人,确需经过“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与“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两道程序;但是,根据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之立法目的,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订立股权转让合同却无需征得其他股东同意,更无需等待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也就是说,“股权转让”和“股权转让合同的订立”概念有别,不能将二者混淆。《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中的“股权转让”应是指,有限公司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的“股权让渡行为”(或者说“股权让与行为”),而非“股权转让合同的订立行为”。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的缔约行为,是他们之间的“内部私事”,与公司其他股东无关。
五、合同有效说的不同解释及相应评述
(一)合同有效说的不同解释路径
合同有效说认为,有限公司的股东违反《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未征求公司其他股东的意见,擅自将其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之人的,转让股东与受让人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不因此而受影响。
合同有效说的基本见解有四:第一种见解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并不是对股权转让自由的限制,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与否不影响转让股东与他人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⑫。第二种见解认为,《公司法》关于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并不是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不能以违反该规定为由而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⑬。第三种见解认为,《公司法》第71条没有明文规定违反该条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合同继续有效也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益,故而该条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条规定的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因此被认定为无效合同⑭。第四种见解认为,《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系针对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而言,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无涉,当事人违反该项规定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只是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受让人可以依约追究转让股东的违约责任⑮。
(二)合同有效说不同解释的相应评述
笔者赞同合同有效的观点,且在解释路径上更认同第四种见解。这种见解区分了债权合同(负担行为)与股权变动(处分行为)各自要件,科学地运用了区分原则。以下笔者先就前三种见解进行评述。
第一种见解为了证成股权转让合同有效,而否认《公司法》第71条系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限制,与通说不符。通说认为,有限公司是一种小型封闭性公司,兼具资合性与人合性,《公司法》第71条旨在维系有限公司的人合性,防止不受欢迎的股东以外之人进入公司、破坏公司的人合性。第71条规定虽然并非禁止股权转让,但其要求有限公司的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应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并赋予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已构成对股权处分自由的限制。
第二种见解为了证成股权转让合同有效,而否认《公司法》第71条系属强制性规定,亦值得商榷。“第71条(前3款)系非强制性规定”的观点是相对于公司章程而言的,也就是说,只有公司章程才能改变第71条前3款规定的内容。只要公司章程不存在“另有规定”,《公司法》第71条之规定就具有强制性,有限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之人转让股权的,就应当履行征求同意的程序。第71条第2款“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的表述,彰显了条款的强制性属性。
第三种见解认为《公司法》第71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而不能以此认定合同无效。此种见解具有合理性,但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之分类是法律解释的结果”[6],在司法实践中容易被误用乃至滥用。同样是违反《公司法》第71条之规定,有些裁判文书以“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旗帜认定合同有效,而另一些裁判文书则给第71条扣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帽子进而认定合同无效。例如,前述“寰琨公司与祁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中,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法》第71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⑭。而在“王宝某与张康某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却持完全相反的意见③。因此,合同有效说的第三种见解也不是最佳的解释路径。
六、合同有效说的应选路径:区分原则解释路径
(一)区分原则解释路径之要义
区分原则解释路径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无涉,但与该项合同的履行有关。(1)合同效力方面。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与是否违反《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无关。如果该项合同仅是违反了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而不存在合同效力要件方面的欠缺,那么应认定合同有效。(2)合同履行方面。虽然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但由于该项交易违反了《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故而合同不能履行。不仅转让股东让与股权的处分行为不产生效力,而且股权买受人也不能要求转让股东继续履行合同。(3)认定合同有效的意义。虽然股权买受人不能要求转让股东继续履行合同,但并非意味着“不能履行的合同”没有意义。此情形下的合同虽然不能被履行,但当事人一方可基于该项有效的合同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反之,如果不承认合同的有效性,则当事人一方仅能追究对方的缔约过失责任。
(二)区分原则解释路径之展开
1.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系针对处分性的让与行为,而非负担性的缔约行为。一项股权转让的交易行为应区分为股权转让合同(原因行为、负担行为)与该合同的履行行为(结果行为、处分行为),要正确认识两种行为的不同法律效果,并科学区分两种行为的效力要件。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直接后果是,转让人因此负有让与股权的义务,受让人因此负有支付股价的义务。使股权直接发生变动的,不是股权转让合同本身,而是该合同的履行行为。
《公司法》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旨在阻止不受公司多数股东欢迎的股东以外之人通过交易取得股权,避免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因股权对外转让而受破坏。也就是说,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所阻止的是转让人与受让人间的股权变动(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行为),而无意否定他们间的合同效力,更无意剥夺受让人通过追究转让人的违约责任从而救济其债权利益的机会。
违反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虽然不影响转让股东与受让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但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合同履行效果。也就是说,其他股东如果主张优先购买权,并且其诉求符合优先购买权行使条件的,法院应依照优先购买权人的诉求撤销转让股东的股权让与行为(合同履行行为)或者确认股权让与行为无效。当股权让与的履行行为被撤销或被确认无效,受让人无法依照股权转让合同取得标的股权,但是由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因此受影响,受让人可通过追究转让股东的违约责任,以此救济自己的债权。
2.承认合同有效,不会侵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1)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间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是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的条件,从逻辑上讲,后者不可能受到前者的侵害。一方面,根据《公司法》第71条之规定,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其他股东原则上并无优先购买权。规定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目的在于维系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只会引发股权结构的变化,没有新人加入,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合性,故而《公司法》在股权内部转让情形并没有赋予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另一方面,优先购买权虽然属于有限公司股权的固有权能,但在转让股东出卖股权前,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只是潜在的权利而不具有行使的条件。只有当某一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订立了股权转让合同时,其他股东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主张在其与转让股东之间形成一个“同等条件”的合同。由此可见,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是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前提条件。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前者为因,后者为果。有因才有果,无因则无果,故而那种认为“股权转让合同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观点在逻辑上存在悖论。
(2)负担行为具有兼容性,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与转让股东形成的合同,并不排斥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成立在先的合同,二者可以共存。买卖等负担行为的法律效果是,出卖人为自己设定给付义务。“一个人可以承担任意多次的义务,虽然他无法履行所有这些义务”[7]。负担行为的兼容性为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和法院会议纪要所确认,不仅《合同法解释(二)》第15条规定了多重买卖合同的有效性,而且《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解释》第10条、《买卖合同解释》第9条和第10条、《八民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5条分别认可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动产、不动产的多重买卖合同的效力。股权转让合同本质上亦属买卖合同,转让人与受让人间关系与买卖关系并无实质区别,故而股权转让合同系属负担行为,且具有兼容性。如前所述,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是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条件,因此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间的合同成立在先,转让股东与优先购买权股东间的合同形成在后。成立在先的合同固然不能排斥后成立的合同,后成立的合同更无正当理由消灭他人间成立在先的合同。
(3)一项交易先有缔约行为、后有履行行为,缔约行为效力瑕疵会“渗透”到履行行为,但履行行为效力瑕疵则不会“反射”到缔约行为,股权转让亦是如此。一方面,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行为,即股权让与行为,从转让股东观之属于处分行为。股权让与行为的完成,将直接引起股权的变动。因此,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间的股权让与行为,会实质性地影响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股东优先购买权是一项法定权利,故而优先购买权股东可诉请法院撤销转让股东与股东以外之人间的股权让与行为。另一方面,合同的履行行为(处分行为)不会影响基础合同(负担行为)本身的效力。一项交易中,先有基础合同后有履行行为,只有基础合同生效了,才会发生履行问题。基础合同生效后,在履行环节出现了问题,即处分行为存在效力瑕疵,不能因此“反射”到基础合同而使其沦为同一命运。因此,优先购买权人固然可以诉请撤销转让股东的股权让与行为,却无正当理由撤销他人间的股权转让合同。
【注 释】
①参见1993年《公司法》第35条。
②《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27条曾规定,违反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定而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9条规定“为保护受让人的合法权益,(违反股东先买权规定而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如无其他影响合同效力的事由的,应当认定合法有效”。
③参见王宝某与张康某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云高民申字第141号民事判决书。
④参见姜文某与李国某等股权转让纠纷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外终字第0011号民事判决书。
⑤参见乐碧某因与李瑞某等股权转让纠纷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川民终字第733号民事判决书。
⑥参见徐某与赵书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提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
⑦参见瓮安世强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黔高民申字第540号民事裁定书。
⑧参见莫某与清水公司、蒋新某等人股权确认纠纷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3)新民二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
⑨参见王宏某与陆某、兴隆县半壁山镇松树林村村民委员会等股权转让纠纷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冀民二终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
⑩参见武汉桥都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陈某股权转让纠纷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终字第00042号民事判决书。
⑪参见解新势与烟台泰达铜材设备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烟商二终字第2094号民事判决书。
⑫参见李海某与霍建某等人股权转让纠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甘民二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
⑬参见深圳市国野股份有限公司与黄飞某、深圳市中联环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
⑭参见格尔木寰琨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祁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青民再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
⑮参见马深某与郭龙某、广东富广联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593号民事裁定书。
——从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3020号判决切入
——以受让人权益保护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