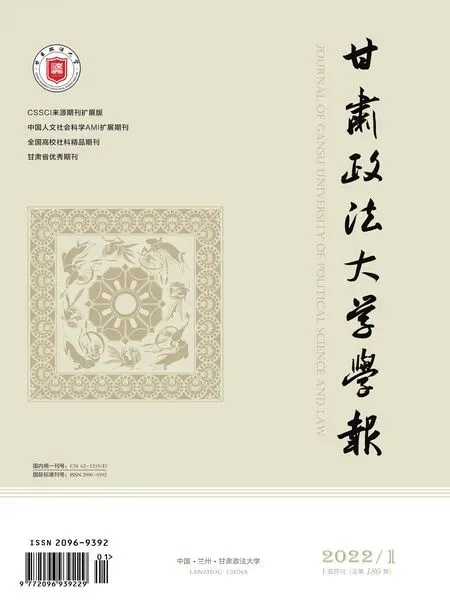董监高责任保险法律关系论
——以投保公司的复合法律身份为基点
赵亚宁
引 言
董监高责任保险(D&O Liability Insurance, 以下简称“董责险”),是一种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在履职过程中,因不当行为而可能产生的责任风险提供保障的责任保险。通过为董监高的履职责任风险提供保障,董责险有助于公司吸引有能力的人才任职,(1)See Noel O'Sullivan, Insuring the Agents: The Role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Insuranc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64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545, 546 (1997); Michael Hendricks, “Umdeckungslücken”in der D&O-Versicherung, CCZ 2008, S. 64.同时激励董监高充分发挥其经营管理方面的创新能力,以提升公司创新绩效和价值;(2)See Till Talaulicar, D&O Deductibles as a New Standard of Responsible Governance, in Ingo Pies & Peter Koslowski (eds.), Corporate Citizenship and New Governance: The Political Role of Corporations, Springer, 2011, p. 150; 方军雄、秦璇:《高管履职风险缓释与企业创新决策的改善——基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制度的发现》,载《保险研究》2018年第11期。通过对因董监高不当行为遭受损失的公司以及公司股东、债权人、公司雇员等提供赔付,董责险有助于保护公司财产,(3)See Till Talaulicar, D&O Deductibles as a New Standard of Responsible Governance, in Ingo Pies & Peter Koslowski (eds.), Corporate Citizenship and New Governance: The Political Role of Corporations, Springer, 2011, p. 151.实现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4)孙宏涛:《公司社会责任视角下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理念分析》,载《时代法学》2010年第3期。通过与证券信息披露制度相结合,董责险的免赔额、保费调整等机制能够发挥对公司内部管理人员的监督作用,减轻董责险可能诱发的董监高道德风险,进而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效果。(5)See Clifford G. Holderness, Liability Insurers as Corporate Monitors, 10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115, 129 (1990).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经济及资本市场发展较早的欧美国家,董责险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化,已实现大范围的覆盖,并成为公司风险管理体系的常规组成部分之一。(6)Michael Hendricks, Umdeckungslücken” in der D&O-Versicherung, CCZ 2008, S. 64.除了在英美国家拥有极高的投保率之外,其在德国的上市公司中也已成为一项通行标准。(7)[德] 迈克尔·霍夫曼-贝金:《德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悖论》,张怀岭译,载蒋锋、卢文道主编:《证券法苑》(第24卷),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87页。反观我国,虽然董责险制度早在证监会200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中就得到了承认,(8)参见《准则》第24条:“经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范围由合同约定,但董事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的责任除外。”但其近二十年来却始终不温不火,直至2019年才重新焕发生机。2019年新《证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对证券信息披露义务和证券民事责任的强化,以及对证券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导致公司董监高人员的履职风险大幅提升,董责险在我国有望迎来广泛的市场需求和扩张机遇。(9)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总共有接近400家A股上市公司投保董责险,而2020年一年则新增了170家,增幅超4成。参见《2020董监高责任险新增投保超4成,业内:市场覆盖不足、风险定价待完善》,载蓝鲸财经,https://www.lanjinger.com/d/150407,2021年1月1日访问。另外,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科创板首批28家企业中,有13家为董监高购买了责任险。参见《信息披露监管从严,上市公司购买“董监高责任险”趋热》,载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cn/gscy/qiyexinxi/2020-01-18/A1579300285335.html,2021年1月1日访问。与此同时,2020年4月初发生的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以及2021年11月发生的独董被判天价赔偿的康美案也相继掀起了业界与学界针对董责险的讨论热度和重视程度以致于证监会在其2021年11月26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可以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但是,关于董责险的承保范围、赔付条件、合同效力等问题,目前仍然存在诸多不明之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之上,为推动董责险向好发展,实有必要对其展开细致法律研究。
我国董责险的理论与实务目前均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我国董责险市场未臻成熟,统一的董责险示范条款尚未形成,市面上的保单条款多是由各保险公司在仿照国外保单的基础上自主拟订,而未基于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法等规范作出适于本土的产品设计,条款差异、矛盾现象比比皆是,甚至关于董责险保险标的的界定都存在重大分歧,从而给实务和理论皆造成了诸多困扰。其次,相关法学研究多是以国外的董责险保单为样本,要么是泛泛而谈我国董责险制度的立法和监管完善路径,要么是在尚未廓清我国董责险制度基本法律架构的情况下,就对承保范围、除外条款范围、被保险人范围、索赔等技术性事项展开事无巨细的探究,而从未对我国董责险制度移植过程中的实践困境予以充分关切,从未就我国董责险制度的保险标的和法律关系等本体论问题展开研究。
董责险在性质上属于责任保险,同时兼有为第三人利益保险和团体保险的特性,公司与董监高之间又存在公司法上的组织关系,这些都使得董责险的法律关系异于一般的责任保险,有必要得到专门的讨论和研析。鉴于董责险制度归根结底是为了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维护公司经济利益,投保公司可能具备的多重法律身份又深刻影响着其中的法律关系,故本文将以投保公司为中心,在探讨和辨明其应然法律身份的基础上,对投保公司与被保险董监高、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展开精细分析,以期明晰我国董责险制度的基本法律关系架构,引导我国董责险制度有序、健康发展,同时为我国董责险未来具体争议的解决提供一定参考。
一、投保公司多重法律身份之质疑与澄清
订立董责险合同不仅是为了董监高个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10)Sieg/Höra, Münchener Anwaltshandbuch Versicherungsrecht, 4. Aufl., 2017, § 17 Rn. 44.董责险除了分散董监高个人的责任风险外,更重要的功能在于提升公司治理效能、保护公司自有财产、践行公司社会责任,由公司投保并支付保费自然具备充分的正当性,而且也一直是比较法上的通行做法。但投保公司是否能具备被保险人、受害第三人的身份,则值得进一步探讨,这同时也关涉到对董责险保险标的的界定。本文认为,我国董责险的保险标的应当仅限于董监高的责任风险,不包括公司的责任风险;而董监高的责任风险则不仅包括其对公司股东等主体的外部责任风险,还包括其对公司自身的内部责任风险。是故,公司不得作为被保险人,但可以作为受害第三人。
(一)投保公司被保险人身份之否定
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以平安、美亚、民安为代表的保险公司所拟定的董责险条款,除了以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被保险人外,还将投保公司也纳入了被保险人范畴。针对后者所承保的保险标的则主要是公司对董监高的补偿责任,亦即当作为被保险人的董监高因履行职责时的不当行为而在保险期间内被首次提出索赔请求时,公司依法或依章程对董监高人员由此遭受的损失所承担的补偿责任。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对董监高个人的保险责任,则仅限于公司无义务或无能力提供补偿时,董监高无法从公司获得补偿的部分。两项保障与英美法国家典型的董责险保单类似,分别对应于其中的Side B保障和Side A保障。此外,平安保险公司还为投保公司自身因被提出证券索赔而应承担的证券责任提供保险赔付,这对应于域外的Side C保障。(11)关于由这三种保障构成的董责险保险单,美国安联(Allianz)保险公司官网有详细介绍和解释,参见https://www.agcs.allianz.com/news-and-insights/expert-risk-articles/d-o-insurance-explained.html,2021年1月1日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董责险的司法实践中,也已经有法院承认了投保公司的被保险人地位。(12)参见吴琼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保险纠纷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京0101民初22256号。而在理赔实践中,同样已有保险公司(美亚产险)为上市公司(海润光伏)因股票除权参考价误差而对投资者承担的补偿责任,提供了基于董责险的保险金赔付,从而体现了董责险为公司分散风险的作用。(13)参见《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163),载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sse.com.cn/assortment/stock/list/info/announcement/index.shtml?productId=600401,2021年1月1日访问。
此处存在疑问的是,董责险就其名称而言应当以董监高为被保险人,缘何国内外的董责险保单皆将投保公司也纳入了被保险人的范围?就域外而言,这种做法其来有自,究其根本是源于其公司法上的公司补偿(Corporate Indemnification)制度。
公司补偿制度是英美法系公司法中一项普遍且重要的制度,目的在于保护公司管理人员免受正常商业决策引发的个人责任威胁,以鼓励其充分发挥才智推进公司发展。(14)See Joseph P. Monteleone & Nicholas J. Conca, Directors and Officers Indemnification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An Overview of Legal and Practical Issues, 51 Business Lawyer 573, 574 (1996).如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45条第(a)(b)(c)款规定,当公司董事、高管、职员或代理人等的履职行为系出自诚信,且合理认为其行为符合公司最大利益时,若其被提起诉讼,公司可以对其实际发生的合理的诉讼费用、法院判决赔偿、和解赔偿等提供补偿(任意补偿);当公司的董事或高管能够证明其被提起的诉讼不具有法律依据时,公司应当对其实际发生的合理的诉讼费用提供补偿(强制补偿)。(15)原文参见https://delcode.delaware.gov/title8/c001/sc04/index.shtml,2021年1月1日访问。由是观之,公司补偿制度与董责险在制度目的及功能上存在重合之处。因此,对于美国的董事及高管而言,若其引发他人索赔请求的行为同时符合触发公司补偿和董责险赔付的要件,为免重复受偿,自应将董责险针对其个人的保障限于公司未补偿的部分,即对应于前述Side A保障。与此同时,由于公司补偿的本质目的与董责险相同,皆是为了减轻董监高的责任风险,将公司补偿责任纳入董责险承保范围(Side B保障)自然亦无不当。公司补偿制度的存在,是美国董责险采上述结构设计的主要原因。至于Side C保障,则在本质上与董责险无关,纯粹是出于为投保公司自身风险保障提供便利之目的,而附加于董责险当中的保险,因为英美最初销售的董责险保单就仅包括Side A和Side B保障。(16)See Vanessa Finch, Personal Accountability and Corporate Control: The Role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57 Modern Law Review 880, 898 (1994); Joseph P. Monteleone & Nicholas J. Conca, Directors and Officers Indemnification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An Overview of Legal and Practical Issues, 51 Business Lawyer 573, 587 (1996).
但我国公司法律体系与英美法系存在较大差异,考察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及实践后会发现,将董责险的上述实践不加变通地植入我国,或者说,将投保公司纳入我国董责险被保险人的范围,并不具有充分的法律正当性及实践必要性。
首先,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从未对公司补偿制度有过直接或间接规定,而且由于我国公司法上的责任体系与美国公司法存在很大不同,我国亦无必要建立公司补偿制度。(17)国内已有学者提议我国效仿美国公司法建立公司补偿制度,参见孙宏涛:《美国公司补偿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郝君富:《中美董事责任保险需求差异的制度因素分析》,载《保险研究》2013年第2期。美国的公司补偿制度主要针对的是董监高对公司之外的其他主体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而这些外部责任有些又属于证券法上的虚假陈述责任(即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依据我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在此种情形下,对于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作为发行人的公司往往需要与董监高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此时公司自身也是连带责任主体,因而不存在对董监高承担补偿责任的必要。可见,建立公司补偿制度会产生与我国既有制度规范相左的后果。
其次,董责险的承保范围宽于公司补偿制度的补偿范围(18)See Joseph F. Johnston, Corporate Indemnification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for Directors and Officers, 33 Business Lawyer 1993, 2034 (1978).,能够更好地发挥风险分散作用。且较之公司补偿制度将董监高的责任风险直接转由公司承担而言,董责险是以公司支付一定保费的方式,将董监高的责任风险转由保险公司承担,不仅尊重了公司的意思自由,也缓解了公司的经济负担,使其经济风险得到了更加有序的管理。随着董责险制度逐渐为我国公司所接受和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对董责险的实施予以鼓励和支持,由之完全代替公司补偿制度发挥董监高责任风险分散作用,更符合我国的公司发展现状,同时也避免了公司补偿制度所致的董责险结构的复杂化及风险分散对象的异化(19)根据汤姆·贝克(Tom Baker)教授的调查,美国绝大多数董责险的赔付均发生于Side B和Side C保障之下,Side A保障通常仅在公司破产或无力偿债,或者为股东派生诉讼支付和解金时,才会发挥作用。See Tom Baker & Sean J. Griffith,The Missing Monitor in Corporate Governance:The Directors' &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er, 95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795, 1803 (2006-2007). 这一结果表明由于公司补偿制度的存在,美国的董责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成了公司保险,而不再是董监高个人的保险。,有助于实现我国董责险的形式简洁化和功能专一化。
最后,公司本身的证券责任风险同样不应通过董责险予以分散。董责险顾名思义是保障董监高本人的责任保险,即使公司自身的证券责任风险有通过保险予以分散的需求和必要,如有助于维护公司的资产和资本价值,防止因公司以自身资产向股东承担责任而使股东间接地自我承担损失,以及给公司债权人和雇员造成不利影响,也并无理由将此种保险附加在董责险之下销售。这种做法一方面会增加对董责险的理解障碍,另一方面会导致有限的保险金额不得不在公司责任和董监高责任之间进行分配,从而大大削弱了董责险对公司董监高的保障效果。(20)See Wim Weterings, Possible Conflicts of Interest with D&O Insurance in Event of Shareholders' Class Actions, 2013 European Insurance Law Review 23, 26-27 (2013).作为应对,据报告美国近年来已有诸多大型公司开始购买单独的Side A保障,或者在传统的以Side A-B-C保障为基础的董责险保单中增加针对Side A保障的保额。(21)See Wim Weterings, Possible Conflicts of Interest with D&O Insurance in Event of Shareholders' Class Actions, 2013 European Insurance Law Review 23, 27 (2013).由此可见,将Side A保障和Side C保障予以分割,更多地侧重于对董监高个人责任的保障,已成为当前董责险的发展趋势。在此意义上而言,投保公司同样不应被作为董责险的被保险人。
(二)投保公司受害第三人身份之肯认
无论是英美法国家还是大陆法国家的董责险保单,均承保投保公司对公司董监高的索赔请求。质言之,投保公司可作为董责险的受害第三人。例如,英美董责险的保险标的主要是公司股东对董监高的诉讼风险(22)Tom Baker & Sean J. Griffith, Predict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Risk: Evidence from the Directors' &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Market, 74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487, 500 (2007).,既包括股东基于董监高违反信义义务而提起的直接或派生诉讼,也包括证券诉讼,但后者居于主要地位,且主要是在董监高涉嫌实施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0b-5条规定的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行为时所提起的证券诉讼。(23)Tom Baker & Sean J. Griffith, Predict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Risk: Evidence from the Directors' &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Market, 74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487, 496-498 (2007).其中股东派生诉讼的法律依据,正是公司因董监高违反信义义务的行为而遭受损害(24)John D. Hughes, Gregory D. Pendleton & Jonathan Toren,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 A Primer for Insurance Coverage Counsel and Other Lawyers, Too, 42 Brief 18, 20 (2013).,投保公司于此种场合担当了受害第三人的地位。德国董责险则既承保董监高对投保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内部责任,Innenhaftung),也承保董监高对投保公司之外的股东、债权人等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外部责任,Aussenhaftung)。且与英美法国家恰好相反的是,内部责任是德国董责险的主要赔付情形。(25)Vgl. Jens Muschner, in: Versicherungsvertragsgesetz, 4. Aufl., 2020, § 43 Rn. 21-22.
然而,与上述域外实践不同的是,我国董责险市场上却存在将公司对董监高的索赔请求一般性排除出承保范围的情况。(26)参见《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条款》第3条:“本公司对与下列对被保险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有关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四、由被保险人或被保险公司所提出的赔偿请求;但下列赔偿请求仍予以承保:……3. 代表被保险公司所提出的股东派生诉讼,但以未经被保险人或被保险公司要求、协助或参与为限;……”,《民安保险(中国)有限公司民安董(监)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条款》第5条也存在类似规定。这或许是出于防范投保公司与被保险董监高恶意串通骗取保险金的考量,但过分排除董责险对董监高内部责任的保障是否合理,着实值得深入探讨。
有学者基于我国《保险法》第65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责任”的规定,认为受害第三人不包括被保险人,并主张由于我国董责险条款普遍将投保公司也作为被保险人,因而投保公司不属于受害第三人,不得因受到被保险董监高的损害请求保险公司赔付。(27)参见谈萧:《董事责任保险的法律考察》,载《证券市场导报》2011年2月号;张怀岭、邵和平:《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他国镜鉴与本土重构》,载《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8期。但这一观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证伪。
其一,如前文所分析,对于我国董责险制度而言,无论是基于法律还是实践层面,均不应当将投保公司作为被保险人。这就意味着,在我国董责险未来的应然条款设计中,投保公司将不具备被保险人的身份,如此上述否定观点即自然地失去其根本支撑依据。但此处仍有疑问的是,投保公司虽不具备被保险人身份,但依然具备投保人身份,投保人身份是否会妨碍其作为董责险的受害第三人呢?一般认为,责任保险的受害第三人是仅相对于被保险人而言的(28)林群弼:《保险法论》(增订二版),台湾三民书局2003年版,第485页。,其判定与保险人和投保人无关。从理论上说,保险人有可能成为受害第三人;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非为同一人时,投保人也有可能成为受害第三人。(29)邹海林:《保险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09-410页。因此,投保人的身份并不影响公司成为董责险的受害第三人,只要公司因为被保险董监高违反信义义务的行为遭受损害,且其所提出的索赔请求具有法律依据,该损害即可依据保险合同约定获得赔付。
其二,即使依据现行董责险条款不得不承认投保公司的被保险人地位,也并不妨碍投保公司在特定的具体案件中取得受害第三人的地位。当责任保险的投保人为单个主体,而被保险人为包括但不限于投保人的多个主体时,投保人尽管拥有成为被保险人的资格,但却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均当然构成实际被保险人。在实际被保险人为投保人之外的其他主体的情况下,投保人即有可能具备受害第三人的地位。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业已得到印证和支持。例如,商业三责险是典型的具备上述结构特征的责任保险,在一起商业三责险纠纷中,投保人(原告)为其起重机投保商业三责险后,因为其所允许的合法驾驶人(被告)在驾驶该起重机时操作不慎而被撞伤。关于投保人能否得到保险赔付,法院认为,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均属被保险人的范畴,后者驾驶起重机时即实际取得了被保险人的地位,此时若投保人未在被保险车辆之上,且因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而遭受人身损害,则投保人系被保险人、保险人、车上人员以外的受害者,符合第三者的定义,应当有权依据商业三责险的赔偿规则获得保险赔付。(30)参见刘建波诉刘秋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健康权纠纷案,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牟民初字第411号。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年第4辑(总第86辑)收录。以此类推到董责险当中,在被保险董监高违反对公司的信义义务而给公司造成损害的情形,实际被保险人即为董监高个人,而非投保公司,尽管投保公司在其他情形(如触发Side B保障和Side C保障的情形)可能构成董责险的被保险人,但这并不影响其在此种情形下被认定为受害第三人进而获得保险赔付。总之,在判定投保人能否构成受害第三人时,应当穿透表象,重点考察其与特定案件中的实际被保险人是否同一,其本人所兼具的一般意义的被保险人身份于此则无关紧要。
其三,将董监高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纳入董责险承保范围具有实践上的必要性。尽管《证券法》的修订显著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的证券民事责任风险(外部责任风险),但董监高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风险(内部责任风险)始终是其责任风险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来源,且近年来呈不断攀升之势。(31)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中,董监高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民事案件截至2021年1月1日共有14317件,其中仅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1日审结的案件就已达11058件。我国《公司法》在2005年修正时确立了董监高对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公司法》第148条)以及违反该义务时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公司法》第150条),并且设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公司法》第152条)作为保障。内部责任就性质而言是一种民事责任,在成立内部责任时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既可能出自故意也可能出自过失,而且与外部责任相同,内部责任一旦成立亦有可能给董监高个人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其具备可保性因而可予认可。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董责险的正当性基础除了为董监高个人分散责任风险外,还在于为公司财产提供保护,后者是公司愿意负担保费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点显然要通过将公司对董监高的索赔请求纳入承保范围来实现。诚然,这种做法可能引发投保公司与被保险董监高串通骗保的道德风险,但由于该风险终究系来源于保险人通过保险合同提供的给付承诺,因而理应由保险人承担。(32)BGH NZG 2016, 745 (748).而且和其他保险欺诈的道德风险一样,此种道德风险也可以通过保险业的相关技术机制得到防范和化解。域外董责险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较为成熟,却始终将内部责任纳入承保范围之中,也为此提供了实践基础。是故,在投保公司作为董责险受害人于我国不存在理论障碍的情况下,将内部责任纳入承保范围不仅符合我国现今的市场需求,同时也与比较法上董责险的成熟实践相一致,因而应当得到承认。
二、投保公司与被保险董监高之间的法律关系
就投保公司与被保险董监高的法律关系而言,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法定的公司机构,其成员与公司之间首先存在公司法上的组织关系(Organverhältnisses)。组织关系的内容可由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确定。此外,实践中董事与高管有时还会与公司签订雇佣合同(Anstellungsvertrag)或劳动合同,以对法定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补充。(33)Wiesner,Münchener Handbuch des Gesellschaftsrechts, Band. 4, 4. Aufl., 2015, § 21 Rn. 1-2; 王军:《中国公司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66页。与此不同的是,由于监事的职责在于监督,不涉及公司经营管理,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是故其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雇佣合同关系,而只存在基于选举或委派及其接受的合意而形成的组织关系。(34)Vgl. Habersack,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Aktiengesetz, Band 2, 5. Aufl., 2019, § 101 Rn. 67; Koch, in: Hüffer/Koch, Aktiengesetz, 14. Aufl., 2020, § 101 Rn. 2.本部分旨在明确公司与董监高在董责险订立等方面的程序及实体法律关系,以对双方自身的风险管理及权利救济提供指引,同时为观照和分析既有之董责险案例(如瑞幸咖啡事件)的得失提供镜鉴。
(一)订立董责险合同的有权机关:公司董事会
当公司章程未就董责险的订立作出规定,且董、高与公司的雇佣或劳动合同中未就董责险的订立作出约定时,公司若欲为其董监高订立责任保险合同,应当由公司内部的哪一机关决定呢?该问题取决于投保董责险这一行为在公司内部属于何种事项,或者说董责险保费在公司法上的法律性质为何。
对此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董责险保费构成公司提供给董监高的任职报酬,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其属于公司的经营支出,投保董责险是公司的一种经营管理手段。德国学界大多采经营支出说,且实务中公司在财务处理上也多是将之作为经营支出而非董监高的薪酬。(35)Vgl. Kersten v. Schenck, Handlungsbedarf bei der D&O-Verisicherung, NZG 2015, S. 497.在我国《公司法》之下,若采任职报酬说,则董监事和高管的责任保险合同应当分别订立。因为根据《公司法》第37和第46条,董事、监事的报酬由股东会决定,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由董事会决定,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决议则分别由董事会和经理执行。如此,便意味着为董监事投保董责险应当由股东会决定、董事会负责具体投保,为高管投保董责险则应当由董事会决定、经理负责执行。若采经营支出说,则董监事和高管的责任保险合同可以一并订立。因为依据《公司法》第46条,享有对公司之经营管理权限的是董事会,因而董事会有权作出投保决定,并由经理负责具体订立董责险合同。
本文认为,公司投保董责险的行为属于公司经营管理的一部分,不应当将之作为公司向董监高提供的薪酬从而必须由股东会及董事会进行决议,而应由董事会一并作出决议。薪酬说的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董责险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公司董监高对于保护其个人财产免因承担责任而遭损失的利益,而非公司对其董监高之管理活动的利益。一方面,董责险提供的保险给付不仅仅是对损失的金钱补偿,还有对公司或第三方向董监高提出之索赔请求的抗辩。另一方面,公司负责购买董责险已普遍成为未来董监高加入公司的一项合理期待,且越来越多地成为后者任职公司的一项必要条件。(36)Vgl. Christian Armbrüster, Interessenkonflikte in der D&O-Versicherung, NJW 2016, S. 900.二是德国《股份公司法》第87条第1款明确将保险费作为董事薪酬的组成部分,且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在最近的判决中表明了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董监高薪酬确定方面,应当严格限制董事会之管理权限的态度。(37)BGH NJW-RR 2015, 988 (990).
但考察董责险的本质功能及作用,薪酬说却存在难以忽视之缺陷。第一,董责险尽管名义上是为了转移和分散董监高的责任风险,为其个人财产提供保护,但提升和促进公司利益却是其根本之旨归:(1)董责险目前已经是国际公认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属于公司为董监高向其提供劳务而采取的必要的保护措施(38)Sieg/Höra, Münchener Anwaltshandbuch Versicherungsrecht, 4. Aufl., 2017, § 17 Rn. 44.,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公司长期绩效,分散董监高责任风险只是实现该目的的必要手段而已;(2)如本文开头所言,董责险通过为董监高的内部责任提供保障保护了公司财产,通过为董监高的外部责任提供保障实现了公司社会责任,公司是显而易见的获益者,正因如此其才得以被域外公司广为接受并近乎成为一项实践惯例。第二,第一点决定了董责险与一般的纯为保障董监高之私人风险而订立的保险(如意外伤害保险、人寿保险)存在显著差异(39)Vgl. Sieg/Höra, Münchener Anwaltshandbuch Versicherungsrecht, 4. Aufl., 2017, § 17 Rn. 44.,因而其保费不应当像一般保险的保费那样,依据德国《股份公司法》被归为董监高薪酬的组成部分。第三,薪酬说导致董监事和高管的董责险必须分开订立,与当前市场实践不符,而且目前订立董责险的多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公众性决定了其股东形成决议较为烦琐、效率较低,董责险作为一项现代性的公司风控及绩效提升工具,其区区数十万元的保费对于资力雄厚的上市公司而言实属微不足道,因而应当由董事会机动灵活地决定其购买事宜,以避免公司因未及时进行投保风控而错失发展良机。
(二)董责险保障因公司行为丧失时的公司责任
当投保公司的某项行为导致保险人解除董责险合同或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时,直接遭受不利的是作为被保险人的董监高。对于自己由此遭受的损失,被保险董监高是否可以请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呢?如若可以,公司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又是否存在一定限制呢?对此,应区分公司是否负有董责险的投保及维持义务(40)所谓“维持义务”,是指公司除了与保险公司订立董责险合同之外,还应当尽力避免保险合同因其行为而被解除,或者保险责任因其行为而被免除。具体体现在公司应当注意履行其依据保险合同所负有的义务,如保费支付义务以及其他可能导致被保险人丧失保险保障的不真正义务等。而分别讨论。
1.公司负有董责险投保及维持义务的情形
若公司章程规定了公司有义务为董监高购买并维持董责险,或者公司与董、高订立的雇佣或劳动合同中约定了公司有义务为董监高购买并维持董责险,那么当公司未投保董责险、因迟延履行保险合同主给付义务(即支付保费)而致保险合同解除,或者因违反不真正义务而致保险人免除保险责任或解除保险合同时,应当认为公司对由此丧失保险给付的被保险董监高,负有损害赔偿责任。(41)Robert Koch, Das Dreiecksverhältnis zwischen Versicherer, Versicherungsnehmer und versicherten Personen in Innenhaftungsfällen der D&O-Versicherung, ZVersWiss 101 (2012), S. 169.该损害赔偿责任的规范基础系《民法典》第577条。(42)《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公司章程并非典型的合同,尽管关于其性质存在“自治法说”和“合同说”两种观点,但两种观点都认同其对公司及其机构、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43)王军:《中国公司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66页。,且我国《公司法》第11条也对此作出了确认。(44)《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因此,公司章程同样可以在公司与其董监高之间创设债之关系以及相应的义务。虽然《民法典》第577条的适用对象是合同之债,但依据《民法典》第468条,非因合同产生的债之关系,只要不存在依其性质不能适用的情况,在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时也可适用合同编通则的有关规定。故此,公司违反的无论是公司章程规定还是雇佣或劳动合同约定的董责险投保及维持义务,皆可依据《民法典》第577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就公司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而言,根据《民法典》第584条,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履行利益在内,但不得超过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应当预见的违约损失范围。在公司违反董责险维持义务导致保险保障丧失的场合,该数额较易判断,即董监高在遭受公司或第三方提起索赔请求时,依据已订立的保险合同,本可由保险人提供赔付但却未获赔付的部分,抗辩费用自然亦包含在内。在公司违反董责险投保义务导致保险保障丧失的场合,由于不存在一个既存的保险合同作为参照,若公司章程、雇佣或劳动合同已就欲投保之董责险的保险金额和免赔额作出了明确,则可依此确定公司损害赔偿责任的数额。但是,若公司章程、雇佣或劳动合同未作明确,此时该如何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呢?本文认为,应当适用“可预见性”规则,将赔偿数额限制在公司章程制定或者雇佣或劳动合同订立时,公司所预见或应当预见的董监高之损失范围之内,最高不超过董监高对公司或第三人提出之索赔请求支出的合理抗辩费用,以及依法应承担之损害赔偿责任的总和。
2.公司不负有董责险投保及维持义务的情形
当公司在未受任何义务约束的情况下自愿投保董责险时,若因公司行为导致保险人解除董责险合同或者对特定保险事故免责,由此丧失保险保障的董监高是否有权向公司主张赔偿呢?对此,德国联邦劳动法院(BAG)关于职工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所作的一件判决或可提供些许思考。(45)BAG BeckRS 2007, 47449.
在该案中,雇主出于自愿为其全体雇员投保了一份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并在之后与保险人达成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被保险人(雇员)有权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46)与我国不同,被保险人在德国保险合同法上并非当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法定的保险金请求权人系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仅在保险合同有特别约定时方有权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且雇主有义务通知雇员该保险的存在及其内容。但雇主始终未向雇员作出该项通知。嗣后,一位雇员发生了该保险承保范围内的意外事故,但因雇主未将该事故及时通知保险人而遭保险人部分拒赔。该雇员遂将雇主诉至法院,请求雇主对差额部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BAG支持了雇员的诉讼请求,判决理由为:雇主未通知雇员的行为违反了其基于雇佣合同所负有的通知义务,正是因其未向雇员履行该通知义务,且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向保险人履行出险通知义务,才导致受伤雇员未能获得全额保险赔付,因此其应当就保险人拒绝赔付的部分向雇员承担赔偿责任。
鉴于董责险与职工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类似,均为团体性质的保险,且均以雇主为投保人,以公司内部人员为被保险人,或可考虑将该裁判思路类推适用于公司自愿投保董责险的情形。但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此种情形是否如上述判例一样存在公司通知义务的事实前提和法律依据。在上述判例中,雇主之所以负有通知义务,是源于德国《民法典》第241条第2款所规定的债之关系中的保护义务(Schutzpflicht)——“债之关系依其内容,得使一方当事人对他方负有考虑他方之权利、法益及利益之义务”。(47)BAG BeckRS 2007, 47449, Rn. 28.由于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雇佣合同关系,且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系雇主基于雇佣关系的存在,为保障雇员之人身利益所为,故通知雇员投保事实属于保护雇员利益的必要行为,从而符合第241条第2款的适用条件。
而就公司自愿投保董责险的情形而言,尽管我国《民法典》第509条第2款(48)该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规定了与德国《民法典》第241条第2款类似的保护义务,因而存在相应的规范基础,但相关事实却并不完全符合该款的构成要件,因而难以据之认定公司对董监高负有通知义务,并须承担违反通知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概言之,公司虽然可能与董监高存在合同关系,但投保董责险却并非基于该合同关系所为,且并非主要为了董监高的利益所为。如前所述,公司投保董责险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利益,包括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吸引有能力的人员任职公司以提升公司业绩、保护公司财产以及履行公司社会责任等,保护董监高免遭责任风险之威胁仅是该目的的外在表征以及其获得实现的必然结果而已,故投保董责险并非公司基于与董监高的雇佣或劳动关系,为后者之利益所为,公司相应地也就无义务向后者通知订立董责险的事实。职是之故,当公司在无义务约束情况下自愿订立董责险时,其在董责险方面对董监高不负有任何义务,无论因公司的何种行为导致保险保障丧失,董监高都无权请求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否则将会与公司购买董责险以提升自身利益的初衷相背离,导致公司无故陷入于己不利之境地,从而抑制公司自愿购买董责险的积极性,进一步减少董监高获得保险保障的机会。
三、投保公司与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之一:作为投保人时
在公司作为投保人的场合,其与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除支付保费外,还需履行《保险法》规定的投保人一方所负有的各项不真正义务。董责险合同的投保人是公司,而被保险人则可能包含多位董监高,这凸显了董责险的团体保险特性。若部分董监高在代表公司投保董责险时存在不诚实行为,是否会影响到其他董监高的保险保障?投保公司的安全防护义务具体应如何履行?此外,当投保公司同时构成受害第三人时,其不真正义务的履行应否予以适当限制或豁免?考虑到董责险的特殊性,这些问题均有特别讨论的必要。故此,下文将根据投保人所负有的不真正义务的不同类别,分三种情况展开论述。
(一)投保公司违反投保人所负不真正义务的情形
如实告知义务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是我国《保险法》上第一类涉投保人的不真正义务,即义务主体仅以投保人为限。由于我国《保险法》第56条仅规定了重复保险的法律后果(即保险人按比例承担保险责任、按比例返还保险费),而未对违反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故本部分讨论将围绕投保公司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对被保险董监高的效力展开。
投保公司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是否会影响董责险的保险责任承担,无论是在域外还是我国的实践中都存在很多争议。例如,投保公司在投保阶段的财务造假是否影响保险赔付和保险合同效力,就是瑞幸咖啡事件中关于董责险的争议焦点。若严格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6条,则只要投保公司在保险合同订立阶段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向保险人提供了财务造假文件,且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即有权利解除保险合同,并可视具体事实免除对已发生之保险事故的保险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投保欺诈虽然属于公司行为,但却并非所有被保险董监高皆实际参与并实施了该行为,让无辜的董监高遭受因此而丧失保险保障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然有失公平。
为避免上述不利后果的发生,在董责险的市场实践中,保险人可能会在保险合同中预先放弃基于投保欺诈的法律抗辩,如放弃基于《保险法》第16条的合同解除权和免责权,以及德国董责险中保险人放弃基于欺诈的合同撤销权。此种弃权条款的效力如何,也直接关系到被保险董监高的保险保障。一说以弃权行为出自保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受到决定自由(Entschlieβungsfreiheit)的保护为由,主张弃权条款有效。(49)Vgl. Melot de Beauregard/Gleich, Aktuelle Problemfelder bei der D&O-Versicherung, NJW 2013, S. 829.另一说则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见为代表,认为保险人通过弃权条款将自己置于对方当事人的意志支配之下,完全放弃了自我决定权,使得实施欺诈行为的投保人能够从其行为中获益,而不必担心合同解除的后果,从根本上冲击了法律行为的决定自由,因而应属无效。(50)BGH NJW 2012, 296 (296).本文认为应采前一观点,具体理由除尊重保险人的决定自由外还在于,保险人之所以愿意在董责险合同中订入对投保公司更为有利的弃权条款,必然是双方谈判博弈的结果,其达成势必要以投保公司承担其他方面的不利条件为代价,如支付更高保费、负担更高免赔额等,而认定弃权条款无效将会打破这一给付均衡状态,并且还会助长保险人的不诚信行为,破坏商事交易秩序,损害投保公司一方的正当利益。另外,尽管弃权条款导致保险人无权再主张解除合同或免责,但责任险实行的经验费率制意味着这并不会给危险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造成不良影响,而只会使理赔经历较多的投保公司自身承担保费提高等不利后果。而且,弃权行为有效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已获得相应支持。例如,在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中,关于“保险人在投保公司未回答核保问题的情况下同意签订董责险合同,是否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这一问题,原告投保公司主张保险合同因其未回答核保问题而不能成立,但法院则认为被告保险人在原告投保公司未回答核保问题的情况下签订保险合同,是对自己民事权利的放弃,并不影响保险合同效力。(51)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39983号民事判决书。虽然该案事实与上文讨论的情形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原理相通,可资参考借鉴。
(二)投保公司违反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所负不真正义务的情形
安全防护义务是《保险法》中第二类涉投保人的不真正义务,即义务主体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限,《保险法》第51条第3款对之有所规定。
对于发生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后、保险事故发生之前的安全防护义务,亦即旨在维护保险标的安全、防止保险事故发生的义务,尽管与保险标的距离较近的通常是被保险人,由其履行安全防护义务更加便利可行,但在特殊情形下仍有将投保人纳入义务主体之必要,尤其是对于董责险的投保公司而言。在此方面,投保公司负有建立合规部门以防控合规风险、避免董监高违规行为的义务。(52)Vgl. Melot de Beauregard/Gleich, Aktuelle Problemfelder bei der D&O-Versicherung, NJW 2013, S. 824.建立合规部门不仅是公司的一项义务,也能够切实给公司及其董监高带来利益。因为受制于免赔额的存在以及保险金额的不足,在董监高因其不当职务行为被判处高额民事损害赔偿甚至行政、刑事罚款时,董责险可能无法对相关损失提供全额补偿,此时差额部分的损失就不得不由董监高本人或者公司来承担。(53)Vgl. Melot de Beauregard/Gleich, Aktuelle Problemfelder bei der D&O-Versicherung, NJW 2013, S. 825.目前,我国相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仅对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中央企业、境外经营的企业提出了建立合规部门的要求。(54)参见《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2006年原银监会发布;《保险公司合规管理办法》,2016年原保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2017年证监会发布并于2020年修正;《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2018年国资委发布;《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2018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外汇局、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但事实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一般的上市公司、非上市股份公司乃至有限责任公司,都有建立合规部门的必要。例如,德国《股份公司法》(Aktiengesetz, AktG)第91条第2款就规定了股份公司的合规义务,并且还有学者主张将该规定类推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55)Vgl. Schaefer/Baumann, Compliance-Organisation und Sanktionen bei Verstöβen, NJW 2011, S. 3601.
依据《保险法》第51条第3款,投保人未履行安全防护义务的,保险人可提出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的要求,后者会导致被保险人遭受丧失保险保障的不利后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该不利后果发生的前提是保险合同对特定的安全防护义务有所约定。因此,保险公司如欲以投保公司未建立合规部门为由主张解除合同,须在保险合同中事先约定投保公司的合规义务。且有必要依据对价平衡原则对第51条第3款作出限缩解释,即仅在投保公司违反合规义务导致承保风险显著提高以至于超出保险人承受范围时,保险人方可请求解除合同,否则仅得请求提高保费。
(三)投保公司违反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所负不真正义务的情形
出险通知义务和单证提供义务则是《保险法》中第三类涉投保人的不真正义务,即义务主体涵盖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保险法》第21条和第22条对两者有所规定。
由于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金请求权的归属主体,为及时获得保险给付,保险事故发生后的通知义务通常由被保险董监高履行,只要能使保险人及时获悉事故发生的事实,投保公司即可免于通知。(56)《保险法》第21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此时,投保公司未履行通知义务并不会使保险公司取得免责权。
相比之下,单证提供义务则有所不同。根据《保险法》第22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因此原则上而言,即便被保险董监高已经提供了相关证明资料,只要投保公司仍掌握其他于事故确认而言必要的证明资料,也仍然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单证提供义务对应德国《保险合同法》第31条规定的信息提供义务(Auskunftspflicht)。关于何为“必要”,原则上由保险人决定,但为了保护投保人利益,其必须同时符合规范性的客观评价(57)Vgl. Wandt,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VVG, Band 1, 2. Aufl., 2016, § 31 Rn. 31.,即保险人必须在发生争执时,说明且证实其要求投保人提供的信息的确具有必要性,即已经或可能对其保险给付产生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58)Vgl. Brömmelmeyer in: Bruck/Möller, VVG, Band 1, 9. Aufl., 2008, § 31 Rn. 28; Wandt,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VVG, Band 1, 2. Aufl., 2016, § 31 Rn. 33.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其他责任保险,董责险的一个显著特殊之处在于,其不仅承保投保公司之外的主体对被保险董监高的索赔请求,也承保投保公司对被保险董监高的索赔请求。在后一情形下,当保险人认为投保公司的索赔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且决定协助或代替被提起索赔的被保险董监高向投保公司抗辩时(59)我国《保险法》尽管并未规定保险人的抗辩权利或义务,但也未对之加以禁止,实践中已有保险条款对董责险保险人的抗辩权利作出规定,如《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业责任保险》第5条第7项(“抗辩行为”)。,其就与被保险董监高一起站到了投保公司的对立面,与后者形成一种对抗关系。此时如若仍要求投保公司依照保险人的请求履行单证提供义务,无疑会导致作为受害第三人的投保公司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或者使其不得不泄露商业秘密,或者使其丧失举证责任规则赋予的保护,从而使其法律地位尚且不及外部责任索赔或其他责任保险中的受害第三人。是故,投保人单证提供义务的适用在此种场合应当受到限制。德国学界有观点认为,此时“必要的”证明资料的范围,应当限于德国《民法典》第810条(“证书查阅”)中所规定的证书(60)该条规定:“就他人占有中之证书有查阅之法律上利益时,如该证书系为其利益而作成,或其与他人间之法律关系由该证书得以证明,或该证书载有其与他人间或其双方中之一人与共同媒介人间所为法律行为之商议者,得请求占有人允许其查阅。”参见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台大法学基金会编译:《德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26页。,而投保人的单证提供义务实际上已经因此得到了免除。(61)Fabian Herdter, Grenzen der Auskunfts-und Belegpflicht in der D&O Versicherung, ZVersWiss 100 (2011), S. 667.此种观点诚值赞同,当单证提供义务中的“必要性”判断标准发生根本改变时,该义务的性质无疑已经发生改变,原本的单证提供义务旋即消灭。于我国而言,当投保公司同时构成受害第三人时,应当将其受害第三人的法律身份置于优位,排除其基于投保人身份而负有的单证提供义务。在保险人协助或代替被保险董监高与投保公司进行的责任诉讼中,保险人请求投保公司提供证明资料的,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11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45—48条关于“书证提出命令”的规定。
四、投保公司与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之二:作为受害第三人时
如前所述,当被保险董监高违反职责给投保公司造成损害时,投保公司也可被作为责任险意义上的受害第三人,其对被保险董监高的索赔请求在董责险的承保范围之内。那么此时,投保公司应该如何通过董责险实现其索赔请求权?其可否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以及当保单责任限额不足以支付全部索赔请求时,应该按照何种标准对保险金进行分配呢?随着董责险在我国的扩张,妥善回应这些问题有望发挥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投保公司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及其构成
1.法定直接请求权的规范基础与适用条件
我国《保险法》第65条第2款规定了任意责任保险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这种请求权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附条件的直接请求权,所附条件包括两项:一是被保险人对受害第三人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二是被保险人怠于请求保险人直接向受害第三人赔付保险金。
就条件一而言,其不仅包括赔偿责任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仲裁裁决确认,还包括经被保险人与受害第三人协商一致以及其他能够确定赔偿责任的情形;(6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4条第1款。就条件二而言,其并不要求被保险人必须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保险人提出请求,只要被保险人在第三人提起诉讼之前能够采取而没有采取合理方式(包括一般的书面或口头方式)向保险人提出请求,即可构成“怠于请求”(6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314页。。鉴于投保公司不同于一般的受害第三人,其与被保险董监高之间存在公司法上的组织关系这样一种特别结合关系,因而较易通过内部协商沟通满足上述两项直接请求权的取得条件,进而取得针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也极有可能滋生被保险董监高与投保公司恶意串通、伪造虚假的损害赔偿责任以骗取保险金赔付的道德风险。作为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4条第2款和第19条第2款赋予了保险人相关权利:依据前者,保险人有权按照保险合同对投保公司的索赔请求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赔偿以及赔偿多少;依据后者,当被保险董监高与受害的投保公司就前者之赔偿责任达成的和解协议未经保险人认可时,保险人可以主张对保险责任范围以及赔偿数额重新予以核定。
2.意定直接请求权的权利来源与表现类型
(1)基于投保公司与保险人之间合意的意定直接请求权
与前述法定直接请求权不同,受害第三人的意定直接请求权系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而产生。关于意定直接请求权,我国《保险法》对之未置一词。《保险法》第65条第1款仅规定对于被保险人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保险人可以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直接向第三人赔偿保险金,而未明确可否通过保险合同的约定为第三人创设一项直接请求权。
对此,首先,若保险合同中的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条款系由投保人与保险人以个别磋商的方式订立,那么基于契约自由的原则,其效力自应得到认可。其次,若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条款系以保险格式条款的形式订立,则需从格式条款效力审查的角度认定其是否有效。在该条款经过保险人说明义务的程序规制而顺利订入保险合同并生效的前提下,其能否终局有效取决于其能否经受内容控制规则——《保险法》第19条的审查。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所控制的条款限于两类:一是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二是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条款。揆诸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条款,其仅仅是赋予了遭受被保险人损害的受害第三人就其损害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付的权利,不仅未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赔付义务,而且由于第三人直接请求并获得保险金赔付,与被保险人请求保险人向第三人赔付的结果相同,因而亦未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此外,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也并未因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条款的订入而被绝对排除。若被保险人已经向第三人作出损害赔偿,则即便存在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条款,第三人也无权请求保险赔付,否则便会构成重复获利,此时仅被保险人有权就其财产损失主张保险人赔付。故此,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条款不在《保险法》第19条的内容控制范围之内,只要其在程序上有效订入保险合同,且保险合同的效力未因某些原因受到影响,该条款即确定有效。
综上可知,对于董责险而言,通过保险合同约定即投保公司与保险人的合意,为投保公司及股东、债权人等其他受害第三人创设直接请求权,是可行的。
(2)基于投保公司与被保险董监高之间合意的意定直接请求权
除了基于投保公司与保险人之合意为投保公司创设直接请求权外,投保公司的意定直接请求权还可通过投保公司与被保险董监高之间的合意创设,这主要通过被保险董监高向投保公司转让免责请求权(Freistellungsrecht)获得实现。有关于此,涉及两个关键问题:问题一,被保险人得否向受害第三人转让免责请求权;问题二,免责请求权转让后的法律后果为何。
关于问题一,所谓的免责请求权是指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对保险人享有的、请求后者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范围内免除其对受害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64)Manfred Wandt, Versicherungsrecht, 6. Aufl., 2016, Rn. 1069.免责请求权是德国法上的概念,尽管我国保险法针对责任保险并未广泛认可并采纳免责请求权的概念,但基于责任保险固有的责任免除功能,即保险给付的目的不在于使被保险人获得保险金,而在于保护被保险人免于遭受因向受害第三人履行已经成立的损害赔偿责任所造成的不利益(65)参见沈小军:《论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的责任免除请求权——兼评〈保险法司法解释四〉责任保险相关条文》,载《法学家》2019年第1期。,我国保险法中同样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免责请求权。具言之,当被保险人的行为给第三人造成损害并依法成立损害赔偿责任时,若其尚未承担该赔偿责任,则被保险人只能请求保险人向第三人给付保险金,(66)这从《保险法》第65条第3款将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条件,限于被保险人已向受害第三人作出赔偿的规定中可以推知。由于保险金在此种情形系归属于第三人,被保险人享有的故而非为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而系免除其对第三人之赔偿责任的免责请求权。而若其已经承担该赔偿责任,则保险金应当支付给被保险人,被保险人的免责请求权此时转化为保险金给付请求权。(67)Lücke, in: Versicherungsvertragsgesetz: VVG, 30. Aufl., 2018, § 100 Rn. 8.鉴于被保险人向受害第三人转让保险合同中的权利,系以其尚未承担赔偿责任为前提,故被保险人转让的权利只能是免责请求权。接下来需要探讨的便是免责请求权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免责请求权以免除被保险人这一特定主体对受害第三人的责任为内容,属于以特定债权人为基础的债权,依其性质应认为不得转让。(68)我国《民法典》第545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债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而以特定债权人为基础的债权,换言之,变更债权人即会引起给付内容变更的债权,即属第一项“根据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之列。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4-715页;崔建远:《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但当受让人为受害第三人时存在例外。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08条第2款对于向受害第三人转让免责请求权作出了明文肯认(69)该款规定:“不得通过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排除免责请求权向第三人的转让。”,并且其判例和学说也普遍认为免责请求权在且仅在受让人系受害第三人的场合,始具可转让性。(70)Wandt,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VVG, Band 2, 2. Aufl., 2017, § 108 Rn. 86.此中的原因在于,债权转让以不改变债之内容的同一性、仅改变债权人为要件(71)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4页;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免责请求权的内容系免除被保险人的责任,亦即向受害第三人给付保险金,而其在转让给受害第三人之后,由于保险金的给付对象仍然是受害第三人,并未导致债之内容发生改变,从而仍然符合债权转让的基本要求,可以获得例外许可。(72)Wandt,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VVG, Band 2, 2. Aufl., 2017, § 108 Rn. 60.据此,被保险人可将其免责请求权转让给受害第三人,而且即便该第三人系投保人,如董责险中的投保公司,出于公平的考量,也同样可得转让。(73)Vgl. BGH NJW 2016, 2184 (2184); Robert Koch, Der Direktanspruch in der Haftpflichtversicherung, r + s 2009, S. 135. 尽管允许被保险董监高将免责请求权转让给投保公司,可能会增加两者合谋骗取保险金的道德风险,但此种风险在免责请求权转让给投保公司以外的其他受害第三人的情形也同样存在。而且,仅因受害人恰巧是投保人就给予其更不利的法律待遇,显然是不公平的,不能仅因猜测性、或然性风险的存在就剥夺受害人本应享有的法律地位。相关阐述,参见OLG Düsseldorf r + s 2014, 122 (125); Christian Armbrüster, Neues vom BGH zur D&O-Versicherung, NJW 2016, S. 2156; Sven-Markus Thiel und Björn Seitz, BGH: Innenhaftung des Versicherers einer D&O Versicherung, NJW 2017, S. 2468.
关于问题二,首先需明确免责请求权转让给受害第三人的法律后果是该权利转化为受害第三人针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74)Vgl. Robert Koch, Der Direktanspruch in der Haftpflichtversicherung, r + s 2009, S. 134; Tobias Harzenetter, Abtretung des Freistellungsanspruchs aus einer D&O Versicherung nach den BGH-Urteilen vom 13.4.2016, NZG 2016, S. 728; Lücke, in: Versicherungsvertragsgesetz: VVG, 30. Aufl., 2018, § 100 Rn. 7.在此过程中,尽管请求权的名称发生了改变,但其实质内容并未改变,这正是其得以被转让给受害第三人的原因所在。其次,和上述法定直接请求权相同,第三人取得直接请求权并不意味着其必然能够获得保险金,保险人有权依据保险合同对其请求进行核查进而作出相应的赔付决定。在此基础上,尚需进一步讨论的是受害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会因此受到何种影响。这取决于受害第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达成的是何种类型的免责请求权转让。基于合意内容的不同,免责请求权转让理论上存在两种类型:一是代物清偿的请求权转让(Abtretung an Erfüllungs statt);二是间接给付的请求权转让(Abtretung erfüllungshalber)。(75)Tobias Harzenetter, Abtretung des Freistellungsanspruchs aus einer D&O Versicherung nach den BGH-Urteilen vom 13.4.2016, NZG 2016, S. 730.但实践中,后者更为普遍。(76)Christian Armbrüster, Prozessuale Besonderheiten in der Haftpflichtversicherung, r +s 2010, S. 456.前者意味着免责请求权转让行为构成被保险人对受害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责任的履行,受害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随之归于消灭,但前提是双方必须约定被保险人仍然有义务履行保险合同中的所有不真正义务,且第三人的请求权未因被保险人在其提出请求后违反义务的行为而失去法律依据。(77)Tobias Harzenetter, Abtretung des Freistellungsanspruchs aus einer D&O Versicherung nach den BGH-Urteilen vom 13.4.2016, NZG 2016, S. 728.鉴于损害赔偿责任不复存在,被保险人针对该项索赔自然亦失去请求保险人为保险给付的权利。后者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免责请求权转让后,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仅在保险人向其赔付保险金之后方才消灭,否则仍然存续。(78)Tobias Harzenetter, Abtretung des Freistellungsanspruchs aus einer D&O Versicherung nach den BGH-Urteilen vom 13.4.2016, NZG 2016, S. 728.是故,争议较多发生于第三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未获满足的情形。第三人的保险金请求仅在损害赔偿责任和保险赔付责任均成立时,才能获得法院判决支持,且法院判决的既判力仅及于保险赔付责任的认定部分。(79)Vgl. Lars Böttcher, Direktanspruch gegen den D&O-Versicherer-Neue Spielregeln im Managerhaftungsprozess?, NZG 2008, S. 649.若法院基于保险赔付责任不成立而判决第三人败诉,则第三人仍有权向被保险人提起损害赔偿责任之诉,但即便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成立,基于先前第三人获得的败诉判决,被保险人也无权就此向保险人请求赔付。若法院基于损害赔偿责任不成立而判决第三人败诉,则第三人同样有权重新向被保险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且对于被保险人因此被判处的损害赔偿责任和支出的必要诉讼费用,被保险人有权请求保险人赔付。
综上,通过被保险董监高向投保公司转让免责请求权的方式为投保公司创设针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在法理上不存在障碍,且相关的法律后果应当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加以判定和适用。当然,依据《民法典》第546条第1款,该免责请求权的转让仅在对保险人作出通知后,方对保险人发生效力。
(二)损害赔偿责任超出保单责任限额时的保险金分配
当投保公司就多个被保险董监高违反职责给其造成损害的行为向保险人提起保险金给付之诉,并得到法院判决支持,但保单责任限额却不足以支付全部索赔请求,且保险合同亦未对保险金的分配方式作出约定时(80)尽管我国保险市场上销售的董责险保单有的在其条款中规定了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参见《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条款》11条、《民安保险(中国)有限公司民安董(监)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条款》第6条),但有的则仅仅只是规定了一个总的保单责任限额即累计赔偿限额(如《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业责任保险》第5条第3项),后者显然不能为发生争议时的保险金分配提供妥适处理规则。,应当适用何种规则在不同被保险董监高的赔偿责任之间进行保险金的分配,对于被保险董监高之外的投保公司也同样关系重大。因为尽管无论如何分配,保险金最终的流向均系作为受害第三人的投保公司,但鉴于各个被保险董监高的个人清偿能力有别,不同的分配规则显然会影响投保公司最终能否就其损害赔偿之债获得完全或尽可能多的清偿。立法对此情形下保险金的分配规则尚付阙如,理论上则形成了“按人头分配说”“按被索赔时间先后分配说”“按责任比例分配说”“区分不同情况分配说”四种不同学说。(81)详见Johannes Grooterhorst & Jörg Looman, Kostentragung des Versicherers bei (teilweiser) Erschöpfung der VersSumme in der D&O-Versicherung, r + s 2014, S. 160; Robert Koch, Das Dreiecksverhältnis zwischen Versicherer, Versicherungsnehmer und versicherten Personen in Innenhaftungsfällen der D&O-Versicherung, ZVersWiss 101 (2012), S. 166; Christian Armbrüster, Interessenkonflikte in der D&O-Versicherung, NJW 2016, S. 898.
但经过对比可以发现,上述各学说其实并没有立于相同的讨论基点之上——并未明确所针对的多个被保险董监高的赔偿责任,究竟是源于同一违反职责损害公司利益的事件,还是不同事件,抑或是对两种情形均得适用。按人头分配说和按责任比例分配说或许勉强可被认为能够普适于一切情形,但按被索赔时间先后分配说则显然只可能适用于第二种情形。更重要的是,区分不同情形分配说的提出,明显动摇了单纯适用某一种规则进行保险金分配的合理性。
此外,不同分配规则的适用也会造成董责险主体间利益格局的差异化。例如,按被索赔时间先后分配规则使得原本具有同等被保险人地位的董监高,仅因投保公司对其提出索赔的顺序选择不同,就在通过保险免责方面被动招致差异悬殊的法律待遇。显然,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可能诱发公司为保全特定董监高利益,而与之合谋使其他董监高遭受不利益的道德风险。尽管董责险以提升公司利益为根本,但公司利益亦应通过正当的程序和机制实现。两相权衡,投保公司获得完全清偿的利益应当让位于被保险董监高获得平等免责待遇的利益。是故,按被索赔时间先后分配规则应当被首先排除适用。
接下来,便需在按人头分配规则、按责任比例分配规则抑或其他可能的规则之间进行拣选,以确定最优的保险金分配方式。如上所述,讨论基点的同一性是得出周延妥适分配方案的前提,因此在具体的讨论分析中有必要进行层次化、类型化的场景区分与规则适用。
1.投保公司就同一损害事故中多位被保险董监高的赔偿责任请求保险赔付
当投保公司就同一损害事故中多位被保险董监高的赔偿责任请求保险赔付时,如何在这些赔偿责任之上分配保险金取决于不同董监高所承担之赔偿责任的关系,总体上包括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两种形态。当然,鉴于董责险不承担故意行为导致的损害,因而下文论及的赔偿责任仅限于董监高在主观非故意状态下依法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针对各董监高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基于连带责任的同一层次性,任何一位董监高承担赔偿责任即可完全实现投保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而免除其他董监高的赔偿责任,故保险金补偿的实际只有一项损害赔偿责任,因而不存在分配之必要。当连带责任的数额超过保单责任限额时,应当由保险人将相当于保单责任限额的保险金直接支付给投保公司,超过部分则由各董监高自行承担,且任一董监高承担责任之后有权向其他董监高追偿。
针对各董监高承担按份责任的情形,鉴于此时须各董监高均履行自身的损害赔偿责任才可完全满足投保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且各董监高作为共同被保险人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故董责险的保险人对各董监高的赔偿责任均有补偿之义务,保险金理应在不同赔偿责任之上进行分配,以平等保障被保险人的免责利益。关键问题在于,此处“平等”的衡量标准究竟应当采“董监高人数”还是“各董监高的损害赔偿责任比例”。由于“各个董监高对保险人均平等享有免责权,但保单责任限额不足以清偿全部此等债权”这一情形与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破产情形相类似,故关于保险金的分配可以类推适用破产情形下债务人的财产分配规则,即按照各债权人的债权比例平等清偿。此时,所适用的保险金分配规则即为上述“按责任比例分配规则”。
2.投保公司就不同损害事故中多位被保险董监高的赔偿责任请求保险赔付
当投保公司就不同损害事故中多位被保险董监高的赔偿责任请求保险赔付,如董事A和经理B分别实施不同违反职责的行为造成公司损害从而引发公司依次提起两项保险索赔时,本文认为若董责险的保险金不足以支付两项索赔请求,则应当适用“按损害行为发生时间先后分配规则”,即按照各董监高实施过失违反职责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时间先后进行保险金分配。由于董监高违反职责造成公司损害行为的发生时间具有一定客观性,不以投保公司的意志为转移,因而可以避免前述适用“按被索赔时间先后规则”进行保险金分配的内在弊端。此种情形之所以不适用按人头分配规则和按责任比例分配规则,是因为责任保险的总赔偿责任限额是一种以损害事故为基础的累计性的赔偿责任限额,即先发生的损害事故所导致的被保险人损失可以在总赔偿限额之内获得赔付,后发生的损害事故导致的被保险人损失则只能在剩余的赔偿限额范围内获得赔付。这意味着,在后实施不当履职行为损害公司利益的被保险人,无权分享在先实施不当履职行为损害公司利益之被保险人基于保险合同所享有的利益,而按人头分配规则和按责任比例分配规则显然是对责任险的该项一般赔付规则的背离,因而并不足取。
结 语
2019年《证券法》的修订促使原本在我国不温不火的董责险制度“枯木逢春”,迎来新增长。董责险制度是完善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和投资者保护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作为一件舶来品,其制度功能在我国能否有效发挥,尚取决于能否根据我国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对其进行合理的本土化。本文对此作出了尝试,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董责险制度相关的实践、规范和理论,明晰了我国董责险制度的基本法律架构,以期纠正我国董责险制度移植过程中的实践和理论误区,推动董责险制度在我国向好发展。此外,尽管目前关于董责险的司法争议还极为有限,但这主要是董责险在我国长期“遇冷”所致。随着董责险市场覆盖率的逐步提高,我国司法实践中必然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董责险纠纷。本文对董责险法律关系进行系统论述,亦是期望能够为这些争议的解决提供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