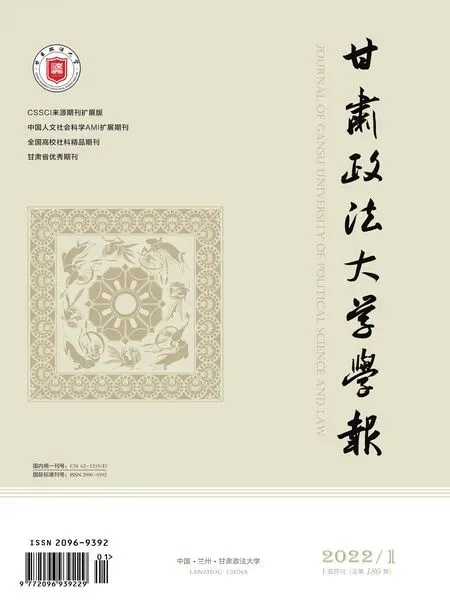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新解:以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置换从旧兼从轻
童云峰
一、问题的提出:实务中同问异答常见频发
“法不溯及既往”体现了对法律主体信赖利益的保护和法安定性的维护,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93条确立(1)《立法法》第93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但允许基于优势利益有条件地溯往。然而,关于司法解释尤其是刑法司法解释是否存在溯及力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于2001年颁行《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01年规定》),对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专项清碍(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1〕5号,2001年12月7日发布)规定:“一、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施行,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二、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三、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四、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但因理解偏差和解读异致,仍困扰司法实践的精准适用。笔者通过裁判文书网,以“法不溯及既往”为关键词,共检索到234份刑事判决书,经逐一筛查,获取直接涉及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判决书92份,对每一份判决书经过提炼和归纳后获悉:(1)主要涉及的犯罪可归纳为19种(3)贪污贿赂犯罪10件,食品药品犯罪4件,侵犯财产犯罪17件,破坏环境犯罪14件,毒品犯罪5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10件,寻衅滋事罪4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4件,组织卖淫犯罪2件,开设赌场罪5件,黑社会犯罪2件,非法侵入住宅罪1件,信用卡犯罪2件,组织传销活动罪2件,故意伤害罪2件,虚假广告罪1件,非法经营罪3件,伪造印章罪1件,妨害司法罪3件。,涉及这些罪名的原因在于相关司法解释出台或频繁修改;(2)实践中法官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司法解释无溯及力”辩护理由,大致有六类回应态度。
类型一:引用《2001年规定》(30件)。法院不做肯否回答,直接引用《2001年规定》作为回应。例如,“伍志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行为发生在2017年2月至5月间,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号,以下简称《个人信息解释》)是2017年6月1日起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被告人伍志强无罪。法院认为,关于司法解释适用问题,《2001年规定》已有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符合该规定,故不违反刑法关于溯及力的原则。(4)参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6刑初76号刑事判决书。此类裁判说理在实务中最为常见。
类型二:回避问题(14件)。法院不做正面回应而是借其他事由否决辩护。例如,“冯志浩、张同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辩护人认为张同同犯罪时《个人信息解释》尚未生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应对张同同适用该司法解释中的“情节特别严重”。法院认为,虽然张同同犯罪时该司法解释未施行,但案发后,该司法解释已生效,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5)参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9刑终79号刑事裁定书。此处法院对司法解释是否具有溯及力并未回答,只是以案发时已有司法解释为由否决辩护理由。
类型三:直接忽略(16件)。笔者通读判决书全文并未发现法院的任何回应,但却径直定罪。例如,“王某甲寻衅滋事案”,辩护人提出,网络短信辱骂他人构成犯罪的司法解释生效于2013年9月10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之前的行为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法院的判决是,根据被告人王某甲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行为的危害程度,其已构成寻衅滋事罪。(6)参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4)新刑初字第180号刑事判决书。对司法解释无溯及力的辩由并无点滴泼墨。
类型四:认为不存在溯及力问题(26件)。其逻辑是溯及力专属于法律,司法解释作为阐明法律规范含义的方法,并无溯及力问题可言。例如,“林贵亮寻衅滋事罪案”,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林贵亮等人的行为在前,《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号,以下简称《办理黑恶势力案件意见》)颁行在后,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被告人林贵亮等人不能被认定为恶势力团伙。法院则认为,虽然《办理黑恶势力案件意见》颁行在后,但其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的解释,其作用是指导司法人员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本院依照《刑法》对本案作出判决并不违反从旧兼从轻原则。(7)参见上杭县人民法院(2019)闽0823刑初196号刑事判决书。
类型五:认为有溯及力(2件)。法院肯定司法解释有溯及力问题,并对其溯及既往予以认可。例如,“王继一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案”,辩护人提出,“一审法院适用2012年‘两高一部’《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公通字〔2012〕1号),违背‘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法院认为,“本案是经检察院抗诉发回重审的案件,在重审期间,一审法院依照刑法、司法解释和‘两高一部’的通知规定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因司法解释具有溯及力,故本案不违背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8)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潍刑二终字第9号刑事裁定书。
类型六:认可无溯及力(4件)。法院认可刑法司法解释无溯及力的辩由,例如,“刘某某等污染环境罪案”,法院认为,本案发生在2014年至2015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应适用2013年6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9)参见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05刑终68号刑事裁定书。又如,“江伟等走私毒品案”,法院认为,被告人江伟实施犯罪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3号)尚未废止,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该司法解释中关于贩卖毒品“情节严重”的规定对被告人更有利,故对江伟辩护人提出的“新司法解释不溯及既往”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10)参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0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
综上可知,同样的辩护理由,各法院的回应却大相径庭,不禁令人深思各异裁判的原因何在?需要反思的是,虽有《2001年规定》的定分止争,但部分法院并未完全遵循,是否意味着该规定本身有欠妥当?刑法司法解释相较于刑法是否具有独立性?是否存在溯及力问题?对于实务中裁判混乱的局面应当如何破解?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先爬梳国内外涉及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争议焦点,并对其形成根源与逻辑予以挖掘和检视,继而澄清刑法司法解释的本质属性,揭橥和证立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解决路径。
二、理论的分歧:溯及力的有无观针锋相对
我国刑法理论对司法解释有无溯及力的争议异常激烈,与此相对,国外虽无统一的司法解释,但有肩负司法解释功能的判例,一旦判例变更也会诱发类似司法解释溯及力的问题。因此,对域外学理争论亦有考察之必要。
(一)对我国既有争论的归纳
通过归纳分析法,可将既有涉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论断,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
其一,无溯及力说。纵观现有研究,几乎无人主张“绝对无溯及力说”,不少学者将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与刑法溯及力作等价理解,即均应坚守“从旧兼从轻原则”。(11)参见刘宪权、阮传胜:《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4期;郑伟:《对蔡某某挪用公款案的法律评析——论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具体运用》,载《法学》2001年第1期;黄京平:《论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以朱某等非法买卖枪支案为视角》,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5期。这类观点在我国实务界与理论界都有一定的市场。但是,若行为时并无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在行为后颁行且是针对该类情形的唯一司法解释,则此说的“从旧”判断并无依据。
其二,有溯及力说。认为“无溯及力说”是对司法解释的误读(12)参见郑东:《司法解释具有溯及既往效力》,载《检察日报》2001年2月18日,第3版。,司法解释不存在从旧兼从轻问题,否则便会以错误适用刑法为代价来肯定既往错误解释的不可思议之现象,一旦承认司法解释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便会形成司法与立法同级的不恰格局,更是脱逸立法权与司法权各行的法治国原则。(13)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6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05-106页。然而,有学者批评到,“有溯及力说”只注重刑法司法解释的形式正义,忽视了实质正义,罔顾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哪怕新司法解释更为苛刻也当然溯及既往,仅此一点足以证明该说的不合理性。(14)参见陈刚:《刑法司法解释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6页。
其三,内容区分说。并不绝对勘定司法解释溯及力之有无,而是以特定的标准或内容分场景地识别。基于不同标准,其内部又可分为多种观点。(1)扩大解释与否说。对于明显属于扩大解释的司法解释,原则上只能对其颁行后的行为有评价功能,对于那些常规化解释或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方可溯及既往。(15)参见刘仁文:《关于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载《法学杂志》2003年第1期。(2)复杂区分说。对于大多常规化司法解释溯及力的判断应以案件是否正在办理或尚未办理为标准,而有扩张解释的司法解释只对其生效后的行为适用。(16)参见张军:《试论刑事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2期。(3)遵循《2001年规定》说。依照《2001年规定》的基本含义确定司法解释溯及力之有无,若司法解释是某类行为的唯一解释,无论颁行在前抑或在后,只要案件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一律适用该司法解释;若存在新旧司法解释,则应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17)参见兰志伟:《对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理论及实践探讨》,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5期。也有学者借鉴美国经验解读《2001年规定》,将司法解释分为立法式司法解释和个案解释式司法解释,前者具有立法意义应禁止溯及形式,这符合《2001年规定》第3条的含义;后者具有司法意义应禁止溯及效果,契合《2001年规定》第2条的旨趣。(18)参见郑泽善、车剑锋:《刑事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研究——对美国司法实践中禁止溯及既往原则的借鉴》,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2期。应当看到,前两种区分说的标准过于模糊和混乱,诸如“扩大解释与否”“常规化解释”本就模糊更难以甄别,并未被理论界普遍认同,而《2001年规定》也因标准异致和理解各异,未被实务部门全面运用。
(二)对德日类似争辩的梳理
德国和日本虽没有统一司法解释,但是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会集聚同类情形,提取同类前案的基本法律逻辑,并据此作出判断,前案就会产生方向性和可预测性。(19)[日]宫原均「先例拘束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アメリカにおける先例拘束理論の歴史的形成―」中央ロー?ジャーナル11巻3号(2014年)86頁。因此,德日的判例与我国司法解释具有相似功能。
在德国,对于变更的判例是否有溯及力存在两种观点:(1)变更判例不溯及既往。公民信任稳定的司法判决犹如信任法律一般,不应让他们失望,应当把那种稳定的和看起来可靠的司法判决改变为对被告人不利的情况,置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制约之下。(20)参见[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德国刑法总论I——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2)判例变更不受禁止溯及既往原则限制。金德霍伊泽尔教授认为,在针对(迄今)有效存续的判例加以更改上,也不适用禁止溯及既往原则。(21)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第6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韦塞尔斯教授也赞同这一观点。(22)参见[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罗克辛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公民不需要认识这些司法判决,也不应当相信他们,而应当相信法律原文!因为司法判决的变化必须保持在可能的文字含义之内,所以,从趋势上说,这种变化没有法律变化那么重要和那么容易预见到,同时,个人能够而且必须在一些情况下适应这种变化……行为人在实施这些行为时,以不受责备的方式相信了一种确定的司法判决……那么,后来虽然出现了司法判决的改变,他也不能为自己的法律忠诚而肯定地受到处罚。在这样一种情况中,本来就应当根据无罪责的禁止错误而宣告无罪。”(23)[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7-98页。概言之,德国司法判例确立的解释规则变更,有无溯及力问题虽有争议,但不受禁止溯及既往原则限制是主流观点。
在日本,司法裁判认为,即便通过溯及适用对被告人不利变更的判例也不违反宪法。(24)参见最高裁判所1996年11月18日判决,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50巻10号754頁。学界存在两大主流学说:(1)否认判例法源性继而认可判例变更具有溯及力,但将问题转借“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路径加以解决。(25)林幹人『刑法総論』(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66頁参照。承认判例的法源性等于承认法官的立法者身份,导致权力失衡,对判例不利变更作为禁止错误较为妥当。(26)小名木明宏「刑法の時間的適用範囲と判例の遡及効」北大法学論集71号(2020年)278頁。山口厚教授主张,只要不存在禁止规定,我们就不能否认其溯及适用,对于被告人的救济,应根据具体情况,通过欠缺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路径寻求免责。(27)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7页。前田雅英教授认为,将不利于被告人的判例变更一般性地都不适用于具体案例,并不妥当。的确,会存在一些处罚不合理的情形,但应当以先例的确定程度以及一般人、被告人对于先例的认识等为基础,在具体的故意论或量刑判断中,去应对给被告人带来的不利益。(28)参见[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西田典之教授认为,判例终究仅属于对法律的解释,而并非法律本身,若对判例也禁止溯及性变更,则有违三权分立原则,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肯定基于缺少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的责任阻却。(29)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2)肯定判例法源性故否定判例有溯及力。(30)佐伯仁志「罪刑法定主義」法学教室284号(2004年)50頁。刑事判例是从属立法或者间接法源,因此当然不能溯及既往。(31)山崎友也「刑事判例の変更と憲法39条」富山大学紀要.富大経済論集2号(2006年)209頁。大谷实教授认为,若判例变更剥夺了预测行动的可能性时,便会侵害国民行动自由,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由于生效判例具有和法律相同的预告机能,所以,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相比,对其应当优先考虑。因此,提倡“判例不溯及既往的变更”。(32)[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曾根威彦教授也认为,对被告人不利的判例变更,应当禁止溯及既往。(33)参见[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总之,日本司法实务与德国司法实践都认可变更判例的溯及力,理论界的争议也大致相同,只是日本学界的争论更为激烈。
总而言之,德日学者之所以对判例变更的溯及力问题持不同态度,是因他们对判例的法源性坚持了不同立场,否认判例法源性则主张判例能够溯及既往,肯定判例法源性则认为判例受禁止溯及既往限制。前者希冀通过违法性认识错误来化解对被告人的不利溯及,但是一方面认为判例不是“法”,另一方面又认为对判例变更的认识错误是违“法”性认识错误,有自相矛盾之嫌;后者主张判例是独立的法源,这在成文法国家难以被接受,也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德日变更判例溯及力之有无观的表象及其生成根源,与我国司法解释溯及力有无观如出一辙,我国纵有《2001年规定》也未能定分止争,我国学界的争论和解决方案与德日也并无二致,皆有首尾乖互和逻辑不恰的症结。为此,下文先具体分析我国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争议的本土化原因,继而对症下药提出解决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规则。
三、症结之所在:对司法解释属性的误判
综合当前关于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讨论,从形式上看,纠缠于司法解释有无独立的时间效力问题;从实质上看,问题的命脉是司法解释与刑法规范是否具有等价性。
(一)直接原因:解释垄断主义的生成与更迭
之所以会产生对司法解释溯及力的不同判断,很多司法解释提倡者也深谙,是因最高司法机关垄断法律解释权所伴随的结果。(34)参见张立刚:《法律解释体制重构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从历史维度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滥觞于1955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而最早的司法解释可追溯至对婚姻法的解释。当时因《六法全书》被废而新的法律体系尚未建成,代替法律的政策较为宏观和抽象,司法案件又亟需规范依据,“司法解释”便应运而生;另一个原因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法院业务工作有指导权力,保障中央法律政策在地方统一实施。(35)参见纪诚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一个初步的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1页。从实践维度看,法典主义并非完美无瑕,成文法典的确定性既是优势也是缺点,由于语言文字的抽象性难免带有模糊性和个案涵摄障碍。由此法典万能主义受到利益法学派的诘难,凸显司法解释之必要。(36)参见蒋涛:《罪刑法定下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完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而我国不仅幅员辽阔又长期受中央集权思想浸染,同时法官因畏忌个性解释而引致担责,不愿发挥解释能动性,而是寄衷于司法解释。于是,解释垄断主义生成并取代法官个案裁量主义。实际上,垄断性司法解释产生了大量立法,有削克辩方权利之虞,但却获法官云集景从。(37)参见[英]麦高伟(Mike McConville):《英国的刑事法官:正当性、法院与国家诱导的认罪答辩》,付欣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99页。我国司法机关颁行的刑法司法解释不仅具有垄断性且常有主动性,宪法确定的法院上下级监督关系,通过这种主动性被扭转为实质上的领导关系。司法人员将司法解释奉为圭臬,由此法官必然如对待法律一般,思考司法解释对其颁行之前的行为有无效力。
“法律规范大多数都有一个解释空间。在这个解释空间内,可以赋予同一法律规范不同的涵义,而在解释的时候只能从中选择一种作为对该法律规范的解释。作为对该法律规范之解释的这种理解应该在考虑到其他解释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接近具有多数公认力的正义观念……然而公认的正义观念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38)[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因此,解释垄断主义生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也会紧随时事迭代更新,单就本质而言这是客观解释的要求,但在适用中便会生成问题,对同一行为在新旧司法解释间如何抉择适用,便是溯及力问题的范例。例如,对于侵犯著作权罪,前后共有6个司法解释(39)分别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30号);(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及录音录像制品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05〕12号);(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7〕6号);(5)《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公通字〔2010〕23号);(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1〕3号)。,对同一行为适用不同解释则会出入罪的情形俯拾皆是。又如,针对污染环境犯罪,最高司法机关先后于2006年、2013年以及2016年颁行三个司法解释(40)分别是《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4号),《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以下简称《2013年环境解释》)和《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6〕29号,以下简称《2016年环境解释》)。,《2013年环境解释》与《2016年环境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这一入罪标准的界定存在区别,前者列举14项情形,后者共计18项,此时适用不同的解释则可能出入罪。若绝对遵循“有溯及力说”标准难免伤及被告人的信赖利益,“法官有时候在没有给他们任何选择机会的冷酷逻辑压力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得出无情的结论。他们对这种牺牲了正义的仪式深感遗憾,但他们依然执行了这样的仪式,眼神躲躲闪闪,在挥动刀锯的时候还说这乃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而那些受难者则成为献给法理学诸神的祭品。”(41)[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李红勃、李璐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因此,原本旨在廓清规范迷惘的司法解释,在化解解释权力冲突后又带来与信赖利益的龃龉。立法未动司法解释先行的情形也较为常见,于是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便纷至沓来。
(二)深层滥觞:司法解释独立性与从属性之争
溯及力问题属于时间效力的子问题,关于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2001年规定》指出,“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施行,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因对该条理解的差异,理论界对司法解释有无独立的时间效力问题莫衷一是。主要有两类观点:(1)从属性说。主张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全面从属于刑法规范。(42)参见游伟、鲁义珍:《刑法司法解释效力探讨》,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6期。(2)独立性说。主张司法解释有独立于刑法之外的时间效力。(43)参见刘宪权:《我国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的再思考》,载《法学》2002年第2期。刑法司法解释应自其公布或规定的时间起生效。(44)参见丁慕英:《关于开创刑法司法解释学之我见》,载赵秉志、张军主编:《刑法解释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页。
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争论,形式上是在讨论司法解释有无独立的时间效力,实质是司法解释与刑法规范之间是等价性抑或附属性的僵持。认为司法解释与刑法规范具有等价性,会主张司法解释有独立的时间效力和无溯及力;认为司法解释从属于刑法规范,则会主张司法解释无独立的时间效力和有溯及力(或不承认存在溯及力问题)。而前文所述的“内容区分说”实为在两者之间纠葛与徘徊后的折中。等价性说则认为,我国已经形成刑法、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五位一体”的刑法规范体系,理论上应当由逻辑论转为道理论,提倡五位一体的广义刑法论,在广义刑法内部出现新旧更迭时都应全面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45)参见姜涛:《刑法溯及力应全面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4期。当刑法规定明显存在不合理之处,且与司法解释抵牾时,优先适用司法解释。(46)参见刘宪权:《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的冲突适用》,载《法学论坛》2020年第6期。附属性说则主张,刑法司法解释并非刑法本身,其本性在于使刑法明确化与具体化,其效力不应与刑法等同。(47)参见黄明儒:《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辨析》,载《时代法学》2007年第6期。
综上可知,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争执的源泉是司法解释“独立性”与“从属性”之争。认可司法解释有溯及力或否认司法解释存在溯及力问题的观点,皆持司法解释从属性说。一旦否认刑法司法解释有溯及力,则会承认司法解释的独立性,但这在成文法和法治国度是永远也无法跨过的藩篱。
(三)正本清源:刑法司法解释“独立性说”之批驳
司法解释“无溯及力”与“无溯及力问题”并非同一命题,前者是在承认司法解释独立性的前提下,认为司法解释如刑法一般,应坚守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而后者认为司法解释完全从属于刑法,毫无谈及自身溯及力有无之必要。本文坚决反对以实践现状为导向的“将错就错”,否决刑法司法解释独立性或等价性的论断,重申司法解释从属性地位,对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予以证伪。
首先,刑法司法解释的本质属性决定其不存在独立性和溯及力问题。但凡“解释”必然依附于被解释的规范,古罗马的解释经典《法学阶梯》与《学说汇纂》便依附于罗马法的时间效力。(48)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李双元、张茂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按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的决定》(法发〔2021〕20号)的规定,即使司法解释分为“解释”“规定”“规则”“批复”和“决定”五种形式,但仍是依照立法精神对司法实践中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是法律的精确化与细致化。无论是其他国家的判例解释抑或我国的司法解释、立法解释,其本质皆为精准理解和执行法规范的工具,并非新构而是释明,并无独立性可言。而法院的解释只是对一种与具体案件事实相关的法律的发现,对类似案件有无拘束力取决于能否妥当地解决具体案件,而妥当与否的标准即是国民的信赖利益。(49)橋本裕藏「判例の不遡及的変更の法理について:岩手県教組同盟罷業事件第二次上告審判決をめぐる中山教授の所説に答えて」放送大学研究年報17号(1999年)31頁。通过司法解释确定的规范意涵从法律生效之日便可如此理解,解释的时间效力从属于刑法。解释是架连刑法与个案事实的桥梁,而司法解释虽褫夺法官的个性解释权,但也难掩其“解释”的本质。解释不是法,即不存在事后法与重法之前提,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解释的溯及力。同时,《立法法》第93条确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仅针对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规章,并未涵括司法解释。《刑法》第12条确立的溯及力规则也仅限于“法律”,此处的法律包含刑法和确定空白罪状的其他部门法、法规和规章,但绝不会指涉司法解释。因此,从刑法司法解释本身的从属性以及溯及力问题所指涉的对象,可以辨别司法解释不应与溯及力问题勾连。即使《2001年规定》第3条针对新旧司法解释变更设置的处理规则与溯及力规则(从旧兼从轻)有相同的效果,也不能倒推司法解释存在溯及力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如不管司法解释内容如何,对其生效之前行为都具有溯及力,必然违反刑法原则上不溯及既往原则。(50)参见刘宪权:《刑法学名师讲演录》(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这里实际上存在逻辑上的“概念偷换”,其推导过程是:刑法司法解释有溯及力→违反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刑法溯及既往→刑法有溯及力,则结论必然是:刑法司法解释=刑法。
其次,刑法司法解释与其他法域司法解释皆无独立性和溯及力问题。刑法因严厉性而比民法、行政法更强调安定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但这只是规范本身的异质。无论刑法司法解释抑或民事、行政司法解释,本质都是对法律意涵的阐明,都是解释垄断主义的外现,不会因被解释规范异质而有所差别。因此,所有司法解释都应还原其从属性,没有必要讨论溯及力问题。与刑法司法解释不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对民事、行政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只是零星散布在相应司法解释中。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2日颁行的《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7号)第29条明确规定:“本规定自2020年9月12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施行前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再审。”概言之,该解释对其颁行之前和之后的行为皆可适用。不同的民事、行政司法解释适用模式的设置也较为混乱,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三类:(1)有限溯及模式,可适用于颁行前的行为,但已终审的不再溯及;(2)涉诉不溯模式,除已终审或正在审理的颁行前行为外,司法解释皆可适用;(3)不溯及模式,仅适用于该司法解释颁行后的行为。(51)参见杨登峰:《新旧法的适用原理与规则》,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6-98页。可见,民事、行政司法解释呈现出不溯及既往的趋势。也有学者认为,民事、行政司法解释多以受理时间而非案发时间为基准确定适用与否,这不仅违背适用的基本逻辑,也会导致起诉时间的早晚决定处理结果的轻重,滋生实质不公,应赋予刑法以外司法解释溯及力。(52)参见孙晓红主编:《法的溯及力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本文认为,各部门法的司法解释不应因被解释规范不同而切分属性,各类司法解释虽解释内容和方向有别,但终将殊途同归,不应将其适用问题偷换为溯及力问题。
最后,以承认“独立性”来缓解“立法化”司法解释的弊病实为饮鸩止渴。实际上,前文所述的“无溯及力说”“内容区分说”已看出我国司法解释侵犯立法的现象,试图以承认(或部分承认)司法解释独立性来保障被告人的信赖利益,或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其基本逻辑为:司法解释立法化(独立性)→有独立的时间效力→无溯及力→从旧兼从轻。这种人文情怀值得赞许,但逻辑错误不可忽视。其逻辑起点是认可司法解释立法化,对司法解释侵犯立法现象不予纠偏反而“积非成是”,恰是以错误地适用刑法为代价换取结果的合理性。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确实存在僭越立法权的现象,例如,承认过失类交通肇事罪在特定情形下可以构成共犯。(5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第4条:“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些越权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备受质疑,且为罪刑法定原则所不容,是当下和将来刑事司法应当清理和避免的问题。不能因对司法解释越权现象无能为力便干脆认可,进而推导出司法解释独立性、无溯及力或从旧兼从轻原则,这是一条不归路。正因司法解释轻视“逻辑论”,才会生成诸多干预立法和溯及不利的现象,若不纠偏反而罔顾法律常识,则必然在错误的逻辑陷阱中无法自拔。同时,应甄别司法解释的权力内外界限。诸如将过失犯罪解释为可以成立共同犯罪的“类推”解释,明显属于权力外的立法现象。但是,诸如“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严重污染环境”等概括性标准,实为立法者故意留下的授权性项目,即使司法解释对该类标准予以前后变更而产生不利于被告人的结果,也未超脱授权,对此不利后果的问题可在解释规则内解决,具体方案下文将会阐论,但不能据此而接纳司法解释独立性。否则,司法解释立法化便大行其道,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力荡然无存。
综上论述可以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刑法司法解释与民事、行政司法解释属性合致,都应从属于被解释的法规范,不应有独立性或等价性,这是其后论断展开的逻辑前提,对于超脱从属性而走向立法性的司法解释应当清理而非“将错就错”。其二,从属性决定刑法司法解释并无独立的时间效力,刑法的生死便是司法解释的寿命。其三,只有法律才有溯及力问题,司法解释并无溯及力问题。不宁唯是,法律的逻辑性必须要关照实践的经验性,否则即使能自圆其说也毫无活力,解释垄断主义的生成与更迭,确实可能侵犯被告人的信赖利益或破坏法秩序的稳定性。对此问题应如何化解,恰为各方争论的初衷,但肯定司法解释独立性之路难以畅通,更是饮鸩止渴,亟需探寻符合规范逻辑和满足实践需求的新方案。
四、困境的化解:“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解释规则之提倡
有效性和垄断性是司法解释的特有要素,这也要求司法解释制定者应避免干预立法或类推解释,否则全国司法机关皆在重复类推。(54)参见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解释法律必须兼维法律之安定与理想,而后法律的功能始能充分发挥。”(55)杨仁寿:《法学方法论》(第2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对越权司法解释应启动审查机制予以清理,对司法解释更迭诱发的侵袭信赖利益风险,应放弃对“独立性说”的痴心,更告别对“溯及力论”的妄想,可在解释论内部觅求破解方案,本文提倡借助“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规则予以化解。
(一)“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解释规则的引证
司法解释的本质是一种垄断解释,会随着客观环境变化而更新,对垄断解释生成前的行为、处于新旧垄断解释之间的行为,究竟适用何种解释?直接牵涉被告人利益的多寡。在垄断解释生成前,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不能“拒绝裁判原则”也会作出个案解释,而此时的个案解释若符合刑法旨趣则合法有效,一旦个案解释串联并形成共识,就会生成“惯例解释”。(56)恳请注意,“惯例解释”不是对惯例的解释,而是在对特定问题尚缺专门的司法解释时,司法实践已基本达成共识的解释,且解释的内容也符合刑法规范含义。例如,对于非法放贷行为,2019年10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9〕24号,以下简称《2019意见》)第1条将营利性、经常性、对象不特定性的发放高利贷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然而,在《2019意见》颁布之前,理论与实务对无罪论基本达成共识。(57)参见刘伟:《论民间高利贷的司法犯罪化的不合理性》,载《法学》2011年第9期;李腾:《论民间高利贷不应司法犯罪化》,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1期。例如,“何伟光等非法经营案”,法院认为,何伟光等人确实存在高利放贷行为,其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因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的具体行为方式并不包括高利放贷行为,因而对公诉机关指控何伟光等人犯非法经营罪的意见不予支持。(58)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深中法刑二终字第429号刑事裁定书。实际上,该案在二审维持裁定之前就已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何伟光、张勇泉等非法经营案的批复》(〔2012〕刑他字第136号)的认可。但是,《2019意见》颁行之后有罪论便大行其道,将其解释进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也符合涵摄规则。此外,新旧司法解释的更迭,也会影响行为入罪标准的升降。概言之,司法解释对信赖利益的侵犯主要包含两种情状。其一,“惯例解释”与司法解释冲突。其二,新旧司法解释冲突。无论惯例解释、新旧司法解释,在特定场景下皆为合法有效,因其而生的既判案应被尊重。但是,当各类有效解释发生冲突时,哪一解释具有妥适性便生疑问,例如,行为发生时旧司法解释明确有效,但审理时旧司法解释已被新司法解释明文取代,且二者对被告人的处置轻重有别。
褪去司法解释垄断性之后,对上述两类冲突再行甄别便可察觉,实际上都是“解释存疑时”如何抉择的问题。众所周知,“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是经典的法格言,在刑事诉讼领域,“事实存疑时”的贯彻较为彻底,是证据存疑时的裁判规则。然而,在刑事实体法领域,当对刑法文本解释存在疑问时能否选择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在学界存在较大争议。肯定论认为,在对法律条文解释模棱两可时,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推断,“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应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皆准的综合性规则。(59)参见邢馨宇:《有利被告的定位》,载《法学》2012年第2期。而否定论认为,对法律含义存在疑惑或争论时,应通过法律解释方法论消除疑虑,而并非一律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60)参见张明楷:《“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界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1期。如果事实清楚罪疑唯轻原则并无适用余地,对被告人作出的解释有利与否,不是取决于法律效果,而是取决于如何正确理解所涉规范,没有在法律适用不明时一定要适用较轻构成要件的道理。(61)参见蔡圣伟:《刑法问题研究(一)》,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8页。纵观既有争论,肯定论式微,而否定论强势。有学者总结到,否定论的立据主要分为两个层面:(1)在价值论上,刑法应秉承价值中立而不应给与被告人倾斜;(2)在方法论上,目的解释始终占据制高点,只要符合法益保护目的,不论解释结论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皆为妥适。(62)参见冀洋:《“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规则之提倡》,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4期。本文赞同肯定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其一,刑法的价值协调功能并不等于价值中立立场。否定论通常主张,刑法既要保障人权又要维护秩序,既要保护法益又要维护自由,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处于同一位阶并无主次之分(63)参见张兆松:《“刑法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质疑》,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6期;段启俊、郑洋文:《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应适用于刑法解释》,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41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刑法既要实现各种价值内容,又要协调各种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实现整体价值的最大化,其理性定位应是价值中立。(64)参见魏东:《刑法各论若干前沿问题要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将刑法的利益协调功能偷换为中立平衡功能。实际上,刑法的功能在于协调各方利益以实现安定性。例如,刑法既要救济被害人权利,又要维护社会秩序,更要保障被告人人权,这种多重利益协调功能并不意味刑法必须要在各方利益之间保持中立。现代刑法与封建刑法的本质区别是通过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以向保障自由倾斜,罪刑法定原则的本义已折射出,当惩治犯罪与保障自由冲突时,偏佑于后者。众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则滥觞于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65)《自由大宪章》第39条:“任何自由人,非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家的法律,不得逮捕、监禁、剥夺领地、剥夺法的保护或放逐出境,或者加以其他任何损害。”,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世界人权宣言》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再次重申罪刑法定原则。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本质是保障人权和限制刑罚权。需要忖量的是,为何通过限制刑罚权的方式来保障人权?折射的是,自由价值在博弈过程中胜出。由此可见,保障公民自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首要价值。因此,在面对刑法规范含义模棱两端时,在不利与有利被告人间摇摆不定时,在“不能拒绝裁判”原则制约下,应当勇敢迈向有利于被告人之路。实际上,无论是程序法上“事实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抑或实体法上“解释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皆为自由价值优先在刑事领域的彰显,事实与规范都不容歪曲,在制度落实上则依次表现为疑罪从无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
其二,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并不排斥被告人的利益。否定论通常将“法益保护”与“有利于被告人”人为对立,形式上以价值中立论试图平衡二者,但实质上却取道目的解释论而倒向不利于被告人。例如,有学者认为,“刑法的任务与目的是保护法益……所以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都是对违反保护法益的事态所作的记述或者描述。既然如此,刑法学当然必须从实质上对构成要件进行解释。”(66)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42页。而所谓的实质解释是以保护法益为导向的目的解释,由此价值中立摇身一变为法益保护优先。然而,当解释存疑时不采纳有利于被告人规则,也暗弃价值中立的平衡主义路线,却使用目的解释论,易生践踏罪刑法定原则的危机。首先,目的解释优先论容易走上类推解释之路。刑法解释不反对扩大解释但抵制类推解释,而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本就难解难分。法益保护优先论的解释者势必挖掘刑法条文潜义,甚至榨干刑法条文含义,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走在类推的边缘。例如,为了对真军警人员抢劫行为适用抢劫罪的加重法定刑,煞费苦心地将《刑法》第263条中“冒充”解释为“假冒+充当”;(67)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解释原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69页。为让窃取支付宝内余额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而将支付宝解释“信用卡”(68)参见刘宪权:《论新型支付方式下网络侵财犯罪的定性》,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5期。,为将没有致人伤害危险的高空抛物行为解释为寻衅滋事罪,而将情节恶劣的高空抛物行为解释为“恐吓”。(69)参见张明楷:《高空抛物案的刑法学分析》,载《法学评论》2020年第3期。诸如此类冒险解释在理论与实务中不胜枚举,这些解释的提倡者通常言之属于语义可能性范围内的扩大解释,但往往超出大多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其次,目的解释优先论之“目的”往往掺杂解释者个人之好恶。“不幸者的生活和自由成了荒谬推理的牺牲品,或者成了某个法官情绪一时冲动的牺牲品,这样的法官把自己头脑中一系列混杂概念中得出的谬误结论奉为合法的解释。”(70)[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解释者以法益保护目的的“高牙大纛”,在规范解释过程中暗塞个人价值观。例如,实质解释论通常认为,“对刑法规范应该从行为是否实质达到了值得处罚的程度进行实质的解释。”(71)刘艳红:《实质刑法观》(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6页。而所谓的“值得处罚的程度”并无客观标准,往往依赖解释者的个人价值观。解释者个人价值观念的差异会影响目的解释的结论,甚至直接左右被告人出入罪,这点在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例如,有学者在总结国外学说的基础上将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划分为三类:(1)法律的评价要素;(2)经验法则的评价要素;(3)社会的评价要素。(72)参见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198页。尤其后两类的判断依赖于解释者的价值观,诸如“猥亵”“淫秽物品”之类要素,解释者个人的性开放程度会影响评价结论,若偏向法益保护目的,不排除有对被告人过度苛责之嫌。最后,目的解释优先论直接偏向预防刑法观。预防刑法观的基本逻辑为:前移刑事违法判断中心,从“没有法益侵害就没有犯罪”向“有法益侵害,就有犯罪”转变,刑法由消极被动介入转向积极主动干预。(73)参见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功能主义的刑法立法观》,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6期。这股风险刑法思潮因使刑法工具化、处罚模糊化和过度干预性而令人担忧,虽有学者试图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设置规则以克服预防刑法观的弊病(74)参见黎宏:《预防刑法观的问题及其克服》,载《南大法学》2020年第4期。,但欠缺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目的解释优先论认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为了实现法益保护目的,试图根绝法益侵害风险,则会寄托于犯罪预防,“恰恰是一些犯罪行为一旦发生结果,法益侵害就难以控制,才对法益进行提前保护。”(75)张明楷:《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5期。这种刑法处罚早期化难免使得实行行为抽象化和扩大化,甚至导致对犯罪的处罚与行为关系不大,冲击着刑法的谦抑性。(76)参见刘艳红:《实质出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5页。不断向法益保护一端添置砝码,则自由保障一侧会失衡,所谓的价值中立变成了掩盖过度惩罚犯罪的遮羞布。本文并不反对目的解释,但反对目的解释优先论,其实际上不仅偏离原设的价值中立立场,更容易滑向类推解释和预防刑法观,对被告人自由的侵犯不容小觑,与罪刑法定原则设立的倾向保障自由的立场相悖。实际上,刑法兼顾法益保护和自由保障,当二者冲突时并非减损或排斥自由,而是在适度倾斜自由的基础上实现法益保护,这便是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根基。
其三,“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解释规则不应被曲解。诸多学者之所以反对“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解释规则,源于对该规则的误解。“我们更不能因为自己不愿意深究法律条文,或者不善于澄清法律疑点,而在遇到法律疑点时,就来一个‘有利于被告’。”(77)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6页。“明确性原则并不要求有利被告解释……责任主义并不意味有利于被告解释。”(78)袁国何:《刑法解释中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之证否》,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6期。以上否定论的见解存在误区。首先,“存疑”并非指任何疑问。不可否认,在对刑法条文理解方面确实存在各种疑问,律师辩护的一项重要策略便是对法律适用觅寻疑点,但并非任何疑问都会被法律认可进而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推断。如同事实存疑的标准为“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一般,法律解释存疑的标准亦应是“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所谓“合理怀疑”的判断应从以下几点勘定:(1)通过合法的解释方法得出对立的解释结论。解释结论并未超脱规范本义,诸如类推之类的非法解释得出的结论无需讨论合理与否。(2)对立的解释结论为一般人所认同。如果不同的解释结论仅为一家之言,并不符合理性的一般人认知,那仅是狡辩。例如,律师提出国企高管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因而不构成贪污罪,这一结论难被公众接受,因此就不是合规范的解释疑问。至于一般人的标准则需要依赖“常理、常情和常识”以及经验法则加以辨识。(3)解释对象因是新生事物而导致解释结论存在疑问。例如,在虚拟财产显现之初将其解释为财物,即是合理怀疑,即使是现在将虚拟财产解释为财物仍存较大争议。合理怀疑会随着时代变迁和认识变化而转变为非合理怀疑,从电被解释为财物,由反对到普遍认同便可确信。其次,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恰是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解释的实质根据。“如果对法规范内容解释存在法律固有的漏洞(原始的缺陷),或者存在后来因情况的变化才出现的漏洞(嗣后的缺陷),刑事法官必须作出无罪判决。”(79)[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86页。明确性要求处罚被告人的刑法规范必须无疑,合理存疑时必须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不能让被告人承担规范不明的恶果,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题中之义。最后,责任主义并不排斥有利于被告人解释。责任主义要求被告人至少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才有非难之必要。当对规范解释存在疑问,尤其是司法解释更迭时,前后司法解释都符合规范语义,一旦行为发生在二者之间,若强行适用新司法解释(更重),必然有违责任主义,于此解释存疑之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抉择,也是责任主义原则的当然旨趣。
总之,当对刑法解释存在合理疑问时,应作有利被告人的抉择。刑法司法解释虽经垄断但仍难改其“解释”属性,也不能拒斥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规则的适用。因此,当新生司法解释与惯例解释发生冲突,新旧司法解释存在抵牾,都应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规则,具体场景下的运用逻辑,下文将详细阐论。
(二)刑法司法解释适用冲突的解困路径
纵观涉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争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冲突类型:(1)类型一:司法解释对其所解释的刑法规范生效以前的行为能否适用的问题;(2)类型二:司法解释对其所解释的刑法规范生效之后而自身颁布之前的行为能否适用的问题;(3)类型三刑法规范生效之后与其对应的司法解释经历了新旧更迭,处于新旧解释之间的行为如何适用的问题。
对于类型一,理论上并无多大争议,该类问题并不牵涉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而应属于刑法自身的溯及力问题。依照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刑法能够适用的行为,作为从属性的司法解释必然也能够适用。例如,“韦东玮受贿案”,韦东玮受贿时间是2015年1月,受贿金额为4万元,依照旧刑法的规定,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无罚金),而按照《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的规定,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法院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刑九》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法释〔2016〕9号,以下简称《2016年贪贿解释》)认定被告人韦东玮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80)参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1702刑初175号刑事判决书。概言之,《刑九》可以适用,则附属其后的《2016年贪贿解释》亦可适用。
对于类型二,本文认为应当分成三种情形加以斟酌。(1)行为时不仅没有司法解释也未形成“惯例解释”。这种情形实际上对法条的理解一直存在疑问,并未形成妥善和统一的裁判惯例或解释结论,作为释明疑问而颁行的后来司法解释若未超越刑法含义,则当然可以适用。例如,“祝亮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所有被告人的行为均在2017年6月1日前实行完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才规定的新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其由特殊主体扩展为一般主体,2017年6月1日首次对该罪出台司法解释(即《个人信息解释》)。辩护人认为,原有的法条虽然规定了“情节特别严重”,但什么是“情节特别严重”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作出详细规定,因此根据法不溯及既往、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不能适用《个人信息解释》。法院依照《2001年规定》,认为此前没有司法解释,因此依法应当适用该司法解释。(81)参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7)川1102刑初334号刑事判决书。就本案而言,“情节特别严重”在解释出台前确实存在疑问,也无法形成惯例解释,司法解释的出台廓清疑虑,指明了裁判方向,更是立法者赋予的解释权限,被告人和辩护人难以否认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也难以否认情节的严重性,只能从“溯及力问题”角度着手。因此,解释的细化并未侵犯被告人的信赖利益。(2)行为时虽无司法解释但已形成惯例解释且司法解释对惯例解释予以确认。此时,司法解释只是对惯例解释的条文化和规范化,适用司法解释并未侵犯被告人的信赖利益。(3)行为时虽无司法解释但已形成惯例解释且司法解释对惯例解释予以变更。若司法解释的变更使得处罚更重,还一味奉行司法解释普世性,则不仅侵犯被告人的信赖利益,更会颠覆生效判决的既判力。有学者主张,此时对已判决生效的案件绝大多数可以司法救济(再审)。(82)参见刘艳红:《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2期。这种观点很难实现也忽视了解释本身的发展性,随客观条件变化而生成新司法解释,并不能认为过去与其不符的司法解释或裁判惯例皆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例如,在农业和工业社会,我们很难想象寻衅滋事罪可以发生在虚拟网络空间。(8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1号)第5条第2款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基于对被告人信赖利益的维护和对生效判决既判力的尊重,应当承认司法解释颁布前惯例解释的有效性。因此,此类案件法官案牍上有两份有效解释,先前的惯例解释和后来的司法解释,且二者皆符合刑法规范含义,此时对刑法的解读便存在疑问,依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规则,应选择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例如,前文提及的“何伟光等非法经营案”,在《2019意见》之前,司法实践中对非法放贷行为不作犯罪处理。《2019意见》颁布之后,基于规范的预告性,现在对“何伟光等”以非法经营罪认定也不会侵犯其信赖利益。问题的关键是如果行为发生在《2019意见》颁布之前,审判时间是《2019意见》出台之后,若绝对适用《2019意见》则会侵犯被告人的信赖利益,也会与之前的惯例解释存在抵牾,更是造成处罚之轻重取决于审判之早晚的尴尬局面。因此,既要遵循《2019意见》也要尊重惯例解释,当二者发生冲突且是合理疑问时,应作有利于被告人解释,即对该时段的非法放贷行为不作犯罪处理。对此,《2019意见》第8条实际上也予以确证。(84)本意见自2019年10月21日起施行。对于本意见施行前发生的非法放贷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2011〕155号)的规定办理。以上问题皆是解释学内部问题,并非法之溯及力问题。职是之故,《2001年规定》第1条本义为,司法解释的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但不排斥先前惯例解释的有效性,当二者冲突且有合理怀疑时,应当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第2条含义应当是,司法解释出台前,行为时没有司法解释,实践中也没有形成惯例解释,或已形成的惯例解释被后来的司法解释予以确认,对尚未处理或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办理。
至于类型三,在司法实践中也较为常见。例如,“单付军非法采矿罪案”,被告人越界采矿行为皆发生在2015年之前,根据2003年6月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第9号,以下简称《2003年解释》)对被告人处罚较轻,若依照2016年1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5号)对被告人处罚较重,法院按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选择《2003年解释》裁判。(85)参见明光市人民法院(2019)皖1182刑初173号刑事判决书。应当看到,对新司法解释颁布后的行为,鉴于对解释垄断主义更迭的尊重,以及新司法解释预告作用已不会侵犯被告人信赖利益,一概适用新司法解释并无疑问。对处于新旧解释之间的行为,法官审判时需要面对两个有效的解释,若绝对适用新解释则会侵犯被告人的信赖利益,若一律适用旧解释也是对规范含义新阐释的忽视。因此,亟需场景化分析。(1)场景一:新旧解释对行为的处置相同。此时为了避免让同时段类似行为的既判行为人和社会大众不会产生任何对法感情的质疑,优先适用行为时的司法解释更为妥当。(2)场景二:新旧司法解释对行为的处罚轻重有别。此时法官需要在两个合规范的解释间抉择,势必产生规范解释上的合理怀疑,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规则,应采纳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通过上述两点分析,可对《2001年规定》第3条进行全新解读,前半段与场景一对应,其设置初衷是为了照顾同时段类案既判犯罪人和普罗大众的法感情;后半段与场景二对应,是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解释规则的条文化彰显。
结 语
司法解释作为阐明规范含义和统一司法裁判的“工具”,并不因垄断性而生成法典等价性,法律才有的溯及力问题不能套用至司法解释。但是,解释垄断主义的生成与更迭确实在实践中产生“类溯及力式”的难题。对此,若贯彻司法解释从属性,则会侵犯被告人的信赖利益;若落实司法解释独立性,又会陷入规范等价性的逻辑陷阱。因此,求助于“溯及力”方案注定破产,“更可取的乃是让法官用合理解释法规的手段去发现他们自己所应采纳的解决解释问题的方法。”(86)[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7页。但恰当的方法必须建立在明确标准之上,解释标准的不公正会引起诸多反对。“在方法论上判决关注容易理解的调适性结果,显得是必要的。”(87)[德]阿图尔·考夫曼、[德]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92-393页。“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应受法律目的及其基础之立法者价值决定的拘束。”(88)[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0页。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规则符合解决司法解释冲突适用的方法论标准,同时也契合刑法通过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倾斜自由保障的价值观。因此,对于《2001年规定》的理解不应囿于法规范的溯及力视角,而要切换至解释论内部。基于解释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立场,司法解释不排斥惯例解释,当二者冲突且有合理怀疑时,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当新旧司法解释更迭且有合理冲突时,既要充分照顾民众的法感情,也要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