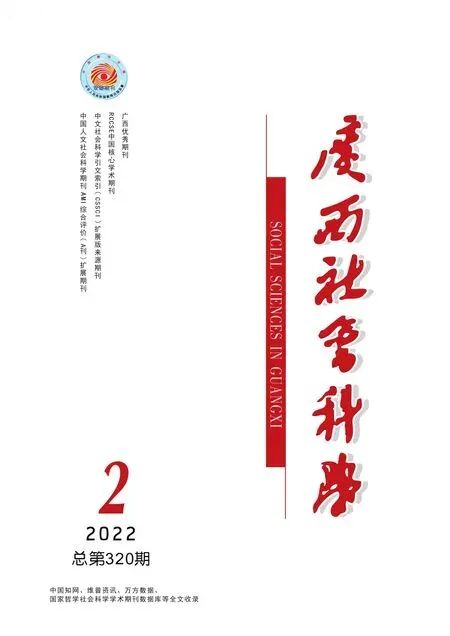论郑献甫对“真”的认知
郑朝晖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郑献甫(1801—1872),名存纻,献甫为其字,又字小谷,其先祖“于明末自北直隶迁粤之象为象人”[1]。其曾任刑部主事,履职仅一年余,即辞官归里,后长期从事书院教学活动,时人称之为“两粤宗师”。郑氏一生,性喜读书,词章、考据、著作之学皆所涉猎,亦重游历,具有强烈的求真崇实倾向。清代岭南大儒陈澧说:“国朝二百余年,儒林文苑之彦迭出于海内,及其既衰,而郑君特起于广西,卓然为一家,学行皆高,可谓豪杰之士矣。”[2]陈澧视郑献甫为清代儒林衰弱之后,“特起于广西”的学术大家,但其肯定郑氏的学术成就主要就其史论造诣而言。其乡人蒋琦龄则除了肯定郑氏“自为一家之学”外,更从学术史的高度,称赞他不分汉宋门户,只求真学问的主张,认为其主张若“学者尊而述之,岂直一隅之幸而已哉”[3],强调郑氏对清代学术整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只是蒋琦龄对郑氏学术倾向的推重,即便在岭南学术史上,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不管如何,郑氏对超越门派之见的学问之“真”的追求,确实推进了对汉学家特别重视的“真”的多方面义涵的认知。当然,郑氏的推进作用,不是通过对“真”的概念解析达到的,而是通过他在经史诗文各项学术领域推进其求真活动时触及的。
一、资料的真
郑献甫主张不问汉宋学派之名目而求真学问,但他也颇为重视汉学家擅长的考据方法,自觉地学习其“读书法”与“著书法”,用作研究经史甚而诗文之学的基本方法。他所说的“读书法”,是指王应麟、顾炎武、钱大昕等人的文献考证方法,“著书法”则指郑樵等人的文字音韵等方法。
余少时见钱辛楣先生《养新录》,欣然喜谓:“读书者当如是矣。”复见顾亭林先生《日知录》,则骇然叹曰:“读书者乃如是耶。”家无藏书,学无师承,姑置之。后得王厚斋《玉海》,观其所著《汉志》《韩诗》诸考,始知读书法。又得郑渔仲《通志》,观其所辑《六书》《七音》诸略,因知著书法。……第以《说文》之异字,《释文》之异音,姑试求之《四书》,颇有发明。更求之《九经》,便漫无归宿。间有得则标之上方,或有论则录之别纸。其后旁读诸史诸子,亦用此法。为日既久,成帙遂多,大都凌杂无次[4]。
熟练掌握了“读书法”与“著书法”,就能于学术上“颇有发明”。此方法无论是用之于“四书”“九经”还是“诸史诸子”之书,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所得有所论。唯一让人担心的是,所得所论“难有归宿”,杂乱“无次”,难以形成系统的认知。郑氏在旷日持久的经史考证工作中,逐步认识到其所得所论难有头绪的原因,实因经史资料散乱不全,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在资料收集的基础工作上,没有余力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传易)可考者不下百人,而今所传者不过数家,可惜也。前明多谈宋易,本朝渐求汉易。如郑玄之注、虞翻之注、荀爽之注,尚可从李氏《集解》采辑成卷。周氏之说、褚氏之说、庄氏之说,尚可从孔氏《正义》摘取成帙。其余散见《释文》者,不过音读字句之异略见而已。此惠定宇、毛西河、孙渊如所以广为搜罗,一字一句,不胜宝贵也[5]。
郑氏举易学为例,指出汉易所传甚少,除了李鼎祚《周易集解》、孔颖达《周易正义》还集中保留了一些汉易资料,尚可“采辑成卷”“摘取成帙”外,他处如《经典释文》等书所存,多是“音读字句之异”,不过“一字一句”而已。原始资料是研究的基础,他因之肯定了惠栋、毛奇龄、孙星衍勤于收集资料的学术贡献。但郑献甫也意识到,收集起来的资料,有可能相互之间的见解是冲突的。不过郑氏认为不必过于担心此看似矛盾之表象,将不同的见解陈列在一起就如同众人“各自议论于前”,而读者好像淘沙者“各自搜捡于中”,反而有益于“一得之见”的灵光闪现。
夫以智者之姿生愚者之前,岂肯留其一以相予哉。然此如淘沙者然,各自搜检于中,得金固无穷也。又如聚讼者然,各自议论于前,折狱固有定也。且庸讵知今人所后得非即古人所先得,吾固不能取说经者之书而尽观之也。抑庸讵知此人所独得非又他人所同得,吾更不必取说经者之口而尽窒之也。然则偶得其一,非剽而取者,一或自是其愚矣;积得其一,纵该而存焉,一亦无补于智矣[6]。
折衷诸说而得到的所谓新见,很可能只是学者个人收集资料不全、学术见识有限的结果。其自以为的“新得”“独得”之处,既有可能是“古人所先得”,也有可能是同时代“他人所同得”的观点。而作为一个诚实的研究者,只要所得“非剽而取”就可“该而存焉”,无论从哪一点上说,自有其存在的学术价值。收集完备的资料是学术进步的必需基础,郑氏因之提出一个大胆的学术建议,主张将古今所有的经文汇集成资料通编,并且对之进行基础性的资料疏理工作,将所有文字音韵的异同之处编集标明,但不必作经说义理的进一步诠释,使之成为学者群体进行深入研究的共同基础材料。
窃谓经说之纷纭,由经文之残缺。近来考据家所得,不过秦汉人之文字,及汉唐人之注疏耳。然每知其一不知其二……又《说苑权谋篇》《列子》语、《三国志》帝纪《注》引孔融说,皆云“可与适道,未可与权”,韩李《笔解》因谓今本倒错;不知《淮南子汜论训》所引亦今本文。此不当据而据者也。……《孟子》伪《疏》于“孟季子”章末云,即下卷所谓季任,是本无“孟”字,乃恍然于宋政和五年封配享十七人所以不及此人也,此《疏》之当据者,而今之考订家皆不据也。……故愚意欲将秦汉间文字引经之有异文者,汉唐人注疏解经之有异字者,先为长笺一一标出,次取《说文》所引之别字,《释文》所出之别本,亦为长笺一一列出。……而经说之是非同异则不必辨也。苟能集门下士为之,第费目力、费手力,不费心力,可以终一年而告成,使惠定宇、翟晴江、臧玉琳辈无从再著手,而戴吉士、江艮庭辈亦无庸再置喙。后有学者,茹古涵今,号为通人,不复向此琐琐中求生活[7]。
之所以不对经说作“是非同异”的考辨,是因为郑氏认为,经说太过“纷纭”,其原因实基于“经文之残缺”。因此,首要的事不是考辨,而是以“长笺”的方式标出异文异字、别字别本,汇为一书。这只是费目力、手力不费心力的体力活,若能“集门下士”只需一年就可“告成”。此书之成必使惠栋、翟灏、臧玉琳、戴震、江藩等人无从以汉学相号召,而使后之学者可以借此资料汇编成为“通人”,再也不必在这徒费精力的“琐琐中求生活”。显然,郑献甫认为,在文字考据与义理考证之前,即辨别“是非同异”之前,当有一个更为基本的资料汇集工作,它是所有研究工作的原点。此汇编工作不单解决了资料汇集问题,更是解决汉宋之争的良药。因其可使人“知其二”,全面了解资料的真实现状,不会发生“不当据而据”“当据而不据”的证据误用情况,从而使其后的“是非同异”工作,即无论是考据还是观理,都有一个坚实的依据。郑氏虽未直接谈到由资料汇编引出的检索问题,但他对书目之学无疑是非常重视的。
藏书万卷无总编,譬如满屋堆散钱。……刘略班志阮氏录,流分派别如导川。丙丁甲乙分在目,经史子集标其颠;残篇断简亦拾取,目览手治心为研。……崇文总目有旧例,或提其要钩其元。记书记名不记卷,渔仲之论真不然。史家小录子小说,位置不定殊拘牵[8]。
他认为收集资料若无编目,就如满屋散钱,无从利用。编目之学是一种专门之学,需要“目览手治心为研”,轻视不得。编制书目应当继承传统目录学的优点,像《七略》《艺文志》等书一样分类明晰,像《崇文总目》一样钩玄提要,同时目录要详细到卷,以便于查找类似主题的相关资料。好的编目,如同筹策在手,可使繁杂的资料运于一心。通过初步整理的资料汇编,一方面可以避免由于编撰者的主观取舍而造成的资料遗失,另一方面也能客观展示资料的原始状态,便于研究者自同一研究基础上出发进行思想发明,也可使每个研究者的研究结论都能回溯到相同的源头。通过建立可信、完整而不回避客观差异的资料来源,并使其便于引用、查找,就可结合观理之法,展开有效的学术讨论,最终形成学者的一得之见。
二、文意的真
郑献甫注重资料建设,与朴学重视博学的学术传统有关。他虽强调汉宋贯通,但自认其才能更适于“参讹正误,嚼字咬文”[9]。基于此种治学兴趣,他主张士子应当阅读大量的经史子集著作,以打下“理解”出新的基础。
《十三经》即不能全熟,必须全读,否则有并其篇简而不能举者矣;《十七史》即不能尽记,必须尽览,否则有并其朝代而不能辨者矣。子书则纯者如《荀子》《扬子》《文中子》,驳者如《老子》《庄子》《韩非子》及《吕览》《淮南》《风俗通》《白虎通》《说苑》《新序》,皆须涉猎,以资学识。文则贾董枚马下至八大家,诗则韩杜苏陆上至《十九首》,必须博习,以为法式。说部则王厚斋之《困学记闻》,洪容斋之《随笔》五笔,王野客之《野客丛书》[10]。
郑氏开列的书目包括了经史子集的基本书目,除《十三经》《十七史》以外还包括经典的子书诗文甚至小说家言,涵括了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家学说。他认为这些书目,有的要“全读”“尽览”,有的要“涉猎”“博习”,以期提高自己的“学识”,领会著书作文的“法式”。更为重要的是,古人流传下来的文本,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都来源于他们的亲身经历,往往真实可信,启人深思。如果自身缺乏必要的人生阅历,仅从字面理解,就很难对书本中所蕴含的事理有真切体会。因此,“读书”之外,更需具备经过亲历得来的感受能力,才能产生对经典文本的同情理解。
夫诗不特当有才情,当有学问,并当有阅历。……有才学而无阅历,是子房之坐谈兵也,可参军而不可行军。是故《卷阿》从游,《柏梁》应制,朝廷之阅历也;青海射雕,长城饮马,边塞之阅历也;浔阳商妇,新丰老翁,身世之阅历也;元和颂德,淮西纪功,承平之阅历也;彭衙哀离,秦中讽谕,离乱之阅历也;夔府咏古,海外标奇,山水之阅历也。古人有如此之阅历,故能道如此之学问,而张如此之才情[11]。
写诗单有才情、学识,并不能打动人心,仅能抒发个人的情感,或者成为博学多识的“脚厨”。只有实经“阅历”,才可“行军”而成“真诗”。无论是《诗经》还是唐诗,其诗情之妙者,都是如此。如《卷阿》《柏梁》之诗蕴有“朝廷之阅历”,高适等人的边塞诗蕴有“边塞之阅历”,白居易的《琵琶行》《新丰折臂翁》蕴有“身世之阅历”,韩愈等人的《元和圣德诗》等蕴有“承平之阅历”,杜甫等人的《彭衙行》等诗蕴有“离乱之阅历”,李白等人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蕴有“山水之阅历”。借此政务、战争、旅行的真实阅历,才能“道如此之学问”“张如此之才情”。后世学者缺乏这样的阅历,仅凭三寸之笔,自然难以企及古人的高度。缺乏阅历支撑的模仿之作,徒具古诗之形,往往多“不可解”“不可读”。
尝谓杨刘诸人之学西昆,如吴中少年,熏衣饰面,自诩风流,沿其伪体,涂字砌句,至不可解;曾吕诸人之学西江,如河北大侠,掀髯张目,自示陡健,沿其末派,谣歌语录,至不可读。……愚以为后世自有真诗,不必拘某代;凡人各有真诗,不必问某家。凡未成室家,先立门户;未具体段,先借衣冠。后世讲学习气,非古人作诗宗旨也。……至其熔铸既久,则操持有定。随所至之地,处所历之事,抒所感之怀,不胜郁积而酌为发挥,此岂有某代某家在其意中者?惟其无某代某家在其意中也,故笔墨之间,清雄淡雅,自成气象。是殆所谓后世自有真诗,凡人各有真诗[12]。
如“西昆”“西江”类的仿古诗作,只能称之为“伪体”“末派”,仅停留在“涂字砌句”“谣歌语录”的层面上,“非古人作诗宗旨”。且因其拘于某代某家的门户之见,沾染“讲学习气”,缺乏基于阅历的内在情感,自然难以创作出打动人心的“真诗”。后世学者固然无法重建古人的阅历,但这并不重要。后世学者自可从自己的真实经历与真实情感出发,经过长时间的“溶铸”工夫,自能形成坚定的内在“操持”。“随所至之地,处所历之事,抒所感之怀”,依据其自身的阅历与情怀,超越“某代某家”之意,“酌为发挥”自家之意,也就能够“自成气象”“清雄淡雅”,从而“自有真诗”“各有真诗”。在郑氏看来,诗与文既有相通之处,亦有相异之处。诗以言志,需遵循一定的韵律格式以便于表达情感,修辞格调对于文章则不重要,文章更重视实际功用。
唐人不尽为有用之文亦不为有格之文,故其善者如韩柳元白,各自成家,其余或骈枝丽词、小说隽语,其弊也杂。宋人务为有用之文又好言有格之文,其盛时如欧苏曾王,如出一手,其余亦自取义理,不失法度,其弊也拘。总之,文不可以无用而又不可以有格也。自不学者舍奏议而言书状,舍论著而言记序,舍传志而言辞章,而文于是乎无用。又舍才情而言义法,舍气韵而言音调,舍体段而言章句,而文于是乎有格。……余持论虽严,不过谓勿作四六骈语,勿作诗赋绮语,勿作注疏琐语,勿作语录俗语,勿作案牍习语,勿作尺牍套语,如是而已耳[13]。
唐有韩柳元白、宋有欧苏曾王等擅长“有用之文”的文章大家,但唐人中有为无用之文的,其失在于杂;宋人中有为有格之文的,其失流于拘;至于缺少个性的后世“不学者”,其为无用有格之文,完全失去了取舍准则。他们都不知奏议、论著、传志所言所论之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固需借助“才情”“气韵”“体段”以增强说服的力量,但不能舍本逐末,将心思花在“义法”“音调”“章句”这些表面的修辞手法上,而为书状、记序、辞章等无用有格之文,以作“骈语”“绮语”“琐语”“俗语”“习语”“套语”炫人耳目。可见,郑氏所谓有用之文指言事、议事、记事之文,有用则指其事其理“确实”可信。
窃以为,志之体,简洁而已矣;志之用,确实而已矣。而近世操笔者不然,不知古者并讹言讹事而沿袭之则不实,不知今者取俗人俗文而杂录之则不简。……既得简括,乃求确实。愚以为唐宋以下之说部,元明以前之正史,有可据者据之,若苦于无征,而实非无稽,则当取存于公牍者为左验,勿概以相传饰其孤陋,夫而后庶几有可信耳[14]。
郑氏晚年,承担了《象州志》的编撰工作,以“简洁确实”为编志原则,主张志文须简洁,记事必确实。地方志的编写往往面临资料匮乏的窘境,因此编写者为求完备,往往将许多相传已久的“讹言讹事”收入其中,而对于同时代的史料,又囿于见识或人情,而将“俗人俗文”滥入其中。这就需要编写者既“知古”又“知今”,一方面根据学理对同时代的史料进行精简;另一方面,对于古代史料,则要验之于可信的私人著述与官方史学,对于一些没有确切证据但其事可信的,应当以“存于公牍者为左验”,不能仅以“相传”为托言,“至俗语所流传,非古籍所记录”者皆“集录以示博”[15]。只有这样,地方志所载之事,才能“庶几有可信耳”。显然,郑氏所求之真,并非仅指文本资料的现存真实状态,更指文本资料所反映的内容,无论是基于阅历的情志,还是记载的事实、推衍的事理,是否真实可信或可感。
三、义理的真
以朴学方法求真文真事有其优长,求真情真理则有所不足。对于朴学方法拙于阐发义理的不足,考据大家如戴震就已有所察觉,甚而直言“所记不如义理之养心”。戴氏之后,桐城学派倡导义理、考据、辞章不可偏废,意图进一步补偏救弊,但终究无法彻底改变清学偏于考据疏于义理的弊病。
儒之术,汉以后日益分训诂、谶纬、义疏、词章,杂然而代……义理之学,至宋而始盛,元述之,明和之,而章句流于隘陋,性命蹈于空虚,则亦不能无弊焉。姚江矫以简易,而空疏滋甚。国初诸儒,以鸿博救之,学始有汉宋之分。学者莫不舍宋而趋汉,述而和之,盛极于乾嘉,弊亦极于嘉道。贱躬行而贵口耳,弃义理而骛名物,学不切于身,用不关于家与国也。当时执牛耳之戴震东原氏,则已悔于末路,谓“所记不如义理之养心”。姚鼐、程晋芳、张海珊、刘开之徒,各著论以挽其失。顾其末流,愈泛滥不可收拾,猖狂而猝不可胜[16]。
儒学本无汉宋之分,由经学衍至义疏之学而臻义理之学,是自然而然的学术发展过程。然义理之学过重章句性命之学,以至阳明之后日益走向“空疏”。清初诸儒欲以“鸿博救之”,儒学才有了“汉宋之分”。此区分在郑氏看来,是所谓“门户之私也,非心理之公也”[17]。学者“莫不舍宋而趋汉”,不注重义理躬行而专注于名物琐碎之学,至于产生“学不切于身,用不关于家与国”的无用之文。这实际上又使用于救弊的鸿博之学,归之于另一种“空疏”之学。戴震、姚鼐等人所开药方显然没有疗效,郑氏遂提出将汉宋学术方法“贯而通之,兼而取之”,并以之决学问之是非。
夫学安得有汉宋之别哉!唐以前论著者多言人事,宋以后乃探天理……然其学问具在也。训故之能事,数百年来亦不多见;讲学之流弊,三百年来遂不可胜言。愚尝谓:“自语录出而天下无真理学,自说部出而天下无真经学,自类书出而天下无真词学。”……顾亭林不肯讲学而自求之经史,黄梨洲不讳讲学而自实以经史,学之分为二者,复合为一矣。承学者第博极群书,讲求实用,杂碎者浑而涵之使鸿博,考订者返而课之使笃实,谓之汉学可也,谓之宋学亦可也。若本原不具而名目是争……贵空言而贱实事,无驳论而有游谈,其为害于学问不更大耶。……学之有汉学宋学,犹诗之有唐调宋调,字之有唐帖晋帖耳。任胶序诸儒入主出奴自为风尚则可,以国家大体分门别户垂为功令则不可[18]。
虽然唐以前学者“多言人事”,宋以后学者“乃探天理”,但他们“学问具在”。自从学者喜“讲学”厌“训故”之后,语录、说部、类书流行,学问俱失,世遂无“真理学”“真经学”“真词学”。清初儒者顾炎武、黄宗羲皆不为讲学所惑,能够自求、自实以经史之学,使考据与观理之学“复合为一”。他们的特点均是“博极群书,讲求实用”,使“杂碎”“考订”者变为“鸿博”“笃实”者。这样的学问,无论是称之为汉学还是宋学,实无本质区别。其中关键在于求“本原”之学,贵“实事”重“驳论”,贱“空言”轻“游谈”。虽然从学者自身材性考虑,选择汉宋任一学术风尚均可理解,但从国家层面以功令形式表现出对某一学风的偏好,则有害于学术的进步。世上学问如同流水,虽有不同的流派,但最终所追求的都是同一义理。因此,涉及学术争论时,不可固守门户之见,盲从权威说法,任意发表个人意见,应当兼取并收,直探学问本原。
王荆公议《孔子世家》谓:“孔子,旅人也。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以迁为自乱其例,不知此正迁之特创其例也。设如荆公言,将置之老韩之次乎?抑置之孟荀之前乎?好议论而不讨论,其弊每至此[19]。
王安石研究《史记》中的纪传体例时,认为司马迁将孔子系之世家,是“自乱其例”。郑献甫则认为王安石的“议论”没有考虑到孔子的特殊地位。将孔子系于何种体例,不能简单套用一般的学派及爵位差异来安排其文本序次。司马迁充分考虑到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至高地位,系孔子于世家是其针对孔子的特殊性而“特创其例”。郑氏从此论例推出一普遍化结论,即任何一个人提出新的观点时,都需充分“讨论”事实的细节,才能得出合乎义理的结论,“讨论”方法是义理判断真实可靠的最终保证,而讨论的关节在于“平心”分析。
郑康成注《礼》云:“水神则信,土神则知。”(《中庸》首章)何妥注《易》,亦以利物配义,贞固配信。(《集解》)故孔氏《正义》云:“元则仁也,亨则礼也,利则义也,贞则信也。不论知者,行此四事,并须资于知也。”此为古今定解。自班固《白虎通义》以信属土,谓“分旺于四时”,厥后理学诸儒皆以土配信,谓“并资于四德”。于是天下事,论诚伪不论是非,而仁非仁,义非义,礼非礼,信非信,至于不可复究。试平心读“贞固足以干事”之说,果当属知乎?抑当属信乎?何必强圣言以就己意也[20]。
五行配五德是中国传统易学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其中土的相配之法有配知配信两种讲法。郑玄以土配知,班固以土配信。何妥以“贞固配信”,贞为冬,冬为五行之水,故何氏实是以水配信。孔颖达谓“贞则信”,则亦以水配信,孔氏又言知资四德,而土旺四季,则孔氏明以知配土。何妥、孔颖达显然遵从郑玄以土配知的看法,郑献甫将此视作“古今定解”。或因班固之说更为早出,理学诸儒多信从其以土配信的说法,因之而形成信资四德的观念。在郑氏看来,以信资四德,做事就会只讲诚伪不论是非,从而造成“仁非仁,义非义,礼非礼,信非信”的有害后果。经此归谬式的义理讨论,郑氏认为信资四德观是“强圣意以就己意”的个人意见。若“平心读”,将语源法与归谬法结合起来进行义理讨论,就会支持知资四德的主张。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平心讨论,郑氏注意到语言表达不清会造成义理混淆的语言现象,例如:
记言:“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客有曰:“诈近知,怒近勇,贪岂近仁耶?”予曰:“仁者断不至贪,而贪者则必托之于仁。”[21]
孔子在《礼运篇》中提出“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的观点,惑者认为将知诈、勇怒对称易于理解,但将贪仁对称,则令人疑惑,两者似无显然之关联。郑氏敏锐地意识到,孔子的知诈、勇怒、仁贪对称,是知者诈者、勇者怒者、仁者贪者的对称,非知性诈性、勇性怒性、仁性贪性的对称。如果一个人是仁者,则必定不至于贪,但一个贪者,则必假托于仁义之名以行其贪,将其与真正的仁行混淆起来,使别人不得不区分真正的仁行与虚假的仁行。因此,所谓去其贪,不是指去除一个真正的仁者的贪性,而是去除一个假托于仁义之名的贪者。通过平心讨论,郑氏指出惑者将主体属性与概念属性相混淆的思想误区。上述讨论过程表明,郑献甫或已意识到,有些义理问题的产生实由语言的表达差异而非语言的意义差异引起。
四、人格的真
郑献甫反对将学说义理与学者人格混为一谈,同时他也意识到人格的真与资料的真、文意的真、义理的真之间具有本质关联。没有人格的真作保证,资料的真、文意的真、义理的真可能都无法实现。而能否保证资料的真、文意的真与义理的真,与学者是否“志在实学”有莫大之关系。如果学者处理不好“实学”与“虚名”的关系,不能先定其志,从而“尽吾学以顺吾命”,就免不了“诱于势利”,追求“速成”,而终身“自困于剽窃、摹仿、因袭中,不复得出”[22],从而无法达到人格、文格的自立。
文判于所学,尤判于所志。志在实学者必恐以揣摩陋其意,志在虚名者必恐以服古妨其功。两者常互讥而未已。殊不知富贵功名关乎命者也,言行文章由于学者也。尽吾学以顺吾命,倘其得则两得也;荒吾学以倖吾命,倘其失则两失也。学者此志不先定,则诱于势利,惊于速成,终身不能自立。文征其学,亦征其品,读方孟旋文知其为孝子,读左萝石文知其为忠臣,读赵侪鹤文知其有风节,读汤若士文知其有风流。故文者,挟吾之性术、精神、气度而出之者也。文中无实际是为浮,中无真际是为伪。彼言与行乖,文与人左者,非特其人不佳,即其文亦不佳,第不得有具眼者为之鉴耳[23]。
文之品格既与作者的学问工夫密切相关,更与作者的精神品格密不可分。文章中蕴含着作者的“性术、精神、气度”,是作者人品的外现。依郑氏之见,读了方应祥的文章就能知道他是一个“孝子”,读了左懋第的文章就能知道他是一个“忠臣”,读了赵南星的文章就能知道他是一个有“风节”的君子,读了汤显祖的文章就能知道他是一个“风流”绝世的人物。作者的人品不真诚,“言与行乖,文与人左”,其文品也就达不到“实际”“真际”的境界而流入“浮”“伪”之途。只不过,人品与文品的正相关性,需要“具眼者”方能鉴别。
一代之世运,与一代之人才合,而成一代文体。如天之有日月风云,地之有江河山岳,体象不同而精彩皆同,故愈久而愈新。若具一孔之见,勒一途之归,则下笔皆陈陈相因而已耳。恶睹所谓“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耶[24]?
或见而哂曰:“古人有诗话,古人亦有文话,经义之体,词人不道,何亦琐琐及此?”曰:“八比文,义理本于注疏,体势仿于律赋,榘度同于古文,体本不卑,作者自卑耳。”[25]
正因为决定文品高低的是人品,所以随着“世运”“人才”的不同而变化的文体,相互之间只是“体象不同”。时间愈久,文体愈多样。不世出之人才,无论使用哪一种文体,都能创作出“精彩”有品的文章。若能利用新文体创作“精彩”的文章,更能体现“愈久而愈新”的文章品格。反之,如果作者囿于“一孔之见”与“一途之归”,眼界狭窄,见识浅陋,下笔作文“陈陈相因”,无法做到“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就会怪罪文体,文章自无“精彩”可言。一般说来,“词人”的“诗话”“文话”,多不言“经义之体”,认为八股文体难以写出“精彩”的文章。但郑氏以为,八股文体并无什么不妥,其修辞手法源于诗词歌赋,义理发挥源于经史注疏,文法又同于古文,至明代达到高峰,也有很多“精彩”的文章出来。因此,八股文“体本不卑”。贬低八股文无品,实是“作者自卑”,故意将文体作为写不出精彩文章的托词。另外一方面,若涉及传记文,则传主的人品与文品亦呈正相关态势。
昔人皆谓人藉天下之奇文以传,余则谓文藉天下之奇人以传。……且夫文也者,性情之清奇,学问之深博,才气之激昂,郁于其中而溢于其外耳。然苟无所藉则韬光敛采,泠然以虚。及得所藉以及发挥,又视所藉之高卑,以极其体势之所至,而浅深判焉,奇平别焉。设以记委巷之常流,颂当途之庸宦,必至于平沓、雷同、枯寂而不振;遂增饰其词则谀而已矣,曼衍其说则夸而已矣,附会其议则诬而已矣……此文所以流于卑陋而不可救也[26]。
文章的“精彩”,是作者“郁于其中”的“清奇性情、深博学问,激昂才气”“溢于其外”的自然表现。即便如此,如果作文“无所藉”,文章“光采”也无由显现。文章“光采”的“深浅”“奇平”,实际上由传主人品的“高卑”而定,文之“体势”只是助其将精彩“发挥”至极而已。如若传主人格平庸无奇,所有的修辞技艺都会流于表面。要么文风平沓、雷同、枯寂,要么“增饰其词”以谀之,“曼衍其说”以夸之,“附会其议”以诬之,而使文章“流于卑陋而不可救”。传记文品的高低与传主人品的高低呈正相关态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传主的选择与认可,实与作者的见识高低相关,如郑氏对《象州志》传记编排体例的安排,即受其识见左右。
旧志……过分名目,反多挂漏。……人物不必皆有科名,纪载亦不必强立定名,但有可书者即缀数语,无庸书者即不烦故撰一言。盖其荣辱不在此,有势者或谬为请属,无识者或妄为徇美,皆可以已矣[27]。
在郑氏看来,“无识”者易于受外在名目的拘缚,不懂得根据人物本身的事迹与人格特征决定是否立传。往往“强立定名”,事先拟定框架来凑足体例,使那些根本不符合立传品格的人物得以厕身其间,滥竽充数。因此,有识者只应考虑入传人物的事迹人格,“可书者即缀数语,无庸书者”连一句话也不能写。至于可书不可书的取舍标准,既不在权势,亦不在男女性别,“妇女可纪者亦为连书”[28]。他所说的“可纪”,既包括传统道德所表彰的烈妇,也包括一些殊有别格异品的才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男尊女卑观的束缚。
五、复数的真
郑献甫“好读书”,35岁考中进士后“早捐俗学”,长期“从事古学”,读书颇为用心细致,“经史各本钩考订正,多余手批;子史各本朱墨丹黄,亦余手点”[29]。郑氏读书于经史子集、汉学宋学,皆下苦功,然其学有得,实因贯穿其中有一求实精神在。
故必博考注本,旁及说部,于其中疑难错综同异处,尤尽心焉。则证据确而文学日工,训诂明而字学日进,虽三而分,实一以贯矣。然此当勉求其实,不可强好其名[30]。
桐城派倡导义理、考据、词章合一,但因其主张道统文统,郑氏批评其“不惟于体太拘,而于事亦太陋”[31]。基于此,他主张以一贯之实学治经史诗文诸门学问,逐步触及“资料的真”“文意的真”“义理的真”“人格的真”等“真”的多重义涵。这些义涵也可表述成文本资料的真确性,文本内容的真实性,文本义理的真理性,文本作者的真诚性。所谓文本资料的真确性,指包含所有异字异音的文本的矛盾现状。所谓文本内容的真实性,指文本呈现的阅历情感、事情事理的真实可感或可信。所谓文本义理的真理性,指通过贯通考据法与观理法的平心讨论方法,厘清因语言表达不清造成的语义混淆现象,明确命题、概念的真实内涵。所谓文本作者的真诚性,指作者人品与文品呈正相关性,就传记作品而言,无论是选择传主人品,还是呈现精彩文品,均依赖于作者的诚实人品。显然,就“真”的多重义涵而言,可将郑献甫在治学经验中所触及的“真”,视为一种“复数的真”①关于复数概念,可参汉娜·阿伦特、熊十力、克里斯蒂娃的相关主张(熊十力《乾坤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147页)。,虽然郑献甫本人并无这样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须指出,“复数的真”中的“复数”,并非意指一个混沌的整体,而是基于明晰个体或确定义项构成的“复数”,蒋琦龄说:“(郑献甫)贯综六经诸子百家,于经义、史论、古文、诗词、四六骈体皆精之。其文于事物必钩述源委,见于何书,一一疏证之,虽至近至微不漏,其讨论条达委备,无艰苦雕刻之态。”[32]
郑氏将其对于“真”的追求,贯穿于“经义、史论、古文、诗词、四六骈体”之中,对事物源委,虽“至近至微”也无遗漏,其讨论“条达委备”。在笔者看来,郑氏触及的“真”的多重义涵是有其内在逻辑的“贯综”,可将其对真的语簇用法归纳成“真()”的悬置表达式。郑氏在描述其经史诗文之学时,使用了“真诗”“真际”“真理学”“真经学”“真词学”等诸多表达。也就是说,“()”中可填充进“诗、际、理、经、词”等不同的名词术语,填充的方式则是“自熹”“自有”“自成”“自求”“自实”“自立”等自觉性的语言填充活动,包括“读书”“阅历”“讨论”“具眼”等具体的语言操作方式。在此语言填充过程中,主体不断推扩自身的语言生活边界,对“真”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多的名词术语也就被填充进去。因其有“归宿”,而统一于“真”名之下,也因其有“发明”,而扩充于“()”之中。所以笔者判定,“真()”表达式不是一种语义分析方式,而是儒者“致良言”的意义生长方式。在此语言填充生活不断丰富的过程中,语言意义不断生成,“愈久愈新”,最终使儒者成长为“通人”,能够说出“复数真”之良言。如若认识到这一层,则无论是从郑献甫学术贡献的表层意义,还是从其蕴含的深层学术史意义而言,后之学者都需要平心而论,去其层层遮蔽,以还其在岭南学术史甚或中国学术史上的恰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