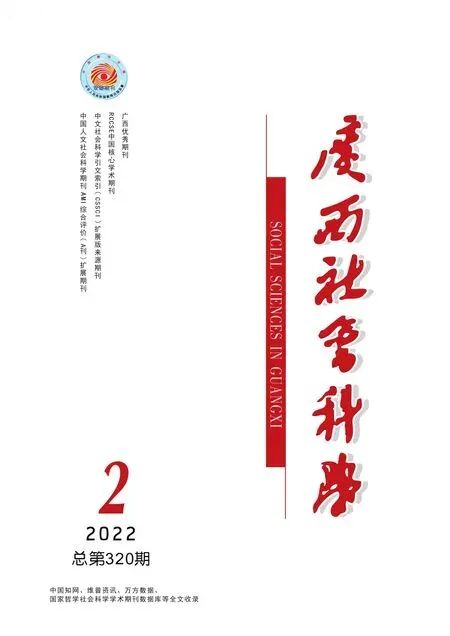中国—东盟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犯罪问题研究
蓝彩箫
(1.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2.广西警察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鲜明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关于恐怖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反恐是各国共同义务,既要治标,更要治本”[1]。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亚洲安全观的构建上,指出中国和东盟各国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2],强调中国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采取零容忍态度。中国和东盟各国应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一、中国—东盟区域内恐怖主义犯罪及反恐合作现状分析
从全球范围来看,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0》的数据显示,与2014年的峰值(33438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相比,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总数下降15%至13826人[3]。自从新冠病毒被宣布为全球大流行以来,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初步数据表明恐怖事故和死亡人数均呈下降趋势。然而,新冠病毒可能会带来新的、独特的反恐挑战,特别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导致的财政赤字可能会使反恐预算被削减。虽然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呈下降趋势,但恐怖主义可以说仍然是全球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
(一)中国与东盟区域内恐怖主义犯罪态势分析
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数据显示,以“9.11恐怖袭击事件”爆发的时间点为界线,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前,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中国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通过制造爆炸、暗杀、袭击警察和政府机关、实施投毒和纵火、建立秘密训练基地、筹集和制造武器弹药的方式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4]。“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东盟区域内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数量迅速上升,恐怖主义威胁加重。虽然“基地”组织遭到美军打击,但是“基地”组织的思想和成员开始向东南亚各国蔓延。东南亚各国的恐怖组织活动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2015年,时任马来西亚内政部长阿末扎希透露,从2012年至2015年初,至少有100多名马来西亚公民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以下简称“伊黎伊斯兰国”),这还不包括警方在2014年逮捕的46名犯罪未遂者。根据印度尼西亚国家反恐局的估计,2012—2014年间,有200多名印度尼西亚公民前往中东加入“伊黎伊斯兰国”[5]。恐怖主义分子往往通过毒气、自杀性人体炸弹、劫持飞机人质、散布放射性物质等危险手段发动恐怖活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恐怖主义分子开始攻击电脑程序和信息系统,利用网络散布或组织恐怖活动。此外,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剧了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对国际反恐形势提出了新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会让恐怖组织趁机巩固他们的领地,扩大他们的运营,有机会成为“替代服务提供商”,通过提供基本服务或社会关心而赢得当地人的青睐。历史告诫我们,经济灾难、社会两极分化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为暴力极端分子提供了大量犯罪机会,对公共安全和社会凝聚力造成不利影响。严峻的反恐形势要求中国与东盟加强反恐合作,共同打击区域内的恐怖主义势力。
(二)中国—东盟各国对恐怖主义犯罪现行的法律规制概述
我国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主要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对恐怖主义的界定,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同时,该法亦对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以及恐怖事件进行了罗列和阐释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恐怖活动,是指恐怖主义性质的下列行为:(一)组织、策划、准备实施、实施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活动的;(二)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或者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的物品,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戴宣扬恐怖主义的服饰、标志的;(三)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四)为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提供信息、资金、物资、劳务、技术、场所等支持、协助、便利的;(五)其他恐怖活动。本法所称恐怖活动组织,是指三人以上为实施恐怖活动而组成的犯罪组织。本法所称恐怖活动人员,是指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和恐怖活动组织的成员。本法所称恐怖事件,是指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关于东盟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规制,从2007年签署的《东盟反恐公约》来看,东盟对恐怖主义并没有下一个明确的概念,而是采取罗列的方式列举了恐怖主义的形式,这跟联合国大会的方式有点相似。《东盟反恐公约》界定的恐怖主义犯罪主要包括恐怖主义爆炸罪、劫持航空器罪、劫持人质罪、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罪、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罪、资助恐怖主义罪、侵害应受保护国际人员罪、核材料犯罪、危害大陆架上固定平台罪等9种犯罪。可见,该公约对于恐怖主义的犯罪所涵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在此合作框架下,东盟各成员国结合本国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的实际情况和反恐的需求,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了相应的规定。
面对严峻的恐怖主义形势,东盟各成员国不断修订反恐的法律。比如马来西亚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最高决策机构,其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为“不论目的是客观的或者正当的,个人、团体或者国家非法使用威胁、武力、恐怖或者其他手段攻击国家、公民及其财产、关键设施,目的是要制造恐惧、恐吓,迫使政府或者组织满足其目的行为,还包括直接或者间接的支持行为”[6]。2015年4月,马来西亚国会通过《防范恐怖主义法案》,据此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独立的防范恐怖主义局,负责扣留涉恐嫌疑人,并且有权在无须审讯的情况下,将嫌犯扣留长达2年的时间。2018年5月,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市曾经发生多起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人们认为2003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过于薄弱,无法有效打击和挫败恐怖主义活动,因此在该事件发生的两个星期后印度尼西亚议会不得不对该法进行修订。旧法规定在恐怖主义行为实施之前,执法人员只能在恐怖分子嫌疑人实施其行为后逮捕他们。修订后的法律将允许执法人员提前更长时间拘留嫌疑人,并起诉那些加入或招募激进组织的人。修订后的法律还扩大了“恐怖主义”的定义。“恐怖主义是指以意识形态、政治或治安混乱为动机,造成恐怖气氛或广泛恐惧的暴力或威胁行为,可导致大规模伤亡和(或)对战略重要目标、环境、公共设施或国际设施造成损害或破坏”[7],跟马来西亚一样,印度尼西亚新修订的反恐法对于涉恐嫌疑人的拘留期限进行了加倍的延长,将拘留期限延长至14天(无须任何指控)和200天(正式指控),执法人员现在将拥有更大的权力。新法律还在新的恐怖主义定义中加入“安全混乱”一词,为军事介入铺平了道路。修订后的法律通过之际,印度尼西亚军队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也同时成立,该司令部将负责军方参与印度尼西亚反恐战争的各项事宜。新法律还包括许多关于预防恐怖主义措施的规定,包括起诉返回印度尼西亚的“伊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法律依据。泰国法律也有许多反恐方面的规定,依据泰国刑法典第135/1至135/4条,恐怖主义被定义为通过暴力威胁人身自由、造成生命危险、损害公共环境与设施(如公共交通工具、电信系统、公共设备等)、损害任何个人资产、影响社会发展等,以达到自己期望目的的行为。其中,威迫泰国政府、国外政府、联合国办事机关,造成国家或国际严重损害的行为默认为恐怖主义罪[8]。虽然各国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反恐已纳入各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东盟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并且认知与国际社会逐渐趋于一致的过程。中国和东盟各国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力度日趋加大,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
(三)中国与东盟各国反恐合作状况分析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经济领域展开合作,20世纪90年代末成为对话伙伴,前期的经济合作为双方开展反恐合作奠定了基础。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加快建立反恐合作的事件发生于1993年5月,正在柬埔寨执行任务的中国维和官兵大本营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多枚火箭弹袭击,两名工程兵大队战士当场牺牲[9]。这使得我国意识到有必要采取切实的合作来共同对抗和打击具有国际性质的恐怖主义行为。但这一时期东盟成员国内发生的恐怖犯罪活动较少(见表1),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反恐合作未曾形成书面形式的合作框架和协议。可以说,双方在反恐合作方面尚处于萌芽时期。

表1 东盟成员国内恐怖犯罪活动状况(1968—2005年)
2011年的“10·5”湄公河大案是中国与东盟反恐警务合作历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发展到现在,随着恐怖主义事件的增多,中国与东盟的反恐合作逐渐增多,并开始走向务实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也由最初的萌芽期到起步期进而到发展期。目前中国与东盟反恐合作主要依托的合作框架包括《反对恐怖主义联合行动宣言》《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联合声明》《关于加强东盟与中日韩首都警察局合作的北京宣言》《东盟反恐公约》《中老缅泰关于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等,警务合作主要依托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以及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这两大合作机制。此外,双方合作的形式多样化,包括开展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不断深化合作交流的成效。例如,2020年9月,第三届中国—东盟地区安全与反恐国际研讨会召开,以马来西亚为主题国,中马两国在反恐合作方面进一步达成共识,认为两国在反恐合作方面应超越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族裔的差异化认同,切实加强去极端化、反恐对话与合作,以期更加精准、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难题。应该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结合成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行为上更加深入,也取得一定的成效。
从《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0》来看,自2002年以来,亚太地区因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仅占全球总数的3%,共7350人[10]。虽然东南亚的一些区域经历了间歇性的恐怖活动,比如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受到恐怖主义的影响,除了缅甸,这些国家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lobal Terrorism Index,简称GTI)①GTI是一项综合研究,分析恐怖主义对163个国家的影响,覆盖世界人口的99.7%,GTI的数据主要基于当今最权威的恐怖主义数据来源的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GTD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包含170000起恐怖事件的系统和全面编码的数据,在此基础上,GTD与全球和平指数专家小组协商制定提供一个综合分数,以便对各国进行GTI综合研究,按照从0到10的分值对每个国家/地区进行评分并排序;其中0表示没有来自恐怖主义的影响,10表示恐怖主义的最高可衡量影响。国家按降序排列,各国中GTI得分最差的国家排在首位。都有所提高。中国在2019年取得了最大的进步,其次是老挝、马来西亚和越南。老挝是该区域仅有的4个减少的国家之一,其恐怖主义的影响低于2002年的水平(见表2)。

表2 部分国家GTI得分、排名和分数变化(2002—2019年)[11]
二、中国—东盟区域内恐怖主义犯罪特点
2019年恐怖主义造成全球经济的损失为264亿美元,与2014年的峰值1160亿美元相比,经济损失减少了77%[12]。尽管恐怖主义的总体危害在下降,但新的威胁不断涌现。从近几年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TI)来看,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大的区域已从中东地区向东南亚区域发生转移。东南亚的恐怖主义活动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一直延伸到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已逐渐形成一个“恐怖新月地带”。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恐怖活动犯罪正经历着升级转型,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恐怖活动犯罪正在增多,犯罪手段的智能化和隐蔽特征更加明显。中国与东盟区域内的恐怖活动犯罪呈现出如下特性。
(一)动机上表现出极端化
绝大多数恐怖活动犯罪的行为人都受到极端宗教主义、极端恐怖主义、极端分裂主义等思想的侵蚀,思想扭曲,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判断。在极端化动机的支配下,恐怖分子已经丧失作为人的基本的怜悯心和正义感,漠视他人甚至自己的生命,而采取自杀式爆炸的恐怖主义袭击方式。以菲律宾为例,“伊黎伊斯兰国”是菲律宾第二致命的恐怖组织,在2019年的4次恐怖袭击中造成26人死亡。自从2016年在菲律宾发展以来,“伊黎伊斯兰国”团体和它的附属团体在菲律宾进行了4次自杀式爆炸,造成44人死亡。其相比其他活跃在菲律宾的伊斯兰恐怖团体更致命,每次攻击平均造成3.4人死亡[13]。其所采取的恐怖袭击武器如生化武器、枪支、燃烧弹、放射性武器等及袭击方式如破坏设备、爆炸等,呈现出极端化的特性。
(二)地域上表现出扩散化
近年来,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犯罪组织以及恐怖分子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联系更加密切,与境外犯罪组织的勾结更加频繁,因此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在地域上表现出扩散化的趋势。从成因来看,中国—东盟区域内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与宗教极端主义有关。儒家、道家等思想及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在这片土地上相互碰撞和融合,多民族的区域交往势必会涉及复杂的风俗习惯的同异性问题。虽然激进的“圣战”恐怖主义是过去20年来最常见的宗教恐怖主义形式,但激进的基督教团体、激进的锡克教派别和印度教极端分子等也曾发动过恐怖袭击。
(三)侵害对象上表现出无差别化
从已经发生的恐怖组织活动情况来看,侵害对象不再是单一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延伸到普通民众,甚至出现单纯的针对普通民众实施的暴力恐怖活动行为。这种无差别化是一种彻底的无差别化,从政治属性、民族属性、人身属性等方面来看,都不存在任何的区别。例如在菲律宾,菲律宾的第三致命的恐怖组织是阿布萨耶夫组织(Abu Sayyaf Group,简称ASG),2019年造成21人死亡。从2018年到2019年,归因于该组织的死亡人数增加的比例为62%。2019年,大多数死亡归因于ASG的事件是针对平民、警察和军人的武装袭击人员造成的。尽管恐怖分子总体上减少了暴力侵害警察、军事和政府目标,2019年对平民的攻击却增加了17%[14]。由此可见,恐怖组织侵袭对象是无差别的,每个普通人,不分政治信仰、民族、性别、年龄,都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
(四)手段上表现出多样性
恐怖主义犯罪已不仅仅是传统的绑架、杀人、纵火、劫持人质等,还出现了大量新型的犯罪手段,如驾车冲撞、劫机、制造爆炸装置、自杀式袭击、网络恐怖活动等。尤其是网络恐怖主义开始盛行。网络具有虚拟性、犯罪成本低等特征,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因此,许多恐怖组织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来发动实施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其所产生和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恐怖活动行为呈上升的趋势。而且,在不同阶段由于互联网所展现的特质不同,网络恐怖主义活动的形式也随之变化,从网络恐怖活动宣传、网络煽动宣传向网络训练指导、网络恐怖攻击行为演变。恐怖组织经常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其政治议程,引诱个人参与其活动。
(五)犯罪主体表现出多元化
所谓犯罪主体表现出多元化,即恐怖分子背景层次多样化。以往恐怖活动主体多为成年男性,而现在出现了多元化发展趋势,不同性别、职业、年龄、民族、生活状况的个体都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分子,如未成年人和女性越来越多,这使恐怖犯罪活动的预防面临更大的挑战。据马来西亚警方透露,“伊黎伊斯兰国”组织透过社交媒体散播其“圣战”信息并招收新成员,最容易受影响者是青年。同时,恐怖组织数量众多,每个恐怖组织所呈现或者所培养的恐怖分子的方向不同,也使得所招募的恐怖分子对象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各恐怖组织都有其一套实施恐怖行为的策略,这使得恐怖事件极其复杂而多变。因此,面对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力量,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只有这样,才能将恐怖活动的危害和破坏性降到最低,才能够维护社会的和平稳定。
三、中国—东盟对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协调,建立全球反恐统一战线,为各国人民撑起安全伞”;“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问题都同地缘冲突密切相关,化解冲突是根本之策”[15]。联合国安理会2017年12月通过的2395(2017)号决议指出,“仅凭军事力量、执法措施和情报行动无法打败恐怖主义”,需要“认识到民间社会,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的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学术界、智囊团、媒体、青年、妇女以及文化、教育和宗教领袖,在提高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识及更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方面的重要性”[16]。为此,中国—东盟在恐怖主义犯罪防控中应增进政治互信,完善反恐合作法律基础,不断拓宽反恐途径,以维护共同的安全和稳定。
(一)增进政治互信,进一步凝聚中国—东盟反恐合作共识
恐怖主义跟病毒一样不分国界,对所有国家都造成威胁,只有通过各国共同努力才能打败恐怖主义。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主力军仍然是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东盟开展合作以来,双方在反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各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制约,美国强权政治的干涉主导,南海主权问题等因素的影响,在政治利益的博弈中,各方在合作过程中难免会存在摩擦磕碰,这就需要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不断交流和合作中进行磨合,在尊重对方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合作增进互信。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发展已紧紧联结在一起。近30年来,中国—东盟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从1991年的不足8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6846亿美元,扩大了80余倍。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东盟首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的前10个月,中国—东盟贸易额已达7033亿美元,同比增长30%[17]。中国—东盟双向投资合作蓬勃发展,双方互为重要外资来源地,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经济融合日益加深,释放出蓬勃生机。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内已取消7000种产品关税,90%以上的商品实现零关税,给区域经济注入强大活力。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往来开放畅通、共同抗疫通力合作等,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经济、贸易、文化上交流互通,在反恐合作中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建立起平等和信任的关系,进一步凝聚反恐合作各方的共识,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二)完善反恐合作法律基础,打造中国—东盟反恐警务合作机制
中国与东盟反恐警务合作已有的法律基础主要包括双方签署的一系列反恐合作宣言、协议以及相关的反恐合作条约,内容较为零散,尚未形成完备的反恐合作法律机制,在恐怖主义犯罪人员的遣返、引渡以及刑事司法协助等方面的规定需进一步加强完善,且相关法律基础的制定应经过双方充分协商,确保已制定的法律基础能确实执行为前提。为此,应剖析深挖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有针对性地巩固中国—东盟反恐合作法律基础,从而保障反恐合作的持续长久性。
1. 掌握恐怖组织犯罪的行为方式,阻断恐怖组织招募。为了更好地打击恐怖主义,必须了解恐怖组织现有和潜在成员的动机,以及这些组织使用的招募、资金筹集、动力等机制。就招募机制而言,支撑恐怖组织运作的因素联结点主要包括:招募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网络密度—网络影响—同情者的支持—招募恐怖分子;就资金筹集机制而言,支撑恐怖组织运作的因素联结点主要包括:攻击的影响—网络影响—同情者的支持—财力和物力—攻击的影响;就动力机制而言,支撑恐怖组织运作的因素联结点主要包括:攻击的影响—网络影响—对国家的负面看法—招募恐怖分子。可见,支撑恐怖组织运作的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形成反馈回路,各机制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节点,其中同情者的支持是招募和资金筹集的联结点,攻击的影响是资金筹集和动力机制的联结点,而招募、资金筹集、动力这三大机制之间的联结点在于网络的影响。
政治信息和社会信息既是网络的目标,也是网络运行机制中的一环。这是所有恐怖组织招募、资金筹集、动机反馈回路的一部分,它对恐怖组织的运行至关重要,这与大多数根深蒂固的恐怖组织最终参与政治进程的事实是一致的。恐怖组织是否会以这种方式结束,取决于其总体目标和组织规模。另外两个因素也非常重要:招募恐怖分子和攻击的影响。招募恐怖分子被定义为个人愿意从事恐怖活动。攻击的影响是指社会和经济损失以及在攻击中死伤的人数。各联结点的存在使恐怖组织得以运作和壮大,而突破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结点是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充分扰乱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结点可以导致它的终结。因此,执法部门对社交媒体信息的监测对于查明关键账户和正在访问这些材料、寻求招募其他人或表示希望向它们提供财政或物质援助的个人至关重要。可通过充分掌握恐怖组织犯罪的行为方式,有针对性地建构反恐合作法律机制,打造中国—东盟反恐警务合作机制,从源头上阻断恐怖组织招募。
2. 完善情报交流机制,打造信息共享平台。情报信息是反恐合作的重要内容,是打击恐怖组织的有效途径,“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是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警务合作理念。“分享信息情报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资源”[18]。我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国际警务合作中,应充分认识情报信息分享(information sharing)的重要性并重视其在数字化信息时代对打击跨国犯罪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和东盟各国都需要加大对情报信息的搜集、研判力度,同时拓宽情报信息的分享渠道。以往的各种合作机制、论坛、各检察长会议虽然都签署了相关的文件和备忘录,但是这些更多的是框架性的信息,要想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我国与东盟的反恐警务合作有必要建立一个情报信息搜集和共享的平台,拓宽分享情报信息的途径,加强双边合作,形成打击合力,掌握工作主动权,以让涉恐分子无处可逃。通过不断完善反恐情报合作化机制,加强反恐情报沟通交流,进一步加强警务合作,建立打击跨国反恐犯罪的联动机制。除了常规的情报沟通交流之外,各国还应建立情报收集站,及时交流涉恐犯罪的动向,做好涉恐犯罪预防的前期工作,促进跨国反恐案件的侦破。
3. 构建网络反恐合作机制,打击网络恐怖主义传播。综合国内外反恐工作研究分析表明,恐怖组织为扩大势力,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影响力,就会想尽各种办法与原本没有任何联系的恐怖势力取得联系,进行合作交流,绝大多数恐怖组织都建立有自己的国际互联网站,利用网站与其他恐怖势力取得联系,并不断更改其网络名称。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也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恐怖行为,特别是极右极端分子发生了更广泛的转变,即越来越多地出现组织后范式,在网上与极端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联系可能与传统的“实地”团体结构的联系一样重要,从而激发暴力。全球伊斯兰运动和极右翼运动日益分散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兴的网络极端主义生态系统实现的。仅仅从“恐怖组织”的角度来分析暴力极端主义的挑战,是一个过于狭隘的框架。相反,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TI)所显示的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得到极端分子动员的证实,表明我们有必要了解暴力极端主义迅速变化的表现形式和组织原则。这意味着不仅要审视正式的恐怖主义团体,还要审视这些威胁日益产生的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意识形态结构和网上的亚文化。
因此,我国应当积极与东盟各国就打击网络恐怖主义进行交流,共同构建起预防、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合作机制。通过加大对互联网的监控来寻找发现恐怖组织网络活动踪迹。恐怖组织只要在互联网上活动总会留下踪迹,我们就可以通过网络监控寻找其IP地址,确定服务位置。一旦发现恐怖组织的网络活动踪迹,应及时报告,以便果断采取措施,防止恐怖活动的发生,为侦查工作获取相关证据。
(三)拓宽反恐途径,增强中国—东盟反恐合作实效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结合成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行为上更加深入,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多元民族、宗教、文化的存在以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反恐机制需开展多种合作渠道,不断拓宽反恐合作的途径。
1. 加强边境管控合作,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开展反恐工作。我国与东盟部分成员国之间有着绵长的陆上边境线,尤其是我国的广西、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山水相连,特殊的地理位置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有效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离不开对边境安全的维护,中国和东盟可对边境的各种便道、界河、口岸出入口进行精心梳理,结合大数据运用系统的数据研制管控边境的电子地图,并部署边境的基础信息系统,推进边境地区联合巡逻执法机制建设。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专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反恐处突案件侦查和侦破工作的作用日益显著,如警用无人机集察、打、管、控、救、通、传等功能于一体,在遇到边境地区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时可通过全方位、大范围的观察实时空中监控,针对恐怖分子的武器、劫持的人质数量、正在进行的活动等进行拍照录音甚至录像,多方面搜集恐怖分子的相关情报信息,多方面固定有关重要的证据。尤其对于地理环境险恶的边境地区,可以充分发挥无人机侦察地形的功能,投入技术装备代替人力巡逻,建立智能化边境管理系统,合力打击涉恐偷渡或者非法入境行为。
2. 充分发挥中国与东盟国家各公安院校和各东盟研究所的作用,助力反恐向纵深发展,为反恐合作提供智库功能。例如,2016年,由中国公安部主办,云南警官学院承办的首次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警察院校长论坛暨执法能力建设圆桌会议在昆明举行,会议指出,随着反恐、禁毒等问题凸显,国际执法合作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可通过成立中国东盟执法培训执行委员会,促进警察院校间交流等措施,进一步做好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执法能力建设的培训规划。2018年,首届中国—东盟地区安全与反恐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学者剖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形势与共同肩负起的反恐任务。2019年,第二届中国—东盟地区安全与反恐国际研讨会在南宁举办,此次国际研讨会以菲律宾为主题国,聚焦菲律宾恐怖主义形势发展、成因及其特征,重点分析中菲在地区恐怖主义问题治理方面的合作路径。2020年,第三届中国—东盟地区安全与反恐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包括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在内的区域内各国与国际社会应在反恐合作方面超越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族裔的差异化认同,切实加强去极端化、反恐对话与合作,以期更加精准、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难题。2020年,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印度尼西亚研究所就印度尼西亚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维兰托万丹遭到激进分子袭击事件进行了剖析,指出:反恐合作是中印(尼)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可以在两国之间以及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框架内推动完善反恐合作机制,可以在情报收集、反恐演练、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跨国串联、去激进的经验共享等反恐能力建设方面加强合作[19]。这些会议的精神为国家制定和实施反恐合作计划提供了智力支持,随着研讨会举办次数的增加,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反恐合作上的交流日益密切。
3. 积极借鉴国际反恐组织的有益做法。典型的是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综合性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主导国际反恐事务的合法性是其最大优势。冷战结束尤其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尽管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扰,联合国仍然在反恐领域深耕厚植,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此外,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与东盟国家的反恐合作做法也有可借鉴之处。中国与东盟在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上,可以充分借鉴国际反恐组织的做法,完善中国与东盟反恐合作机制。一是在反恐合作法律基础上,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的法律合作协议既要包括反恐协调、司法协作和制裁机制,又要涵盖国际刑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合作协议的内容应具有高度的可执行性,促进反恐合作向务实化方向发展。二是就反恐技术而言,我国应注重对东盟恐怖主义多发地的治理,可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与东盟成员国建立执法合作中心,如2017年12月启动的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执法合作中心的建立既可以满足东盟成员国对反恐技术的需求,促推东盟各国反恐能力建设,又可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反恐合作。三是注重对恐怖组织资金链的调查和防控,可通过建立中国—东盟金融管控合作机制,对恐怖组织的资金链进行管控,以便及时阻断恐怖组织的资金链,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总之,恐怖活动犯罪作为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一大“毒瘤”,始终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升级并呈现出新特征、新动向。与之相伴的不只是恐怖活动犯罪防范难度的增大,更是恐怖活动社会危害性的进一步增强。从世界范围看,当前全球恐怖活动犯罪呈现出新一轮的高发态势,严重影响了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对外交流,成为各国发展必须面对或克服的一大难题。世界各地仍在频繁发生的恐袭事件警醒我们,恐怖主义并未远去,国际反恐合作任重道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反恐应当坚持多边主义,坚持综合施策,坚持统一标准,坚持开放包容。对于中国和东盟各国来说,应本着务实、高效、团结的合作机制,维护共同的安全与稳定,积极推进中国—东盟在国家治理中反恐警务合作方面的机制化建设,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良好的警务合作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