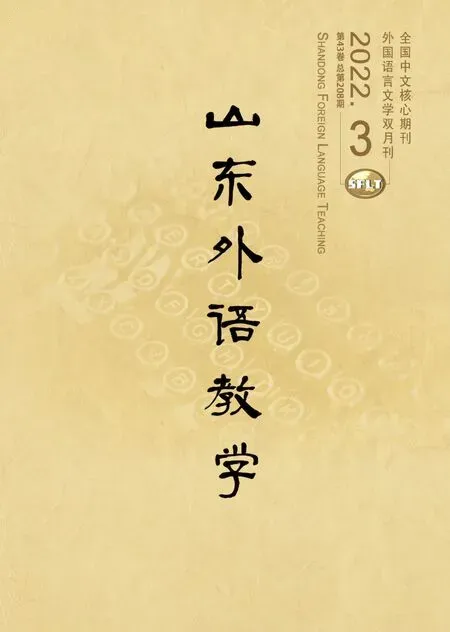或然历史中的现实宿命:《地下航线》的种族主题分析
张坤 李锋
(1. 华东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1620;2. 上海外国语大学 犹太研究所,上海 200083)
1.引言
美国科幻小说家本·温特斯(Ben H. Winters)凭借《最后的警察》三部曲等架空题材小说斩获了埃德加奖、菲利普·K·迪克奖(杰出科幻小说奖)等。2016年出版的《地下航线》(UndergroundAirlines)更是打破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引发广泛关注,被评为《纽约时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以及亚马逊的年度畅销书。该小说虚构了一个奴隶制仍大行其道的当代美国社会,负责追拿逃跑奴隶的黑人特工维克多在追捕黑奴“寒鸦”的过程中接触到声称要解放奴隶、撼动国家体制的“地下航线”组织,然而随着追捕行动的开展和“寒鸦”的死亡,维克多挖掘出案件之后的诸多隐情以及蓄奴四州和美国政府的反人道阴谋,从而揭示了美国种族制度的真面目。整部作品在或然历史的架构中集合了侦探小说、悬疑小说、科幻小说、犯罪小说和恐怖小说的元素。故而有评论认为鉴于其深刻的主题、精妙的情节、紧凑的节奏和紧张的氛围,该书注定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或然历史小说”(Zimmerman, 2016)。
作为该小说题材的或然历史(alternate history)是指“显然从未真实发生过,因此也就不能声称有任何历史真实性,不过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上(随着受压制成分的回归)或许会实现”的历史(Wessling, 1991:13)。换言之,或然历史就是一套假定历史在某一个点分叉出其他可能性的历史或文学呈现模式。《地下航线》作为典型的或然历史小说,重新设定了林肯遇刺的时间——将其从1865年4月14日提前到1861年2月12日(即历史上南北战争开始之日),由此假定南北战争并没有发生,更没有后续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奴隶制在南北妥协过程中被保存了下来。然而讽刺的是,如此明显的历史偏移非但没有将黑人命运引向他方,还和现实有惊人的相似。评论人舒尔茨(Schulz, 2016)认为“他旨在让我们透过现在看历史——种种迹象表明我们仍旧生活在一个蓄奴社会中”。《华盛顿邮报》也认为,“《地下航线》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让人不适地贴近当下现实”(Michaud, 2016)。该书从虚拟的奴隶制延续历史中投射出真实的种族平等历程,成为一部不是历史却胜似历史的种族交响诗。
2.体制化的种族架构
美国的种族主义观念源头可回溯到殖民时代白人至上的种族意识,认为白皮肤的英国人“像上帝本人”(Jordan, 1968:20),而黑皮肤的人则是“魔鬼的后裔”(Reiss, 1997:65),是肮脏、丑陋、原始、邪恶、暴力、愚蠢和死亡的代名词。这种种族分化在被称为“圣经地带”的南方(即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卡罗莱纳“顽固四州”)更为突出。白人有基督教预定论(Predestination)的加持,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黑人则为弃民,选民与弃民的等级分化源于上帝的意旨,也就是所谓的“上帝的和自然的秩序”,即“具有卓越能力和知识的人拥有最高权力,他们应该控制和统治那些低劣的人”(陆镜生,1997:221)。这种控制与统治既是有形的(如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奴役)也是无形的(如剥夺知识获取、进行文化灌输)。在《地下航线》中,这种全方位体制化的种族架构伴随奴隶制被保存下来,成为南方乃至美国社会运作的内核之一。
《地下航线》中南方奴隶的命运着实可怜——他们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是可以被随意使用、买卖,甚至杀戮的生产资料,这与真实历史中的黑人遭遇并无两样。值得关注的是在奴隶制阴影笼罩下的北方黑人,他们被称为“自由民”,是得到法律认可、具有完全自主行为能力的人。理论上讲,他们是和白人平等的美国公民,然而历史分叉造成的“自由北方”恰恰是一个充满反讽的现实隐喻。例如南方黑人埃达一语道破北方“自由”的虚伪性——当被问及为何不逃亡北方时,她说:“去北方?把我的命交到你那疯子神父手中?然后一辈子都要担心买东西时被人跟踪?……每次开车时就会被警察截停?走路时随时可能让警察一枪崩了?”(温特斯,2020:311-312)①对于黑人而言,南方与北方并没有本质区别。实际上,埃达所描述的北方并非危言耸听,北方黑人维克多的经历坐实了她的想法——他每一次停车,都要思考如何应对警察的盘问和骚扰。在进入阿拉巴马州的国内边检处前,他要接受包括舌头、头皮、肛门和睾丸在内的全身搜查。这种带有成见的、侮辱性的检查将所谓的“自由人”打回跟动物无异的奴隶原形。由此可见,北方实质上就是一个打着解放和自由旗号的改良版奴隶社会,与南方大种植园文明下的野蛮种族秩序并无本质差异,甚至更典型、更严格。
一个种族体制能够顺畅、高速地运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强硬而深入的控制和管理机制,即福柯所说的规训。他将其阐释为“使肉体的种种力量永久服从的、并施于这些力量一种温顺而有用的关系方法”(福柯,1999:155)。这种关系方法并非是抽象的关系设定或理论路径,而是一系列具体措施,它“可以通过定位、时间限制、监视、甚至对动作、姿势语言加以规定和改造”(福柯,1999:264)实现对个体的驯服。小说中奴隶的身上刺有所属者的信息,“自由民”到哪儿住宿需要登记“有色人种来宾簿”,就连为政府工作的维克多脊椎里也嵌入了定位的芯片,他们的行踪被完全曝露在公众视野中,没有隐私,无处可逃,正如维克多所言:“即使它不会发声,我也一直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是钩住我的鱼钩,是拖住我的船锚,是驯服我的缰绳”(62)。警察的车上装有印第安纳的逃犯数据系统和全国系统,用以锁定黑人位置。不论是政府明面的监控系统还是暗地的“火炬之光数据库”都将黑人置于“全景敞开式监狱”中,即以观察者瞭望塔为中心的环形监牢,“在环形边缘,人被彻底观看,但他自己却看不到;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却不会被看到”(福柯,1999:230)。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比在《地下航线》中尤为突出——奴隶主、政府等“观察者”通过对企业黑人军事化管理、对家庭黑人全天候剥削,不断向其灌输“被观察”的意识,从而在体制层面掐断其逃离和反叛的可能性。这种严格的监视机制不断被黑人内化,最终形成其“自我监视”,导致他们对自由的渴望远不及对监视的恐惧,与其等待白人以暴力方式规训甚至惩罚自己,不如“规范”自身,尽量顺从。小说中维克多时常想摆脱白人上司布里奇的控制,却始终没有行动,因为在这个严密的体制下,他被剥夺了逃离的方法和目的地,一切都是无谓的挣扎。
在大种植园文明盛行的时代,不仅宗教思想和政治体制偏向建立森严的种族秩序,就连科学也成为论证黑人规训必要性的工具。18世纪之后,白人信徒发展了“生物大链条”(the Great Chain of Being)理论,将人与猿的关系纳入其中,而黑人则是离猿猴最近、进化最慢的人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农场主称黑奴为“我的奴隶猿猴”或者“狒狒”(李学欣,2014:79)。小说通过白人之口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你看见这些牲口了么?他们(黑人)就是这种人”(188)。黑人的低能与冲动被科学以“真理”的形式确定下来,在这一知识体系中,黑人被动物化、低能化、幼儿化,于是不仅是农场主,就连准备营救他们的神父也将其视为无法进行理性交流的劣等人。
小说中因直接造成“寒鸦”的死亡,维克多被迫接任其工作,成为“地下航线”的南派间谍,寻找剥削奴隶的“南雄成衣公司”的违法证据。然而在看清该组织不成熟、不彻底的致命缺陷后,维克多为获取自由,转头与代表官方的布里奇达成协定,变身双面间谍,虽仍需南下取证,但证据则交给政府销毁。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取证过程中,维克多都以为自己是在寻找神父反复强调的“一个小包裹……(装有)一个密封的南雄成衣公司的信封,里面有文件,背面有(寒鸦)名字标记”(249),内容是布里奇暗示的企业违法金融操作,或者财务层面的官商勾结的证据,但最后他找到的却是一个装有人体细胞、用以人工繁殖奴隶的器皿。维克多分别与神父和布里奇对质时发现,他们早就知道信封内是细胞而非文件,“取证”只不过是建立在谎言上的一个说辞,在真相面前,一直宣扬众生平等、鼓吹解放黑人同胞的巴顿神父表示:“因为真相太沉重,太危险了,尽管他费尽心机想要拯救黑人,但并不相信穷困、愚蠢的黑人能保守秘密”(403)。
不论是“生物大链条”还是布里奇和神父的种族社会公共认知体系,都从来不是独来独往、客观中立的。福柯认为知识总是和权力携手并进,知识只不过是权力扩张的手段,它凭借真理的表象,隐藏起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而知识的发展与传播“从来都不旨在建立和肯定一个自由的主体,而是制造一种与日俱增的奴性,屈从它的狂暴本能”(Foucault, 1977:163)。身为黑人的“寒鸦”和维克多在其出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不可信、不开化的野蛮印记,是布里奇眼中肮脏愚钝、不可救药的动物,是巴顿口中智商低下、需要保护和教化的孩童。诚然,表面上看政府的蔑视和“地下航线”的同情水火不容,是充满矛盾的敌对势力,然而因为两者的信条都源于同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种族认知观念,故而不论是剥削还是解放,实质上都是巩固种族制度的手段。
3.内化的种族内憎
被边缘化、受剥削的人群一旦觉醒,常常会狂热而迅速地凝结成一股团结的反叛力量,冲击正统的社会架构——女性主义者们倡导“姐妹情谊”,矛头直指男权社会,无产阶级更是提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专制。虽然这些运动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不可否认,这两项事业在一系列革命后就愈发艰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兴起时忽略了自身内部的各种个体差异和利益冲突。作为另一个社会边缘群体,黑人也一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为获取尊重、争得话语权进行斗争,然而这些抗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反倒使小说中的维克多感受到多重身份危机,成为不被白人统治者和黑人同胞接纳的局外人。在温特斯看来,这与日渐深化的种族内憎不无关系。
种族内憎其实是种族歧视的延伸,内憎的源头是内部差异,而相当一部分的差异是由白人强制规定或者有意安排的。小说中美国当局颁布了《肤色分类表》,黑人肤色就像装修色卡一样被精细地区分开来,维克多在查看“寒鸦”资料的时候曾坦言:“他的肤色描述是晚夏蜜色,听着似乎有几分诗意,但其实不然。‘晚夏蜜色,暖色调,色卡号:76’……就我而言,我的肤色登记为‘中等炭色,有黄铜亮光,色卡号:41’”(55)。这种内部的差异规约已然成为维克多的无意识反应,以至于每见到一个黑人,他都要通过白人设定的色卡对照一番,“午夜黑”“浅咖啡”“212”“220”等划分肤色的词汇层出不穷,这些是他界定黑人的标准。也正是由此,当他见到南方黑人玛丽莲时竟十分陌生:“(我)竟发现脑海中没有可以形容她肤色的词汇,比如野蜂蜜色或浅色系什么的”(305)。由于对方的肤色并不符合色号体系,他在初见时竟不能确定对方是否为黑人,从而毫无种族认同感。肤色差异只是浅层的外在符号,它时刻叮嘱黑人其内部的不一致性,从而瓦解黑人族群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小说中肤色相对较浅的女前台安吉,手捧满是穿着泳装的白人明星的杂志,对似乎走投无路的维克多投以帮助残障儿童般的关怀,以类似白人拯救者的姿态现身,尽量撇除自己黑人的身份残留,从而迎合主流价值标准。
如果表象的肤色差异还不足以引发内部矛盾与歧视,那么经济或者阶级差异则将该问题进一步尖锐化。《地下航线》吸取了相当多的真实历史事件,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和“自由之夏”公民运动等,其中有一个事件是蒙哥马利黑人妇女为要求当局结束奴隶制而绝食,并在整个南方掀起绝食抗议运动的事件。刚开始浩浩荡荡,甚至总统都为之摇旗呐喊,“号称美国新发展目标——‘我们这个时代的废奴法案’”(255),然而结果却颇为讽刺:“黑人劳工党正式宽恕了白人,并为绝食抗议者强制灌食”(255)。废奴运动也因彼此利益相左而划分为暴力派和非暴力派,“保障权利”派和“争取自由”派,于是白人主导的政治当局都不需插手就能看到“‘废奴运动’自食其果”(255)的结局。阶级差异带来的种族内部歧视更是比比皆是,不论是农场中的黑人监工和老奴,还是工厂中的黑人警卫和管教,都将地位次等的同胞视若牲畜,南雄的黑人巡视员从着装到行为都透露着自己在族群内的特殊性,虽然“和我们一样,他也是黑人,不过他穿着衬衫和靴子”(365),他经过的地方,奴隶们纷纷低头让道;一旦他出现,就没有人敢动了;他可以随意盘查奴隶,强迫检查,随意抓人。监工的特权来源于其相较奴隶更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族群内较高的位置使其相信与白人跨族群的差异要小于与奴隶间的族群内差异,故而,他们可以借用白人的视角去压制甚至迫害奴隶。监工的形象让维克多“感到一阵眩晕,仿佛天崩地裂”(365),因为这与其在贝尔农场见到的场景毫无差异。
除了阶级差异以外,种族压迫带来的心理扭曲也不可小觑。直接与施害者对抗、挑战白人专制无异于以卵击石,绝非黑人个体所能担负的,于是部分黑人将目光投射到本族群中,将种族仇恨转嫁到同胞身上,造成内讧。南方的地下组织甚至利用这一特点,通过群殴的方式和维克多接头,因为他们知道,在白人警察眼里,黑人暴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件了。
废奴后的北方开辟了所谓的“自由城”,其实就是一个破败不堪、又不能迁离的黑人聚居地,白人开车经过此处都要紧闭车门,迅速逃离。这里居住的自由民徒有自由之名,不过是被社会排挤和抛弃的边缘人。然而就在这座城中,维克多被两个黑人小混混围堵,他们着装嘻哈,行为粗鄙,一口一个黑奴地骚扰他,拿出廉价的手枪企图逼维克多就范,还商量着如何联系奴隶掮客卖掉他。这两个小混混是典型的黑人底层,身处垃圾场般的自由城,无所事事,生活困窘,他们循环播放着禁播的饶舌歌曲,胸中的郁结和无能的处境逐渐将其逼上绝境,在近乎窒息的时刻,他们找到出气筒维克多。尽管后者衣冠楚楚,言语斯文,毫无奴隶痕迹,他们还是一副地痞做派地认定维克多势单力薄,可任其欺辱。其实底层互轧,以求安慰的行为并不罕见,这种被压迫群体的人性之恶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卑。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德勒(Alfred Adler)指出生理、能力和价值缺陷都会引发的个体自卑,而被社会抛弃的黑人小混混正是社会价值缺陷的化身。然而这种自卑心理非但没有导向自我妥协或超越,反而使其陷入吊诡的优越情结。乍一看,他们体格健壮、飞扬跋扈,不仅不自卑,反倒极其自负,然而在阿德勒看来,这恰恰是其自卑的伪装:“对于一个有自卑情结的人来说,发展一种优越情结是逃避困难的办法之一……这种虚假的胜利补偿了他所不能忍受的自卑状态”(2019:38)。虽然假想出的优越感对改变自身命运毫无益处,但却给他们带来片刻安慰,而这也进一步强化了种族自憎。
4.荒谬的平等悖论
不论在现实还是在小说中,平等是贯穿种族议题的核心概念,似乎所有的所谓正义的立法与改良都将其视为终极目的,而且“人们总是坚信法庭与司法体系能够改善黑人的处境”(Bell, 1995:302)。然而以纽约大学法学教授贝尔(Derric Bell)为首的种族现实主义者坚信,现实世界的种族平等是虚幻的,将这一从法理角度讲已经赢得胜利但实际根本不会实现的理念作为奋斗目标,无疑会导致“沮丧与泄气”(1995:308)。贝尔的论断看似逻辑不通,且基调悲观消极,然而美国种族法律发展却以合理合法的形式印证了贝尔的推论。秉承同样理念的温特斯也在多处访谈中强调,即便经历了这么多的立法与改革,“奴隶制仍与我们同在”(Hart, 2016)。在《地下航线》中,他重新建构的基于奴隶制的种族法律发展体系竟和现实法律隔空呼应。
在小说的历史时间轴中,看似进步的种族法律推进大致如下:1861年,国会通过了《克里坦登妥协案》,规定各州可依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奴隶制的去留,对于逃亡北方而不获遣返的黑奴带来的损失,由政府补贴给奴隶主,避免了内战的爆发;1934年,罗斯福总统签订法案,规定在非蓄奴州内不可持有、售卖和消费基于奴隶制的商品;1944年,杜鲁门总统以准许贩卖军火为交换,实现了乔治亚和肯塔基两州名义上的废奴;1984年颁布的《逃犯条例》修正案豁免了黑人执法者,免其奴役之苦。
虽然这是历史分叉后的法律发展,却与现实惊人的相似——小说中的法案兼顾了美国种族法律的两大特性:反复式改良和不彻底修正。文中提及的《克里坦登妥协案》在现实历史中确实存在,只不过最终因几票之差而流产;表面上看,奴隶制历史就应从此被改写,分叉之处截然不同的抉择应有不同的后续走向,然而现实历史中,经历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宪法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选举权法》和1968年的《民权法》后,美国才部分地保证了黑人的生命安全权、选举权、居住权等权利。值得一提的是,直到2013年密西西比州才正式通过了1865年就已经实行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在法律层面全部彻底地废除奴隶制。从这一角度讲,现实与温斯顿笔下的种族立法史并无二样。
读者难免追问:既然扯起了种族平等的大旗,也深知其中大义,为何不论现实还是《地下航线》中的平等都命途多舛、遥不可期?贝尔(Derric Bell)曾以南北战争时期频繁修正的宪法为例,指出这些表面看来渐进式推动种族平等的法案,本质上都是政治动机的载体——“自私自利性质的动机几乎可以保证,一旦政治需要发生变化,为先前的奴隶提供的保障措施就不再执行”(1995:307)。换言之,种族平等的法律制定动机从来就不是平等本身,故而不论是发生了南北战争的现实,还是延续奴隶制的《地下航线》,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种族平等。
可见,表面上拯救黑人的法律实则是政治家们的伎俩,迎合的多是当权者的统治体系。一如小说中所展现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才是引发种族相关法律和政策进展的主要动力。小说中的南方德克萨斯州1939年就取消了奴隶制,制定了向所有移民开放的政策,欢迎各地获得自由之身的黑人,1964年更是提出独立并引发了长达11年的内战。然而,这些看似民族主义高涨、呼吁自由与平等的激进政治行为都以经济利益为驱动——接纳黑人是因为政府急于补充油田劳动力,宣布独立是为了独占石油资源,而双方勉强握手言和也不是因为达成了种族平等的认知,而是多年战争耗费大量人财物。此时,战前不可调节的种族认知矛盾已经淡出视野,剩下的只有经济利益:“我们(美国政府)建立了特别行政区来保护自身在墨西哥湾的石油利益,而他们(德州)也建立了海湾地区非正规军来保护他们的利益”(145)。几经挫败的维克多看清了德州虚伪的政治面具,直言“德州人对联盟没兴趣,不想管我们,压根就不想插手奴隶制的事儿”(142)。整个社会的宪法制定和政治策略归根结底是为了巩固统治和抢夺资源,抱有平等幻想的黑人涌入所谓尊重人权的北方“自由城”和宣扬种族解放的“德克萨斯共和国”,却又在新的一轮盘剥中沦为奴隶。
此外,贝尔(Derric Bell)还指出,种族平等的另一阻力来自法律实施。法律文本的阐释与执行为种族主义打开了一扇窗,在“不偏不倚”和“种族平等”的掩护下,完成符合当权者利益的实际操作。小说中美国早在1927年就通过法案,对蓄奴州进行经济制裁,北方各州也出台公平劳动法,保证商品没被打上奴隶制的烙印,但实际上所谓制裁并无具体措施相伴——南方种植园的产品依旧在北方畅销无阻,法律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显得一无是处,最终又要政治面子又要经济里子的北方竟“正气凛然”地表示“我们无法结束悲剧,要与奴隶制共存,要在国内和公然允许种族歧视的州共存,我们甚至在经济上与南方那些围墙里的坏蛋绑在了一起”(253)。表面上看,法律无法贯彻、平等无法达成是政客们迫于现实做出的悲痛让渡,他们用“悲剧”来定义自己和南方“坏蛋”的合作,然而实际上经济腾飞的南方为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收,南方公司赚取的利润也大量流入华尔街股市,基于经济利益的南北合作击碎了废除奴隶制的可能性,所谓“无可奈何”与“爱莫能助”不过是政府虚伪的政治做秀。
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种族平等抗争,美国黑人的命运仍未扭转,“一切并没有真正改变……美国还是从前那个美国”(256)。温特斯以一个巨大的反讽,揭示了种族政策的内核,架空历史中平等法案的无力与多变恰恰和现实法案的变迁如出一辙,在当权者政治利益和财阀的经济需求威胁下,平等总是被妥协、折中和无视,温特斯深知,冠冕堂皇的妥协肆意践踏着平等,人们口中的自由、平等与民权在麻木的自我安慰中沦为空洞的口号,“妥协不是人类最坏的原罪,但却是人们犯下最频繁的罪过。只有这个罪过是所有人每时每刻都会犯的”(385)。
5.结语
作为典型的或然历史作品,《地下航线》塑造的新时空不是毫无凭据的穿越或者异想天开的科幻,它“有力地‘再现’了历史……透过‘或然’的角度,设想‘假如(历史不是这样)则会怎样’的场景,反映了作者所述的时代潮流和集体记忆”(Li & Lewis, 2021:153)。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改革举步维艰,鉴于其深刻的历史、文化、经济以及法律本源,不平等的种族关系仍旧会寄居在美国社会中,一如温特斯所描述,改变黑人命运的南北战争其实根本没有发生,《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也并未实际发挥作用,时至今日,奴隶制的残余力量依旧难以撼动。
然而温特斯创作《地下航线》的意图并非是让致力于种族平等的人们知难而退、自暴自弃,而是在警示读者要“看清种族主义的本来面目及黑人的从属地位”(Bell, 1995:308)。小说最后,揭开美国政府和“地下航线”组织虚伪面庞的维克多非但没有逃离美国,反倒联合白人女性玛莎投入到新的解放抗争中,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是他淬砺自我、保持清醒的尝试。一如贝尔(Derric Bell)所言:“通过抵抗,我们的人性得以幸存且变得更加坚强,即便面对那种压迫,我们也永远不会被征服”(1995:308)。此刻的战利品已不再是早已写入宪法的平等,而是不屈不挠的意志与永不退让的勇气。
注释:
①引文出自本·H·温特斯,《地下航线》,邓超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以下出自该著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