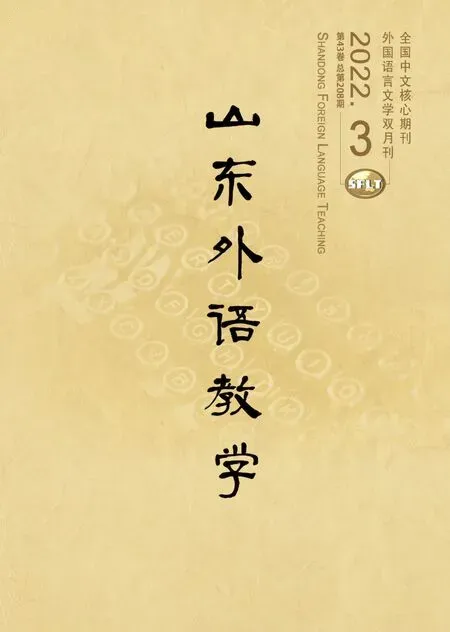中西双重哲学视角下《高堡奇人》小说人物的罪与赎
单谊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1.引言
“救赎”主题,或者范围更为广泛的“罪恶—救赎”主题(以下简称“罪—赎”)历来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常见主题。作为救赎主题的发轫之作,《圣经》中涉及“罪”(sin)与“赎”(salvation, atonement, redemption)的章节比比皆是。《高堡奇人》是一部典型的或然历史小说,其罪—赎主题的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该书表面上是对现实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做出或然假设,但其深层焦点却是对《圣经》中罪—赎主题的异化与重塑;其次,该书的不少段落在思想和语言方面渗透着《圣经》的韵味,同时也印刻上了东方哲学思想的烙印,这充分体现在分布于各章的《易经》卜卦中。本文以中西方哲学为视角,探讨《高堡奇人》中人物的罪-赎主题,旨在剖析其如何借助主题阐述与叙事框架的非典型写作技法刻画这一核心主题。
2.英美文学骨髓中的罪—赎主题
英美文学中诸多重要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的作品都与《圣经》中的观念与准则、故事与典故、修辞与意象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圣经》作为“万书之书”,“在不少方面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已超越对《圣经》本身的文学分析……它是西方文学最伟大的源头,对文学的象征意义产生了巨大影响”(Ryken & Longman, 1992:12)。英美文学史上很多著名作家的扛鼎之作,都不同程度地与罪—赎主题有所关联。从宏观的历时角度看,我们可以将英美文学作品与《圣经》文学的关联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以借用与改写为主要特点的直接关联阶段;(2)以延伸与深化为主要特点的间接关联阶段;(3)以重塑与变异为主要特点的微弱关联阶段。可见,两者的关联程度逐渐呈弱化趋势。
第一阶段以莎士比亚的诸多戏剧、约翰·弥尔顿的《乐园三部曲》和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为代表。它们直接借用《圣经》中的话语、意象、人物或情节,或对其进行改写和创新。例如,《失乐园》取材于《旧约·创世记》,将撒旦的魔鬼形象改写为叛逆之神。第二阶段的典型作品包括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1859)、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1891)、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1850)、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1851)等英美小说。《双城记》中的西德尼·卡顿是个基督式的人物,耶稣用自己的肉身为人类赎罪,卡顿则为成全自己所爱之人露西· 莫奈特的幸福,代替查尔斯·达奈登上断头台;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是西方文学中自我救赎的经典形象之一:作为善良、具有多重性格的农村女性,她既离经叛道,又追求真爱,是人性善与恶的典型化身;《红字》里的齐灵渥斯则是阻止自我救赎的代表:他不仅外表十分丑陋,灵魂也异常畸形,恶魔般处心积虑地摧残和折磨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白兰,最终变成阻止自我救赎的恶魔(王丽丽,2010:114)。20世纪后的英美文学为第三阶段,作品更关注罪—赎主题的重塑与变异,以西奥多·德莱赛的《美国悲剧》(1925)与威廉·戈尔丁的《蝇王》(1954)等现当代小说为典型代表。其中,《美国悲剧》的主人公克莱德欲壑难填,完全丧失人性,为娶到富家千金竟丧心病狂到谋杀已孕情人的地步,最终却在无尽贪欲中自我毁灭。本文认为,《高堡奇人》大致属于其中第三阶段的作品,其对罪—赎主题的典型重塑与变异将在下文逐层剖析。
3.“三个世界”掩饰下的罪—赎主题
《高堡奇人》向读者展示了二战后三个政治格局迥异的世界:第一个是原作故事所发生的那个世界(即“菲利普·迪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打败了同盟国,占领美国的东西海岸,成为全球霸主;第二个世界是《高堡奇人》中神秘作家阿本德森所写的“书中书”《蝗虫成灾》(TheGrasshopperLiesHeavy)向《高堡奇人》中的人物(以及作为读者的我们)展示的那个世界(即“阿本德森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轴心国被击败,美国和英国成为了全球霸主,但是很多地方又与第三个世界(即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有所不同,例如二战后的整体政治格局由现实中的美苏争霸变成了美英争霸。
《高堡奇人》中有多处涉及《圣经》的内容或者反映出其思想与观点,例如“书中书”《蝗虫成灾》的书名便源自《圣经》——“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传道书》12:5)。当然,书中也不乏同罪—赎主题相关的段落,例如主人公之一、日本官员田芥先生心生慨叹:“罪恶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倾倒在我们身上,渗透进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脏,甚至渗透进路面”(迪克,2017:124)①。此句就直接套用了《圣经》里的原罪思想;再如,书中对纳粹内部极端派别的狂妄与野心的揭露,同天主教七宗罪之一的“傲慢”息息相关:
他们想成为历史的代理人,而不是被历史抛弃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拥有和上帝一样的力量,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这就是他们疯狂的根源。他们被某种原始意象征服,自我疯狂地无限扩张,不知道什么时候取代了上帝。这不是狂妄自大或傲慢得意,这是自我的极度膨胀……人没有吃掉上帝,而是上帝吃掉了人。(52)
在现当代小说中,双重主题屡见不鲜——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1929)就被众多文学批评家视为一部贯穿战争—爱情双重主题的小说;《双城记》中则渗透着压迫与反抗、暴力与博爱、动乱与秩序、复仇与和解等多个双重主题。不仅主流的英美文学常涉及双重或者多重主题,其他的文学支流也对双/多重主题情有独钟。美国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的二战题材小说《金陵十三钗》就以1937年沦陷后的南京为故事背景,在强烈控诉日本侵略者兽性与罪恶、细致描述人间地狱中生命低贱与脆弱的同时,也细腻刻画了人性的高贵与坚强,十三位南京烟花女子以及几位避难的中国士兵舍生忘死营救十二位金陵女学生。“赴死”与“求生”这对矛盾对立体便成了小说中交织在一起的两大主题(贾磊磊,2012:43)。
同样,《高堡奇人》也是一部将深层主题内嵌于表层主题之中的双重主题小说,其表层主题主要涉及二战前后的世界政治、历史格局,而其深层主题则主要剖析人性的罪恶与救赎,揭示了人们难以摆脱的人性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罪恶的必然性与救赎的自主性。《高堡奇人》这种将人性救赎隐藏于架空历史层中的创作技法,堪称该书救赎主题的最大特色。小说不少地方将重新架构世界格局的表层主题和探讨人性罪—赎关系的深层主题进行交织式叙事,例如下面两段就体现了以贝恩斯和田芥为代表的德、日统治阶层内部反战派人士对于大众生命的珍惜,对于终极世界秩序和终极正义的思考,以及对于人性缺陷的克服和所犯罪行的救赎。
然而,贝恩斯先生想,问题的关键不在当下,也不取决于是我死还是这两个德国国家安全警察死。问题的关键在于未来。将来发生的事情能否证明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我们能否拯救千百万人的生命?(265)
显然,我们还是继续活着,一直如此,日复一日。眼下我们努力阻止蒲公英计划。以后我们又要努力打败警察。但是我们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必须一个一个地处理。这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我们只能通过在每一个环节中作出选择,来控制最后的结果。(327-328)
具体说来,《高堡奇人》对涉及人性善与恶、伟大与渺小等矛盾对立体的罪—赎主题的阐释有三点独到之处。其一,罪—赎主题二元化,即个人救赎与集体救赎并行不悖。几百年来,绝大多数英美小说讲述的都是个人救赎,这也体现了西方社会所崇尚的自由主义精神。英美小说中主人公之所以能改过自新、除恶扬善,其最大的内在动机或根本原因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其次才是弘扬社会正气;而东方文学中的救赎主题则往往更关注主人公所处的宏观社会层面,并非每一个独立个体(熊伟、侯铁军,2008:67-68)。作为一本当代历史题材小说,《高堡奇人》中的人物表面上几乎人人都在自我救赎,实际上,这些独立个体的个人救赎凝聚成几股合力来实现整体的社会救赎。贝恩斯(真名鲁道夫·韦格纳)、田芥先生、寺夫木将军代表的德国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和平派,想方设法阻止德日之间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弗林克、朱莉安娜、齐尔丹、埃德等代表的美国平民和小商人等阶层,依然保持着独立顽强的美国民族意识,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抗争与不合作态度勾勒出满怀爱国主义情怀与强烈民族自豪感的人物群像。
其二,救赎方式与手段多样化,救赎目的与过程自主化。《高堡奇人》的主要人物大致可分为三类:表现正面形象的美国普通民众与不同派系的德日军政商界高层,这两类人有的穷凶极恶,有的良心未泯,有的开明变通,有的介于其间;第三类则是资本家温德姆·马特森、杀手乔·辛纳德拉等较为负面的人物。小说除了描述某些德国极端派系的政治高层外,其刻画的其他主要人物只不过是善恶同体的芸芸众生,既非十恶不赦之徒,亦非至善至美之士。他们虽然永远挣脱不了人性的丑恶,但偶尔也会闪耀出人性的光辉;他们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改正所犯的过错,或修正所做的不妥之事。朱莉安娜便是他们的代言人——她是典型的矛盾复合体,既放荡不羁,对性爱持无所谓的随意态度,又不忘旧情,演绎着甘愿为前夫自杀的忠贞秉性。以下几段引文勾勒出朱莉安娜的多重性格与复杂人性:
朱莉安娜想:狄塞耳不是从轮船客舱的窗户跳下去了吗?在远洋航行的时候跳海自杀了。或许我也应该这么做。但这儿没有海。不过想自杀总有办法。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一样。在衬衫的胸口扎根钉子,就和弗林克永别了。一个绝望的人无惧任何凶险和痛苦。她跳不了海,但还可以有其他死法。(37)
难怪她(朱莉安娜)四处漂泊,换了一个又一个男人,一直在寻找。甚至她自己都不知道个中原委,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是我知道她需要什么。这次与麦卡锡的重大合作——无论如何——就算是为了朱莉安娜,我也要让它成功。(67)
多么古怪的人…… 他跟她在一起时是那么主动,差不多折腾了一个晚上。一刻也没停。但在做的时候,心思似乎又没放在上面,光有行动,没有感受。心思或许放在别的事情上了。(101)
朱莉安娜在汉堡店认识了伪装成意大利人卡车司机的秘密纳粹杀手乔·辛纳德拉,随后就与乔过夜并一同驾车去夏延市拜见《蝗虫成灾》的作者阿本德森,但在猜出乔的真实目的是谋杀她的这位崇拜对象后,朱莉安娜勇敢地与之搏斗,并去告知阿本德森实情,以主动自救的方式纠正了自己的过错。日本驻旧金山第一商会会长田芥先生虽是带有政商双重身份的日本上层,但又是正直、有正义感的有识之士,他与犹太裔美国工匠弗兰克·弗林克虽从未谋面,却因一枚银质装饰品而相互拯救。换言之,这是一种“他者拯救”。弗兰克通过要挟他的前雇主温德姆—马特森而获得了制作首饰的2000美元资金,也正因为此事后来被警察逮捕。而银质饰品则由古董商齐尔丹代售给了商会官员田芥,并在精神上给予田芥“道”的启发,使得田芥最终非但没有屈服于德方压力,反而签署文件释放了弗兰克,让他免于被遣送德国处死的噩运。白人古董店商人齐尔丹内心受到爱国主义的感召,拒绝了日本客户香庄良思提出的批量生产廉价护身符的建议,重获丧失已久的个人与民族尊严,可谓是一种“被动式”的自我升华与拯救。
其三,“不是救赎的救赎”,即救赎结果并非尽如人意。《高堡奇人》的主要人物并非都能得到救赎,较为典型的人物是韦格纳上校。他属于德国统治阶层内部的反战派,为使“蒲公英计划”(即对日本本土及其势力范围进行大规模核打击)胎死腹中,韦格纳化名贝恩斯,赶赴旧金山将计划细节告知日本高层,回国后即被德国安全警察部门挟持,生死未卜。乔·辛纳德拉真实身份虽是纳粹秘密警察,被派来暗杀《蝗虫成灾》作者阿本德森,这只不过是他的职责所在,并不能说明他是十足的坏人,可是他最后却死于非命。而为富不仁、大发国难财的奸商温德姆—马特森虽然坏事做绝,但最后也未遭到报应或天谴,依然活得潇洒自如。《高堡奇人》的人物并不因行善而必然得救,也不因作恶而必然遭难,这种救—赎模式自然异于传统的救—赎定式或俗套,颇具颠覆性。
4.罪—赎叙事中的中西哲学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高堡奇人》救—赎主题刻画的创新除了上述双重主题与三个特征之外,还通篇引入了东方哲学思想。这一显著特色主要体现在《易经》对整部小说主题的烘托效果以及对小说叙事结构的构建作用上,下文将作详细阐述。
从中国哲学的视角审视《高堡奇人》的罪-赎主题,我们会发现整部小说围绕两个问题——“有理之罪与顺势之赎”与“戒恶行善还是趋利避害”——展开论述,并给予了隐喻性、开放性的解答。针对第一个问题,《高堡奇人》借鉴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善恶观,而之于《易经》则体现在承认善与恶不过是一个矛盾对立体的两个方面,“无善则无所谓恶,无恶亦无善”,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诚如小说里日本商会会长田芥所说,“当‘阴’无处不在时,在最黑暗的深处,第一缕光明蠢蠢欲动”(299)。这句话与上文提到的他的另一句话“罪恶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倾倒在我们身上,渗透进我们的身体……”(124)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明显是一种西方风格的善恶观。因此,从东方哲学视角来看,《高堡奇人》中各类人物人性的弱点以及他们所犯的种种罪过并不是不可饶恕的,甚至不是非救赎不可的。书中没有至恶至善的人物,因此也不必有至善至美的救赎。恶既然是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缺点既然是人性的自然属性,那么救赎也不妨顺势而为之,不必强求,成也罢不成也罢,都只是一种选择而已。《高堡奇人》中人物的救赎与其说是有意而为之,不如说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发行为,是每个人性格和本性的自然延伸,故好人不一定不做坏事,做了坏事也不一定刻意要去补偿。
再以朱莉安娜为例。她之所以割喉杀死纳粹杀手(也是自己的临时伴侣)乔·辛纳德拉,并不是缘于乔十恶不赦,而仅仅是因为朱莉安娜欣赏和崇拜《蝗虫成灾》的作者而已。对于“戒恶行善还是趋利避害?”这个问题,西方人的回答是把救赎分为三大类,即死亡救赎、善行救赎与爱的救赎,有罪之人只有通过其中一种甚至多种救赎才能获得上天宽恕,得到拯救(周家斌、王文明,2013:310-322)。但是,融合了中国哲学思想的《高堡奇人》中人物的救赎则显示出“趋善避恶”的本质,无论是日本商会官员田芥、古董店商人齐尔丹,还是男女主角弗林克和朱莉安娜,他们遇到棘手之事首先想做并去做的事情就是拿出《易经》占卜,以神谕预示的凶吉来决定后续对策与行动。《易经》作为《周易》的释书,其本身包含了一整套系统的空间与时间辩证思维体系,其主要目的在于纪晓岚所言的“推天道以明人事”(《四库全书提要·易类》)。可以说,《易经》的神谕贯穿了《高堡奇人》的整个叙事空间,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整部小说都是神谕的产物。田芥在会见化名贝恩斯的德国海军上校韦格纳之前,就已占卜得出结论,即贝恩斯的真实身份并非商人——“料是强人,不合世道,言语耿直,不重虚礼,为人正直,必有人应……”(25)。
神谕叙事(亦即《易经》的占卜)对整部小说的情节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也对整部小说的主题起到了风向标的效果。迪克凭借“两书三世界”(两书即《高堡奇人》和书中书《蝗虫成灾》;三世界即上文所说的“菲利普· 迪克世界”、“阿本德森世界”和现实世界),以及模式的混沌叙事手法,向读者抛出了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虚幻的世界、虚幻世界中的虚幻世界,以及我们真实生活的世界,到底哪个更好?到底哪个才是我们更加向往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都不是!神谕的真实性恰恰证明了历史的不确定性——阿本德森依据《易经》的神谕所写就的《蝗虫成灾》描写了二战同盟国胜利而德日战败后的世界政治体系,但却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又不尽相同,书中虽然描述了轴心国的覆灭,但却是英美两国(而不是美苏两霸)瓜分了世界,因此战后美英冷战代替了美苏冷战。这种历史设定或许证明了迪克对于当今世界与政治格局的悲观态度:就算同盟国战胜轴心国又如何?现实世界并不会变得更好,也许会更坏。三种或然世界,类似阴与阳、善与恶、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转化,它们没有一个是世界末日,哪一个世界也有善举、也有义人,同时也有恶行与邪恶之徒。
《高堡奇人》不以悬疑开头,却以悬疑结尾,或者说以某种“虚无”结尾——朱莉安娜等人寻找《蝗虫成灾》作者的住处和底细如果被视为一个“谜”,那么在小说结尾处谜底揭晓之时却发现其对故事的结局竟然毫无影响,因为《蝗虫成灾》的作者阿本德森创作整部小说不是根据自己随心所欲的设想,而是完全依据《易经》的神谕完成的。简言之,迪克通过道家儒家思想等中国哲学为不确定、虚幻的社会与历史带来了某种确定与真实,带来了希望与憧憬,同时也为真实的历史与世界带来了不确定性与虚幻性。这或许因为《圣经》故事多是虚构,而《易经》占卜法则却总被当成是确然的缘故吧。
5.结语
《高堡奇人》对或然历史的叙述有别于其他或然历史小说,其差异主要有两点:其一,通过《易经》对于故事情节的预设。该书将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之间的界限模糊化,抹杀了现实世界与假想世界之间的本质区别,由此在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双重审视下,“或然”之事变得“不或然”,真实世界与或然世界变得同质,“不兼容”之物变得“兼容”,例如善与恶;其二,小说表层主题对于真实世界与或然世界同质性的探讨被进一步映射到小说的深层主题中,即将人物的救赎从宗教的神圣化、虚幻化与义务化的罪—赎关系桎梏中解脱出来,使其更为世俗化、现实化与自主化。本质上,《高堡奇人》中人物的救赎是一位西方作家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审视救赎。《圣经》(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古典文学)认可原罪,虽然现当代西方文学由于受到民主政治、先进科技与现代文化的影响,救赎主题本质上已经与古典文学貌合而神离、分道扬镳了,但依然带有几缕抹之不去的痕迹。《圣经》视角下的救赎被认为是一种必然、一种义务、一种契约,而融合中西优势与特点的现代哲学则视救赎为一种或然、一种选择、一种扬弃,《高堡奇人》中人物的罪—赎主题与叙事正反映了这一观点,体现了这种趋势。
注释:
①引文出自菲利普·迪克,李广荣译,《高堡奇人》,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以下出自该著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