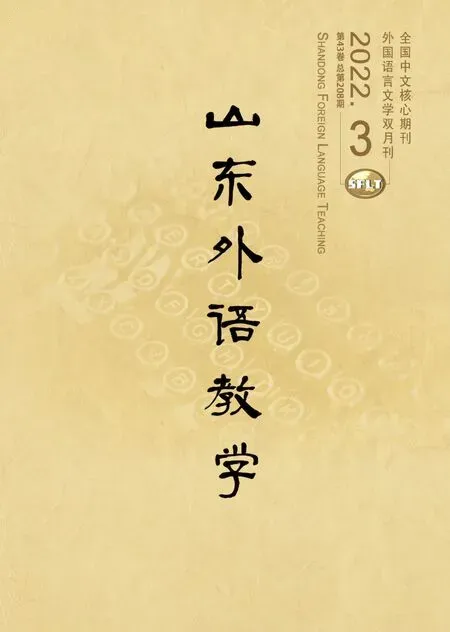《米与盐的年代》中的中国形象与共同体想象
张莉
(郑州大学 英美文学研究中心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1.引言
美国著名小说家金·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ey Robinson, 1952-)凭借《米与盐的年代》(TheYearsofRiceandSalt, 2002)于2003年获得“轨迹最佳长篇科幻小说奖”(Locus Award for Best Science Fiction Novel)。小说对“西方人缺席的世界近代史”进行了大胆的假想,设定“中国”机缘巧合之下发现美洲大陆,并成为拥有广阔殖民地的全球性国家。与此同时,科学和工业革命分别在中亚和印度展开。经过七个世纪的发展,中国、印度和穆斯林国家形成三足鼎立的霸权局面,它们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
在这段“或然历史”的构想中,“中国”显现出既先进又野蛮的矛盾形象。一方面,小说假想中国通过殖民扩张推动经济、科技、军事的飞速发展,进一步稳固了世界中心地位,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另一方面,与先进的文明样态相背离,“中国”又是内外积弊已久的保守的帝国和野蛮的侵略者。这一矛盾形象的塑造,基于西方由来已久的“中国发现美洲”假说,虽然是以近代西方殖民史为基础,体现的却是冷战后西方“中国威胁论”的思维模式,也表达了作者在世界一体化背景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和思考。
2.历史与当下:循环的宏大叙事
或然历史(alternate history)指那些“显然从未发生过,因此不能称之为事实,不过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上(随着受压制成分的回归)或许会实现”的历史(Wessling,1991:3)。作为史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史学家通过“假如历史不是这样则会怎样”(what if)的假设,以及在此假设基础上的推断和演绎,可以更好地确定这些事件和人物的相对重要性究竟几何(李锋,2014:75)。作为一种文类,或然历史小说常常通过假想过去而指涉当下,对某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变形或移植,即通过展现“what if”的假想场景,警示读者“本来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what could have been otherwise)(李锋,2020:48)。这一历史事件往往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旦有所偏离,就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般巨大的反应。在这一历史分叉点之后,或然历史小说尝试创造出一个偏离已知世界发展轨迹的新世界。《米与盐的年代》就是一部典型的或然历史作品。小说通过设想传染病杀死了99%的欧洲人、中国在出征日本时意外偏航发现美洲,一改真实历史中西方在世界近代发展史中的主导地位,将世界塑造成以东方为中心的全新形象,对“假如中国发现美洲,世界将会怎么样”这一西方经典命题进行了别样的解答。
然而,与传统意义上的或然历史小说相比,《米与盐的年代》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独特性。首先,该书展示出全球史的视野和重写人类文明史的抱负。传统或然历史小说大都聚焦于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南北战争、美国总统选举等,故事背景通常设定在某一特定地域或范围,而《米与盐的年代》借助几位主要人物的生命循环,跨越了从14世纪到21世纪末的数百年历史,周转于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的不同地理空间,俯视着整个世界的进展,描绘了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重构了全球科技、文化发展史和战争史。其次,《米与盐的年代》引入了佛教文化中的“转世”思想,让主要人物的灵魂在“中阴世”会面,带着前世的经验和知识投入下一世的“游戏”之中,以不同的名字、性别甚至物种反复呈现,由此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并在叙事上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结构。作者这种轮回装置“提供了一次又一次重新进入历史和发展的流的可能性”,这使得罗宾森能够赋予他的史诗以个人的尺度,并将“个人与集体的时间、个人与历史的变化联系起来”(Kneale, 2010:301)。小说的第一章援引了我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典故,把轮回之初的主角布尔德看作是踏上旅程的孙悟空,由此开始主人公们在大陆之间的轮回之旅。小说的最后一章中主要人物和故事重新回到中国,罗宾森借中国历史学者之口反思历史对当下的意义,由此完成了情节和叙事的闭环。显然,在这一循环中,中国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最重要的是,《米与盐的年代》设定了反转历史与真实历史“殊途同归”的相似性结尾,凸显了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的认知,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传统或然历史小说旨在通过设想历史在某一重要节点上的转折,呈现反转历史与真实世界的明显差异。以著名或然历史代表作《高堡奇人》(TheManintheHighCastle, 1962)为例,反转历史中轴心国集团战胜了反法西斯同盟,美国被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国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反美阴谋》(ThePlotAgainstAmerica, 2004)中假设罗斯福大选落败,飞行英雄林德伯格当选第33届美国总统,继而一个亲法西斯政权在美国确立。而《米与盐的年代》中的历史却在转折点之后似乎重走了老路。尽管小说呈现出全新的地缘政治,也有与史实完全不同的设想(例如印第安人在抵抗外国殖民入侵时表现出强大的力量),但是在这个想象的世界里,科学发展、奴隶贸易、工业革命、文艺复兴、世界大战和女权运动等都在沿着与真实历史相似的走向进行。罗宾森似乎重演了历史,只是置换了故事的主角并将欧洲中心转移至了亚洲。
对于这种重复的选择,罗宾森(2004)认为,虽然读者期待在或然历史作品中拥有与现实不同路径的历史体验,但在科技和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时,诸如战争等历史事件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罗宾森将“中国”想象成与近代西方相似的殖民者,借助对外扩张,印度、北美、日本等地区的发展状况得以展现。同时,“中国”成为多元文化碰撞的中心,儒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相互激荡,呈现出彼此冲突又交融的特点;少数群体的身份和地位成为“中国”的显性问题,族裔、性别、阶级等冲突日益严峻。可以说,“中国”成为这段或然历史中各种文明的载体,也是罗宾森施展其全球性视野的“演练场”。“中国”成为世界的缩影,折射的是真实历史中的全球性问题。在罗宾森的冥想中,“中国”已不再是我们认知中的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超越了国界、综合多种文明和思潮的中心,也是他重构历史、反思当下与展望未来的载体。
3.先进亦或野蛮:小说中矛盾的形象
在《米与盐的年代》中,中国不仅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域和重要背景,甚至它自身也成为小说重点塑造的主体形象,但小说中的“中国”呈现出来的并非只是先进、发达的文明代言人形象,它还是殖民侵略者的代表,是兼具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矛盾综合体。
首先,中国被塑造成国力强盛、技术发达的东方大国形象。第一部分“觉悟虚空”中,跟随“B”姓灵魂的第一世人物布尔德(Bold)的脚步,中国的强国形象首先通过先进的船舶业和城市建设展现出来。以郑和为首的中国人远航至阿拉伯世界,他们的船队气势恢宏,“每条船都像个城镇似的”“有十几条独桅帆船那么长”(罗宾森,2008:26)①。“喜欢建造大的东西”,这符合不少欧洲人、非洲人对中国的认知。中国拥有杭州这样的超大都市,城市里高楼鳞次栉比;丝绸、瓷器和檀香等货物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出口,“中国一直都是中心,也一直都是人口最多的地区。自古以来,世界各地的人都会买进中国的货物”(369)。商品贸易加上对殖民地的掠夺使中国成为财富中心,也使其政治野心不断膨胀。小说中郑和向黑人男孩可玉(Kyu)解释船队的政治策略:“在那里扶植一个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当政者。其他的东西,不要去破坏,要跟他们做买卖,保证国王对我们友好,已经有十六个国家向皇上进了贡品,这都是我们的船队四处航行的结果啊”(55)。这一政治策略是书中整个“中国”殖民政策的缩影。在这段或然历史中,中国俨然是拥有重要影响力的超级大国。
除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小说中的“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成为世界的中心。在小说第四章“炼金术士”中,中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中亚,灌溉了中亚的科学革命。“穆罕穆德就说过‘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225)。中国国内知识界也浸润在先进文化中并积极倡导文明的融合。以康有为女儿为原型的“康寡妇”不为封建伦理纲常所束缚,不仅勇敢改嫁,追求个人的自由生活,还挑战“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训,著书立说并整理编纂中国古代女诗人的作品,俨然成为女性运动的先驱和女性传统的建构者;她所改嫁的丈夫伊布哈姆秉持开放的宗教立场,极力促使佛教、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的融合。作者罗宾森借此人之手完成的“论财富与四大不公”的煌煌大论,表达了先进知识分子对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深刻体察和深入思考。可以说,小说中的中国也展现出作者对多元文化愿景的想象和描绘。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小说中的“中国”拥有两幅面孔——它既是思想进步、技术领先、国力强盛的超级大国,也是残酷贪婪的“奴隶贩子”“野蛮侵略者”和“战争狂魔”。小说第一章详细地假想了中国商人在非洲奴隶市场进行贸易的场景。欧洲人布尔德和黑人男孩儿可玉作为奴隶被卖往中国,可玉在船上惨遭阉割。这种非人的待遇导致可玉性格的异化,诱发了他报复的欲望。显然小说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移植进了东方中国的故事中,不但达成了对历史的反讽,对奴隶制的控诉,似乎也在昭示着所有剥削者、压迫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小说中,随着历史的推进,中国形象逐渐被建构成“殖民侵略者”。小说中的万历38年(1610年),由干将军(Kheim)领导的中国军队出发远征日本,旅途中遭遇无风带偏离航线,其中一部分人随波漂流驶向了美洲大陆。根据小说的描述,这里民风淳朴、风光优美,但中国人带来的瘟疫很快使这个世外桃源上的原住民灭绝。中国军队继续航行,发现了盛产黄金的国家,他们禀告皇帝,“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征服那个地方,一统天下,并把那里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带回来”(181)。新大陆的发现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为其加速殖民扩张和对外侵略提供了资本。“中国”在美洲的太平洋沿岸、澳洲大陆、东南亚地区很快建立了殖民统治,并将侵略的触角伸向全球各地:向东占领了日本、朝鲜半岛;向南征服了缅甸等地;向西,他们逐步深入中亚,威胁伊斯兰世界。
小说描写了对外的侵略扩张并不能掩盖“中国”内部深重的流弊。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和顽固的官僚作风已经使得这一泱泱大国危机重重:反清运动和宗教冲突此起彼伏,西北地区的穆斯林暴动时刻威胁着清政府的政权;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到处是破产的作坊和贫民窟;在中国的殖民地,日本人在北美秘密组织独立运动……而此时中国皇帝仍然夜郎自大,固执地认为“大清国正处在最兴盛、最辉煌的时期”(361);“他们只关心中国,觉得中国正是天与地的终端,地球的中心……大多数人认为世界的其他地方住的都是蛮子刁民”(349)。小说暗示了世界各地人们反抗意识的觉醒,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在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中,罗宾森展现出了对东方历史、文化及宗教知识的熟稔。他特意使用了中国古代皇帝年号纪年法,重述了14世纪以来郑和下西洋、万历援朝抗倭、甘肃回乱、江南妖术大恐慌等历史事件。虽然有精细的历史考据,罗宾森对这段中国历史的重述却并不旨在还原史实,而是有意将中国与近代西方发展史进行了“嫁接”,以移花接木之术使中国代替西方成为野蛮的殖民主义者。这一历史的假想和重构,表面上是在讲述虚构的或然历史,实际上却在映射历史事实。“先进与野蛮”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真实写照。在真实历史中,西方殖民国家借助“航海大发现”进行对外扩张,获得早期资本积累并占据世界霸权,但“先进”的西方这一神话是建立在奴隶贸易和殖民侵略等罪行之上的,侵略者才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
4.命运共同体:多重的镜像功能
《米与盐的年代》里中国的世界霸权无疑是虚构的,但这一虚构的历史映射出了西方自己的社会现实。“先进而野蛮”的中国形象符合现代西方对中国的集体想象,也是西方冷战思维下“中国威胁论”的直接产物,投射出了当下全球化视野下西方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和想象。
从18世纪开始,关于“中国发现美洲”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三个世纪之久。法国汉学家德经(J. de Guignes)首次提出“中国发现美洲”的假说,认为中国古代史书中记载的“扶桑国”就在北美的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一带。随着中国本土乃至美洲近海海底文物的发现,“中国发现美洲”的讨论出现了“僧人慧深漫游美洲”“殷人航渡美洲”等不同版本的假说(徐波,2016),中国人到达美洲时间的考证也不断提前。2005年,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郑和及其船队成为中国发现美洲的主角。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1421:TheYearChinaDiscoveredtheWorld, 2002)中认为郑和船队在第六次航行中到达了世界上每一块大陆。这一观点引发了巨大争议,这本著作成为2003年《纽约时报》畅销书,被翻译为十几种语言,销量突破一百万册(王冬青,2019:47)。2015年,马克·尼克莱斯(Mark Nickles)等撰就《郑和发现美洲之新解》,认为郑和率领的中国舰队曾经分别于1423年、1433年抵达密西西比河谷。“中国发现美洲”成为西方热门的命题。
为什么中国成为西方“地理大发现”历史重构中的热门对象呢?首先,中国古代辉煌的文明成就和世界领先的造船与航海技术使得“中国发现新大陆”成为不少学者的臆想。中国由于种种原因与“海上霸主”失之交臂的史实,也成为很多人心中的遗憾,于是“中国发现新大陆”的假说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对这一遗憾的弥补。其次,近代以来,中国常常被传教士描绘成为这样一个国家:“繁荣富庶,安定和平,人民安居乐业,讲究道德,彬彬有礼,充满智慧、文明和和谐的气氛”(武斌,2004:120)。中国的理想形象促使西方学者设想近代史的另一种“乌托邦式”进程。在著作《1421:中国发现美洲》的结语中,孟席斯认为“文明的中国人倡导‘怀柔远人’,但代替他们的基督徒殖民残忍,几近野蛮”(Menzies, 2002:406)。在他看来,如果郑和没有被迫终止航行,中国或许将取代欧洲称霸全球,那么西方殖民者的血腥屠杀史便可避免。罗宾森在《米与盐的年代》中就操演了这样一个剧本,却给出了与孟席斯不一样的结尾。中国军队欣赏南美洲的自然之美,与当地人建立起友好关系,将土著小女孩“蝴蝶”视若珍宝,教她语言文字并悉心照料,但他们仍然像近代西方殖民者一样散播了传染疾病、抢掠了金银矿藏,以此推动帝国的扩张,成为横跨太平洋两侧的世界霸权。 “地理大发现”表达的历史想象,正是90年代史学界反思现代性发展的核心问题:即如果具备“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世界其他文明同样具备相似的发展可能性(王冬青,2019)。如果说以往西方学者对中国在“地理大发现”中的作用的想象是基于一种期待,希望看到中国发现美洲后能带来不一样的世界,那么罗宾森打破了这一幻想。
周宁认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每一次反复,都有西方文化内部深远的动因”(2005:18)。表面上看,《米与盐的年代》以东方为中心,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解构。但罗宾森笔下的中国,实际上是带了顶“东方”帽子的“西方”,还是走上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老路,这一虚构的征服世界史清晰地反射出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影子。作为文化的他者,中国在《米与盐的年代》中充当的正是殖民主义的“替罪羊”形象。
比较文学形象学告诉我们,“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孟华,2001:157)。《米与盐的年代》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后冷战思维下,西方大国对中国的集体想象。这一形象本质上源于西方根深蒂固的“中国威胁论”思想。1984年,美国“冷战思维之父”凯南(G.F.Kennan)曾经指出,某些美国人有“真古怪”的怪癖:“时时刻刻都想在美国国境以外找到一个罪恶的中心,以便把美国的一切麻烦都算在它的账上”;“总是自动而有意识地夸大假想敌国的军事潜力,从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对这个假想敌的怀疑、恐惧和对抗心理” (1989:130,137-138)。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上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这自然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高度关注。西方意识中的“黄祸论”又重新被唤醒,鼓吹者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传统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吴飞,2015:8)。《米与盐的年代》一反以往“中国发现美洲”叙事中的乌托邦期待,将中国想象成推行殖民统治的霸权形象,体现的正是冷战思维下西方“中国威胁论”的意识形态。
李锋认为,或然历史小说创作者往往有“文化甚至意识形态上的考量,其中比较常见的是作者对当前社会现实的极度不满或担忧,通过描述一个梦魇般的世界,来达到讽喻当下、警示世人的效果”(2014:76)。尽管《米与盐的年代》中的中国形象以西方为原型,重述的是西方的殖民史,但“中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设想毫无疑问是18世纪特别是冷战后西方人眼中“梦魇般的世界”,是他们担忧的“威胁”。在小说中以东方为中心的世界,西方人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沦为东方人的奴隶,这无疑为西方读者敲响了警钟:如果一种文明不寻求进步,就很可能会被其他文明迎头赶上甚至取代,就像西方人曾毁灭性打击印第安文明一样。因此,罗宾森将中国书写为发达的强国形象,不是对中国的赞美和肯定,而是要对西方发起警示。
然而在发出警示的同时,《米与盐的年代》也表达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和信仰。中国扮演的正是一个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体的角色,在这一共同体中,展现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各种问题:种族、性别、殖民、科学、战争、人性、贫富不均、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等。在小说最后一章,借助中国历史学家之口,罗宾森将创造历史、建构乌托邦的责任和希望给予了历史进程中的普通人和普遍人性。历史是“一部人性斗争的浪漫史”(576)。历史的演变是人类共同为追求更好归宿的努力:“为了更进步更完善的社会,一代代人努力为公平而斗争,力求实现一个天下大同的梦想,这是一个长期的远景”(577)。实际上,对未来的展望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小说第七章中印度首领喀拉拉畅想:“让世界各地都成为花园,让一切都富足……不再有帝国、贵族,不再有贫富差异或个人财产……不再有部落和种姓的划分,不再有饥饿和折磨,所有的人在有生之年共同享受世界上的成果”(410)。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学生,罗宾森笔下这样一幅消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人人美好幸福的幻景正是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最好体现。无怪乎有批评家认为“小说本身是乌托邦式的”(Kneale, 2010:301)。
5.结语
在或然历史的空间下,《米与盐的年代》展示并预演了人类文明史上的重重问题和危机,塑造了先进而野蛮的中国形象。在小说描述中带有两种不同面孔的中国,既充当了文化他者的作用,映射出冷战思维下西方意识形态中“中国威胁论”的影子,也反映出当下全球一体化语境下西方学者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矛盾心理。中国成为世界的缩影,折射出东西方文明发展共同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无论历史发生怎样的分叉和转折,世界中心经历怎样的更迭和交替,只要霸权主义仍在盛行,社会公平遭遇破坏,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伦理道德逐步沦丧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人们共享和平、幸福、美好的社会愿景就不会实现。与此同时,只有人们能够摒弃偏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信念,容纳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和多元价值观念并存,才能真正建构起“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
注释:
①引文出自金·斯坦利·罗宾森:《米与盐的年代》,李玉良、刘建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以下出自该著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