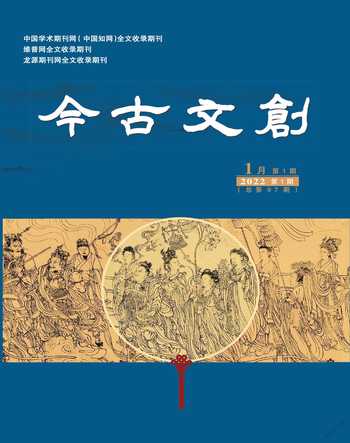山水与人生:谢灵运《游名山志》发微
丁琳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替,政治混乱,思想出现了空前的活跃。在儒教继续发展的大背景下,释、道二教也加入文化交锋。孔子的形象逐渐在历史中复杂化,老学的勃兴导致玄学清谈成为主要的文化活动,在学问上呈现出由人事到玄理的趋势。谢灵运处于熟稔汇通儒释道三教的南朝之初,《游名山志》作为山水游记散文,蕴含着他的学术观点和独特的人生观,颇能代表同时代一批文人的心声。面临“心”和“口”的矛盾,“出”和“处”的抉择,谢灵运选择遍游名山,书写山水以获得慰藉。谢灵运无论是在游历中体悟释、道二教之理,抑或是借山水的背景营造名士之风,都可见山水填满了他的精神空间,从中可观个人精神、生命意识在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关键词】 谢灵运;《游名山志》;出与处;魏晋之风;山水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1-0038-04
三国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战乱频仍,在此期间思想文化呈现出勃兴状态,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逐渐复杂化,士人在精神解放中获得了“人的发现”。同时随着学者对先秦经典“三玄”的不断探究,道家学术参与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交锋。其时清谈之风大盛,清谈上承汉代的清议,最终演变为关于玄学的清谈,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老学的影响日显,其二由具体人事到玄理也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1]更有逃避时事,探究、辩论、品评的原因。
清谈从魏初到刘宋两百年间,玄风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文人们论辩之中也可见儒家名教思想或隐或现地藏于谈论之中,到谢灵运时,较能明显地感受到儒释道三家的交相渗透。其时文学多写山水,因为山水可以探索生命之本源,写尽自然造化,因此有所谓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2]。谢灵运处于熟稔汇通儒释道三教的南朝之初,其著作蕴含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内涵。
学界对谢灵运的玄理山水诗、佛道哲理论文研究较多。谢灵运哲理思想滥觞于汤用彤,他认为谢灵运《辨宗论》“其中提出孔释不同,折中以新论道士(道生)之说”,包含了两个基本的问题,即:“佛是否可成,圣是否可至;佛如何成,圣如何至。”
《游名山志》是谢灵运的游记体著作之一,散佚于宋朝,散见于《文选》李善注、《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古书中。后世学者不断辑录,但由于条文较少,学界关于《游名山志》的讨论不多,张兆勇在对顾绍柏辑录的《谢灵运集校注》做笺释时简要分析了《游名山志》 [3]。
一、《游名山志》及并序
谢灵运失意于家族的衰落,仕途不得意,之后游历名山大川,结交文人僧侣,留下了不少山水诗赋的佳作,其中最著名的大赋当属《山居赋》,另外还有《游名山志》和《居名山志》两部游记体著作。《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三“地理类”中,谢灵运名下有《居名山志》一卷,《游名山志》一卷,这是两部著作最早的记录。《游名山志》作为一篇早期的山水游记散文,与他的其他作品相比,褪去了“藻丰论博,蔚然满目”的华丽,语言清新质朴,毫无雕琢。
现存的《游名山志》大约涉及永嘉、东阳、会稽、临川四郡,包括横阳诸山、楼石山、石室山等名山,神子溪、强中(强口溪)、新溪等秀水,以及临江楼、南门楼等名胜。本文重点分析《游名山志并序》,为方便讨论录全文如下:
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俗议多云,欢足本在华堂,枕岩漱流者乏于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谓不然。君子有爱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横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己以济彼,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邪!语万乘则鼎湖有纵辔,论储贰则嵩山有绝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愿辞汉傅。推此而言,可以明矣。[4]
世俗意义的欢乐富足只有高居庙堂才可达到,而枕岩漱流的隐士却总是胸无大志,所以不免神形枯槁。谢灵运并没有遵循世俗,他认为真正的君子虽然会有世俗的感情,也应有入仕力挽狂澜的能力,所以处在灾祸乱离的年代,只有真正的君子雄才才能施展其能力,挽救国家于危难之际。这种行为是“屈己济彼”,所谓的“己”所说就是前面的“山水”“性之所适”,离了本性去济物达仁,进到官场之中大展身手。他以这样的论证反驳世俗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是名利场上的人并不比隐士更贤能。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并没有要贬低“名利之场”而抬高“清旷之域”,他只是以此论回应世人重彼薄此的看法。
这篇小序隐含了三个层面的观点。其一,心与口、山水与物质的轻重之别。其二,君子居庙堂(出)和处旷野(处)的分别。其三,山水玄学对于人生的助益作用。
二、知人论世:谢灵运的失意人生
此书现存辑录的条文中可见干脆利落的记录文风。作为一本游记,《游名山志》上承《山海经》中的奇瑰想象,这散见于一些条文之中,例如:“龙须草,唯东阳、永嘉有。永嘉有缙云堂,意者谓鼎湖攀龙须,时有坠落,化而为草,故有龙须之称。”[5]此用黄帝鼎湖升仙,乘龙垂下的龙须解释龙须草的得名来由。除了偶有奇诡之想象,《游名山志》的其他条文都是冷峻的记录之笔,以说明文的方法呈现出游名山所见的风物,较少想象与评论。对于名胜所处方位的细节性描写显出文笔严谨,写南门楼:“始宁又北转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园南门楼。自南楼百许步,对横山。”写神子溪:“神子溪,南山与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涧数里。”[6]
谢灵运(385年—433年),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谢玄之孙,世袭爵位康乐公,后世称之为谢康乐。由于晋宋易代,谢家受到政治的风波,谢灵运多次易官,永初二年(421年)之前是谢灵运仕途最得意的一段时间,他还有机会侍奉君侧。直到少帝上位(422年),谢灵运因所在党派与权臣徐羡之等人嫉妒,被调出京都,出任永嘉太守。一年以后谢灵运辞官归隐始宁。元嘉三年(426年)文帝掌权之后,谢灵运被征为秘书监,负责整理秘阁图籍,編纂《晋书》。两年后告归始宁,以恣意遨游被免官,重归山林。元嘉八年(431年)孟顗诬告谢灵运谋反,后经文帝核无此事,起用谢灵运任临川刺史,后又因不理政务被流放,不久谢灵运因谋反的罪名,于广州受刑弃市。
纵观谢灵运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见其坎壈的一生,自第一次免官之后,他在政治上也不愿为官得人,任职时十分消极态度,只见其交游好友,吟诗作赋,但他心态是沉郁痛苦的。他在游历期间写了不少佳作,排遣心中块垒。山水于谢灵运而言已经超越了本身,引山水入诗更是抒写万物之本源,是虚无之有,寂寞之音。汤用彤先生认为写自然之造化是为了接近人生。“人生遭不可抗之命运,何以自遣?”“文章本为遣怀,抒发怀抱而有,故《文赋》‘遵四时以叹逝’。”[7]
三、抉择:居华堂或游名山
由清议演绎成的清谈发展出十分系统的评骘人物的标准。汤用彤先生认为魏晋名士的谈论中心问题就是“理想中的圣人人格究应该怎样?”刘邵《人物志》就是汉代品鉴风气的结果。“其所采观人之法,所分人物名目,所论问题,必均有所本。”[8]自东汉党锢之祸以来,曹氏与司马历世猜忌,士大夫恐怕祸及自身纷纷由具体时事转向玄远的哲理。直到元康年间,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及人生经历中,能感受到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孤怀独往、直面现实而又追求玄远之境界的关切”[9]。永嘉时期,郭象、向秀以注《庄子》而名重天下,他们主张儒道合一,认为“名教”合乎“自然”。西晋末期大盛的佛学是与玄学同调,将“名教”与“自然”再次分开。谢灵运处于东晋末期,自然深受佛学的影响,然而整个时期有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名教”实际上潜伏于士人的内心,在他们人生处世时发挥着若隐若现的影响。
谢灵运在《游名山志序》中强调“君子有爱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横流之弊,非才不治”。可见他从本质上是不反对儒家提倡君子济物达仁的标准,而是认为儒家崇尚的“名教”有悖于君子本性。谢灵运的文学作品中也有类似体现,《从游京口北固应召》围绕第二句“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10]展开,即以为性理需要名教实践,大道要汇通神明方可认識。由此看来,他认为回归自我和为名教所用是可以达成统一的,是人生两种不同的状态。收录在《乐府诗集》的《鞠歌行》以“德不孤兮必有邻”开篇,表达自己渴求引荐的心情。在一些诗歌中反复表达修德的意愿和修德不成的遗憾,儒家思想对谢灵运有潜在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所认为的“德”并不只是传统儒家的道德,而是蕴含着道、释两家的内涵。谢灵运有《述祖德二首》,述祖上之德,这种德具有儒道两种人格精神,祖上“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氛”,功成之后“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谢灵运的认为德“包含了能力、品行和人生态度”[11]。作为贵族子弟,谢灵运始终对儒家的礼乐教化怀有崇敬之情,出守永嘉之后他曾积极作为,《种桑》一诗便能体现他怀有的教化民众之心。虽然在任期间他常不理政事,狂歌纵酒,但其心中常常觉得惭愧。“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登池上楼》)一“愧”一“怍”便是明证。在辞官隐退期间,他认为最理想的人生选择就是功成身退,寄情山水,但其心中常怀修德不成的遗憾。这样看来,谢灵运难以知行合一,在“出”于“处”的摇摆中走完人生悲剧的四十七年。
西晋陶渊明与谢灵运比较来说,关于“出”和“处”的态度明显不同。世人公认“陶诗以自然为贵,谢诗以雕镂为工,二家遂为后世诗人分途”[12]。谢灵运在为官与归隐的纠结中走完一生,虽然身处山林之远,心中时时怀着郁郁不平的情感,诗作工于精巧,足见他谨小慎微、敏感多思的性格。由于谢陶心态的明显不同,二者对于自然山水的观念也有较大的差异。山水之境对于谢灵运是一个营造自由之场,排遣苦闷自我安慰的场所。而对于陶渊明来说山水自然则是精神归宿,因此“陶公无须夸耀他对自然的喜爱和亲近,而那种真实的亲和之感与喜悦之情却无处不在”[13]。
四、游名山所得:玄理与慰藉
(一)山水入诗得玄理
汤用彤先生认为“自然”有三义:第一玄冥,是自然的非人为的,最初的境界,在本体上无分别、无生死、无动静、无利害。因此在精神上非常自由,无礼法限制。第二义是法则秩序,天地自有纲纪。第三义是和谐,符合天地之性,自然之理的混沌不分状态。时人对自然的追求体现在他们的诗作画作之中,就当时绘画可以看到魏晋时期画作由人物画向山水画的转向,他们作画更注重传神而不是摹状“人物之神以山水语言代表,以此探生命之本源,写自然之造化”[14]。
“感”是魏晋士人勾连外界的通道,如何更好地寻求玄理,成为时人不断求索的中心论题。“三玄”中《易》有“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15],“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物交感之论,《老》中有“敛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16]虚静之说。“物”实“情”虚,在“感”的作用下融通二者,这需要以“象”为媒介,当人对选择将自然物象作为媒介,将自然山水看作玄理的载体。这也是出现魏晋玄言诗大盛,“迨元嘉间谢康乐出,始创为刻画山水之词”[17]转变之因。“神”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心物交感,常呈现为持续运动方式的“游”。当二者打通时,文思已成熟,刘勰的“神与物游”即此意。
和其他魏晋文人一样,谢灵运写诗更注重言外之意,追求上乘之文所体现虚无寂寞,大象无形的境界,因此他能用简单的山水体会出玄远的意境。文人的玄言诗用寻常的物或言,指示玄远“此种语言,指示而有余,意在言外”[18]。类似月、筌、鱼、蹄等意象在魏晋诗歌中具有无限的象征性意味,自然山水与其说是作为被诗人描写、赞美的对象,毋宁说是作为媒介或喻体而存在,然而谢灵运诗中的玄理从表达方式到含义上已超越了玄言诗。
山水是诗人内心境界的体现,《游名山志》成书期间,他游历于山水之间,有寄情山水的用意。在成书的同时期,谢灵运写了很多山水玄言诗,其中多有提到游历所见之景。所得玄理禅意皆入诗之中,谢灵运《游名山志》云:“永宁、安固二县间,东南便是赤石,又枕海。”此时他作诗记录游览赤石之感:“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游赤石进帆海)这一句已经超越了风景本身,联想到崇尚空名不足为道,万事万物皆是虚妄。
(二)藉山水以化其郁结
谢灵运游历期间写下的诗文虽拖着玄言诗的尾巴,但也充分展示了其个人意识的萌发,对于个人情绪的描写不为少数。在经过斤竹涧时,谢灵运想到山鬼,写下《从斤竹涧越岭溪行》: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苹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这首诗大半部分描写一路所见的景色,最后四句才加入谢灵运的观感,取意于《楚辞》《九歌·山鬼》篇:“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薛萝兮带女萝。”“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19]谢灵运由山鬼联想到感情是以互相赏识为至善至美,这种事不能用言语说清楚。观览沿途的景物,便抛开了尘世的各种烦恼,最后一个“遣”字点明了诗人的心境,也总括了谢灵运游历名山之动机。借山水排遣郁结的胸怀,引玄理入诗的最终目的也是一个“遣”字。
郭象《庄子》注:“将大不类,莫若无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于无遣,然后无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20]观魏晋之风,名士风流,放浪形骸,其中出于逃避、排遣、疏解苦闷情绪,佯装放达之士人不为少数。笔者不否认谢灵运以审美的眼光陶醉于山水之间的可能性,但观诸篇游历山水诗作,我们可以获知其中浓厚的哲学关照,写山水自然甚至有套路化的倾向。原因有三点:
第一,谢灵运诗中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是单一的景色,画面之中缺少人与自然的互动。虽然他多次表达醉于山水,如《石寺山》中云“灵域久韬隐,如与心赏交”,《过白岸亭》云:“援萝聆青崖,春心自相属”,但这种互动不过是神理相交的一种表现。
第二,他的行旅诗很少对山水的细致描写和刻画,主要是具有整体性陈述,其中不少是以昏旦气候作为诗歌的首句,以玄理结尾: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杳杳日西颓,漫漫长路迫……搔首访行人,引领冀良觌。(《南楼中望所迟客》)
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富春渚诗》)
诗中对于山林、岩石、云雾、川渚的描写都没有呈现出个人化的色彩,难证谢灵运于自然山水中获得审美体验。
第三,谢灵运眼观景物时,不是以赤子般的摹状眼光去发现,亦不是觀之以情绪之眼,而是夹带着厚重的典籍意识,因此看山不是山了,而是《诗经》《楚辞》、魏晋“三玄”中的景色。“别时花灼灼,别后叶蓁蓁”(《答谢惠连诗》)一句巧妙化用了《诗经》的“灼灼其华”“其叶蓁蓁”[21]二句,但已失花叶原貌。
当山水已不是山水本身时,便变成了一个概念符号,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谢灵运尽管刻画得如何繁复细腻,自然景物却并未能活起来,他的山水诗如同顾恺之的某些画一样,都只是一种概念性的描述,缺乏个性和情感”[22]。仕途不顺的谢灵运旅居于山水之间,从此中获得间接的慰藉,虽心中所想并非眼前所见,山水能为流泻其心中的郁闷提供路径。通过山水写玄理,另一方面也是谢灵运不断地自我安慰,企图说服自我的一种尝试。在诗文中故作洒脱是一种情感需求,不断向世人强调自身某种品质,恰恰因为缺少这种品质。
在崇尚自然的时代背景下,游历山水为谢灵运提供了身份认同,尽管这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当山水这意味着精神自由的空间填满了他生命的时间时,他失意的人生就得到了意义的装饰和价值的提升。”[23]他在游历期间留下了不少诗赋、游记,和精通释、道的好友交游,使他对佛学和玄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五、结语
细读谢灵运《游名山志》,在面临“出”或“处”的抉择时,谢灵运展示出了他儒道兼通的思想,既渴望建功树德,又想枕石漱流,不愿“屈己以济彼”。“穷者欲达其言,劳者歌须其事” [24],在仕途不顺时主动或被动地辞官归隐,他感到深深的愧疚,他诗歌流露出深玄学哲思,隐藏着迫切想要排遣的忧思。他在永嘉任太守时不理政务,“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25],导致被弹劾,可以说谢灵运的命运悲剧是不仅是历史遗留问题,还要归咎于他的不作为。用怀有“温情与敬意”的眼光回顾,也许能体会到谢灵运亲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26]时,他的落寞和不甘。
谢灵运遍游名山是一种倾泻苦闷、浇灭心中块垒的尝试。无论是在山水中悟得玄理,还是在游历中体悟释、道二教之理,抑或是借山水的背景营造名士之风,山水填满了谢灵运的精神空间。当山水变成象征性的符号时,美感会消遁无踪,审美感受被人生哲思无限压缩。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以来不断发展的个人意识、生命意识从未停止,谢灵运的诗作就是一个佳证。他是玄言诗向山水诗过渡历程中的代表性诗人,不少人认为,后世的山水诗皆滥觞于此。
参考文献:
[1]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明诗第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67.
[3][4]张兆勇.谢灵运集笺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5]姜剑云,霍贵高.谢灵运新探与解读[M].北京:中华书局,2018:171.
[6]张兆勇.谢灵运集笺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72.
[7]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127.
[8]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11.
[9]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9.
[10]谢灵运著,李运富编注.谢灵运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9:85.
[11]姜剑云,霍贵高.谢灵运新探与解读[M].北京:中华书局,2018:186.
[12]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上编)·陶渊明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9.
[13]蒋寅.超越之场:山水对于谢灵运的意义[J].文学评论,2010,(02).
[14]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2.
[15]梦远.图文全解《易经》[M].上海: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238.
[16]老子.道德经[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74.
[17]王士禛.双江唱和诗序//渔洋文集卷二,王士禛全集第3册[M].济南:齐鲁书社,2006:1542 .
[18]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4.
[19]屈原著,刘向辑.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97.
[20]庄周著,郭象注.庄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4.
[21]方玉润评.诗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0.
[22]李泽厚.美的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76.
[23]蒋寅.超越之场:山水对于谢灵运的意义[J].文学评论.2010,(02).
[24]庚信著,舒宝章选注.庾信选集[M].开封:中州书画社,1983:167.
[25]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10:1753.
[26]刘禹锡.刘禹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