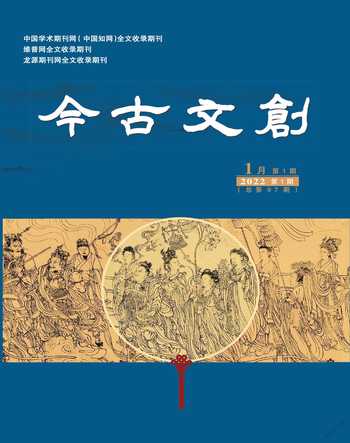对余华小说“死亡美学”的探讨
【摘要】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往事与刑罚》,从《在细雨中呼喊》到《第七天》,余华做出了巨大的改变,但却从未停止对死亡的观察与书写。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看待死亡的目光显然与以往大不相同,死亡不再只是先锋小说中极端的形式,人们能够从后期的死亡书写中体会到美感。死亡作为文学的永恒母题,具有无限的探讨价值。本文将结合《在细雨中呼喊》这部转型之作,对余华小说的死亡美学从形式及意义双层角度上进行深入探讨,旨在剖析其对死亡的艺术化处理方式及其构建全新的死亡意义,并由此加深人们对死亡的认识与理解。
【关键词】 余华;死亡美学;《在细雨中呼喊》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1-0004-04
基金项目:2020年度广东省“十三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典文学疾病写作与疾病隐喻的人类学研究”(GD20CZW03)阶段性成果。
近40年的创作生涯里,余华始终穿梭、游荡于文学的幽静森林间。从前期小说的暴力、毁灭、冷酷到后期小说的苦难、温情、关怀,余华做出了巨大的改变,但却从未停止对死亡的观察与书写。然而,余华前期的死亡书写是不够美的,那些描写所带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排斥与不适感,读者难以在先锋化的死亡中构建起对生命力量的敬重和对死亡本身的豁然。但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逐步从“上帝”的位置上卸任,他变成了村庄绿树下一个叼着烟的陌客,甚至成了主人公本身。尽管意外的死亡和荒诞的死法未从他的作品中消逝,但他看待死亡的目光显然与以往大不相同了,死亡不再只是极端的形式,人们从后期的死亡书写中体会到一种超越了生命、跨越了空间的永恒之美。
一、直面死亡
死亡主题并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属。自原始社会起,人类作为生命个体已开始接触与关注死亡。但原始社会形态下的人类对于死亡的认知更多地建立在死亡恐惧与超自然力量之上,将死亡赋予神话气息。先秦时期,道家、儒家对生命与死亡的探讨以时间意识表现出来,并表达着对生命短暂、生死无常的感叹与惋惜。但道、儒在死亡问题上的出路并不相同。道家在“人固有一死”的认知中建立起了循环时间观,相信永生的可能性,死既是生命的终点,在循环的状态下也将成為生命的起点,而生死的转换是极其容易的。儒家则以伦理的规则来追求生命延续,坚信宗族血脉的传承使个体生命与灵魂永在。同时,儒家显然比道家更追求死亡价值,这与儒家集体意识有一定关联。从原始到先秦,人类都在有意识地模糊生与死的界限,并致力于传达出死而复生、长生不死的观念。但毋庸赘述,这些观点与论述实际上并不是就死亡本质进行探讨的产物,它是为生而存在,借以消除死亡的不可抗拒及其带来莫大的恐惧感,因此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生死观是逃避、避讳死亡的。余华自早期写作先锋小说时,便已开始对传统生死观进行彻底性的反叛,那时他将重心放在对死亡过程的生理描写上,以给人们带来强烈的感官冲击,增强死亡的存在感。但对死亡形式的过分追求极易泯灭死亡的意义与价值,死亡书写如同机械化的文学工具。不过,这足以说明余华打破了传统框架,对死亡的探索不再望而却步。到了后期,余华在转变创作风格的同时自然也改变了书写死亡的方式及对待死亡的态度,他的叙述不再咄咄逼人、锋芒毕露,但这并不意味着死亡视角的转换,他仍然在正视、直面死亡,并热衷于通过死亡来剖析惨烈的人性与现实。
在《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中,大量的死亡情节充斥文本,死亡的方式与起因、对死亡事实描述的角度都不尽相同。在对孙光明的死亡描写中,余华以旁观的视角理性、客观地交代出死亡当下的环境及其他人物的情节:孙光平扔掉镰刀奔出屋外、孙广才从菜地急步跑向河边、母亲的头巾随着她的奔跑上下舞动。在整段死亡故事里,余华并未留恋于死亡即刻的叙述,他贡献了更多的笔墨去详细描写父亲孙广才及哥哥孙光平面对孙光明之死的态度转变。孙光明的意外死亡最先给父子俩带来的是生理上的疲惫,他们背着孙光明的尸体一路向着家的方向奔跑,因为过度劳累而呕吐不止。然而当被孙光明拯救了的八岁小孩的父亲上门赔罪时,孙广才与孙光平竟没有表现出一丝歇斯底里的悲痛,而是要求报道孙光明的“英雄事迹”。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孙广才都在以“英雄”父亲的身份自居,企图获取儿子“舍己为人”般死亡所带来的名誉和荣耀。
在对苏宇的死亡描写中,余华便进入了当事人的身体里,对死亡当下的状态与感受作了极为细致地刻画,将苏宇弥留之际的状态以上升、下沉来表述,其死亡过程仿佛被无限延伸。对冗长的死亡过程的叙述、诗意性描写死亡感受,是对死亡本身最直接并富有美感的探寻。就死亡方式而言,《在细雨中呼喊》既描述了孙广才失足掉进粪坑、曾祖母被野狗吃掉的意外之死,也叙述了祖父孙有元、苏宇的宁静、平和的死亡过程,甚至花费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围绕着孙有元风烛残年漫长的自然死亡安排了一场孙广才与孙有元的父子之战。
从早期先锋小说到转型之作《在细雨中呼喊》,再到巅峰时期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余华没有在哪一部作品里彻底抛弃死亡。哪怕当他的目光逐渐柔和下来,他放弃了极端、暴力的文字,转而关注苦难与现实,他都没有试图挣脱死亡书写的怀抱。对于余华而言,死亡从来不是水底下充满危机的暗潮,它就像一池清泉,开放而澄明。只有当人们真正直面死亡、探索死亡,才能由死观生,也才能以对死亡的通透理解构建起死亡之美。
二、死亡的审美体验
从科学意义上讲,死亡乃世间万物的归宿。然而,生命的彼岸如何状,濒死之时是何感,却并非活着的人所能经历与洞晓。因此,死亡充满着未知,而未知带来了不可名状的恐惧。被恐惧气氛所笼罩的死亡成了探索的禁地。余华在20世纪末创作先锋小说时率先打破了这种死亡描写的僵局。不过,虽然余华热衷于端详自己笔下人物的死亡状态并对其死亡过程进行详细描绘,但他的死亡书写并非一直是充满美感的。
在《死亡叙述》中,余华极端冷酷的死亡描写、对暴力的迷恋和掌控近乎登峰造极。他在描述小说主人公“我”的死亡过程时这样写道:“……镰刀像是砍穿一张纸一样砍穿了我的皮肤,然后就砍断了我的盲肠……于是里面的肠子一涌而出”,镰刀的铁刺接下来割穿了肺部与心脏的动脉,血液如同洗脚水一般倾泻而下。余华这一大段描写,加以对人体组织器官名称的运用,从腹部、肠子到肺、心脏,被杀害的过程极富节奏感,就像是冷血法医轻盈地拿着手术刀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解剖活动。结尾处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了。”伴随着主人公血尽而亡,死亡的叙述也走到了终点。诚然,从死亡表现空间上看,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扩展与突破。对死亡“步骤”的逐步描写,直接将读者投掷到了死亡现场。但也就是这样粗暴、极度冷静的方式,却很难带给读者有关死亡的审美体验。读者从文字中仅能产生生理不适感,或间接感受死者的身体痛苦,但心灵层面却得不到对死亡的体悟与超越,也难以平静地对死亡过程进行鉴赏。
《世事如烟》中,余华在描写女子自杀过程时,其用词显然不如《死亡叙述》那么残酷、犀利。他将女子走向江水更深处、水慢慢盖过身体的状态描述成“穿上一件新衣服”,其死亡状态便也如潺潺流水般安然、平缓。
在《往事与刑罚》中,余华以冬日纷纷扬扬的雪、杂草丛生一般的月光等意象,来对酷刑之下的残暴与血腥进行褪色。这些对死亡艺术化的处理,在减轻死亡痛苦与恐惧情绪的基础上,给读者带来了错位的审美感受。而死亡作为一直以来被遮蔽的存在,也能够以美的形式更加光明地为讀者所接受,并显示出其自身的完整性,以此构建完整的美感。
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超越了自己原先设定的先锋框架。其中对苏宇之死的描写,已在极大程度上做到了死亡表现空间拓展与死亡审美体验的统一。苏宇在清晨因为脑血管破裂而陷入昏迷,正向死亡的深渊坠落着。苏宇听见父母在卧室外的走动声,感到自己下沉的身体似被微风托起般上升,然而他的万分虚弱使他无法做出回应,于是当父母只是责备苏宇为什么不像以往一样起床打水时,“苏宇的身体复又下沉,犹如一颗在空气里跌落下去的石子。”弟弟苏杭对哥哥的“关切”犹如“最后一片光明的涌入”,伴随着“门的关上”,苏宇的生命之门也彻底被铐上枷锁。在经历了漫长、挣扎的死亡过程之后,苏宇的肉体如同被微风吹散般“化作了无数水滴,清脆悦耳地消失在空气之中”。
余华擅长于对死亡进行想象性呈现,无论是以旁观的姿态叙述死亡场景与画面,还是成为死者本身表露死亡感受,他都如同生与死之间的摆渡人一般,掌控着所有死亡的信息,并始终以各种方式将这类信息传递给读者。
在对苏宇濒死状态及死亡全程的细部描写中,读者几乎看不到先锋余华的影子,他的目光是那样平和、笔触是那样轻盈以至于苏宇的死亡如同一片绿叶被风从枝蔓上轻轻刮落,而下落的过程又极其自然与缥缈,仿佛苏宇不是死了,只是酒醉在了美丽的梦里。通过这样的描写,读者似乎随着苏宇下沉、上升,感受着生命最后一刻时光的照耀,也感受着黑夜里的宁静慢慢将身体包裹,但这种感受并不痛苦。余华在自己构建的世界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生命的旅行,他好像在这片大地上存活了几万年,甚至能够越过时空亲临生命彼岸。他以诗意的方式叙述死亡,就像从亡灵世界里捧着无数朵孕育着人类灵魂的花朵走到读者身前,读者在流萤纷飞中观望着花蕊里跳动的灵魂,倍感圣洁与心安。
当死亡被余华蒙上一层美的面纱,人们对所谓生命终结将更加释怀,对死亡本身也将建立起美的体验与感悟。
三、消解死亡意义
面对必然的死亡,道家谈“生死齐一”、儒家论“舍生取义”、佛家信“生死轮回”。为应对人类生存困境,古人始终探寻着死亡意义,以“死得其所”作为死亡的理想境界,借以化感伤、恐惧为释然。余华从创作之初便是传统的叛逆者,既然传统放弃死亡本身而追求“虚无”的意义,那么余华就在反叛路上让死亡意义无处可寻。在其创作生涯中,川端康成、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是巨大的。余华从川端康成的文学里建立起了对死亡之美的认识,又在卡夫卡的笔下解放了死亡的写作方式。
在《乡村医生》里,“我”遭遇着各种离奇、怪异的困境,受制于非常规的情境中,驾着一匹“神”马,漫无目的地在不归路上游荡。人物行动的无意义、死亡的无意义不仅是卡夫卡对人物异化的结果,甚至是对生存观、死亡观的扭曲与消解。从先锋走向现实,余华在其创作的40年里进行着文学试验,也陷入过写作困境,但卡夫卡式的死亡书写始终如影随形。
余华前期对死亡意义的消解较后期更加直白、残暴。《一九八六年》里的疯子在自己的人生里自导自演了一部血淋淋的恐怖片,为自戕而尝试各种酷刑。他提着冰冷的钢锯对准了自己的皮肤,皮肤在诡谲的电锯声中被锯开,“被锯开的皮肤先是苍白地翻了开来,然后慢慢红润起来,接着血往外渗了”。他的自戕过程于他自身而言,或许仅如一场愉快的游戏。而死亡的意义在疯癫、痴狂的状态下,也就消失无踪、无法追溯。
自《在细雨中呼喊》起,余华开始了其写作视角与形式等多方面的转变,然而他对死亡的迷恋却未减少分毫。当他学会以善的目光和悲悯情怀去对待自己笔下的人物、社会乃至人们生活的现实,他仍然在尽力消解死亡。当然,消解的方式同前期大有不同。
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他对孙广才的死亡描写颇有“黑色幽默”之意味。孙广才是在一个黑夜里喝醉酒掉入粪坑而死的,当天晚上曾被醉醺醺的罗老头误认成一头猪。当罗老头用麻绳将孙广才打捞上来时才发现“猪”的真面目,他破口大骂,一脚将孙广才踢回粪坑。等到翌日清晨孙广才被人们发现时,“他俯身漂浮在粪水之上,身上爬满了白色的小虫”。孙广才作为整部作品中贪婪、无耻的代名词,其人性如他的死亡地点般脏污狼藉。然而,当人们基于对孙广才的认知看待他的死亡,死法的荒诞、死亡的意外却消解了读者对人物的厌恶。在充满滑稽感的死亡情境中,死亡感伤作为死亡带来的最普遍的情绪也将被诙谐、幽默所取代。
余华将死亡装饰成马戏场里正在上演的一场喜剧,人物陡然变成聚光灯下的小丑,但人们却更加关注舞台的内容与形式,至于“喜剧”本身的意义,并不是观众在意的重点。如果人们将这种意外死亡看成是命运的把戏,那么从“宿命论”的角度看,孙广才不过是命运的一个符号,他的死亡甚至不能够被其自身把控。如此一来,死亡意义也就更加虚无。
余华对死亡的戏剧化处理,让死亡从金字塔的神秘顶端坠落,同沙砾相融,死亡也就变成了人们摸得着、看得清的事物。
四、重构死亡意义
死亡在余华的笔下跌落神坛。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尝试着挣脱先锋的牢笼,但其内在的先锋品格始终存在。他在关注现实、命运与人性的同时,唤醒了自己的生命意识,并试图构建起全新的死亡意义。纵览其创作生涯,存在主义对余华的影响显然是深刻的。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本身是无意义的,是在自我塑造与成就中逐渐获得意义。存在主义的悲剧论认为,社会充满了丑行与罪恶,世界氤氲着苦难、冷漠与悲观,人生绝望不堪。人生活在如此处境之中,面对未来混沌而无目标,人们唯一知道的,即人生的真实终结是死亡。也就是说,死亡作为迷乱世界里可靠的风向标,能帮大家确认自我,从而建立起存在的意义。那么在这样的视角下,中国传统观念里的死亡意义成了一个伪命题——人们并不是为意义而死,是死亡给予了人们意义。当然,存在主义是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其内部本身也存在许多分歧与冲突。在这其中,余华似乎更倾向于将死亡看作是人脱离现实苦难的捷径,能够带领人们重获新生与自由。这一观点十分接近于海德格尔所信仰的“向死而生”。
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的死亡意识集中体现在以“一劳永逸”评价死亡事实之上,余华在描述死亡时至少在四处使用了“一劳永逸”一词。小说开头描写的第一处死亡即孙光明之死,作者在这里首次使用了“一劳永逸”来形容孙光明的死亡——“孙广才以为孙光明是口中吐水,那时他还不知道孙光明已经一劳永逸地离去了”。脑血管破裂的苏宇听着卧室外父母走动的脚步声,感到自己的身体被微光拉扯上升,他“躺在一劳永逸之前的宁静里”,无声地发出求救。而在孙有元与孙广才围绕死亡而起的拉锯战中,孙有元早已感到自己的灵魂已经离开肉体,他迫切地期待着“自己的生理也进入一劳永逸的境地”。
对于余华而言,所谓“劳”便是人们活着的现实。人们活着,不过是承受着人生劳苦,遭遇着命运的玩弄及其带来的惨烈打击。生存本身充满着荒诞与绝望,人类沿着命运的轨道奔跑,反抗的力量微乎其微,甚至会因追求生存尊严而陷入灾难深渊。当人们挣扎一生走向死亡,便可以享受死亡所带来的“永逸”。似乎在死亡中,人们才足以逃离命运的奴役,真正在一种虚无缥缈、无所关联的状态下达到自由。死亡帮助人们找寻自我,确认存在,其意义也在此过程中得到重构。在余华的死亡观念里,死亡与自由存在着极强的联系。
对于个体而言,人们终其一生所要追求的,即是在消除死亡恐惧中超越死亡,以“生”为路向着“死”而进。当人们已知死之必然,并能够直面死亡时,人们便足以在生的有限中观望自我、理解自我,不再一味眺望着生命结果而畏惧前进。余华所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在经历了对时空、生命、万物本质的思索之后,超越物质束缚而确立起精神归宿的美好、纯净的品质。
五、反思与总结
在余华后期创作中,随着他对命运的关注及对世界本质的剖析愈发深切,他似乎又步入了另外一条歧路。他痴迷地窥探着现实,每探一尺,现实的荒诞性就在他眼前暴露一寸。从《活着》开始,余华笔下的人物无不经受着现实苦难的践踏,并走向不幸。但最初这种苦难还受制于一定的空间范围,人物所遭遇的灾难大体上根源于个人命运。但到了《兄弟》,这种情形便不受控了。李光头和宋刚被淹没在了时代洪流中,与其说是个人命运的驱使,反倒更像是整个时代所造就的荒诞与悲哀。人物在一种近乎疯癫的集体狂欢中如行尸走肉,个体的精神连同肉体一并麻木不仁。然而,无论苦难以何种形式出现,他笔下的人物都还是颤颤巍巍地接受并忍耐。如果说《在细雨中呼喊》里不顾一切、奔波万里寻找母亲的鲁鲁让读者看到了反抗者的姿态,那么余华往后的小说里,这种角色已难以寻觅。他们大多被命运牢铐着,在苦难中隐忍着,面对无比荒诞的现实,便绝望地融进车水马龙,潜身于酒池肉林。当人物蒙受灾难却不做出抗争,与现实发生冲突却选择退让,悲剧精神也就无影无踪。在如此情形之中,死亡之美该如何呈现?人们还能谈死亡的美吗?当人类一味掉落进更荒诞的深渊,在命运的掌握下难以超越自身,精神达不到解放的状态,死亡之于存在的意义就不够重要了。毕竟人们理解死亡美学,找寻死亡之美,终归是为了参透人们活著的现实,并在有限的人生里创造永恒的价值与无限的意义。
诚然,在余华的死亡美学中,死亡内涵已获得了极大丰富,并且在对存在的探讨上,他已超越了许多人。他解放了死亡的书写方式,拓展了死亡的想象空间,人们一次次地在他搭建起的村庄、巷子、街口、房屋内目睹着各种人以不同的方式死去,并获得了直面死亡的勇气。余华一头撞破了现实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的假象,但他又似乎太过于纠结其中而忘却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力量与魄力,缺乏对人类出路的探寻。不过,他的死亡美学仍然如明珠般宝贵,对人们理解生命、理解世界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余华.余华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2]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张清华.死亡之象与迷幻之境——先锋小说中的存在/死亡主题研究[J].小说评论,1999,(01):27-34+8.
[4]余华.我的文学道路——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J].当代作家评论,2002,(04):4-19.
[5]张瑞英.论余华小说的宿命意识[J].山东社会科学,2005,(07):94-97.
[6]张瑞英.论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J].文史哲,2006,(03):95-101.
[7]李建,朱焕.余华小说对传统“死亡”命题的变革与承继[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116-119.
[8]金秀贞.探寻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D].浙江大学,2007.
[9]洪治纲.绝望深处的笑声——论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02):1-6.
[10]李菁.存在主义死亡观的美学阐释[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0.
[11]王永兵.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与新时期小说审美范式的变化[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7(02):21-28.
[12]张若星.余华作品前后期关于“死亡”主题的语言变化探析[J].西部学刊,2016(09):25-28.
[13]解亚姣.余华小说中的死亡问题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6.
[14]涂昊.从暴力到温情的变奏——余华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关系研究[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39(04):92-97.
作者简介:
王婕婷,女,汉族,广东深圳人,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2019级本科生,网络与新媒体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