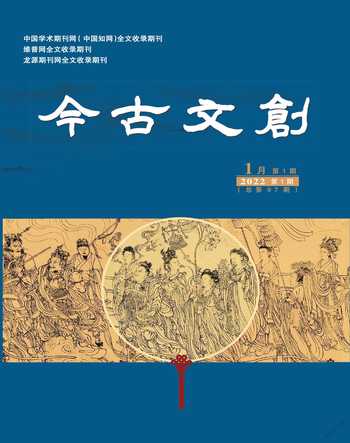病迹学在文学评论中的应用
【摘要】 本文简述以弗洛伊德潜意识研究为基础的精神分析学如何应用于文学批判,通过精神异常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文学创作对精神世界的反作用的过程,可以借用对角色的精神分析实现对角色人生轨迹的分析和结局的预测,给文学批评提供鲜活的有迹可循的资料。本文以夏目漱石末期三部曲《心》为例,分析角色K走向自杀的必然性。
【关键词】 病迹学;夏目漱石;精神分析;文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1-0014-03
病迹学早在18世纪末便已作为研究成为体系,病迹学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繁盛,近十年来进入中国学者视线,作为精神病学研究手段有所涉及。作为文学研究手段分析作家、作家笔下角色使用的相关研究寥寥可数。病迹学虽起源于欧洲,但在日本发展繁盛,日本学者对于日本文学家利用病迹学手段的研究已成规模且有独立体系。本文试图解析病迹学作用于文学批判的原理,以夏目漱石后期三部曲中《心》为示例进行解读。
弗洛伊德和荣格认为文学本质来源于潜意识,二者关于潜意识的研究成为病迹学研究的基石。本能潜藏的力比多的释放可能会对外部世界和自身产生伤害。如夏目漱石后期三部曲《心》中塑造的角色“先生”。彭吉[1]将先生失败的根源总结为自我本我超我的失衡,前期本我控制自我导致先生设计成功获得小姐,在K自杀后本我消退,超我控制本我,导致先生一切悲观自责自我惩罚,表现为抑郁症症状。如何释放力比多而不产生伤害,荣格与弗洛伊德归之为“升华”,“性成分的可塑性通过升华能力表达出来,这可能确实提高了一个很大的诱惑,即通过彻底的升华而寻求更高的文化成就”,刘宏宇总结文学的本质为原欲的升华。[2]
文学与精神的关系已被大量探讨,可以得知精神异变与文学创作乃至艺术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影响。特别在日本近代文学表现得出奇明显,此处所指的所谓精神异变指已被确诊的精神疾病,未被确诊的精神疾病倾向,由于时代而产生的特别的精神影响,身体苦难导致的精神状态变异。且可知精神异变与文学创作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精神异变促进文学创作,包括躯体疾病导致精神异变和精神疾病导致精神异变。躯体疾病包括梅毒三期等造成精神改变的疾病,如分析尼采、莫泊桑、福楼拜等作家等的创作年谱结合人生疾病经历就能发现,在梅毒病毒影响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亢进,创作欲增加,梅毒精神症状引发的兴奋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可能同躁郁症对文学创作有着类似影响,在讨论病迹学时绝不能摒弃身体症状对作家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如同在对夏目漱石文学进行病迹学研究时绝不能忽视胃溃疡造成的躯体痛苦,漱石作品中经常出现患有疾病的人物角色,特别于后期三部曲中多次出现,作品《心》中出现躯体疾病角色分别为我的父亲、先生的父亲、小姐的母亲,而精神异常的角色为有较之常人更为“正直”的K、后期自我惩罚的先生,大量疾病角色的描写与漱石人生后期的躯体痛苦不无关系。既可以分析为来源于漱石生命后期痛苦的人生实际体验,通过弗洛伊德和荣格文学批判分析则为本能的痛苦通过文学升华从而体现于作品。精神疾病影响的文学疾病可以分别同疾病症状对照,例如三毛前期作品的消极,青年期文风则改变为热情充满感染力。这同三毛的人生经历吻合。三毛一生抑郁期和躁郁期交替,在作品中得到体现。精神状态予之作品创作灵感得到印证。
文学创作反作用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一切艺术创作对精神症状有积极或消极的反作用,弗洛伊德分析为力比多的释放,正如刘宏宇引用荣格对于歌德与浮士德的关系“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通过内心原欲的释放,可能产生正向或负面完全相反的反作用。如郁达夫在双向情感障碍与创作的互动中刻意放纵自己的想法情绪,通过设想等方式将自己沉浸入悲哀情绪,以烘托气氛创作灵感[3]。
日本近代文学家中通过受到艺术创作反作用而导致自杀的有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等作家。一方面正确地通过文学释放力比多能够带来救赎,此处引用张蕾[4]在关于日本近代病迹学的研究中对谷崎润一郎的分析,“谷崎的作品大多是以扭曲的性为主题,受虐、倒错、嗜物癖等描写随处可见。生活中的谷崎有明显的恋母情结和女性崇拜的倾向。但他整个生涯中却没有出现明显的发病症状。或许他是把自己异常的能量都升华到创作上。把自己偏执倒错的价值观施加在作品中,从中恰到好处地宣泄了自己异常的能量。也就是说他们巧妙地控制住了现实和作品之间的界限从而得以保持在日常世界中的平衡”。弗洛伊德解释为,通过文学的表现形式将内心原欲进行升华,释放力比多以达到内心平衡,谷崎润一郎具有同郁达夫类似的行为,刻意将自己放置于异常精神状态中以达到创作灵感(郁达夫为抑郁情绪,而谷崎润一郎则刻意徘徊于潜意识和前意识的虚无缥缈的状态),作为结果而言,谷崎作品虽然备受争议却并未具有确切诊断的精神异常,他人记述及个人经历中的谷崎也并未出现一般精神异常作家所具有的自我斗争(如芥川龙之介),人生痛苦感受(如太宰治)。通过升华而达到心灵平衡印证了文学创作对精神的正向反作用是确实成立的。
清楚文学创作与精神状态的相互作用给病迹学下的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已知疾病的症状预测人物角色的人生轨迹,呼应故事情节发展。对文学人物解读带来新观点,同时作者本人的精神症状在其中也同样起重要作用,相较于文学研究以往的研究解读方法,通过病迹视点的文学分析更有迹可循,比之单纯来源于文学作品内容的理论分析更具科学性。同时对于没有明显疾病表现或明确病例记录或异常人物描写的作家和作品而言,病迹学的批判作用几乎可以不计。相较于传统文学研究而言,研究对象受限。
下文尝试利用病迹学视点对夏目漱石末期作品《心》中人物形象K作出解读。日本夏目漱石病迹学研究者普遍将漱石一生分为三个病期,第一病期从明治27年至28年基本为20岁后半部分,第二病期为明治36年到39年的30岁后半部分,第三病期为大正2年到夏目胃溃疡病发身亡为止的40岁后半部分,发表作品《心》为大正3年,即漱石身亡前的最晚年作品,此时的漱石深受身体疾病和精神困境困扰,身心痛苦给予漱石文学作品的影响可以在后期三部曲中多次出现的疾病形象中体现,如《心》中出现的先生、K的前后自杀,《行人》中患有胃病的友人,神经过敏的哥哥的異常行为等。
本文选择人物K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文中具有明显异常气质的人物,漱石对于人物K的与众不同即异常状态有具体描写,交代清晰,利于研究。总结文中夏目漱石对人物K的描述,成长背景部分描述可知,K成长于养父母家庭,信奉真宗,“我们确实满怀凌云壮志,想要出人头地,特别是K,更是心性好强。出生于寺院的他,动辄口称‘精进’。在我看来,他的行动坐卧几乎都可以用‘精进’一词来形容。我常常暗自敬畏他”。[6]人物K登场便具有与第一人称“我”或者说与常人明显异常的性格。同时有强烈自我主张,为了追求自己的精神成长违背养父母的愿望并拒绝妥协以至于与养父母和亲生父母断绝关系,“K的生母早逝,可以说,他性格的某一方面是在继母抚养下长大的结果。我想,如果他的生母还活着,或许他和自家的人也不至于產生这么大的隔膜。他的父亲虽然是个僧侣,但在讲求人情这一点上,倒有点像个武士”。
以弗洛伊德为基础的精神分析学认为自卑感、欠缺感、不安全感,共同决定了个人的生存目标。[5]孩子极力想吸引他人和父母的关注的倾向,从一出生便开始显露出来目标确立后,达成目标能确保个人得到优越感,或为赋予其生命以意义,使其人格获得提升。这种目标将价值赋予了个人感觉,并整理、协调个人感情,刺激个人想象,指引个人创造,确定个人应铭记何事,又应遗忘何事。这说明感觉、情绪、感情、想象这些个人精神活动关键元素的价值都是相对而言的,乃至一直在发生变化。个人确定的奋斗目标作用于这些元素,并掌控、决定着个人的真实思想,个人极力追逐的终极目标,就相当于隐藏于这一切元素中。可以想象童年时期的K缺少母亲的陪伴,父亲具备同“武士”一般的性格,缺少安全感的成长环境使得K极力追求权力与优越感以弥补自身自卑与获得来自父亲的认同感。阿德勒认为,人的行为模式根源在于社会感及对权力的追求。通过对K的分析,童年处在严重压力环境下(失去母亲,父亲性格严苛,寄宿于养父母家)导致K社会感与对权力的追逐成反比发展,极度追求自我优越感以获得安全感,社会感减弱,表现为进攻型人格特征,“行为激烈、豪迈,若拥有足够的勇气,这种人便可能把勇气上升为鲁莽,以让自身能力得到鲜明的展现,这刚好彰显了安全感匮乏对他们造成的巨大干扰。陷入忧虑之际,这种人会为淡化心中的忧虑与恐惧,表现得强悍、残酷。为了佯装自己是真正的男人,他们装腔作势,甚至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惹人发笑。他们之中的部分人将一切温柔的感情都视为懦弱,因此费尽心机想避免自己有丝毫这样的表现。这种人也许会表现出野蛮、残酷的品性,若其兼具悲观倾向,这种倾向就将改变其跟身边环境的一切关系。同情心与合作能力的缺失,将导致他们跟全世界对抗。他们还经常表现得骄傲、自大,这是基于他们极佳的自我感觉”。在同养父家断绝关系后K试图通过工作兼顾学业,“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同时又背上了新的重负,勇武向前。我很担心他的身体,而刚强的他只是一笑置之,全然不理会我的劝告”。[6]其外部表现为精进自己的身体、精神,实则为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在面对强压环境下的表现,其本身并不具备相应能力,必将造成相应不良后果。“恢复原籍是在他一年级的时候,以后直到二年级上半学期,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他都是靠自己打工来维持生活的。然而,过度劳累显然已经渐渐影响了他的健康和精神。再加上离不离开养父家这一令人烦恼的问题,他渐渐变得感伤起来。有时他说,只有自己是独自背负着世上所有不幸的人。我若予以反驳,他立刻会激动起来。他还觉得自己一片光明的前途渐渐远去了,因此焦虑不安”。对照进攻型人格的表现完全一致。[5]行为鲁莽、盲目、性格骄傲自大、远离人群、具备悲观倾向,将温柔感情视为懦弱,完全可以说是K的性格写照。
通过病迹学研究得以得知K的性格特质和行为模式背后的成因,究其原因是缺乏安全感下对权力的追逐,其行动模式的一切动因是对安全感缺乏的补偿行为。通过这种补偿行为达到心灵上的安宁,起源于儿童时期在特殊环境下为适应环境而形成的性格特质。故此可得知这种心灵模式一旦被打破,将给其本人带来巨大冲击。其一切行为模式,即便看起来完全不合理并有异于常人,而本人并未有意为之,在无意识情况下的行为都能带来某种好处,即心灵上的平衡以减轻精神压力。这种平衡使人可以向所定人生目标努力实现人生意义。K的人生在养父母及亲属父母断绝关系后发生动荡,随后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被迫工作兼顾学习)给心灵平衡造成冲击,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K遇见了小姐并深陷情网。K一直将女人及温柔感情等同,视为阻止自己精进的障碍,而对于小姐产生的爱情相当于对K当前行为模式的破坏,必然打乱总体精神机制。“只要察觉便会打乱他总体行为模式的倾向,全都被揭露出来,不带半分掩饰。无论什么人,都拒绝采纳所有或许会阻挠自己根据自身意志采取行动的观点,宁愿采纳能证实自身态度与行为合理性的观点,这是人类共有的特征”。在对待小姐上,K无法得以按照惯有行为模式行动这一点也被先生察觉并加以利用“他的个性并不懦弱,不大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他有胆有识,只要认定一点,就敢于一个人向前突进。在他和养父家的那件事上,就充分反映出他的个性,让我难以忘怀。因此,我敏锐地觉察到了他今天的反常表现,也是顺理成章的”。“当我问他为什么现在来征求我的看法时,他说:‘我是个懦夫,深感羞愧。’他的语气从未如此沮丧……他答不上来了,只是说:‘很痛苦。’他的神情一看便知,确实是很痛苦。倘若对方不是小姐的话,我一定会让他久旱逢甘露一般,得到一个最渴求的回答。我相信,自己生来就是具有这般慈悲心的人,但是,那时的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心灵平衡被小姐的出现完全打破,理所当然地带来了心灵痛苦。已知童年形成的行为模式很难改变,就算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人生经验,改变想法观念,要脱离童年建立的行为模式颇具难度。行为模式和现实的冲击改变了精神机制导致无法按照弥补路径完成。故而“很痛苦”。在得知先生同小姐的婚约后选择自杀。K选择自杀的原因表面上看是无法接受所爱之人小姐的婚约而死,在先生看来是自己通过计谋将K害死,以至于悔恨至死,实则通过分析可知K的死亡是在复杂条件下心理失衡所致,对于K的人物性格而言其死亡具有必然性。漱石对K死亡的铺垫完整且完全合理,对K的背景描写,性格刻画,最后在心理斗争中自杀,虽然从先生的视点出发描写,言语中包含先生对K的愧疚之情,但是并不影响对角色K心理的分析,得以证明K自杀的必然性。自杀行为同时具有惩罚自己和惩罚他人两面,从结果上看,K的目的已经达到,“先生”一生为K的死亡所困,最终走向自杀。
通过对角色K的童年经历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他性格的形成因素为缺乏安全感,追逐权力,社会感减少,进攻型人格特征。此性格特征在精神平衡受到冲击时失衡导致角色自杀。通过精神分析能对角色人生轨迹作出合理解读,逻辑自洽。病迹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故在此。将科学的分析方法引入文学批判,对人物发展作出预测,对人物结局作出解读,给予故事新的视点。
参考文献:
[1]彭吉.人格与生命的毁灭——以弗洛伊德的三我理论解读《心》中先生自杀的原因[J].湖北社会科学,2013,(02).
[2]刘宏宇.弗洛伊德与荣格精神分析文学批评观比较[J].湖北社会科学,2014,(08).
[3]陈智民.精神障碍与文学创作关系初步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7.
[4]张蕾.狂气、病迹学与文学创作——兼论日本文学病迹学研究[J].文史哲,2005,(06).
[5](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洞察人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6]夏目漱石.心[M].竺家荣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
作者简介:
勾应菡,女,汉族,云南昆明人,辽宁省大连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