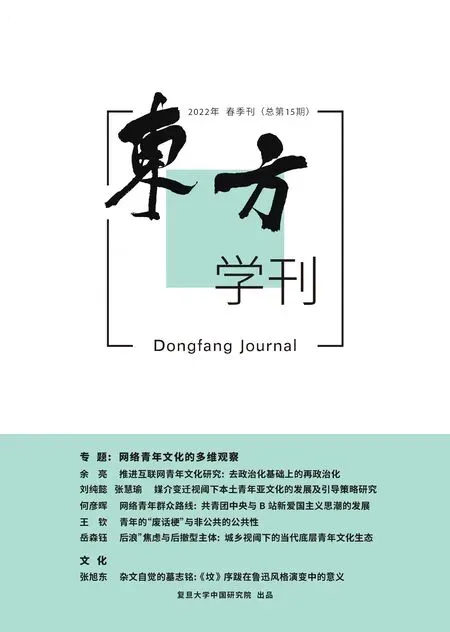大一统,中国为什么能:评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萧 武
作者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一
自1990 年代以来,宪政理论在中国兴起,时至今日,无论是欧美学术著作的译介还是国内的历史研究,关于宪政理论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但这些研究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以欧美为研究对象,解释宪政为什么重要、欧美为什么产生了宪政,以及欧美宪政是如何运转的;另一类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着力点在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宪政道路,以及中国未来应当如何走向宪政。不过,大多数此类宪政理论研究,无论研究对象是什么,其学术背后的政治意图都是不言自明的,如有人概括的那样,即如何让美国宪法在中国落地生根,让中国成为美国那样的宪政国家。
不过,这些宪政理论研究即便以欧美宪政为对象,能够真正深入到一个国家的宪政是如何形成并具体运转的却并不多,尤其是宪政在历史过程中的变迁,只是一味地鼓吹宪政如何好,乃至将宪政神秘化,并将宪政与基督教文化传统挂钩,称之为宪政的超验基础。这样的宪政研究固然在理论上不是不可以自成体系,但将这个逻辑延伸开来,落实到中国今天的政治现实,就不太可能了。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像中国这样的非基督教国家,便无所谓宪政了,除非让中国也彻底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否则这样的宪政便与中国毫无关系了。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来确实有些研究宪政的学者真的变成了基督徒,但他们变成基督徒之后却又并不怎么关心宪政问题了。
主流宪政理论一直试图以反政治的姿态来规训政治,回避实际的政治过程,以为只要有一套宪政规则,政治就可以像给电脑装上一个程序一样自动按程序运转,不用过多考虑人的因素。主流宪政理论对欧美国家政治的介绍,大多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实际的政治过程,而把那些国家的宪法过度美化乃至神化。比如,对美国宪政的介绍就过分拔高了原初的宪法的意义,而忽略了南北战争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美国,罗斯福新政又再次改变了美国;过分拔高三权分立,而忽略了三权之间事实上此消彼长的博弈过程。
在中国,对这种宪政理论的第一波冲击来自对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译介,其中刘小枫的《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影响尤为深远,该文借助施米特对自由主义宪法学的批判,将宪政重新拉回到政治的轨道。比如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强调的敌友划分、主权决断,都是对原有宪政理论的批判和挑战。但主流宪政理论对此并没有什么严肃的回应,尤其是对施米特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深入的讨论,只是将这样的理论归为政治宪法学了事。
作为纳粹德国的“桂冠法学家”,施米特提出了“空间”的问题,也就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所处的地理环境对其政治形态和宪政有决定性的影响。虽然“空间”这个概念因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使用比较多,从而变得臭名昭著,但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这是客观事实,是无可回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冷战的到来,地缘政治学复苏,“空间”重新成为国际政治理论必须关注和回应的问题。而且时至今日,地缘政治理论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之一。相形之下,宪政理论反而是在里根-撒切尔的自由主义回潮之后才成为主流政治理论,并成为欧美国家极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的政治理论。而中国的主流宪政理论也是在这一波欧美国家的推动之下才兴起的,倒是很跟得上国际潮流。
在这种背景下,苏力每次谈到宪政问题,都像是在对主流宪政理论发起挑战。比如苏力曾批评过,国内主流宪政理论和宪法学学者沉迷于国外各种高深理论,但在谈到中国宪政问题的时候,却总是回避一个最现实也最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宪政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怎么摆?因为按照主流宪政理论和宪法学理论,是没有党的领导的位置的,这也是导致宪政理论在中国只是看上去很“美”,始终无法落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涉及施米特所说的决断,也就是主权的问题。
《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①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本文涉及对该书的引用,随引文标注页码,不再另外加注。(以下简称“《大国宪制》”)自然也不例外,是苏力对主流宪法学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宪政理论的研究领域的拓展。从读者的角度看,尤其是从法学学者的角度看,全书最为精彩也最富于激情的部分可能是“序”和“结语”,因为这两部分最直接地批评了中国的宪政理论和宪法学研究现状,尤其是唯洋是举的风气:
除非“贱人矫情”,千万别把宪制/政读成了“从此过着幸福生活”的格林童话。(547 页)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宪制空间中,更经常更大量的人和事是各种形式和方式的利益争夺、钩心斗角甚至公开冲突,令人心烦,甚至令人厌恶。宪制是要为这样一个其实不大可能和谐,不可能令每个人满意却都希望按自己的理想改造的社会稳定持续且生动的存在,创造最重要最基本的制度条件。不但要能在这个社会中运转起来,后果大致可以接受,而且这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和条件还能支撑这个宪制长期运转。(548 页)
二
按照苏力的说法,《大国宪制》虽然主体内容是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讨论,但这不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作品,而是“一个基于中国经验关于一般宪制理论的尝试”:
我希望提供一种研究宪制问题的立场、视角和进路,甚至是范式,加入目前,不限于中国国内,宪制/法/政/法律研究的学术竞争,但不是学术政治的竞争。(40 页)
也就是说,苏力这次的意图不只是批评国内主流宪法学和宪政理论,而是“不限于国内”的,希望挑战国际主流宪法学和宪政理论。所以,开宗明义,苏力在“引论”部分就对“宪制”一词进行了词源分析,将“宪制”扩展到了“制度构成”。接下来,全书详细讨论了苏力认为构成历史中国的基本制度,包括政治上的皇帝、封建与郡县、军事,作为社会基础的家庭、婚姻,经济上的度量衡,文化上的书同文与科举制等他认为重要的制度。
全书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在于解释三个字,也就是“大”“一”“统”,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大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体,以及如何维持这个共同体不解体和崩溃,为此,中国历史上创造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概括起来,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大一统,而且持续了两千年?
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大国,而且一直都是大国,这是苏力首先要解释的问题。正如苏力所说:“为何本书书名是《大国宪制》,而不是《历史中国的宪制》?”(44 页)苏力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只有大国的宪制才有意义,有研究的必要。因为只有大国历史上的制度构成才有规律性的东西可以追寻和总结,而小国的宪制很容易受到外力的影响,历史上的偶然性远大于必然性,自然就没有多大的研究和总结价值。比如,即便今天的专家学者能够把一个太平洋小岛国的历史上的宪制研究得十分精妙,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自然也就没什么必要去关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苏力认为过分拔高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民主制度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从中国的角度看,那些国家实际上就是几个村子大小的人口和土地规模,而欧美后来形成的民主制度实际上也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没什么关系,而是在经历了复杂的政治博弈之后才形成的制度。毕竟,制度需要设计,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步演变而成的,太滞后了不行,太超前了也不行。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统一。中国虽然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分裂和战乱,但最终都走向了统一。而且,每一次分裂都是中国核心区域的大开发时期,而且都是先完成局部的统一,为下一次全国性的统一做准备。比如从东汉末期开始,中国进入大分裂和战乱时期,虽然中间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未能维持多久,因为导致分裂的那些因素并未消除,所以很快就又一次陷入了分裂,而且是远比东汉末期群雄并起时规模更大的战乱,也就是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但在此之后,中国又重新走向了统一,并且迎来了又一个文明高峰,即隋唐。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让中国始终能够在治乱循环的同时,又在分裂与统一之间循环,并且总是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在横向上把统一推向空间上的扩大,同时又能在纵向上把统一的深入程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苏力对此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分封与郡县等角度都做出了解释: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真正值得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做法是否没有弊端,全是收益,而是(1)总体而言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或(2)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否无可替代,乃至是必要之法;或(3)放在历史发展中来看,这些努力对于人类来说是否是有益和必要的尝试。(331 页)
最后,“统”在这里是统治的意思,也就是不仅有主权,而且有治权。古代中国能够对面积如此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使之始终处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下而不至于崩溃和瓦解,而且从现在能够追溯到的华夏文明起源的夏商周时代直到现在,始终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中国是怎么做到的,哪些制度起到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苏力从官僚制、分封制、行政区划、改土归流、精英政治等角度做了解释。虽然他的解释未必让人信服,尤其是在历史学家看来,结论未必正确,但正如苏力所言,该书本来就是写给法学界的,尤其是宪法学界,从这个角度说,苏力在该书中所讨论的议题以及分析问题的方式,足以大大拓展国内宪法学界的研究论题。
三
难能可贵的是,苏力一直极力避免形而上的解释,尤其是过度拔高文化的作用,而是一直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以社会科学的方式进行了解释。苏力反复强调,他尽量避免做价值判断,也就是以好坏来评价一个制度,而是用是否有效以及是否更有效率来作为衡量标准。比如对儒家的态度,苏力明确表示他本人并不喜欢,但他仍然使用了儒家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齐家治国平天下:
坚持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本书因此完全彻底拒绝了近代那种强调“内圣外王”的新儒家传统,一种思辨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传统。拒绝的根本理由是社会实践,而不是个人的学术好恶。
……
我不喜欢规范性和伦理性“齐家”话语。那可以算是学术或思想,却不是我喜欢的、源自可分享的社会经验并可能进入现代社会实践的社会科学的理论。(168—169 页)
这和近些年来那种一旦讨论中国历史问题,就必然要抬高儒家传统、从文化到文化的研究方式大异其趣。所以,苏力明确表示,他在解释方法上更多地使用了功能分析:
我更多使用了功能分析,解说某种社会实践或制度对于人类生存和国家社会整合的作用。但功能分析是研究者的事后分析,能说得通,却很难验证。只展示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不敢妄称其真实或可靠,更没打算接近真理。(561 页)
但危险也在于,如果将功能主义用到极致,就可能会推导出一些说服力不足的结论。全书论证最为薄弱的也许是关于经济的两个部分,也就是第六章“度量衡的宪制塑造力”和第七章“经济的构成与整合”。苏力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之所以优先统一度量衡,而不是统一货币,就是因为统一度量衡的作用更为基础、更为重要:
度量衡在中国从封建到中央集权的制度演变和发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1)改造土地制度,创造赋税制度;(2)实践俸禄制,创造理性的官僚制;以及(3)对官员的监察和绩效考核制。(271 页)
这个解释未免有牵强之嫌。首先,改造土地制度实际上是从“鲁税亩”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到春秋晚期,由于铁器的出现和发展,原来的井田制逐步崩溃,所以到战国时期,各国纷纷进行变法,做法总体上大同小异,和商鞅变法的内容相近,即国家的统治和管理要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尤其是井田制崩溃的现实,于是逐步实施赋税制度了。而这早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即便各国内部统一度量衡和货币,也是在井田制崩溃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其次,俸禄制出现在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逐渐普及。春秋之后贵族有爵位,官员都是贵族,有自己的世袭领地,所以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爵位享有收益,担任与爵位相对应的级别的职务。但在官员之外,周朝还有一大批胥吏,他们没有世袭领地,只能从国家或者领主那里按月领取口粮。到战国时期,随着世爵制逐渐被废除,官员的任免和升降越来越频繁,开始普遍实行俸禄制,即官员按照自己的级别按月领取相应的俸禄。最早的俸禄以谷物的形式发放,所以叫若干石。不过,苏力这个解释的有效之处在于,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只有低级官员才按级别按月领取俸禄,最高只有一千石,到了秦统一六国之后才出现了比较高级的两千石。①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55—56 页。
此外,在第十章“作为制度的皇帝”中,关于嫡长子继承制的解释也稍嫌牵强。苏力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三种继承制度,分别是嫡长子继承制、立幼制和立贤制,这三种继承制度各有利弊,但相比之下,嫡长子继承制是风险最小的继承制度,所以被作为皇权继承制度规定了下来。但嫡长子继承制实际上并没有一直得到坚持,无论是秦汉、隋唐还是宋朝,都不是完全的嫡长子继承制,更多的时候是综合考虑的结果,真正贯彻嫡长子继承制的反而是明朝,清朝也不是嫡长子继承制。事实上,嫡长子继承作为一种原则性的规定,并不是因为嫡长子继承制的风险更小,而是因为“子凭母贵”,嫡子出自嫡妻,而嫡妻在宗法制度下的地位高于庶妻,所以嫡子在继承权上也优先于庶子。这也就是《春秋》开篇“郑伯克段于鄢”表述的意思。因为嫡庶和君臣一样,是有上下尊卑的。
四
苏力在《大国宪制》各章节中的讨论建立在一些基础性的概念之上,主要是农耕文明、小农社会、同姓村落、精英政治。这几个概念在不同的章节中都是苏力展开讨论的关键词。其中,农耕文明在“引论”部分关于国家的起源、父慈子孝与长幼有序、军事的宪制塑造等几个部分处于核心地位,小农社会在父慈子孝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等部分处于核心地位,同姓村落主要是在关于“齐家”的两章中,精英政治主要支撑了书同文和官话、政治参与等部分。
其中,关于精英政治的讨论中非常有启发性的地方在于,苏力不仅考察和解释了从推举制、察举制到科举制的精英选拔制度,更重要的是他加入了空间的维度,也就是官员分为不同区域录取,这是只有大国才会遇到的区域之间的政治均衡问题,小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也可以说明,中国之所以是大国,治理需要通过很多技术手段来实现,尤其是要通过一些所谓的传统智慧来保持区域之间的均衡,以免让一部分地区失去对中央的忠诚。这就是说,虽然各种选举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选拔精英来进行统治,但在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谁是精英谁不是精英的问题上,很难有一个全国“一刀切”的标准。一定程度上,今天高考以省为单位设置不同的分数线,也可以视为这种传统政治智慧的延续。
我在这里重点讨论农耕文明。当然,这不是对苏力关于长城的功能的解释的批评,而是一种补充。希望这个补充有益于提高苏力的解释的有效性。
所谓农耕文明,当然是与游牧文明相对而言的。自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提出“400 毫米降水分布线”①参阅[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这一观点以来,关于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讨论,就经常会提到这一点。近年来一些影响很大的关于边疆的著作中,也经常出现这样的划分,典型的比如施展的《枢纽》。
施展重点论述草原地区“武德充沛”、中原地区“费拉不堪”,草原游牧民族一旦接受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也会变得“费拉不堪”。②参阅施展:《枢纽:3000 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强调的恰恰不是长城分割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作用,而是重点指出长城南北地区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形态文明的交流的地带。因为这是一个既可以游牧也可以农耕的地带,但究竟是游牧还是农耕,取决于中原农耕帝国的政治是否稳定,能否对这一地带有足够的控制力。辽东地区、今天的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的一些地区都是这种区域的典型。中原王朝强盛,能够对这些地区形成有效控制,这些地区上生活的即便是内迁的游牧民族,也会逐步转变为农耕生活方式;而当中原王朝政治混乱,无力实际有效控制这些地区的时候,这些地区的汉人也会逐渐胡化,比如北齐的皇族高欢,就是典型的胡化了的汉人。
《大国宪制》在第四章“宪制的军事塑造”中,也提到了长城的作用:
曾有不止一个人称,长城纯粹是个神话,因为从其第一天建设,在军事上,长城就毫无用处。我必须打其脸。(200 页)
苏力认为长城不但有用,而且非常重要,因为它作为一项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国防工程,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为农耕地区提供了保护,“秦汉正面例证了长城对于维护中原农耕文明的制度意义”(203 页)。也就是说,苏力认为长城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农业时代扮演了一种制度性的角色,以此来保护中原农耕文明。如果从空间的角度看,这当然没有问题,而且把长城的意义提升到了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的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从中原王朝的角度看,修建长城就意味着中原王朝为自己建立了一条能够进行实际有效控制的防御线,实际上长城不仅是防御线,同时也是进攻出发线,每个王朝在国力强盛时期,对北方游牧民族发动进攻的时候,都是在长城沿线完成军事集结、储备军事物资的。
但从客观效果来说,正如苏力自己也承认的,长城作为一项被动防御战略下的国防工程,要发挥其功能,需要许多其他条件的配合。长城形成在秦朝,但发挥作用在汉朝。然而如果稍微熟悉汉朝的历史就知道,在匈奴强盛的时期,几乎每一次匈奴的大规模南下,长城都未能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匈奴经常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长城以南的农耕地区,劫掠一番之后从容离去。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朝放弃了沿长城被动防御的战略,而改为主动进攻姿态,以大兵团多路出击,越过长城线,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与匈奴进行战略决战,才最终迫使匈奴逐渐走向衰落。也就是说,在秦汉时期,最终解除匈奴对中原农耕地区的威胁的,不是长城的防御功能,而是中原王朝的主动出击。换句话说,长城作为防御线的功能可能被高估了,而作为进攻出发线的功能却被低估了。“筑城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改善阵地,有利于自己部队的行动、不利于敌人行动的一种手段。”①康宁:《长城与古代战争》,载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史学月刊》编辑部编:《中国军事史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68 页。
这其实不难理解,只要到过长城的人都会发现,长城实际上并不高大。而且,长城并不都是用砖修砌而成的,在河西走廊漫长而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都是夯土墙。在几万人的大兵团进攻面前,很难真正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只有在长城沿线屯驻大量军队,由军队依托长城的工事来进行防守,长城才能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而要在长城沿线长期驻扎这样大规模的兵团,其代价是非常高昂的。比如秦统一之后,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军队一边在长城沿线驻防,抗击匈奴,一边为修筑长城提供军事掩护。长城防线真正成熟是在明朝时期,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绝大部分也都是明朝时期修筑的,而明朝在长城线形成了九边防御体系,就是把今天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区,驻扎了近百万人的军队,才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即便如此,在土木堡之变后,大同守将仍在坚持抵抗,也先也能够率领瓦剌军队,拆毁了一段长城,长驱直入,直抵北京城下,与明军在北京城下进行决战。到晚明时期,女真崛起,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尤其是皇太极,也曾多次绕过防守严密的辽东防线,从居庸关附近突破长城防线,直逼北京城下,打乱了明朝的部署。
也就是说,在大规模军事进攻面前,长城能够发挥的防御作用其实非常有限。但正如苏力指出的,这并不是说长城毫无作用,长城依然非常重要。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长城虽然无法阻止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军事入侵,但可以阻止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小规模的、日常的侵扰和劫掠。实际上,拉铁摩尔所谓的长城沿线地区两种文明和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交流,相当一部分就是以这种游牧民族在农耕地区的劫掠的形式进行的。因为对游牧民族来说,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农耕地区获取一些生活物资,他们很难在这种贸易中占到什么便宜,如果只是和平贸易,他们很快就会像今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下与发达工业国家进行所谓自由贸易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变得一无所有,完全被农耕地区控制。所以,对他们来说,最为便捷的方式就是劫掠。这既包括劫掠物资,也包括劫掠人口。汉朝时期,匈奴南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从中原农耕地区劫掠人口,充当匈奴贵族的奴隶,在适合农耕的地区种植粮食;准噶尔强盛时期,也曾在南疆劫掠维吾尔族人口,劫去伊犁河谷适合农耕的地区为他们种地,后来为祸清朝的大小和卓,就曾被准噶尔劫持到伊犁河谷地区种地,直到清朝消灭准噶尔,才被放回南疆。长城虽然无力阻止数万人规模的军事入侵,但是阻止这种几十、几百人的日常化的侵扰、劫掠还是够用的。这是长城的第一个作用。
长城的第二个实际作用是,游牧民族虽然可以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时候拆毁长城,但小规模的人群在长城面前是无计可施的,只能通过中原王朝沿长城设置的各个关口进入中原地区,进行贸易往来。这就意味着,是否在长城沿线地区开放中原内地的商人与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主动权完全在中原王朝手中。这种贸易对中原王朝来说,除了作为军事战略物资的战马是内地非常需要的之外,游牧地区所能提供的其他贸易物资,对中原地区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可有可无。如果没有长城,在长城附近游牧的部落就可以与内地进行日常化的物资贸易往来,中原地区很难对这种物资交流进行有效管理。而有了长城,无论是内地的商人把内地的物资贩运到长城以北的游牧地区,还是游牧地区的部落与内地开展物资贸易,都必须到中原王朝指定的地区进行。也正是因此,才有了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所说的那种中原与游牧帝国之间的战争。按照巴菲尔德的解释,游牧部落必须从内地获取大量的生活和生产物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给中原王朝施加足够大的压力,逼迫中原王朝开放贸易;如果游牧部落都联合起来,形成大的游牧部落联盟国家,在军事上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中原王朝往往会对游牧地区采取强硬的物资封锁策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经济制裁和经济封锁。①参阅[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明朝在对待蒙古的策略上,从土木堡之变后,实际上已经转入了全面防御阶段,修筑长城也是在这之后。但也正是在这之后,明朝一方面加强和完善长城沿线的防御体系,另一方面拒绝先后崛起的俺答汗、达延汗等已经形成局部性游牧部落联盟国家的贸易要求,始终不同意像宋朝那样以“岁币”的形式对双方之间的贸易差额进行补偿。这种游牧部落的敲诈始终无效,最终导致蒙古日渐衰落,无法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国家,只能分别接受明朝给予的封号,以朝贡的方式与明朝进行贸易。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白登之围的时候,冒顿单于会轻易地接受汉朝使节的建议,形成了和亲和岁币的策略。而和亲的主要意义实际上并不是政治联姻,在游牧帝国与中原农耕王朝之间建立血缘关系,而是因为和亲都是以汉朝公主出嫁到游牧帝国的形式进行的,汉朝会按照公主结婚的规格,并且一般都要远远高于这个规格,在出嫁的时候赠予大量的物资作为嫁妆。在和亲之后,汉朝还要周期性地派遣使节携带大量物资进行探望。这些物资对汉朝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只关乎面子问题,而对匈奴单于来说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正如汉朝使节所说的,只要单于同意放汉高祖一马,以这种形式进行物资交流,所有的收益都会由单于独享,单于如果坚持要以武力消灭被围困的汉高祖及其率领的三十万军队,即便匈奴能够打赢,战利品也是由匈奴各个贵族分享,并不完全归单于所有和支配——因为匈奴在战利品分配上的原则是谁抢到就归谁。按照巴菲尔德的观点,实际上,单于得到的这些财物也并不完全归单于独享,单于仍然要在贵族之间进行分配,只是单于掌握了这个分配的主导权,从而可以形成他与其他贵族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汉朝希望与匈奴之间的物资交流是以官方对官方的形式进行,因为这样才能使朝廷掌握贸易方式的主导权。而且,汉朝以己度人,认为这样的交往方式对匈奴自身也是适用的,而且对匈奴单于个人也有利。对一个强调秩序和稳定的农耕王朝来说,始终将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关键所在。当然,这并不是说,汉朝拒绝与匈奴之间的民间贸易往来,汉朝当然也是愿意进行这种贸易往来的,只是这种贸易往来同样必须在朝廷指定的地区、以朝廷指定的方式进行,而且在交易的物资品种上,也必须遵守朝廷的规定。比如铁器对大多数游牧民族来说,一开始都是不能生产的,只能从内地通过物资贸易来获取,而中原王朝将铁器视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禁止中原地区的商人把内地的铁器贩运到游牧地区去。
也就是说,长城作为苏力所说的一种制度,实际上并不只是一种针对游牧民族的防御工事,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为中原王朝实际有效控制的疆域划出的一个边界,而这个控制和管制对象也包括中原地区的人民。而对人民、物资的有效管理也是国家的重要目标,尤其是在物资相对比较紧缺、绝大多数人口实际上都挣扎在温饱线边缘的农业社会,这一点尤其重要。那些不重视长城,或者失去了长城沿线控制权的朝代,也就因此失去了对物资的控制权,从而要么像五胡十六国时期一样,整个北方的农耕人口都成为游牧民族的奴役对象和劫掠对象,要么像宋朝一样,燕云十六州成为辽国源源不断地获取生产和生活物资的地区,而辽国因此与其他游牧帝国完全不同,发展为一个兼有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帝国,其稳定性远高于一般的游牧帝国,北宋只能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的境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长城对历史上的中国而言,是一个苏力所说的重要的制度构成,因为如果失去了对长城沿线的有效控制,无险可守的整个华北平原地区门户洞开,中原王朝就完全暴露在游牧民族的刀尖之下。
五
对于中国的宪政理论和宪法学研究来说,《大国宪制》的贡献和意义自不待言。苏力在书中所坚持的立场和所用的分析方法也是有效的,许多解释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也没有问题,但因为这部近五十万字的皇皇巨著涉及的历史问题太多,而且是跨多个学科的,所以在细节上难免会出现一些缺乏说服力的地方,但这仍然无损于这部作品的精彩和贡献。尤其是对更年轻的学者来说,《大国宪制》的贡献在于,把更多的问题纳入了宪政研究的范畴,拓展了宪政理论的空间,有心人还可以沿着他开创的进路继续走下去,让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解释更加深入。这其实也是苏力的著作一贯的风格,读者不一定同意他的分析方法和结论,但在阅读过程中总是能够得到启发。
此外,正如苏力所说,“历史有时即使会极大程度地影响今天和明天,却无法完全规定今天和明天”(543 页)。历史上曾经有效而且高效的一些制度,在今天可能已经无效了。原因很简单,随着技术进步,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时代,许多农耕时代的经验在今天很难再发挥作用了。即便有些制度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已经和历史上的面貌完全不同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制度被创造出来及其运转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思考、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无效了。因此,宪制不仅需要空间的维度,同样需要时间的维度,对许多曾经有效的制度的理解必须放在历史变动的背景下来把握,而不能完全拒绝这种历史条件的变动。
比如该书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小农社会,但小农社会只是基础,小农究竟如何组成社会,这是一个漫长的变动的过程。打个比方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好比是砖头,但如何用这些砖头来盖房子,组成一个社会、一个政治共同体,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方式。秦汉时期的庄园农奴制、魏晋时期的领主制都是建立在小农的基础上的,但它们的组织方式迥然不同。与此相应的则是一些制度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比如我们常说的“皇权不下县”,实际上就是个误会,秦汉时期的皇权就是下县的,亭长就是县以下的官吏。真正的皇权不下县,是宋朝以后才出现的现象,因为这时候才出现我们常说的意义上的真正的小农社会。宗族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基层组织体系的功能,这是建立在许多制度基础上的,而在中晚唐之后,宗族赖以存在和维系的条件变了,制度逐步瓦解,宗族对单家独户的小农家庭已经失去了强制性的硬约束能力,这才有了宋明理学比较关注的乡规民约制度,乡贤在基层社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当然不是说苏力不应该坚持“拧干时间”的态度,而是说,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上,还需要考虑时间的维度,要考虑一些外部条件的变化,这样才能让自己的解释更有纵深,更为有效,也更有说服力。这与从历史经验中抽象出理论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