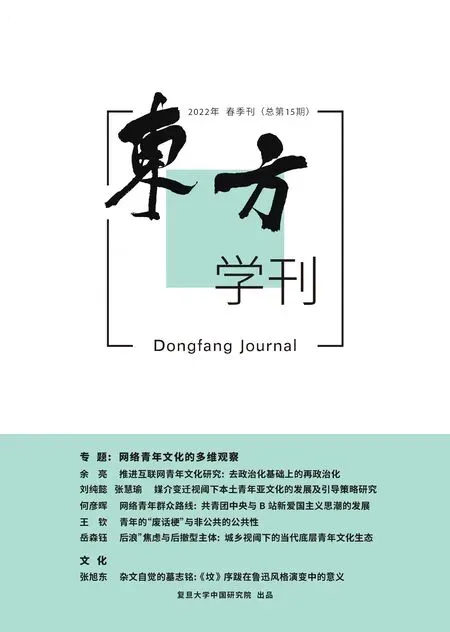“网络神曲”:折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青年亚文化消费品*
罗 峰
作为最后一项束缚于人类身体手口相传的艺术,①参阅[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中信出版社2014 年版。直到1877 年爱迪生制造出了人类史上第一台留声机,转瞬即逝的音乐才变成一种可供销售的商品。1998 年,时年18 岁的肖恩·范宁(Shawn Fanning)开发出在线音乐服务软件Napster,便携式MP3 播放器也于同年诞生。音乐开始成为储存和传播于二进制世界的文化消费品,数字和网络的结合在音乐这一可复制文化消费品的推广上表现出惊人的力量。进入新千年之后的我们悄然发觉,原本用来欣赏和传播音乐的录音机、CD 机等,已经被智能手机中的一段段音乐、短视频App 所取代;原本流转于磁带和光盘等储存介质上的音符也被转换成0 和1 的数字信号在互联网上传播。截至2014 年5 月,苹果公司旗下的iTunes 音乐商店便以0.99 美元的单价售出了超过350 亿首次歌曲。②Apple’s iTunes Store Passes 35 Billion Songs Sold Milestone,iTunes Radio Now Has 40 million Listeners”(May 29,2014),MacDailyNews,https://macdailynews.com/2014/05/29/apples-itunes-store-passes-35-billion-songs-sold-milestone-itunes-radionow-has-40-million-listeners/,retrieved Mach 31,2022.而据相关数据估计,2020 年我国的网络音乐用户已经高达6.35 亿,市场额超过2000 亿人民币。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 年4 月),第48 页,中国互联网络中心网站,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004/P020210205505603631479.pdf,最后浏览日期:2022 年3 月31 日。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音乐这一文化消费品最重要的消费场域。
在网络音乐逐步兴起的过程中,大批“网络神曲”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产物而涌现,并在全民泛娱乐化风尚的影响下逐步成为“三俗”的代表。和所有泛娱乐化的文化消费品一样,“网络神曲”一面契合了《娱乐至死》④[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一类作品中对于社会泛娱乐化的批判,另一面又在这种批判中不断扩张,逐步风靡整个中国社会。本文试图分析“网络神曲”这一文化消费品的特质及其风靡现象背后的机制,并从中透析出其作为青年亚文化产品所蕴藏的社会转型现实。
一、作为青年亚文化典型的“网络神曲”
(一)“网络神曲”的出现及其发展脉络
在互联网日渐“入侵”中国人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过程中,流行音乐也逐步成为无法脱离于网络而单独存在的文化产品,于是一大批创作并传播于网络的流行音乐开始风行,并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音乐门类——“网络神曲”。一般而言,“网络神曲”指的是那些旋律简单、节奏感强、风格奇异,歌词通俗易懂且趣味性十足,并且通过网络在青年群体乃至全社会中得到迅速传播的歌曲。①杨芳:《浅谈对“网络神曲”现象的三点思考》,《大众文艺》2013 年第8 期。自2001 年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神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诞生以来,尽管出现了诸如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之类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甚至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歌曲,但是总体上,“网络神曲”还是“坐实”了主流精英对社会文化“泛娱乐化”转向的“指控”(当然,这种指控早在港台流行音乐进入我国大陆之初,就以“靡靡之音”的称谓出现过一次了)。20 年来,“网络神曲”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②本文的阶段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吴剑锋的论述,详见吴剑锋:《“网络神曲”走红的现象研究——基于传播学视角》,《出版广角》2017 年第2 期。
第一阶段:野蛮生长期(2001—2009 年)。这一阶段“网络神曲”的创作者以草根为主。随着网络开始进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一批中国网民开始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便捷性来创作和传播自己的音乐。他们避开了传统音乐行业冗长复杂的生产过程,大批量生产出网络音乐,一批名不见经传的网络创作者也逐步获得了不亚于知名流行歌手的市场号召力。例如,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就通过网络运营商的彩铃业务,获得了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的版权分成。很多“网络神曲”的创作者一曲走天下,开始频繁在各地通过走穴演出获得巨大的收益。不过,野蛮生长期的“网络神曲”在整体上还只是流行音乐的一种补充,只是他们将生产与传播的场域搬到了网络上,同时在曲风和歌词上比传统的流行音乐更“俗”而已。
第二阶段:高速发展期(2010—2015 年)。随着网络的全面普及,一些传统的音乐行业从业者也开始涉足网络平台,并顺势推出大量“神曲”。比如:民族声乐歌唱家龚丽娜的一曲《忐忑》开创了专业歌手唱神曲的先河;从中央电视台选秀节目《星光大道》出道的组合凤凰传奇,则推出了《最炫民族风》《荷塘月色》等经典“神曲”,并迅速成为三线以下城市市民和农村居民的广场舞伴奏必备曲目;韩国歌手PSY 的《江南style》则成了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首“外国神曲”。同时,网友们的自发参与也进一步深入,无数不知名的网友通过对热门事件的改编,集体创作出《一百块钱都不给我》《我想静静》《你有本事抢男人》等。
第三阶段:多元开放期(2016 年至今)。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社交分享的时代,“网络神曲”的创作方式与风格以及传播路径也日趋多样化。传统音乐行业进一步“入侵”,例如,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就先后推出了《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哪里了》《感觉身体被掏空》等,其贴近生活的歌词与高雅的合唱艺术的“反差萌”得以迅速风靡全网。同时,随着第一首“抖音神曲”《学猫叫》的走红,抖音等短视频平台逐步成长为音乐消费的重要场域。众多专业的音乐制作公司和制作人开始将各种短视频App 或音乐App 作为其音乐发布的平台,甚至开发出了“抖音神曲”这一全新的音乐类型。当然,互联网草根也依旧保留了一席之地,李袁杰就凭借一首《离人愁》,获得了全网超过15 亿次的播放量,创造了一个不亚于《两只蝴蝶》的新神话。
(二)“网络神曲”:理解当代青年亚文化的典型文本
流行音乐研究者很早就意识到,音乐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其由音响、歌词、图像以及乐段等诸多元素组成,更包含了必须与之紧密联系的复杂社会语境。①[美]布鲁斯·霍纳、[美]托马斯·斯维斯主编:《流行音乐与文化关键词》,陆正兰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47 页。对于青年而言,流行音乐更是一种对位式的单向身份认同方式,并且通过其风格的嬗变,体现出青年在社会意识形态规约与文化制约下对于自我身份的追寻。②谷鹏飞:《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与身份认同》,《学习与探索》2012 年第8 期。本文也从“网络神曲”这一当代青年亚文化的典型文本出发,来探寻其文化符号背后的社会语境,及其体现出的青年的成长性诉求。
与“网络神曲”所追求的曲调简单化——在曲调上通过保持较窄的音域范围和较小的曲调起伏以获得传唱率,通过不断重复的、较短的旋律小节以达到洗脑效果——一样,其在文本上的追求同样如此。这种简单化的追求首先体现于歌词的意象之上,例如《鲨鱼鲨鱼》《小水果》《八戒八戒》《小鸡哔哔》《小苹果》《我的滑板鞋》《小鸡小鸡》《学猫叫》等歌曲都是直接选择了动物等直观且简单的名词作为歌名。同时,“网络神曲”还体现了歌词与日常生活的深度关联,《败家娘儿们》的歌词表现的是青年情侣两人之间的打情骂俏;《每天回家都会看到我老婆在装死》讲述的则是每天勤劳工作的小夫妻的搞笑生活日常;《给力钱钱钱》简单明了地抒发了青年群体对于金钱的向往;《化学是你,化学是我》贴近的是学生这一最大的青少年网民群体的生活;《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哪里了》则是直接来源于一则生活中的无聊琐事。
作为日常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情感记忆资源,“网络神曲”的歌词文本还表现出充沛的情感表述倾向。《我想静静》讲述了一个生活于城市钢筋水泥森林中的普通白领对于生活和爱情的迷茫;《错错错》用问答的形式表达了身陷情感漩涡中的男女对于逝去爱情的强烈追忆;《离人愁》则借助中国风的歌词渲染了一段略带古典气息的爱情悲歌。这些略带夸张的情感表述配合“网络神曲”特有的编曲方式,往往更能激发观众对歌曲的认同。此外,强烈的画面感也是其重要的文本特征,这一点由于各种粗糙却又天马行空的自制MV 在网络上的广泛流传而表现得更加强烈。《小苹果》通过与“简单意象”的歌词高度融合的MV,用大量韩流元素来唤起年轻人的“潜意识”,从而激发出他们对于韩国流行文化的美好回忆和体验,并产生条件反射式的好感;③汪振军、冀佳佳:《“神曲”文化奇观的意义生产与大众传播——探析〈小苹果〉爆红的原因》,《现代传播》2014 年第12 期。《五环之歌》则配合“车一直塞,表情痴呆,早就漫无目的地一直开”等歌词,将北京城市中堵车的画面放进了MV 之中,勾起了北京等大城市居民在面临堵车之时的焦虑与无奈。
此外,网络流行语这一“文本盗猎者”④参阅[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郑熙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用来抵抗传统主流文化话语体系的武器,被青年亚文化群体在“网络神曲”的文本创作中再次“盗猎”。例如《我想静静》《小样儿》《为什么放弃治疗》《一百块钱都不给我》《你有本事抢男人》《我爸是李刚》《感觉身体被掏空》《佛系少女》等歌曲都是直接将时下网络最流行的语言作为歌曲名称以及歌词的重要内容。而“网络神曲”歌词文本背后的叙事内容也是青年亚文化的高度凝结,“网络神曲”所描绘的故事充满了简单与直接、快乐与忧愁、生活与工作、青春与爱情、独立与成长等当代青年生活的具体写照。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所充满的规则的混淆、深度的缺乏、强烈的情感承载、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边界的瓦解、表达的戏谑化以及主体的去中心化等特征,①[英] 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06—107 页。也在“网络神曲”的歌词文本中得到了体现。因此,和被视为一种另类的、具有网络时代文化特征的民间表述、为当下社会记忆的形成提供了可资评议的“主观细节”的网络流行语一样,②李明洁:《流行语:民间表述与社会记忆——2008—2011 年网络流行语的价值分析》,《探索与争鸣》2013 年第12 期。“网络神曲”也可以成为理解当代青年成长性诉求的典型亚文化消费品。
二、从生产到传播:“网络神曲”何以风靡
当然,音乐的意义必须通过其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文本与语境之间的互动,才得以建构。③[美]彼得·约翰·马丁:《音乐与社会学观察:艺术世界与文化产品》,柯扬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年版,第6 页。对“网络神曲”的意涵把握,也无法脱离对于其作为文化消费品——从生产到传播所共同构成——的文化消费过程的考量。也正是由于完成了这样的过程,“网络神曲”才得以从青年亚文化的典型发展为风靡全社会的大众文化消费品。
(一)生产:全民参与与获利满足
传统的文化消费品生产模式中存在一种二元结构:大规模文化产品的生产场域与有限文化产品的生产场域。前者的支配者是政治或者经济力量,因而必须服从外部力量并且追求商业成功;而后者的生产者独立性更高,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④江山:《文化产品生产与消费中的阶级差异——以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为例》,《社会科学论坛》2010 年第4 期。“网络神曲”的生产则兼具了两个场域的特质。首先,作为一种大规模文化消费品,“网络神曲”必然以大众文化为导向以获得市场,希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所说的文化消费品的“商品化”,指的正是它们完全受到商品市场供销关系的操纵。⑤[德]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高两中译,载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版。凭借现代工业的生产和技术能力,即便是像贝多芬交响乐那样的高难度文化产品,也可以在短期内成千上万地复制成符合同一规格的商品。这样一来,音乐被其工业和商业过程改造成“标准化”“单一化”“规格化”“形式化”的文化消费品。⑥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6—167 页。同时,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指出的,数字网络技术让普通网民能轻松成为“使用者兼生产者”(users-turned-producers)。⑦Manuel Castells,Communication 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66-67.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大众文化水平的提升,普罗大众也不由自主地参与“网络神曲”的生产,从而模糊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于是,“网络神曲”中不仅有主流音乐产业之外的业余音乐人的创作,如《屯儿》《马云说》《为什么放弃治疗》《姐姐》《请开门》《洛天依投食歌》《老男孩》《爱情买卖》《哥只是个传说》等;也有完全出自草根甚至是不知名网友之手却大获流行的歌曲,如《我想静静》《败家娘儿们》《我的滑板鞋》《可爱颂》《每天回家都会看到我老婆在装死》《织毛衣》等;更有由网友集体参与创作的《你有本事抢男人》《一百块钱都不给我》《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等。
此外,如同流行音乐、商业电影、畅销小说、电视剧等所有的文化产品一样,“网络神曲”的生产,离不开生产者的符号报酬和物质报酬的满足。①[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王小章、郑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48—151 页。“网络神曲”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表征,不但在整个文化群体中实现了符号性报酬的整体分配,更是在网络时代的推动之下,将符号性报酬有效地转化为各种形式的物质报酬,从而维系了生产。当然,由于大众消费习惯的转变,以及创作者本身的草根特质,网络时代的神曲创作红利被生产者所直接享有变得越发困难。但是,互联网开拓出了其他获利渠道,例如,依靠网络积攒的名气进行频繁的线下演唱会,以获取丰厚的出场费,《老鼠爱大米》的作者杨臣刚就借此赚得盆满钵满,并且通过彩铃的下载,赚取高额授权费。而到了“网络神曲”发展的第三阶段,由于大量资本的涌入,神曲的获利渠道则被赋予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一方面,“网络神曲”的草根生产者更加容易被包装而出现在前台,并且借助其名气而非神曲本身来获利。例如《离人愁》的作者——李袁杰就凭借该神曲坐拥数百万粉丝,一跃成为各大音乐选秀节目的座上宾,完成了从素人到网红的蜕变。另一方面,各种互联网的音乐平台为了吸引音乐创作者入驻,也启动了各种扶持计划(如抖音的“造音行动”、网易云音乐的“云梯计划”、QQ 音乐的“银河计划”等),并给予入驻者数以亿元的补贴,以及相应的播放分成。
(二)传播:技术、场景与资本
被工业化的大众文化消费品不仅仅意味着购买与销售,更应该被视为“一个社会系统中意义和快乐产生及循环流通的积极过程”,②John Fiske,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London:Routledge,2010,p.23.因此,对于文化消费品而言,传播的重要性可能还甚于生产,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神曲”本身的某些特质,则共同促成了其广泛而迅猛地传播。
首先,正如所有的音乐都会伴随使其得以存在的技术、事物和能动者而不断变化一样,“网络神曲”的传播首先得益于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给传播方式带来的便利性。随着网络技术和电子工业技术的高度发达,各种高科技的移动设备的出现、数字化与网络化使得音乐可以被无限次重复地“使用”,这也是“网络神曲”得以风靡的技术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的诞生再一次创造了音乐。而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以小咖秀、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所创造的配乐加视频的互动传播模式,不仅深刻发展了“网络神曲”的视觉化传播优势,更让其“使用”场景更为丰富多样。③赵曼玉、张路凯:《现代音乐传播场景变化:一个媒介技术变迁的视角》,《视听界》2021 年第6 期。
其次,正如安德鲁·本尼特(Andrew Bennett)所言,流行文化工业能提供一个共享的、代表着群体感受性的文化资源,并被社会中的行为者们反复使用。①转引自[美]彼得·约翰·马丁:《音乐与社会学观察:艺术世界与文化产品》,第72 页。作为一种必要的社会活动,音乐同样需要通过群体化的行动和体验来推广和维系这种个体性感受。“网络神曲”的传播也离不开这个情绪资源群体化的过程。在线下,大量的“网络神曲”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各种非目标受众的青睐,《社会摇》《新宝岛》等神曲成为公司年会上的青年们和跳广场舞的大妈们的必备舞曲,从而实现了文化资源的跨群体共享。在线上,最为典型的案例则是流传于各种移动音乐软件的评论文化,各种“网络神曲”在此获得数以十万计的评论,网友们的各种“神评论”共同编制出无数基于“神曲”——或煽情、或幽默、或哲理——的故事,从而将原本独立的个体化音乐鉴赏过程,汇集弥漫成跨越时空的群体性狂欢。
最后,资本市场的介入进一步丰富了“网络神曲”的传播途径。随着网络逐步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主阵地,各路资本开始有意识地选择,甚至是创造爆款,来作为其推广各种IP 的工具,于是很多“网络神曲”开始改变其草根性,变得“高大上”起来。例如,《小苹果》《卡路里》等神曲因成为热门影视作品的主题曲而持续翻红。而抖音、快手等巨型流量平台在开创了短视频和音乐结合的推广模式之后,更是将平台的流量优势发挥到极致,在有意识的“音乐爆款”打造中,许多原本寂寂无名的音乐摇身一变,获得了早期“网络神曲”无法想象的传播渠道,得以以“重复的”“连续轰炸的”传播策略,曝光在大众面前。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网络神曲”得以从青年亚文化的典型,发展成为风靡整个社会的大众文化消费品的原因,不仅在于其文化符号体现出了青年的成长性诉求,更得益于网络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模糊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极大地改造甚至重塑了文化消费品生产场域。而生产门槛的进一步降低,生产者报酬(符号性与物质性)实现的进一步便捷,以及传播方式的日趋便利、传播体验的群体共享、传播途径的资本加持等,则共同推动了“网络神曲”从生产到传播的完整文化消费过程的实现,“网络神曲”已然成为网络大潮拍打在文化消费峭壁上一朵亮眼的浪花。
三、折射网络时代社会变迁的“网络神曲”
尽管文化研究一直将音乐视为最能区分社会阶层文化品位的文化消费品,②Tony Bennett,Mike Savage,Elizabeth Silva,Alan Warde,Modesto Gayo-Cal,and Divid Wright,Culture,Class,Distinction,London:Routledge,2009,p.251.但是,纵观流行音乐的崛起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流行音乐往往起源于亚文化群体,最终却得以兴盛于全社会。③参阅Andrew Bennett,Popular Music and Youth Culture,London:Macmillan Press,2000。这与传统的时尚文化流行方向大相径庭,也说明了音乐作为文化消费品的特殊性。而“网络神曲”的勃兴及其演进,所折射出的网络时代的中国社会变迁趋势,则是本文希冀进一步加以讨论的议题。
(一)从同源性到文化杂食:网络时代的文化消费
若干年后回顾当下,我们也许都会感慨,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沉默的大众”(silent majority)被推上历史前台的时代,这是普通大众的饮食男女、审美趣味、自我实现等各种需要和欲望被精心推测、揣摩、引诱、建构和强化的时代。①方文:《大众时代的时尚迷狂》,《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5 期。在这样的时代中,不但大众的需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更关键的是,他们亲身参与到了这个需求的满足过程之中。正如电视的发明和现代都市的形成,通过打破信息垄断和从生产场域向消费生活中心的转型,构建出单一的观众和共同的文化趣味,②[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 年版,第4 页。网络时代的来临,变相地在文化消费领域产生了一个无比“富裕”的群体,他们进行消费的目标选择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需求(need),而且是迎合欲望(desire),限制消费的不再是成本,而是是否符合自己喜好。于是,文化消费作为一种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区分参照物的意义就被削弱了。
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品位-阶层适配模式出发的传统文化资本研究脉络对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文化同源性论点,到对于“亚文化成员所采用的文化物品与实践之间适合(fit)”③[新]罗伊·舒克尔:《流行音乐的秘密》,韦玮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年版,第232 页。的强调,面临来自现实与学者们的挑战。④张敦福、崔海燕:《以社会学为主的跨学科研究:中外文化消费研究的比较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7 年第10 期。“网络神曲”被全社会广泛地消费,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挑战者之一的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彼得森(Richard Peterson)提出的“文化杂食”(cultural omnivorousness)论点。彼得森认为,当代社会的品位制度已经从精英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转变为以开放为特征的文化产品多样化情况,一些消费者不再将自己的品位限制在精英形式内,反而参与一些异质性的文化实践并从中获得声望。⑤Richard Peterson,“Understanding Audience Segmentation:From Elite and Mass to Omnivore and Univore”,Poetics,1992,21(4).由此,社会分层与文化消费品位之间的联系被进一步稀释。相较于传统社会中,将某种群体的文化视为一种固定的存在,且被特定群体或者个体进行选择和占有,网络时代的文化及其持有者均表现出了更大的主动性。因为,在个体并没有实现社会阶层身份的变化的情况下,其已经可以很容易地突破自己的文化边界,去共享原本并不属于自己社会阶层的文化。
由此可见,“网络神曲”反映出一幅这样的社会现实图景:网络时代,由于网络的便利性,各种文化均可以以相同的面貌被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去接受乃至接纳,文化与阶层从固定对应的同源模式转向了文化杂食模式,社会结构也有望变得更为扁平。如果把前网络时代的文化消费视为一栋等级分明的公寓的话,那么在网络时代,这座公寓则变成了一座面向全体社会阶层免费开放的公园。
(二)网络时代的青年:如何成为一个“阶层”
20 世纪中叶,作为青年研究的主流范式,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将青年视为一个无差别的消费群体,其创造的文化只有年龄区别而没有阶层差异。而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则更为注重“结构解释”(structural explanation),它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只注重“世代”和年龄,转而研究青少年与其社会阶级、地位的关联,并考察他们是否受阶级因素、结构因素的影响。这种模式将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建立于社会阶层地位的结构构架上,强调同一结构中的青年文化的一致性,特别是阶层结构本身之矛盾,⑥吴剑锋:《“网络神曲”走红的现象研究——基于传播学视角》。从而将青年带入了“阶层问题”的讨论之中。
事实上,中国的青年概念也一直在代际与阶层的两套泾渭分明的话语体系中不断纠缠,如“五四”以来的青年阶级形象常常被定义为“小资产阶级”。而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青年也逐渐被塑造成中产阶层的形象,①南帆:《代际与阶级:青年形象的理论坐标》,《学术月刊》2018 年第10 期。甚至这种形象在消费文化的营造下有向全社会蔓延的趋势。当然,这种形象并非社会等级层面的中产阶层,而是生活方式的中产阶层化,比如说丰裕的收入(得以承担起必要的文化消费开支)、充足的闲暇时间(对于青年而言)等。与出生于前所未有的丰裕(affluence)、共识(consensus)和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的历史背景下的青年一样,成长于网络时代的青年,其成长迥异于比他们稍大一些的人,仿佛处于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过渡。对此,科林·麦克因斯(Colin McInnes)曾经宣称:我们社会的“两大族群”可能不再是“富人”和“穷人”,而是青少年群体和所有已经承担成人责任的人。②转引自[英] 斯图亚特·霍尔:《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0 页。于是,年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传统的阶层分类,被视为一种更有效的社会地位指标,这种差异也被生动地转译为“代沟”,并进一步合成了一个神话——青年是一个“新阶层”。
从阶层文化的角度来看,青年亚文化可以被视为青年这个新生的阶层对于社会变迁的一种感受和反应。因此,亚文化其实是作为社会阶层分类的一种中介性概念而存在的,亚文化资本为青年以文化的形式参与到社会分层体系中提供了原始动力。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因素往往是年龄、性别和种族等,而非阶级、收入和职业。③[英]萨拉·桑顿:《亚文化资本的社会逻辑》,载陶东风、胡疆锋主编:《亚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356 页。实际上,亚文化的区隔甚至会故意模糊阶层,塑造出一种无阶层的幻想。在当代中国,计算机与网络的普及,使孩子第一次能够从父母、老师以外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从而获得了在与长辈的互动中的“反哺”能力或“话语权力”。④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中国新闻周刊》2006 年第36 期。在剧烈社会变迁(尤其是城市化与消费社会)的助推下,这一切构成了代际之间代沟形成的独特性社会土壤,进而形成代际冲突,并预示了传统文化传承模式的危机。而违背“文化消费趣味的纵向传递机制”的“网络神曲”,及其类似的大量“文化反哺”现象似乎也在暗示着,“青年成长为一个新的阶层类别”这幕大剧在中国也同样上演着。
四、余论:重新审视网络时代的社会文化
当然,大众文化消费品的统一性意味着社会阶层界限的模糊之论断,究竟是一种事实还是假象,学界亦有争论。反对者认为,文化消费品为各社会阶层所普遍接受,只不过意味着其社会阶层烙印被去除,但实质是掩盖而非消弭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对抗关系。因为大家都在享受整齐划一的文化产品之时,恰好表明统治阶层渗入大众需求和满足的程度是何等深厚,⑤[英]尼古拉·埃尔潘:《消费社会学》,孙沛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74—75 页。这正好是统治阶层地位稳固的佐证。
上述观点在前网络时代,无疑是洞见性的,然而网络时代却带来了变数。卡斯特指出,网络新技术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交互作用。⑥[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周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2—3 页。“结构-文化”关联存在于不同的场景中,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关联方式,而当互联网成为这一关联发生的具体情境之时,这种改变的深度、广度和复杂性也许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也认为,互联网无疑是继印刷术、留声机、电视机等之后最有冲击力的一个媒介工具。①[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9—10 页。因为“计算机与因特网普及,在同一接口上整合了所有媒介,才真正全面性地造成社会文化变革,一场人类社会及人际关系的革命,就在我们面前如实展开”。②转引自翟本瑞:《从社区、虚拟社区到社交网络:社会理论的变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5 期。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的后现代部落(posemodern tribes)理论则揭示了网络社会结构变化与文化变迁的一种可能方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短暂性地参与那些介于个人与大众之间的过度饱和的团体,这种团体(即后现代部落)标示了大众文化的终结,也表明了当今社会的一个趋势:理性化的“社会”(a rationalised social)的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同理心的“社交性活动”(an empathic sociality)。③[英]约翰·史都瑞:《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张君玫译,巨流图书公司2002 年版,第189 页。因此,学界对于网络时代所招致的“人们社会关系模式的性质变迁,导致了经济生产、政治治理和流行文化所嵌入的社会基础的改变”④杨江华:《从网络走红到网红经济:生成逻辑与演变过程》,《社会学评论》2018 年第5 期。还是保持了普遍的认同,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去衡量其改变的大小和具体机制。本文对以“网络神曲”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消费品的研究努力,正是一个试图引发对该问题深入探讨的楔子。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神曲”的生态在抖音等平台型音乐传播场域兴起以后,已然发生了微妙却深远的变化。当初那种长时间为全社会所“传唱”的热门头部神曲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更新换代越来越快、数量越来越多、“各领风骚三两天”、出自“音乐裁缝”之手的批量化产品。其新陈代谢之快和原创性之弱,甚至让人萌发出“神曲已死”的“哀叹”。这之中既有平台主导下流行音乐再度产业化的关系,也有全社会文化产品快消化的缘由。这种变化(尤其是数字平台的崛起及其对于大众生活的深度介入)究竟是互联网链接社会的一种延续,还是蕴藏着更深层次的颠覆,本文限于篇幅,未能深入分析,希望能够在后续的研究中予以专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