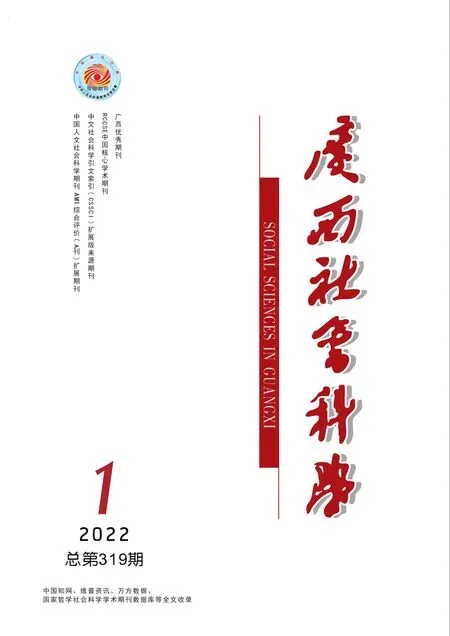《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的“消灭私有财产”: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吴自选,李欣
(1.天津理工大学 外语教学部,天津 300384;2.天津外国语大学 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天津 300204)
博古译本(以下简称“博本”)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汉译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而“消灭私有制”是《宣言》中的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命题,“私有制”及“私有财产”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核心概念。“消灭私有制”在博本中这个命题翻译如下: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表示自己的理论——消灭私有财产[1]。考证表明,1949年以前的另外四个主要汉译本①“四个主要汉译本”指1920年8月以日译本为底本的陈望道译本,1930年3月以英译本为底本的华岗译本,1938年8月以德文本为底本的成仿吾、徐冰合译本,1943年9月据推测以英译本为底本的陈瘦石译本,而没有将以英译本为底本并以成、徐合译本为参照的1948年乔冠华“校译本”包括在内。学界对1920年陈望道译本面世后迄今《宣言》有多少译本,存在不同观点。同样译为“废止(废除)私有财产(私产)”,只有莫斯科译本译为“消灭私有制”[2],与1949年之后的通行译法一致[3]。《宣言》德文原本中的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原初指涉和中文表达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概念是人类思维体系中最基本的单元,构成了对世界抽象性认识把握的重要环节。本文以博本为例讨论“私有财产”概念的起源、演化以及在《宣言》这个命题中“私有制”取代“私有财产”的概念史之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沉淀于概念,概念既是历史转折的标志(Indikator),又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Faktor)。对概念生成和演化基于理论自觉的多元化考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路的转换以及翻译史研究空间的拓展。
一、“私有财产”的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由概念构成,没有基本概念,就谈不上有中国现代文化,而翻译是话语体系构建的主要路径之一[4]。翻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语境之一,概念考察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研究的应有之义。
(一)概念的原初指涉
博本以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的俄文版为底本,并在对成仿吾、徐冰合译本的校订基础上生成[5],而成、徐合译本以德文原本为底本。德语“Aufhebung”有“废除”“取消”“结束”和“撤销”等多种含义,如将其视作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则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含有肯定和否定的双重意蕴”[6],即“扬弃”之义;privateigentum也是一个有“私有财产”“私人财产”“私有制”等含义的多义词。对“消灭(废除,废止)”与“扬弃”私有制之辨,学界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版本研究及其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已得出“消灭私有制”是正确“译语”的结论[7-9],如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一种话语体系,可以确定《宣言》中privateigentum的原初指涉是“私有制”,而不是“私有财产”。“私有制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形式,不仅仅是受资产阶级宪法保护的私有财产”[10],而“共产党人要废除的是私有财产制度,而不是简单废除包括私人生活资料在内的私产”[11]。私有制与私有财产如果不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也存在重大差异。如将乔冠华“校译本”包括在内,1949年之前《宣言》共有七个主要全译本。学界长期以来仅将《宣言》中的“私有财产”与“私有制”之别视作一个“翻译”的问题[12-14]。如是,则无从诠释除莫斯科译本之外的以不同底本(原本与译本)为依据的六个译本中privateigentum皆“翻译”为“私有财产(私产)”。
(二)“私有财产”生成的跨文化性
20世纪后半叶发端于德国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ete)为诠释博本的私有财产概念所关涉的翻译或非翻译的抑或其他因素提供了一种范式。概念史的首要命题是概念即历史,历史沉淀于概念之中,通过对“基本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可以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15]。依据概念史代表人物莱因哈特·科赛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又译“历史性基础概念”)是指“在历史上特别显赫”,在政治和社会语汇中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概念[1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生成的历史性以跨文化性为最显著表征。
汉语中“私有”和“财产”古已有之。“私有”义为“私人拥有的东西”或“私人占有”,《吕氏春秋·孝行览》中即有一例:身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17]。“财产”义为“家庭所有物”或“财富”,早在《汉书·食货志第四上》已经出现:生之者甚少而糜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18]。《后汉书·马援传》也有一列: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19]。德国汉学家李博(Wolfgang Lippert)考证,日语中的“shiyū私有”来源于古汉语的“私有”,“zaìsan财产”受到了古汉语中“财产”这个组合的影响,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私有财产”在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文献中已经出现,并且它的出现形式是“shiyū-zaìsan私有财产”[20]。19世纪末20世纪初,“shiyū-zaìsan”即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被汉语吸收,出现在定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所用的“废除私有财产”这一搭配中:“废私有财产,使归公分配之主义,谓之公产主义,一名社会主义。”[21]王力的研究也表明,尽量利用日语译名是鸦片战争后现代汉语新词产生的一个主要特征:在明治维新之后,利用日本译名成了一种风气[22]。沈国威将中文借用的日语译名称为“近代新词”,近代新词“超越了汉语、日语、朝鲜语等个别语言的框架,成为汉字文化圈概念共享的媒介物”[23]。进入20世纪,私有财产的概念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运用,“在留学和非留学作者的文章中都被使用,在当时的汉语中普及度较高”[24]。对私有财产的概念史梳理表明,日语借词①学界关于“日语借词”有不同界定。王立达认为,日语借词即是某一汉字序列与西方新概念的结合是假日本人之手首先完成,并且为汉语所借用的那些词(参见《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载《中国语文》1958年第2期,第90页);王力对日语借词有更严格的定义:我们不应该认为是汉语向日本语“借”词,这些词并不是日本语固有的,而是从西洋吸收过来的,就一般说,日本原有的词我们并不需要借(参见《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8页)。本文采用王立达相对宽泛的定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生成的主要渊源。早在博本生成的1943年8月之前,私有财产的概念已以日语借词的形式进入中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部分。
概念史又被概括为“历史语义学”,即将概念视作一种动态的、历史主义的建构过程,内含历史经验和理论嬗变的辩证统一,用历史的眼光去考察重要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25]。从以历史性的角度呈现概念的主张出发,博本的“私有财产”具备了历史的“正确性”,“消灭私有财产”具备了历史的合理性。从概念生成之后的语境出发,判定概念“翻译”的“对”或“错”,有悖于概念生成的与生俱来的历史性,是非历史主义的“时代错置”(anachronistic)。
二、“私有财产”的语境性和互为镜像
任何概念的生成以及生成之后的延续生命都不是抽象化的。马克思主义译本研究既要对某一概念作小语境的考证,即上下文(context)考证,又要作大语境考证,即对当时人们普遍使用此术语的情况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作考证研究[26]。概念史视域的博本私有财产概念的“大语境”有两个指向:上述的概念移植所关涉的跨文化的语境迁移,移植之后的概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呈现的语境变迁,且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互动、互释,构成了互为镜像的历史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助推器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大多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也接受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物质的语言形式[27]。博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助推器主要出于两个方面:其一,博本是新中国成立前《宣言》6个汉译本中“发行规模最大、传播范围最广泛”的译本。博本发行量高达62万册,比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及徐冰合译本三者发行总量的10倍还要多[28]。其二,博本在整风运动时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高级干部学习的课本共6种,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名列其中[29]。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又提出要读《宣言》等5本马列原著:“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30]概念是译本的基本组成,而中国化的概念构成了译本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动力。毛泽东说,正是在1920年他第一次看了包括《宣言》在内的几个译本,“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31]。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史观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背景和现状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中国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32]。也正是基于这个概念的中国化,毛泽东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示器
博本中的“私有财产”折射出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和过程性。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延安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3]。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备显著的时代特征,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突出其实践性[34]。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35]。1941年10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作《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指出:“理论还是要学的,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36]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性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37]。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为私有财产的概念赋予了新的政治—社会意涵,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充实和扩展,这种充实和扩展本身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将私有财产视作历史的范畴,认为它的产生与阶级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38]。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出发,在1939年5月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39];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40];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41]。在论述土地问题时则指出“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42]。可见,延安时期的“私有财产”与《宣言》的原初语境和日本的中间语境的“私有财产”产生了不同的意涵与指涉,通过中国革命实践的重新形塑,具备了基本概念的主要属性。
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前提之一是历史在概念中得到表达和阐释。在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为根本目标之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之前,“私有财产”成为“吸纳了社会、政治、经验的‘意义’,并因此储存了丰富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也蕴藏着大量的经验史的历史的‘基本概念’”[43]。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属性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是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实际问题[44]。是否“消灭私有财产”首先取决于延安时期对外来的私有财产概念的诠释和改造,最终和根本的决定因素是中国革命的实践,并非“本本”或从语境中抽离的概念。
(三)互为镜像的概念演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概念由语境形塑,又有助于形塑语境[45]。概念的生成及其生命延续与语境须臾不可分离。博本“私有财产”以汉字文化圈概念交流的形式进入中国语境之时与之后,在折射出历史性的同时也表现出语境性。历史性和语境性是马克思主义概念生成与演化不可分割的两个属性。
梅尔文·里克特(Melvin Richter)认为,科赛雷克、波考克(J.G.A.Pocock)和斯金纳(Quentin Skinner)除强调概念考察“历史化”(Historization)的重要性外,均注重其“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46]。在进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之时,概念自动与日本语境脱离,其社会、文化和政治诉求被剥离,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中被赋予新的政治和社会意涵,启动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再概念化”的进程。其一,如上所述,概念以译本主要元素的形式助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开了概念,则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即是概念中国化的历史,反之亦然。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用于概念的演化。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和范畴”的“实践”的考证表明:毛泽东在1937年7月发表的《实践论》中对“实践”概念加以中国化,对后来“praktische”的翻译产生很大的影响[47]。博本之前的三个译本“实际”与“实践”混用,而博本之后的莫斯科译本、1978年成和徐校译本以及中央编译局定译本统一“译”为“实践”。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和差异性[48]。概念演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互动与互释之上的互为镜像的关系。
三、概念史的“鞍型期”假设与“四化”
概念史关注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和演化逻辑以及导致概念消亡或被替代的缘由。作为一种历史分期的研究假设,“鞍型期”(德:Sattelzeit,英:Saddle Period,又称“马鞍时代”)是科赛雷克1967年提出的重要命题。同时,科赛雷克又推出了概念史的第三个重要命题,即概念是否演化为基本概念的四个标准。
(一)科赛雷克的“鞍型期”与“四化”
鞍型期借用了鞍型山体的意象,即两座山峰之间的过渡地带,指概念的意涵从起源到定型所经历的过渡期(Ubergangszeit)或急剧转变期[49]。科赛雷克将启蒙运动晚期至法国大革命前后一百年的时间(约1750年至1850年)设定为欧洲现代转型的鞍型期。与鞍型期的假设相关,他提出了基本概念的“四化”标准: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时间化(Verzeitlichung)、可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barkeit)和政治化(Politisierung),认为这四个标准使现代政治—社会概念与其前现代的含义区别开来[50]。作为源于西方现代知识制度的研究假设,历史分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角度和问题意识,其上下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四化标准也“既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获得了重要启示,更受到了施密特政治哲学的深刻影响”[51]。方法论意义上的概念史内嵌着西方的价值预设,必须面对一个“中国化”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鞍型期假设
孙江针对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语境提出了基本概念的“四化”,一是规范化:概念无论是本土生发,还是异域传入,都有一个不断被阐释和运用,逐渐走向规范化的过程。二是通俗化:概念应通俗易懂,易与使用者的固有知识嫁接,且应进入社会流通,成为社会性的概念。三是政治化:概念必须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发生关联。时代的变化赋予概念特定的政治—社会意涵,从而成为理解该时代的基本概念。四是衍生化:概念可能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衍生出下位概念,构成概念群[52]。同科赛雷克的标准一样,孙江的四化并非界限分明,也可能互相指涉,然而用以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变迁仍有认识论价值。
严格意义上的基本概念疏证属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主要面向。不论是杨金海的“四段论”[53],还是程勤华的“三段论”[54],延安时期均属于承前启后的重要过渡时期。首先,延安时期是概念大量生成且意涵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一是对外来概念的“化”。外来概念进入延安时期的政治—社会语境,或被吸纳、融合后获得历史性延续,或经批判、改造后被新概念所替代,如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创造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二是对本土概念的“改”。毛泽东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概念赋予新的意涵,以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其中国化,如“民生”“实事求是”“天下为公”等[55]。又如毛泽东对三民主义概念的语义指涉、表达与使用进行批判性继承基础之上的改造,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概念。三是基于革命实践的“创”,如“三三制”“减租减息”“拥政爱民”“统一战线”等。其次,延安时期以不同路径生成的大量概念不仅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而且衍生了概念群,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衍生的“两重任务”“两步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最后,基于革命实践而生成的概念均具有通俗化的特征。然而,将延安时期确定为鞍型期仍与科赛雷克对鞍型期的界定相左。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呈现螺旋式的整体上的行进状态,如将1920年陈望道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视为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呈现概念大量生成且意涵不断变化的状态,不能确定概念起源和定型的“两座山峰”,也不存在概念从起源到定型的一个低落时期。故此,与德国历史经验迥异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不存在明显的鞍型期。
(三)从“(消灭)私有财产”到“(消灭)私有制”
如果以规范化为准绳,进入中国革命和建设语境的“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概念皆具有与生俱来的超经验性,需要在特定的政治—社会语境下得到反复阐释和持续运用,才可能内化为“中国的概念”,并成为在特定时空语境下对政治与社会产生不可替代之影响的基本概念。其一,私有制的概念在1949年之后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深度参与了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运动,承载着改变现状的政治意义,完成了政治化。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56]。1953年6月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质即是生产资料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1953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指出,“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57]。私有制的概念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功能,完成了政治动员和主体召唤的使命。其二,1949年之后,“私有制”在不同历史时期衍生出了概念群。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衍生了“个体小私有制”“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合作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在“54宪法”实施之后,衍生了“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等,形成了庞大的概念群或概念链。“78宪法”的颁行则衍生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多种所有制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等。
科赛雷克提出的基本概念是参与政治和社会史塑造的概念,其演变和运用的过程折射历史变迁的重要特征。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之后,中国政治—社会语境即已完成对“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在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区隔,“私有制”演化为理解1949年之后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宣言》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中privateigentum的译语在博本之后由“私有财产”定型为“私有制”。翻译是诠释,诠释必定是在特定的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等语境下进行;译者是当下语境的译者,必须面对译本生成之时与之后的语境。任何概念都不可能不从当下或传承下来的语境中获取意义[58]。无论是1949年前后《宣言》关于privateigentum的“私有财产”和“私有制”之别,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Aufhebung的“消灭”和“扬弃”之争,与语言和文本已然无涉的特定语境是主要动因之一。
四、结语
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载体。没有概念的中国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私有财产”的历史语义学探索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生成、演化具备特有的跨文化性和语境性,并以互为镜像为表征。同时,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中国化与翻译的异质性、历史性存在深层关联。沈国威认为,语言接受外来新概念,大凡有两种方法,即“译”与“借”[59]。一般意义而言,“译”和“借”分属两个范畴。博本的私有财产概念在近代以降中日概念的密集交流中生成,不属于翻译的范畴。然而,以日语借词的路径生成的概念存在于翻译客体之中,是译本的基本构成。王力认为,汉语词汇与西方语言(主要是英语)的翻译上的对应关系的确立,主要得力于日本的近代译名[60]。由此,“借”的实质是“译”,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日语借词应置于翻译的范畴;如是,概念史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国化研究深化了对翻译为何、翻译何为等本质问题的探索,通过从更广阔的时空考察翻译的内外部诸要素的复杂关系,推动了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的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