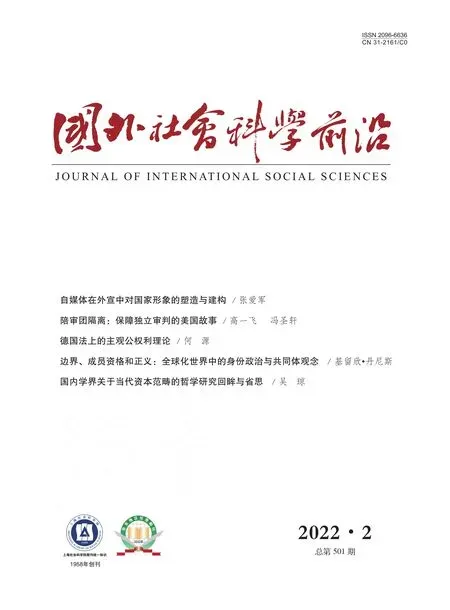陪审团隔离:保障独立审判的美国故事*
高一飞 冯圣轩
1215 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确立了陪审团制度,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后,陪审团制度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同时也出现了较大的不同。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在英国对美洲的殖民扩张中得以建立和发展。经过200 多年的发展,当初的制度基础,陪审团的选拔、组成、运作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在面对蓬勃发展的新闻媒体行业时,美国创造性地建立了陪审团隔离(sequestered jury)制度,用以隔绝媒体报道、社会舆论等外部因素对陪审团裁决的影响。本文对陪审团隔离制度这一古老而奇特的制度进行介绍和评析,并期待给中国司法制度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陪审团隔离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陪审团隔离制度可以追溯到18 世纪,历经200 余年的发展,它自身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其变化的特点是:从最初要求所有案件都隔离陪审团,发展到后来的陪审团隔离的有限适用。其基本方法是对陪审团与外界进行物理上的隔离。
(一)陪审团隔离的历史沿革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收藏着一幅史上第一个被隔离的陪审团即帕蒂·赫斯特陪审团1The Bancroft Library, Patty Hearst Jury: First sequestered jury in history of U.S. San Francisco Federal Court, https://calisphere.org/item/ark:/28722/bk000602j1b.的画像。该陪审团作为“波士顿大屠杀”案的陪审团,于1770 年被隔离。在当时,一旦陪审团宣誓就职,在作出裁决之前就不能离开法庭,由于案情的复杂、相关先例和法律规定的缺失,该陪审团被隔离了8 天。在“波士顿大屠杀”案的审判过程中,陪审团成员在审理期间被禁止与自己的亲人、朋友接触,最终裁决8 名士兵中6 名士兵无罪,2 名士兵犯过失杀人罪。2Boston Massacre Historical Society, The Boston Massacre Trial, http://www.bostonmassacre.net/trial/index.htm.这被认为是陪审团隔离制度的正式建立。在早期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不管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所有的审判都对陪审团进行了隔离,借此来保障陪审团认定事实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同时,由于早期案件情况通常比较简单,陪审团往往在一天之内就能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决。在这种短期的隔离中,陪审团隔离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更未得到重视。
在注意到陪审团隔离的负面效果之后,各州和联邦政府逐渐缩小了陪审团隔离制度的适用范围。在民事案件中,完全取消了陪审团隔离制度的适用,它在刑事案件中的适用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3James P. Levine, The Impact of Sequestration on Juries, Judicature, vol. 79, no. 5, 1996, p. 266.在1819 年一个案例中4Marcy Strauss, Sequestration, 24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996, p. 71.,法院没有强制适用陪审团隔离制度,而是让陪审团在正常的社区环境中进行案件审判,强制隔离陪审团的原则被突破。在这一阶段的初期,虽然法律强制规定隔离所有的陪审团,但在实际操作中,由法官裁量决定是否适用陪审团隔离,即使是在某些可能被判处死刑以及其他严重的暴力犯罪的案件中。5Marcy Strauss, Sequestration, 24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996, p. 71.到了20 世纪初,陪审团制度有了新发展。陪审团成员不再仅仅局限于案件管辖地区,从案件管辖区外筛选陪审员成为可能,改变审判地点也成为了陪审团隔离的替代性措施。到20 世纪中叶,大多数法官都将隔离陪审团作为一种非常规的手段,而不是必须遵守的规定。6Nancy J. King, Juror Delinquency in Criminal Trails in America, 1796-1996, 94 Michigan Law Review, 1996, p. 2673.正如一位法官写道:陪审团的隔离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和关注,刑事审判历时很长以及隔离陪审团所付出的住房和生活需要等昂贵代价,加剧了现代陪审团隔离观念从古老的“隔离陪审团是确保案件裁决正确的前提”观念中淡出。1State v. Pontery, 117 A. 2d 473, N. J. 1955.这意味着司法观念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法官不再认为隔离陪审团是保证案件公正处理的前提。
总体来说,民事案件完全禁止陪审团隔离制度的适用,这是因为民事案件仅是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并不值得通过隔离陪审团的方式来认定案件的事实。在刑事案件审判中,法官一般也不会采取隔离陪审团的措施,除非媒体报道得过于严重,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官才会下令隔离陪审团。2Bruce Tomas, Jury Sequestered in Trial of Former Dallas Cop Who Shot Black Man in His Home, https://www.msn.com/en-us/news/us/jury-sequestered-in-trial-of-former-dallas-cop-who-shot-black-man-in-his-home/ar-AAHIyZa.陪审团隔离的有限适用成为主流的观念。
(二)陪审团隔离的基本要求
根据美国国家法律网站的定义,陪审团隔离是指对陪审团的整体隔离,以避免对陪审团意外的或故意的污染。3US League, Definitions of Sequestration, https://definitions.uslegal.com/s/sequestration.为了保护陪审团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通常在隔离陪审团的决定作出之后,陪审团成员将被聚集在一起,他们的饮食起居由法院来统一安排。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联邦和各州都有自己的规则,但内容相差无几。在此,我们以联邦陪审团隔离规则4United States Courts, Juror Pay, https://www.uscourts.gov/services-forms/jury-service/juror-pay.为例。在隔离期间,法院会发给每一个陪审员每日50 美元的薪酬,在隔离10 日之后,每日薪酬增加为60 美元。在隔离期间,陪审团成员不能与外界联系,必须遵守下列规则:(1)陪审员不得在陪审室使用手机;(2)陪审团审议期间使用洗手间时必须有法院人员陪同;(3)陪审团必须与法院人员一起乘坐公共汽车往返法院;(4)陪审员必须在经过法院人员监督的情况下入住经批准的酒店;(5)陪审员必须在经批准的餐厅内用餐,并接受法院人员的监督;(6)陪审员不得阅读报道案件的报纸或互联网信息;(7)陪审员不得收看报道案件情况的电视节目;(8)陪审员之间不得讨论案件情况。
陪审团隔离的时间一般比较短,早期的陪审团隔离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一天,也就是所谓的“一日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日益复杂的案件导致陪审团隔离的时间不断延长,远远超过初期隔离的期限。在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O. J. Simpson)案件中,陪审团被隔离了265 天,5Thomas MacMillan, How the Psychological Toll of Isolation Might Be Affecting Bill Cosby Jurors, https://www.thecut.com/2017/06/sequestered-jury-psychological-toll-cosby-trial.html.超越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案8 个半月的隔离时间,6Alene Tchekmedyian, Charles Manson Hospitalized in Bakersfield; Prison Officials Says He’s Still Alive, https://www.latimes.com/local/lanow/la-me-charles-manson-hospitalized-20171115-story.html.成为历史上陪审团隔离时间最长的案件。
(三)陪审团隔离适用的程序和比例
陪审团隔离的决定程序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法官根据实际决定,另一种是法律规定必须隔离陪审团。具体说来,第一种是所有案件都由法官裁量决定是否隔离陪审团。在联邦和大部分州是这么处理的。如肯塔基州1KY. REV. STAR. ANN § 29A. 310, Michie 1992.,如果要将陪审团隔离,必须由法院作出指示,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哪些情况必须隔离陪审团。同时,大部分州都规定,隔离陪审团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补救手段,如新泽西州2N. J. R. GEN. App.p.1: 8-6.规定:在法院指示陪审团之前,任何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不得隔离陪审团,除非法院发现有特殊情况,如为了保护陪审员的人身安全,或者为了公正裁判需要。俄亥俄州3OHIO R. CRIM. P. 24 (G).、田纳西州4TEEN. CODE ANN. § 40-18-116, 1990.、北卡罗来纳州5State v. Wilson, 322 NC 117, 1988.也有类似规定。
第二种是死刑或特殊案件由法律规定一律隔离陪审团。如佐治亚州6GA. CODE. ANN § 15-12-142, Michie 1994.、路易斯安那州7LA. CODE. CRIM. P. ANN art. 791, West 1981 & Supp. 1996.规定,死刑案件一律隔离陪审团;爱达荷州8IDAHO CODE § 19-2126, 1987.规定仅在被告被指控一级谋杀罪时,才强制隔离陪审团。纽约州则经历了一个变革的过程,在1995 年之前,规定在任何由陪审团审判的刑事犯罪案件当中,审议阶段必须隔离陪审团;在重罪案件中,审议和审判阶段都必须隔离陪审团。9James P. Levine, The Impact of Sequestration on Juries, Judicature, vol. 79, no. 5, 1996, p. 267.同时,纽约州也是最后一个在所有重罪案件中都适用陪审团隔离的州。在1995 年6 月修改法律后,纽约州也采取了与其他州相同的灵活政策,进一步限制了强制隔离陪审团的案件范围,仅在最严重的暴力犯罪案件中强制隔离陪审团。
陪审团制度是美国诉讼制度的重要基石,但是近年来,陪审团审判的案件却逐年递减,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为“消失的陪审团”。美国民事案件中适用陪审团的比例为2%,在刑事案件中适用的比例为3%。10Thomas H. Cohen, Felony Defendants in Large Urban Counties, 2006, Working Paper for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May 2010, NCJ 228944.而陪审团隔离制度的适用比例则更低,民事案件禁止隔离陪审团;刑事案件方面,由于美国司法系统的复杂性,我们难以找到年度的全国统计数字。纽约州1994 年隔离陪审团1400 个,占所有刑事案件的比例不足1%。纽约州是美国各州中陪审团隔离制度适用频率最高的州。11James P. Levine, The Impact of Sequestration on Juries, Judicature, vol. 79, no. 5, 1996, p. 267.可以推断,其他地区的隔离比例远低于1%。尽管如此,在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以及被指控一级谋杀的案件中适用更加严格、更加独立的陪审团事实认定程序,这既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也对保护被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违反陪审团隔离的程序性后果
违反陪审团隔离的程序性后果体现在,如果因为没有满足被告人隔离陪审团的要求而导致审判不公,被告人可以因此提出上诉,要求上诉法院认定原审无效。审判无效的案件应当重新组成陪审团进行一次新的审理。
在研究违反陪审团隔离要求是否能够单独否定判决有效性的问题时,笔者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案例。在1995 年《纽约州刑事诉讼规则》之前,就已经存在强制隔离陪审团的情形。在1990 年的卡农案1People v. Coons, 75 N. Y. 2d 796, 1990.中,初审法院在审判时未按法律规定强制隔离该案件的陪审团,在陪审团作出有罪裁决后,被告提起上诉。上诉法院裁定初审未隔离陪审团,违反法定程序,判决初审无效,应当重审;并认为,虽然被告并没有在审判时提出反对初审法院未隔离陪审团的做法,但是这并不妨碍对于本案的重审。
1991 年发生在纽约州的韦伯案2People v. Webb, 78 N. Y. 2d 335, 1991.中,初审时辩护人与控方在庭审过程中,讨论了如果陪审团未在下午4:50 之前作出裁决,是否允许陪审团成员回家休息的问题。讨论达成一致,辩护律师及被告韦伯都允许陪审员在上述情况下回家休息,并明确表示同意放弃《纽约州刑事诉讼规则》第310 条第10 款隔离陪审团的权利。第二天,陪审团裁定被告有罪,被告立即提起上诉,其声称初审法院允许其放弃强制隔离陪审团的权利是错误的。上诉法院认为:在该案中,法官对于案件的处置属于法院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之内,并没有表现出对被告的偏见;而且未隔离是无法逆转的,本案中没有强制隔离陪审团符合联邦对于该问题的认识。因此,上诉法院维持了有罪判决。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规定强制隔离陪审团的地区,未隔离陪审团也不会必然导致“审判无效”。纽约州的案例明确了一点,即陪审团隔离制度是一项法律规范,并不是“反映被告的一项既定的普通法权利”。3People v. Webb, 78 N. Y. 2d 335 339-340 (1991).如果要重新审判,那么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严重损害司法公正或者造成了对被告的偏见,这一条件是否满足由法院进行判断。
二、陪审团隔离制度的预设功能
陪审团隔离制度在美国适用的频率虽然逐渐下降,但不可否认该制度曾为司法公正作出的贡献。陪审团制度的创立就是为了公正审判,法官认定的案件完全交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进行裁决,陪审团对于案件事实的一致裁决也被教会认为是“上帝声音最可靠的显示”4J. Roland Pennock, Majority Rul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536.。
(一)阻却偏见性报道
“根据证据决定事实,你们是事实的法官,你们将听审证据,得出事实结论,作出裁决”,这是对陪审团责任的描述。5Jeffrey Abramson, We, the J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9.但陪审员也是普通人,可能受到媒体的影响,这就是所谓媒体审判。6高一飞、华迪·莫汉森:《审前报道对美国刑事审判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7 年第5 期,第221~226 页。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了新闻媒体报道的自由。随着新闻媒体行业的不断更新发展,公民获取信息的途径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从口口相传,到通过书刊、报纸,再到通过互联网,公众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之前不可能了解到的信息。如果陪审员在日常生活中了解了案件的有关信息,特别是当陪审员得到了带有偏见性的误导,那么极有可能会导致媒体审判。
美国很早就对媒体可能对司法造成的干扰表示了关切,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在1907 年的一个判决中提到,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唯有依证据以及公开审判辩论后,才可以对被告定罪,绝对不能受到法庭外的任何影响,不论是私人的议论还是出版品。1陈新民:《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一个比较法制上的观察与分析》,《台大法学论丛》2000 年04 月号,第89 ~134 页。但新闻报道却无孔不入,例如在辛普森案件中,案件在全美国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人们想象。据统计,从1994 年到1997 年,关于案件的新闻报道多达2237 条。2Alan M. Dershowitz, America on Trial: Inside the Legal Battles That Transformed Our Nation,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04, p. 607.甚至电视台都在直播对于辛普森的追捕,几乎找不到对案件情况一无所知的人。3Marcy Strauss, Sequestration, 24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996, p. 109.即使在选择出合适的陪审员并要求他们拒绝接触外界信息之后,审判阶段中对于案件的新闻报道也很有可能被陪审员知晓,媒体报道必然会对陪审员的独立判断产生影响。
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确立了被告有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这就要求陪审员必须在没有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依据案件的证据材料,独立地作出对案件事实的裁决。陪审团隔离成为了破解媒体审判的一种“笨办法”,建成了防止陪审员接触外界信息的物理屏障。陪审团隔离制度在独立审判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冲突中扮演了一个调和者的角色。
(二)防止亲友和民众的影响和干扰
由于陪审员是从普通的市民中选出的,一旦被选为陪审员,就意味着陪审员原有的正常生活遭到破坏。对于社会影响较小的案件来说,审理周期较短,对陪审员的正常生活冲击较小;而对于社会影响巨大的案件来说,审理周期可能长达数周甚至数月,那么陪审员就不可避免会接受来自家人和朋友的询问、干预。
在没有陪审员隔离的情况下,陪审员每日回家,与其接触的亲友会传达对案件的看法。举例来说,一个陪审员的配偶对于案件事实的看法、对于死刑的态度,或种族歧视、宗教偏见,都会传达给陪审员本人。4Nancy King, Nameless Justice: The Case for the Routine Use of Anonymous Juries in Criminal Trials, 49 Vanderbilt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96, p. 123, 127.又如,在一起案件中,7 位陪审员在休庭时,收到了来自民众的纸条,上面写着,“这些几内亚母狗有罪。你们不要考虑审判后面临的压力而改变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毋庸置疑,陪审团隔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来自亲友和社会的压力和干扰,有利于陪审员对案件作出理性、客观的判断。
(三)保证陪审员的人身安全
在极端情况下,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可能会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来干扰陪审员的独立判断。这些情况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例如,在涉及黑手党头目的一些案件中,出于安全的考虑,许多陪审团被隔离。
在1985 年发生的一个案件中,由于案件被告的特殊身份,为了保护陪审员的人身安全,法院下令隔离陪审团。1United States v. Thomas, 757 F. 2d 1359, 1365 (2d Cir. 1985).这也是法官首次出于担心陪审员人身安全而隔离陪审团。1992 年,在联邦警察被指控殴打罗德尼·金的案件中,州法院陪审团在宣布被告警察无罪时,局势十分紧张。1993 年联邦法院重审此案时,联邦法官担心联邦陪审员的人身安全,陪审员因此被隔离了57 天。2Stephanie Simon and Ralph Frammolino, Despite Perks, Sequestration is a Gilded Cage, Jurors Say,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5-01-15-mn-20300-story.html.在隔离陪审团的审判中,陪审员获得安全环境,可以在没有顾忌的情况下进行审判;在审判之后,因为要求一致裁决,责任分散在12 个陪审员的身上,一般也不用担心事后报复。
由此可以看出,陪审员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人身威胁。这种类似好莱坞影片中的桥段在日常生活中也在上演。完全有理由认为,在陪审员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其作出的裁决是难以符合内心确信的。陪审团隔离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四)通过形式正义增强司法公信力
保障司法公正是陪审团隔离制度得以存在的最重要的价值。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确立了被告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也即在任何情况下,被告都应当接受到相同的审判待遇。在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的审理,法官负责案件量刑的确定。为了确保被告享受到相同的审判待遇,陪审团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应当保持同等的理性和客观。
陪审团隔离制度消除了审前宣传、外界压力等因素,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被告和社会公众对于司法不公的担忧,保证了陪审团独立进行审判,这对于实现“看得见的正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自认为法律制度高度完善的国家,在辛普森案件审判完成后,如果没有陪审团隔离制度,我们难以宣称我们的审判实现了最大可能的公平公正。”3Marcy Strauss, Sequestration, 24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996, p. 104.尽管陪审团隔离并不能完全保证司法裁判结果的绝对公正,但至少其保证了裁判具有一个公正的基础和外观,增强了裁决的社会认可度,让被告和社会公众在案件审判中感受到司法的公正。
三、陪审团隔离制度的现实局限
陪审团隔离制度的建立初衷是隔绝外界偏见性报道,保障陪审团根据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进行内心确信,作出独立、公正的裁决。但在现实中,陪审团隔离对公正审判的预设功能并没有全部实现,而是存在很多局限。
(一)孤独心境下的仓促审判
在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一旦被决定隔离,在漫无终点的隔离期间内,陪审团为了早日从隔离中解放出来,有可能仓促决定,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隔离就其本质而言,是对陪审员个人权利的一种减损,那么加快审判进程就可能会变成陪审员用来摆脱隔离状态的重要方法。在辛普森案件中,陪审员在经过265 天的隔离之后,其精神状态和判断能力已经与正常人有些不同。在面对多达45000 多页的笔录和1000 多张照片的证据材料时,陪审团仅仅在4 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1Marcy Strauss, Sequestration, 24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996, p. 112.陪审员的效率令人震惊。该案的一个陪审员迈克尔·诺克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在这种隔离的情况下,我认为每个人都渴望得出结论。”2Thomas MacMillan, How the Psychological Toll of Isolation Might Be Affecting Bill Cosby Jurors, https://www.thecut.com/2017/06/sequestered-jury-psychological-toll-cosby-trial.html.陪审团成员毕竟是来自公民群体的普通人,在被隔离近9 个月之后想与亲人团聚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这与设立陪审团隔离制度的本意就相去甚远。
正如一位记者在评论中指出,“许多律师和社会科学家认为,马拉松式隔离的痛苦将导致陪审员审议的速度过快……隔离的目的甚至就是判决本身。”3James P. Levine, The Impact of Sequestration on Juries, Judicature, vol. 79, no. 5, 1996, p. 270.在电影《十二怒汉》中,其中一名陪审员将他的投票由有罪转化为无罪,以加快判决形成,因为他不想错过一场棒球比赛。尽管这种轻率的行为可能并不常见,但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陪审员急于从严肃的隔离状态中脱离出来。经过长时间的隔离之后,陪审员回家的愿望可能与做一个正直的陪审员的愿望一样急切。4Marcy Strauss, Juror Journalism, 12 Yale Law & Policy Review, p. 389.动机不纯的仓促判决,可能会扭曲正常的陪审团审议过程,破坏审判过程的完整性,导致案件草率处理,甚至出现错案。
(二)亲密关系下的附和决定
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相同身份的陪审员们往往更容易产生亲密的朋友关系。即使是在对于案件证据、事实的认定上存在严重分歧的陪审员之间,他们的关系也会如此。而陪审团审判的特殊要求即“一致裁决”又不允许陪审员们不顾他人的意见而作出多数裁判,这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陪审团“一致裁决”要求12 个陪审员要么全部同意有罪,要么全部同意无罪,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则解散陪审团,另组陪审团进行审判。这一制度起源于英国,但英国一致裁决原则在1967 年刑事司法法中被修改,这一法律规定:如果陪审团未能在2 小时内达成一致裁决,可以采用绝大多数人同意的裁决。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坚持要求陪审团达成一致裁决,但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是否规定陪审团一致裁决。5高一飞:《陪审团一致裁决原则的功能》,《财经法学》2018 年第6 期,第114 ~128 页。一致裁决使被隔离的陪审员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变化,也产生了陪审团内部复杂的社会关系。从美国所谓“吊死的陪审团”的情况来看,有大约3%的联邦刑事案件会在陪审团僵局的情况下终结,而在各州这一比例会高一些。1Nancy Jean King, The American Criminal Jury,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62, Spring 1999, p. 41.绝大多数案件在大家的协商与说服过程中形成一致裁判,而这个过程,就是陪审员之间亲密关系形成的过程。
陪审团寻求的是决定者人数较多这样一个数量上的安全;要求通过协商一致和深思熟虑达成一致裁决;要求在独立的法庭上进行审判,与国家隔绝,扮演上帝的角色。2Jeffrey Abramson, Four Models of Jury Democracy, 90Chi.-Kent L. Rev., 2015, p. 861.一致裁决的要求在美国电影《十二怒汉》、俄罗斯翻拍版《十二怒汉》、中国电影《十二公民》中都有展现。
在陪审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形成后,大多数陪审员可能会更倾向于认可其他陪审员的意见,而忽略掉自己对于案件事实的独立分析和认识。隔离催生了一种彼此之间潜在的利益关系:聚居在一起的陪审员相互陪同,会感慨艰辛的陪审员经历,以及抱怨与法院之间的沟通不足;当陪审员之间相互熟悉之后,特定陪审员的偏见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陪审员;隔离状态下产生的交流欲望,还可能使他们忽略文化背景差异而加强沟通。一起案件结束之后,陪审员之间已经成为了一个“家庭”。3Andrew L. Yarrow, Jury Renders Mixed Verdict in Atticn Case, https://www.nytimes.com/1992/02/05/nyregion/juryrenders-mixed-verdict-in-attica-case.html?searchResultPosition=5.虽然不能确定陪审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陪审员的独立审判,但这种关系对陪审员独立判断的影响是必然存在的。
总的来说,隔离期间的陪审团成员会因为在一起的经历而相互熟悉,这有利于促使陪审团达成一致裁决。但这种熟悉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又可能导致附和判决,成为司法公正的潜在威胁。
(三)异常心理下的情绪化裁决
鉴于隔离期间的特殊规定,陪审员往往会感觉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种不公平的来源便是控辩双方。陪审员很可能将怒气发泄在控辩之间某一方的身上。
一项纽约州的比较研究表明,隔离陪审员的定罪率比非隔离陪审员的定罪率高出16%。4Winick Smith, Post-Trial Sequestered Juries Tilt Toward Guilty Verdicts, New York Law Journal, Dec. 1986, p. 1.在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刺杀罗恩·里根(Ronald Reagan)一案中,一位陪审员认为欣克利有罪,但其他陪审员坚持认为无罪,最终该陪审员改变意见,案件达成一致裁决:认为被告欣克利精神失常,作出了无罪判决。这位陪审员说道:“我迫于压力而改变自己的意见,我整夜都在颤抖,我必须离开那里。”5Reporter, 2 Jurors Assert That Pressure Forced Them to Alter Votes, https://www.nytimes.com/1982/06/23/us/2-jurorsassert-that-pressure-forced-them-to-alter-vote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在被隔离的高压环境之下,陪审员很容易产生对原告或被告的偏向,而故意作出与内心确信相反的判断。
这种情绪性裁决是有利于被告人,还是有利于控诉方?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许多律师坚称隔离陪审团有利于控方,原因在于陪审团会认为,让他们饱受隔离之苦的罪魁祸首是被告人,从而在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中,更倾向于认定被告人有罪。1C. Winick and A. Smith, Post Trail Sequestered Juries Tilt Toward Guilty Verdict, New York Law Journal, Dec. 1995, p. 1.如有人认为:“至少在陪审员的心中,正是被告人的错误使他远离家人、工作和熟悉的社区环境。”2Marcy Strauss, Sequestration, 24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996, p. 115.相反的观点则认为,隔离陪审团是被告的福音,因为陪审员会认为自己目前的遭遇是由于国家下令将陪审团隔离,毕竟是国家权力直接作出的隔离决定。3Marcy Strauss, Sequestration, 24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996, p. 115.因此,陪审团也可能在认定案件事实的时候对控方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认定被告人无罪。
在情绪化裁判中,不同的陪审员可能存在不同的倾向。但是无论陪审员如何倾向,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看见的。法院隔离陪审团是期望陪审员能够完全公正、客观、中立地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决,而非存在对某一方的偏向。
(四)隔离前或者配偶探访中的信息污染
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报道权与宪法第六修正案所保障的被告接受公正审判权发生冲突时,多数法官不赞成绝对禁止对新闻媒体进行一切事前约束。在美国的司法传统中,法院可以通过颁发“媒体禁言令”(Gag Order)来要求新闻媒体不得对某一案件的某些内容进行报道。但是,“媒体禁言令”在1976 年遭到联邦最高法院以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而遭到废弃。4[美]唐纳德·M. 吉尔摩等:《美国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第六版)》(上册),梁宁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366 页。更重要的是,在自媒体时代,一旦发生重要案件,自媒体通过手机就可以对案件进行自由地报道和评论。5高一飞:《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中外法学》2016 年第2 期,第492 页。陪审团是进入审判阶段才选出的,而案件经过了侦查、起诉等漫长的诉讼阶段,在这一段时间内,作为网民的陪审员候选人对案件已经作了了解。可以说,在今天,要选出一个没有看过审前报道的陪审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陪审团隔离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只能隔离成为陪审员以后这段审判时间的媒体信息,但是,审前报道的影响和对陪审员内心的污染已经无法挽回。
除了审前媒体报道的影响,在陪审团隔离期间,陪审员也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信息,其重要的方式就是配偶探访中的配偶信息交流。为了解决陪审团隔离措施对陪审员人身自由的过度强制问题,所有的法院都允许陪审员隔离期间,在特定的短暂时间内与自己的配偶正常接触。这种规定被称为“配偶访问(conjugal visit)制度”,被隔离的陪审员的伴侣在可监管的前提下进行私密会见,期间他们可以有性行为。配偶访问通常每周进行一次,一般来说在每周日的下午,但是在某些隔离时间特别长的案件当中,为了保证陪审员正常的心理状态,配偶访问次数可以增加到每周两次。6Keith W. Hogg, Runaway Jurors: Independent Juror Research in the Independent Age, Wester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Jan. 2019, p. A121.辛普森案件便是如此。在这起案件中,部分陪审员在配偶访问期间接触到了新闻媒体报道的“福尔曼录像带”,在当时,这一电视台广泛播放的内容并没有提交法庭,陪审员是不被允许接触这类物品的。1Keith W. Hogg, Runaway Jurors: Independent Juror Research in the Independent Age, Wester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Jan. 2019, p. A121.配偶访问制度的存在表明,陪审团隔离制度并没有绝对完全隔绝媒体新闻报道,仍然存在陪审员接触媒体报道的潜在可能。然而,作为对陪审员最低限度的人权保障,每周1~2 次的配偶访问又是必要的,这就给了陪审员间接了解媒体报道和受到社会影响的机会。
综上,在担任陪审员之前通过媒体报道对所审理案件的了解,以及配偶探访中的信息交流,导致被隔离的陪审团实际上可能被媒体和其他舆论污染,隔离的作用因而被消减。
(五)法院为减轻管理负担而限制正当程序
一般来说,采用陪审团审判的案件数量较少,采用隔离的案件数量少之又少,但是一旦陪审团被隔离,法院就将承担起相对于普通案件更大的责任,同时也要付出更多的人力、财力。隔离时间越长,投入的人力、财力就越多,法院也会通过相关的方法来加速审判的进行。
为了减少法院在陪审团隔离中管理上的负担,法官在庭审中会尽其所能,如通过限制证人人数或限制律师陈述等方法来加速案件的审判。2Commonwealth v. Hayes, 414 A. 2d 318, 348, 1980.因为过于冗长的审判过程不仅会耗尽陪审员的耐心,对法院管理或法官精力也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无论是好是坏,面对陪审团隔离的案件,法院都极有可能利用其掌握的所有方法来最大限度地缩短案件审理的周期。3Marcy Strauss, Sequestration, 24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996, p. 116.而法院和法官对正当程序、辩方权利的限制,必然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这样一来,隔离陪审团就不能成为促进司法公正的措施,反而造成司法审判过程的扭曲,破坏司法审判的完整性和公正性,对司法公正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四、陪审团隔离制度的衍生问题
除了上述提到的难以实现公正目标的局限,陪审团隔离还存在其他方面的现实困境。
(一)耗费巨大的诉讼成本
在决定隔离一个陪审团之后,国家至少要承担12 名陪审员以及2 名预备陪审员(或译为候补陪审员、替补陪审员)的相关经济成本,包括住宿、饮食、交通以及陪审员薪酬等必要的费用。设立预备陪审员的目的是:当有一名陪审员出于某种原因从陪审团中被剔除,就会有一名预备陪审员加入陪审团。当所有预备陪审员都进入陪审团但仍然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事实认定团体时,一切程序甚至还会被推倒重来,这是更加严重的财务成本消耗。
在隔离时间较短的案件中,费用一般还可以接受,但在像辛普森案件这样的隔离时间长达265 天的案件中,费用十分高昂。据统计,辛普森案件隔离陪审团总花费超过300 万美元。4William Brown, James Duane and Benson Fraser, Media Coverage and Opinion of the O. J. Simpson Trial: Implications for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ommunication Law and Policy, p. 263.在隔离时间没那么长的其他案件中,也存在花费不菲的情况,例如在罗德尼·金案件的隔离过程中,57 天的隔离花费高达204055 美元。1Stephanie Simon and Ralph Frammolino, Despite Perks, Sequestration is a Gilded Cage, Jurors Say,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5-01-15-mn-20300-story.html.纽约州作为隔离陪审团最频繁的地区,1994 年强制隔离陪审团的花费超过400 万美元。2Marcy Strauss, Sequestration, 24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996, p. 106.应当注意的是,以上数字并非案件诉讼的全部费用,而是指陪审团隔离这一项费用,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因此,沉重的财务负担成为限制陪审团隔离制度的一个合理理由。
(二)影响陪审员正常生活
一旦决定隔离,陪审员就将从原来生活的环境中搬离,进入另外一种完全陌生,甚至与外界彻底隔绝的环境。并且,这段时间多长是不确定的,时间越长,对陪审员造成的影响就越大。在隔离的环境中,陪审员将无法与亲人、朋友见面,可能错过婚礼、孩子出世或父母病重等对人生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甚至有陪审员因此离婚。在被隔离期间,陪审员的个人生活完全暴露在摄像头之下,与外界的通信受到监听和筛选,甚至在卫生间也有法院的官员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个人权利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害。
许多被隔离的陪审员在回顾案件审判过程时,都认为那是一段“极其糟糕的经历,像地狱一般”。3Marcy Strauss, Sequestration, 24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996, p. 107.在查尔斯·曼森案的审判中,一位在审判期间被隔离了8 个半月的陪审员说道:“我就像一个犯人,没有任何的权利。”4James E. Kelley, Addressing Juror Stress: A Trial Judge’s Perspective, 43 Drake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94, p. 96.另一位陪审员在审判过程结束后离婚,并把离婚归因于陪审团的隔离决定。5James E. Kelley, Addressing Juror Stress: A Trial Judge’s Perspective, 43 Drake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94, p. 97.在前劳工部长雷蒙德·多诺万(Raymond Donovan)的受贿案审判中,一位陪审员因隔离时所遭受的压力而精神恍惚,在隔离结束几天内就被解雇。6Marcy Strauss, Sequestration, 24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996, p. 109.因此,隔离这种非常规的措施将会严重地打乱陪审员的日常生活,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会严重改变陪审员的人生轨迹。
虽然陪审员所承受的压力可能并非全部来自隔离本身,但是,隔离加剧了陪审员心理状况的恶化,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种伤害不仅充斥在整个隔离过程中,还波及陪审员结束审判之后的日常生活。同时,这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伤害,还包括物质上的损失。
(三)导致陪审员心理问题
隔离的环境造成了压抑的氛围,这对有些陪审员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禁止同外界交流所带来的孤独和无助,都在不断刺激陪审员原就紧张不安的神经。同时,鉴于被采取隔离措施的案件的特殊性,陪审员们往往需要接触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细节、情绪激动的证词以及难以理解的法律术语。因此,隔离期间越长,对陪审员影响越大。
在纽约州的一个案件中,陪审团在经历4 个月的长时间隔离后,经过多次审议仍然得不出确定的裁决,于是他们恼怒地要求会见法官,要求解除隔离,法官最后裁定解散陪审团。1Raymond Hernandez, Westchester Trial Illustrate the Burdens of Jury Service, https://www.nytimes.com/1994/12/19/nyregion/westchester-trial-illustrates-the-burdens-of-jury-service.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有研究表明,在孤立的环境下被迫与陌生人共同生活的人有时会感到沮丧,并富有攻击性。在纽约发生的另一个案例中,一名陪审员因受不了长期隔离所产生的心理压力,在夜间尝试逃离隔离场所。他利用床单连结成绳索从隔离宾馆二楼跳出,后来在第二天被法院工作人员发现。2Robbie Manhas, Responding to Independent Juror Research in the Internet Age, Michigan Law Review, 2014, p. 816.在辛普森案件中,陪审员特雷西·肯尼迪(Tracy Kennedy)在被隔离2 个月之后,因为违反伊藤法官的一项命令,而被责令退出陪审团,在这几个月后她曾试图通过服用药物自杀。3Linda Deutsch, Simpson Jurors Get Guarded Maps, Beacon Journal, Jan. 1995, p. A5.该案中的其他陪审员也都表示,被隔离的经历不堪回首,他们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
不难看出,隔离陪审团所创造的封闭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保证陪审员身体上的安全,但隔离陪审团的措施对陪审员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
五、评论与启示
纵观整个陪审团隔离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隔离制度在应对偏见性报道、保护陪审员人身安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不能否认,隔离制度存在自身的功能局限和负面作用。只有在经过对影响案件审判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之后,才能适用陪审团隔离制度。
陪审团制度的设计是以陪审员具备基本理性为基础的,既然选择将案件交由陪审团来审判,那么就应当相信陪审员能够公平公正地认定案件事实,能够理性对待外界因素的影响。在陪审团独立审判的问题上,不仅要靠技术和细节处理为独立裁判创造客观条件,更多地要靠陪审员作为公民代表的理性和良心。同时,在技术方面也不应当固守古老的做法,要对传统进行适当改革和完善。
在隔离过程中,探索使隔离更加人性化的措施,保障陪审员的正常需求,这样才能让这一古老而特有的制度扬长避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如在2017 年纽约州发生的一个案例中,法官注意到了陪审员的不良情绪,为了防止不良情绪干扰到审判过程,在隔离的22 天里,法官组织陪审员去打保龄球和购物,还组织所有陪审员去看了电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孤独的游侠》。4Thomas MacMillan, How the Psychological Toll of Isolation Might Be Affecting Bill Cosby Jurors, https://www.thecut.com/2017/06/sequestered-jury-psychological-toll-cosby-trial.html.隔离并不意味着陪审员只能待在法院和宾馆两个地方。根据笔者在美国陪审团审判现场的观察和采访,在陪审员被隔离的过程中,除了在宾馆播放与新闻报道无关的、不属于电视台节目的影视节目(特别是冗长的肥皂剧)外,由法官组织的与外界无联系的、隔离状态下的购物和文体活动,能够让枯燥的隔离生活丰富一些。这种灵活的隔离措施值得推广。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除了对陪审团隔离制度自身的优势、局限作出分析并提出评论之外,还对新闻自由、司法公正等重要价值的意义、边界和实现机制进行了思考,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情权是基本人权,但也不是绝对的。在现代社会,知情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国际非政府组织“第十九条组织”1“第十九条组织”是一个致力于保护和提高表达自由水平的民间国际组织,该组织因主张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第19 条“为表达自由”而得名。该组织通过系统和平的工作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和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其所制定的为维护言论自由的相关原则和规定,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借鉴和接受。在《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立法的原则》中提出:“信息是民主的氧气……坏的政府靠秘密来生存,它允许低效率、浪费和腐败发展。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观察到的,在政府民主和媒体相对自由的国家里,没有严重的饥荒。”2第十九条组织:《公众知情权: 信息权立法的原则》,https://www.article19.org/data/files/medialibrary/38117/a19-FOI-principles-original---chinese.pdf。但是,公民知情权也存在有限的例外,当然,这种例外应当用清晰和详细的语言规定下来,并满足三个严格的标准:合法目的确认、严重损害平衡、公共利益高于一切。3第十九条组织:《公众知情权: 信息权立法的原则》,https://www.article19.org/data/files/medialibrary/38117/a19-FOI-principles-original---chinese.pdf。在陪审团隔离中,陪审员在隔离期间获取所有新闻信息的权利都被暂时牺牲,目的是维护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同时,这种隔离是短暂的,在隔离时间结束以后,陪审员可以再获取这些信息。因为隔离针对的是少数人,这些人信息获取权的暂时中断并不会影响社会上其他人的信息自由,其他人仍然可以行使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知情权的牺牲是必要的、相对较小的,符合平衡标准和公共利益。
第二,在现代社会,通过物理方法实现信息绝对隔离是不可能的。在1966 年著名的谢泼德案4Sheppard v. Maxwell, 384 U.S. 333, 1966.中,克拉克法官列出了审判法院为了确保公正应该考虑的9 种措施:(1)通过对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的限制来控制新闻界在法庭上的行为;(2)将证人与新闻界隔离;(3)防止信息从当事人和警方泄露出去;(4)警告记者注意他们报道的潜在偏向性和准确性;(5)限制甚至禁止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向新闻界发表庭外言论(即未经法院允许而发表的言论);(6)直到大家的好奇心减弱时才继续审理案件;(7)将案件移送到新闻界关注程度比较弱的地区审理;(8)隔离陪审团,阻止他们与新闻界接触;(9)如果上述的所有措施都失败了,进行一次新的审理。5[美]唐纳德·M. 吉尔摩等:《美国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第六版)》(上册),梁宁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355~358 页。以上9 种方法都是为了防止媒体审判,但有些并没有实际意义。正如前文所述,陪审员隔离可能抵消掉审前宣传的影响。美国法院认识到了单一措施的局限,为此还采取了包括上述9 种措施在内的其他措施。如果上述的所有措施都失败了,媒体的影响导致了不公正审判,上诉法院可以认定初审裁判无效,要求案件重新审理。在美国历史上,因媒体污染陪审团而导致重审的案件是存在的,如埃斯蒂斯案1Estes v. Texas, 381 U.S. 532, 1965.和谢泼德案2Sheppard v. Maxwell, 384 U.S. 333, 1966.。这些补救性措施也充分说明,通过物理方法实现陪审团与媒体信息的绝对隔离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一种以牺牲言论自由和知情权为代价的规则都应当谨慎和有限。
第三,正当程序要求司法程序设计精密、重视细节,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在英美国家的审判中,对案件事实裁判只能是一次性的,除非程序违法导致程序无效而需要更新程序,进行一次“新的审判”3高一飞:《东亚文化背景下的建议性陪审团》,《财经法学》2015 年第1 期,第97 页。。这种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程序无效、推倒重来的做法,对程序具有很高的要求。在陪审团审判中,陪审员接触了媒体、内心被舆论污染,都可能导致程序无效,这也是产生陪审团隔离制度的重要原因。而在隔离过程中,陪审员住的宾馆、看的电视、与外界的通信联络、与配偶的周末见面都成了法院管理中需要考虑的细节。陪审制被认为是英国人发明的“精密之作”和“经典之作”。4施鹏鹏:《法国参审制:历史、制度与特色》,《东方法学》2011 年第2 期,第120 页。陪审团隔离这一制度设计,隐含着对各种社会价值的取舍和平衡之道,可以为我国完善程序的正当化提供参考。
在本文中,我们综述和分析了“陪审团隔离”这样一个“冷知识”,是一种涉及诉讼法学、新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制度,对它的研究角度可以是多重的。作为第一篇研究这一问题的中文论文,我们的研究是初步的,也许只是抛砖引玉,需要各学科的学者们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