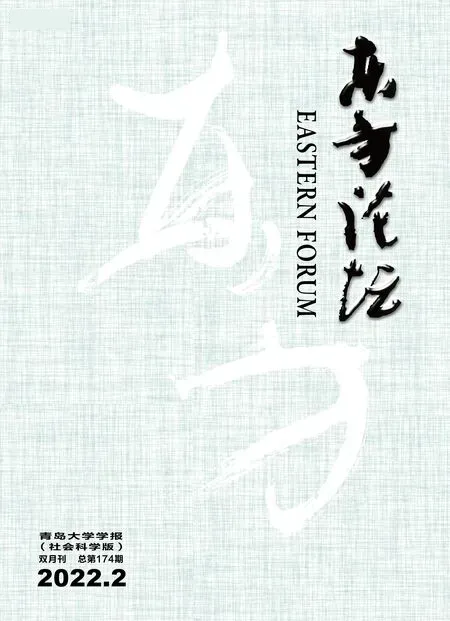河西宝卷与农民生活记忆
张天佑 赵世昌
1.西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部,甘肃 兰州730000;2.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000
河西宝卷是指河西人编写的,带有河西文化、历史痕迹的宝卷,也指那些河西人念唱、抄写、刊印的外来宝卷①这类由外地传入的宝卷,经过河西人的念唱、抄写和刊印,已浸透了河西人的情感、身份认同,是“河西化”了的宝卷。。河西宝卷在民间以口传的形式展演、流布,经过抄写、刻印固化而成,其故事或者说“事迹”,往往在民间口耳相传,由民众共同创作而成。河西宝卷无论作为仪式中的讲唱脚本,还是阅读文本,其受众基本上都是农民,宝卷诸多匿名生产者也都是粗通文墨的底层知识分子。河西宝卷除了一定的信仰,还记录着民众的苦难、地方历史的变迁,以及在变迁中个体的经验与伤痛。民众的日常家用、制度仪轨、生存观念不仅呈现在已经固化的文本中,也呈现在流行的念卷仪式、抄卷过程中,成为民众生活的道德指南。对于河西宝卷所呈现的内容来说,其所宣讲的故事,是农民日常生活中所能够体验和感悟到的“历史记忆”。因此,我们可以将河西宝卷称之为“河西农民的史诗”。
一、河西宝卷与农民生活语境
河西宝卷的传播方式有口头和文字两种,而文字的传播方式又分为两种:刻本和抄本,抄本亦可称“写本”。关于刻本与抄本的不同,正如伏俊琏在分析敦煌写本文献时所言:“下层文人写本和民间写本,更是有很大的随意性,其对文学、文体的概念相当模糊,一切以实用为目的。所以写本带有流动的、零散的、个性化的特征,与刻本的固定性、完整性、社会化的特点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①伏俊琏:《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研究概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明清以来,尽管刻印技术、纸张的生产技术都有了长足发展,但在贫穷的河西地区,宝卷仍主要以抄本形式流传。其原因有三:一是印刷成本较高,普通民众仅凭个人、家族的力量很难承受,我们在刻本宝卷的“序”或“跋”中时常可以看到,板印者一再提及刻印的经费问题;在卷尾也往往附有众多捐助者的名单、捐资数目等信息,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大量刻印的宝卷,基本仰仗官府或寺庙的支持才能完成。二是许多宝卷在民间信众手中流通,属于最神圣也是最秘密的“经卷”,故大批量刻印受到限制。这似乎与宝卷编写者希望宝卷得到广泛传播的愿望相矛盾,但事实确实如此——大张旗鼓地刻印存在一定风险。三是崇尚宝卷者对印刷技术并不信任。他们认为,只有倾心尽力地抄写才是虔敬的表达方式。
抄经写卷,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佛经道卷,都被大众所认可并习以为常。通过熟练地抄写来理解经文,是民众常用的学习方式。科举士人深谙此道,宝卷艺人也是如此。一般来说,传习宝卷的人家往往有读书人——抄写宝卷的人自幼受到宝卷内容的熏陶,习字描红的底本也是祖父、父亲辈曾经抄写过的宝卷。在摹写过程中,这些人不仅能够习得一笔好字,而且也能因此走上科举之路。但由于此路未必通畅,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不得不重复父辈耕种念卷的营生。念卷之所以能够成为营生,来源于民众社会生活的需要:一方面,由于民间存留大量的“神”和“鬼”,而这些神鬼需要仪式进行祭奠和安抚,才能给民众带来福祉,不致干扰其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民间对于疾病、死亡事件,也需要通过仪式进行治疗和归葬,唯有如此,才能给民众带来慰藉。仪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是经文、祝由科文——经过乡间艺人本土化之后的各类文字或者文学。这类文字或者文学由念卷者抄写并裱糊,大都耐磨损、耐使用。尽管如此,由于岁月漫长、寒暑往来,凡物皆易老旧,重抄重写依旧是抄卷人的日常功课。
根据传说,“家制(置)一部经,可保万事平”。普通民众能够识字,且写得一笔好字的人并不多见,但由于崇敬文字、经卷,并相信经卷即神灵,具有救赎的功能,所以他们或请抄卷先生到家里抄写,或是自己帮抄卷先生干农活,折算工钱,以此换取宝卷。进行宝卷抄写前,请卷者会举行一个或简单或隆重的仪式。总的来说,宝卷的抄写过程漫长,抄卷先生每日抄写前都要净手净口、焚香祈祷,抄错一个字不仅会被东家不满和同行讥笑,还会给自己死后增加一份罪孽。由此,抄写过程极为缓慢,一卷经的抄写时间往往月余。如果抄卷先生的“作品”得到认可、获得声望,则会保证其营生得以继续扩展。
抄写宝卷固然是一项神圣严肃,需按照一定规范而行的事业,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允许抄写者进行个性化改写与创造。如对原文本中的文字,进行方言的替换和部分内容的删减与增添等。有些卷本甚至还出现了整体文本本土化、通俗化的现象。这从根本上造成了文本内容越来越简化,文本中一些繁琐的仪规被删减,已经失传的曲牌甚至被省略等一系列问题,进而使宝卷文本的神圣性逐渐减弱,故事性逐渐增强——宝卷也因此走向了文学化、寓教于乐的方向。这一现象的出现,使得与民间信仰相关的宗教宝卷呈现式微之势,而故事性极强的、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为主要内容的“故事宝卷”,以及具有现实性、经验性的“事件宝卷”逐渐兴盛起来。“事件宝卷”中最典型的代表为《救劫宝卷》,它以民国时期河西本地故事为蓝本写成。
宝卷的装裱也有其严格的规范。早期宝卷的装裱仿照佛经的形制——经折本,一般宽15厘米,长25厘米左右,封面的里衬使用多层硬纸,有些干脆用薄木板,外皮则包以绸缎或布面,并在上面写有卷名。有些讲究的还在扉页绘制神像、龙牌,在尾页标有题识,表明宝卷的拥有者、抄写者等信息。中后期的宝卷版式大都是方巾本、大折开本等。抄写装裱后的宝卷经过仪式化,就有了神的灵光。民众常将这些卷子与佛像、玉皇、关爷、祖宗的牌位供奉在一起——此为物的“神圣化”过程。明清时期,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家中藏有一部年代久远的经卷,或者一部稀缺的卷子,往往是社会声望、地位的标志。
总体上来讲,宝卷的日常文化生态表现为:抄卷、念卷、听卷;接神、送神;请念卷先生、送念卷先生;在自家设坛念卷,在公家(公共场所)听卷;因突发事件设坛,或因节日设坛。由此,人和人、家族和家族、村社和村社之间形成精神文化的交流,并达成某种共识,从而形成互动仪式链①“互动仪式链”是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提出的概念:“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机制是,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活动。”参见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9页。与文化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宝卷既是联结的媒介,也是目的本身;既是一种装置,同时也是结果本身。原本,宝卷并非被用来阅读,而是按照一定的仪规讲唱的脚本。宝卷编写者和抄写者都深谙此道,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观——文本用通俗易懂的词汇、方言、土语来进行程式化的处理。板存于“杭城新宫桥聚文齐富润德刻字店”的刻本《潘公免灾救难宝卷》开篇序文云:“善书者,与其精而微,不如粗而显;与其深而博,不如浅而庸。”②张天佑、任积泉:《丝路稀见刻本宝卷集成》(第十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08页。就是说劝人向善的书,应该写的通俗易懂,把各种道理写得明白晓畅。但宗教宝卷又以宣扬教理而与其他俗文学区隔,以示不同。如古凉州(今武威)刻印的《七真天仙宝传·凡例》云 :
此书深观深者见深,浅看浅之见浅,篇篇明以显道,回回暗以隐玄。知此者方可读七真天仙传。
此书道遗参同悟真,法阐三教贯通,休当记书歌词,莫作小传俗说。知此者方可读七真天仙传。③张天佑、任积泉:《丝路稀见刻本宝卷集成》(第三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0页。
宝卷的主要受众并不是有学识的人。编写者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宝卷的传播教化学识不高的人。于是,“化俗”的文本采取了一种必然的创作方式——“俗化”。它的俗化首先表现在叙述风格上。它将原本晦涩难懂的经文、佛理、教理,用故事和押韵的句子表现出来,这样一来,所产生的宝卷便能够使无论哪一个阶层的民众,都能够听懂、读懂,进而有了被接受的可能。再者是措辞的俗化。宝卷不再使用经典文本中佶屈聱牙的字与词,也不再使用文人作品中带有典故的修辞,而是大量使用民间的俗语、方言以及稍显粗鄙的比喻。这样的宝卷虽然是“浅而庸”的,但却能够更好的使乡间农民接受,因为浅显的语言更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三是程式上的套话与重复的运用,保证了“听”的可靠性与效果。可以说,宝卷的“俗化”创作是一种自觉,带有显见的目的性:宝卷为农民而写,依乡村文化而在。
二、河西宝卷与农民生活苦难书写
以种植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在生活样态方面,具有生存空间的相对稳定性、生活经验的相对可靠性,以及聚落关系的相对亲密性等特点。这样的生活样态,一方面固然保证了生产与传承的可靠性;但在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保守、顽固,缺少变通。农民所尊崇的生活准则——耕田读书、尊老爱幼、行善积德——是儒释道教化的结果,也是他们世代遵从的观念。每逢时局动荡、社会变迁,既有的经验无法应对生存的艰难,民众需要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使之能够安身立命。此时,乡村知识分子①具体指那些没有能力和运气被官府所吸纳,而生活于乡间的、有文化的农民。便成为农民的代言人。此类知识分子深知农民的精神需要,掌握官府的秘密,也有自身的诉求。因此,借用流行的文体编撰故事、传说,甚至神道设教,在获得精神超脱的同时,也获得经济上的满足。但强大的文化体系、粗浅的文化认知,以及文化观念本身的限制是他们无法超越的。这些知识分子的内心实际上是自卑的,处境也是尴尬的。因为在农民心目中,他们是另类,在官府眼中,他们又是“逆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不被任何一个群体所接纳。
需要注意的是,其中部分宝卷编写者类似于鲁迅所谓的“妄人”,他们或是自我膨胀为神灵转世,或是自封为“天帝”“老母”“古佛”,试图通过类宗教的行为、仪规,实现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欲求。不仅如此,他们还借用民众熟悉的神灵系统和惯习的知识经验,进行自我形塑。比如借神仙托梦,授天书、咒符、圣物等,以此显示自身的“神性”。显然,借用的不只是形式,也是观念——借用有时变成了僭越。
何为农民自我认知中的卑贱感?卑贱感是对个体实际生存状态的体认,来自于社会关系中的自我认知。其基础是生存的匮乏,匮乏导致欲求不能满足,进而导致卑贱感。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等原因,农民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比例,因而吃饱穿暖成为他们的最大愿望。实际情况却往往事与愿违,农民总是遭遇饥荒——无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的饥荒。“宁当城里的狗,不当乡里的人”是乡间的谚语,道出的却是令人唏嘘的实情。“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现状,使得农民很难仰望天上的星空,而只能俯瞰地狱的景观,这大概是宝卷文本中存在大量地狱叙事情景,并且能够被民众普遍接受的原因。如果说经济、物质生活的促逼,只是降低了农民的生活质量,那么不识字、没文化的知识困境,却使他们丧失了话语权:无法表达自我。农民成为政治、文化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处于边缘地位②此种境遇一直要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根本性转变。。作为农民群体中的知识分子,对于卑贱感有着更切实的感受。这种感受促使他们在儒释道中寻求出路,将原本存在分歧的三家经验贯通,变为所谓的“三教合一”,并用天命、轮回等给苦难提供一套说辞。
所有文体都有自身的意识形态性,正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个阶层也有一个阶层的文体。有据可考的宝卷编撰者基本上都非庙堂之人,而是底层的生活者。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要数罗清①罗清(1442—1527),明万历间山东莱州即墨县人,其编纂的《五部六册》对宗教类宝卷的内容、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清门徒曾言:“生下祖,三岁时,丧了父亲。七岁上,又丧母,撇下单身。可怜儿,无父母,多亏叔婶。蒙抬举,养育祖,长大成人。”②罗清:《苦功悟道卷》附兰风作《祖师行脚十字妙颂》,明万历二十四年注本。十四岁时,罗清便代替叔叔在今日之北京密云县从军戍边。濮文起的研究表明,明卫所军人的生活比一般农民的生活还要艰难,“敝衣菲食,病无医,死无棺”③罗清:《苦功悟道卷》附兰风作《祖师行脚十字妙颂》,明万历二十四年注本。。而到了二十八岁时,罗清便“每日里,怕生死,恓惶不住。想生死,六道苦,胆战心惊”④罗清:《苦功悟道卷》附兰风作《祖师行脚十字妙颂》,明万历二十四年注本。,由此开始了所谓的“苦功悟道”。一方面,由于正宗的儒释道皆是“有为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罗清的问题;另一方面,有限的知识水平,导致其很难领悟《金刚经》中的法旨,于是在《销释金刚科仪》的启发下,背弃了正宗的佛教以及儒道思想,发明了“无极圣祖”的概念——自身也因此变成了“老祖”。
关于罗清的修行,刘正平曾将《聊斋志异》中的《罗祖》与无为教的典籍进行互文解读,认为《罗祖》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即墨人罗祖少时家贫,长大后在密云戌边,有一子。后随守备至陕西三年时,“适参将欲致书北塞,罗乃自陈,请以便道省妻子”⑤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73页。,但罗妻与其所托付之人李某私通,“罗抽刃出,已复韬之曰:‘我始以汝为人也,今如此,杀之污吾刀耳!与汝约: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马匹械器具在。我逝矣’”⑥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第373页。。再后来,石匣营有樵夫在一山洞见一道人,“或有识者,盖即罗也”⑦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第373页。。在蒲松龄讲述的这个故事中,地名、人名等与《三祖行脚因由宝卷》相类,只是没有朋友违约、妻子背叛的情节,大概是因为其信徒对此事难以启齿。
就笔者调查采访过的河西宝卷念唱人来说⑧材料源自笔者团队于2017年7月24日、7月28日,分别在乔玉安、代兴位二位先生家中的访谈。,他们虽然没有罗清一样坎坷的经历,但都是农民出身。2007年被确定为河西宝卷国家级传承人的乔玉安,1944年出生于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上坝镇营尔村,拜父亲的朋友于加儒为师,学唱宝卷。其师于加儒,上坝镇新上村人,民国后期是酒泉、高台、安西、敦煌、玉门、金塔、鼎新七县的会道门玉花堂法师冯三品的徒弟,后来也做了堂主,主要靠念经送神、料理丧事为营生。2018年被确定为河西宝卷国家级传承人的代兴位,1953年出生于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花寨乡花寨村,是代家宝卷传承的第三代。代氏家族第一代念卷人代登科,官名代天恩,曾考中秀才,因贫寒无钱打点,被降为童生,以私塾先生为业。第二代念卷人代进寿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也常为周围乡亲念卷。代兴位的文化程度不高,仅读到小学三年级,但自幼就跟随父亲走乡串村念唱宝卷,演唱技艺纯熟。可以说,河西宝卷念唱人大多出身农民,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在农村来说,已经称得上是知识分子。其在念卷过程中,自然融进了自身的经历,融进了农民的苦难——宝卷念唱成为宣泄苦难的出口与通道。
罗清们的经历在旧时苦难的社会,并不是偶然。传统民间文学中大量出现的后母虐子、孤子哭坟的故事,更多的是农村艰难生活的表征。值得注意的是,在宝卷中常常出现的“哭五更调”,在其他民间文学体裁中也常以不同称谓出现,几乎成为一种程式。如在秦腔中,主人公在大悲苦境况下的哭唱及其二胡配乐的“苦音”①秦腔音乐曲牌之一,分苦音尖板、苦音垫板、苦音慢板等。苦音悲伤苍凉、哀怨凄清,与花音正好相反,民间亦将之名为“哭音”。,“苦”与“哭”将人类难以克服的悲剧性命运——生离死别展演得淋漓尽致。“我叫叫一声娘啊,娘啊!哎,我难见的老娘!哎,我难见的老娘啊……”②秦腔传统曲目《朱春登哭墓》,商芳会唱词。,孤子在亡人灵前一诉衷肠,令人泪怆。哭者,苦也。哭声代替了文字、图像,表达出难以言说的伤痛。而在《破邪详辩》中,黄育楩根据宝卷对大量民间曲调、戏曲人物、故事的运用,论述到:
噫!造邪经者系何等人?凡读书人心有明机,断不肯出此言,凡不读书人胸无一物,亦不能出此言。然则造邪经者系何等人。尝观民间演戏……至于邪经人物,凡古来实有其人而为戏中所常唱者,即为经中所常有,戏中所罕见者即为经中所不录,间有不见戏中而见于经中者,必古来并无其人而出于捏造者也。阅邪经之腔调,观邪经之人才,即知捏造邪经者乃明末妖人,先会演戏而后习邪教之人也。以演戏手段,捏造邪经,甚至流毒后世……③黄玉楩:《破邪详辨》(卷三),光绪癸未嘉平重镌,板存荆州将军署,第27—29页。
事实上,这类人不尽都会演戏,但是他们肯定都生活在底层,熟悉民间,并且即使在底层,也属于边缘人群。只有这样的人,才更愿意在宗教中讨回尊严、洗涮卑贱。诚如恩格斯所言:“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④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29页。
三、河西宝卷与农民社会的道德戒律
河西宝卷大多讲述因缘故事,前因后果非常清楚,不容置疑,因而具有明显的伦理色彩和劝善意味。“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民众相信因果,因此也畏惧因果。一切因果故事的诞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源自道德戒律和自我警示。
首先,宝卷通过对惩恶故事的展演,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希望以“因果论”来维持家庭的和睦。“家和万事兴”是寄托,也是经验。如是,宝卷中描写的大量家庭生活,总是有后母欺凌孩童,或是妯娌之间彼此陷害,再或是夫妻感情不睦等情节。虽然不能说中国传统家庭生活总是充满不和谐,但这一类宝卷的流传,还是说明比较常见的不和谐家庭生活及其危害性。同时,这也是此类宝卷流传的基础。其次,与惩恶相对应的是劝善。民众听人念卷,或是自己誊抄宝卷的内容,都是为了祈愿得到“佛”缘,并以此保佑自身和家人无灾无祸。民众讲述“种善因,得善果”的故事,也是为了提醒自己,只有广行善事,才能得到福报。第三,“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观念被民间教派所利用,制造出“三期末劫,收圆聚会”的天堂景观与末日审判的意象。具体表现为,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人的恣意妄为的行为描述,指出:众神愤怒是因为人作孽太多,诸如杀生害命、不孝父母、打僧谤佛、不惜字纸、吃喝嫖赌等行为,犯者最后皆入地狱、不得超生。显然,正像孝道观念延伸至人死后的丧葬、守孝等礼仪一样,惩罚行为针对的不仅是活着的人,也延伸至死后的灵魂。
由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讲,都是生活中的戒条、榜样及生活指南。河西宝卷中有各式各样的戒律,这些戒律承继了佛教“三皈五戒”和儒家的孝道精神,并且在不同时代不断添加内容。如“戒洋烟(鸦片)”与“戒溺女婴”。《还乡宝卷》云:
洋烟本是害人物,亏了神气丧真铅。
若不戒除三宝损,烟波地狱受煎熬。
千般苦楚难枚举,切记不可入套圏。
水汉蓝烟休沾染,流入肺腑是祸愆。
……
口中含着杀命枪,面皮黄廋鬼王样。
腹中厌气喷出来,冲倒了四大天王。①徐永成主编:《金张掖民间宝卷》(第三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029—1033页。
显然,通俗的文句更符合底层民众的接受心理。另外,儒家重男轻女的观念,本与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相互矛盾,但宝卷中诸多女性修行得道的故事,以及民间信教者中大量女性的存在,表明女性追求平等的愿望。而宝卷中对“溺女婴”的劝诫,就是最好的证明:“世间人好溺女这桩要禁,天生之人杀之恼恨天心”②酒泉市肃州区文化馆编:《酒泉宝卷》(第一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47页。。宝卷以“劝化”为手段,维护以“孝”为核心的社会道德体系和以“因果报应”为准则的价值评判体系,从而构建出一种为社会所接受的宝卷信仰文化系统。
四、河西宝卷与农民生活历史记忆
某种意义上讲,官方史书、历史文献是一种由官方认可的“历史记忆”,而民间文学是留存于民众代代相传的口头传统中的“历史记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记忆,都离不开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已经固化的文本。通过对仪式和文本的阐释,形成对情感的认同、民族的记忆。宝卷就是一种历史记忆的“文本阐释”,其所反映的宗教、文学、社会等诸多方面,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在河西宝卷中,最具有此类历史品格的卷子是《敕封平天仙姑宝卷》《救劫宝卷》和《王进宝鞭扫大草滩宝卷》③《王进宝鞭扫大草滩宝卷》又名《草滩宝卷》,在河西诸宝卷编目中均有其名,但未见刊本或抄本。笔者也曾四处寻找未果。内容讲述的是康熙三年(1664)王进宝将军的故事。王进宝(1626—1685),今甘肃白银平川区人,曾任河西永固营大草滩(今甘肃山丹、民乐一带)守备,有“马踏定羌庙,鞭扫大草滩”之功。过逝之后,康熙赠其太子少保,谥“忠勇”。今甘肃白银平川区存王将军墓。。产生于张掖市临泽县的《敕封平天仙姑宝卷》(以下简称《平天仙姑》)自车锡伦发现后④车锡伦关于《平天仙姑》的研究见:《清代民间宗教的两种宝卷》,《兰州学刊》1995 年第4期;《明清民间宗教与甘肃的念卷和宝卷》,《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也可见其著作《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8—278页。,引起宝卷研究者,特别是河西宝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先后有崔云胜、程国君、李贵生、王文仁、朱瑜章等学者的论述见诸报刊。其中,崔云胜的文章考证了《平天仙姑》与张掖历史、碑记的关联,解决了对《平天仙姑》进行历史定位的问题,在学界有较大的反响①崔云胜关于《平天仙姑》的研究见:《西夏黑河桥碑与黑河流域的平天仙姑信仰》,《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平天仙姑宝卷〉中的河西历史》,《河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仙姑宝卷〉的版本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河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在张掖民间传说中,仙姑有名有姓。传说中的仙姑故事,主要围绕仙姑为民众修桥,民众为仙姑建庙而渲染。有关仙姑的故事不仅在河西宝卷中被讲述,民众还为之修庙建寺。如《肃州新志》载:“仙姑庙,在肃城北门外半里许。雍正元年监屯通判毛凤仪建,以求嗣。”②吴人寿纂,何衍庆修:《肃州新志·祠庙》,选自《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9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52页。《鼎新县志》载:“离城五里许有仙姑庙,奉甘州何仙姑。”③张维修:《鼎新县志·祠庙》,选自《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48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688页。河西张掖、酒泉地区的平天仙姑庙基本上每县都有,对此,崔云胜在其文章中已有考证,不再赘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民乐“上天乐石窟”。石窟始建于明末神宗万历年间(约1615),康熙六年(1667)时即凿洞36处,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亦重修洞室,名为朝阳洞,是全国唯一一处以宝卷故事为蓝本开凿的石窟。石窟内绘有《仙姑灵迹图》壁画,内容完全与《平天仙姑》相吻合。第五号窟“仙姑显灵图”清晰神妙:“仙姑显神通三殃彝人”“仙姑将逆妇变狗”“仙姑救王志仁”“玉帝敕封平天仙姑永合黎山感应无边”“功圆行满显像于板桥之西十里”,分别对应《平天仙姑》之“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五”“第十七”“第十九”诸“分”所记载的内容。
卷子里的平天仙姑处处显灵、解厄除困,给民众以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是河西民众,特别是当地妇女的崇拜对象。显然,后世民众将诸多历史想象、集体记忆叠加在这一形象之上,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与意识形态需求。这样一位伟大的女神产生于河西地区,使当地民众,特别是河西女姓感到自豪,并从中获得文化自信。也更由于河西人在其中看到了熟悉的山——合黎山,熟悉的河——黑河,熟悉的村庄——板桥堡,熟悉的饭食等,这一切给河西人以安全感与集体感。
《救劫宝卷》主要讲述1927年甘肃古浪大地震之后引起大饥荒,1928年大靖(今古浪)民众逃荒到宁夏中卫,1929年荒年过后又回家乡的故事。宝卷既有对逃荒群体及逃荒路途的叙述,也有对作为个体的逃荒家庭的描写。“上凉州,走甘州,又走肃州。南逃的,去西宁,寻找活路。东逃的,走中卫,又走宁夏。北逃的,走沙窝,蒙古鞑靼。”④张旭:《山丹宝卷》(下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85页。一直到了民国十九年(1930),终于由玉帝降旨抚慰百姓,从此风调雨顺、粮食丰收。逃荒在外的人,听说家乡天降甘露、粮食丰收,便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救劫宝卷》从盘古开天辟地,上古三皇和女娲补天三个创世神话开始讲起,一直到宣统登基,紧接着讲述民国史:
革命军 起了义 南讨北征
出了个 新圣人 中山先生
除帝制 造民国 劳苦功高
现在的 军和民 把他纪念
把这些 古圣贤 一一提念
古是今 今是古 万古留名①张旭:《山丹宝卷》(下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83页。
河西宝卷对民国历史的书写,延续了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中“断代史”的传统。在《五部六册》中,罗清的“古是今来今是古”的历史观,体现出宝卷的编写者对历史、当下与未来的一种明确态度:一方面要“遭荒年,苦难事,人人亲见。血和泪,教化人,代代相传”②张旭:《山丹宝卷》(下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92页。,另一方面要“把有时,当无时,常记心中。万不可,今朝饱,不管明天”③张旭:《山丹宝卷》(下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92页。。也就是说,民众需要记住过去、立足当下、想象未来。“今是古来古是今”的历史态度,意味着历史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意味着过去对现在的制约和规范,但同时,历史的书写又要立足于当下需要。历史活在当下,当下人们选择的对历史的不同诠释策略,赋予历史以活力,使之在当下复活④陈静:《“历史民族志”与“历史的民族志”——民族志实践中的历史之纬》,《东方论坛》2011年第5期。。宝卷文本往往从历史源头起始,观照当下的苦难,表达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导致灾难的悲悯情怀,其实何尝不是立足于当下,寻找整体性、构建整体性的努力。在宝卷中,天下太平与天下大乱代表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唯有团结与和平、善良与宽容才能有盛世,有太平,此为河西宝卷所宣扬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余论
黑格尔认为,史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属于这个整体的一方面是人类精神深处的宗教意识,另一方面是具体的客观存在,即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⑤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7页。显然,如果从其“绝对理念”出发,“正式史诗”只能是荷马史诗、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而引起笔者注意的是,黑格尔又认为,其他一些具有整体性、真实性、具体性特征,又有别于抒情诗的文类也属于史诗范畴,只不过是史诗的“变种”,或者说是“非正式史诗”。其所讨论的“非正式史诗”包括田园诗、传奇故事、民歌、小说等⑥其相关论述有“属于史诗变种的首先有近代意义的田园诗”“传奇故事和民歌虽然是诗,但没有明确的类型特征。它们是中世纪和近代的产物。民歌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史诗的,而表现方式却大半是抒情诗的,所以既可以属于史诗,也可以属于抒情诗。”“至于近代市民阶级的史诗,即小说……”等。,这类文体所叙述和表现的已经不是“全民族的原始精神”,也不是“原初时代的事迹”,但同样属于史诗⑦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6、107页。。卢卡奇从黑格尔“小说是近代市民的史诗”这一判断出发,提出小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对这个时代来说,生活的外延整体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了,感性的生活内在性已经变成了难题,但这个时代仍有对总体的信念。”⑧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9页。显然,黑格尔、卢卡奇认为,史诗的最基本特征是:通过具有整体性、客观性和叙述性的“事迹”,表达民族的、时代的精神。由此,如果说小说是市民阶层的史诗,河西宝卷当然可以看作河西地区“农民的史诗”①对此,郑振铎认为,佛曲(宝卷)、弹词、鼓词,“都是以第三人的口气来叙述一件故事的,有时用唱句,有时用说白,有时则为叙述的,有时则代表书中人说话或歌唱。不类小说,亦不类剧本,乃有似于印度的《拉马耶那》,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特赛》诸大史诗”。郑振铎:《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1926年,第17页。有引者将此号外的出版时间错为1927年,后来者亦续延,今在此订正。《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亦可见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上册),开明书店印行,民国二十三年版。。
河西地区的“走廊”地域特点,决定了河西人包容、接受外来文化的心态,但他们包容与接受的原则是“为其所用”,即地方化或者说河西化,其结果是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文化体系——河西宝卷文化圈的形成与流传就是最典型的证明。实际上,这种包容与接受是土地根性、大地母神的本质特征,深植于土地的农民,所具有的精神特质又何尝不是如此。河西宝卷作为河西农民的“百科全书”:首先是其生存所需要的,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技术、交换技术;其次是其日常生活的道德指南、情感认同与历史记忆;再次是其乌托邦想象与对自然的改造、妥协与敬畏,同时又是河西各民族互相交流与融合的产物;最后是其生存智慧和由此生成的品质——极似胡杨的耐受力和绵长的生命力,既能够适应风的形状,又能够秉持农民的根性——善良、温顺、谦和、朴素,但也固执、保守,而这一切就是黑格尔所谓“史诗的整体性和民族的精神”。在当今河西地区的乡村振兴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要充分认识并利用与农民生活书写、历史记忆密切相关的河西宝卷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地区发展提供文化软实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