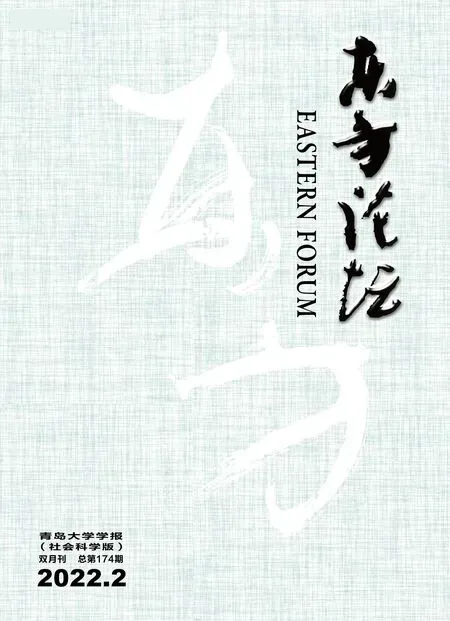文本的生产与文学经典的诞生
——基于《阿Q正传》文本生产过程的历史考察
李 宗 刚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文本生产的状态对文学经典的诞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学经典的诞生并不一定为作家自觉地意识到,但正是在这种无意识的自由自然状态下,文学经典才获得了其所需要的诸多内部和外部条件。实际上,有些作家也许在创作之初便抱定一种信念,试图创作出一部可以称得上是“经典”的文学作品。然而,由于作家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过度地倾注了自身的功利化诉求,反而破坏了文学经典所需要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其生产出来的文本也难以成为文学经典。与此相反,有些作家在创作之初尽管没有抱定创作出文学经典的信念,其作品反而获得了读者的认可乃至推崇,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经典。鲁迅日记显示,他在创作《阿Q正传》时,既没有过多地关注《阿Q正传》的创作与刊载情况,也没有明显的要将《阿Q正传》写成“经典”小说的诉求。他甚至没有想到过自己塑造的阿Q形象会成为时人热议的对象,更没有料到这部作品将会成为文学经典。他一如既往地按照既有的节奏生活着、工作着、创作着。然而,恰是这样一种自由自然的写作状态成为《阿Q正传》成为文学经典的原初动力。目前,学界研究《阿Q正传》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基本围绕着“思想史”和“文学史”这两个维度来进行解读,从“文学理论”维度来探究《阿Q正传》的成果又难免陷入“理论先行”的强制阐释中。真正从文本产生的“原初”状态切入,探究文本生产与经典诞生之关系和规律的并不多见。本文拟通过鲁迅日记、民国报刊等原始材料来还原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生产“现场”,以期揭开文学经典诞生的内在奥秘。
一、鲁迅创作《阿Q正传》时期的生活状态
在民国十年和十一年间,一九二一年农历的十一月初六、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廿日、十一月廿七日、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月十八日、十二月廿五日和一九二二年的正月初九、正月十六日不过是几个平淡无常的日子。然而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发展而言,却是极为重要的九天。在这几日内,《晨报》副刊连载了一部作者署名为“巴人”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这部作品嗣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常读常新的文学经典。《阿Q正传》的第一章被编辑安排在“开心话”专栏,自第二章开始被相继移入“新文艺”“文艺”专栏,前后刊登时间共计10个周(其中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初四这一周没有连载)。具体刊发情况如下:
1921年12月4日(农历十一月初六),周日,鲁迅的《阿Q正传》第一章“这一章算是序”在“开心话”栏目刊出,列副刊的第二篇位置。
1921年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周日,鲁迅的《阿Q正传》第二章“优胜记略”在“新文艺”专栏连载。
1921年12月18日(农历十一月廿日),周日,鲁迅的《阿Q正传》第三章“续优胜记略”在“新文艺”专栏连载。
1921年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廿七日),周日,鲁迅的《阿Q正传》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在“新文艺”专栏连载。
1922年1月8日(农历辛酉年腊月十一日),周日,鲁迅的《阿Q正传》第五章“生计问题”开始连载。
1922年1月15日(农历辛酉年腊月十八日),周日,鲁迅的《阿Q正传》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在“文艺”专栏继续连载。
1922年1月22日(农历辛酉年腊月廿五日),周日,鲁迅的《阿Q正传》第七章“革命”在“文艺”专栏连载。
1922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九),周日,鲁迅的《阿Q正传》第八章“不准革命”在“文艺”专栏连载。
1922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十六日),周日,鲁迅的《阿Q正传》第九章“大团圆”在“新文艺”栏目连载完毕。
为了尽可能地还原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时的生活状态,现据鲁迅日记,对其创作《阿Q正传》时期的基本生活情况进行一番还原。考虑到鲁迅发表《阿Q正传》第一章的时间节点为1921年12月4日,我们把考察的时间点提前到1921年10月1日。在约两个月的时间维度中,我们追溯到了鲁迅创作《阿Q正传》最直接的缘起。通过日记、书信及报刊材料显示,孙伏园的主动约稿、鲁迅在大学的兼课以及鲁迅日常的“公务交游”与“文学交游”均与《阿Q正传》的创作存在或隐或显的关联。
首先,鲁迅孕育和生产《阿Q正传》这一文本与《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有着密切的联系。据已有史料,孙伏园的约稿对鲁迅创作《阿Q正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编辑的孙伏园是《阿Q正传》文本生产最重要的“发起人”。从1921年10月到12月,鲁迅在日记中有关孙伏园的记载便有25次之多。其中,鲁迅与孙伏园的信件往来有13次,见面有12次。鲁迅与孙伏园交往最为频繁的是10月份和11月份(每月均有5次之多),12月份有2次。两人的具体交往情况如下:
1921年10月7日,上午得遐卿笺。午后往大学讲。……晚伏园来。/10月9日,星期休息。……晚孙伏园、宋子佩、李遐卿先后至,饭后散去。夜半小雨。/10月13日,……晚孙伏园来。/10月22日,……晚孙伏园来。/10月30日,星期休息。晚孙伏园来。蒋子奇来。/11月6日,星期休息。下午孙伏园来。/11月11日,上午孙伏园来。/11月20日,星期休息。下午孙伏园来。/11月25日,晚孙伏园来。宫竹心来。/11月27日,星期休息。午李遐卿来。晚孙伏园来。/12月3日,上午得孙伏园信。午后寄沈雁冰信并爱罗先珂文稿及译文各一帖,又附复胡愈之笺一纸。晚孙伏园来。/12月15日,晚孙伏园来。①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5—450页。
由于鲁迅1922年的日记已经缺失,我们无法了解1922年初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情况。但通过对1921年相关日记的统计,我们发现鲁迅与孙伏园的交往在10月和11月变得非常频繁。再结合孙伏园在1921年10月12日开始接手《晨报》副刊这一历史背景,可以推测在二人频繁的交往过程中,应该会涉及孙伏园向鲁迅约稿一事。事实也的确如此,鲁迅在此期间曾断断续续地为孙伏园提供了一些稿件。因此可以说,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区间内,孙伏园介入乃至推动了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历史进程。
其次,鲁迅在北京高校从事兼课等教学活动,与《阿Q正传》的创作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现代大学及其课程的建立与新思想的传播,需要一批具有现代知识谱系的教师堪当此任。由于许多大学体制内的教师又往往缺少这一知识谱系,这便在客观上为担任教育部“公职”的鲁迅兼课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从鲁迅的文化启蒙自觉来看,进入大学兼课使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在“文化启蒙这一基点上获得了统一”②李宗刚:《民国教育体制下的鲁迅兼课及新文学传承》,《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从鲁迅创作生活来看,进入大学兼课不仅没有妨碍其从事文学创作,反而还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同时在北京各高校兼职授课,有史料表明他在课堂上曾经与学生谈及过“阿Q”的形象。这说明,鲁迅兼课使其文学创作居于一个相对自然的社会状态下,这成为鲁迅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因素。那么,鲁迅在此期间到过哪些高校、又在哪些时间到这些高校兼课呢?为了能够清晰地呈现出鲁迅的兼课情况,现根据鲁迅日记枚举如下:
1921年10月5日,午后往高师讲。/10月7日,午后往大学讲。/10月8日,下午至女高师校邀许羡苏,同至高师校为作保人。/10月18日,午后往大学讲。/10月19日,午后往高师校讲。/10月25日,午后往大学讲。/10月26日,午后往高师校讲。/11月1日,午后往大学讲。/11月2日,午后往高师讲。/11月8日,午后往大学讲。/11月9日,午后往高师讲。/11月15日,午后往大学讲。/11月16日,午后往高师讲。/11月22日,午后往大学讲。/11月23日,午后往高师讲。/11月29日,午后往大学讲。/11月30日,午后往高师讲。/12月6日,午后往大学讲。/12月7日,午后往高师讲。/12月13日,午后往大学讲。/12月14日,午后往高师讲。/12月20日,午后往大学讲。/12月21日,午后往高师讲。/12月27日,午后往大学讲。/12月28日,午后往高师讲。①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445—451页。
日记显示,鲁迅在这一时期到高校兼课有24次,此外还有一次是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高师”)办理具体事务。由于鲁迅往返高校的路程需要不少的时间,因此兼课教学所花费的时间较创作时间更多。但是,不能因此就认定兼课活动“挤压”了鲁迅的创作时间。早在1920年,鲁迅便在北京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小说史。1921年,他又在北京大学、“高师”主讲中国小说史。因此,在其孕育和生产《阿Q正传》的这段时间,鲁迅不仅没有因创作《阿Q正传》而终止大学兼课,相反他依然按照既有的生活和工作节奏,边兼课边创作。从其创作的具体情形来看,兼课并没有影响到鲁迅的文学创作。相反,鲁迅所主讲的中国小说史很可能让他在创作中产生小说的“现代意识”,同时在“文学史”的观照下从事小说创作②李宗刚:《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鲁迅现代小说的生成》,《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有学生这样回忆道:“在《阿Q正传》头两章刚发表之后,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在北大上完课之后来到新潮社,从阿Q谈到绍兴话中‘攎’与‘摸’两个字在使用时的区别。”③川岛:《和鲁迅先生相处的日子(选录)——当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时候》,见孙伏园、许钦文等:《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即便在兼课之余,鲁迅仍然无法排遣脑海中有关人物形象构思和塑造的创作思绪,这一方面说明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的互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鲁迅将创作和兼课视为生活的常态。另一则史料显示,鲁迅在发表《阿Q正传》期间曾经与学生们透露过自己使用的笔名“巴人”。川岛回忆说:“当《阿Q正传》陆续在《晨报副刊》每一周发表一章的当中,我们,也只有我们几个人,在知道作者是鲁迅先生而不是蒲伯英先生之后,对许多问题不像起初时那么去猜测:以为是专在讽刺哪一个人。”④川岛:《和鲁迅先生相处的日子(选录)——当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时候》,见孙伏园、许钦文等:《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第279页。这说明,在创作《阿Q正传》的过程中,鲁迅便已经被“我们几个人”就作品问题产生了互动。由此观之,大学课堂内外的“师生互动”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便会影响到鲁迅的文学生产。也就是说,兼课使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时居于一个相对开放自然的系统之中,其中不乏学生的某种反响和回应。鲁迅由此获得了某种积极的情绪体验,这使其文学生产处于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之中,为其文学创作臻于佳境提供了驱动力。
再次,鲁迅在教育部周遭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公务交游,为鲁迅创作《阿Q正传》提供了现实素材和思想资源。教育部是鲁迅供职的单位,自然也是鲁迅人生赖以展开的最为直接的社会场域。他白天要到教育部签到上班,有时候还在夜里赶往教育部开会①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448页。。这说明教育部的日常工作也占据了鲁迅很大一部分时间,但鲁迅并没有觉得这对创作产生影响。毕竟他不是以职业作家的身份在从事创作,这种自由自在的创作心态对《阿Q正传》的风格形成非常重要。除此之外,教育部的其他公职人员与鲁迅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他们构成了鲁迅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重要社会关系。作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其人员的构成相对多元,这里既有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熏陶的人,也有一些背负着传统沉疴、从传统体制中走过来的人。在文化性格上,这些人难免遗留着鲁迅所特别关注的“国民劣根性”,也会影响到鲁迅对承载着“精神胜利法”的阿Q形象的塑造。
最后,鲁迅除了在教育部门的公务交游外,还与文坛上的友人保持着文学交游,这些因素也影响了其创作《阿Q正传》。从接待来访者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鲁迅在沉潜于文学创作的同时,还不断地参与一些友人组织的活动,或者接待一些友人的来访。这在客观上也使得鲁迅的文学创作居于一种相对开放的社会关系之中,并不可避免地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产生某些影响。在日记中,鲁迅对此有着较多的记载。从鲁迅的信函往来的情况来看,鲁迅不时地接到友人的来信,也不时地给友人回信。如在创作《阿Q正传》的前三个月,鲁迅便收到很多来信。据鲁迅日记记载,这一时期与鲁迅有信函往来的便有沈雁冰(茅盾)、李遐卿、章士英、胡愈之等。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期间,与茅盾书信往来较多,单就1921年11月2日到1921年12月29日来看,二人书信往还多达9次。其具体信函的往来情况如下:
1921年11月28日,上午得沈雁冰信并校正稿,晚复之,并寄阿尔志跋绥夫小象一枚。/12月1日,夜得沈雁冰信并爱罗先珂文稿一束。/12月3日,午后寄沈雁冰信并爱罗先珂文稿及译文各一帖,又附复胡愈之笺一纸。/12月9日,上午得沈雁冰信,下午复。/12月16日,上午得沈雁冰信并阿尔志跋绥夫象一枚。/12月17日,下午复沈雁冰信。/12月20日,夜校《一个青年之梦》讫,即寄沈雁冰。/12月22日,下午寄沈雁冰信。/12月29日,晨往齐耀珊寓。得沈雁冰信。②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449—450页。
日记显示,鲁迅与沈雁冰在这一时期的交往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信函往来,而且还有稿件的往来,特别是一些外国作家的文稿。其涉猎的外国作家作品有阿尔志跋绥夫、爱罗先珂、《一个青年之梦》、《最后之叹息》(爱罗先珂赠)等;寄胡愈之信并译稿一篇。除了与沈雁冰的文学交游外,鲁迅在这一时期还与外国作家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如在日记中他提到了在高师听爱罗先珂君演说,在此之前鲁迅还与爱罗先珂有书信往来等情况,这使得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期间,与世界文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鲁迅在自然自由的状态中内化了这些资源,这使得鲁迅创作的《阿Q正传》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特质。这也许是《阿Q正传》这部作品获得世界读者认可和推崇的缘由之一吧。
从日记、书信等材料还原《阿Q正传》创作的原初状态,还不能忽视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对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影响。在《阿Q正传》的创作中,鲁迅曾自嘲自己趁着孙伏园外出把阿Q“枪毙”了。鲁迅较早地结束了阿Q的生命,从而及早结束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这似乎和中国农历的春节有着潜在的关联。“大团圆”两章的刊载时间是一九二二年的正月初九、正月十六日。鲁迅曾经说过:“《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①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8页。为此,鲁迅把最后一章“大团圆”已经写好了,还随时准备给阿Q画上句号。从时间节点来看,农历春节正是中国人向来重视的一个节日,在强大的民俗力量下,鲁迅选择给阿Q画上人生的句号并非偶然。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推测,如果不是农历春节的翩然而至,即便孙伏园不在,鲁迅也还会让阿Q多活几个星期?
二、孙伏园的约稿与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缘起及发展
历史大都是在悄无声息中绵延向前的,即便是宏大历史的孕育与发展也需要机缘和巧合。这在历史主体那里似乎也没有觉察到,新的历史即将在自己的手中生成。也许孙伏园没有想到,自己也曾经作为一个历史主体,参与到了《阿Q正传》经典化的历史进程中。那么,孙伏园是以怎样的“身份主体”参与到《阿Q正传》文本生产中的呢?
一部作品在孕育之初,大都是作家脑海中一种抽象的乃至朦胧的存在。这种存在表现为作家在脑海中那个既清晰又朦胧的“胚胎”,这相当于画家下笔前的“胸中之竹”。然而要将“胸中之竹”外化出来,变成可以感知的“纸上之竹”,不仅需要借助文字或线条,更需要“下笔”的契机。正是孙伏园的约稿,促成了鲁迅把内心孕育许久的“为阿Q作传”提上了现实议程。孙伏园是浙江绍兴人,又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他与鲁迅除了有同乡之谊外,还有师生之情。八道湾的聚会,每每也有他,且往往是热闹的人物。孙惠南在《怀念父亲孙伏园》中写道:“父亲结婚后,就在小学教书,但总感到自己学问不够,想学点知识。周树人(鲁迅)是他的老师,后又成为同事。父亲很敬重周氏三兄弟,并常向他们学习、请教。”②孙惠南:《怀念父亲孙伏园》,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绍兴鲁迅纪念馆编:《绍兴文史资料选辑 》第13辑,绍兴:绍兴鲁迅纪念馆内部印刷,1994年,第49页。显然,这种特殊的师生之情和同乡之谊,为孙伏园向鲁迅约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921年10月12日,孙伏园开始接手《晨报》副刊。自当日开始改版扩容增至每天一张,每月合订一册取名《晨报副镌》。据同时代读者的回忆,《晨报》副刊“每逢星期天就登载一些较为轻松、活泼的短小作品,内容和平日的副刊有些两样。有一栏名为‘开心话’,经常登载一些讽刺性的或者轻松些的散文”③川岛:《和鲁迅先生相处的日子(选录)——当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时候》,见孙伏园、许钦文等:《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第276页。。然而,“开心话”这个栏目刊登的文章要做到“开心”似乎并不容易。毕竟,具有讽刺性的或者轻松些的散文并不多见,而且许多讽刺性或轻松些的散文大都流于形式,缺少应有的思想深度。而一味地追求思想深度又没有“开心话”的外表,难以对接读者的审美趣味,从而影响到报纸的销路。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孙伏园的出现不仅为鲁迅创作《阿Q正传》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也为《晨报》副刊建构“新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可能。
1921年,鲁迅在文学创作上已经获得了盛名。由于孙伏园是一名受过现代教育熏陶过的“新人”,对五四新文学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心理。因此,他一方面对拥有“文学盛名”的鲁迅保持着景仰,另一方面也将鲁迅视为最具潜力的大作者。孙伏园担任《晨报》副刊编辑后便向鲁迅约稿,似乎有某种历史必然性。早在1911年,孙伏园在浙江山会师范学堂读书时便是鲁迅的学生,在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师时再次成为鲁迅的学生。1919年,孙伏园出任北京《国民公报》副刊编辑时便向鲁迅约过稿。鲁迅把翻译出来的作品《一个青年的梦》交给孙伏园发表在《国民公报》上,这是孙伏园首次成为鲁迅文学创作和翻译的“责任编辑”。有学者认为鲁迅的文学功绩的某些方面“得归功于孙伏园的约稿”,因为“如果没有孙伏园的约请,鲁迅也许不会翻译这篇文章,更不消说一版再版,在中国的读者中产生巨大的影响”①孙惠连、孙惠南:《读〈孙伏园评传〉》,《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由此说来,孙伏园担任《晨报》副刊编辑不仅对其人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也间接地影响到了鲁迅的文学生产方式。
从鲁迅与报刊的结缘来看,鲁迅的文学创作所依托的报刊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自己及其同仁独立创办杂志,如他所办的《新生》杂志,这样的同仁报刊可以直接登载创办者的文章,但遗憾的是,这种独立创办的报刊承载了创办者思想的同时却很难获得读者的认可,其难以为继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严格说来,一份杂志没有多年的苦心经营与自我调适,是难以赢得读者的认可的,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市场。二是通过他人创办的报刊来发表自己的文章,如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借助《新青年》杂志刊登出来的。众所周知,《新青年》在刊登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前已经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显然是鲁迅当年自己所办的《新生》杂志望尘莫及的。换言之,鲁迅的文学生产之所以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与鲁迅借助现代报刊这一平台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正是借助现代报刊这一平台,开启了《阿Q正传》的创作之路。在这条创作之路上,孙伏园不仅为鲁迅与现代报刊搭建起重要的桥梁,而且以“锲而不舍”的约稿精神深度地影响了鲁迅的文学创作。鲁迅在还没有创作出《阿Q正传》之前便答应了孙伏园的约稿。这使鲁迅走出了既有的“铁屋中”的思想困境,从当初文学创作时的无限寂寞体验中走进了较为高亢的文学体验之中,在自由对话与复合型的社会交往中,开始了文学经典文本的生产过程。
从创作的规律来讲,作家的创作既深受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又深受其自我多年来的文学思考的影响。在孙伏园向鲁迅约稿之后,鲁迅要借助“开心话”专栏创作这部小说。现代小说生产的“连载”形式,或许为鲁迅提供了自由发挥的可能。而且,鲁迅无意于全景书写的心态,为立体多面地展现阿Q形象提供了心理条件。鲁迅在孙伏园约稿之前,以“为阿Q作传”的思考开启了《阿Q正传》的“十月怀胎”历程。鲁迅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开启了《阿Q正传》创作历程,是他多年来文学思考的自然结果。鲁迅后来回忆《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阿Q这个形象在其头脑中存在多年了,最后终于将他写出实在是欲罢不能“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②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12页。。这就是说,鲁迅要通过塑造阿Q这样的人物形象,把自己思考了多年的“国民性”问题外化出来,必须借助这一形象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③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鲁迅曾经发出这样的自我诘问:“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①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3页。这说明,鲁迅在脑海里尽管已经孕育出了阿Q这一人物形象,但并没有把他外化为文字,而孙伏园的约稿则激发了鲁迅下笔去创作《阿Q正传》。这正如鲁迅自述的那样:“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②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96页。可以看出,《阿Q正传》既是作家长期思考偶然得之的自然结果,也是孙伏园“锲而不舍”地约稿的结果,而《晨报》副刊所开设的“开心话”这一栏目更是从风格定位上影响到了《阿Q正传》的创作。从“开心话”专栏的定位来看,阿Q这样的人物形象的确具有某种“开心”的效能,只不过这效能不是那种落入油滑的“开心”,而是人物形象承载着国民劣根性而给读者带来的笑与泪的“开心”。这也是为什么经孙伏园“一提”,鲁迅便“忽然想起了”的由头——从某种意义上说,阿Q这样的艺术形象的确与“开心话”栏目的风格定位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孙伏园在《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中说:“一面要兼收并蓄,一面却要避去教科书或讲义式的艰深沉闷的弊病,所以此后我们对于各项学术,除了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引人研究之兴趣的,或至少艰深的学术而能用平易有趣之笔表达的,一概从少登载……日报附张的正当作用就是供给人以娱乐,所以文学艺术这一类的作品,我以为是日报附张的主要部分……文学艺术的文字与学术思想的文字能够打通是最好了。”③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 第3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7页。这说明,孙伏园作为栏目的编辑对栏目的美好想象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故事打通“文学艺术的文字与学术思想的文字”。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从第二章开始,孙伏园便把《阿Q正传》从“开心话”移到了“新文艺”栏目。显然,“新文艺”专栏的定位要比“开心话”专栏严肃得多。这样严肃的基调自然潜在地影响到了鲁迅的《阿Q正传》的创作,于是“渐渐认真起来了”④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97页。。实际上,孙伏园向鲁迅约稿本身便是极其认真的,他在编鲁迅的《阿Q正传》第一章时也是认真的。只不过在这样的“认真”背后隐含着某些“开心话”这样一些“非认真”的因素,也包含了孙伏园通过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赓续新文化传统的意图。鲁迅主动地“认真”起来,也是对孙伏园编辑意图的领会。换言之,孙伏园的这种认知变化不仅直接地影响到了他自己对这部作品的定位,而且也间接或潜在地影响到了鲁迅的文学创作——既然《阿Q正传》不再隶属于“开心话”的范畴,而是作为现代小说移植到了“新文艺”栏目中,这自然增加了阿Q在让人“开心”之余的悲剧性特质,使这部小说更吻合“新文艺”的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孙伏园是鲁迅创作《阿Q正传》文本生产的“发起者”与“传播者”。鲁迅在回忆孙伏园到八道湾住所来催稿的情形时这样写道:“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⑤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97页。鲁迅的这番话恰好说明了孙伏园的“催稿”对于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没有编辑的外在催促,作家能否如期完成某一部作品的创作也许是一个未知数。编辑缘于现代报刊出版的周期性需要,主动地介入到了作家的文学创作过程中。这促使现代作家的文学生产不再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或意愿往前推进,而是在外在作用力的驱动下往前推进,从而深度地影响了文本的生产。鲁迅能创作出《阿Q正传》这部作品,应该视为作家“内驱力”与编辑“外驱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至于鲁迅接受了孙伏园的约稿而进入了创作阶段时,孙伏园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就更为深刻了。后来孙伏园因为回家而中断了既有的催促“节律”,这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让鲁迅及早结束阿Q的生命,也切断阿Q人生未来实现的可能。在大大缩短了《阿Q正传》篇幅的同时,也缩小了这部作品应有的社会涵盖面。对此,鲁迅曾专门作文写道:“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①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98页。后来有读者曾不无惋惜地对孙伏园的儿子感喟道:“你父亲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大错误,他老人家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这节骨眼上回家去了。”②彭匈:《我所景仰的三位编辑大师》,《会心一笑:彭匈随笔》,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批评家西谛(郑振铎)也曾写道:“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③西谛(郑振铎):《闲谈》,《文学周报》第251期,1928年11月。甚至鲁迅自己也对《阿Q正传》的结尾有过预设,他说:“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④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98页。可以想象,如果阿Q多活几个星期的话。不仅《阿Q正传》会又要多出几章的篇幅,“大团圆”的结局也许会因为其他设计而有所延宕,至于鲁迅让阿Q在随后多活的几个星期里干些什么,可能的猜测一定是丰富而复杂的。
从孙伏园深度介入鲁迅《阿Q正传》创作中去的案例可以得知,经典作品的孕育乃至诞生的确是由众多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孙伏园不是因故回家,我们所看到的《阿Q正传》在篇幅上肯定要长一点,阿Q也会在社会的舞台上继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穿行于复杂变化的社会生活之中。阿Q如何认知与回应辛亥革命的余波,也许会更为丰富立体多面。然而,历史不需假设。我们很难说鲁迅“放”阿Q多活几个星期后,就必然会对这部作品产生积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已经在连载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阿Q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画出了国人的“魂灵”。尽管如此,孙伏园依然深度影响着鲁迅的《阿Q正传》创作的编辑,他不仅以约稿的形式促成鲁迅开启了《阿Q正传》的创作,而且还通过“催稿”的方式影响了《阿Q正传》的创作。
三、“反响—回应”关系与鲁迅《阿Q正传》创作
任何一部文学经典的生产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偶然性。所谓必然性主要强调了作家需要一个孕育的历史过程,这是其在“十月怀胎”之后能够“一朝分娩”的根本之所在;所谓偶然性主要强调了作家在生产作品的过程中又受到了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作家在从事文学作品创作时受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有些作家在进入创作之后,绝少受外在因素的干扰,像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外化出来了。有些作家在进入创作之后,并不是一下子便完成了作品的创作,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创作,这便使得其创作受到了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至于那种“边写边发”的连载文学创作所受到的影响则更大,因为读者的反响与作家的回应会对文本的后续创作产生重要影响,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时便属于后者。这种情形从读者的反响到作家的回应这一视域来看,外在因素便成为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具体到《阿Q正传》创作上,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时深受周围同事的影响。同在教育部共事的诸多同事,自然是鲁迅首要面对的社会关系圈,这一社会关系圈对鲁迅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从人的社会化来看,与社会的诞生相伴而来的是组织的形成。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被组织纳入到不同的层级中,成为构成这一社会组织的“细胞”,且由此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价值和意义,鲁迅也概莫能外。鲁迅创作《阿Q正传》这一作品的写作活动属于教育部这一社会组织之外的个人活动,其同事甚至无从知晓鲁迅在忙完了公务之后还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且鲁迅在创作时使用了少见的“巴人”这一笔名。这既使得鲁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创作空间,也使得鲁迅客观地接收到来自读者对《阿Q正传》的意见。
鲁迅的同事在阅读《阿Q正传》后到底会有哪些反响呢?据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一文中的回忆,当时在鲁迅供职的教育部,人们对这部小说产生了热议。他们“纷纷议论,毁誉不一,鲁迅就在旁边,茫然相对”①周作人:《关于鲁迅》,见张菊香编:《周作人代表作》,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14页。。对此情形,鲁迅曾经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但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倘是没有,就不成为小说。……有谁相像,就是无意中取谁来做了模特儿,不过因为是无意中,所以也可以说是谁竟和书中的谁相像。”②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37页。这昭示出阿Q的性格经过抽象之后,可以概括出一种带有人所共有的普遍性或共性的性格。正因为如此,阿Q表现出来的文化本质属性,如“精神胜利法”“对革命目的个人化象”,都具有某种普遍性,这也许是阿Q引起“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甚至还“硬说是在讽刺他”的缘由。
我们不禁要追问,鲁迅塑造出来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为什么会引起 “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甚至还“硬说是在讽刺他”呢?这显然又与鲁迅对自己周边的同事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无情的解剖有关。无法否认,鲁迅对身边的同事有着更为真切的了解,也更能洞察到他们背负的国民性弱点,这甚至已经内化为鲁迅的潜意识的组成部分。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时,难免会把这潜意识的内容转化为阿Q性格的组成部分。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③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第537页。似乎也并非空穴来风。
其二,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时,受到了批评家和读者多个“主体”的影响。真正优秀的读者大多是那些超然于具体的“索解”而进入理论解析层面的批评家。在《阿Q正传》刊载期间,有读者于1922年1月2日写信,一方面表达了对文坛缺少优秀文学作品的失望,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阿Q正传》的期待:“《晨报》上连登了四期的《阿Q正传》,作者一枝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也算不得完善的了。创作坛真贫乏极了!贵报目下隐然是小说界的木铎,介绍西洋文学一方,差可满意,创作一方却未能见胜。至盼你们注意才好呵!”①雁冰等:《通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2期,1922年2月10日。茅盾针对读者来信,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阿Q正传》的推崇:“至于《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②雁冰等:《通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2期,1922年2月10日。茅盾在此期间对《阿Q正传》的阐释,一下子把时人就阿Q是“谁”的追问,不仅提升到了“中国人的品性”和“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的高度加以确认,甚至还提升到了世界文学的高度。从世界文学、尤其是在俄罗斯文学的坐标体系上对《阿Q正传》加以确认,这无疑为后来批评家奠定了阐释《阿Q正传》的基本路径和基调。这样的阐释,对鲁迅创作《阿Q正传》自然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理论上讲,鲁迅应该关注到时人对《阿Q正传》的有关评述。考虑到鲁迅与茅盾过从甚密,他更有可能关注到茅盾的有关评论。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茅盾的评论也许会使得鲁迅在进行创作时有意凸显“中国人的品性”和“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在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刊登之后,鲁迅笔下的阿Q的文化性格更具有了社会的某种普遍性,而其所反映的内容更具文化反思与社会启蒙的自觉性。鲁迅能够将阿Q的个人命运纳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风云际会中加以展现,可以看到茅盾等人的文学批评对《阿Q正传》创作产生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对《阿Q正传》的基本评价,在他后来的文学批评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尽管茅盾在1923年的这次评述并没有参与到鲁迅《阿Q正传》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但其阐释可以视为茅盾对1922年初所作阐释的补充:“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我以为这就是《阿Q正传》之所以可贵,恐怕也就是《阿Q正传》流行极广的主要原因。不过同时也不免有许多人因为刻画‘阿Q相’过甚而不满意这篇小说,这正如俄国人之非难梭罗古勃的《小鬼》里的‘丕垒陀诺夫相’,不足为盛名之累。”③雁冰:《读〈呐喊〉》,《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10月8日。显然,茅盾这一阐释无疑真正地切中了阿Q形象的肯綮。这可以视为鲁迅与茅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位优秀作家在内在精神上的同构性——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学的时代,是一代新人而不是一两个人在崛起,他们共同的精神追求促使着五四新文学走向深入。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文学创作与读者的文学接受是两种“主体”交互作用的关系。读者对作品的钟情乃至推崇将会激发作家文学创作的潜能,使之进入和谐的状态,进而创作出更加臻于完美的作品;同理,作家越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便越会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这又会反过来得到读者的钟情乃至推崇。这种作家与读者的交互作用的“反响—回应”关系,在“边写边发”的连载类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愈加明显。鲁迅能够创作出《阿Q正传》这一文学经典,与这种独特的文学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有着一定的关系。换言之,我们在解读《阿Q正传》这一文学经典的生产时不能忽视“边写边发”的文学连载所引发的作者与读者之间“反响—回应”的关系,鲁迅创作《阿Q正传》便深受这一关系的影响。从这部作品连载伊始,鲁迅作为创作者便进入了一个与接受者交互作用的关系中,并由此在其文学创作上深深地打上了这种的关系的烙印。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发表第一章之后,读者便有了很好的“反应”。有读者这样回忆道:“《晨报副刊》在星期日像另出特刊似的一新面目的办法,是很受当时读者的欢迎的。就在这样为读者所欢迎的情况下,每星期日一早就期待着它的到来的心情下,一个阴冷的早晨,在‘开心话’这一栏中发现了《阿Q正传·第一章·序》,作者‘巴人’。”①川岛:《和鲁迅先生相处的日子(选录)——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时候》,见孙伏园、许钦文等:《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第276页。这说明,《晨报》副刊改版后的全新面目已经深受当时读者的欢迎。这恰好为鲁迅的《阿Q正传》的靓丽登场营构了很好的接受氛围,为这部小说获得读者的推崇奠定了基础。
在最初的阶段,读者对《阿Q正传》的另眼相看与特别关注主要表现在对“巴人是谁?”“阿Q究竟是指谁?”等问题的追问上。也许,鲁迅在创作该部小说时用笔名“巴人”并非刻意为之,而是率性而为。但就客观的效果来看,这一笔名反而带来读者对作者的真实身份探究的兴趣。对此,王任叔曾这样回忆:“之后,我又从北平出版的《晨报》上,看到了《开心话》一栏里的《阿Q正传》,也许是我们的嗅觉特别的敏锐,我和朋友都断定这是鲁迅先生作的。虽然他署的名是下里巴人。北平的报纸是不能按日寄到的,我们争看着这一篇小说,可惜有时常常落空,因为那小说并不是逐日发表,而是每礼拜发表一回,这叫我们非常失望,没有能把他整篇的看完。”②王任叔:《我和鲁迅的关涉》,《回望鲁迅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页。王任叔之所以断定巴人即鲁迅,也许与他对鲁迅作品的风格有着一定把握有关。然而,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巴人是谁依然是一个亟待破解的“谜”。川岛曾经回忆道:“在当时我所接触到的北大里的前辈们,他们有的对《阿Q正传》,对‘巴人’,感到兴趣,以为我和伏园有些来往,见面时总是不在意似的问我:‘巴人是谁?阿Q究竟是指谁?’关于这些问题,我只是说不知道。当时觉得,某人既不愿意把真实姓名告知读者,用了笔名,对所写的文章同样地负起了责任,读者就毋需再去寻根究底了。至于他们为什么这样来打听,据我的打听,是他们大部分疑神疑鬼的,以为‘巴人’是他们的老朋友,就在讽刺他们。”③川岛:《和鲁迅先生相处的日子(选录)——当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时候》,见孙伏园、许钦文等:《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第279—280页。这就是说,巴人的笔名对许多读者来说,不仅没有消解他们对这部作品的兴趣,反而引起了他们更为强烈的追问——要搞清楚巴人是不是他们的老朋友,是不是这个老朋友在讽刺自己?类似的担忧并不是发生在少数人那里,而是发生在许多人那里。高一涵当时在《现代评论》第4卷第89期曾发表一篇《闲话》,文中写道,有些读者以为作者骂的就是自己:“……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④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96页。这恰好说明,鲁迅在阿Q这一形象上放置了自己对国民性弱点的诸多揭露与批判,这从反面说明了这部作品具有了超然于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鲁迅给主人公命名为“阿Q”也增加了这部小说的悬念性。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类似这种带着小辫子的阿Q的名字的确从未出现过,即便是拉丁文进入了中国之后,中国现代小说崛起之后,小说的主人公的这种命名方式也不多见。因此,这种命名方式便具有了某种神秘性和符号性,由此促成了读者在接受时深入探究的内驱力。对此,鲁迅自己是这样解释的:“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①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13、514页。
鲁迅的这种命名办法还引发一些读者的“考据”兴趣,有读者认为“况且无论小说的主人公是‘阿桂’还是‘阿贵’,如果用英文来拼音,照流行的拼法,应该第一个字是‘K’,而不应该用‘Q’。既用‘Q’,就难免别有用意。这是我们几个人在刚读到《阿Q正传·第一章·序》时的一些‘考据’”②川岛:《和鲁迅先生相处的日子(选录)——当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时候》,见孙伏园、许钦文等:《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第277页。。还需要指出的是,在《阿Q正传》中,鲁迅除了把主人公命名为阿Q之外,还把次要人物形象命名为“小D”,并赋予了这两个人物形象在文化性格上的同构性,这正如鲁迅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所说的那样:“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③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55页。这就是说,小D是阿Q过去的缩影,阿Q是小D的未来影像。这样的一种贯通便使鲁迅所要批判的国民性这一遗传密码得到了具象化的呈现。从本质上说,鲁迅的这样的命名方法并不仅仅体现在读者对读音等问题的考据上,还在于这样的命名方法把汉语命名的具体个人扩放到了更大的群体之中,也就是说,这种命名方法放大了阿Q这一人物形象的指代范围,由此让读者沉潜于“阿Q是谁”的疑问中,进而增加了读者在阅读接受时对阿Q所指代的具体个人的普遍性的体认。
文学经典的诞生是在多个“主体”交互影响下产生的,作者主体、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到文学生产中,最终完成了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历史过程。从《阿Q正传》自“约稿”到“创作”进而到“传播”的原初现场来看,不管是鲁迅本人还是文学编辑,抑或普通读者,大家也许都不曾意识到《阿Q正传》会成为文学经典,但毋庸置疑的是大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了《阿Q正传》“经典化”的历史进程中去。随着副刊的连载,课堂的互动以及批评的跟进,《阿Q正传》逐渐地显露出了其作为文学经典所具有的思想峥嵘本色,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意蕴才逐渐地得到人们的确认和重视。《阿Q正传》这一中国现代小说的标志性作品即将横空出世,中国现代小说即将迎来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实际上,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期间,并没有因为文学创作而中断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兼课,他依然保持着既有的生活工作节奏,以至于他在日记中鲜有创作《阿Q正传》的片言只语。这就是说,鲁迅把自己置于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不断接受着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由此使得外在的现实生活等要素依然具有穿越时空阻隔而直抵作家内心世界的能力,这恰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至高境界。鲁迅在文学创作时始终敞开着生活和社会的大门,始终保持着一种自由自然的心态,这才使得他能够以自主自足的心态沉潜于文学创作中,并把自己经过了多年孕育后生成的阿Q形象外化出来,从而确保了《阿Q正传》具有直接回应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功能。与此同时,鲁迅还与世界作家作品保持着艺术和思想上的密切联系,这又使得《阿Q正传》具有世界文学的某些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既是在东西古今文化碰撞下诞生的新文学,也是在作者、编辑与读者等多个主体交互作用下产生的新文学,《阿Q正传》的诞生及其“经典化”历程清楚地显示了新文学背后多维的历史合力与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