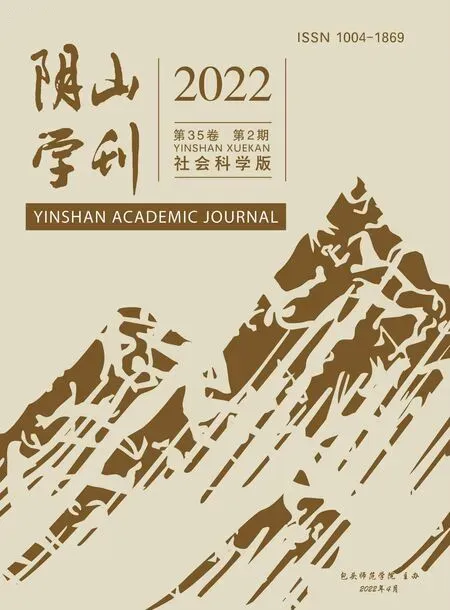论罗兰·巴特神话学中的语言批判*
沈 祖 新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与法国的罗兰·巴特是该领域中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流派与研究者,为该领域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思路、治学方法与学术范式[1]18。其中,罗兰·巴特的大众文化研究的特点是将文学研究的思路移植到该领域,将大众文化现象视作文本,将现代语言学作为分析大众文化现象的理论基础,再利用符号学对其进行丰富与掘进,最终形成以能指、所指和符号为基本结构的神话学。值得注意的是,罗兰·巴特将自己对语言的执着投射到神话学中,语言是解析神话的基本单位,也是理解和分析神话学的关键所在。
一、神话学的语言结构
语言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中有着本体性的地位。从本源上说,神话是语言的变体;从结构上看,语言的基本结构“能指与所指”是神话结构的基础;从认知上讲,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成为理解神话的理论基石。可以说,理解神话学的语言结构是理解神话学的基础与前提。因为在罗兰·巴特看来,“语言学的对象也是没有限制的”[2]191,他认同本维尼斯特“语言结构就是社会性本身”的论断,不仅将语言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也将现代语言学视为符号学建构的基础,神话学正是该思路在大众文化领域的学术性延伸。
罗兰·巴特将神话界定为“一种言说方式”[3]139。由此可见,他一方面将神话归结为语言,确立起二者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又强调神话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言说方式,在更为具体的层面突出神话研究的重点在于它如何讲述、建构自身。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相比,神话是语言的变体,其变之处在于语言是将世界/现实文本化,神话则是将文本化后的世界/现实再次符号化。在索绪尔之前,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是词与物的一一对应。索绪尔则打乱了语言的历史秩序,认为语言中的词与物是在差异的结构中获得识别与意义,并且,这个差异的结构也是社会文化的历史产物。罗兰·巴特不仅接续了索绪尔的基本理念,用现代语言学的视角将世界文本化为能指与所指的语言结构;更是从大众文化现象中探寻出“隐秘的角落”——被文本化的世界被再次符号化为神话。
符号化是罗兰·巴特谈论神话的真正兴趣所在,他的研究目的并不仅是揭示出神话的虚假之处,更是解剖这种虚假得以成立并有效的结构,并由此发现神话是如何成为我们认知中的样子的,换言之,揭示了我们是如何按照神话设计者的意图来认知它的。这也正是罗兰·巴特将神话界定为“言说方式”的原因所在:言说方式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方式,存在方式又直接影响着接受者对其的认知与理解。罗兰·巴特钟情于符号学,或许正是因为符号学能清晰地展现出这个结构,并可以对其做出最为透彻的解释,因为在罗兰·巴特看来,符号学的对象就是“由权势运作的语言结构”[2]193。以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例来说明符号学的解释方法与理论效能。可以说,这是海子的全部诗歌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首,也是被误读得最为严重的一首。如果脱离诗歌的语境,单纯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带给读者的感觉是温暖的祝福与柔情的舒适,这种感觉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现象,一种语言在读者心中的投射。如果顺势将之写在海滨度假村的广告牌上,再搭配上具有夕阳、沙滩、椰树、三角梅等意象的照片,这句诗就摇身一变成海滨度假村的最佳广告语,因为它既符合海滨度假村的宣传形象,更迎合了消费者对休闲的想象。这句诗可以成为宣传语,就是由于商家抽取了它的诗歌意义,将之符号化为“空洞的能指”,再向其注入新的意义,最终使它成为符合商业宣传的神话。
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的主要内容就是用符号学的方法呈现出神话修辞术中潜藏的不为人知的“两步走”式的内在结构,即神话学的语言结构。在罗兰·巴特看来,任何符号学系统都需要三项因素:能指、所指与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组成基本的语言模型,这一模型又在不同的情境中被不同的使用价值重新赋型为符号;这个符号被抽离了所指,成为意义空位的形式;它再在新的情境中与概念组成新的符号,此即神话。可以说,罗兰·巴特从语言的角度认知、理解、分析神话,并将之界定为言语方式的根本原因在于神话和语言都与世界相关,它们均是关于现实的言说,是对真实的描述与表达。二者的区别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或许还能让自身与世界在现实的层面相关,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关联到现实,甚至构成对真实的指涉;但神话将语言抽空为“单纯的语言”,进而让其与另外的意义嫁接,最终结出名为神话的果实。罗兰·巴特之所以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神话,一方面是在根本上将之视作“一种有待曝光的欺骗”[4],另一方面或许也是由于他在其中见识到意义的缺失与补位竟如神话般变幻莫测。
二、神话学的现实呈现
神话与语言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是通过与世界相连而完成对现实的呈现以及对真实的指涉,而神话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通过符号化的修辞术来建构属于自己的现实,并将之确认为真实。而这个建构现实的过程就体现在神话的意指作用中。
罗兰·巴特认为“意指作用就是神话本身”[3]152,因为意指作用所完成的任务就是神话的自我实现,即符号与概念的嫁接。在此过程中,神话的神奇之处是它并不藏匿现实,而是扭曲现实,但又不让现实销声匿迹。这里的关键是,神话在扭曲什么,而答案依然在语言中。现代语言学将语言建构为一个共时性结构,能指与所指正是此结构的两块基石。但不可忽视的是,能指与所指的组合虽然不是先验性的彼此咬合,却也不是偶然为之的突发现象,其背后是历史文化与社会惯习积淀下的共识,这是语言得以有效的关键所在。也正因此,语言背后的历史共识便是神话需要架空的世界,即“神话是由真实的历史性质的流失构成的:事实丧失了其中蕴含的记忆,这记忆原本造就了事实”[3]173。由此可见,意指作用在发挥其效能时,需要将语言中积淀的历史事实抽离出来,将语言符号化为空洞的能指——形式,进而将概念灌入其中。罗兰·巴特反复提及的“法兰西黑人士兵向三色旗敬礼”的例子正是说明此问题的范例。当这张照片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关注到的是黑人士兵向三色旗敬礼时专注的神情、凝望的眼神以及三色旗飘扬的背景。此时,黑人背后的历史真实反而成为对终极目的的强调——即使是曾经的被殖民者也心甘情愿地效忠于宗主国。作为历史见证与民族创伤的黑皮肤反而强化了法国国家意识形态的现实需求,显示出法兰西的强盛与包容。在神话将反讽转化为强调的过程中,它并未回避更不藏匿历史,反而在不断地突出历史;只不过,它在突出历史的同时更回应了当下的需求,呼应着当下强大的意识形态召唤。
因此,罗兰·巴特认为神话改写现实的本质是“使意义异化了”[3]153。更为重要的是,被异化的意义依然是现实,只不过是一种被建构的现实,情境化正是这种现实的突出特征。在《作家度假》一文中,罗兰·巴特分析了《费加罗报》所拍摄的作家纪德度假的照片。在他看来,这张照片达成的效果是“真实地提供了资产阶级对作家的看法”[3]19,“真实”一词是此处的重点。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来源于其日常性,即照片中作家与常人无异,他与普通的中产阶级共享着同样的休闲方式,他所享受的是普通人也有能力支付的闲暇时光,而这种认识正是神话所期望达成的效果。罗兰·巴特指出,人们在重视度假这一情境的时候忽略了纪德的作家身份。在这张照片中,神话架空了作家的社会身份与历史标志——天才、机遇、独异性等,通过情境化将其还原为普通人,但这张照片的重点依然是作家的特殊身份。照片是在利用作家的特殊性来让读者以为他并不特殊,照片的真实性恰恰来源于普通人也可以像作家那般度假休闲。但人们忽略的是,这种认知本身就是对作家的特殊性的认可与强调,人们所相信的只是作家走下神坛的姿态。正是在神话学的烛照下,这种“平等”的背后潜藏的鲜为人知的社会等差被昭然若揭。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境化的现实“具有命令的,强迫使人正视的特性”[3]155,这正是其意识形态性的体现。罗兰·巴特正是针对其“真实效应”所掩盖的意识形态性将其解读,也是还原为一抹流光溢彩的片影,一段被刻意截取的画面。
三、神话的意识形态性
透视现实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因素,揭开遮羞的虚假性的帷幕,厘清现实中压抑性的潜流,这正是批判理论的常规理路。概括地说,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在根本上是面向现实的理论,它一方面在思想谱系中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的感召,将“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作为理论的终极所指,另一方面又立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语境,尝试用批判理性抗争工具理性,在总体上表达出一代知识分子介入社会实践的意识与努力[1]40。但是,当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是罗兰·巴特时,则需要在这里停下脚步,并扪心自问——此种理解路径与思维方式契合研究对象吗?毫无疑问,罗兰·巴特曾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神话修辞术》中也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现实关怀与批判精神;但是,罗兰·巴特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并不感兴趣于意识形态背后的政治经济体系与社会阶级结构,也没有过于强烈的介入意识,“巴特贯彻的常常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饱含着一种马克思主义情绪、马克思主义的处世风格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5]52。相较之下,罗兰·巴特的社会批判意识更多地建立在知识分子对权势的拒绝以及对压迫的警惕上。他对现实所呈现的真实的怀疑便是这种心理的投射,神话恰好是他揭示虚假、表达怀疑、刺破真实的绝佳范例,真实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也就顺势成为其神话学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理解罗兰·巴特的意识形态概念,应该与他在《写作的零度》中所透露出的对真实的怀疑以及对幻觉的拒绝相关联,与其文学批评中的“真实效应”理论相呼应,并结合《神话修辞术》中的神话学分析,将之还原为语言批判中的一环,最终定位在语言上。
可以说,对语言的看重贯穿了罗兰·巴特的整个写作生涯,渗透在他写作的各个方面。他如此重视和执着于语言的原因在于,语言是人类面对世界的最基本中介,真实便存在于词与物的关系之中。巴特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便是这种观念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投射,他在《写作的零度》中批判了作家-艺匠的写作风格,认为这种写作方式是作家潜在性地依赖于外部世界,这类作家是在用精心雕琢的文学形式营造真实。在罗兰·巴特看来,这种真实只不过是用“无用的细节”营造成的“真实效应”,是作家利用写作技法创造的幻觉。他以福楼拜小说中的气压表和米什莱笔下的小门儿为例,意在说明这些“无意蕴的标记”对于现实主义文本的意义是让文本中的细节“变成了现实主义的能指本身”,使其成为“拟真的基础”[6]。这些细节召唤读者将其视作现实的对应物,向读者表明“作者客观描摹现实的意图,保证了文本所言的真实性”[7]。罗兰·巴特对这种“真实效应”嗤之以鼻,认为这只是不足为信的“指涉幻象”。他的“真实效应”理论促成了现实主义的话语转型,将语言-现实的反映关系扭转成语言-语言的互文关系,把语言视作与现实世界一样的独立性存在,认为“在叙事中‘所发生者’,从所指者的(实在的)观点看,实际上只是空无的,‘发生’的东西只是语言、语言的历险,它的出现永远是值得庆贺的”[8]144。这种话语转型所表达的正是罗兰·巴特对现实主义的怀疑以及对真实的追求。
当罗兰·巴特怀揣这份对真实的怀疑和执着与光怪陆离的大众文化现象相遇时,他才会一头钻入其中,并经营出精致而奇崛的神话学,雕琢出充满奇想的神话修辞术。与作家利用现实主义的技法与风格所营造的“真实效应”类似,神话也是在营造属于自己的“真实效应”,并将其确认为现实本身。较之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神话建构自身、表现真实的手法更为多样,也更具意识形态性,更能贯彻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意志。只不过,罗兰·巴特用意识形态性这个概念所指明的是与真实相对应的虚假,他的兴趣在于揭穿和刺破制造出“真实效应”的结构。可以说,这是一种学术志趣,也是一种智性趣味。他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虽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却并不以政治诉求的本体论为鹄的(1)韩子勇、高佳彬在《“意识形态”概念流变考梳》中梳理出意识形态作为术语的四种内涵:观念科学、精神想象、本体论哲学和政治学说。本文认为,罗兰·巴特对该词的使用介于后两者之间,偏重于本体论哲学。所谓本体论哲学的用法是界定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本质,突出的是社会现实反映说和社会现实异化说。在这一点上,罗兰·巴特对意识形态的使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同;不同的是,罗兰·巴特对意识形态的使用只是为了突出其研究对象的虚假性与控制性,他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批判虽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却并不以后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根本依据。这是他在使用这一术语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差异之处。,这也是罗兰·巴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诸君子的大众文化研究的区别所在。
罗兰·巴特将资产阶级所制造的神话称为“右翼神话”,认为它以大众文化的形式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内部肌理之中,并以“无名化”与“去政治性”的方式使自身得以“普遍化”,以远离政治的方式达成政治性的目的,以日常性来掩盖其意识形态性的本质诉求,最终完成维持现状的总体性目的。右翼神话得以普遍化的基本策略是将自身的价值理念与现实诉求提升并虚化为以普世性、永恒性为标识的世界观,让民众生活在被神话过滤和装点的日常生活的表象之内,即“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身,是资产阶级将现实世界转变为想象世界、历史转变成自然的活动过程”[3]172。可以说,这种“普遍化”后的生活表象指向的是“伪自然的总体景象”,而“伪自然是当代资产阶级世界梦想的界定”[3]180。秩序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想伪装的“自然”,如同纪德的照片,他们将特殊装扮成普通的模样,伪装成大众唾手可得的共享资源;但在实际上,大众朝向它的姿态依然是仰视和效仿。罗兰·巴特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伪装秩序的手段称之为“将历史产物变成本质类型”,认为它的最终所指是“使世界固定”[3]184,也即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呼应并表达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护。“伪自然”的“右翼神话”就如同“嘉宝的脸”,美的理念就是其最大的现实性,而与此同时,“本质日趋模糊,逐渐被眼镜、宽边软帽和尘世生活掩盖住了,但它绝不会败坏或改变”[3]52。这也正是右翼神话的实践路径——将秩序伪装成自然,进而将这种自然上升为现实逻辑与宇宙秩序,被压迫者虽然始终有发言的机会,但他们的声音早已在真空的环境中消弭,世人看见的只是张嘴的动作。
归根到底,神话是在营造自身所需要的“真实效应”,“真实效应”的背后便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诉求。罗兰·巴特在文学批评中颠覆现实主义风格,在大众文化现象中解剖神话的组成结构与运行方式,其目的都在于刺破“真实效应”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假面。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大众文化现象,它们的书写与构成都是“给幻想物洒上了真实性的亮辉”[9]142。肉搏的摔跤场景、悠闲的作家度假、忠诚的法军将士均是如此,他们都是以真实的样貌来表达幻觉的内容,而幻觉的实质是“符码上覆盖符码”,它所达成的最终目的是对自身统治的维护以及对民众的整合,即“符码之无限循环一经确定,身体自身便无法逃脱这循环了”[9]78。
在罗兰·巴特对神话的意识形态性的揭示以及对“真实效应”的关注中可见这背后潜藏的是他对真实本身的期许与追求。与意识形态相对,罗兰·巴特认为诗化可以成为一条走出神话围城的道路,而诗又是语言的代言人。由此可见,面对神话的围追堵截,巴特还是对语言寄予厚望。因而,在罗兰·巴特的理论范畴内,无论是对意识形态和神话的理解,还是对真实的期许与追求,都应落实在语言批判的基础之上。
四、神话学的语言批判
语言是罗兰·巴特思想的整体出发点,也是他探寻真实的基本单位;在神话学中,语言是神话的基础,现代语言学也为神话学架构出基本的理论框架,语言也因此成为神话学中最基本的关注点。总之,罗兰·巴特一方面展示出神话对语言的劫掠,另一方面又对语言心存期待,甚至寄予厚望,认为语言是走向真实的必由之路。
在罗兰·巴特看来,“神话总是一种被劫掠的语言”[3]163,劫掠的过程正是生产神话的过程,即语言的所指被抽空,继而被符号化为形式,最终与概念相嫁接。罗兰·巴特在《今日神话》中专门辟出《神话作为劫掠的语言》一节来阐述神话对语言的架空、嫁接与改写。在神话面前,即使是数学语言与诗歌语言这类独异性与自我指涉性极强的语言类型都难逃厄运,因为“神话可以击中一切,腐蚀、改变一切,乃至可以击中、改变那正在拒绝神话的行为本身”[3]164。而神话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劫掠并改写诗歌语言的原因就在于其引以为豪的抵抗性与自我指涉性,也就是说,神话可以利用诗歌语言“符号的明显无序”的特点将之改写为“空洞的能指”。仍以广告对海子诗句的利用为例。实际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的“明天”“尘世”等意象都透露出海子的绝望心情,作为标题与诗眼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是在温情的背后隐露出绝望的弃决。以这首诗中的“明天”为中心,就有学者认为其中蕴含主题是“以宣称拥抱爱的方式来哀悼爱的失去与不可能”[10];也有学者认为它表达了“自居于精英位置的文化阶层在现实生活的失落感的反应”[11]。但无论是哀悼还是失落,都与诗句的字面意思相差甚远;而神话所劫掠的对象,正是诗句中单独且纯粹的“字面的诗意”。这让诗歌语言成为神话的猎物,使其最终成为“富有表现力的行尸走肉”[3]164。
当罗兰·巴特脱离神话而专门谈及诗歌语言时,又透露出对诗歌语言的看重与期待。他认为,在诗歌语言中可以“发现语言的前符号状态”[3]165,也就是说,诗歌语言不仅可以让词与物达成绝妙的契合,甚至能够让物在词中脱颖而出,让语言挣脱社会惯习的束缚,让真实从语言中突出重围。更确切地说,诗歌语言可以让语言接近真实,具有抵抗性与自主性的语言也是真实的表征。在《写作的零度》中,罗兰·巴特便认为现代诗将古典语言的“连续体”升级为具有“非连续性”的“中断性的自然”,其中排除了人为因素,让诗歌成为“语言自足体的暴力”[2]33。这也显示出罗兰·巴特的神话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同源一体性。“语言批判”这个概念便出自《批评与真实》这本讨论文学批评的小册子,罗兰·巴特在这里将“语言本身”视作文学批评的对象,将“语言批判”视作“文学本身”[12]38。他在这本书中划分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前者指的是语言的辞典意义,后者才是文学的对象,因为“假如第二语言没有扰乱或解放‘语言的确定性’,那就没有文学了”[12]36。由此可见,语言批判指的便是语言的自我批判,即语言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达到自我更新的目的。巧合的是,神话学也是由两层结构组成,神话正是在“第二层”上将“字面的诗意”劫掠成“富有表现力的行尸走肉”。罗兰·巴特在这里重拾诗化的抵抗潜能,让诗歌语言或者说现代诗以这种“暴力”的方式与意识形态相抗衡,以诗化的姿态与意识形态分庭抗礼,不得不说这是将文学批评的思路平移到神话批评中。在《今日神话》的结尾,罗兰·巴特将诗化与意识形态化并置,认为诗化是“一种最终难以穿透、不可简化的现实”[3]188,认为二者可以构成抵抗性的张力关系。
语言的诗化是罗兰·巴特面对神话的最后武器,也是神话将他逼到现代性的死角后所能祭出的最后一招。在文学批评中,语言是罗兰·巴特最为看重也是最想解放的事物,他一路贬低作者的目的就是将语言推至理论的前台,神话学正是这种思路的延续。在面对神话的十面埋伏时,他依然寄希望于语言。透过语言之镜审视神话之相,罗兰·巴特解剖神话的语言学结构,批判它的情境化现实,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性,最终还是将思想的矛头反身射中语言的靶心,继续着他对真实的不懈追求。并且,罗兰·巴特所期待的境界,或许也是其神话学的终极指归,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洋溢的介入热情与批判激情,而是“现实与人、描述与解释、对象与知识的调和”[3]189。而这一系列对应关系的根本就在于语言之中,在于词与物之间。
五、批判精神的异与同
可以说,对语言的执着与看重是罗兰·巴特的大众文化研究的独特之处,也是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异之处。但即使罗兰·巴特没有形成系统化、明确性的批判理论,批判精神(critical spirit)也是他与法兰克福学派诸君子之间相互联系的精神纽带与思维共性,对偶像的批判正是这方面的体现。罗兰·巴特在《作家度假》中发现纪德的照片中隐含着以普遍的名义去掩盖特殊的障眼法,照片所营造的“日常的生活细节”所达成的效果是“把肉身和精神的综合存在归属于超人特性”[3]21,其实质还是对“超人”这种不属于大众的非日常性因素的维护与强调。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理论家列奥·洛文塔尔也对大众偶像进行过专门研究,他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的传记对象由“生产偶像”变为“消费偶像”,传记作家用“最高的语言”铺陈、渲染传记对象的成长经历与个人特质,重复读者已经心知肚明的生活内容,将传主的生命轨迹压缩为“造物主的指令”,营造出他生来就会成功,并且一切都在助力他成功的人生假象。而如此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认可这种“虚幻的成人教育”,最终造成读者“对常态的认同,甚至是对庸俗无聊的认同”[13]。可以说,对偶像真实性的警惕与批判,对其背后隐藏的消费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揭示与解构,对权势的拒斥与控诉等都是批判精神的体现,更是罗兰·巴特与法兰克福学派诸君子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他们都秉承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理论自觉,并且都对社会文化中的虚假性、压抑性、权力性因素保持着敏锐的警惕与坚定的拒绝;另外,他们都将各自的理论应用于鲜活的现实生活之中,不仅用前者烛照后者,也用后者激活前者,更在激活的过程中延展、丰富自身已有的理论形态。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的彰显,更是理论自觉的体现。
这或许是罗兰·巴特最为重要的精神遗产,也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学术镜鉴。从21世纪初的“文艺学的边界”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开始,文学研究中存在的批判精神的缺失与介入效能的减弱的问题就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赵勇、陶东风、周志强、金惠敏等学者也纷纷就此问题进行过论述。赵勇就认为“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它丢失了文学性,而在于其批判精神的不断流失”[14],他从文化批评的理论资源与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入手来分析批判精神流失的原因,认为知识分子需要重拾批判使命与道义责任。赵勇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作为批判精神的重要资源,在多年的潜心研究中提出批判诗学的理论构想,力图弥合以美学分析为中心的内部研究和以意识形态分析为内核的外部研究之间存在的范式裂痕,努力为当下疲软的文化批评乃至于文学研究注入批判的活力与底气[15]。与之相对,周志强提出的“寓言现实主义”、金惠敏倡导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等理论命题都是为了激活文学研究的批判效能,以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方式拓宽文学研究的理论视域,让文学研究在当代仍能对现实发声,向未来召唤。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学者的理论命题的背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其中的响亮音域,而罗兰·巴特的相关理论却几近哑声。同样是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源头与研究范式,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接受差异呢?这一方面源于学者们个人的理论志趣与学术取向,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这暗示出罗兰·巴特的理论在应对现实问题上的后劲不足。
如前所述,语言是罗兰·巴特的理论基点与学术立足点,他以语言为参照进行文学批评、神话批评以及理论建构。对语言的执着与痴情贯穿了他的一生,但这也牵绊着他的理论思考。在面对现代社会中的神话乱象时,他以语言为基本单位,将文学批评的思路平移到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对神话的警惕也影响着他对文学问题的看法,《叙事结构分析导论》中对叙事结构中的大众文化潜能的揭示便是例证。罗兰·巴特认为“每一叙事都依存于一个‘叙述情境’,一组规约,叙事按其加以完成”[8]136,资本主义社会的叙事特征在于对叙事情境的规约的回避与遮掩,大众文化更是将连续性的叙事进行自然化的处理,以期达到“人人要求记号看起来不是记号”的效果[8]137,为神话这种资本驱动下的人造物罩上一圈自然的光晕,甚至将其升华为宇宙秩序。面对文学作品,罗兰·巴特将叙事视作句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剖析叙事结构,将叙事情境中对规约的倚重和使用具象化为现实主义文本对细节的采纳和凸显,用“真实效应”点出叙事结构中蕴含的虚假性;面对神话,罗兰·巴特同样着眼于探索神话建构自身的结构与方式,搭建出神话的语言结构。在文学与神话之间,在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之间,罗兰·巴特骑在语言的高墙上左顾右盼,语言的高地成为他审视二者的绝佳视点,但终究无法让他左右逢源。第一,文学作品与神话终究是两个范畴,诗化在文学中可以是反抗意识形态与社会权势的方式,但“诗化的神话”又是什么呢?可以说,诗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渗透着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罗兰·巴特的一厢情愿。第二,罗兰·巴特的语言观本身就存在矛盾之处。巴特一方面对语言的指涉功能抱有警惕,认为“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权势于其中寄附的东西就是语言”[2]182,将语言结构视作权势的投射;另一方面又对语言寄予厚望并饱含珍惜,将语言的诗化视作一种抵抗的策略与解放的途径。但是在根本上,语言可以拆解神话的内在结构,揭示它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共谋关系,但很难将批判的思路延伸至社会与现实本身,让罗兰·巴特能够如阿多诺那样在流行音乐的旋律中捕捉到飘荡的法西斯的魅影。即如汪民安所说,罗兰·巴特的神话学所实践的是“解神秘化”的活动,“巴特将神秘化限制于巴黎,限定于小资产阶级,限制于日常生活与大众传媒,总之,他限制于一种经验、一种感性、一种细微局面”[5]67。罗兰·巴特不仅在巴黎城市日常生活的细微局面中发现神话,他对神话的分析多是将问题的根源指向一个极为宽泛的代称——资本主义社会,而未由此再往下深入探索,考掘出神话与社会之间更为隐秘且丰富的联系;他的研究重点与写作志趣在于发现神话的言说方式,也即资本主义社会在如何讲述自身,如何搭建、呈现自身所需要的真实。在这个层面上看,语言确实是绝佳的切入路径,但是对神话/大众文化的研究却不能止步于此,资产阶级社会更不是批判之旅的终点站。
这样看,神话学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定位更倾向于方法论,而非世界观或认识论。汪民安就曾用神话学的思路分析过家乐福超市的空间布局及其隐含的政治经济学内涵。汪民安一方面对“家乐福”这个名词进行语言学分析,认为“家”“乐”和“福”这三个字指涉并营造出民族记忆中的集体乌托邦想象,商家以此掩盖其中的商业策略与跨国资本的痕迹,让我们“在一种刻意剔除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中购物”[16]168;另一方面,汪民安也将家乐福超市的空间结构视作一个暗含强迫性的巨大的语法模式,购物者必须遵从超市已经规划好的购物路线与货物分类体系,关注那些被摆在显眼位置的商品。由此可见,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可以用于空间批判,将空间布局视作语言结构或语法体系,将眼睛的关注点视作对语法的无意识遵从,由此展开以视觉为中心的空间批判。除此之外,文本批判也是神话学的拿手好戏。比如《我是余欢水》这部网络电视剧的叙事结构就是对“好人有好报”的民间生存逻辑的重复和强调,但是在该剧内核之上却笼罩着一层“倒霉的老实人”的叙事面纱,并利用诸多的现实细节迎合当下城市白领阶层的工作体验与生活感知,让观众在余欢水所经历的妻子的背叛、家人的嫌弃、同事的挤兑等事件中获得自我的认同感与挫败后的满足感;制作者用剧中来自栾冰然的个人情感来补偿余欢水所经历的众人造成的现实坎壈,将情升华为生存价值与现实寄托,以此让余欢水的现实解困变得顺理成章,并呼应好人终得好报的叙事内核,为大众留下做个好人的人生选择与前路方向。该剧的制作者抽空了余欢水的生活困境的现实因素,用情的补偿来劝导观众成为一个好人,以此创造一出道德劝诫意味浓厚的好人神话。综上所述,神话学的特征体现在展示好人神话的呈现方式与叙事结构,剖析超市空间的语法模式,但无法将思想引向更深的症结处并提供周志强所说的危机意识和政治想象力[17]。汪民安在《家乐福:语法、物品及娱乐的经济学》中便是使用了罗兰·巴特的神话学思路却并不拘泥于此,他将分析由对购物行为的勾勒引向关于劳动的隐身与娱乐的显形的论述,指出“在家乐福里,一切都滑向了游戏、滑向了表层、滑向了肤浅的戏剧”[16]179。如果只有神话学的工具,而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底气,汪民安的论述难以到达这样的深度。或许,罗兰·巴特及其理论正是因此才没有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举足轻重的精神资源。
但瑕不掩瑜,扎根现实的批判性与面向未来的乌托邦性依然是罗兰·巴特与法兰克福学派诸君子共有的精神状态与理论意涵。与后者相对照,罗兰·巴特的独创性在于通过语言的棱镜透视出神话的潜在秘密,用符号学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并将其应用到最为现实与鲜活的大众文化领域,打通了这一纯理论面对现实的任督二脉,以此开辟出一条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路径,延伸出一脉颇具智性趣味与现实洞见的理论谱系;但是在批判精神与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层面上看,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紧密的精神性关联。法国文学批评家安托万·孔帕尼翁把罗兰·巴特的理论生涯视作可供理论家们学习的范本,认为巴特的身上充溢着理论探险的精神[18]。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巴特的理论涉及文学批评、大众文化、服饰、摄影等多个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都能点石成金、落地开花。这不仅得益于其机智敏锐的理论思维,更受惠于其扎根现实生活的批判精神,敢于让理论迎接现实的挑战,成为朝向当下的言说。我们在神话学中,便能领略到巴特理论的精妙、睿智与勃勃生机。正因如此,在词与物的离散与耦合之间,在批判精神的异与同之间,我们始终可以在当下最新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现象中为罗兰·巴特的神话学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并由此更加清醒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