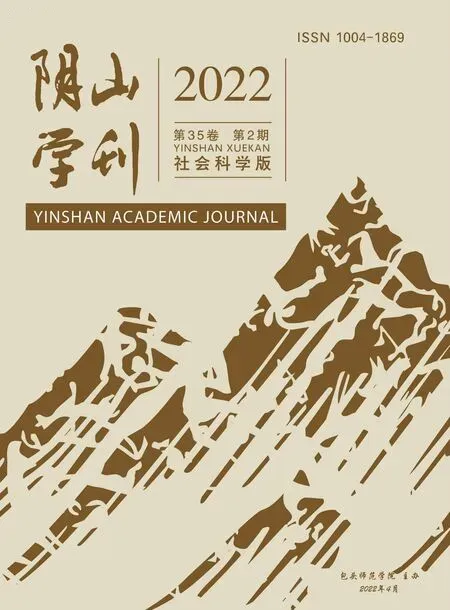西方环境美学中人类主体的死亡与重生*
贾 珊 红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理查德·塔纳斯在《西方思想史》尾声中阐述了在西方思想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原则与被排斥贬低的女性原则从分离对立走向融合统一、万物归元的过程。本文认为塔纳斯在书中提到的男性原则主要指西方思想中伴随着主体性觉醒而发展起来的崇尚理性、不断求索、追求自由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人类走向对未知的追问,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但近代以后,随着人类主体性不断膨胀并逐渐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人也走向了全面异化。人类因此逐步反思自身,开始与以往贬低排斥的“他者”达成和解,这些“他者”便包含人类以往极力摆脱的自然母体。在“人们认识到女性原则不是客体化的‘他者’,而是根源、目标和无所不在的存在”之时[1]485,人们也认识到自然的整体性和包容性,以往肆意支配自然的人类主体在融入自然之时逐渐死亡,而全新的人类主体又在生态构建中获得了重生并走向了万物。
一、元分万物:前环境美学时期主体的觉醒与独立
古希腊哲学最初以自然哲学为主,当时的哲学家专注于探索外部自然世界,企图在纷乱的众生之中找到世界的本原,哲学带着浓厚的本体论色彩,此时人类还并未产生明确的主客意识,人和自然尚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从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的主张,哲学便从天上转向了人间,此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都开始从不同方面论证人的幸福和理性的生活,人的主体性逐渐觉醒。但此时西方哲学仍主要关注对世界统一本原和秩序的探索与解释,新柏拉图主义提出“流溢说”,系统解释世界的本原与秩序,在这一学说的统帅下,纵然万物纷乱但终源于太一。随着人类主体性的不断觉醒,最初无差别的统一状态逐渐走向了分裂。近代以后,哲学的研究对象逐渐从实体转向主体,笛卡尔将“我思故我在”作为其哲学的第一原理,充分肯定人思维的作用,世界成了与思之主体相对的客体,人类开始从对本体的迷信中解脱而出,对自身的理性充满自信。康德在其哲学中进一步肯定人的理性,人通过先天认知形式从纷乱的现象界中获得种种认识,知识的可靠性由上帝转向了人,人同时能为自然立法。正如塔纳斯所言:“西方思想的演变发展是受到这样一种巨大的推动力推动的,这种推动力就是通过把他自己与自然的原初的统一脱离开来而铸造独立自主的理性的人类自我的一种推动力。”[1]482沿着主体性发展的道路,理性而自主的人类主体从自然母体中分离并获得新生,原本浑然一体的世界走向了分裂。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裂并不只是人与自然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而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事物的分裂。首先,当人作为主体从客体世界分离之时,主体也成了一个可被量化分解的整体,自古希腊哲学时期便萌生的精神与肉体的区分在主客二分潮流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精神最终获得了独尊地位,肉体则被贬低和遗忘。此外,在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推动下,机械宇宙观逐渐深入人心,以往宗教笼罩下对外部世界的敬畏感不断消散,人类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对自身的理性更加自信。在现代科学方法的鼓励下,人将客观对象从统一的环境中孤立出来,分解成零散的要素进行量化分析。由此,外部世界在与人分离之后也与人一样走向破碎化,走向了“元分万物”的阶段。
在哲学领域,随着人类主体性的觉醒,人逐渐与外部世界分离。在美学领域,这种分离的倾向主要体现于18世纪盛行的审美静观理念上,受其影响,这一时期的自然审美以科学化、客观化的眼光观察世界。观赏者将自然对象从统一的环境中分离出来,排除利害考虑和主观感受,对自然对象的色彩、线条、形式组合等感官特性进行审美欣赏。原本统一的自然整体在人的觉醒过程中被迫与人分离,又在孤立的审美静观下被分割和量化,变得更加破碎。这种无功利的审美静观看似对自然进行科学客观的审美欣赏,实则暗含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随着主客体的进一步分化,自然审美中的审美静观逐渐发展成如画的欣赏模式,并在18世纪走向兴盛。此时,在审美领域人与自然彻底分离,人以主体的视角去看作为客体的自然对象,看与被看本身便透露出人与自然不平等的关系。“体验如画性就是以画家的眼光去观看自然”[2],人根据主观意愿框选自然风景,按照欣赏艺术的方式去欣赏自然。连续整一的自然环境被分割为一个个破碎孤立的优美景观,自然环境中并不优美的部分被直接舍弃,自然在走向破碎化之时也丧失了自主性,“艺术中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制度蔓延到了自然欣赏之中”[3]。如画的欣赏模式实则将自然作为可被人随意操控的对象,在这一模式的推动下,人在从自然母体中分离而获得新生后,不断成长最终肆意操纵自然。
如上所述,随着人类主体性的不断觉醒,人从最初无差别的统一母体中分离而出,理性自主的人获得了新生。这在自然审美中表现为审美主体与自然审美对象的分离与对立,自然审美进入了“元分万物”的阶段。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分并不是指分化形成万物,而是指自然在与人分离后,又被人任意操纵,走向了分裂和破碎。自然的审美地位也不断降低,至黑格尔将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后,自然在美学领域便被人忽视和遗忘。
与此同时,人类思想中的男性原则在推动人类走向独立与进步之时,也为人暗藏反思的线索:笛卡尔哲学在肯定人的思维之时割断了人与本体的联系,康德哲学在赋予人自信时将人的认识领域限制在了现象界,现代科学在推动人认识宇宙万物时也使人意识到自身的渺小与孤独……人在前进的道路上逐渐意识到自身所经历的异化与幻灭,这些都使人在脱离母体后又回望母体,最终在旧有主体的死亡中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回归。
二、万物归元:环境美学下狂妄主体的死亡
主体性的觉醒促进了自信理性的人类个体的诞生,新生的人在成长过程中摆脱了以往自然、宗教等各种因素的束缚,成了世界的主宰者和自然的立法者。但在这之后,人类逐渐发现并未获得期许的幸福,工具理性迫使人变为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孤独齿轮,上帝死后,人在精神上也无家可归。塔纳斯总结道:人在不断觉醒之后,也“逐渐地并且不可避免地从笛卡尔—康德的状况逐步发展成为卡夫卡—贝克特式的生存的孤独和荒诞的状态。”[1]472肉体和灵魂上的双重漂泊使人对过往的启蒙历程进行反思。同时,人类对自然的狂妄操纵和肆意索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人类也反受其害,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日益加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这些因素的驱动下,人类重新认识自身并虚心与外部世界和解。这种和解与回归的倾向在环境美学的兴起中有所体现,环境美学重新发现并重视以往被忽视的自然美,反思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推动人类与自然走向平等与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狂妄自大、肆意妄为的人类主体也走向了死亡。
首先,新兴的环境美学力求消解主客体的二元区分与对立,主张人与自然的融合统一,这既是万物重新归元的过程,也是旧有人类主体在融合中走向消解的过程。西方环境美学之父罗纳德·赫伯恩在《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中提出,与艺术审美中主客体分离的关系不同,在自然审美之中,人本身便处在自然环境之中,这也就改变了传统自然审美的视角,人从看自然转变为在自然之中。这一认识在阿诺德·伯林特的交融美学中得到了更为深远的阐发。伯林特重新界定了环境的概念,认为完全不受人类影响的自然环境已然消失,而环境是包含人类各种活动与自然万物的一个综合体,人本身便在其中,人与自然环境不存在内外与主客之分。因此,在自然审美中,也就并不存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说,人不仅在自然环境之中,而且与自然相互融合、相互依存,这就以人与自然融合为一的一元论彻底瓦解了自然审美中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从根本上消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这种融入的主张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与统一,人不再将自己作为高于万物的主宰,而是在实现平等的过程中主动融入自然万物。
除了主客二分的审美倾向,环境美学也反思了自然审美中的审美静观传统和对自然感官形式的单一强调,反对以如画的艺术欣赏模式来欣赏自然环境。赫伯恩在其论文中对自然审美和艺术审美的特点进行了讨论,他认为除了不同的主客关系外,自然环境与艺术对象的另一区别便是“无框架”(frameless)的特性,这实则认识到了自然对象与其所处环境间的紧密联系。赫伯恩进而强调自然环境所具有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反对将自然对象孤立出来进行欣赏的如画模式。他同时也反对传统自然审美对自然感官形式的单一强调,认为这种将自然分解为线条、色彩、组合的行为势必会抹杀自然带给人的多样的、沉浸式的审美体验。这些观点同样也在伯林特的交融美学中得到了发展,伯林特不仅关注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还强调人对自然体验的连续性。他认为在自然审美过程中,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在内的人的各项感觉都参与其中,彼此相融,达到通感的状态,与此同时,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也影响着人的审美体验。于是,在自然审美中,人通过体验理解自然,人在其中并非被动静观,而是积极地投入和参与到自然之中,与自然融合为一,难分难离。这种人与自然全方位、各要素的融合在其他学者那里也得到了阐发,斋藤百合子、托马斯·海德等人都提倡利用民俗故事、神话传说、个人经历等人类文化信息对自然审美欣赏加以辅助,这也就弥合了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界限,推动二者融而为一。在环境美学发展中,这种对自然环境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尊重延伸至对人类体验连续性的强调,最终走向了人与自然的全面融合,体现了人类打破自然审美中主客界限的决心。在融合的过程中,以往主体性膨胀所导致的偏执和狂妄走向了死亡,而具有自主观念的人类则在更高层次上主动回归了自然母体,实现了万物归元。
环境美学推动人与自然走向融合,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自然各要素之间的平等,在万物归元之时排除人类中心主义与等级主义立场。卡尔松围绕“适当的自然审美”提出的观点便能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平等关系的追求。卡尔松认为只有尊重自然的真实特性,如其本然地进行审美才是对自然适当的审美。这也就从理论适用性上否定了传统运用艺术欣赏模式欣赏自然的做法,体现了当代环境美学对自然真实样貌的尊重,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平等的理念。在这样的自然审美中,人不再以主观意愿随意地赋予自然以特定的审美价值,而是运用相关知识,在真正理解自然的基础上对自然进行审美,从而祛除以往人类社会强加给自然的意义,还自然本真的样貌。同时,环境美学也重视自然环境中不同部分、不同要素的平等性,排除了如画传统影响下自然审美中的等级主义倾向。以卡尔松为代表的环境美学家提出“肯定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认为“所有未被人类触及的自然,在审美层面本质上都是好的。对自然世界正确或适当的审美欣赏基本上是肯定的,否定的审美判断很少或没有。”[5]“肯定美学”所提到的肯定的审美属性并不局限于优美这一单一特性,秩序、和谐等都是肯定的审美属性。由此,以往在如画的审美模式中被排除的自然环境如今也在环境美学中拥有一席之地,其审美价值获得了尊重和肯定。
综上可见,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环境美学兴起之后,与自然母体分离的人类逐渐与自然走向了新的融合,以往带着明显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人类主体走向了死亡。需要注意的是,环境美学虽然倡导人与自然的交融合一,有的理论甚至消解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但并不是鼓励人回到前理性时期蒙昧无知的浑然状态之中;而是在保有理性的前提下,推动人类破除主体性迷障,认识到自然环境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达到融合统一。这样,原本一元整合的世界分裂出的孤立破碎的万物在更高层次上走向了统一,自然审美也进入了万物归元的阶段。
三、走向万物:环境实践中主体的重生
如上文所述,西方思想在反思自身后,“为了达到与受压制的女性原则的这种重新统一,男性原则必须经受一次祭礼、一次自我死亡”[1]485。这种自我牺牲的意识在自然审美中的体现是环境美学的兴起,人放弃了支配性地位,主动地走向环境、平等地体验环境,最终融入自然环境。但人与自然的融合并不意味着人丧失了自主性和能动性,自然虽然将人包容其中,却并未消解人,正如伯林特所言:“景观就如同一套衣服,如果离开了穿它的人就变得空洞而无意义。没有人类的存在,景观所拥有的只是可能性。人类不仅通过思考而且还通过存在创造知识并对景观做出贡献;通过行动而不是静观获取理解。”[6]14由此可见,人走向自然环境,并不是被动地融入其中,而是积极地参与到实践中,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随着环境美学的不断发展,人在万物归元后又走向万物,这种从元到万物的过程不再是分裂与对立,而是在实践中对环境的生态构建,在融合的基础上对个体独特性与差异性的保有与尊重。
环境美学在进行理论建构之时也认识到了其需要实现的实践性,伯林特曾在《环境美学》中将环境美学归属于应用美学,“所谓应用美学,指有意识地将美学价值和准则贯彻到日常生活中、贯彻到具有实际目的的活动与事物中,从衣服、汽车到船只、建筑等一系列行为”[7],可见,伯林特在研究的早期阶段便十分重视环境美学的应用性与实践性。随着环境美学的深入发展,有关实践的设想与规划也更为具体,“在环境美学中,理论思考和实践目的是不可分割的……环境美学能促进以下这些相关的合作研究:城市和区域规划,公园、森林和荒野的保护政策的制定,对现存问题的理解以及区域划分和环保准则的建立。”[6]28由此可见,环境美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走向对环境的生态实践,其中最为普遍的途径便是与景观设计相结合,在实践中实现生态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交相辉映。
西方景观设计学科早在环境美学兴起之前便已有发展,那时的景观设计主要集中于对风景园林、景观建筑的规划和构造,所创造的景观作品也大多如同风景画一般割裂而孤立,并未考虑环境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此种类型的景观实践实则与西方自然审美中的如画传统不谋而合。在环境美学兴起后,西方的景观设计学科逐渐与环境美学走向融合,在此过程中,环境美学为景观设计的生态转向提供理论指导,景观设计则为环境美学走向实践提供着力点。其中,韩裔美籍景观设计师贾科苏·科欧(Jusuck Kou)提出的生态景观设计为环境美学与景观设计的结合提供了范本。他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生态设计:整体哲学与进化伦理视野下的后现代设计范式》中认为“现代环境设计向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者设计(或生态设计)转变实则是现代还原主义路径向后现代整体主义设计路径的转变。”[8]科欧指出景观设计的现代范式立足于实证主义和决定论,将环境视为可被客观描述和科学评估的实体,而忽视对个人、社会、文化等因素的考虑,在设计中从人类视角出发,必然会导致人与环境的二元分离。为了弥补景观设计现代范式的不足,贾科苏·科欧提倡后现代的“生态设计”(ecological design),这种生态设计以整体范式(holistic paradigm)将人类与环境纳入相互影响的统一系统之中,从景观整体生态演进的角度出发进行规划与设计,更好地发挥景观设计的生态功能。贾科苏·科欧在论文中倡导的富有生态色彩的景观设计理念体现了环境美学与景观设计的交融,使环境美学在万物归元的融合统一中真正走向了对自然万物的具体实践。
此外,西方环境美学在强调各种类型自然景观的整体性和平等性之时也尊重其独特性,在人与自然走向融合之时保有万物,走向万物。以卡尔松为代表的科学认知主义所提倡的“如其本然地欣赏自然”便包含尊重自然环境独特性和真实性的内涵。伯林特也在其论著中反对景观评价的标准化,认为“景观是独特的,对它的研究就如同对艺术对象的研究一样,需要个性的思考”[6]18。在具体实践领域也同样如此,西方景观设计在实现后现代转向后不仅注重景观的生态性,还尊重景观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景观美学的倡导者布拉萨认为景观设计中的现代主义带有功能主义的色彩,呈现出一种以功能和理性至上的机械性,而这种功能主义随着景观设计蔓延至各个地方与各个时期,缺乏对景观所处地区的地理及人文因素的考虑。针对这一问题,布拉萨主张“批判的区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这一原则“了解普遍采用的技术,但是却并不会不考虑当地的条件而武断地使用它们”[9],承认在景观设计中当地文化、社会风俗、政治事务、建筑技术、气候和地形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充分尊重不同景观的独特个性。这实则也是景观设计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转向的一个表现,与贾科苏·科欧在生态景观设计中所提倡的后现代转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从环境美学与实践的结合可以看出,虽然人与自然走向了融合统一,重新归于母体,但人的主体性与实践性并未就此消解,相反,一个谦逊友好、积极实践的人类主体在生态构建中、在对不同景观独特性的尊重中走向了重生,也从平等整合的元中走向了万物。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人类主体性的觉醒,人类从最初的蒙昧统一中成长,实现了自我认知和区分,最终走向了与母体的分离与对立。但在理性不断发展之时,人类也逐渐陷入了灵与肉的双重迷失,产生了重新回归母体的渴望。受此影响,在自然审美中,人类也经历了新生、发展、膨胀、死亡、重生的复杂过程。正如塔纳斯在《西方思想史》结尾所言:“人是某种需要克服的事物——而且人是在对女性原则的接受中必定会得到实现的某种事物。”[1]486死亡和重生本就是人类主体成长的一体两面,西方环境美学见证了人类主体从元分万物的分离状态走向了万物归元的融合统一,又在实践中将人类主体推向了万物,自私狂妄的人在这一过程中被克服,理性实践的人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重生。重生后的人也会在求索精神的推动下再次踏上反思自身的征程,人类便在这种构建、反思、解构和再构建的过程中不断进步,不断实现更高层次上的超越。
——《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