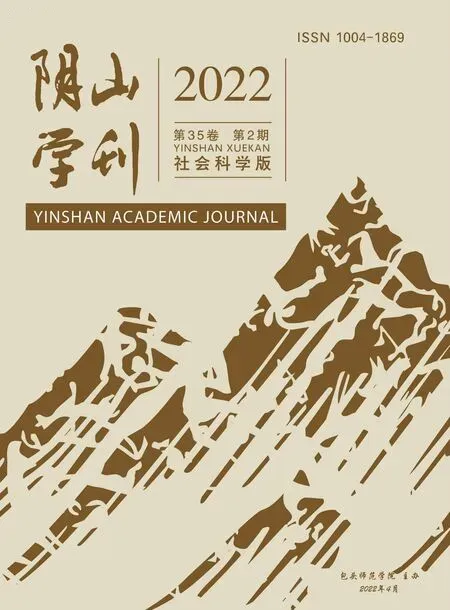元代上京竹枝词之新变*
蒙 翔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元末大诗人戴良信心十足地说:“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九灵山房集》卷十九《皇元风雅序》)有元一代,疆域辽阔,创作环境也相对自由宽松。故此,无论南北方文人,抑或各民族墨客,大多怀拥着超迈往古的自豪感。元廷认同了中原文化,汉儒也大多认同了蒙古统治者,元儒多信而好古,往往以继承汉魏传统为己任。也正因此,查洪德先生指出,元代文学在“文倡于下”的土壤上,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景观。(1)“文倡于下”的提法参见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在这多元的文化景观之中,发生在至治元年(1321年),同时拥有民歌创作、纪行写作与馆阁酬唱多种属性的上京竹枝词唱和活动值得我们关注。
竹枝词,本为巴蜀民歌,一般认为是从唐代刘禹锡开始将其演化为文人诗体,不过一般依旧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歌色彩。诗题命名,除“竹枝”“橘枝”外,还有“柳枝词”“棹歌”“欸乃歌曲”等。笔者据《全元诗》统计,题中明确有“竹枝”二字的,共214首,又根据诗人活动年代分析,其中创作于上京竹枝词之前的,只有王恽一人。由此可知,至治以前,元代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文人创作竹枝词现象。然文人创作虽少,唱竹枝却已经成为元代蔚为流行的文艺活动。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元初诗人、政治家。其棹歌当中便写道“岊江滩头苦经过,音节听来噪未和。不似吴侬音韵美,遗声全是竹枝歌。”(2)见杨镰编《全元诗》第5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17页。本文所引王士熙、王恽、虞集、马祖常、袁桷、许有壬、吴当等人竹枝词均据此书,下不一一说明,以避繁冗。岊江,在今天的福建一带。此外,元初文学家戴表元《赵寿夫游杭》:“好辞松叶面,来听竹枝歌”[1]579一句,亦可为证。关于竹枝一体起源的争议,历来多围绕着巴蜀与湘楚,于是给它打下了地方性诗体的烙印。以诗观史,可知元代竹枝吟唱活动不再囿于某地,已成为全国性活动,是以为上京竹枝词唱和提供了发生环境的可能性。
对上京竹枝词唱和的详细记录,可见于诗人袁桷诗集自序。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浙东四明鄞县(今宁波鄞州区)人。其《次韵继学途中竹枝词》收于《开平第三集》中,集前小序称:“至治元年……四月甲子扈跸开平。与东平王继学待制、陈景仁都事同行,不任鞍马,八日始达。”[2]836以“次韵王继学”与“扈跸上京”为切入点,便不难得到参与唱和的人员名单。王士熙(1265—1343),字继学,东平人,是这场活动的中心人物,王氏现存《竹枝词十首》《上京柳枝词七首》;袁桷除《次韵继学途中竹枝词》十首外,另作有《次韵继学竹枝宛转词》四首;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号石田,雍古人,属色目一支,占籍河南光州,作有《和王左司竹枝词十首》《和王左司柳枝词十首》;许有壬(1286—1364),字可用,彰德汤阴(今属河南汤阴)人,作有《竹枝十首和继学韵》《柳枝十首》《和继学壁间韵》;此外,柳贯等也作有诗歌相和。据《全元诗》统计,共计73首之多,可说是诗家、诗作众多。
总地来说,单是这一场唱和中所作竹枝词,便已超过元代至治以前文人所作竹枝词之数量,唱和之盛况,可以想见。此后,上京竹枝词的创作蔚然而兴,较之以往历代的竹枝词创作,产生了诸多新变,我们可加以归纳阐释。
一、诗境的新变
元廷实行“两都制”,每年夏天,帝王都要到上京避暑、理政。上京,又称上都、滦京,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上都音郭勒镇东北处。辽宋金政权长期对峙,“上京”对于中原及南方文人来讲,是完全陌生的,上京竹枝词的审美对象是新鲜的。诗人们无法从过往的诗歌中得到经验。且元朝疆域辽阔,前朝往代所作“边塞诗”的“边塞”,在元代已成了上都京城。如此一来,诗人在意象选取方面做了何种尝试便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试与元代早期竹枝词做比较,早期的元代竹枝词写作中,“河流”“舟”等是频繁出现的意象,譬如王恽十二首棹歌的《余自闽中北还,舟行过常秀间,卧听棹歌,殊有惬余心者,每一句发端以声和之者三,扣其辞语敷浅而鄙俚,曾不若和声之欢亮也。因变而作十二阕,且道其传送艰苦之状,亦刘连州竹枝之意云》,题目很长,类于诗序,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棹歌可以竹枝词视之,这种民歌流行于川泽一带,自然意象上离不开水。反观上京竹枝词,且不论诸如袁桷只字未写水,纵是那些描写渡河的诗人笔下也毫无“水意”。试举例如下:
居庸山前涧水多,白榆林下石坡陀。后来才度枪竿岭,前车昨日到滦河。(王士熙《竹枝词十首》其一)
宫装騕袅锦障泥,百两毡车一字齐。夜宿岩前觅泉水,林中还有子规啼。(王士熙《竹枝词十首》其二)
居庸泉石胜概多,桑干北去渐沙陀。龙门钩带水百折,一日驱车几渡河。(许有壬《竹枝十首和继学韵》其一)
同是舟车劳顿,王恽“雨雨风风一叶舟”“岊江滩头苦经过”“梦惊蓬底卧秋江”“不容停待晚潮生”,多少疲惫皆与风雨纠缠,满纸雨打芭蕉之意。反看王、许两人,或有音韵与主题限制的原因,写诗如写笔记,山山水水都好比形胜图铺得满纸。开新之处在于山水以外“騕袅”“毡车”等意象的游牧民族气息。而诗名更盛的袁桷,其《次韵继学途中竹枝词》里如“毡房锦幄花簇匀,酥凝垒饼生玉尘”则更为典型。
与前代比较,需注意不同元代诗人笔下一些相同意象的书写。“沙陀”“芍药”等都出现在了王士熙、袁桷、马祖常的竹枝词当中。可以猜测,这些相同意象背后是旅途的共同见闻与共同情绪表达,具有纪实性。同样“陌生化”的是,植物意象的隐喻象征的属性消失了,它们不再承担着“香草美人”的内涵。如芍药,常出现在文人骚客笔端。唐人韩愈《芍药》:“浩态狂香昔未逢,红灯烁烁绿盘龙。”他笔下的花卉是审美的对象。五代后蜀诗人张泌《芍药》:“零落若教随暮雨,又应愁杀别离人。”这是托物以言志抒情。我们再来看元人袁桷《次韵继学途中竹枝词》其六:“山后天寒不识花,家家高晒芍药芽。南客初来未谙俗,下马入门犹索茶。”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词》其七:“红蓝染裙似榴花,盘疏饤饾芍药芽。太官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他们笔下的“芍药”,凸显的是食用或者药用价值。早前有学者总结过,宋代竹枝词在唐代吟咏风物、讴歌爱情的基础上,强化了吟咏风物的部分,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与说理性。(3)参见莫秀英《从唐代到清代文人竹枝词题材内容的发展演变》,《中山大学学报丛刊》2002年第2期。现在看来,元代的上京竹枝词中又增加了纪实性、说明性,这是元代竹枝词有别唐宋的独特性。
相应地,意象的扩大伴随着题材的扩大,汉族乃至色目族诗人以自己的视角去记叙边疆风俗。以往中原是政治的核心,殆及元代,华夷一体,昔日金戈铁马的边塞变成了元上都的京城。便如“太宫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词》其七);“宛人自卖葡萄酒,夏客能烹枸杞茶”(许有壬《竹枝十首和继学韵》其七)两诗同韵,分别客观地描写了不同的风俗,单从诗文表述看已没有夏夷民族间的高低分别。按照著名学者吴文藻先生的观点:“边疆”有两个含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4)参见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年第1期。在元代,汉人处于政治上的边疆,与元政权的疏离感较强;但汉文化底蕴丰厚,辐射力强,仍然是元代文化的主体,蒙古等少数民族处于文化上的边疆。这样说来,汉人首次地以“边疆”看“边疆”,不再怀揣着夷夏之防,而是客观、平等甚至带有逢迎心态来书写少数民族风俗,这在元代以前的诗歌创作中未曾出现。
鉴于此,选择竹枝一体进行唱和则更值得我们注意。如杨维桢《西湖竹枝词》序所说:“竹枝本夜郎之音,依声制辞,实起刘朗州。”夜郎位于西南边陲,暂且放下竹枝词的真正起源不论,杨维桢的观点应该是元人的普遍观点。又如《元诗纪事》中记载杨维桢《西湖竹枝集》选录王士熙竹枝词,并评价:“继学竹枝本滦阳所作,山川风景虽与南国异,而竹枝之声则无不同。”[3]245王士熙等人、滦阳风景、竹枝体三者都是一定意义上的“边缘少数派”,因此奇妙地形成了“边缘”诗人以“边缘”诗体写“边缘”地区。台湾学者王明珂曾指出,民族之间有着彼此差异的观看角度,“每种观看角度,都反映观看者自身的社会文化认同、认知体系及其时代情境;每一种观看角度所造成的印象与记忆,被书写、描绘及流传,造成不同的‘边疆’。”[4]上京竹枝词的创作是特殊的,其中诗人们的观看角度、由此形成的新的“边疆”书写为元代独有,而由边缘进而能更好地体会“中心”,窥探元诗乃至元代文学整体风貌,这也是上京竹枝词的价值所在。
黄仁生认为,由于杨维桢的努力,竹枝词得以从民歌体发展为风土诗。(5)参见黄仁生《杨维祯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231页。该书“杨维桢”作“杨维祯”。诚然,杨维桢为有元一代文坛巨擘,其倡导、创作的西湖竹枝词也是竹枝词发展史上的高峰,但我们仍旧不能忽视上京竹枝词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铺垫、推动作用。上京竹枝词不论是传统意象的笔记式描述,还是异域意象的选择,都可以看到其在吟咏风物上审美性的降低与说明文般纪实性的增加。至于上京竹枝词的边缘书写,则更是文学史上崭新的一幕。
二、文学接受主体的新变
唐人刘禹锡在写就《竹枝词》九篇时称:“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5]852刘禹锡认为当地的迎神词是鄙俚粗陋的,是以作竹枝,他的主要目的在于变风,是文人士大夫对“未开化”人群的文艺教育。文学研究者常常将关注点放在诗人对民风民俗的搜集上,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竹枝词也是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互动的手段。这种互动,表明了早期的竹枝词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层差距。
以往的文人竹枝词,接受主体主要是普通民众。上京竹枝词有所不同,它创作于扈从上京途中。所谓“铺扬咏歌,词林之职也”[4]1199,诗人们是敏锐而又自觉的。试举诗人们临别之时最后的几首竹枝词创作:
龙冈积翠护新宫,滦水秋波太液风。要使竹枝传上国,正是皇家四海同。(王士熙《竹枝词十首》其十)
流杯池边是镐宫,金舆翠幰逗微风。妫川玉液清如水,湛露承恩乐大同。(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词》其十)
大安阁是广寒宫,尺五青天八面风。阁中敢进竹枝曲,万岁千秋文轨同。(许有壬《竹枝十首和继学韵》其十)
阊阖云低接紫宫,水精凉殿起薰风。侍臣一曲无怀操,能使八方歌会同。(袁桷《次韵继学途中竹枝词》其十)
这些歌词满纸“宫”“国”“臣”,已和台阁诗没太大差别,必然不是供给普通民众演唱的。上京作为统治者的文化命脉,具有无可比拟的政治地位,扈从上京也是馆阁文人的重要职责,如马祖常便往往“奏事幄殿,敕近侍给笔札,命公榻前赋诗”(苏天爵《马文贞公墓志铭》),歌咏升平盛世,也是历代馆阁文学的题中之意。无疑,竹枝词写作的理想读者已经发生了变化。读者已变,诗人们在选择词语上也要颇费苦心。上京的所谓宫殿,可能是草原帐篷,但诗人们却以“广寒宫”“阊阖”“紫宫”描绘,把上京宫殿说成天宫,当有迎逢蒙古贵族之意。
前文已述,上京竹枝词减少了文学的隐喻色彩,从接受主体考虑,一方面是为不精汉学的蒙古贵族服务的要求限制,另一方面也如美国学者斯定文所概括的,元明以来竹枝词愈加注重风俗,到了清代更是往往附以长之又长的民俗注释,虽然失去了文学色彩,但保存史料资讯的作用却与民族志相近。(6)参见(美)斯定文《从民族志视角看竹枝词》,《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元以前的少数民族人物、风俗在汉族人的诗歌当中常以“胡虏”视之,这些诗歌的接受主体主要是汉人,创作者自然也不会从少数民族读者的维度考量。而上京的诗文创作主体是汉人及部分少数民族文人,这些文学作品与以往不同,会留存当地,譬如邱江宁教授所言,“蒙古人在凭借弓矢扫荡世界的时候,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而汉文人随巡幸的队伍来到蒙古人的地盘后,却在他们的宫宇墙壁上处处留迹。”[6]综合竹枝词的民族志特性与上京诗文留存当地的特殊性,上京竹枝词可以看成是汉族文人进行的少数民族“民族志”书写,并且还供少数民族聚落的当地人阅读。鉴于此,诗中出现的传统汉文化意象可说是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为实现民族融合所做出的努力。
未参加此次上京竹枝词创作,但与王、袁诸人私交甚笃的虞集也在这方面做出过尝试。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虞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生。(7)参见刘嘉伟《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页。试举虞集《次韵表兄陈溪山先生棕履》其三:“缚人夜送军,吏卒何草草。蛮獠亦人类,义利启戎好。”[7]19值得玩味的是,虞集用了“人类”这样的字眼替代以往的“炎黄子孙”,这与王、袁诸人所言“四海”“大同”有异曲同工之处。王明珂有一个观点,忘记一些祖先或特别记得一些祖先,这一种“结构性失忆”,经常用以重新整合族群范围[8]45。创作者们使用传统的春秋笔法,拉近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未必不是一种守正出新。汉儒以为,在政治军事上虽然不敌北方少数民族,但可以用文化的力量“以夏变夷”,进而也可以接受少数民族政权。许有壬竹枝诗中出现的“文轨同”,在元代是一个普遍、广泛的话题,戴良为诗人丁鹤年所作《鹤年吟稿序》就称:“(元代蒙古、色目士人)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九灵山房集》卷十三)可见,用夏变夷的策略是有效果的,王道教化能够传之广远也是汉族士大夫乐于看到的。
肇始于上京竹枝词的创作,竹枝词的理想读者便有了上层统治者这一个选项。邱江宁在《元代上京纪行诗论》中以大篇幅论述虞集于政治上的不得志进而表露在其纪行诗歌创作当中,事实上,虞集的竹枝词创作也体现了他的不平。如以下二首:
江水江花无尽期,安得同舟及此时?燕山春燕更北去,南人休唱鹧鸪词。(虞集《次韵竹枝歌,答袁伯长四首,并序》其一)
忆奉君欢伎未成,不承恩泽尽留情。疑思却恐伤明德,不敢人前哭失声。(虞集《竹枝歌,奉陪诸公送旧而归,暮闻短歌江上,其竹枝之遗响乎?因成四章》其三)[7]203
前一首写友人相隔南北的离情别绪,这样的感怀本不足为奇,但这是给袁桷的唱和诗,则大为不同。袁桷扈从上京五次,如前文所说铺扬咏歌于词林之间,反观虞集,同僚记载仁宗皇帝曾叹“今儒者尽用,惟虞伯生未显擢耳”(欧阳玄《虞雍公神道碑》)。末句“南人休唱鹧鸪词”,与袁桷上京竹枝词当中“我郎南来得小妇,芦笛声声吹鹧鸪”(《次韵继学途中竹枝词》其四)一句相对比,便不难推测虞集借怀友发不遇之愁思。至于后一首,诗人借艺伎自况的传统古已有之,虞集不遇之情更是跃于纸上,但“却恐伤明德”,诗人不敢表露伤感,惶恐的地方正是理想读者中存在君王,虽言“不敢人前哭失声”,却还是写诗吐露之,正如诸葛孔明“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之意罢了。
要言之,自上京竹枝词起,竹枝的文学接受主体便从下层民众转到了上层贵族,亦是一变。
三、创作目的的新变
孙杰博士认为,以竹枝词为题,大规模唱和,“在唐宋以来是未尝有过的,是元代竹枝词成为竹枝词发展史上第一座高峰的标志”[9]。孙杰是从整个竹枝词的发展史来论说的,具体到整个元代甚至元代中期诗坛生态,这次同题唱和活动又有歌咏盛世的创作目的,值得寻绎。
上京竹枝词唱和的主导者是翰苑名臣王士熙,清代四库馆臣谓其“在馆阁日与虞集、袁桷等唱和,论者比之唐岑、贾,宋杨、刘,为有元盛世之音”[10]1546。这并不是针对王士熙个人的评价,而是对他、虞集、袁桷等人的馆阁酬唱持肯定态度,称为有元盛世之音。“盛世之音”这个命题在元代文坛大佬虞集的诗文当中并不陌生,查洪德教授在论文中援引了虞阁老“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的观点,并更深入地解释:“盛世诗文,就是与此世运国运相副之盛大之文。”[11]鉴于此,我们可以说上京竹枝词唱和是元代中期馆阁文臣在创造元代盛世诗文过程中一个具体的文学实践。
事实上,这一批诗人都拥有相通的文学思想。虞集曾感慨:“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大抵雅乐之不作,声音之学不传也,久矣。”(《中原音韵序》)除了有对《诗经》风雅传统的呼吁外,虞集隐隐批评了宋末以来的诗学文风,这也与其超迈往古的大国自豪感有着一定联系。王士熙也有着同样的感慨,他在一次儒家文化活动中感叹道:“《韶》之不作,久矣!”(《曲堤镇修建大成庙碑记》)韶,虞舜乐也,王士熙同样推崇先秦诗乐传统。“宗唐得古”是元代诗学思潮,虞、王等人便是试图回归盛唐,以风雅来倡导与国运相匹配的盛世诗文。
那么如何将竹枝这一楚地民歌与风雅联系起来便成了新的问题。元末傅若金的诗论或可供参考,其《诗法正论》云:“见有浅如诚斋之作者,则指之曰‘此俗学者诗也’。嗟,是徒岂足知诗哉?”又云:“诚斋之诗,如竹枝欸乃之作,不害其为国风之余也。”可以看到,傅氏一方面指出清浅直白的诗并非俗学者诗,另一方面将竹枝视为“国风之余”,是以为竹枝一体“正名”。此外,杨维桢《铁崖乐府注》自称:“《海乡竹枝》,非敢以继风人之鼓吹,于以达亭民之疾苦也,观民风者或有取焉。”观民风,是《诗经》采诗的传统,结合本文之前论述,竹枝词从民歌体转向风土诗于上京竹枝词时期便已开始,我们可以断言,竹枝一体于元代中后期已作为“国风之余”,成为诗人恢复《诗经》传统、呼吁盛世之音的手段之一。诗歌发展的过程中,上京竹枝词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竹枝”这一诗歌形式的发展,进而产生了杨维桢主导的、令人瞩目的“西湖竹枝词”唱和。
同样是少数民族政权,清代走向了几乎完全“汉化”,而元代蒙古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放弃本有文化,元代的文学文化活动常常是“文倡于下”。由于统治者的重视,馆阁文坛核心人物的存在,倡导“盛世之音”的上京竹枝词创作繁盛于元中期,其最后回响,在顺帝至正十三年(1354年),吴澄之孙吴当上京期间连同同僚写下《王继学赋柳枝词十首,书于省壁。至正十有三年,扈跸滦阳,左司诸公同追次其韵》,试以摘录一首:“貂帽驼裘休叹侬,从官车骑莫从容。柳花飞尽雪花起,才见西风又是冬。”此时,已是元末,不复当年“天下大同”之气势。
综上所述,元代上京竹枝词有着民歌、台阁诗、上京纪行诗等多种属性,它既深刻地反映了元代政治与民族生态的复杂性,又是元代中期文人诗歌创作的一次创新性实践。而上京竹枝词于此期间产生的诸多新变,与元代特殊的政治、地域、风俗、民族环境相关联。概而言之,即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的诗人创作反映边疆民情的诗篇,形成了一道奇异的文化景观。这些都是之前的竹枝创作乃至之后的繁盛一时的“西湖竹枝词”所没有的,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上京竹枝词的产生与新变,是元代特殊历史文化时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对其加以研究,自然有助于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书写,也希望能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实施提供历史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