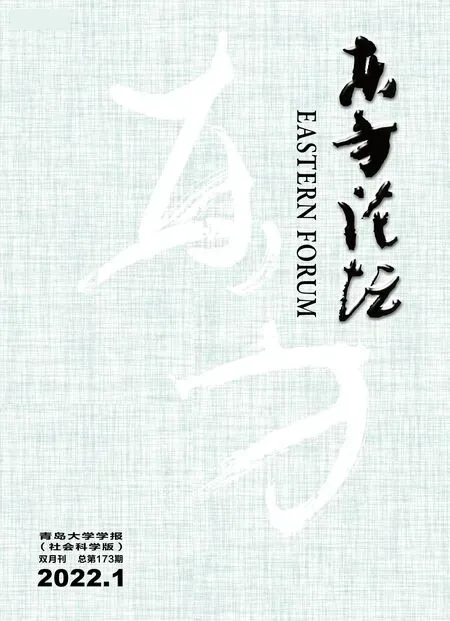利维坦:现代法治联合体的隐喻
汪 栋
山东农业大学 泰山法治研究院,山东 泰安 271018
一、引 言
德国学者施米特断言,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确立了现代法治学说。但是,霍布斯在形式主义法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利维坦的机械与形式要素最终压倒了其实质要素,结果使得现代法治联合体成为失去灵魂与价值的机械空壳,形式主义的“价值中立”会导致价值虚无;施米特悲观地预言“法治利维坦”的前景不妙,认为现代法治国最终将毁于其自身致命的形式主义。①利维坦的实质与形式在霍布斯那儿是统一的,对霍布斯而言,机械装置、有机体和艺术作品,所有这一切都还是机器——作为人类最高创造力的产物——的组成部分。因此,机械装置或机器对他和他那个时代来说,还完全具有神话含义,也就是具有实质意义。然而,后来到了19和20世纪,机械装置或机器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机械装置”既与“有机体”,又与“艺术作品”分离开来,结果导致了活的存在和死的物质之间的对立,这就剥去了“机械装置”的一切形而上学的、生机勃勃的特征,也即剥去了“机械装置”象征的国家的实质要素,而只剩下空洞的形式意义。Carl Schmitt, The Leviathan in the State Theory of Thomas Hobbes, Meaning and Failure of a Political Symbol,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41.这种评论的言过其实之处暂时不论,就霍布斯对形式法治的贡献而言,施米特的批评毋宁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赞誉。现代法律的形式主义特质集中体现在法律程序规范体系。法律程序作为一种与传统“压制型法”相对应的“协作型法”,是现代社会分工合作关系的规范性表征。①[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93页。社会分工愈发展,社会差异性愈大,在这种不断递增的差异性中产生了对个性与权利价值的尊崇,产生了对维护日益扩展的交易合作秩序的法律程序的需要。就法的价值而言,法律程序是“权利法”;就法的功能而言,法律程序是涂尔干社会学意义的“协作型法”。②[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361、365页。以权利价值为核心的宪法共识需要法律程序机制加以建构与维系。近代以来,法律程序对于打破血缘与地域封建壁垒,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建立和维持广泛的经济社会协作具有重要意义。③[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潘华仿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昂格尔将现代法治归纳为“形式法治”(rule of formal law),认为以法律程序为代表的法律形式是现代法治历史上包容一切压倒一切的问题。④[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9页。美国学者科尔曼认为,霍布斯是现代宪法哲学(constitutional philosophy)的思想先驱,其自然权利概念是“政治程序”(political process)的源头,是程序法治实践的政治哲学基础。⑤Frank M. Coleman, Hobbes and America:Exploring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7, p.3.科尔曼的研究受益奥克肖特的法治理论甚多。奥克肖特对霍布斯的国家理论精辟地评价说:“它(利维坦)是一种否定性的礼物,仅仅使被追寻的东西成为可能。”⑥[英]迈克尔·奥克肖特:《〈利维坦〉导读》,载渠敬东主编:《现代政治与自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0页。“法治利维坦”不能驱使其成员追逐特定的具体目标,而只能协调处理他们的权利交易冲突。奥克肖特用“法治联合”这个概念总结霍布斯自然权利论的精义,⑦[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81—182页。阐释其中的有限政府与程序法治原理:“政府的职能是解决多种多样的信仰和活动产生的某些冲突;维护和平,不是通过禁止从偏爱中产生的选择和多样性,不是通过强加实质的统一,而是通过一视同仁地将程序的一般规则实施于所有国民。”⑧[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第145页。
涂尔干从实证角度描述社会分工的历史发展,揭示了权利价值与程序法治之间的经验和事实联系,尽管其未从思想史角度分析程序法治的内在逻辑与政治哲学基础。科尔曼则试图从逻辑上探索自然权利与法律程序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有限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以程序协调权利之间的竞争,而不是负责分配权利。科尔曼将思想史与美国政治实践相结合来证明其观点,其关于宪法程序或者程序法治的论述虽然重要,却受制于思想史的写作框架,未就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论进行更深入的论证。本文认为,古典宪制以政治理想主义为思想基础,着眼于人的德性完善来对待道德和政治事务;⑨[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8—129页。利维坦隐喻的现代法治联合体则立足于政治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也即从自然权利出发,⑩霍布斯认为古典政治哲学是“空中楼阁”,霍布斯的志向,是将政治学建立在虽然“低俗”然而“坚实”的基础之上(low and solid)。他和马基雅弗利的“现实主义”的新政治科学是把政治生活的标准自觉地降低,不是把人类完善的目标,而是将大多数人和多数社会在大多数时间里所实际追求的目标作为政治生活的目标。按照人的较低的却更有实际效力的目标制定的政治规划比古典学说中的乌托邦更有实现的可能。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1—452页。旨在满足权利协调与保障的需要,不负责人性的完善与救赎。“法治利维坦”的功能是通过法律程序协调权利价值之间的竞争与冲突。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论是以程序法治为特质的现代法治联合体的思想源头。
二、作为现代法治价值渊源的自然权利
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概念源于其机械唯物论哲学。据此哲学观,物质世界只有运动和力的相互作用,物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力量关系,或者,可以还原为这种关系,万物之间不存在自然的高低等级秩序。古典宇宙论的自然等级秩序观实质上依赖于这样的信念:低级事物不能产生高级事物——无机物质不会产生生命和欲望,经验不会产生理性。据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与宇宙的自然等级秩序相一致,人类社会同样存在着自然等级秩序。而霍布斯的观点则可称之为“本体还原论”(ontological reductionism):理性被还原为复杂的经验,价值追求被还原为欲望,经验与欲望又被还原为纷繁的外在事物刺激人体所引起的运动。①John Watkins, Hobbes's System of Ideas,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73, p.26.人根本上作为物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力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关系没有自然的高低序列。人与人之间只存在量的差别,这种量的差别不足以将一个人置于他人之上。因为就人而言,根据自然权利论,均是由相同的材料制造而成,并按相同的方式运动。
霍布斯新政治科学的要旨是以自然权利概念否定传统自然法观念。自然中没有如此这般的等级和阶梯,没有真正完美的秩序——一个比另一个更高贵,正如有生命和感觉的物体比没有生命的物体高贵,理性与推理比感觉高贵。所谓“高级”的理性沉思与价值计算均可化约为外在事物刺激人体感官所引起的心理与生理运动,也就是还原为自然欲望或自然权利。
霍布斯还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是体力、经验、理性和激情四个要素的复合存在,平等源于每个人的体力、经验、理性和激情方面的差异微乎其微,这些微小的差异不足以形成人的自然尊卑等级。首先,体力平等意味着人体力上的差别微弱因而不具有实质意义。其次,人在经验方面的智力大致上也是平等的。例如,慎虑这种经验,如果人们有着相同的生活阅历,他们所积累的经验也就基本相同。霍布斯写道:“人人都满足于自己的智力,却恰好证明了人的智力的平等。”②[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92—93页。再次,理性或推理实质上是名词的计算。理性作为人本质的属性,不过是一种认识或推理能力,也即观念的排序的能力。理性与“人”这两个词“范围相等,互相包容”。③[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20页。只要是人,就都具备理性,人的理性能力之间虽然有差异,却并无高低之分。
理性和激情构成人的存在,两者都可还原为感觉,感觉又可归结为外物与人的物质感官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运动,而各种运动之间无法比较高低。这样,霍布斯从实证角度回到根本的机械论宇宙观,完成了人生而平等的证明:自然权利作为根本的物质运动只有量的差别而无质的高下。
由上可见,霍布斯比洛克更有资格被称为现代立宪主义之父。洛克“从未走出《利维坦》的影子”,④[英]彼得·拉斯莱特:《洛克〈政府论〉导论》,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94页。比之于洛克,霍布斯对自然权利概念的宪制精义——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作出了最为透彻的阐释:“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①[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97页。
人不仅生而自由,生而平等,而且这种平等的自由也即自然权利,具有相对于义务的绝对性,在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或盟约(covenants)脱离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社会后,进而成为主权者不可加以剥夺的宪法权利。
人们通过契约向主权者转让自然权利的目的在于保障其自然权利。这表明臣民的义务是有条件的:其他参与人履行政治盟约的程度,以及主权者为臣民所提供的履行义务的安全程度。这就为臣民保留了不服从主权者的权利。契约加之于臣民的所有义务均以自我保存为前提。例如,臣民被主权者讯问其罪行时,如果没有获得宽恕的保证,他就没有义务要承认。臣民拒绝服兵役而不为不义。②[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169—170页。
权利转让给主权者只限于契约的方式。政治盟约不同于普通的商业契约,它要求转让权利而非交付实物。人们将权利转让给主权者,不像转让商品、财产或金钱那样永久丧失了这些事物。臣民不可能对主权者放弃或转让他们的意志本身,而只能对主权者承诺维持某种意志状态;臣民有义务维持的意志状态是履行契约的意志。③John Watkins, Hobbes's System of Ideas,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73, p.116.霍布斯以“契约”作为转让权利的形式,旨在保留臣民对主权者能否保证其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判断权。
对霍布斯所描述的臣民而言,社会契约提供保护的理想图景是,每个参与约定的人都承担义务,除了他自己之外,自我利益驱动的个人总是企图规避契约义务。臣民永远在计算履行盟约的成本和收益,社会契约恰是建立在这种自我保存与自我实现的利益考量之上。
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命权,也包括财产权。霍布斯对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界定,包括了所有为实现人的生存和生活美好而不可或缺的权利。“放弃权利、转让权利的动机与目的,无非是保障一个人使他的生命得到安全;并且保障他拥有既能保全生命,而又不对生命感觉厌倦的手段。所以,有些权利不论凭什么言词或其他表示都不能认为人家已经捐弃或转让”。④[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100页。霍布斯列举的促使人们立约进入公民社会的激情之中,除了对死亡的恐惧之外,还包括对安全、舒适、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希望。追求人民的安全是主权者的职责和利维坦的目的,这里的“安全”一词是宽泛的所指,不仅包括人身与生命的有保障,而且包括对国家、社会与他人不构成威胁与危险的所有的生活上的满足。⑤[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260页。显然,霍布斯既为生命权,也为财产权的不可剥夺性而辩护。
霍布斯根据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关怀,对财产价值的轻重进行排序。他说:“在保有所有权的一切事物中,人们最为珍视的是自己的生命和肢体,在大多数人身上其次就是有关夫妇之爱的一切,再其次就是财产和生活手段。”⑥[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266页。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固然深刻,但是,受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商业热情的影响,他过多注目于人们通过劳动和贸易所获的金钱和土地等有形财产,或多或少冲淡了财产权的政治哲学意蕴。霍布斯则立足于生命价值和宪制意义去阐释包括财产权在内的自然权利,哲学视野更为开阔。
自然权利是迥异于传统自然法的霍布斯式自然法的出发点与终极旨归。①传统自然法是高于实在法的超验规则,而霍布斯定义的自然法既不是一种超验规则,也并非高于实在法,而是与实在法并列平行的规则。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208页。霍布斯在《利维坦》第十四章、第十五章集中论述了十八条自然法,在最后的“综述与结论”部分又加上一条自然法,共计十九条自然法。②[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98页、第108—120页、第569页。这些自然法规则是从自然权利概念推导的结论,其中六条自然法是程序规则。第十一条自然法:秉公处理争端。第十三条至第十七条自然法分别是:凡斡旋和平的人都应当给予安全通行的保证;争议各方应将其权利交付公断人裁断;禁止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者应该回避;禁止偏听偏信。第一、二、三、五、九、十、十二条等七条自然法间接与程序规则相关。这十九条自然法可概称“和平规则”或“权利规则”。霍布斯根据自然权利概念提出的第一条自然法是:应该寻求与信守和平,以实现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其他自然法均是以第一条自然法为逻辑起点的推演,而十九条自然法中有十三条在直接或间接意义上是程序规则。由此可见,将这些自然法加以宪制化、实在化的“法治利维坦”是自然权利与程序规则的统一体,这一政治体的目的在于通过程序规则以实现与保障自然权利。
三、政治的目的:德性抑或权利
“权利”保障与有限政府是立宪政体的一体两面,是立宪政体区别于古代“德性”政制及其现代变体“事业”型国家的本质特征。立宪政体或“法治联合”型国家对于政府只作最低限度的要求:保障人们的人身与生命安全以及和平的交易秩序;即便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福利国家”以“积极行政”干预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却从未逾越有限政府原则的底线。立宪政府的职责只在于为公民的权利冲突设置一个协调应对程序,而不像古典“最佳政体”那样旨在全面关照人的生活,促进人的德性或内在生活的完美,也不像“事业联合”型国家那样意在建设某种具体事业。
政治生活以人的完善或德性为目的是古典政体论的核心观点。由于着眼于人性的完善来对待道德和政治事务,因此与霍布斯的平等观相反,古典政治哲学否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平等;③[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128—129页。政治的功能指向实现人的德性完善这样的目标,为实现此目标,首先,人就必须生活在一个最好的社会,其次,这个最好的社会还必须是由最有智慧的人进行统治。
据古典政体论,最好的社会就是最好的政治(politeia)。最好的社会只能是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政府的职能不限于对政治事务的管理,还要为公民的德性和幸福负责,指导人们向至善的生活努力。美国学者施特劳斯认为,Politeia通常被译为“宪法(constitution)”,“宪法”一词在现代政治语境中指的是一种法律现象,某种类似于一个国家的基本法的东西。然而,Politeia并非法律现象,它比法律更为根本,是一切法律的源泉。比起宪法是要管制政治权力而言,该词是指对共同体内部权力的事实上的分配。①[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37—138页。
Politeia(政治)与constitution(宪法)的区别对应于最佳政体与合法政府的区别。前者意指“完美的生活方式”或“完美的城邦”,它囊括人的生活的全部内容,这与古人对政治的高度期待相一致。宪法是一个现代概念,而且首先是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概念与政府相联系,并预设了有限政府的原则。现代宪法概念否认政治生活是人的本质的、内在的要求,因而政治虽有必要,却并不是人生活的全部追求,更不是人生活的终极追求。
古典派规划的政治是最佳政体或最佳城邦。其要义是,生活于城邦中的人是不平等的,物的自然构成有着高低之分,人的自然秉赋良莠不齐。因而,最佳政体必定是智慧者的统治,就像人的灵魂统治肉体一样,城邦中的高级部分(智慧者)统治低级部分(普通人)。最佳城邦是合于自然的终极的人类团体。
合法有限政府构成现代宪法概念的基本内涵。根据宪法组织的政府根本上才是合法的。宪法确认并保障人人平等的自然权利,每个具有足以自治的理性的成年人都是自我保存的最终判断者。霍布斯敏锐地指出:“一个普通农民对于自己的家务比一个枢密大臣对旁人的家务更能深谋远虑。”②[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53页。亚里士多德断言,人类从天性上说,有些人更宜于“治人”,有些人则以“役于人”为相宜。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3页。霍布斯批驳道:“这种说法不但违反理性,而且也违反经验;因为世间很少人会愚蠢到不愿意自己管自己的事而宁愿受治于人的。”④[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117页。因而现代宪制不是一种智慧的统治,而是同意的政治,人们同意的政府即是合法的政府;合法政府也是有限政府,政府只是维持秩序与协调冲突,而不负责人的德性完善和灵魂救赎。
古典最佳政体追求自然至善的道德秩序,而现代国家以保障人的自然权利为最高目的。施特劳斯对古今政治哲学之争总结道:“政治的难题就在于要调和对于智慧的要求和对于同意的要求。可是,从平等主义的自然权利论的观点看,同意优先于智慧,而从古典自然权利论来看,智慧优先于同意。”⑤[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143页。古典派从人的德性完善出发来设计最佳政体,现代政治哲学则从人的最低但却是最强烈的自然欲望出发来规划合法政府。“自我保全的欲求乃是一切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国家的职能并非创造或促进一种有德性的生活,而是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⑥[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185页。
“事业联合”型国家是古典最佳政体的变异,是当代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提出的概念。奥克肖特将其定义为与“法治联合”型国家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人们加入其中寻求满足一种选择的共同需要,或促进一种共同利益。这里,有关的人认为他们自己不是在从事一个计划满足他们不同需要的交易时相关的各方,而是伙伴、同事、同志或同谋,联合起来寻求一个共同的实质满足。”⑦[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第158—159页。依托于此种关系模式的公共权威亦可称之为技术型国家。
技术型国家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导的“事业联合”型共同体。奥克肖特认为,这种类型的国家之所以是事业型或技术型的共同体,原因在于它设定了一个所有成员必须服从并努力加以实现的集体目标,政府对国家实行技术统治,组织、整合所有的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以实现事业目标。因此,“事业联合”型国家的法律也是一种特殊的规则,即技术型规则,它是对共同体成员的授权,是分配事业产品的工具,国家类似于公司,而法律则近乎公司的章程。①[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第185页。“事业联合”型国家往往以行政权力主导一切,而无视甚至压制人们的权利追求,个体价值受到忽视。个人在“事业联合”型国家中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与目标选择。
奥克肖特从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论出发提出“法治联合”的概念。与“事业联合”型国家迥然有别,奥克肖特指出,人类创造了另一种基于自然权利价值的关系模式,“在这种联系模式中,两个或更多的人只是为了寻求,也许是为了获得他们不同的当前需要的满足而联系在一起”。②[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第157页。奥克肖特称这种关系模式为“法治联合”。
奥克肖特运用“法治联合”概念阐明了自然权利与有限政府之间的必然联系。他说:“‘法治联合’是一种道德联合,公民法治联合体的法律不是为了达到共同的事业目的,而是与关心过‘像我这样的人’的生活的人多种多样、不可预见的选择和交往有关,而不是为某个功利目的做具体事的技术规则。这些人联合在一起不是为了共同的目的或约定,他们追求的目标像他们自己一样多种多样。法律是公民联系的唯一纽带,而不是促进公共利益的工具 。”③[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第29页。奥克肖特认为,在阐释“法治联合”的理论家里,霍布斯坚持法治代表一种(而不是一种精明的)道德关系;坚持它决定的不是行动,而是“行动善恶的尺度”,“利维坦这个正义和欲望的尺度是一个既不应被藐视也不应被高估的发明”。④[英]迈克尔·奥克肖特:《〈利维坦〉导读》,载渠敬东主编:《现代政治与自然》,第241页。“法治利维坦”只能是有限政府,必须尊重人们价值选择与目标追求的多样性。
四、法治联合体的功能:压制抑或协调
“法治联合”型国家的政治权威源于每个人自愿订立的契约。利维坦的权威惟有通过人们的权利或价值的互利交易来加以维持。主权者垄断了所有合法的暴力,当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威胁到法治联合体的基础和主权权威时,则必须运用强制力;但是主权者应尽量不用或只在危急时使用强制力,从而避免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激烈对抗,实现一种较为温和的政治。
人们以平等的自然权利为基础的互利交易是“法治联合”型政治的特点。交易与商谈关系,易言之,权利的和平竞争与制衡构成程序法治的实质内涵。
政治社会必须严格控制运用强力解决权利冲突。因为当主权者实际使用武力而不仅是武力威胁时,臣民就恢复了其原本完整的自然权利;如果主权者直接威胁到臣民的生命和生计,后者能够运用任何手段进行自我保存与防卫。违反自我保存目的一切行为都与自然权利相冲突,因而不以强力反抗强力的信约,以及不防卫自己身体的信约就是无效的。①[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106页。既然立宪政治在主权者与臣民的冲突之中拒斥强力高压,则只能诉诸和平的商谈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争执。
武力威胁是主权与臣民之间的政治关系中的重要成分,而实际运用武力则似乎暗示着利维坦的缺陷或失败,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以同意为基础的政治的终结;武力只有未被实际运用时它才是成功的。②Frank M. Coleman, Hobbes and America:Exploring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7, p.3.霍布斯对“征服”的定义表明,逻辑上,使用武力会导致利维坦或盟约政治的失败。“征服”与“制服”的区别在于前者基于契约,即胜利者与投降者彼此之间对各自权利与义务的约定,“征服”的实质之所以是契约,是因为它确立的是一种保护与服从关系。而“制服”不过是运用武力剥夺他人的反抗能力,并未取得失败者的甘心服从,因此,“制服”他人后的状态仍然是一种战争状态。③[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570页。
强力不能创造和维持利维坦。主权者必须借助强力之外的其他方法以维系自己与臣民的宪制关系。霍布斯写道:“这些权利的根据很需要经常确实地教示给人民,因为它们不能靠任何世俗法或刑罚之威来加以维持。”④[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261页。因此,主权者对人们“畏之以刑”的同时,必须尤其注重公民教育,使之明晓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保护与服从之道。
霍布斯拒斥强力产生权利(might makes right)的主张。他承认,在臣民对于主权者的服从当中,不免含有恐惧成分,实际上,在推动人们建立政治社会的激情当中,恐惧的激情丝毫不逊于自我保存的激情,两种激情是一体两面。但是,主权者的权威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不是来自于主权者的力量。主权者权威和主权者力量的区别,同意的政府与依靠武力的政府的区别,人们对自然状态中的死亡和苦难的无尽焦虑与对利维坦的可预见的恐惧之间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主权者权威的基础是契约或者同意,武力能够加强主权者的权威,但是不能创造他的权威。⑤Frank M. Coleman, Hobbes and America:Exploring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7, p.90.
立宪政治的主权权威以自愿互利的权利交易关系为基础。交易与商谈是指两人或更多的当事者之间通过和平对话,各方同意做或避免做一些事情,以换取彼此未来的好处。这种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商谈过程即是缔结与维持契约的政治过程。
臣民可以为自身利益而正当地对主权者施加影响。霍布斯举例论证道:“如果臣民的私人利益要在会议中加以辩论和审议,他因此而尽可能多和别人交好,这种做法并非不义,……而在没有听审并裁决以前,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的理由是正义的。”⑥[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184页。主权者同样可以为己谋利,也可运用权力服务于某些社会团体或个人。人性的利己倾向无可避免,主权者的公共人格与自然人格之间并不总是若合符节,政治设置应该寻求主权者之私利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霍布斯说:“当公私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主权者)就会先顾个人的利益,因为人们的感情的力量一般说来比理智更为强大。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公私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公共利益所得到的推进也最大。”①[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144页。
霍布斯鼓励臣民与主权者将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利冲突诉诸司法程序解决。②[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171页。法律诉讼作为重要的交易和商谈程序,其功能是协调价值竞争与权利冲突。立法程序、行政程序亦以此为旨归,宪法程序则是法治社会权利博弈关系的最高法律形式。
社会契约的实质是每个人通过限制其自然权利来保证彼此安全,契约关系是一种权利交易与商谈关系,能够发挥对话、沟通功能的程序规则是霍布斯社会契约理论的逻辑延伸。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是霍布斯理论的回响。他说:“正当性的惟一的后形而上学来源,显然是由民主的立法程序提供的。……从正当程序产生的结果,多多少少是合理的。”③[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684页。主权者由以产生的盟约源于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通过法律程序,主权者将重返与臣民的权利交易与互动过程,从中获致其权力的正当性。在主权者与臣民之间以及臣民相互之间的权利博弈之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争取特权或豁免,通过法律程序的商谈机制来促进各自的利益。就此而论,宪制程序是主权者与臣民之间权利交易关系的权威载体,是最为根本的民主商谈机制。
奥克肖特的“法治联合”概念的现实样本是美国联邦宪法,④虽然斯托纳将普通法对于美国宪法的作用置于自由主义之上,但是他也确实看到了霍布斯思想是美国宪法的哲学基础。他说:“霍布斯政治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更适合于描述我们的世界而非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或者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世界。与制宪者的时代相反,霍布斯在我们时代广为流行,这一点,不仅反映了思想界流行时尚的变化,也体现了他的洞见的力量,也许也能衡量他的影响力之范围。”确实,在美国历史上制宪者的时代,“很少有证据表明,霍布斯的著作曾为制宪者们所知晓或阅读。他的书在早期美国的图书馆中显然付之阙如,因而,毫不奇怪,最近完成的一份有关建国时代小册子文献中引用权威作者之频率的研究显示,霍布斯远在孟德斯鸠、布莱克斯通和洛克之后,甚至排在专业色彩很强的柯克之后——更不要提霍布斯究竟是被作为权威还是作为坏蛋引用”。See Stoner, James R. Jr. 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Coke, Hobb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p.134, p.72.而美国宪法的理论源头是霍布斯哲学。⑤Frank M. Coleman, Hobbes and America:Exploring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7, p.2.从自然权利论出发,“宪法之父”麦迪逊认为,人们是根据自己的教育、阅历和性格来对何者有利于自己进行判断。他观察到,人们的不同秉赋导致人们在财产拥有的数量和种类上差异极大。财产的数量差别将社会分成债权人和债务人,富人和穷人;人们拥有的财产种类的不同则会导致派系冲突,如土地、商业、金融、手工业等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⑥[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6页。
自然权利中的理性要素依附于自我保存的激情,而自我保存的激情必然导致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异和价值冲突。麦迪逊的这段话对人性洞烛幽微,却可能因人们过度熟稔而容易被忽略:“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就有财产权的产生,这种多样性对于达到利益一致来说,不亚于一种无法排除的障碍。保护这些才能,是政府的首要目的。由于保护了获取财产的不同才能,立刻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和各种各样的财产占有情况;而由于这一切对各财产所有人的感情和见解的影响,从而使社会划分成不同利益集团和党派。”①[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46页。自然权利与财富分化相互作用,利益冲突导致党争不断,利益或财富分化冲突深植于自然权利,因而不可能消除,只能对其加以规范与协调,使得财富分化向着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发展。
麦迪逊诉诸自然权利以论证主权权威的正当和限度。他认为,人们无论强弱均意识到需要公共权威来协调他们之间的冲突,②[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267页。麦迪逊宪法方案确定的法治联合体的功能仅限于此。这种有限政府设计的理论基础在于,同意优先于智慧,政府必须尊重每个人的权利追求,不能予以蔑视或以强力进行压制,而只能协调人们的权利冲突。宪法产生于人们之间的权利交易与冲突关系,人们也要依宪法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尤其是法律程序制度来协调权利交易与价值竞争关系。
五、“法治利维坦”的形式与实质
利维坦喻指的现代法治国家集四重形象于一身:巨兽、巨人、上帝与机器。就实质而言,现代国家是一个以权利价值为核心的道德共同体;恐惧与自我保存的激情是政治结合的最大动力,利维坦的巨兽、巨人与上帝形象表示恐惧、激情与意志,指涉国家的实质在于保障每个人的自然权利。③汪栋:《宪法程序考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1页。就国家或法律秩序的形式而言,利维坦的机器形象隐喻的是国家的形式要素,也就是说,从形式上看,国家是一台巨大的机械装置,是“像钟表一样用发条和齿轮运行的自动机械结构”。④[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第1页。
现代法治国家是一个权利价值与法律形式相融无间的公民联合体。形式理性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质。韦伯的法社会学理论认为,形式理性是现代法律的根本特征。韦伯说:“以严格形式化法律概念为基础的理性判决与以神圣传统为指导的判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缺乏对每一个案件判决的清晰基础。它的判案是以神秘的正义,即对神谕的具体启示,先知的判决,或神明裁判为基础。或者,它是非形式主义的库海蒂司法,根据的是具体的伦理和其他价值判断。或者,它作为经验性的司法,但却依赖类推和先例的解释。”⑤韦伯本人其实也已经意识到英国法的形式主义并非完全付之阙如,他看到,英国法律人严格依法律程序而行,在法律外行人看来,这些行为近乎刻板而不近情理,但是,任何人都必须学会适应,而且将律师看作是生活中任何不测事件的法律教父。英国的商人都是如此。他们既不要求,也不期望法律给予什么,因为“逻辑的”法律解析可能会打破一切期望。此外,还有针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另一个保障,也即“遵循先例原则”。因此,在私法领域,普通法和衡平法在被用于处理案件时,都是非常“形式主义的”,在遵循先例和法律职业的传统精神约束下,几乎使得法律执业者难以越雷池半步。然而,韦伯却又完全将英国陪审制当作是一种非理性、反形式主义的设置,这种看法是很不全面的,陪审制其实具有极高程度的形式主义,是一种理性的司法程序。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14页、第353页。虽然韦伯在此将英国经验主义司法等同于非形式主义司法的观点有待商榷,但是,他以形式主义特质为标准区分传统与现代法律的主张是成立的。
形式(form)的概念是西方哲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古代希腊哲学视万物由质料与形式二要素构成,形式将质料组织成为具体事物,形式相当于柏拉图所说的事物的“理念”或原型,或人们通常所说的原理、原则或内在逻辑结构之类。形式是事物的存在与运动方式,没有形式,则事物无从形成,也无从表现自己,而且,事物的组成、结构与运动方式之不同,决定了事物的不同性质。就此而言,形式对于事物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据施米特的归纳,韦伯的法社会学提出过三种不同的形式概念,在某种情况下,形式是指法律内容的概念规范,即法律内容的形式,用韦伯的话说就是标准规则。另外,韦伯有时也将形式等同于理性化的、经过专业训练的以及可计算的。形式概念的第三个含义是指现代法律在法理上日趋细致的理性化趋势,以及“形式化性质”的发展。①[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理性同样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概念。韦伯的法社会学理论在以下四层意义上运用理性的概念,首先是指法律程序能够使用合乎逻辑的方法以达到其特定的、可预计的目的。其次是指法律的体系化特征。理性的第三层含义是用来说明“基于抽象阐释意义的法律分析方法”。②吕世伦:《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37页。最后,理性也指“可以为人类的智力所把握”。③吕世伦:《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第337页。在韦伯看来,现代化的进程可以用“理性化”或“袪魅”概括之,而“袪魅”则指一切皆可计算,可预期,可确定。因此,理性概念的主要含义是指逻辑可计算性。
“形式”与“理性”这两个概念均有逻辑可计算性之义。但是,两者之间也有区别,“理性”与“非理性”相对应,侧重指逻辑必然因果关系;而“形式”则与“实质”相对应,主要指标准的可识别的法律条文体系。形式主义法律体系是自给自足的系统,能够保证法官“把一般的法规运用于特殊情形下的具体事实,从而使司法具有可预测性。司法的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够像技术合理性的机器一样运行,这就保证了个人和其他主体在这一体系获得最大限度的相对自由,并极大提高了预测他们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④[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4页。
形式理性法治方案要求构建逻辑清晰、前后一致、可以覆盖任何实际情况的完备的规则体系。⑤就法律理论和法律体系而言,可以依据它们更趋形式化或实质化的倾向,对其进行划分。因而,在一个极端,我们可以识别出各种高度实证主义化的理论,它们坚持“法律就是法律”,认为在事实上,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官方制定的法律;法律理论的主要功能,是为这种有效的法律及其所提供的形式性依据给出理由和说明,而这种形式性依据只能通过参照正式的渊源——官方“制定”的规范,并以可识别的规则的形式出现。处在另一极端的法律理论,则极其关注有效法的实质内容和工具作用。这些理论强调,除了渊源取向外,内容取向也是确定有效法律的标准;在确定规则的含义时,应当关注存在于规则之中和规则背后的实质性依据,而不是规则的字面意思。多数法律理论在“形式的—实质的”划分中,都趋于、倾向或偏向于其中的这一极或那一极。参见[美]P.S.阿蒂亚、R.S.萨默斯:《英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法律推理、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金敏、陈林林、王笑红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这个理想型的法治方案不排斥伦理、道德、价值等实质内容,相反,形式理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将体现社会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上的诸多实体价值凝固于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变动不居的实体价值必须通过复杂的程序、概念和命题等法律形式予以协调、规范和确定,并以主权者命令这样权威而公开的形式加以识别与确定。社会价值共识已经最大程度地为法律形式所吸收,形式与实质合一,形式合法性(legality)即等于实质正当性(legitimacy)。①David Dyzenhaus, "Now the Machine Runs Itself ": Carl Schmitt on Hobbes and Kelsen, 16 Cardozo Law Review12 (1994).
如果形式理性法治的方案能够完全实现,那么,作为法律秩序的利维坦就是一种自动平稳运行的机械装置。法律秩序的形式要求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法律应以有形的,可以识别的,具有外部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不管是以一定的词语、签字的仪式,还是实施具有一定特定意义的行为,法律都具有程式化、外部化的特征。其次,组成法律的是一些可能远离具体事物和行为的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和命题,法律的适用有赖于对抽象法律概念和规则的逻辑分析,以及从规则到具体判决的形式逻辑推理。②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以法之确定性问题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由此来看,法律概念与命题表现为成文规则,而成文规则从性质上分为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程序规则具有更多的形式意义;而实体规则就其形成来看,需要程序规则的塑造,从其表现方式来看,需要以成文的规范形式存在,方能为人所识别,因此,实体规则对法律的形式性也有根本的依赖。就此而论,自动运行的法治机器正是由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组装而成。
实体规则以其逻辑结构与成文的制定法的方式体现了法的形式性,程序规则本身更具有突出的形式意义。③孙笑侠:《程序的法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5页。形式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程序法治,程序法治则以宪法程序之治为根本。宪法实体规则与宪法程序规则相互紧密交织,两者的区分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实体规则是对法律主体地位、资格、能力、利益等方面的规定。④莫纪宏:《宪法程序的类型以及功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尽管实体规则不可或缺,而程序规则在现代法律系统中却占据枢纽位置。⑤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首先,将所有的公民实体权利都载入成文宪法不具有立法技术上的可行性。其次,宪法实体性内容需要确定的形式加以表述,过多的实体性规定会造成宪法文本冗繁。再则,人们所追求的实体权利与价值需要程序规则加以保障与实现,“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⑥The opinion of the Court delivered by Justice Felix Frankfurter in LcNabb v.United States, Se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Reports(87Law.Ed Oct .1942Term),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1943,pp.827-828.——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F·福兰克弗特。转引自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页。对实体利益与价值作过多的设定,反而构成对实体权利的不必要的限制。因此,与其逐一规定或列举实体权利,毋宁以具体的程序规则对抽象的实体利益加以保障。最后,但最为重要的是,宪法应尽可能避免为公民设定特定的公共目标。如果宪法设定实质性的特定目标,国家则成为奥克肖特所说的“事业联合”型国家或行政技术型国家,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将会受到不适当的限制。在此意义上,有限政府原则要求避免或最大程度减少将实质性特定目标纳入政府决策范围。宪法的基本要素是自然权利、有限政府、权利竞争与法律程序,⑦Frank M.Coleman, Hobbes and America:Exploring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7,p.16.这四个要素是彼此具有内在关联的逻辑整体,共同构成有限政府原则。
诚然,宪法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与幸福为最高价值,旨在实现民众的福祉预期,但是,却不是以设定过多的特定公共目标的方式,或者以“事业联合”的方式去实现这些价值目标。人类的价值追求表现为纷繁多样的个体偏爱与选择,国家不能代替个体作出这种参差多样的选择。因此,宪法不是不能规定公共目标,而是尽可能确立抽象而宽泛的国家目标,从而留给人最大限度的选择空间。
就实体价值的高度抽象性而言,即便是法的实体规则也更多地具有程序性规则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特点。“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①Lon L.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p.106.美国学者富勒的这个法律概念具有很强的实证主义意味,而对法律的实体价值并未作具体界定与限制。富勒提出的两个基本的实体自然法:保持人类目的的形成过程的健康性,保持人类交流渠道的开放性,②谷春德、史彤彪:《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也更多地带有法律程序的性质,“人类目的”与“健康性”都是高度抽象的实体价值标准,而“形成过程”与“交流渠道”显然指涉法律程序。可见,作为自然法学家的富勒其实要比其学术对手哈特更为强调法的形式理性。
正如实体规则具有程序属性一样,程序规则同样具有实体性,程序规则从根本上也是实体价值的表现。③汪栋:《正当法律程序价值内涵的历史嬗变——以英美普通法为核心的考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就宪法而言,人民的权利是其实体价值的根本,须对人民的权利作最低限度的实体规定,而对实质性公共目标则只作抽象的描述。宪法列举实体权利有限,却不意味人民实际享有的权利有限。如汉密尔顿所言,人民并不向国家交出任何权利,④[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429页。他们只是委托主权者行使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也就是作自己案件法官的权利和使用强力的权利。政府的权力只限于公民所委托的这两项权利,即政府作为不偏不倚的第三方,对公民彼此之间的权利纠纷进行居间裁决的权力;另一项权力是对暴力加以集中的管理,必要时代表公民使用最低限度的强力。除此两项权利委托第三方即主权者行使之外,公民保留其正当的偏爱与选择。
当然,人们的不同权利与价值选择必然会发生冲突,也正是因为权利冲突不可避免,所以才会授权政府对这些冲突进行协调与裁决。无论是在公民个体之间还是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当冲突发生时,主权者应当克制使用武力,坚持最低限度的武力原则,避免强制冲突的任何一方出局,而必须主要依靠宪法与法律程序,将权利竞争过程中产生的激烈冲突与对抗纳入理性、公允、和平的商谈程序中加以协调,达成冲突双方的利益妥协与价值共识。
无论是“最佳政体”还是“事业联合”型国家,均预设个人不能自主判断利害取舍的前提,否定每个理性的人都是自我保存的最终判断者。对于“最佳政体”而言,个体必须服从于社会整体的至善秩序,对于“事业联合”型国家而言,个体必须将自己奉献给某种特定公共目标,逻辑上,这两种政体类型都会抑制人们相对独立的权利追求。“法治联合”型国家则以承认人们的权利追求为前提,权利是原因,宪法与国家是结果,原因先于结果,权利先于宪法和国家而存在。利维坦既然是从自然权利出发进行推演的结果,它就不具有偏离自然权利的独立的价值目标,因而也就不能以自己的价值目标为依据命令与强制人们服从,而只能保障权利,协调社会的权利关系,为权利追求与竞争提供和平的宪制秩序与环境。利维坦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权利理论,自然权利原则根本上要求每个人自主自治,人们通过法治联合体协调彼此的权利追求。自然权利学说既拒斥古典“最佳政体”的“智慧的统治”,也否定“事业联合”型国家为个人预设目标追求。实际上,“事业联合”型国家不过是“智慧的统治”的变体,因为它同样否定人们具有判断自我保存利益的能力。霍布斯以自然权利概念为中心的新政治科学则突出个人责任伦理,尊重个体权利追求,这在逻辑上必然要求利维坦以公断人的身份,运用程序规则协调人们彼此之间的权利关系。就此而论,利维坦隐喻的现代法治联合体的精髓是程序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