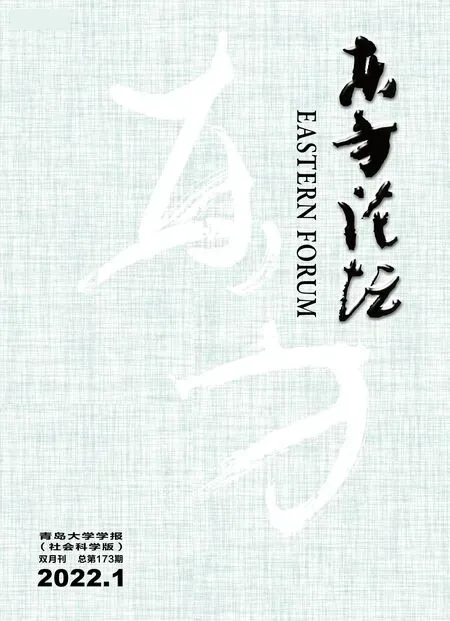鲁迅的纪实创作及其影响与意义
章 罗 生
湖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关于“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人们已形成基本共识,即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是中国现代作家第一人”“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化业绩,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最重要、最宝贵和具有最高成就的部分”①彭定安:《鲁迅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页。等。然而,这里的“现代”主要是指从1917至1949年的传统“三十年”,如将其延伸至1949年后的“当代”,即考察“鲁迅与中国当代文学”或“鲁迅与新时期文学”“鲁迅与21世纪文学”等,其研究就不但谈不上系统、深入,而且可以说还刚刚开始。而对“鲁迅与纪实文学”来说,不论是传统的“现代”,还是包括“新时期”与“21世纪”在内的“当代”,其研究成果更微乎其微。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鲁迅是小说家和文学家,而文学又以虚构为中心,他与“纪实”有何关系?尤其是,中国纪实文学的异军突起是在新时期后,学术界对此还未引起足够重视,鲁迅能与其产生联系吗?因此,提出“鲁迅与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的命题,实际上包含了关于拓展“鲁迅学”研究的两个相关方面:一是鲁迅与中国“当代”尤其是与“新时期”和“21世纪”文学,二是鲁迅与纪实文学——包括其创作与理论建构。而就其价值和意义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大:它不但关系到开辟纪实文学研究新领域,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视野,等等,还直接影响到文学观念的更新与文论体系的重构等根本问题。因而本文试对此作一探讨。
综观鲁迅的全部创作,我们发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和杂文大师的鲁迅,实际也是纪实文学大家:其纪实创作的数量几乎占全部创作的一半。我们通常将鲁迅的创作分为小说、杂文与散文,且将其笼统视为“纯文学”或“虚构”文学,这实际是对鲁迅的误读。因为,通观《鲁迅全集》可知,其中不但有纯“纪实”的《两地书》等书信和日记等,而且其“散文”类中的《朝花夕拾》是正宗的纪实文学——“纪实散文”,其“杂文”类中包括许多“纪实”文体,甚至其小说中的一些篇什也可视为“纪实”小说或散文。即连鲁迅历史小说的“在‘历史的文本性’、即‘是这样’想象中阐释历史是真实和虚构的统一”①姜振昌等:《艺术真实的两极想象》,《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期。,也有纪实的成分。而通过其纪实创作,我们也进一步认识到,鲁迅的确“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实质意义,最富思想文化内涵的文学家”。
关于“杂文”。杂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杂文应当是兼容各种体裁、各种形式,写法不拘一格”,“狭义的杂文主要是指议论色彩比较浓的一种文章,即《汉书·艺文志》里所说的‘杂说’一类文章”。②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页。而综观鲁迅杂文可知,它并非狭义的“杂说”,而是“兼容各种体裁、各种形式”的“广义杂文”;或者说,它既包含了较多狭义的“杂说”,又“兼容”了“各种体裁、各种形式”的其他文体,其中不但有少量诗歌,而且包括了通信、题记、赠答、自传、日记与其他写人记事的大量“纪实”作品。据笔者初步统计,在鲁迅18部杂文集的800多篇作品中,这类“纪实”文体有250多篇,将近三分之一。这一点,在《集外集》《集外集拾遗》和《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尤为突出:在这3部文集的282篇作品中,除41首诗歌外,其“纪实”类作品有126篇,几乎占其总量的一半。其中题记、小引、序言和后记等38篇,通信、答问等15篇,有关写人、记事和说明等70篇,另有《鲁迅自传》《自传》和《俄文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等“自传”3篇。其实,关于鲁迅杂文所包含的“纪实”文体或所具有的“纪实”特色,早已有人指出,“被作者收入杂感集的,还有别一种类型的作品,如《记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且介亭杂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等篇,因其记事怀人,密切地联系着当时的直接现实,它的记述与抒情,也就显示出与那种只是‘回忆的记事’又不尽相同的风格特色,我们似乎可称之为抒情的记事散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和《为了忘却的记念》(《南腔北调集》)”——它们“亦属于回忆记事散文之列”,但“既与一般的杂文写作不同,也和《朝花夕拾》的风格不尽相同”。③李希凡:《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0—180页。正是如此,鲁迅“杂文之义,不仅在于‘文集’是编年的,所有体裁的文章都收在内,以其文章品类之‘杂’,而为‘杂文’集;而且,也以文章思想、感想评论对象之‘杂’和思想观念自身之繁杂,而成其为‘杂’”④彭定安:《鲁迅学导论》,第224页。。然而,正是这种“杂”与“实”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其独特的“诗史”:它“作为一种‘文本人类学中的中国纪事’,其‘纪事’不仅是艺术地完成的,而且是更侧重于从心态角度和心态史视角,从灵魂的窥视与揭示上,来表达的。因此,更有了民族灵魂镜子的作用。”⑤彭定安:《鲁迅学导论》,第216—217页。可见,讨论鲁迅的“纪实”文学,离不开对其创作与思想的整体把握,尤其是必须联系其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方法等。
关于“散文”。在鲁迅创作分类的通行“三分法”中,“散文”是与“杂文”相对的大类——除《朝花夕拾》外,一般把散文诗《野草》也归于其中,同时,也把《朝花夕拾》视为与《野草》一样的“虚构”文学——狭义散文。实际上,“散文”的概念比“杂文”更复杂,它不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且其内涵与外延更游移不定。按现行散文理论,“杂文”与《朝花夕拾》属广义散文,而《野草》则属狭义散文,将它们比肩并列,严格来说是不科学的。因为“狭义散文侧重于抒情,融合形象的叙事与精辟的议论;广义散文则侧重于议论或叙事,在不同程度上融合抒情性”①方遒:《散文学概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8页。。因此,有人认为散文分为小品、杂感、随笔、通讯四类, 有人认为“小品文是包括杂文、随笔等在内的”②树森:《散文创作艺术》,见方遒:《散文学概论》,第33页。;还有人认为“抒情性很强的散文”是小品文,“抒情成分更浓,基本上省略了叙事的因素”的是散文诗,“侧重于议论性,然而在议论中又渗透了形象与感情”的是杂文;“就狭义散文领域而言有小品、随笔、游记、日记、书信这些体裁,就广义散文领域而言有杂文、政论、学术小品、序跋、回忆录、人物特写、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这些体裁”。③林非:《林非论散文·关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研究的问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第6、82页。这些看法虽然不完全正确,如将文学报告、传记等当今已独立出来了的体裁仍归于广义散文,就显得较传统、保守;将日记、书信等归于狭义散文,也值得讨论、推敲,但它们都认为狭义散文以“抒情”为主,广义散文以“议论或叙事”为主,却是简明、实用之论。它不仅为我们重新认识鲁迅创作中的文体问题提供了依据,而且为我们认识当今的纪实文学以及建构其独立理论,提供了重要资源。
的确,在鲁迅创作中,“名为散文,其实依然不过是在回忆之中杂了抒情成分的杂感的,是《朝花夕拾》”④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它充分反映了一个时代——由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衰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面貌。这也是一部自传性系列散文,对作者的寂寞的童年、不幸的少年和成长的青年时代,作了系统的记述。”⑤彭定安:《鲁迅学导论》,第196页。而在《朝花夕拾》中,无论是写人的《阿长与〈山海经〉》《父亲的病》《藤野先生》和《范爱农》,还是叙事的《狗·猫·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五猖会》等,其内容不但都是“回忆”中的真人真事,而且其态度甚为冷静、客观,确属“纪实”散文。正如有人所说的“‘纪实散文’里所记之‘实’,主要不是‘情’与‘感’,而是‘实人’‘实事’‘实地’‘实物’。其表现方法,也是以记和叙为主,文字中适当掺以议论,暗暗渗入感情”⑥佘树森:《散文创作艺术》,见方遒:《散文学概论》,第37页。;“与《野草》前后衔接的带有自传性的叙事散文《朝花夕拾》的写作,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并曾名之曰《旧事重提》”,但它们“追怀作者青少年时代的往事,既渗透着对哺育他的前辈们的诚挚的怀念,又真实地抒写了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前后作者所经历的生活种种”。⑦李希凡:《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第190页。
不仅如此,关于《朝花夕拾》,近年的研究更进了一步。有人认为:它“绝非一般的回忆性散文”而是一部完整的“自传”。因为,其中各篇单独看似乎是作者“从记忆中抄出来的”生活片断,但深入细察,不难找到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叙述的正是鲁迅相对完整的生活历程。它们之间不仅有先后承接的时间链条,也包含着严密的空间转接,恰好完整地映现了作者自幼年至北京工作后的完整生活。总之,《朝花夕拾》以作者自我人生为主干,联缀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富有个性、动态变化着的生命世界;“它不是生平资料的堆砌,也不着意于个人日常生活(的)琐屑记录,更迥异于传统传人(记)的‘何人、何方人士、其祖为谁’一类的老套作品,而是通过生动的场面、形象的刻画、饱含主观意绪的文笔以及不无根据的文学虚构,完成对一个独立人格的形成过程的再现。”①辜也平:《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论》,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166—170、439页。
关于小说。如果我们把“小说集”中的《社戏》《鸭的喜剧》《故乡》和《一件小事》等,与“散文集”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五猖会》《狗·猫·鼠》与《范爱农》等比较,可见出两者并无多少区别:它们都不重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而都以第一人称“我”“回忆”故乡或童年等的“实事”“实地”“实物”甚至“实人”——如爱罗先珂是真人真名、润土是真人假名等。因此,实际上,它们应视为纪实散文或纪实小说——正如有人所指出的“《社戏》不是小说,乃是纯粹的美妙的散文”②李长之:《鲁迅批判》,第92页。。
关于书信与日记。这确属“纪实”文学,但其研究“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大多局限于人物、事实的考订”,因此,“改变这种对于鲁迅‘非创作文本’之一的‘书信文本’的研究状况,是鲁迅学发展中的一个待开辟的领域”③彭定安:《鲁迅学导论》,第260—261页。。的确,如果我们破除以“虚构”为中心的“纯文学”观,树立包括“纪实文学”在内的“大文学”观的话,就可见:鲁迅的书信与日记等,不但具有资料意义与认识价值,而且具有理论意义与文学价值。尤其是《两地书》,不仅涉及鲁迅与许广平两人的思想与生活及其所涉及的种种问题,而且“还涉及鲁迅这时期对时代、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等的看法以及其中反映的他的哲学、社会、文化观;也涉及这期间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与同时代人的关系”;因而“在诗学的‘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思想’/‘文学与心理学’等范围内,都是十分有价值的”。④彭定安:《鲁迅学导论》,第260—261页。如“透过《两地书》的相互倾诉,我们看到了鲁迅对人生、对社会、对当时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和看法,看到了鲁迅和许广平的相知相爱的心路历程,更看到了鲁迅与许广平的崇高和美好品格”,其中“表现了鲁迅为人处世的严肃认真,更显示了他对爱情、对爱人负责的品格”,“也表现出鲁迅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七情六欲的平凡人!”⑤郭久麟:《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鲁迅日记也是这样:从家庭、情感等方面,进一步揭示了平凡与伟大相统一的鲁迅形象。其中包括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真爱,有关鲁迅与原配朱安,及有关鲁迅与母亲、孩子之间的关系,等等,其风格含蓄、委婉、朴素。如与郁达夫日记比较,“鲁迅日记可做史料读,郁达夫日记可当散文看……鲁迅日记极其客观,不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郁达夫的日记时断时续,完全为情感的变化所驱使……鲁迅的日记为记事,郁达夫的日记为抒情”⑥参见丁仕原:《鲁迅与郁达夫之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89—95页。。
不仅如此,鲁迅不但热切关注纪实文学创作,而且还写过有关纪实创作与评论等。如1932年9月19日,他为所编辑的苏联短篇作品集《一天的工作》写了后记,认为其中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不只是‘报告文学’的好标本”,而且“是实际的知识和工作的简要教科书”,肯定这样的作品是苏联作家“应了时代的要求”,深入到“工厂”“农村”和“大建设的地方”“以最短的限期”创造出来的艺术品。1933年5月,他为曹靖华译的高尔基的文学报告《一月九日》写了“小引”,认为它可作创作的借鉴。而这两篇文章,也表露了鲁迅的文学报告观念,即认为文学报告是作家深入生活的产物,应符合时代要求;它具有启蒙功能,应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同时,除会见来华访问的捷克报告作家基希外,他还在《三月的租界》中提及高尔基与基希及其文学报告,表露出对文学报告作家的赞许之意。而对国内的作家作品,他更予以热情扶持。如为了让曹白揭露反动统治的《坐牢略记》躲过当时的书刊检查,他将其引入自己的《写于深夜里》以曲折发表。①参见朱子南:《中国报告文学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17—219页。不仅如此,鲁迅还写了文学报告(纪实散文)《略谈香港》和《再谈香港》:前者寓庄于谐,揭露了香港恶劣的政治环境,后者则记叙了香港警察在“察关”时勒索财物的种种丑行,等等。②参见张春宁:《中国报告文学史稿》,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60—61页。
还须指出,在学术、理论方面,虽然鲁迅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在小说等方面,但也有关于“纪实”的重要论述,只不过他主要是从文学与生活或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强调其现实主义或“实录”精神罢了。如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③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0页。,肯定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④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9页。,称之“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34页。。此外,在论述中国小说史时,鲁迅也提到不少“传记”类纪实作品,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五柳先生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以及《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⑥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9 卷,第 70、75、76、80、110、120 页。,等等。
那么,鲁迅为何没有太多有关纪实文学方面的直接论述?这是因为鲁迅所处的时代,既是一个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时代,也是一个以小说等“纯文学”为正宗而“纪实文学”不甚发达、不被重视的时代。其中报告至1930年代才被正式定名并逐渐成熟,传记处于由“历史”向“文学”的观念变革与文体过渡期。而在“纯文学”中,人们又普遍推崇与看重小说。在这方面,鲁迅与梁启超的观点基本一致,或者也受到梁启超有关小说“新”国、“新”民、“新”政治等思想的影响。因而他不但翻译域外小说、写作《狂人日记》等,而且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等。可以说,鲁迅与梁启超的观点及其文体选择,与其特定时代的文化环境与审美风尚密切相关。
与此相连,鲁迅的这种审美选择还有作家与文体等方面的原因。就作家个人而言,主要是因为鲁迅不但是革命家,而且是思想家。他之所以主要选择小说这种形式,不是为了“消闲”或“玩文学”,而是要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赋予小说以“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新功能,即利用小说既能自由虚构又通俗易懂的特点,以更好地表达其“革命”“思想”。正是如此,他才通过狂人、阿Q等不朽典型,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入骨地刻画国民的魂灵与深刻地揭示“吃人”的封建文化。当然,不是说文学报告、文学传记等纪实文学就不能“为人生”和造就革命家与思想家——相反,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已证明,它们在批判现实、直面人生、推进改革和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更能显示其“真实”力量与直接发挥作用。然而,其前提,一是须有民主、宽松的时代环境与言论自由的文化氛围,二是须有调查采访的时间、条件和较完备的图书资料,三是须有较成熟的文体基础与较广泛的读者群体。而鲁迅所处的时代,这三者都不具备:在文网密布、动辄得咎的“文化围剿”中,连发表小说、杂文都只能不断变换笔名且用“曲笔”;在“破帽遮颜过闹市”“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环境下,根本谈不上调查采访与资料搜集——如他所说:“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①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2页。至于文体与读者基础,如前所述,文学报告与文学传记尚在初生与转型期,而明清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等“消闲”小说所形成的审美惯性与消费时尚仍占统治地位。也许,这就是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小说家多、小说成就高的重要原因吧!
然而,即使鲁迅后来主观上计划写长篇小说,但客观现实却使他只能以“杂文”为武器冲锋陷阵。如此,历史在给我们造就一代杂文大师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纪实文学遗产。而当我们站在当今的“纪实时代”而致力于理论建构时,我们发现:我们不但绕不过鲁迅,而且仍然要从鲁迅出发,并认真吸取其精神与力量。
首先,在纪实散文方面,鲁迅不但奠定了扎实基础,而且也做出了重要示范。正如有人所指出:“《朝花夕拾》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传性,是民元前那一历史时代和世态风俗的真实记录,但由于它们是写于一九二六年的那样一种血腥环境和鲁迅思想发展的这段时间的背景上,渗透着这些回忆性散文的,也同样有尖锐的现实斗争的内容”;《记念刘和珍君》与《为了忘却的纪念》“都以反语写了‘忘却’,而主题又是强烈地指责‘忘却’的惰性,抒写‘不能忘却’的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它们与《柔石小传》《白莽作〈孩儿塔〉序》等一样,“把记述、议论和抒情浑然融为一体,又贯串以革命抒情的主旋律,使读者对于这种‘情感中的理性的美’,有着深刻的感受”。②李希凡:《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第181—182页。而鲁迅书信、日记等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也不仅表现在它是一种其他研究的“实证材料”,而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言说’/‘对话’中,可以看到所表现出来的鲁迅的思想、心理、性格、人格,从他这一‘个体’——‘言说主体’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时代、思想、文学、文化、政治的面貌”③彭定安:《鲁迅学导论》,第260页。等。
其次,鲁迅的纪实文学创作,也充分体现出“主体虔敬”“题材庄重”与“守真求实”等“新五性”④“新五性”是笔者提出的关于纪实文学特性与价值规范等方面的创新概念,详见章罗生的《中国报告文学新论·第四章 “新五性”:文体特性与价值规范》(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与有关系列论文。特色。而他在这方面所开创的传统,实际上与其小说、杂文等一样,也不但为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给后世以深远影响。如在纪实散文方面,我们从1930年代“由重自我、重抒情、重审美的抒情美文,向重群体、重写实、重功利的记叙散文转移”⑤佘树森:《爬坡集·20世纪中国女子美文一瞥》,见方遒:《散文学概论》,第20页。,到“文革”期间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与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等“潜在写作”,再到1980年代以来以巴金、杨绛、李辉、章诒和、王树增等为代表的历史反思散文;在书信、日记文学方面,从郁达夫、沈从文到《傅雷家书》《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等,我们也可看到鲁迅的内在风骨与深远影响。
当然,鲁迅对当代纪实文学的影响,最鲜明、突出的,还是其“鲁迅精神”。“鲁迅精神”包括“政治远见”“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其中“政治远见”包括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清醒的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精神;“斗争精神”包括“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精神、独立精神与彻底反封建的韧性战斗精神;“牺牲精神”包括“俯首甘为孺子牛”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报告等纪实创作,就全面、深刻地体现了这些精神质素。①参见章罗生:《鲁迅精神与新时期报告文学》,《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如赵瑜、胡平、徐刚、卢跃刚、黄传会、陈桂棣、王宏甲、张正隆与金一南等作家,以及《中国农民调查》《第一种危险》《中国新教育风暴》《雪冷血热》《苦难辉煌》与《共和国粮食报告》等作品——尤其是赵瑜、卢跃刚、张正隆与张扬的“敢于碰硬”,及胡平的“学术体”与“思想美”等,分别从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将鲁迅精神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正是如此,有人认为: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等,“是对20世纪初鲁迅发出的震撼人心的文学‘呐喊’的呼应,是对‘五四’文化批判精神的继承”;它“告的是民族和国家之急,诉的是民族和国家之痛”;作家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及看法,“与鲁迅当年把文学作为‘改革社会的器械’、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文学观有相同处”。②余三定、周淼龙主编:《何建明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年,第31、64页。
总之,综观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可知,鲁迅的伟大创作实践,不但为虚构文学,而且为纪实文学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示范,指明了方向。其不朽的思想文化与艺术精神,不但深刻地影响着虚构文学,同时也长久、广泛地哺育着纪实文学。如果说,“鲁迅以他特有的精神力量,影响与造就了一代又一代‘鲁迅式’的作家、学者及‘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和‘鲁迅式’的中国人”③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那么,这种“鲁迅式”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在纪实文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他所开创的“为人生”等现实主义、启蒙主义文学传统及其创作实践,不但为虚构文学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而且为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点,我们从赵瑜、胡平、卢跃刚、陈桂棣、徐刚、张正隆、张扬、冷梦等的创作中都能具体看到。我们应高度重视鲁迅精神在当今纪实“大文学”中的继承与发展,及其在纪实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构等方面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