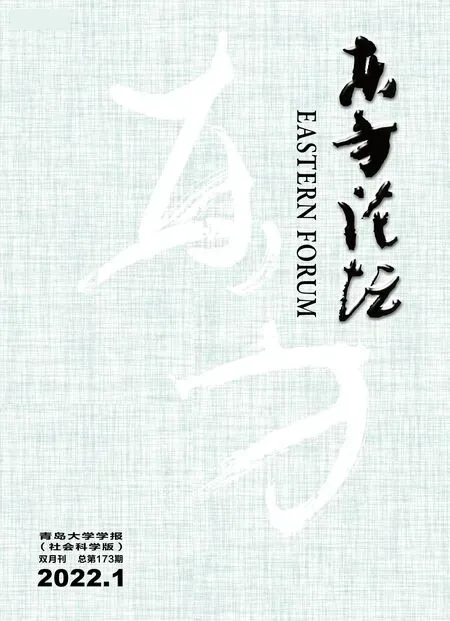理学视域下的朱子理想人格修养论
李 涛
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儒家的修养,传统上一般称为修身之学,虽名为“修身”,但真正的意蕴既不像道教那样是为了尽可能地延长人的寿命,修成神仙,亦不像佛教那样为寻找另一个世界来安顿人的心灵,而是为了延长人的精神生命,成就一种理想人格,即一种突出道德特征的人格修养。何谓“修”,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引用胡安国的解释很贴切,即“治而去之。”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31页。对于一般人来讲,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身之有病之人往往会知而治之,而对于心之病却视而不见,或明知心有病,却放任其肆掠生命之性体,病到一定程度以至心身分裂,麻木不仁。朱子所谓“治而去之”,治之要当在治其心病,其心病当在除去使心患病的各种不良气质、欲望,克己复礼,复归心体之仁,修身实为修心。人心如镜,本自光明,但为气禀、物欲之灰尘沾染,心之镜蔽而不彰、昏而难明,唯有施以打磨、擦除之工,方能复归心镜之本明。朱子曰:“镜本明,被尘垢昏之,用磨擦之工,其明始现。”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17,武汉:长江出版传媒;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第283页。人心虚灵不昧,犹如镜之本明,只是被气禀、人欲所染,故道德修养就是磨镜的工夫,诚心而为,坚持不懈,定有所成就。宋明儒受佛教影响通常以镜喻心,朱子亦多有所用,再略举数例。如:“要验学问工夫……如一镜然,今日磨些,明日磨些,不觉自光。”(语类·卷5)“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镜子,本全体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边皆照见,其明无所不到。”(语类·卷15),“心如镜相似,仁便是个镜之明。镜从来自明,只为有少间隔,便不明。”(语类·卷31)王阳明曰:“(问)曰:‘无所偏倚是何等气象。’(答)曰:‘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着。’”(传习录·76条)他的学生徐爱亦好此喻,曰:“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传习录·63条)。为人者,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修慝何为时,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治人在治己,治己则在治心。朱子曰:“专于治己而不责人,则己之恶无所匿矣。”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1页。心在酬酢应事的过程中,总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欲望牵引,它们往往是心之病灶,开始时,则会匿而不显,而慝正所谓心有恶而匿于心者,人如能以张载所言之“责人之心责己”的态度来坦诚面对自己,则心之病何以藏?治身之病相对较易,而治心之病却很难,难就难在它是我们一生都要精心去治,需要有超强的意志与毅力,不能懈怠,持之以恒。
一、人格修养何以可能
在儒家看来,修养是人由庶人通向圣人的根本途径,通过诚心修养,人能改变自我的气质,浑化气质中的渣滓,复归人性之善。《中庸》提出了人通过修养何以可能通向圣贤的基本命题,曰:“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4页。,所谓“曲”,即是人之气质偏于一边,或清、或浊、或薄、或厚、或明、或暗,此对人之仁性的显现皆有遮蔽。朱子曰:“盖人之性无不同,而气则有异,故惟圣人能举其性之全体而尽之。其次则必自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曲无不致,则德无不实,而形、著、动、变之功自不能已。积而至于能化,则其至诚之妙,亦不异于圣人矣。”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4页。《中庸》提出致曲的工夫,也即是修养心性的工夫,让普通人看到成为圣贤的希望,让普通人的人生有了美好期许,为人们通向圣贤之域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可能的途径,此亦是人之为学、格物、敬持等修养工夫的内在依据。
在朱子看来,人性的修养中,心上的工夫非常关键。心具有“虚灵知觉”的功能,朱子继承《中庸》的观点,对人心与道心进行了阐发,但朱子实际上并不认同人心与道心是对心的二分,实际上,心是一个不能二分的整体,“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页。朱子说得非常清楚,“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而之所有人心、道心的不同在于发生的根源不同,人心生于形气之私,道心根源于性命之正,也就是说,人心是从生物学意义上来思考的,禀得的气有多少、厚薄、清浊之分,而道心则是从性理上来考虑的,虽然万物都禀气而生,但是气所以如此形成必有所以如此的理——天理,此正是人所以能成圣贤的形上保证。而形气总是对天理有不同程度的遮蔽,此是必然的、普遍的、客观的,即是朱子所说的“形气之私”。有学生问此,朱子曰:“人心是‘形气之私’,形气则是口耳鼻目四肢之属。”朱子做了肯定回答之后,学生又觉可疑,曰:“如此,则未可便谓之私?”朱子释曰:“但此数件物事属自家体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个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个不好的根本。”⑤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卷62,第1115—1116页。朱子认为,由气禀形成的耳目口鼻而产生的饥饱寒暖之类的欲望虽为人人所有,但是人人又有所不同,可能你有饥饱寒暖之欲,他人却无此欲,我的饥饱寒暖是“生于吾身血气形体”而具有的,“而他人无与”,这就是所谓的形气之“私”。虽为私,有危,但并不是不好,人虽都有饥饱寒暖之欲,但此欲望均具有因个人气禀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属性。现实中的人性具有可塑性,既可朝着道德理性的方向发展,亦可朝着生命欲望的方向发展,每个生命都有食色的生命欲望,圣人亦是如此,“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而此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心显然是不稳定的,具有危险性,“危殆而不安”,“形气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朱子进一步解释了人心何以危的理由,曰:“人心有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但为物欲而至于陷溺,则为害尔。故圣人以为此人心,有知觉嗜欲,然无所主宰,则流而忘反,不可据以为安,故曰危。”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卷62,第1117页。
可儒家之所以是儒家,正由于不只是从生物的自然意义上来理解人,而是在此意义上看到人之本有的道德理性意识,每个人亦都有一种先天的道德意识,哪怕是下愚之人,“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人可以超越生物意义的层面而进入道德的境界,实现此一跃层的基本路径就是人的修养。人其实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既有人心,又有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如果没有修养之治,则人就容易滑落至一个生物性的人,所以朱子曰:“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页。朱子所说的人心、道心之二分正是从“不杂”的意义上来讲的,即是说要“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让人之本有的道德意识发挥主宰作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二分,而是“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不能让人之所本有的道德意识(道心)淹没在人之所具有的食色欲望的海洋之中,同时,亦不能离开人心只谈道心,因为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避开人的现实生活谈人性易陷入佛老之虚无之地。因此,朱子曰:“若专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则固流入于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则是判性命为二物,而所谓道心者,空虚无有,将流于释老之学。”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卷62,第1117页。而人之所修所治,正是要使觉于理的道心来克治觉于欲的人心,让人心听命于道心,不让人自然之生命欲望偏离了人的道德本性,握好、握稳人性之柁,正如朱子所言:“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船无柁,纵之行,有时入于波涛,有时入于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运之,则虽入波涛无害。”④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卷62,第1116页。
总之,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意地将之二分为人心、道心,虽为一,但心之所觉有不同,觉于欲即为人心,出于形气之私,觉于理即为道心,发于性命之正,人心、道心之异只是心之知觉不同,并非是两个心,心只是一,这始终是朱子坚持的一个基本立场。然而,人之心必感物而动,不可不有饥饱冷暖之欲,此为人心,圣人亦不可无,是普遍的客观实存,不可去,然欲必有所欲之理,当食则食,不当食则不食,此为道心,下愚亦不可无。朱子一方面认为心不能二分,一方面又强调人心、道心不能混杂,表面上看似乎自有抵牾,实则道出了“心”意的真谛,人人皆有道心,但往往杂于人心之欲而不知,流而忘返,堕于形气之私。而怎样使人能觉悟到自我本有的道德意识,让道德意识主宰引导人的自然生命,使生命有层层推进的动力,同时,又不能空谈道心,则须要修养的功夫才能实现。因为每个人皆是形气而生的自然生命,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的生命欲望,欲望可克制却不能消灭,道心不能脱离人心而成为一个独立的道德理想王国,否则,人就会脱离现实生活的本真与依托而陷入释老的虚无之境。释老之学一味地强调人的道心而压制人性之欲望,正是要削掉人之现实生活的根源,最终使人的修养进入不归之途,正如朱子所反复追问的那样:“饥能不欲食乎?塞能不假衣乎?能令无生人之所欲者乎?虽欲灭之,终不可得而灭也。”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4册卷62,第1118页。
修养,尤其是人的人格修养对人之所以重要,在于人之生命既有自然的生物性的一面,即人有知觉运动,此为人形气之生命,同时,人亦有道德的精神性的一面,心具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道德本能,即道德之生命。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人性的复杂在于,人的本性虽然是善的,但人往往对自己的善性没有充分的觉醒,容易陷入物性的一面,也即生物性或动物性的一面,这样人与动物的区别将消弭,人就等同于一堆只知道寒而衣、饥而食、渴而饮的血肉之躯。气化生命具有向下垂落的惰性,需要进行反方向的向上提升,以纠正气化生命向下的垂落。其实,人格修养的一个重要功夫就是要善于扩充自我的善良仁性,正如孟子所说的那样,如果人的仁性能够得到很好的扩充,就会如同“火之始燃”“泉之始达”一样,相反,如果不能扩充人的本性,也就不能守住人的本性。能不能守住人的本性,是涂人与贤人的重要区别。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涂人和贤人都具有“天之所与,我固有之”的仁义礼智之性,所不同的地方在于:“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11页。,即并不是独有贤者具有仁义礼智之心,只是贤者能够不断修养自己的德性,浑化生命的渣滓,醇化自我的气质,能够彰显扩充自我生命中的仁义之性,使之保持本有的光明而不丧失。所有学问之道没有什么特别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学会守住自己的本性,即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12页。求放心,就是将由于物欲等原因而被牵走的仁义之心找回来,也就是要回归人之所本有的善良之心。
二、朱子的圣贤气象论
儒家谈修养的一个终极目的就是成就圣贤人格,它是通过人的气象表现出来的。宋儒好谈气象,对于圣贤气象更是十分追崇,朱子亦不例外。圣贤气象,即天道流行贯注于圣贤生命中所自然显发的一种实然之相。实现天所赋予我们的善良德性,欲做圣贤,是求道的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先贤圣人传承了一系列关于理想人格实现的路径、方法。朱子借助《论语》中孔子与颜子、子路的一段各言其志的对话,将圣贤气象分为三个层次:子路气象、颜子气象、圣人气象。《论语》载曰:“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敞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④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3页。子路气象所展现的是一种轻财重义的人格特征,颜子气象所展现的是一种意欲无我的人格特征,圣人气象展现的则是一种天理流行、浑然一体的人格特征。我们谈气象,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从低往高一步步地踏实做工夫。当朱子和弟子叔器就修养工夫提出“先识圣人气象,如何?”的疑问时,朱子认为圣人气象最重要是通过踏踏实实的做工夫来逐渐涵养的,曰:
也不要如此理会。圣贤等级自分明了,如子路定不如颜子,颜子定不如夫子。只要看如何做得到这里。且如“愿车马,衣轻裘,敞之无憾”,自家真能如此否?有善真能无伐否?有劳真能无施否?今不理会圣贤做起处,却只去想他气象,则精神却只在外,自家不曾做得着实工夫。须是“切问而近思”。向时朋友只管爱说曾点、漆雕开优劣,亦何必如此。但当思量我何缘得到漆雕开田地,何缘得到曾点田地。①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29,第569页。
程伊川常让弟子看圣贤气象,目的就是让弟子以圣贤为榜样,学做圣贤的模样。认识了解圣贤气象当然重要,但对于禀赋不好、悟性不高的人来讲,往往容易将大量的精力放在认识圣贤气象的表面上,陷入玄思妙想,脱离现实生活,走入虚空,“却只是想他气象,则精神却只在外”,这样就会偏离实做的工夫,所以相对于识圣人气象来讲,更重要的是着实去做工夫,如同子路的“愿车马,衣轻裘,敞之无憾”,先不要去想子路的气象如何不如颜子,此自是如此,而是先学做到子路那样。对于《论语》中记载的“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这句话,朱子释曰:“前所闻者既未及行,故恐复有所闻而行之不给也。”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8页。子路的这种不虚言妄行、诚实力行的品格深为朱子所称颂。朱子所在的南宋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在意书本上的学问,不注重践行,恰恰与子路相反,这种社会风气对于塑造踏实精进的学问风气是很不利的,朱子无不忧虑地曰:“子路急于为善,唯恐行之不彻。臂如人之饮食,有珍羞异馔,须是吃得尽方好。若吃不透,亦徒然。子路不急于闻,而急于行。今人惟恐不闻,既闻得了,写在册子上便了,不去行处着工夫。”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29,第547页。书本上的学问做得再好,如果不转化为我们的道德实践,“不去行处着工夫”,那么书自是书,人自是人,书和人自相两隔。
圣人除天资优良之外,更注重在日用伦常的生活世界不断修养自我,让仁体之流遍润周身,视、听、言、动皆中和有道,所显发的生命气象也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此亦是德性得到长期修养而自然显发的一种气象。圣人虽能生而知之,但从来不以圣人自居,谦逊有礼,不妄自尊大。如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④杨伯峻:《论语译注》,第93页。此圣人的谦逊品格跃然纸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定《春秋》,为儒学道统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功不可谓不大,但仍保持此谦逊之品格,表明圣人是一种极高的人格修养境界,朱子云:“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0页。“德愈盛而心愈下”,此句非常精到地点明了圣人谦逊的人格特质。当人持守心中的天道而不让其放失于外,则狂妄慕荣之欲心就会因仁德的力量而缩小。今之有人,德业稍有所进,便浮泛飘忽而忘己,心不能定,身不能安,与此对比鲜明也。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圣学日衰,天道不能行于世,社会伦常体系崩塌,孔子发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的感叹,忧道不能弘,他以周公之道为目标,终身孜孜不己,只可惜岁月如流淌的河流,衰老悄然而至,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①杨伯峻:《论语译注》,第94页。此叹既表达了对天命之必然性的一种无能为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弘道夙愿还没有完全实现,而行道之身所能发挥的力量就开始弱化的一种深深遗憾。朱子对此释曰:“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1页。
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是孟子提到的几位圣贤,在总结他们各自的人格修养的特征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③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54页。伯夷清高、伊尹承责、柳下惠随和、孔子识时务。朱子认为,孔子的人格更具代表性,是集大成者。从理的角度来看,伯夷、伊尹和柳下惠三子的人格都有偏缺,“力有余而巧不足,是以一节虽至于圣,而智不足以及乎时中也”,就是在某一方面具备圣人的人格要求,而孔子之道,“兼全于众理”,以四时来比喻,“三子犹如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大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95页。对于孔子的弟子颜子、仲弓等人,朱子点评说:“颜子之于仁,刚健果决,于天旋地转,雷动风行做将去!仲弓则自敛藏严谨做将去。颜子如创业之君,仲弓如守城之君。颜子如汉高祖,仲弓如汉文帝。”学生潜夫回应朱子评价二子的话曰:“颜、冉二子之于仁,譬如捉贼,颜子便赤手擒那贼出!仲弓则先去外面关防,然后方敢下手去捉他。”⑤黎靖德:《朱子语类》第3册卷42,第807页。显然,颜子的工夫注重修内,不为外之形色所动,在孔门弟子中,显然高于其他人一筹,如正孔子称赞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⑥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2页。对于子路,朱子则评价曰:“子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其志可谓高远,然犹未离这躯壳里。”⑦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29,第566页。子贡的修养境界虽然比较高,但是相对于颜子来讲,还是差不少,朱子这样评价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未能忘我故也。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能忘我故也。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敞之而无憾’,未能忘物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能忘物也。”⑧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28,第544页。显然,“未能忘我”是一个私意未除净的我,“未离这躯壳”;“无我”则是一种接人应事自然而为、心与理自然相合的境界,“离了躯壳”。“未能忘物”是人心尚存在着私欲、私念,不是那么纯粹无杂,须要通过主体的克制工夫来消除,而“无物”则表征的是一种人心全无私欲、天理静净的境界,由“未能忘我”“未能忘物”到“能无我”“能忘物”是人格修养层次不断提升的过程。
在人格修养的过程中人亦会寻找到快乐,就如同小孩子在马路上捡到钱交给警察一样,内心里会有一种自足的快乐。它是人之本心在某种情景下一种自然流露,不是刻意追求的,不依赖于人的富贵贫贱。孔颜乐处就是一直支撑宋儒追寻实现生命价值和理想的精神支撑,亦是儒学门徒时常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儒学发展至宋代,为了重建儒学的价值理想,人们亦对此话题非常有兴趣。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对孔颜乐处又注入新的理学血液,使之更加鲜活,更能提起人的精神生命,更能成为人格修养和实践的方向。
三、朱子的孔颜之乐论
从《论语》所载来看,孔子说“乐”有多处,既有说自己的“乐”,如开篇即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①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页。“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②杨伯峻:《论语译注》,第99页。亦有说弟子的“乐”,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颜子,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③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2页。朱子解释“颜子之乐”曰:“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故夫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叹美之。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曰:‘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朱子在解释完之后加了一个单独的按语,曰:“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5页。对此问题,朱子和弟子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首先,颜子之乐不是乐贫。人之富贵贫穷皆由气禀而定,不是人能够选择的。朱子曰:“富贵、死生、祸福、贫贱,皆禀之气而不可移易者。”⑤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册卷4,第59页。既然贫穷不是由我们自己能选择的,我们虽可以通过奋斗改变,但人生精力有限,对于有志于道的颜子来讲,他没有选择做实业致富的理想。既然如此,如其不能选择,何不乐于其中呢?但我们应该看到,并不是颜子自甘贫困,以贫为乐,伊川云:“贫贱而在陋巷者,处富贵则失乎本心。颜子在陋巷犹是,处富贵犹是。”⑥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0页。朱子曰:
问:“颜子‘不改其乐’,莫是乐个贫否?”曰:“颜子私欲克尽,故乐,却不是专乐个贫。须知他不干贫事,元自有个乐,始得。”叔器问:“颜子乐处,莫是乐天知命,而以贫窭累其心否?”曰:“也不干那乐天知命事,这四字也拈不上。”义刚问:“这乐,正如‘不如乐之者’之‘乐’。”曰:“那说从乐天知命上去底固不是了,这说从‘不知乐之’上来底也不知那乐是乐个甚么物事。‘乐’字只一般,但要人识得,这须是去做工夫,涵养得久,自然见得。”⑦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31,第596—597页。
一方面,颜子之乐不是以贫穷为乐。虽处理贫困之中,但贫困绝不是颜子乐的理由,只是说颜回处在贫困当中,仍不忘记修道志学的使命,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醇化自我的气质,在做人行事方面力避欲望的牵引,努力发挥心的主宰作用,克制不良的欲望,使生命显示一种纯乎天理的气象,颜子也在自我的反证体验中感受到这种纯乎天命之理的境界,遂而感到快乐。正如朱子所说:“不干贫事,元自有个乐。”另一方面,颜子之乐亦不是乐天知命,而是自得其乐。明道说:“百官万务,金革百万之众,饮水曲肱,乐在其中。”①黄宗羲:《宋元学案》第1册卷13《明道学案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65页。即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本有天道性命之理得以实现的快乐,只是被欲望遮蔽了而己,一旦我们通过不断地修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后,就能体悟到此种快乐。朱子精辟地指出:“不要去孔、颜身上问,只去自家身上讨。”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29,第598页。
其次,颜子之乐是工夫达到一定境界后的自然显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虽然都蕴含着实现天命之理的快乐,但如果工夫不纯熟,则天理所贯注于生命而本有的快乐就很难显现。朱子曰:
问:“颜子乐处,恐是工夫做到这地位,则私意脱落,天理洞然,有个乐处否?”曰:“未到他地位,则如何便能知得他乐处!且要得就他实下工夫处做,下梢亦须会到他乐时节。”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29,第597页。
颜子乐处不是随意的显现,须要我们肯下工夫修养我们的生命,开掘我们生命中蕴含的丰富道德矿藏,当工夫修养到达一定的程度后,具有知觉之灵的心便能体会到天理本体的纯一无杂的境界,便知得这个乐处,“日用间义理纯熟后,不被那人欲来苦楚,自恁地快活。”④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29,第600页。所以朱子曰:“颜子不改其乐,是它功夫到后自有乐处,与贫富贵贱了不相关,自是改它不得。”⑤朱熹:《朱熹集》卷 61《答林德久》,成都:四川出版社,1996 年,第3170 页。
最后,颜子之乐不是物质获得之乐。一般人理解,我们欲想得到的物质财富得到满足就是能获得快乐,人们也正是在乐于求得物质财富并在得到之后获得快乐。而在理学家的眼里,这样的快乐不是真正的乐,真正的乐是天理遍润周身而体会到的一种快乐。
问:“颜子之乐,只是天地间至富贵底道理,乐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以下未可便知,须是穷究万理要极彻。”已而曰:“程子谓:‘将这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谓:‘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颜子乐处。这道理在天地间,须是直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彻,无有不尽,则于万物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问:“颜子‘不改其乐’,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浑是天理流行,无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贵之理,举天下之物无以尚之,岂不大有可乐!”曰:“周子所谓至富至贵,乃是对贫贱而言。今引此说,恐浅。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为所累,何足乐!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于心亦不乐。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动静语默日用之间无非天理,胸中廓然,岂不可乐!此与贫窭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乐。”⑥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31,第597—598页。
人的生命之高贵在于人身上流有仁性的血液。物质之需虽能养人之身,但未必能养人之性。人之仁性禀自天地生生之道,人与天地万物本自一体,周茂叔从“窗前草不除”中体会到生生之仁的快乐;苏轼被贬黄州时在困顿的生活中也能躬耕东坡、发明“东坡肉”,找到生命的自然、自得之乐。⑦董德英:《人间有味是清欢》,《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2月26日。人皆有不以外物为依托的自在、澄明之乐,只要尽心而求,不放逸自我,穷理尽性,克己修养,便会打通物我的阻隔,欲望尽除,身心和谐,心中纯是天理流行的境界,畅达活泼,浑然一体,心中便会自得其乐。孔子说:“仁者无忧”,梁漱溟先生说:“你几时懂得乐,几时懂得仁”,并打了一个贴切的比喻解释说:“如小孩比大人哭的时候多,他哭的时候,有时直是他畅快的时候。因之,他的心无所蕴蓄,一味流畅下去。仁者如小孩一样,他的生活时常在生命之理上,是以是时流畅,他并不是没有悲哀,没有忧惧,但是由那种悲哀、忧惧所生的忧伤烦恼他却没有。因为照生命之理而生活,只是有感触便起一个意思,并未于此外加一点意思。”①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一)》,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4—465页。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孔子之乐,那圣人之乐和颜子之乐有何区别呢?同样都是乐,为何孔子要说颜子不改其乐,而对自己却说乐在其中呢?朱子认为两者大体相似,主要区别在于天理流行的自然体段和工夫的纯熟上。在孔子而言,乐是一种完全不带勉强、自然而然的显现,“乐在其中”,工夫与本体合而为一,心即理,理即心,“圣人之心,直是表里精粗,无不昭彻,方其有所思,都是从这里流出,所谓德盛仁熟,‘从心所欲,不逾矩。’”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31,第599页。“盖形骸虽是人,其实是一块天理,又焉得而不乐!又曰:‘圣人便是一片赤骨地立底天理’”,③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31,第599页。颜子虽然有近圣人之气象,面对“一箪食,一瓢饮”的贫困处境,一般的凡夫俗子自难寻得其乐,而颜子却能依靠心的修养,不改其生命本有的乐,但相较圣人言,则“未如圣人从来安然”,故曰:“不改其乐”,颜子之乐最重要的体现在实做的工夫上。人之所以不能有颜子之乐,朱子认为,就是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心身是分裂的,只是一味地满足身体的欲望,而没有注重加强心灵的修养,“如猫子狗儿相似,饥便求食,困便思睡。一得富贵,便极声色之娱,穷四体之奉;一遇贫贱,则忧威无聊。所谓乐者,非其所可乐;所谓忧者,非其所可忧也。”④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31,第599页。所以只有除去心中的私欲,便自有孔颜之乐。朱子曾在《延平先生李公行状》里对其师李延平的修养境界作过这样的描述:
若先生之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世,殆绝伦比。然不求知于世,而未尝轻以语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学者亦莫之识,是以进不获施之于时,退未及传之于后,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乐者于畎亩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将至。⑤朱杰人等:《朱子全书》第25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7,第4520页。
从朱子的描述来看,李延平应该是体悟到了孔颜之乐。所以,乐是一种超然于自我局限的道德境界,贫贱也罢,富贵也好,内心皆足以宽容以待,不仅不为其左右自己内心的坚守,还能享受坚守的乐趣。
孔子的学生子贡因货殖而积累了不少财富,并且不为自己的富贵而心生谄骄之病,这在一般人看来已经是很不错的坚守,子贡亦自得于此,并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来求问其师孔子的看法以期得到老师的赞许,孔子回答“可”,并指出一种更高的修养境界,即:“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也。”朱子释此曰:“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无谄无骄,则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贫富之外也。凡曰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好礼则安处善,乐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贡货殖,盖先贫后富,而尝用力于自守者,故以此为问。而夫子答之如此,盖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4页。不难看出,这种忘贫之乐是一种很高的道德修养境界,它是一种人在身处贫困时所自然产生的一种情感,不是一种人为的伪装。乐以忘其贫,心不为形所役而超然于形之外,修养不可谓不高!朱子曾经写过一首叫《春日》的诗云:“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①朱杰人等:《朱子全书》第20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第285页。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出,朱子对“孔颜之乐”已经有很深的体悟。孔颜之乐是人修养到一定程度后所自然显现的一种境界,不是人刻意去追求的一种快乐,如果刻意去追求,那就是将心与身作了分离。当朱子的弟子陈淳问怎样去求得孔颜之乐时,朱子教导曰:“这道理在天地间,须是真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彻,无有不尽,则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②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册卷31,第597页。
综上,朱子在理学的视域下,将先秦儒学的“孔颜之乐”提升为一种具有人生终极意义的境界,使人通过不断修养超越有形的生命局限以达无限的道德价值之域,以此安顿人的心灵,实现人性彻底的复归。孔颜之乐是人之仁性与天地之生理合一而显现的一种自然之乐。这在当时应对佛老从一个外在世界来寻求心灵的超脱有本质的不同,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儒力图在日用伦常的生活世界中为人们建立起一个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以成就一种理想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