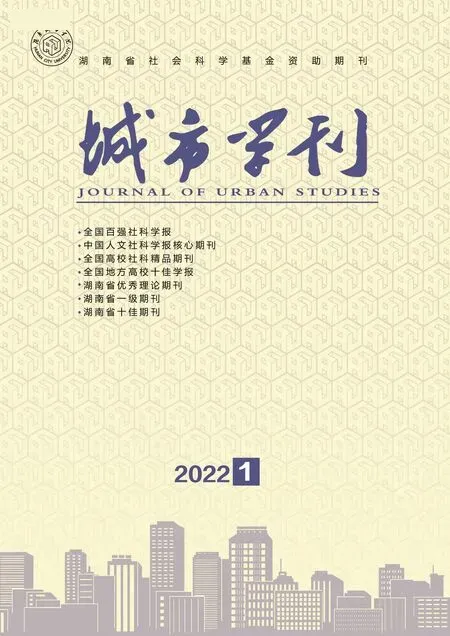黄永玉新型小说创作理念的建构
——论《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的艺术创作观
杨景交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教育学院,湖南 永州 425000)
“艺贯中西,肆意人生。耄耋顽童,痴狂大师。”[1]1这是画家黄永玉留给世人的自画像。他的前半生,在美术的世界画人间百态,后又在其年迈之际,坚持创作了长篇巨著《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这部小说自2009年在著名文学刊物《收获》上连载,因其独特的行文结构,瞬间引来中国当代文坛诸多人士的“围猎”。文学研究界对此议论纷纷,褒贬不一,有人赞之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买账者亦是层出不穷。这部小说一经刊载就陷入毁誉参半的尴尬窘境,其根因在于耄耋老人黄永玉放荡不羁的新型小说艺术观。
一、文体的多重性——形色各异的朱雀浪荡汉
对小说(尤以长篇小说)文体的革新和实验,在1990年初至新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文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文体革新的思潮上,出现了马原、格非、洪峰等人的“叙事圈套”的先锋派小说思潮,池莉、刘震云、刘恒等人的“一地鸡毛”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思潮。在作家个体的创作上,则有韩少功的词典体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有莫言的书信体长篇小说《蛙》,有王安忆的纪实体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有王蒙的“拟辞赋体”长篇小说“季节系列”等繁杂的小说文体革新实验。追求多变的小说文体范式,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们创作小说的共同意识,这显示出中国新世纪小说文体革新的重要性。
黄永玉于 1990年代开始构思创作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在文体上也展现出他随性而为的新型艺术理念和革新精神。这部小说在文体上具有多重性,无法以传统长篇小说的创作原理予以打量。小说兼具了人物传记类文体的纪实性、散文文体的自由性、小说文体塑造人物典型的艺术特质,突出体现在黄永玉对小说庞杂人物形象群的处理上。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这部长篇小说共计70余万字,共出现约90个人物。面对庞杂人物形象群,黄永玉不同于传统长篇小说的创作思维,他似乎放弃了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在叙事上的虚构性与紧凑性,转而投向传记类文学的纪实和散文文体的随意的怀抱。一方面,小说中出现的大部分人物,都切切实实参与了黄永玉的前半生,整部小说可以说是作者在追忆自己那逝去的似水年华;另一方面,小说中许多人物命运的变迁,也没有得到清楚的始末交代,人物的出场都是按照自然的方式出现,然后又以自然的方式在小说中退场,就像创作者在与人“负暄琐话”。小说的纪实性和随意化的多重创作倾向,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它是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既定事实。
那么,《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杂糅纪实文体和散文文体的嫌疑,是否又真的说明黄永玉消释或放弃了作品是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呢?其实,黄永玉粗暴的人物出场方式,并没有损坏这部作品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艺术特质,他的创作依然实实在在遵循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注重塑造人物典型性的艺术规律。面对朱雀河上形形色色的浪荡汉子们,黄永玉充分发挥画家的艺术敏感性,在同一单位时间内勾勒出每个朱雀人身上的特性,每个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朱雀人。
如小说中作者对朱雀城里“朝”神这一人物形象群出场的布置:对羝怀子、老祥、唐二相、萧朝婆、“侯哑子”等“朝”神们的处理,作者直接以照相式的方式在小说中依次出场。不过,小说中的每个“朝”神又有着异于常人的地方,他们都是朱雀城里独一无二的“朝”神。如具有文人忧郁气质的羝怀子,“他永远的自我忧愁,头耸着胸脯往前蹿。”[2]打更的唐二相对中国文学有独特的领悟力,别人以挑逗的方式说:“二相作诗了吗?”[2]251唐二相“——摇头摆尾踱方步……啊!学堂女学生随侍着……啊!白话文诗比文言诗难做万倍……”[2]251其中,还有善妒却不乏善良的萧朝婆、隐藏在民间的真正艺术大师“侯哑子”等都是朱雀城里形态各异的“朝”神。
又如小说中的雅士人物形象群,在张幼麟、序子二舅、韩山、段一罕等“雅士”的身上,承载着朱雀人特有的文化内蕴,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和传承者。小说中的张幼麟是作者倾注较多笔墨的人物,“雅士”张幼麟近似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零余者”,他时时刻刻都透露出一股现实的苦闷情绪。张幼麟对艺术和音乐有着无限的热爱,但在现实中找不到支撑自己艺术理想的基点。他困于现实生活的物质压迫,最终不得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我早到上海就好了。我舍不得朱雀,舍不得沅州,舍不得这条河,舍不得桃源、常德……现在好了,一屋人,不要再讲‘走’了。”[2]695“上海也不是什么好地方,要熬,熬十年,八年,二十年,不一定熬得出名堂来,万一……怎么办?一屋人在等我,嗷嗷待哺……”[2]695虽然,张幼麟的艺术与音乐理想随时都遭受着现实的捆绑,而那渗透进他骨子里的文人雅士气质,却是无法磨灭的。作者借此人写出了朱雀城里“张幼麟们”这一群体的普遍生存现状:身处美好理想与残酷战争现实相交织的尴尬处境。小说中序子二舅,可用“文痴”一词予以概之,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近乎痴狂。序子二舅在小说中似乎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天才式的敏感。他渴望与别人谈论中国古典诗词,但现实没有给他遇伯乐的机会。于是序子二舅把年幼的狗狗当成自己的文学知音,他强烈渴望将自己的中国古典诗词库倾吐给他。序子二舅形象的深层内蕴是作者对如何延续中国传统文学生命力的深入思考。
还有,小说中刻画的王伯、柳惠、幺舅娘等朱雀城女性形象群,她们拥有湘西传统女性坚韧、豪气的人性之美,散发着生命个体的特有魅力。其中以王伯这一人物形象的描摹为最甚。“在‘无愁河’第一部中,王伯是作者着墨最多、所占篇幅最长、最光彩浑沉、最感人也堪称戛戛独造的人物。”[3]在王伯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生命个体复杂性的领悟,“王伯这婆娘是个假乡里人,又是个假城里人。”[2]334王伯的一生经历了生活的凄惨,却依然怀抱希望,她对生活的苦难有自己应对的状态。“王伯从没讲过后悔当女人的话。各人有各人的衣禄。一个人活得有没有仪派是不论男女的。”[2]393于她而言,人生的苦难是无可奈何的,人不应该去怪罪生活,而应该以坦然的方式主动化解生活的不公。“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的受苦人相比,王伯这个人的光彩来自哪里?来自,她不是被动之‘物’,她是一个‘人’,一个‘深深自省’的人。”[3]165王伯身上素朴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作者对朱雀城“王伯们”的赞颂。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在文体上呈现出多重特征,表面看似掺杂了人物传记类文体和散文文体,但作品的实质还是根植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相关艺术特质。作者在文体创作上的多重性处理技巧,既避免了由于人物形象刻画过多带来文本内容的枝蔓太多而造成小说最后难以收拢,又刻画出了每一个朱雀人身上的特性。黄永玉在长篇小说文体上不拘束的艺术革新理念,何尝不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文体创新过程中的一次成功实验?
二、结构的静态化——浓烈深重的朱雀情
在学术界,《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一经发表,研究者便形成两极分化的状态。这部小说在著名文学杂志《收获》上连载时,受到学术界一些学者如韩少功、张新颖、李辉等人高度称赞的同时,也遭到了许多读者的无情批判。“《收获》从二〇〇九年开始连载这部作品,连载了五年,‘浪荡汉子’才走出故乡闯荡世界。据说非议不断,有读者宣布,一天不停止连载,一天不订《收获》。”[4]76“《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部奇特的小说,自连载以来就争议不断,爱不释手者有之,弃之一旁者有之,还引起众多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的解读。”[5]“在《收获》博客的留言里,不少读者抱怨《无愁河》的连载没完没了。‘建议黄永玉的狗狗尽快长大,别看了一期又一期,还是狗狗长狗狗短的,多没劲呀!’‘《无愁河》最大的缺点是太没有长篇的那种节奏感!整个故事一点没有吸引人的地方,情节推动也缺少张力。《收获》杂志的大编辑们,不知为何要顽固地登这种东西?”[5]读者对这部小说产生无所适从的阅读体验以及发出的相关争议,主要是源于这部小说散漫的文本结构。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本应讲究文本结构的谋篇布局,讲究故事的紧凑性。但黄永玉并不囿于传统长篇小说常规化的创作模式,他在创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时,抛却小说文体对结构的考究,整部小说如散文随笔一般自由散漫地书写着笔下的故事。黄永玉没有老老实实地遵从一条紧密的行文线索,去构筑起整部小说的逻辑框架。小说的行文结构可以说是毫无章法可言,抒情、议论、叙述视角等任意切换。小说故事的设计也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一切都随着创作者的心性而定。那么小说行文结构的“随意”化,是否真的是因为黄永玉是文学的“圈外人”呢?在黄永玉心里,文学与画画一样,都是他生命之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黄永玉之所以会选择无拘无束的创作方式,并不是他不懂文学艺术,而是因为“与其说这部作品写出来要面对‘读者’,不如说是要和故乡人说说故乡。”[4]75故乡思维的设定,也就注定了《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这部小说的创作不会为了迎合精致的小说结构和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有意删掉小说背后的朱雀历史和作者浓烈的故乡情。创作者舍弃传统长篇小说强调文本故事的紧凑性与情节环环相扣的艺术创作理念,其出发点只是为了更加自由地向外界传达出他蕴藏在小说深处的朱雀情。
恰如中国现代作家陆文夫在《漫话情节》一文中谈及长篇小说情节叙事时指出的:“也有一种作品,它不写什么环环紧扣的故事,避开大起大落的情节,着重人物、生活、意境和心理描写,像清溪流过山林、乱石和草地,真实、诚朴而优美。”[6]408相对于许多的传统长篇小说为构拟故事性强的情节,创作者多会通过时间线的明确移动来串起整个小说文本紧凑和完整的结构,在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的叙述进程中,时间似乎一直都处在一种缓慢甚至静止的状态,70多万字的小说容量没有随着人物命运历时性的变迁而得以逐层推进。黄永玉故意对小说的时间线作静态化处理,在缓缓的时间进程里展开小说的故事情节,主要是为了让朱雀城的民俗民风在静态化的时间里得到共时性的呈现。整部小说在娓娓道来的平缓语调里,让作者和读者得以惬意地徜徉在那满溢着湘西民俗风情的朱雀城里。
在小说静态化的时间域里,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作者对朱雀城风俗习惯和朱雀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横切面式描写,如对舞狮子、布口袋等湘西民俗的叙述,还有对朱雀城中每一条街道上人们的生活风貌进行不厌其烦的叙述。如小说对王伯到木里“赶场”情节的描述,在作者简单的语言叙述中,整个木里场上人们的日常赶集生活场景跃然纸上。作者通过王伯的视角,自己似乎也回到了小时候木里“赶场”的热闹场面。作者用静态的时间方式让朱雀城的民俗民情在小说中展览开来,更能体现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我写得很慢,因为我是老老实实地写,没有随意删改,我要把所经历的每个时代与社会的各个侧面勾勒出来。一些年代久远的事就让笔触随着记忆逶迤而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写多长。”[5]作者一开始构思和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在于以故乡思维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故土深沉的爱恋和怀念之意。因为故乡在黄永玉的心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一再强调故乡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重要性,“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7]153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并不是为了创作小说而进行小说创作,它更多的是一位耄耋老人对自己故乡人、事、历史、文化的缅怀。作家韩少功在《黄永玉的百年悲悯》一文中指出:“可以肯定,一个二流作家也能把这些局部处理得更‘专业’,但这个作品独特而丰富的生命质感,还有巨大的艺术创造能量却是众多一流作家也难以企及的。作者天马行空,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投入了一种另类的、狂放的、高傲的、藐视一切文学成规的写作,大概一开始就没把‘专业’太当回事。”[8]在小说看似散漫而不逾矩的行文结构之下,其实是作者用惊人的记忆力,挣脱小说文体的规范性,故意放慢小说的时间进程,在对故乡的无限想象中还原故乡的风貌,由此展现半生漂泊异乡之人对故乡文化、故乡人、故乡景、故乡历史的思念之情。
三、语言的内蕴性——饶有意味的朱雀民俗
学者李辉在《传奇黄永玉》一书中谈到黄永玉的文学语言艺术,“‘营造汉语之美’,让人们看到了他如何摆脱文字的政治性污染,还原语言本色的纯粹、鲜活,贴着土地生长,在空气中自由呼吸的那种优美。”[9]470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中,无论是对中国古典式语言的选取,或是对中国现代白话的运用,还是对湘西方言土语的穿插,黄永玉都洗去了汉语的空洞玄乎,而复归一种朴实与简单的语言叙述策略。他尤为注重增加文本语言的内蕴性,致力于用生活化的语言艺术构建起一个满溢着湘西民俗风情的朱雀城。
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对每一个日常生活场景的语言描写,都是一次饶有意味的文学语言盛宴,小说的语言“拒绝一切平庸的过度开采的成语和俗语,作者用充满趣味的方言,典雅的古诗词品评,色泽温润的民国遗风遗调和粗话野话市井大白话,混合成一个语言嘉年华。”[10]如小说对朱雀城人“过年”这一传统节日的语言叙述:首先,作者运用“过年”这一简单的短语开始了朱雀城忙碌而盛大的节日,然后,又在平白如话的素描中,对朱雀城“过年”习俗里的一些庆祝活动作朴实无华的文字叙述。其中,尤以对朱雀城“玩狮子”这一习俗的细致描写最为精彩。作者既有对“玩狮子”这一朱雀习俗的知识性介绍,又注意延展至习俗之后的朱雀文化。朱雀人“玩狮子”,是朱雀城过年的一种组织形式,隆重而壮观,它是朱雀城的一种文化象征,是源远流长的朱雀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朱雀人眼里,它“不轻佻,不浅薄,不媚俗,远不止提供欢乐,热闹这么意义简单。它影响人的一生,一代又一代。”[2]195朱雀人对“不轻佻”“不浅薄”“不媚俗”的“玩狮子”习俗的尊崇和延续,是他们为保存朱雀城民俗文化的共同努力。最后,作者还由“过年”这一习俗联想到习俗背后所承载着的朱雀城的战争历史文化。“战争时期,对双方指挥来说,‘过年’是个‘息怒’的‘暂停’。太平年月,老百姓把破坏了的民族庄严性质用过年的形式重新捡拾回来。抚摸创伤,修补残缺。所以,过年是一种分量沉重的历史情感教育。”[2]195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中语言的内蕴性,还表现在对一个个色彩斑斓的生活场面作哲理化思考。如小说中对狗狗离开木里时的语言叙述:在狗狗离开木里的那段文字描述中,作者一是避免文学的矫揉造作与舞文弄墨之嫌,整段话散发出无限的童真之味。作者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撷取了一段再平常不过的人物对话场面,通过现代白话和湘西方言土语相互交错的方式,去揣摩小孩子心理的微妙变化。二是作者在人物日常的对话中又穿插了很多耐人寻味的语言,使日常的闲语得以文学化。如,“这两人一辈子就这样分开了,他两个哭得多么词不达意……离别的语言‘天籁’得很。”[2]447这句话看似简单平坦,实则内蓄着语言所指的爆发力。一方面,这段语言间接衬托出朱雀城看重人与人之间朴素而真挚的和睦关系;另一方面,创作者用“词不达意”来形容人哭得伤心的程度,具有一定的新意,它虽无句子语序结构的正确性可言,却极富日常生活的画面感。三是作者通过切换叙述视角的方式,抒发自我对历史这一概念的认识。恰如小说中所写到的,“日子一过就成历史。留给你锥心的想念,像穿堂风,像雷,像火闪。世上没一个回忆是相同的。之所以珍贵,由于它留不住……”[2]447作者认为每个现实生活中的生命个体都在历史性地生活着,随时随地都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与在参与着别人的历史,于是人才极其容易产生对过往历史的怀念之意。
小说中关于王伯和“芹菜”在溪里洗澡时所述的语言,一样具有深意。“芹菜”为表达在溪里洗澡舒适时所说的话,背后蕴含着朱雀城女性对个体生死轮回的哲理性体验。“你看这四周围山,树,这水,那天,那云,雀儿叫,太阳,世界要是这样,都忘记了,都不牵挂了……一辈子不怕冷,不饿,没人打我,骂我,不生儿,不养女……”[2]380“芹菜”用以表情达意的语言,虽然没有精美的文辞修饰,是乡下人最普通不过的语言,却让人读出了朱雀城“芹菜”们身上所特有的诗性美。这段话,不仅写出了朱雀女性对美好生命状态的向往之意,还侧面写出朱雀城女性对诸多生活苦难的隐忍之力。
对黄永玉而言,“文学是他永远排在第一位的行当。”[11]54他认为文学“有文字语句的讲究,有上下句音韵的节奏,有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酝酿出来的那种情调和气氛,它不能光是讲故事,它要进入情境进入角色,要集中精神,鸦雀无声地促涌出来。”[12]229在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的创作过程中,黄永玉凭借自己对文学艺术的感悟力,敢于创新小说艺术理念,颠覆传统长篇小说艺术的创作范式,并成功地建构起了自己的新型小说艺术大厦。韩少功称赞这部小说,“总体而言这部作品已是堪比《百年孤独》的一大文学收获。”[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