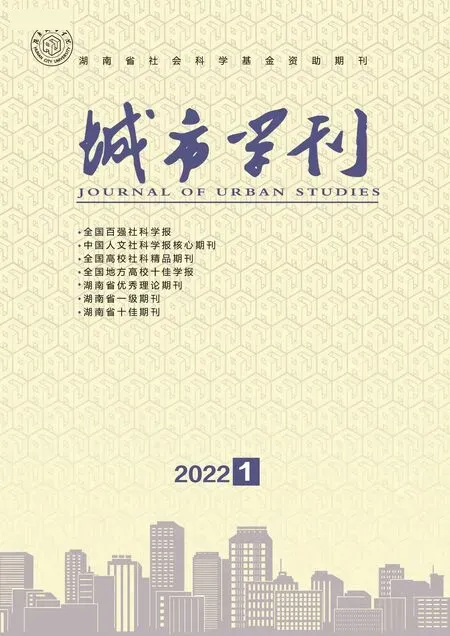冲突与融合:杨昌溪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革命话语
龚敏律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杨昌溪(1902—1976),四川省仁寿县人,早年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并短期留学日本。他在抗战前后曾担任《贵州日报》总编辑、《幸福报》主编。杨昌溪著有《鸭绿江畔》《三条血痕》《给爱的》等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黑人文学》,也译介了大量的外国作品和理论文章。杨昌溪的文学活动和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引人注意。目前有关他的学术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学者韩晗的《重读〈刀“式”辩〉及其它——以杨昌溪早期文学活动为中心的史料考察》,[1]另一篇是董小希的《国家、种族、阶级:〈黑人文学〉与“哈莱姆文艺复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2]前者可以说是对杨昌溪这位名不见经传,甚至被后来的研究者刻意遮蔽的作家的“正名之作”。韩晗通过大量的史料回答了他所预设的三个问题,一是鲁迅之所以批判杨昌溪“涉嫌抄袭”的深刻原因,二是杨昌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三是杨昌溪的翻译工作和报告文学创作为中国新文学史添加了什么样的丰富内涵。后者则是从翻译学的视角对杨昌溪所写的学术著作《黑人文学》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其中谈到杨昌溪对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关注和思考,还是进一步丰富了杨昌溪作为著名翻译家、知名学者的形象建构。这篇文章应该是对韩晗所提出的第二、第三个问题的有力补充和声援。
笔者也试图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历史文化语境,来思考置身于20世纪 30年代的上海都市革命话语场域中的杨昌溪,究竟为这一历史阶段的上海都市革命话语添加了怎样的精神内涵以及提供了哪些独特的个人思考?它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它的历史局限性何在?笔者的这些思考其实也是对韩晗在他的那篇大作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的呼应和补充,即对于杨昌溪的进一步研究,可以为中国新文学史丰富新的思想内涵。
一
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空间呈现出丰富驳杂的精神面相,各种文学力量和政治派别试图在这个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国际性大都市里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抢占文化的生存空间和强大的话语霸权。尽管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背后代表着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或者多样的文学观念,但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即被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红色革命文学话语或多或少的吸引,从而把自己想象并置于历史进步方向的一端。也就是说,无论是上海都市文化空间里的左翼还是右翼作家,或者是无党派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他们在这一个历史阶段所创办的刊物和从事的文学实践活动,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苏联、日本以及欧美等国家的红色革命话语的影响,从而使得他们浸润在这种革命话语之中,从积极或者消极的层面对30年代上海都市革命话语论争场域提供了多维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思考。
杨昌溪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空间里,有着多重社会身份和文化角色。杨昌溪早年曾留学日本,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这所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全英语授课的学校,也是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享有“东方哈佛”之称。正是在这所开时代风气之先的高等学府的求学经历,使杨昌溪个人的学识和素养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可以说,他毕业以后成为翻译家、自由撰稿人、作家、学者,这些社会身份和文化角色都离不开圣约翰大学为他打下的坚实基础。杨昌溪走入社会以后,据相关的研究者张宝林考证,1930年6月南京成立了线路社,杨昌溪是其主要成员。杨昌溪还曾参与或者追随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与许多有国民党背景的文人交往甚密。[3]但是,韩晗也在他的大作里面谈到杨昌溪“与一些知名左翼作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在一九三一年,他与左翼作家胡风(署名张光人)共同完成了评述类文章《太戈尔的近况》并发表于《青年界》第1卷第1期。”[1]无论后来的研究者如何界定或者评说杨昌溪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角色,从杨昌溪30年代在上海都市革命话语场域中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到他并没有依附于任何党派和政权,有着自己的独立人格意识以及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度思考。杨昌溪在这个历史阶段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在思想观念上也是有着明显的进步色彩。这首先表现在杨昌溪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红色30年代”革命思潮的翻译和介绍的活动之中。
《现代文学》于1930年7月创刊于上海,主编是赵景深,这是一份博采众长,无论普罗文学、新写实主义、新感觉派还是古代的文学都可以刊发的纯文艺刊物。杨昌溪在这份杂志的第1卷第1号就刊发了一篇文章《“哥尔德论”——美国的高尔基》。这篇文章开篇就对哥尔德的文学身份进行了界定:“哥尔德(Miohael Gold)是美国现存的青年无产文学家,他的‘120Millions’已经译成了中文。在新兴的作家中,他是最活跃而最接近民众的一个;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真实的,活跃的无产作家。”[4]其次则是大力介绍哥尔德对工人文学的建设以及如何建设。另外,文中也分析了哥尔德的具体创作方法。最后,作者对哥尔德这位被人称誉为苏联高尔基的无产阶级作家进行了高度的赞美和肯定:“被人称为巴比塞高尔基的哥尔德而今正偏重工人文化的开始,他的努力的深入实生活,是比辛克莱更勇猛,比费边主义者萧伯纳之群更伟大。而且在事实上他几乎取得了超过辛克莱地位的声誉和信念,与那工人们崇拜的高尔基遥遥相应,在资本主义气焰高涨的美国为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开放着灿烂的花朵。”[4]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杨昌溪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尤其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家哥尔德的熟悉程度。杨昌溪似乎对美国无产阶级作家哥尔德特别感兴趣,因此在1930年第1卷第5期的《现代文学》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哥尔德的作品《无钱的犹太人》又获得了好评,并对他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哥尔德在无钱的犹太人中由同情的启示已经发出了一种控诉,虽然是一种由小孩心理所形成的控诉,但在本书结局处已经说:‘你把工人底革命给我这一个孤独的,自戕的孩子带来了。你是真实的救主耶稣。当你来时,你要破坏东边区,而且建设一座为人类精神的花园……是对于未来有了启示。’由这些批评,我们可以认识哥尔德之伟大而同时对于无钱的犹太人也可以窥见他底价值之一般了。(附注:无钱的犹太人已由我与洛夫译出,社会的落伍者也由我与钟英译出,不日出版。)”[5]
杨昌溪在1930年第1卷第1号的《现代文学》还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雷马克的续著及其生活》。雷马克是德国左翼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是《西线无战事》。雷马克以反战文学而蜚声国际文坛,也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正如杨昌溪在这篇文章开篇就指出:“在一九二九年度中轰动全世界文坛,抓着全世界读者的心使他们战栗,使六架印书机和十架装订机为一部小说而忙碌,压倒战事小说中的巴比塞、杜哈美尔(Duhamel),赖兹珂的人是谁?那便是不到半年间全世界已销上二百万本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候补者,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的作者德国青年军人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了。”[6]雷马克不仅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在中国国内文坛也备受重视。短短的几年时间,这本《西线无战事》竟然出现了四个中文译本。此外,雷马克的另一本小说《战后》,其实也是《西线无战事》的续著,于1931年在德国出版了,小说也很快引起了我们国内翻译家和学者的注意。一共有七个中文译本,其中就包括了杨昌溪和林疑今合著的《西线归来》。杨昌溪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现代文学》杂志上能够发表有关雷马克的评论文章,可见他的知识视野是相当开阔的,能紧紧把握住世界最前沿的文坛动态,应和世界文学发展的最新潮流,从而使得西方这股以雷马克、巴比塞等为代表的非战文学潮流能敏捷迅速地传入上海的都市文化空间。
杨昌溪在这篇评论文章里面引用了雷马克自己的创作谈作为论述的例证,其中有一个例证是关于雷马克对于新世纪美国文学作品的评价。文中写道:“尤其是最后一本使我永不能忘怀,新兴的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无产阶级方面的小说史描写得很有力的。关于哥尔德(Mochel Gold)据说也是与辛克莱和杰克伦敦同时以描写无产阶级文学闻名的,只自恨我的英文程度不好,不能去鉴赏,以后我要努力。”[6]从雷马克的这段话,我们还是感受到那个时代具有进步色彩的雷马克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憧憬和向往,有着向左转的内在精神契机。杨昌溪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是相当勤奋的年轻翻译家,他能够把 20世纪 30年代最具进步色彩的德国作家雷马克的相关情况介绍给国内,并且也并不避讳雷马克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亲近之意,这也是他作为翻译者在思想立场上具有进步革命的一面。
杨昌溪除了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有关哥尔德、雷马克的评论文章之外,还在1930年第1卷第3号的《现代文学》杂志上刊发了一则有关法国准备刊行全世界革命诗歌集的消息。文中写道:“法兰西无产作家雷麦(Tristan Remy)等觉得在普罗文学运动,诗歌很占重要的地位,而各国的革命诗歌与普罗列塔利亚特诗歌已有极丰富的收获,决定短期内将各国关于这方面的诗歌集印一册。关于美国方面之材料收集,一面征求无产作家哥尔德(Michael Gold)之诗外,并由哥尔德介绍新群众(New masses)杂志诸作家之作,对于黄种黑种之诸作家作品均托哥尔德介绍和搜集。”[7]杨昌溪还在这一期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是有关英国工人的戏剧运动:“在工人主持的工人剧院运动(Workers theatre movement)已第一次将加里士(Goe Corries)底在争斗时(In time of strie)底第二幕改为独幕逆贼(The traitor)上演时,很能强烈的把英国早年煤矿总罢工时工人的生活情形表出。”[8]杨昌溪还在这个杂志的第6期上发表有关日本剧场出演美国新兴戏剧的消息:“日本新筑地剧场为现今日本唯一活动的左翼剧场,自一九二九年五月创立以来,曾出演过二十部著名的戏剧,如高尔基底母亲,伊凡诺夫底铁甲车(The Armoured Train)雷马克底西线无战事,杜里牙柯夫(S.Teriakov)底怒吼罢,中国关地藤丸底突起。这剧场最近已与美国新兴文学运动诸人取得联络,对于美国新兴文学产品的销路因为他们的介绍已得着非常的突跃。”[9]杨昌溪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的这些国外左翼文坛消息,也是符合这份杂志的求新求异的办刊宗旨。杨昌溪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对国际上的这股左翼革命文学潮流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和积极的姿态,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杨昌溪不仅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数篇有关苏联、日本、欧美的左翼文学思潮的文章,也在《读书月刊》上发表了相关的文章。《读书月刊》也是没有任何党派色彩的综合性刊物,1930年11月创刊于上海,由顾凤城主编,主要偏重对国外书籍的译介,也刊登中外文学作品、作品评论、作家论等。杨昌溪在1930年第1卷第1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谈到的是他一直关注的美国左翼作家哥尔德。杨昌溪在文中写道:“从这种评价,我们可以认识哥尔德的伟大和他底作品一亿二千万和无钱的犹太人的名贵了。更是他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新兴文学运动主潮的重要人物,所以,由苏俄革命文学国际局今年十月召集在卡柯夫(Charkov)集会的世界革命文学家会议,在美国被邀请的代表便是他和拔苏士(John Dos Passos,)格拉卜(William Gropper)等,这样,更可以看出他在美国新兴文学中的重要了。”[10]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杨昌溪对美国新兴的左翼革命文学运动也是十分熟稔,这也是他受到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红色30年代”思潮影响的产物。
同样,杨昌溪还在1930年第1卷第1期的《读书月刊》上继续关注哥尔德以及他领导的工人间的文学与艺术运动。他指出“美国工人间的文学与艺术运动,自从新群众属下的哥尔德(Michael-Gold)和他底同志们加以努力后,文学与艺术在工人间已有特别的地位,而且新群众与其他同性质的日报等等成了工人间唯一的普遍读物。所以美国工人方面的文学宣传,此刻已达到了尖锐化的领域。他们在哥尔德等领导之下,很能认出新兴阶级的观念形态,把他们从资本主义下所接受的经验在文学上加以尖锐的表现。最近麻省纽·柏德甫德的织工组合为纪念他们罢工胜利的周间计,曾在纪念日出演戏剧‘一个工人底生活’(The life of a worker)这剧的目的在描写旧日典型的工人透过暴乱与斗争的生活而进为革命组合的一员。很能深切的刻画出工人们在实际斗争中的演习,使他们渐渐的由实际的体验而认识了革命。”[11]这段有关美国左翼文坛的消息,还是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杨昌溪作为美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如此迅捷地传播以哥尔德为中心的美国工人之间的文学与艺术运动,并敏锐把握这些运动的革命性质,这也显示了他在30年代对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文学运动的理解与同情。
二
杨昌溪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空间里面,不仅积极译介和传播世界范围内的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相关消息和作家作品,同时也表现出对世界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和文学动态的热情关注。杨昌溪在1931年第16期的《橄榄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黑人文学中民族意识之表现》的文章。《橄榄月刊》于1930年创刊于上海,也是一份没有任何党派色彩的综合性刊物,重视文艺批评与政治理论文字,刊登的文章大多与上海都市生活以及流行的社会思潮相关,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杨昌溪在《橄榄月刊》发表的这篇文章,主要探讨黑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问题,这其实是与30年代上海的都市革命话语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兴盛有着密切的联系。1930年6月1日,朱应鹏、范争波等人在上海成立前锋社,同年6月29日、7月6日在《前锋周报》第2、3期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正式发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先后出版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与《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这些刊物分别于1930年6月、1930年10月、1931年4月在上海创刊并发行。前锋社的产生是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和历史背景的。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形势来看,国民党的政权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呼声越发高涨,这也使得国民党的部分官员和旗下的文化人试图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来维护当局的统治利益,同时也试图用这种文艺精神提升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从而从思想文化的层面为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思想主张一开始还是具有进步色彩和革命意义的,也因此得到了定居在上海的众多文化人的支持和拥护。孙俍工、汪惆然、叶秋原、傅彦长、陈抱一、陈穆如等人就是其中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他们大多是上海一些高校的大学教授、编辑、自由撰稿人。杨昌溪当时也是定居在上海,他应该是受到了上海文化圈这些朋友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也对当时带有进步色彩的民族主义文艺有所向往和期待,因此在这场运动开展的第二年就发表了这篇有关美国黑人文学与民族意识之间关系的文章。
杨昌溪首先对近现代黑人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进行了评述。第一个阶段的黑人作家在表现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主题时还是表现比较平和,但是第二阶段的黑人作家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开始走向了激烈的状态,也为未来的黑人文学开拓了新的时代。杨昌溪在文中着重对第二个阶段的代表性黑人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评述,他谈到了麦克开、突平、沃特、浮色德、波依士、淮提等黑人作家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表现了美国战后解放黑奴以及黑人如何受白人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并决意反抗的思想主题。杨昌溪由此得出了一个有力的论断,即“现在,在黑人的诗歌和小说中,已经抛弃了白人所给予他们‘奴隶教养’的实惠而走到了民族觉醒的一点。”[12]杨昌溪还引用了美国无产派批评家卡尔佛吞的话语作为援引自我观点的例证。文中引用了卡尔佛吞的一段话语:“黑人文学的出发点的观点是民族的,而是为民族的自我而创作,为民族的痛苦而歌吟,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且黑人文学之兴起,将来会因着文学之成长而达到全民族的兴起。”[12]
杨昌溪不仅在上海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有关黑人文学与民族意识的文章,同时也于1933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一部研究专著《黑人文学》。这部研究专著出版以后,在上海的思想文化界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杨昌溪的这本书其实是以美国的“哈莱姆文艺复兴”为中心,对20世纪初所有重要的非裔美国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梳理和研究。他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写道:“美国的尼格罗人(Negro)是世界上最被压迫的民族,在过去百余年间非惟他们的祖国亚非利加洲被帝国主义者分割,而且几乎全民族都成了最终主人所有的奴隶。”[13]《黑人文学》这部理论专著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黑人的诗歌”“黑人的小说”“黑人的戏剧”。在这部著作中杨昌溪提及了美国黑人文学中一些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例如黑人诗人约翰·亨利、兰斯顿·休斯的作品。杨昌溪认为在亨利的诗歌中表现了黑人遭受白人资本家的疯狂剥削和压迫,又面临现代化大工业机器生产而导致失业和死亡的悲惨命运。杨昌溪也提到了黑人小说中的一些代表作,麦克开、突平、沃特等黑人作家都是他重点介绍的对象。他在介绍美国黑人小说的一些观点,与他在《黑人文学中民族意识之表现》一文中的观点有很多重合之处。
杨昌溪关注美国的黑人文学,同时也对欧洲其他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发展有着一定的关注和理解。3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空间里,无论是左联领导的普罗革命文学运动,还是国民党引领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抑或是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创作,这些文学运动中总是离不开对世界弱小民族国家的独立与解放的关注。这种现象的发生具有复杂的历史文化成因。中国作家对世界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关注其实也有某种内在的精神投射与认同以及外在的精神诉求与呼唤。中国作家试图在对这些国外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译介之中寻找一种果敢勇猛的民族精神,呼唤中华民族的觉醒与独立。正如化鲁在1934年《文学》杂志第2卷第5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世界的弱小民族及其概况》的文章所指出的:“现世界还有在苏联,民族问题,获得正当的解决,苏联各民族在联邦制度之下,经济文化,都有平等自由发展的机会。此外的各民族,都在帝国主义的直接间接宰制下。除了苏联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外,全世界二十万万的人口中,就有十六万万的弱小民族。”[14]由此可见,1933年创刊于上海的《文学》杂志对世界弱小民族问题的关注也是相当深入的。可以说,在上海的都市文化空间里,无论何种政治背景的报刊杂志,其中不乏一些对波兰、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阿根廷等国家的文学作品的译介文章,带有鲜明的革命反抗精神和进步色彩。
《现代文学评论》杂志于1931年4月创刊于上海,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成员创办的刊物,主要宣扬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杨昌溪早在1931年第1卷第1期的《现代文学评论》杂志上就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匈牙利文学之今昔》。文章开篇写道:“欧洲的机器工业勃兴,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促成了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命。因此,每一个弱小民族赖以维系民族精神的小说,戏剧,诗歌,民间故事等都伴着民族独立运动而兴起了。……所以,在十九世纪的匈牙利文学也经显示它独特的精神,产生了不少的作家。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初期到十九世纪末叶的几十年间,而能作为诗歌和小说的代表的,却只有小说家摩尔(Jokal Mor 1825-1904)和诗人皮托非(A.Petofe 1823-1849)两人了。”[15]杨昌溪在介绍了摩尔和皮托非的作品以后,又对 20世纪匈牙利的莫尔纳,拉兹古、玛可维兹等作家作品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最后,杨昌溪在文中结尾总结道:“现代匈牙利文学在内容方面是注意于社会问题的分析,对于个人幸运的祸福,恋爱,精神等方面是不如从前一样的流行,这种思潮是伴着匈牙利农业奔溃而走向工业建设而兴起的,虽然在实质上没有如何的成就,假如再持之以恒,一定将来是可以成为匈牙利文学的主潮。”[15]
紧接着,杨昌溪在1931年第1卷第2期的《现代文学评论》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土耳其新文学概论》的文章。文中开篇就谈到数千年来土耳其作为弱小民族,似乎在世界文学中没有占着什么地位,也没有像阿拉伯、波斯那样产生过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但是新土耳其的建立和文字的革命,使得土耳其文学在世界文坛大放光彩。文章着重谈到了在民族革命尚未成功之前的土耳其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在文字上也受到了帝国主义者作为文化侵略工具的教会学校教育对其恶意的干扰的历史过程。[16]杨昌溪从这一历史文化背景来谈土耳其的新文学发展状况,强调了土耳其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
杨昌溪还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成员主办的《前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班牙的文学与革命》的文章。文中开篇指出,“西班牙最近的民主革命成功后,愈见得文学和革命的连锁性呈现出来了。”[17]杨昌溪还谈到,西班牙的文学家无论是否反对过西班牙的皇室,参加过实际的民主革命活动,他们的作品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却是异常紧密的,尤其是着重谈到了西班牙1920年12月的革命暴动,更是由西班牙的阿拉西、吉色提和玛拉朗三位作家鼓动起来的。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杨昌溪对西班牙的文学与革命做出了如下的论断:“从前西班牙人不相信笔有怎样大的力量,因为这次革命成功的前身是源于文学的宣传和鼓励,而在与帝制短兵相接时,又贵在与文学家们实际的斗争,所以说西班牙的文学是与革命大有关连,并不是空谈。”[17]
西方文坛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以战争为题材从而对其残酷性和荒谬性进行无情讽刺和批判的非战文学作品,并形成一股文学潮流。这股潮流在世界文坛显得相当耀眼和突出,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深切关注和集中介绍。尤其是在上海的都市文化空间里面,不同政治身份和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也投入了相当大热情来关注这股非战文学思潮。
杨昌溪在1931年第1卷第1期的《现代文学评论》刊登了一篇题为《雷马克与战争文学》的文章。杨昌溪在文中首先梳理了欧洲文学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出现了文坛上的两股对立的文学力量,一类是非战派,一类是讴歌战争派。杨昌溪对讴歌战争派的文学是带有批判的意味,但是对于非战派的文学创作,则是表现出了欣赏和肯定的态度。紧接着,杨昌溪还把雷马克与其他的欧洲非战派作家如巴比塞、罗曼·罗兰、拉兹古等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找出这些作家在具体的创作方法和艺术表达上的细微差异。最后,杨昌溪得出了一个结论:“所以雷马克的作品给人的紧张和兴奋,非惟比不上巴比塞的火线下,即是拉兹古的战争中所暗示的革命思想,也是西线无战事中所不及的。因此,狂热的读者盲然地把他认作无产作家,在雷马克本人是并未如此承认的;仅为了他写的是‘战争,一时代人的命运,和真挚的友谊,’三件要素,并不曾把他的作品作为此种控诉状,忏悔录。但是从艺术上说,仅以一个出身兵士的青年作家,藉着公馀的试笔便写下了一部惊人的作品;不由得他的狂热的读者们把他当作法国的巴比塞,俄国的高尔基,美国的辛克莱了。”[18]杨昌溪对雷马克与战争文学的论述相当睿智清醒,因为当时上海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有党派还是无党派,面对着西方所传入的这股带有正义和进步色彩的非战文学,他们也会情不自禁地结合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思考中国当时日趋紧张的国际形势和混乱不堪的国内政局,从而思考战争这头巨兽对国人和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惘然威胁。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下,杨昌溪在国民党所领导的期刊杂志上刊发这篇文章,介绍雷马克以及欧洲的非战文学潮流,并且把雷马克与20世纪30年代国际知名的左翼作家巴比塞、高尔基、辛克莱相提并论,从而表现出开阔的知识视界和不畏流俗的政治勇气。
三
如前所述,可以看到杨昌溪对世界范围内的红色左翼文学,尤其是欧美左翼革命文学运动以及黑人文学、欧洲弱小民族文学、非战文学等思想潮流相当感兴趣。这种兴趣并不局限于对这些文坛消息的关注和重要作家作品的译介,同时也融入了他对这些文学思潮的深度思考和独到见解。这也就能够丰富我们对杨昌溪本人的认知和理解,也能够在这些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中爬梳和提炼出杨昌溪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革命话语场域提供的独特思考维度和有益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探索了上海都市革命话语中的现实主义叙事的深度和广度。从倡导革命文学论争的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这场轰轰烈烈地在上海都市文化空间发生的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把自己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苏联以及日本的各种文艺观点的翻译和传播之中,也极力提倡文学是政治的工具这一口号,从而使得这些革命文学家对文学本身的艺术规律性和主体性缺乏足够的重视。针对上海都市革命话语的这种状态,上海一些纯文艺刊物开始加大了对苏联、日本以及欧美左翼文学作品的具体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的重视,试图纠正和扭转中国普罗革命文学运动过于重视文学的政治功能,把文学作为宣传工具的这种做法。这其中也包括了杨昌溪在译介欧美左翼作家作品时,不仅仅是停留在简单的翻译层面,更是从学理的层面对其翻译对象的一些基本创作方法和艺术特征进行了深入介绍与评析。例如,哥尔德是当时美国比较知名的左翼作家,但是在左联的机关刊物上很少有对他的专文介绍,只是在1932年1月3日的《文艺新闻》上发布了一则消息,其中提到了哥尔德。文中写到《世界革命文学》杂志的国际顾问有“巴比塞,格莱塞,哥尔德,高尔基,鲁那查尔斯基,柏苏士,棱·莎拉费玛维支,辛克莱等人。中国之郭沫若亦其中之一。”[19]但是,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作家那里,似乎大家对这位作家的创作特色更感兴趣。如前所述,杨昌溪也对哥尔德的创作饶有兴趣,不仅向中国读者介绍他的作品,更是从学者的视角来阐述和分析哥尔德小说的具体创作方法。杨昌溪把哥尔德称为美国的高尔基,并且指出:“为矫正单是用头脑去体验,每一个作家必定要属于一种工业。要投入那种工业许多时日,从各方面去体验和研究,使自己成为一个关于那种工业的专家,因此,当他描写那工业所包容或连带的一切时是一个内行的逼真的事实而不是如布尔乔亚们凭着头脑所幻想出的一种隔靴搔痒的考查。作家可以在罢工或有什么运动的时候作公开的活动,那样他才有由事实而培养成专家的力量的来源,我们要接近现实,决不要像费边主义者的作家们仅仅根据于他们所读的书来作为写论文写作品的材料。要每个作家彻底的对于一种工业有专门的知识和经验是在事实上可能的,生活愈丰富的人,在作品中也觉得更丰富。而且这样的人也可称为作家。”[4]杨昌溪这段话是对哥尔德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尊重事实,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的肯定。同时,杨昌溪也根据哥尔德的创作特色大胆提出了作家必须是关于那种工业的作家的看法,这也是对普罗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深入思考。正如杨昌溪所言,哥尔德对生活事实的观察和体验是远远比布尔乔亚们凭着头脑所幻想出来的一种“隔靴搔痒的考查”要更好一样,越是生活丰富的人,才能配得上作家的称号。这无疑是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革命话语体系中的现实主义叙事的深度探索和反思。
第二,对上海都市革命话语中的非战文学叙事提供了有价值的艺术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昌溪对上海都市革命话语场域做出的第二个贡献就是积极翻译并介绍了欧美文坛的非战文学潮流,并且促使这股潮流在上海都市革命话语场域之中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也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战争小说提供了借鉴的范本,从而加深了国内战争小说的思想深度。上海都市革命话语中的非战文学叙事主要受到苏联及欧洲的非战文学潮流的影响。这其中不可忽略的是欧洲的非战文学潮流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革命话语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上海各个阵营主办的期刊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欧洲非战文学作家作品的相关介绍,但是这些介绍大多只是一些零星的、印象式的文字说明,缺乏从更高的学理层面和艺术层面去探究其艺术魅力。在这些译介文章中,杨昌溪的文章显出了他思考的独特之处。杨昌溪并不仅仅停留在对欧洲非战文学的一般现象的梳理和归纳,更是从小说艺术的层面来思考他所欣赏的德国非战作家雷马克的创作魅力。杨昌溪在1931年第1卷第1期的《现代文学评论》撰写了《雷马克与战争文学》一文。文章开篇就指出在英国美国都有非战的文学出现,但是在价值和声誉上来说,都不及巴比塞的小说《火线下》,拉兹古的小说《战中人》以及罗曼·罗兰的小说《克莱朗饱尔》。杨昌溪认为罗曼·罗兰的《克莱朗饱尔》不像前两部都是描写战争之中的兵士心理,而是描写大战之中的智识阶级的心理。因此他认为罗曼·罗兰的这部小说不如前两部非战文学感人之深。紧接着,杨昌溪对巴比塞和雷马克的非战小说的主题思想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巴比塞的非战小说的伟大之处并不仅仅是暴露战争的罪恶和黑暗,而是通过对事实的昭示来指示人们一条永久的光明之路。雷马克的非战小说则并不是控诉战争,而是把侥幸从战争的死亡边缘生还者的一切经历写出来,指示人们要如何因此来消灭战争。最后,杨昌溪指出:“而且巴比塞作品中的主人公和他们的同伴却大半是智识阶级——平民。前者是被迫的去到战场,后者是爱国主义的热忱所鼓动;前者是有主义的,有思想的,有意识的,有教训的有出路的;而后者是无主义的,无思想的,暗示的,容忍的,浪漫的,灰色的,无意识的。所以雷马克的作品给人的紧张和兴奋,非惟比不上巴比塞的火线下,即是拉兹古的战争中所暗示的革命思想,也是西线无战事中所不及的。”[18]杨昌溪的这篇评论文章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他并不止于对20世纪30年代欧洲左翼文坛反战文学潮流的一些作家作品的简单介绍,而是从现象看到本质,从对比之中找出这股反战文学潮流中的不同思想和艺术的分支。杨昌溪对巴比塞和雷马克的小说艺术创作特色的异同辨析,可以说是为上海都市革命话语中的非战文学叙事提供了颇有深度的艺术思考。
第三,为上海都市革命话语中的民族主义叙事提供了自己的思考维度和创作范本。如前所述,杨昌溪对黑人文学以及欧洲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叙事作品的关注和译介,从某种层面上促进了上海都市文化空间中日益盛行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发展。这是杨昌溪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做出的重要贡献,也应和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有着时代的进步意义。
另外,杨昌溪在这股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潮流的影响之下,也热情地从事文学实践活动,创作了一部小说《鸭绿江畔》。韩晗在梳理和分析鲁迅与杨昌溪之间的那场笔墨官司的过程中,主要强调了鲁迅之所以批判杨昌溪创作的小说《鸭绿江畔》,是因为杨昌溪的《鸭绿江畔》涉嫌抄袭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根据韩晗在他文章中为杨昌溪的辩护,认为杨昌溪在这本小说中的一些对白尽管类似于鲁迅所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但这种“对白相似”并不能作为判定抄袭的铁证,应该说成是模仿或者戏仿。笔者也很同意韩晗的这一观点。小说《鸭绿江畔》主要讲述了一支靠近鸭绿江边的朝鲜游击队的故事。文中最精彩的是负伤战士张侠魂与当地一位名叫皮嘉善的老人的对话。老人皮嘉善的儿子死于战场,但他并不了解儿子为何而死,张侠魂解释说,老人的儿子是为朝鲜民族的革命运动牺牲,是正义的战争。
《鸭绿江畔》这部小说的主题在于澄清日本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鼓舞朝鲜民众为寻求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战斗。在这场解放战争中,个人主义的观念,罗曼蒂克的思想是次要的,一切以民族解放为第一要义。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虽然也是讲述的一支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但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是讲述从小资知识分子到布尔什维克的蜕变的革命小说,这部小说尽管也是写西伯利亚的游击队与日本干涉军和白军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并不是民族和国家的矛盾,而是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矛盾。这就是两部小说在思想主题上最为本质的区别。
因为鲁迅自己翻译《毁灭》这部小说的用意在于鼓舞中国的年轻人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专制政权中寻找精神的出路,燃起革命的斗志。杨昌溪的《鸭绿江畔》则是上海都市文化空间中兴盛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背景下的产物。杨昌溪的这部小说是借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来表现一种伟大又崇高的民族主义精神,从而呼唤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强大,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革命色彩。但是因为后来的民族主义文学阵营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公开诋毁和攻击中国左翼文学,一步一步地远离了他们最初倡导这场文艺运动的初衷,走上了历史的反面。这也就促使左联人士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偏见更加激烈,从而妨碍了对民族主义文学评价的准确性。正如张中良所言:“距离太近,本来就难以从容评断,加之强烈的政治激情与左翼的排他性,使得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不屑于多做考察,因而了解得并不全面,批评也仅限于左翼阶级论与苏联式‘国际主义’相交织的政治视角,这就不能不妨碍评价民族主义文学的准确性。”[20]鲁迅尚且如此,更何况左联内部的其他人士。这也是韩晗在他的大作里探究鲁迅之所以批判杨昌溪的“抄袭”事件更为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背景。无论杨昌溪的创作是在细节上的模仿或是戏仿,还是在主题表达上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同气相求,都会促使鲁迅以及其他左联人士对杨昌溪的这部小说有着一种厌恶和嫌弃之情。但是,也正如张中良所言:“1935年,左翼文坛重提“国防文学”,1936年,鲁迅、胡风、冯雪峰等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两个口号的论争并非几年前讨伐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那样的矛盾冲突,而是对建立怎样的民族统一战线意见不同,其中多少也掺杂了一点意气之争的成分。民族话语此前曾被左翼回避、曲解、甚至批判,而到了 1936年,却成为左翼的热门话题。对民族主义文学,左翼从激烈的否定到个体的参与再到整体的行动,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一演进,固然缘自时事的变迁,但不能说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没有关联。”[20]尽管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上海的都市革命话语体系里有着不同程度地误读和曲解,其自身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思想的误区,但是参与其中的杨昌溪对上海都市革命话语体系中的民族主义叙事有着自己的艺术思考和思想诉求,这也从某种意义上促使了他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成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致力于对抗日战争尤其是川军战场的文学书写。杨昌溪的这些抗战报告文学作品,是对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的张扬与书写。他在抗战时期的这一亲身文学实践活动,有力回击了人们对杨昌溪作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参与者的一些历史偏见和误会。
可以说,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杨昌溪作为优秀的翻译家、作家、学者,在这一历史阶段和这一文化空间里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尽管局限于当时的历史具体条件和自身的思想认识缺陷,杨昌溪在一些文艺理论观点和文化立场上还是有些偏差和缺失,在个人的创作上也还是没法形成自己的独特艺术个性,但这都不影响杨昌溪在这个历史阶段为中国新文学做出的一些有益贡献。因此,进一步深化探索和研究杨昌溪其人其文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这条学术研究的道路还是任重而道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