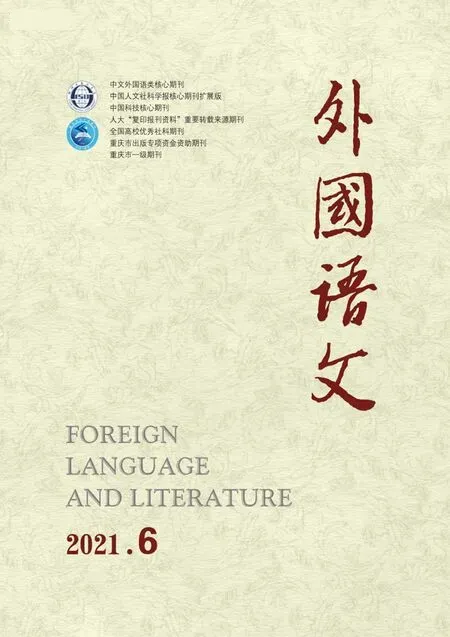《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的社会学考察
陈文荣 郭亚东
(1.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重庆 400031; 2.南京审计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3.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0 引言
《共产党宣言》可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陈望道先生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作为最早系统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译品,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期信仰的发生与对真理的探寻产生了重大影响。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西行漫记》(RedStarOverChina)中曾记载:“我(毛泽东)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够找得到的中文共产主义的著作。有三本在我的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之后,便从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翻译的,是用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诺,1979:134)
陈望道中文全译本诞生以来,百年间产生了数十种译本。学界对不同时期《共产党宣言》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时代背景与价值取向等进行了多维研究,但仍缺少从社会学视角宏观、立体地对译本生产的社会历史语境进行溯源式的探讨。本文综合运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理论中的“场域”(field)、“资本”(capital)、“惯习” (habitus)及“幻象”(illusio)、“信念”(doxa)与“信仰”(croyance)等概念,对该译本生产的翻译场域进行考察,将其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政治语境中,梳理陈望道在翻译前累积的各类资本及其译者惯习的生成脉络,据此分析其惯习在翻译选材、翻译观、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影响。同时,审视译者的译介信念与主体信仰间的相互关联及转化过程,对于《共产党宣言》翻译的认知重构与多维剖析多有裨益,充分体现了特定社会场域下“对译本构建社会的重视”(胡牧,2013:72)。
1 社会历史与翻译场域的构建
翻译的结果呈现通常源自文本内外的共同作用,“外部情形指通常所称的文学机构,即场域,内部情形指文本生产及产品、生产行为者及其惯习”(Gouanvic,2005:147)。翻译场域是特定时空的汇聚,是历时空间场域的接续与共时空间场域的叠置,即特定场域生成的历时结构与演变关系和共时结构与内外空间联系。
1.1 《共产党宣言》译介的历时空间场域:早期译介的迟滞与蓄势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在英国发表后产生了世界影响,以至“既颁布,家户诵之,而其所惠于法国者尤深”(朱执信,1979:15)。然而,在我国的译介与传播并非易事。陈望道译本1920年诞生,其传播已逾半个世纪,且国内已有若干对其思想的节译、编译与传播。
首先,清末外交官的引介。1871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随员张德彝与高从望亲历巴黎公社起义后分别在《三述奇·随使法国记》及《随轺笔记》中对共产主义作了相关记录(李长林,2003:177)。清驻德大臣李凤苞在《使德日记》中也记载了各国对共产主义的称谓,称“德国查屡次谋弑之平会,西语莎舍尔德玛噶里,各国皆有之。瑞士为民政国,故混迹尤多”(钱德培 等,2016:201)。
其次,传教士的初译。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上海担任“同文书会”督办时与人合作节译自颉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并在《万国公报》连载。《万国公报》1899年2月(第121卷)刊载其译文《大同学》第一章首次提及“马克思”与“恩格斯”名,并译述了一段《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转引自朱美荣,2018:128)
第三,留日华人的转译。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二卷第 11号上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源并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及其思想(胡为雄,2015:120)。朱执信1905年11月起在《民报》上连续载文,较详实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译出了部分《共产党宣言》,指出其影响并“片段介绍科学社会主义”(陆学艺 等, 2007:433)。
第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引介。梁启超1897年在上海创立“大同译书局”,其名即初显共产主义与“大同”观之契合。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他开始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并在1902至1905 年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拖拉斯》及《杂谈某报》等文中多次论及马克思及社会主义,称之为“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 其学说是“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最美妙之主义”(梁启超,1957:253)。
此外,1906年3月,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日文全译本刊于《社会主义研究》第一号,该译本为各类留日人员学习、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陈望道后来即参考了该版(1)有学者指出:“1903年,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在日本《平民新闻》创刊周年纪念号上发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日文译本。1920 年,陈望道所译的我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就参考了这部日译本。”(王东风 等,2019:27)据笔者考证,该说法有两处值得商榷,第一,年份有偏差,应为1904年。1903年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合作创立了“平民社”并发行周刊《平民新闻》,幸德秋水于该年单独发表了《社会主义神髓》(高书金 等 1990:711)。其次,1904年二人发表在他们主办的《平民新闻》周年纪念刊上的并非完整版译文(缺原文第三章),因此,陈望道参考该版可能性较小,而应为1906年经堺利彦补译修订后在其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全译本。另经笔者与王东风先生交流,王先生认为,要确认陈望道究竟参考的1904还是1906版本,可对陈望道译本第三章进行深入考察,依据其为堺利彦补译这一特征进行甄别。笔者深表赞同,谨致谢忱!。
然而,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对思想文化的巨大禁锢,西学东渐的步伐受到了极大迟滞,致使在西方政治舞台大放异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只能由少数人逐步引进,且囿于译介主体的阶级与历史局限性,对共产主义内涵与革命性的认知缺失,致译介难掩功利痕迹。只言片语式的译介和刻意歪曲以阐述自身政治主张的译介行为不仅有损译文“充分性”,也导致马克思主义传入的支离破碎。仅将马克思视为社会活动家,将其思想视为一种新兴社会学说,《共产党宣言》仅作为该学说的理论注脚,也“远远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在改变世界格局、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能,更谈不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谭渊,2018:89)。因此,尽管《共产党宣言》在清末民初多有引介,但未被普遍接受,也未出现中文全译本。
辛亥革命成功,十月革命胜利,五四运动兴起,思想界展现出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热切呼唤,中国社会对一套切实可行的思想学说的渴求变得迫在眉睫。少数知识分子准确捕捉并确认了该需求。由此,《共产党宣言》的译介“由自发翻译介绍进入到自觉研究介绍的新阶段”(陈家新,2012:119),开启了从被动接触到主动接受、从章节式译介到系统性传播、从“天下大同”“均贫富”的浅层认知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阐释,全面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期待。
可以说,《共产党宣言》全译本诞生的历时空间场域是以清末外交官、传教士、留日华人、资产阶级改良派等社会各阶层人士与行为主体的前期译介铺陈为背景,经十月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重大社会事件在连续时间场域下的共同作用。尽管存在社会及权力场域的种种迟滞因素,其清晰的历时空间场域蓄势同样形成了不可逆转之势,催生着《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适时诞生、系统学习与广泛传播。
1.2 《共产党宣言》译介的共时空间场域:时代的共振与回响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模型——[(惯习) (资本)]+场域=实践(Bourdieu,1984:101)表明,实践的形成是场域、资本和惯习的互动,是不同逻辑主导下不同场域的差异化路径实现。不仅场域内主体互动频繁,场域间亦互动密切。因此,对《共产党宣言》译本生成的场域考察离不开对当时社会独特文化、思想与权力结构等共时场域的追问与探寻。
1.2.1 新文化运动对译文风格的影响
“历史就像是树之年轮,从中可以看出特定时期特定的翻译运作,同时也可以通过特定的翻译运作反观特定时期的文化风貌。”(王东风 等,2012:76)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始于1919年12月,成于1920年4月。彼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作为中国现代社会文化转型及思想变革的重要标志,在语言上突出表现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语言变革质的飞跃并最终形成典型的文白过渡时期。正如蔡元培所述:“民元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滕浩,2016:245)陈望道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行者,其译作风格难逃白话文运动影响。结果是,其译作与严复、林纾的文言相比,“句子变长了、四字格少了、‘之乎者也’的文言功能词几乎绝迹了”(王东风 等,2012:76)。全文变长的标志便是对“底”和“的”字的高频使用,如“阶级争斗底历史”和“社会底历史”。“底”是该时期的独特用法,功能类似“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底”与“的”混用,如“用自己党底宣言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从封建社会底废墟上发生的近代有产社会”。由此,新文化运动所引出的文化场域剧变对同期翻译场域形成了有效的投射,时代主流场域营造的翻译规范对翻译方法与策略、译本语言等产生重大影响,整体趋于全面系统、准确忠实地再现原作理论体系与实践规范。当然,以陈望道《共产党宣言》译本为代表的翻译场域也会对彼时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反向投射与充分互涉。
1.2.2 思想场域在翻译场域的映射
清末民初《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零星译介与传播在早期翻译场域受众不多。然其优势在于,读者多为有较高社会地位且能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群体,其社会影响力与建构意义不言而喻。彼时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取向各异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蔡元培等在反专制、反传统、反蒙昧大旗下暂时结成联盟,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现代气象”(林红,2017:233)。经诸多学贯中西、具备高度文化与象征资本的社会名流宣扬及《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运动前沿阵地推介后,整个社会思潮为之而动,民众思想随之一新,时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知不断深化,逐渐意识到马克思思想之伟大。以话语转换为表征的翻译场域与以社会思潮为症候的思想场域必然在此产生交集并进行激烈的对话与碰撞,思想场域所生发的观念及其自身的不断聚合与演变在翻译场域不时“显身”与“登场”,使该时期翻译场域产生了结构性形变。于是,翻译场域内行动者出于各类符号资本的争夺需求,与思想场域的社会实践需求一拍即合,催生了各阶层对《共产党宣言》进行系统译介与学习的需求,从而酝酿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诞生。
1.2.3 翻译场域的权力抉择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是个层级化的差异空间,权力关系在此交织并根植于日常实践中,以无意识的方式进行自我再生。”(Buzelin,2013:187)《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核心内涵的展示与呈现,是进行社会改造的重要理论,在其译介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各类权力主体以种种差异化的方式进行赞助或直接参与其中。事实上,“由于译者的诗学观、文化观等惯习会内化成他的身体化文化资本,整体而言,译者的翻译场域就表现为他与其他行为主体间的资本较量所构成的权力关系”(黄勤,2018:96)。该权力关系的目标机制是冲破原有翻译场域与社会运行的平衡结构,对社会权力运作机制进行重构并进行权力关系的重新抉择与分配。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在生产及出版过程中,除早期共产党人的积极投入与共产国际的赞助外,戴季陶、邵力子等国民党元老也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彼时经五四运动洗礼过的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并独立登上了政治舞台。及至陈望道中文全译本诞生时,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及共产党早期组织已先后出现,这也为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进行科学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基础。自此,“用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重要性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飞跃”(谭渊,2018:92)。
2 译者的资本累积与赞助人的资本推动
场域既按照一定规范运行,也是松散凌乱、充满斗争的不确定性空间,尤其当行为者均为有意识、有独特“性情倾向系统”和认知属性的个体时,难免彼此角逐,进行资本争夺。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泛称为“信息资本”,并以“具身化”(embodied)、“客体化”(objectified)和“机构化”(institutionized)三种形式存在(Bourdieu et al.,1992:119)。行动者只有认定自身需要何种资本,方可积极投身其中,以期因此获益。那么,在《共产党宣言》翻译场域中,陈望道如何进行自我“认定”和资本积累,并最终“获益”呢?
2.1 译者的多元资本累积
古希腊先贤普鲁塔克(Plutarch)认为:“在追求/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思想与身体要连成一体,不得分离。”(克罗宁,2014:96)这就将主体的“具身资本”(embodied capital)提升至和思想与文化资本并列的层面,与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具身代理”相类,后者认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取决于身体、文化、生活方式等”(Taylor,1995:63)。我国学者文旭也认为,“具身是一种身体体验”(文旭 等,2020:1)。可见,主体对世界的认知是具身化的,是认知主体与客体的身体化相互作用与经验的累积。
陈望道经历“一师风潮”后,于1919 年12月被浙江省教育厅革职查办,被迫去职。此事令其在思想上深受触动,转而思考救国之途,并“逐渐认识到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文化思想,必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陈家新,2012:119)。经此风波,陈望道获得了全国声誉,其具身认知发生转变的同时赢得了诸多“具身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戴季陶曾想自己译《共产党宣言》,“无奈,细细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此书的翻译难度相当高,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叶永烈,2005 :98),于是请邵力子推荐。陈望道是邵力子的浙江同乡,常为其主编的《民国日报》及《觉悟》副刊撰文。邵知其留日经历,精通日语又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文学功底亦深,便信心满满地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陆茂清,2011)充足的知识及语言资本,以及通过浙江事件获得的丰富的具身资本及象征资本等多元资本的累积,使得陈望道最终成该“雄文”译者的不二人选。
2.2 外部资本的推动与多元赞助系统
赞助人作为特殊行为主体在翻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凭借自身资本优势影响或左右译介主体的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风格。陈望道《共产党宣言》译本的赞助人系统呈现多元趋势,该系统形成了其重要的客体资本。
部分国民党元老对《共产党宣言》引介的积极参与极大地拓展了其影响,为其蓄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如前述戴季陶和邵力子。二人主持的《星期评论》和《觉悟》副刊是当时西学译介的重要刊物及马克思主义早期的重要传播阵地,形成了其重要的隐性机构资本。与邵力子的熟识亦构成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重要人际与客体资本。
众多民主革命人士与进步知识分子主持的报刊和出版社亦为该赞助系统的重要构成,不仅为《共产党宣言》的译介与传播提供阵地,客观上也成为大批译者与进步人士的赞助人。培养了大批共产主义者,为译介主体积攒了丰厚的文化与机构资本,为接受语境的形成提供了助力,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接受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共产党宣言》因《星期评论》停刊而致其连载计划夭折,后获共产国际资助并在党组织的印刷厂付印。因此,共产国际是实际的机构资本赞助人。此外,初稿完成后,陈独秀与李汉俊二人作为校阅人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赞助人体系,其客体资本为译本权威性提供了保证。
多元赞助系统的资本合力使得《共产党宣言》陈译本于1920年8月一经诞生便大受欢迎,以至“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第一版 1000 本很快售尽,9 月间再印 1000 册,又供不应求。读者纷纷来函询问何处有卖……”(陆茂清,2011)。其后数年一版再版且不断遭遇盗版。该译本使得共产主义思想在国内影响日趋壮大,且后来“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各类赞助人的努力确保了中共在全国翻译场域都赢得了明显的资本优势”(王传英,2017:195)。
3 陈望道的译者惯习考察
译者在文本生产时,未必刻意选用某一策略,或许是译者目标语惯习的复合呈现。通过对陈译本的综合考察,发现了一些译者策略,如白话文与非正式文体的相对高频使用及各类修辞的灵活运用。这类策略较大程度与译者惯习关联,是译者惯习内化翻译规范于心后的综合表征与外显,是主体隐性倾向的文本化。下面试析其修辞惯习与文体惯习。
3.1 修辞惯习
陈望道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著名修辞学家,其在译《共产党宣言》时即已展示出明确的修辞惯习并对其中的修辞作了独特关照。他在翻译时参考了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译本和戴季陶提供的幸德秋水与堺利彦的日译本。在默认主要译自英文的前提下(2)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主要译自英译本还是日译本,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据陈望道的学生陈光磊在1990年3月8日告诉笔者(指叶永烈),陈望道生前与他谈及,周恩来在50年代曾问及《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据英译本译。”(叶永烈2005:98)笔者认为该说法可信度较高,陈望道的日本留学背景导致众多研究者默认其主要译自日文版,应为误会,殊不知陈望道亦精通英文,且日译本也译自英文。因此,本文分析时仅采用英汉对照,省略了作为“中间文本”的日译本。当然,无须争议的是,陈在翻译时是将英译本与日译本放一起进行比对的。,他对英文中的重复修辞、比喻修辞、排比修辞等均做了较好处理。限于篇幅,仅选英汉语言一例进行比对:
A spectre is haunting Europe—the spectre of Communism. All the Powers of old Europe have entered into a holy alliance to exorcise this spectre …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因为要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陈望道,2018: 221)
该段是流传极广的首句,胜在其重复与比喻修辞的并用。在《修辞学发凡》中,陈望道认为重复修辞是“用同一的语句,一再表现强烈的情思的,名叫反复辞。人们对于事物有热烈深切的感触时,往往不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申说;而所有一而再、再而三显现的形式,如街上的列树,庆节的提灯,也往往能给予观者以一种简纯的快感,修辞上的反复就是基于人类的这种心理作用而成”(陈望道,1997: 199)。在他看来,这种“章句上的辞格”是一种积极性修辞,“怪物”一词的三次重复,呼应了原文“spectre”所表现的“强烈的情思”及作者“热烈深切的感触”,用语掷地有声,节奏明快,较好地再现了原文本的鼓动效应。
在陈望道看来,“譬喻”或称“比喻”,是“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说话和写文章时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陈望道,1997: 72)。“比喻”是一类能够引起或触发主体联想的心理机制,因而是能够起到一定程度鼓动效应的修辞结构模式,《共产党宣言》全文运用较多。开篇的实词“spectre”即为比喻修辞,该词本为贬义,意为“妖怪”“怪物”“幽灵”等,此处为作者的刻意反讽。
3.2 文体惯习
陈望道尤重文体研究,并在《修辞学发凡》中详细划分了八类文体,其中第四类是“目的任务上的分类,如通常分为实用体和艺术体等类,或分为公文体、 政论体、科学体、文艺体等类”(陈望道,1997 :256)。
“世上能够读懂读通皇皇巨著《资本论》者,必定要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而《共产党宣言》却是每一个工人都能读懂、能够理解的。”(叶永烈,2005:98)因此,尽管同为马克思著作,二者却在语言与文体风格上差别迥异。《共产党宣言》是一类正式的“政论体”,但也出现了不少非正式文体词汇,如do away with、nursery tale、pushed on one side之类,可谓“非正相隔,文白相间”。
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竭力遵从原文特征;另一方面对白话文口语体的运用,较其他译本有显著超越,与原文相比亦有过之。例如,“草了下列的宣言”“他的特色就是把阶级对抗弄简单了”“大规模的‘近代产业’,便取了手工工业底地位”等。
比较而言,五四运动前的译介目的是“为我所用”,故主要使用了上层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文言”,并更多关注译本的“可接受性”;而无论“白话文运动”抑或后由陈望道等发起的“大众语运动”则与文言针锋相对,明确反对,旨在宣扬“引车卖浆者言”的大众语,以倡新语体风格。对此问题不可孤立视之,而需联系当时文白过渡期的文化语境,及此语境中译者的主体倾向。陈望道在白话文运动中将该运动的结构性规范不断转化,生成其自身内在的主体惯习倾向,同时又将该主体惯习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外化为译文的文本现实,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翻译风格。
4 从翻译“幻象”到译者“信仰”
布迪厄将场域中的斗争喻为游戏的角逐,其手段是资本的争夺与惯习的比拼。译者与所处场域存在相互构建与转化关系,具体表现为从初级阶段的翻译“幻象”向高级阶段译者“信念”(doxa)演变,直至更高级阶段译者“信仰”的目标构建与社会实现。如图1所示:

图1 译者的“信仰”构筑
翻译“幻象”是翻译行为者参与场域游戏时“对游戏的坚守,对其根本前提的接受,无论科学抑或文学游戏,均值得认真对待和参与”(Bourdieu,1996:333)。因此,翻译行为被视作译者群体参与的游戏角逐,同为文化生产实践者的译者和作者,基于对实践活动价值和意义的认可,积极参与并维持被看作游戏的角逐,从中获得一种“幻象”的审美愉悦。
作为政治宣言类文本译者的陈望道,其译介过程必然伴随着权力角逐与博弈,同时也会收获其所追求的审美愉悦。译介过程中,陈望道需依据文本自身逻辑,从内化于场域中的文本意图出发,对其进行“幻象化”阐释。翻译“幻象”的目标实现取决于译者的惯习构成,这一惯习构成贯穿翻译行为始终,使翻译行为受到影响,并重构译者的社会轨迹(邵璐,2011:127)。而当陈望道所坚持的个体“幻象”进入群体意见领域并进行正统与异端的博弈时,翻译的“幻象”游戏便进入延展了的“信念”领域,再历经长期群体实践验证与个体检验后,便上升为译者所“笃信”的对“实在”(法文realite,德文Wirlichkei)的“信仰”,并在未来可能以“正题”或“悬置判断(epokhe)”的面貌出现(布迪厄,2017:239)。这一被布迪厄称为“常识”(sens commun)的不可动摇的信仰便于译者通过“悬置判断”解决信念领域的相左意见,并最终将陈望道引向了共产主义的永恒“正题”。在此信仰“正题”激励下,陈望道克服了极端的困难,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信仰故事的思想原点。
陈望道的多元内外资本与丰厚文化惯习充分作用于物化了的译介场域的游戏对象,其历经“悬置判断”后在实践中逐渐深化的“独特确定性”的共产主义信仰在其自身对《共产党宣言》译品的认知思维、译介决策以及评估模式中发生作用。“信仰”作用下的译者陈望道亦通过自身的艺术再生产与实践以渐进的方式构建并强化了其自身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的终生信仰。可以说,信仰既是《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事件的场域游戏运行的基本前提,亦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5 结语
将作为社会行为人的译者的语言转换行为与所处社会历史语境及场域中的行为轨迹相结合,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翻译行为与社会现实的相互关联及其巨大推进作用。借鉴布迪厄的“场域”“资本”“惯习”以及“幻象”与“信仰”等概念对《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诞生的场域进行考察,从社会学视角对该译本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进行追踪,有效拓展了《共产党宣言》翻译与传播的社会功能及其影响研究。同时,对译者进行了全方位社会学考察,分析陈望道译前译后的资本量变,探讨其译者惯习的形成及在翻译选材、翻译观、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影响,追溯了译者陈望道的信仰构建历程及其与翻译场域的互构,为研究翻译的文本实践何以演化为重大社会实践并对历史与现实产生重大影响等问题提供了注脚。正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指引着包括陈望道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通过不断奋斗,一步步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国家富强,取得了一个个新的辉煌成就,谱写了新中国历史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