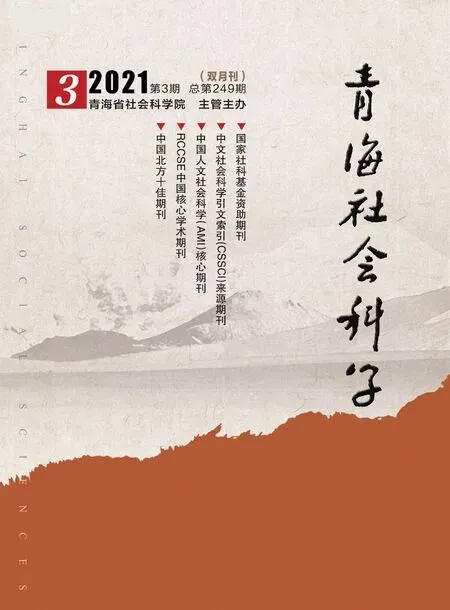“气”与明代前后七子的诗学思想
◇李 明
关于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诗学的具体观念,学界已经做了很多研究。诸如七子派对“情”的重视、对“格调”的讲求、对模仿与自得的争论等,都成为学界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前后七子诗论中大量出现的对“气”的讨论,尚未得到充分的注意和总结。“气”自古以来就是诗学的核心范畴,但在明代七子派诗学中,似乎占有更加特别的地位。可以说,“气”是理解明代前后七子诗学观念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角度。
“气”的范畴具有多义性,在明代诗学的语境中也具有不同方面的涵义,如理学中“理”“气”关系层面上的气、士风层面上的“气节”之“气”,诗学观念中的“气”等。但这些不同方面的涵义当然也具有一种共通的感性层面的生命力。本文拟从思想、士风、诗学等几个方面来讨论明代前后七子关于“气”的观念。
一、理气关系的转变与七子的气论思想
宋代产生的程朱理学到了明初,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明成祖诏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并以之规范科举,统一思想。因此,在前七子产生之前的思想界,呈现出程朱理学定于一尊的局面。在程朱的哲学体系中,“理”“气”的关系决定了人性论中性、情的关系。程朱认为形而上的“理”为本源,而形而下的“气”是次位的。而“情”属于形而下之“气”,需要被形而上的“理”所规范。所以理学家都提倡符合“理”的中和之气,这无疑限制了诗的情感性。另外,对“理”的强调也破坏了诗的形象性。
但是到了前后七子所在的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的控制开始出现了松动。很多不同流派的思想家都强调“气”的重要性,从而开始颠覆“理”对“气”的压制地位。①对明代中期以后“气”论思想的发展情况,葛荣晋的《王廷相和明代气学》第十四章《王廷相及其气论学派》和第十五章《王廷相继承者的气学》(中华书局,1990年)进行了介绍。王俊彦的《王廷相与明代气学》(秀威咨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的第二编《明代之气学思想》分“以气为本”、“理气是一”、“心理气是一”、“由易说气”几章分别进行了总结。罗钦顺、唐鹤徵等人,均认为“气”为万物之本源,“理”只是“气”之条理。罗钦顺提出:“理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1](《困知记》卷上)唐鹤徵也指出:“盈天地间只有一气”,“自其分阴分阳,千变万化,条理精详,卒不可乱,故谓之理。”[2]605(《桃溪札记》)杨慎认为元气为天地之本源,主张“道以器寓”批评程朱“离气而言道”;由此,他认为“性与情相表里”[3](《丹铅总录》卷二十二《琐语》),反对把性与情对立起来。
在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批受北宋大儒张载影响的“关学”的继承者。张载的“关学”认为宇宙的本源和万物的本体皆是“气”,而非“理”。韩邦奇继承了张载的思想,认为“道”或“理”只是“气”的流行发见:“由气化可以言道矣。”他认为,“道”在“气”之中,“非气而上也”。[4](《正蒙拾遗序》)作为前七子成员之一的王廷相是关学在明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思想,批判程朱理学认为气根于理的学说:“若曰气根于理而生,不知理是何物,有何种子,便能生气?不然,不几于谈虚驾空之论乎?”[5]602(《横渠理气辨》)明确指出“气”的本体地位:“气者,造化之本。”“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慎言·道体》)论“气”“理”关系云:“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5]751(《慎言·道体》)同时代的关学人物所持思想皆与王廷相类似。受王廷相的气本论思想影响的还有黄绾、吴廷翰、高拱等人。
心学一系的思想家多主张“心即理”,而“心”实属“气”之层面,因此“心”、“气”、“理”为一体。如湛若水认为:“夫人之喜怒,气也,其中节焉,理也。气有形,故曰形而下,及其适中焉,即道也。”[6]王俊彦评论此段道:“湛若水乃以气中之表现为道,而不是在气之外另有一道,同样,人的喜怒中节就是理,而非喜怒之外另有一理。”[7]339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其实是理与气的统一体,他说:“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8]70(《答陆原静书》)正如上田弘毅所总结:“可以说,理是良知的条理,气则是良知的运动。在王守仁那里,理气的关系不是两样东西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是把良知的不同侧面分别作为理、气的理气一体关系。”[9]425据王俊彦的分类,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家中,以心、理、气一体者还有吕柟、高攀龙、刘宗周等人。②参见王俊彦《王廷相与明代气学》第二编《明代之气学思想》第三章《心理气是一》。
除了王廷相外,前后七子中的其他一些人也不同程度地具有以气为本的思想。前七子中,李梦阳、康海、王九思为关中人,何景明、王廷相也长时间在陕西任官,他们与关中地区的关学学者多所交往,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以气为本的关学思想的影响。③史小军在《论明代前七子的关学品性》(《文艺研究》2005年第6期)一文中前七子所受关学影响有详细论证,可以参看。有学者认为李梦阳的思想有关学的影子:“所著《空同子》八篇,关学色彩浓厚。”[10]李梦阳在《空同子》中批判宋人言理:“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说拘而泥。”[11]1979进而他多以“气”解释各种现象,如解释寒暑:“阴阳必争也,二气旋转坱圠,以负胜为寒暑。”[11]1971解释海市:“或问海市。李子曰:此处偶有此怪异气耳。”[11]1974解释鬼神:“曰:有鬼神形者何也?曰:气动之也。气散则散。”[11]1969李梦阳又说:“天地间惟声色,人安能不溺之?声色者,五行精华之气,以之为神者也。凡物有窍则有声,无色则敝,超乎此而不离乎此,谓之不溺。”[11]1970他认为声色等“气”只要不过于陷溺就是“理”,这显然是以“气”为本的思想。又如后七子核心人物王世贞,其《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说部”中,他论曰:“天地间一气而已,初无有善恶也。有气必有理,以理求之,则有善无恶;以气求之,则有善有恶。”[12]“有气必有理”说明他是以“气”为第一性的。他以“气”来解释各种气象灾害现象:“天地无心而任气,任气故不能无过,无心故未尝累德。天地之有薄蚀晕孛震雹水旱崩竭灾厉也,是阴阳之所为也,犹之人血气之灾疾也。”[12]
如上所述,在前后七子所在的明代中期,“气”的思想十分活跃,开始突破“理”的压制。而且七子中有些人甚至具有了明确的气本论思想。这与他们在诗学理论和批评中对“气”的重视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尚气”与七子派士风
明代前期的专制政治和思想管制,形成了卑弱的士风。明太祖的严刑峻法和文字狱使士人动辄得咎,明成祖对士人的杀戮使士人丧气。明太祖以来,虽然表面上尊崇理学,但剥除了理学中以理抗君的正面价值,而是以之作为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工具。而程朱理学对性情之正的规约,又使得士人追求一种温厚和平的个性。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氛围中,明代前期的士人失去了昂扬奋发的浩气,而是以老成安稳为追求。当时的理学名臣、台阁领袖,对于渐渐成风的宦官专权等窊败政治皆无指斥,而是以明哲保身为追求。“这一时代精神生活的典型特征还是刻板。没有激动人心的理想,读书人以其持重老成的共同风格告别了热情与活力,读书人追求的是安全、地位,而不是新的思想与希望。”[13]6
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士风振奋运动。对于他们来说,文章、气节是一体的。他们崇尚气节,言行亢直,充溢着一种刚大耿介之“气”。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就是其中的典型。弘治十八年,李梦阳应诏上书孝宗皇帝,指出当时社会的二病、三害、六渐,其一病为“元气之病”。[11]1406他所说的“元气之病”是指出当时人们明哲保身、处事圆巧的卑弱士风。而李梦阳则通过自己的人格与行事,引领了一代“尚气”之风。他先是在应诏中弹劾外戚寿宁侯张鹤龄,因而被诬下狱。出狱后遇张鹤龄于市,乘醉击落其二齿。正德元年,梦阳更因草书攻刘瑾被夺官归家,并于正德三年被逮北上,赖康海、何景明设计才得救免。李梦阳曾在给杨一清的书信中抱怨,因其种种“作士气”的行为而被人称为“尚气”,因而被人忌恨:“凡所振纲纪,慑权贵,兴礼教,作士气,起废举坠,拔冤伸枉,植善锄强,皆置不说。而妒者目为生事,异者倡为尚气,仇者指为奸邪,私者诬为善讦,排者劾为不谨。”[11]1930(《奉邃庵先生书》)李梦阳的“尚气”所尚的,正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前后七子中的其他成员也多以气节为尚。正德年间刘瑾弄权,前七子坚决站在反对刘瑾的立场上。如何景明则上书吏部尚书许进,劝其不向刘瑾妥协。边贡也在正德初因忤刘瑾而出知卫辉府。康海解救李梦阳以及“康状元琵琶击客”之事都为人津津乐道。朱孟震《刊对山康先生全集序》评价道:“先生素绝阉瑾之交,乃以微权缓颊而解北地之厄;至琵琶击客一事,海内士大夫类能言之。此其气雄万夫,与文力相赑屃。”[14]678南轩《对山先生全集序》也说:“余闻寓内学士家称说国朝状元,率推毂关中康先生,谓其文章气节有古豪杰之风云。”[14]678后七子的风骨和气节则主要表现在同严嵩、严世藩父子专权的抗争中。嘉靖三十年,严世藩欲构陷边将,时任刑部郎中的李攀龙不为所屈。王世贞官刑部时,奸人犯法为世贞搜得,严嵩出面说情,世贞不为所动。梁有誉中进士后,严嵩欲网罗门下,梁不肯往。嘉靖二十九年,刑部郎中徐学诗上书请罢严嵩父子,被杖,削籍出京。亲友无人相送,只有谢榛相送。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后七子坚决站在杨继盛一边。杨继盛入狱后,王世贞、徐中行、宗臣、吴国伦经常探视。杨继盛被杀时,王世贞、宗臣、吴国伦哭祭刑场,并为之料理后事。李攀龙有诗云:“意气还从我辈生,功名且付儿曹立。”[15]1964很好地概括了后七子们意气慷慨的风貌。
三、“气”与前后七子的诗风追求
明代前期直到前七子复古运动发生之前,占据诗坛主流的是“台阁诸公”的台阁体诗。台阁体文人深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程朱理学认为“情”要受“理”节制,主张“性情之正”,因此台阁诗人所尊尚的是一种温厚和平的诗风。前七子以慷慨尚气的诗风振奋了萎靡卑弱的诗坛,这与他们崇尚气节的人格追求正相表里。他们以富有“风骨”的汉魏盛唐诗为学习对象,而“风骨”就是指一种充溢在诗中的强盛的生命力,也就是“气”。作为前七子的领袖和整个明代复古运动的引领风潮者,李梦阳的诗风即是如此。李开先在《李空同传》谓其:“以雄豪不可下之气,而为闳肆不可遏之文。”[11]2073闳肆的文风正是发自于尚气的人格。康海论诗也十分重“气”。《四溟诗话》载:“徐伯传问诗法于康对山,曰:‘熟读太白长篇,则胸次含宏,神思超越,下笔殊有气也。’”[16]1174
前七子后,复古诗风衰歇,李攀龙、王世贞等人起而振之。姑苏刘凤在为李攀龙所作诔文中描述道:“然自何、李以还,气亦稍衰下矣。公与三数少年,夙夜淬励,力振起之。风于是再变,雄峭奇劲,矜厉庄迒 ,可谓古之极轨,无复遗憾。”[15]871后七子正是以“雄峭奇劲”的诗风振奋“气稍衰下”的局面。刘凤在诔文中形容李攀龙的诗风:“郁勃气往,凌切才肆。横奔绝驱,焉复曩态。”李攀龙自己在《送元美》诗中云:“夙昔二三子,慷慨扬奇声。”“骨肉非一身,意气乃合并。”[15]114很好地概况了后七子群体的诗风。宗臣在《五子诗》中形容谢榛的诗风:“悲歌慨以慷,惊飙奋孤翼。”[16]4171(《谢山人》)又形容王世贞的诗风:“高歌以慷慨,顾盼酬知音。”[16]4172(《王比部世贞》)宗臣诗风也以气雄见称,王世贞评论道:“吾友宗子相,天姿奇秀,其诗以气为主,务于胜人。”[17]1061(《艺苑卮言》)梁有誉的诗风也是如此,吴国伦在诗中评价他说:“之子秉异灵,躯孱气何雄。”[16]4138(《梁公实》)吴国伦论诗多以慷慨磊落之气为标准,如《王屋山人稿序》谓对方之诗:“辩博通经济,而慷慨磊落之气传焉。”[16]4154又如《大隐楼集序》评曰:“其气豪宕不羁,其风度廓宏高远。”[16]4160此类评论在他的别集中随处可见。
与其他诸子相比,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特别强调由内心郁结之气遇物抒发而出的不平之气。李攀龙在《比玉集序》中说:“夫诗,言志也。士有不得其志而言之者,俟知己于后也。”[15]474又在《蒲圻黄生诗集序》中说:“有所不得、有所不安,而后有以欲之,是为诗之教也。”[15]475可见他认为诗是一种不平之鸣。李攀龙又在《送宗子相序》中论曰:“诗可以怨。一有嗟叹,即有咏歌。言危则性情峻洁,语深则意气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摈弃不容之感,遁世绝俗之悲,泥而不滓,蝉蜕滋垢之外者,诗也。”[15]500由于不平之气的导泄,诗的言语表现为激烈悲壮的意气,更能感人。
当然,前后七子中也有不同的诗风,如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等。但这些不同类型的诗风则恰恰被认为是非典型和有所缺憾的。王世贞在《明诗评》中评论何景明说:“气力稍让李梦阳,烨烨动人,颇自不减。”[16]4348评论徐祯卿云:“使稍加沉郁之思,微振浑灏之气,何、李无易也。”[16]4349又评论边贡:“所惜气格稍让,师友或疏耳。”[16]4350从王世贞的评论看来,何、徐、边等人如果能更加以雄浑之“气”,就更为完美了。七子派后进胡应麟在其《诗薮》内编卷二中说:“曹刘阮陆之为古诗也,其源远,其流长,其调高,其格正。陶孟韦柳之为古诗也,其源浅,其流狭,其调弱,其格偏。”[18]28可见在他看来,曹刘阮陆的梗概多气是更高更正的格调,要胜过陶孟韦柳的平淡神韵。
明代七子派慷慨尚气的诗风,被认为与西北地区的“雄峻之气”有关。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我朝相沿宋元之习,国初之文,不无失之卑浅。故康李二公出,极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既高,加发以西北雄峻之气,当时文体为之一变。”[19]前七子的主要成员为西北和中原之人,李梦阳为甘肃庆阳人,康海、王九思为关中人;王廷相、何景明为河南人,但都正曾在陕西多年任官。自古认为南北地气不同,西北之气朴厚雄峻,因此前七子的诗风可以说带有了这种地域气质。相比西北、中原的尚气诗风,吴中的诗风则相对软媚。吴中人徐祯卿一见李梦阳而心服,正代表了西北地域之气的胜出。王世贞是吴中人,但他也对吴中诗风颇有微词。在《李氏山藏集序》中,王世贞自道:“某吴人也,少尝从吴中人论诗,既而厌之。夫其巧倩妖睇,依闾而望欢者,自视宁下南威、夷光哉。”[16]4387否定了吴中诗风的“巧倩妖睇”,并称道对方的诗具有“沛然气怂,溢而动”的风格。又如《玄峰先生诗集序》:“吴中诸能诗者,雅好靡丽、争傅色,而君独尚气;肤立,而君尚骨;务谐好,而君尚裁。”[16]4397以及《叶雪樵诗集序》:“夫雪樵子生江左,顾能脱甚靡靡冶柔之习,而能完其气。”[16]4464以上两序也都认为吴中诗风缺少“沛然之气”。
四、反“意”复“气”:七子派以“气”论诗的相关主张
前后七子诗学批评中频繁出现的“气”,主要的理论指向在于通过对“气”的强调来反对宋人的以“意”为诗。
汉魏盛唐诗学的核心精神就是“气”。建安诗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形成陈子昂所谓“汉魏风骨”。同样,盛唐诗风也以“风骨”见称。而所谓“风骨”即是一种慷慨磊落之“气”。从理论批评上来看,汉魏盛唐诗学的几个核心命题,如《诗大序》的“诗言志”、曹丕的“文以气为主”、陆机的“诗缘情”、钟嵘《诗品》的“气感”说,其思想背景也是先秦两汉以来盛行的气论思想。先秦时期,“气”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两汉时期的元气论也十分盛行,在《淮南子》和两汉之交盛行的谶纬之书中,都以元气为生成天地、化生万物的本源。东汉的王充、张衡、王符等人也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自然元气论。东汉产生的道教的宇宙论和方术论也都是以元气论为基础的。从气论哲学来说,“志”、“情”等范畴都是由人体的“气”所感发产生的。《大戴礼记》说:“气为志。”[20]171《文心雕龙》也说:“气以实志。”[21]506可见“志”由“气”发;《白虎通论·情性篇》指出:“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之情”[22],可见“情”亦为“气”所生。因此,“诗言志”“诗缘情”等古代诗学核心命题的思想背景正是汉代的元气思想。①很多学者对这一点有相关论证,如郑毓瑜《从病体到个体——“体气”与早期抒情说》论“体气”与抒情自我形成之关系,载杨儒宾、祝平次主编《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又如龚鹏程《从〈吕氏春秋〉到〈文心雕龙〉——自然气感与抒情自我》,郑毓瑜《〈诗大序〉的诠释界域——“抒情传统”与类应世界观》,二文载陈国球、王德威主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第592页和第622页。
但是到了中唐以后延续到宋代,汉魏盛唐以“气”为核心的诗学范式产生了转变。这种转变的内在精神,即以对“意”的重视为核心。宋诗重意,这是古今诗论家公认的命题。晚唐齐己的《风骚旨格》论“诗有三格”中以“上格用意”而“中格用气”,正体现出这种转变。宋代诗学中这种言论甚多,如北宋诗僧惠洪的《天厨禁脔》卷下论古诗押韵法时说:“古诗以意为主,以气为客。故意欲完,气欲长,唯意之往而气追随之。”[23]149以意为主而以气为客。对于这种转变,明代人屡屡论及。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七言绝句,盛唐主气,气完而意不尽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气不甚完。”[16]4239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也指出:“中唐人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24]1417现代学者中论唐宋诗之分的一段著名论述出自缪钺先生,他也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25]31萧华荣在其《中国诗学思想史》总结说:“中唐诗学思想的变异,在我看来,其深层根柱是‘尚意’。”[26]139
明代前后七子在里诗学批评中对“气”的重视,目的正在于恢复以为“气”为本源的汉唐诗学,反对以“意”为核心的宋型诗学。七子派论诗重“气”的具体表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别论析。
1.“气”与自然兴感。
汉魏盛唐诗学特别强调基于“气感”而自然成诗的创作论。钟嵘《诗品》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27]2人身之气与外部世界之气相互感发而产生诗,这也就是“兴”的本质。关于“气感”与“兴”的关系,可以从王昌龄的《诗格》中见出。王昌龄十分重视“兴”,在《诗格》中说:“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28]160他又说:“夫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闻于耳,见于目,录于纸。”[28]162从他所说的“文章兴作,先动气”可以看出,诗学创作论中的“兴”正是建立在外物与自身的气感作用之上的。
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诗学在诗歌创作论中特别强调这种自然而然的兴感作用。李梦阳多次指出诗情的产生是由于“遇”的作用,如他在《梅月先生诗序》中说:“情者,动乎遇者也。”“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寓而发者也。”[11]1679李梦阳所说的“遇”即主体与外物的自然兴感。谢榛在其《四溟诗话》中特别突出“兴”的重要,如曰:“诗有不立意造句,以兴为主,漫然成篇,此诗之入化也。”[17]1152又曰:“凡作诗,悲欢皆由乎兴,非兴则造语弗工。”[17]1194
这种以“气感”为本质的“兴”,要义在于不假人工锻炼,“无意”而成诗。明代复古诗学十分看重汉魏盛唐诗的这一特点。七子后学胡应麟在其《诗薮·内编》卷二评论两汉之诗:“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汉之诗也。”[18]22“两汉之诗,所以冠绝古今,率以得之无意。不惟里巷歌谣,匠心信口,即枚、李、张、蔡,未尝锻炼求合,而神圣工巧,备出天造。”[18]25又论古诗十九首曰:“诗之难,其十九首乎!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盖千古元气,钟孕一时,而枚、张诸子,以无意发之,故能诣绝穷微,掩映千古。”[18]26在他看来,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两汉诗歌正因是“千古元气”的自然发露,所以不假人工,是“得之无意”的天成之作。盛唐诗之极诣也是如此。李攀龙认为:“太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盖以不用意得之。”[15]474(《选唐诗序》)又如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比较李杜有云:“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16]4238可见李攀龙和王世贞都认为,李白的绝句正因为以“气”为主,所以出之无意,自然天成。
中唐以后直到宋代,诗学由以气感之自然兴发为主,转向以苦思锻炼为主,即由以“气”为主转变为以“意”为主。宋人认为对于作诗来说,“命意”是关键。《诗人玉屑》载韩驹论诗观点:“陵阳谓须先命意。”[29]171明代复古诗学注重由“气”驱动的自然兴感,对中唐到宋以来以“意”为诗的观念表示反对。谢榛在《四溟诗话》中屡申其旨,如曰:“宋人谓作诗贵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17]1149正如上文所论,李白以气为主,其诗由气而生意,而不是刻苦立意。谢榛又说:“诗有不立意造句,以兴为主,漫然成篇,此诗之入化也。”[17]1152“诗以一句为主,落于某韵,字随意生,岂必先立意哉?”[17]1194谢榛所说的“以兴为主,漫然成篇”和“意随笔生,不假布置”就是以气感作用产生的诗情和这种诗情的发展为基础,自然而然地发展出诗“意”。也就是说,诗意的表达是出自感性的发挥,而不是理性的建构。对由“气”生“意”这一点,王廷相也有所论及,其《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说:“气不充则思短而不属。”[5]503意思就是说气充则思长,气短则思断。又如李攀龙在《与徐子与书》中所说:“十二团营,一军吏领神机诸部,匕劑相载,声闻百里,此何故?气欲实也。精思非气所为乎?此固元美养气之学以望诸子与。”[15]811精思乃气之所为,所以养气是关键。
2.气格之“浑”。
前后七子论诗追求一种浑然的气格。李梦阳《潜虬山人记》中论“诗有七难”之一即有“句浑”一条。他又在《刻阮嗣宗诗序》中称赏阮籍诗的“混沦之音”:“予观魏诗,嗣宗冠焉。何则?混沦之音视诸镂雕捧心者伦也。”[11]1661谢榛《四溟诗话》中论诗以一“浑”字为核心,指出:“凡炼句,妙在浑然。”[17]1223谢榛还在诗中反复以“混茫”论诗,如《读沈国主诗集三首》:“才全奇崛下,气胜混茫中。”[16]3206《周子才见过谈诗》:“神游浩渺下无地,气转混茫中有天。”[16]3206《读李兵宪允吉关中诗集》:“太华峰头如可到,浩歌声彻混茫天。”[16]3207
他们之所推崇汉魏盛唐之诗,正在于这种浑成的气格。南宋严羽就推崇汉魏盛唐诗的浑厚之气,曾在《沧浪诗话》中指出:“汉魏古诗气象浑厚,难以句摘。”[30]151又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30]253(《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明代前后七子祖述严羽。何景明《王右丞诗集序》指出:“盖自汉魏后而风雅浑厚之气罕有存者。”[31]594他们认为,这种浑成气格的破坏,正源于宋人的以意为诗。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诗有辞前意,辞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17]1149将王世贞也说:“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今之操觚者,日哓哓焉,窃元和、长庆之余似,而祖述之。气则漓矣,意纤然露矣。”[16]4391(《徐汝思诗集序》)谢榛和王世贞都指出,盛唐诗具有混融无迹的特点,而宋人的“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正破坏了这种浑融的境界。
从前后七子的诗论来看,“浑成”气格的达成有赖于修辞的自然天成。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评论皮陆诗云:“皮日休、陆龟蒙馆娃宫之作,虽吊古得体,而无浑然气格,窘于难韵。”[17]1219皮陆的唱和诗因为牵于押难韵,所以修辞显得不够自然,因此“无浑然气格”。谢榛又评许浑“年长每劳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两句说:“实对干支,殊欠浑厚,无乃晚唐本色欤。”[17]1204许浑的这两句诗在对仗上显得十分堆砌造作,因此也不够“浑厚”。谢榛还认为,造成气乏浑成的原因,在于作者刻意追求新奇,因此造成辞气的滞涩不畅:“务新奇则太工,辞不流动,气乏浑厚。”[17]1200而刻意追求新奇正是以意为诗的宋诗的特点,故此处也隐含了对宋诗的批评。
以气格浑成为高格,与气论哲学有关。两汉的元气哲学认为,在天地未分之前是一种元气浑沦的状态:
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混成,而未相离。[32](《易纬·乾凿度》)
说《易》者曰:元气未分,混沌为一。儒书又言:溟涬濛澒,气未分之类也。[33]472(王充《论衡·谈天》)
道根既建,自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气同色,混沌不分。[33]472(张衡《灵宪》)
明代复古派诗人或者无意识,或者有意识地接受了这种传统的气论思想。王廷相《太极辨》论太极云:“求其(太极)实即天地未判之前大始浑沌清虚之气是也。”又论元气:“以天地万物未形,浑沦冲虚不可以名义,故曰元气。”以及太虚的状态:“太古鸿蒙道化未形,元气浑涵茫昧无朕,不可以象求,故曰太虚。”[5]596王廷相认为,“太极”是在天地未判之前的元气状态,是“浑沌清虚”“浑沦冲虚”“浑涵茫昧无朕”的。王世贞在其《弇州四部稿》的《说部》中也表述了类似的思想:“天地之始浑乎,国之始朴乎,人之始婴儿乎。”[34]这种元气浑沦的本源状态就像朴素的民风和人的赤子之心一样,是一种原始的健康的自然状态。但随着宇宙元气的演化,这种原始的浑沦状态不可避免地被打破,社会的发展也就意味着那种健全的混沌状态的失落,正如《庄子·应帝王》著名的“七日而浑沌死”的故事所寓示。可见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思想和他们对气论思想的接受是有关的。
3.“气”与“象”。
汉魏诗和盛唐诗都重视诗中的比兴和意象,而重意的宋诗减弱了这种形象性。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诗学力求向汉魏盛唐复归,强调“象”对于诗歌的重要性。李梦阳指出,诗忌直陈而托之物象:“盖诗者,感物造端者也。”“故古之人欲感人也,举之以似,不直说也;托之以物,无遂词也。”[11]1692(《秦君饯送诗序》)何景明也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强调“意象合”的重要性:“夫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是故乾坤之卦,体天地之撰,意象尽矣。空同丙寅间诗为合,江西以后诗为离。”[31]575王廷相论诗也重透莹之“意象”:“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5]502(《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王世贞论诗也重“象”,如其评徐中行诗曰:“养气完矣,意象合矣。”[16]4406(《青萝馆诗集序》)评宋望之诗:“其灿然者,皆天地之色,然意有造而象发之。”[16]4407(《华阳馆诗集序》)等等。
古代诗论中,“象”常常与“气”并用,组成“气象”一词。明代七子派也常用这一术语论诗。谢榛《四溟诗话》谓贾岛“秋风吹渭水”两句“气象雄浑,大类盛唐”[17]1158,又谓陈后主“日月光天德”两句“气象宏阔”[17]1159,等等。被列为“后五子”之一的胡应麟多以“气象”论诗,如曰:“盛唐气象浑成,神韵轩举。”[18]92又评老杜《九日》、《登高》等诗曰:“气象雄盖宇宙。”[18]93由此可见“象”与“气”的紧密相关,七子派论诗重“象”与他们对“气”的重视是一体的。
明代七子派论诗重“象”和“气象”,与他们对气论哲学的接受有关。古代气论哲学认为,“象”由“气”而生。张载《正蒙·乾称》篇云:“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35]320王廷相的气本论思想远绍张载,论析了“象”与“气”的关系,其《慎言·道体》篇说:“象者气之成,数者器之积。”[5]751又有如下一段更为详细的文字论说由“气”生“象”的过程:
道体不可言无,生有有无。天地未判,元气混涵,清虚无间,造化之元机也。有虚即有气,虚不离气,气不离虚,无所始、无所终之妙也。不可知气所至,故曰太极;不可以为象,故曰太虚,非曰阴阳之外有极有虚也。二气感化,群象显设,天地万物所由生也,非实体乎?是故即其象,可称曰有;及其化,可称为无,而造化之元机,实未尝泯。故曰道体不可言无,生有有无。[5]751
在张载的基础上,王廷相的文字更为具体地论述了由气生象的过程。气即太虚,具有混涵的特性。太虚之气通过感化作用,生成“群象”。正因为“元气”是“混涵”、“清虚无间”的,所以由元气生成的群象才如“水中之月,镜中之影”,是一种“透莹”的状态,而不能用理性的语言穷尽和说明。对于诗歌意象的这种混涵特性,严羽等人已经指出,但王廷相则从气本论思想出发来进行阐释,是对古典诗歌意象论的深入。①陈书录《王廷相诗歌意象理论与气学思想的交融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对此有详细论证,可以参看。
4.“气”与“声”“色”。
前后七子论诗十分重视诗的声响和色泽。他们认为,“声”对诗来说是核心的要素。李梦阳《刻戴大理诗序》云:“且物不能无声也,于是乎吟出焉。”[11]1699徐祯卿在《谈艺录》中也强调“声”对诗的重要性:“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戏,怒则为叱咤。”[27]765王世贞也说:“夫诗,必之精神发而声音者也。”[16]4391(《金台十八子诗选序》)
除“声”外,明代复古诗派同样重视“色”。《四溟诗话》载:“黄司务问诗法于李空同,因指场圃中菉豆而言曰:‘颜色而已。’”[17]1174可见李梦阳认为“色”是诗的核心要素。梦阳又在《潜虬山人记》中指出对于诗来说“非色弗神”:“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11]1616李梦阳列举了诗的七种要素,其中涉及了“调逸”“音圆”这两个“声”的方面。他认为,这些方面诚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色”这一要素,诗就难以达到神妙的境界。谢榛论诗也说:“作诗虽贵古淡,而富丽不可无。譬如松篁之于桃李,布帛之于锦绣也。”[17]1139“富丽”即富于色彩之谓也。王世贞也认为,诗文是需要“五色错综”的:“物相杂故曰文,文须五色错综乃成笔,采须经纬就绪乃成条理。”[17]963(《艺苑卮言》卷一)故世贞多以“壮丽”“宏丽”论诗。
前后七子评同代人之诗,往往从“声”与“色”两方面来切入。如王世贞的几则评论:“大要辞当于境,声调于耳,而色调于目。”[16]4399(《李氏在笥集序》)“览之渊然色,而诵之铿然声。”[16]4405(《王少泉集序》)“至于近体,铿然其响,苍然其色,不扬而高,不抑而沉。”[16]4467(《方鸿胪息机堂诗集序》)又如吴国伦《大隐山人稿序》:“诸稿不独具体作者,而音节铿然入耳,色泽莹然入目。”[36](《甔甀洞续稿》卷七)
七子诗派之所以推崇汉魏盛唐诗,否定宋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从诗的声响和色泽方面来考虑的。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论盛唐诗曰:“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相反,元和长庆以后之诗,则“歌之无声也,目之无色也”。[16]4391李梦阳在《缶音集序》中也是从声、色这两个角度来否定宋诗的:“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11]1694唐诗音律和谐,多可歌,而宋诗则以意为主,以文为诗,甚至拗折声律,不重音调。唐诗多以景物含情,富于色泽美,而宋诗以平淡为美,黄、陈等人甚至刻意摆脱风景、回避声色。这都是明代复古派所否定的。
论诗重声、色,与重“气”正相关。先秦以来的“气”论思想认为,五声、五色都是由“气”所生。如《左传》昭公元年载医和言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37]1222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大叔言曰:“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37]1457这种气生声色的观念,也被明代复古诗派中的很多人继承了下来。作为复古派先声的李东阳即以“气”论“声”,如其《刘文和公集序》云:“人有形斯有气,有气斯有声。文者,声之成章者也。气昌而大,则其文雄伟明畅,惟所欲言而无所底滞。”[38]183李梦阳在所撰《空同子》的《化理篇》中指出,声色皆为五行之气所化:“声色者,五行精华之气以之为神者也。”[11]1970《论学上》篇也说:“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发之声为音,吐其采为色,腾之为气,滋之为味,天以之成,人以之生。”[11]1995王廷相则著《律吕论》十三篇,在《五音》篇中论音声与气之关系:“人之音声,随气而吐,故气呼而声出,必自宫而徵,自徵而商,自商而羽,自羽而角。角者,气平之声,音之终事也。故曰:发于宫,达于徵,返于商,极于羽,而收于角。盖声气自然之机理,非一毫人力可以强而为之者。”[5]706吴国伦有《风》诗云:“太虚噫气,众籁成声。”[36](《甔甀洞续稿卷一》)也反映了同样的思想。
在这样的本体论思想影响下,七子派的诗学思想中对“声”“色”与“气”的关系也是有明确的自觉的。徐祯卿在《谈艺录》中说:“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27]765所谓“引而成音,气实为佐”、“ 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正是说诗之音声由气而来。此外,像“声气”、“气色”这样的论诗术语被前后七子频繁使用,正可以说明诗的“声”、“色”与“气”的一体性。如李梦阳《张生诗序》:“夫诗发之情乎?声气其区乎?”[11]1677又如王世贞《与魏顺甫书》:“四律气色,奕奕射眼。”[16]4424《何仲仁》:“足下诗,声调气色,高朗华秀。”[16]4528
“声”“色”即“气”,汉魏盛唐诗歌之所以富于声色,正因为其以“气”为主。而宋诗之所以少于声色,则因为中唐以来诗学发展由尚“气”转为尚“意”。尚意的宋代诗学倾向于理性化的老成、平淡之美,对于感性化的声色是有意回避的。而明代复古诗学以声色论诗,正是对汉魏盛唐尚“气”诗学的回归。
结语
“气”是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也是汉魏盛唐诗学的本质精神,其本质是一种感性的生命力。这种“气”表现在士人的人格气节上,也表现在诗的慷慨风骨中。以“气”为本的汉魏盛唐诗重自然的“气感”,而非刻意的经营;追求浑成的气格,而不是词意的刻露;重“象”而非直陈;重“声”“色”而非枯淡。这与重“意”的宋型诗学均不相同。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诗学正是要一反宋人的重“意”而一归于汉魏盛唐的重“气”。这与明代中后期“气”论思想对程朱理学的反转正相表里。以“气”的思想为结合点,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与同时期的原始儒学复兴运动融合在了一起。因此,“气”对于观察和解释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是很重要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