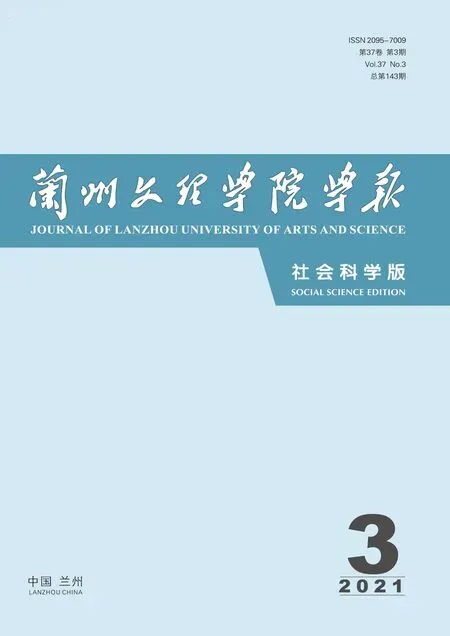维柯的魅力及人文教育的意义
——评叶淑媛《人文时空:维柯和〈新科学〉》
张 慧 敏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在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已然成为不言自明的背景和常识的语境下,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的介绍也从“补课式”地学习渐渐呈现出同步化跟踪趋势,特别是从上世纪末八十年代以来,从言必称萨特、海德格尔,到新世纪初的言必称福柯、哈贝马斯,再到当下的言必称阿甘本、朗西埃等,学术新宠不断变换面目,学术明星不断地引领、塑造着学术圈的时尚和趣味。这一方面的确说明我们越来越能够及时地跟进西方重要思想家的最新思考并很快地将其译介入汉语学界,但另一方面也需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一直以来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我们在不断跟踪译介西方的过程中,其中既有近似于赶时髦的追新逐奇,又有功利性现实语境下的为我所用,用过即丢,结果常常导致很多西方思想理论像原子似的从其话语谱系中被割裂出来又很快地被丢弃一边,而很难或很少能够完全融入我们的思维深层,进而成为我们精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面对西方的时候,只有能够以坚定踏实而非走马观花或蜻蜓点水的态度来进入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世界,才既是真正值得尊敬同时也真正有益于学术积累和文化积淀。在这样定位的学人中,叶淑媛教授及其新著《人文时空:维柯和〈新科学〉》(以下简称《人文时空》)可谓是一典范。
一、“以维柯的方式”重新认识维柯
相比较于当下那些炙手可热的西方大家来说,维柯的名字显然显得过于沉寂甚至于几近于被遗忘。实际上,维柯是公认的18世纪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众多理论学说,其地位和意义不言而喻是属于世界性的。在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朱光潜先生译介《新科学》以来,也曾启发了诸多学人对维柯的关注和研究。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些研究中,所论者多是单涉及其历史哲学和美学观念,既少有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论述,更缺乏对维柯的全面研究,这实在和维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所赋予我们的思想资源极不相称。因此,叶淑媛这部对维柯的研究专著《人文时空》对汉语学界的维柯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收获。
然而,要对维柯做出全面理解和研究实非易事,这也是全世界诸多学者不断发掘、探究维柯意义的动力和缘由。维柯的主要著作《新科学》可谓是一部历久弥新之巨作。因为人们越来越发现,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学科乃至于不同立场的思想家都可以与维柯及其著作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甚至把他视为是自己的先驱,“无论是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者们,都能从维柯那里找到所需的资源”“维柯俨然一位现代的柏拉图”[1]。因此,《新科学》不仅是近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当代思想中反思和批判启蒙现代性的必要武器。其实很难用当下既定的学科分类来对维柯进行定位,因为在《新科学》中涉及到了今天所谓的法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历史学、语文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修辞学等。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如果离开了《新科学》那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甚至是最严重的缺憾。
今天意义上的诸种学科分类其实是18世纪以来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每一个特定的学者都归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互相之间少有交集。其形成特别受工业革命以后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影响,与现代文化领域随之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分化密切相关。大体上说来,原始文化是整合不分的,从原始文化到古典文化再到现代文化,其契机之一就在于分化现象的出现,各学科专业领域的形成,既是其自身不断追求自律性和合法性的表现,也是现代社会分化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伴随着这种分化的结果是社会和文化总体性的丧失,一方面人们在欢庆解构主义击破“元叙事”“宏大叙事”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面对满地无法整合的意义碎片而无能为力。卢卡契在批判资本主义文学因丧失这种“总体性”而陷入一种“颓废”风格时说到,“其(颓废)特征在于,生命不再存在于整体之中,每个字都是自主的,它跃出了句子;而句子又侵犯别的句子,于是模糊了整页字的意义;整页字又牺牲了全篇而赢得了生命。全篇就再也不成其为整体了……每一个原子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意志则土崩瓦解了……生活,同样的活力,生命的震动与繁荣被排挤到最小的形象里面,剩余部分则缺少活动。到处是瘫痪、困倦、僵化或者敌意、混乱:把这两者的组织形式提的越高,它们就越清楚地跃入人们的眼帘。整体根本不复存在了;它是一个经过计算拼凑起来的人工制品”[2]。虽然时至今日有很多证据表明,在大众文化日益膨胀和扩张的条件下,很多文化边界业已消失,日益化为宽泛无边的文化现象,整个(后现代)社会主要的游戏规则不再是分化,而是去分化。例如,艺术和非艺术、艺术和生活的界限逐渐模糊;现代艺术纯粹性的打破以及混杂艺术的兴起等,原先现代性分化所形成的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审美—表现理性的边界也消失了,在学科领域也的确出现了一些学科融合、跨学科或反学科等的倾向,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专业和学科之间的壁垒绝非在短期之内就能打破。
维柯生活的18世纪正是西方社会资产阶级开始迅速崛起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在欧洲思想史上常常被称为理性时代,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正是强调理性思维的笛卡尔主义,这种唯理主义也成为西方启蒙现代性发展不竭的动力基础。维柯虽然没有能够亲眼目睹日后西方社会在技术理性的引领下畸形发展的现实,但他显然早已对笛卡尔的“理性”的危害有所怀疑。在浪漫主义尚未展开对资本主义启蒙现代性的批判之前,维柯就已经单枪匹马地向笛卡尔哲学提出了挑战。维柯的理论虽然也追求可靠的认识, 是十六、十七世纪以来寻求科学真理传统的一部分,但其基本倾向是反笛卡尔主义的,同时又继承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文化传统。在维柯生活的年代,西班牙治下的那不勒斯城邦是彼时意大利的文化重镇之一,维柯在这里以学习当时最发达的法学开始了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维柯绝不满足于此。他认为分门别类的学科缺少一种融会贯通的整体性,导致初学者很容易误入学术迷宫而距离真正的学术殿堂越来越远。为了高屋建瓴地把握人文学术的命脉,从整体上指导各门学术,维柯构思并写作了《普遍法律的唯一原理》及其附编《论法学的融贯一致性》,这两部文献也成为《新科学》的基本素材以及其整个学说的基本框架。我以为,正是这种追求融贯一致或曰整体性的努力成为他不断吸引20世纪以来现代语境中的学者的最大魅力。“维柯的思想是求深、求高、求远——求深,即在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政体之下去探索永恒的正义;求高,即在形而上学的高度上去探索天意神恩对于世俗历史、人间意志的干预作业;求远,即一头扎进邈远迷茫的古代,探索初民诗性智慧的创建力量,去发现真正的荷马。”[3]维柯不愧是孤独思想家的典范。
正是在这一点上,《人文时空》的写作体现出了一种以“维柯的方式”来研究维柯的追求。作者在对理论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力图多角度、全方位地来解读维柯及其《新科学》,既注重维柯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维柯思想在全世界产生的文化效应,也突出关注维柯思想的古典来源和古典精神。前者强调的是向后的效应史,如对维柯思想的传播、影响的研究、对其“诗性智慧”说与后来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潮之关系的研究等;后者强调的是向前的谱系史,如对维柯思想来源的分析、与笛卡尔的分歧、与格劳秀斯的共鸣和超越、如何融合经验派和理性派的观点等;同时,她还努力突破自身文学专业出身的界限,对维柯的人文教育思想、历史哲学思想、美学思想以及人类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这种跨学科求取融贯一致的追求,避开当下的热点而一头钻入古典文献《新科学》中去发现真正的维柯的努力,不是上文所述的“维柯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二、“像维柯一样”面对人文教育
维柯生活在一个神学流行的世界。他信仰天主教的神,反对当时新兴的学说,特别是笛卡尔。笛卡尔哲学的出发点是思维的自我。在他看来,人类日常的感觉和常识都是不可靠的,一切都可以怀疑,一切都必须由思维的自我来重新审定。怀疑一切的自我最后发现,唯一无可怀疑的是他自己在思维、在怀疑这个事实,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存在的可靠性首先在自我的思维中得到证明,所以叫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认为抽象的逻辑思维能明确肯定地把握住事物的性质,可以把认识到的真理用数学语言描述出来,而具体的感性事物却很难明确肯定地把握, 容易造成人的偏见和错觉。在这种唯理主义观念支配下,所谓科学只能是自然科学,可靠的认识必定是可以数量化的认识, 而法律、历史等等属于人类社会范畴的理论,都算不得科学的真知。笛卡尔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纯然客观的数学-科学系统,可以解释宇宙一切,而维柯却认为,自然界的科学知识应该留给上帝,人创造出来的世界则必须由人来解释,在《新科学》中第331段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以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的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4]。
这个认识和解释的方法是什么? 其实就是今天意义上人文和社会学科。维柯所谓的“新科学”就是指对于自然界以外的人的世界——包括历史、法律制度,甚至远古时期的神话,他认为这样一种科学在完整性上比物理学强,在真实程度方面又比数学强,这当然是对人文学科的意义和性质的极大肯定。
可以说,维柯及其《新科学》所要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和人类社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今天重估维柯的意义,也许可以这样说,维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贡献和成就,可以和与他同时代的牛顿在自然科学中的建树相媲美。”[5]人人都知道,人是复杂的动物。人类所具有的那些禀性:理智、情感、想象、幻想、创意、抽象思维、潜意识欲望、身体感官的各种感觉和刺激等等,无一不是历代哲人所关心和思考的重要命题。现代大学里相应地有诸多不同的专业和学科来研究人类的行为和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人文学科,它和研究人类组织的“社会科学”密切相关而且互动。实际上人文学科本来就应该是“跨学科”的,它和自然科学不同,因为人不能被肆意分解成几块,分解开了反而失去人的意义。然而,如前所述,今日所有大学的专业化趋势——现代性分化和合理化的必然结果——也使得人文学科支离破碎,很少人做整合的工作,甚至连跨学科的对话也很罕见。专业化的结果必会导致人文学科的边缘化和凋零。
人文学科的衰落已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种衰落,实非短期之内才出现,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在西皆是如此。正是注意到了这一严峻的事实,才引起学界持续不断的呼吁和争论。然而,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学人,我以为这又是一个无论强调多少次都不过分的话题。本书作者当然毫不例外地对此有深刻的切身感受,她说:“当精神的乏味成为人们普遍的忧患,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为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阅读维柯的意义可能就在于他以‘诗性智慧’和他对人文社会科学深邃的思考回应着这个时代的要求,引导人们关注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唤起人们对可贵的人文精神的追寻。”[5]在书中,作者除对《新科学》作细致的剖析外,还重点挖掘了维柯的人文教育思想。当然,这两者本身也是密切相关,自成脉络的。维柯的人文教育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早期在担任那不勒斯大学修辞学教授期间所发表的七篇开学典礼演讲,后人将其结集为《维柯论人文教育》,每一讲都各有专题,包含着维柯丰富的人文教育思想,如果高度概括起来的话,那就是,维柯认为人文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哲人-公民,即完整的人,这一点和马克思对人的存在理想也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维柯的人文演讲自有其特定的语境。在他的时代,维柯一方面要面对旧的基督教神学教育传统,去论证只有人文教育才能治疗日益败坏的人性;另一方面则要面对方兴未艾的、以笛卡尔主义为代表的整个现代哲学唯科学主义的知识体系和教育理路。后一境遇时至今日成为人文学科的最大障碍,全世界程度不等的来自理工类自然学科的排挤,意识形态的统辖,使得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倍感艰难。当代教育以精细的专业分工、极度工具化理性来获取最大现实收益的教育目标,使得教育成为为了专业知识而组织的专门训练,教育走向了职业教育而不是人文教育。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把自知作为教育目标的意识,所以数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教育都受到了损害——在人文科学知和社会思想领域中也是如此”[6]。而维柯的全部演讲就拥有一个苏格拉底式的开头:认识你自己。在维柯看来,上帝是认识的目的,而自知是认识的开端,人的自己就是其精神,“认识你自己”也就意味着“认识你自己的精神”。如此朴素的真理却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被人们遗弃而难以真正践行。
约翰·亚当斯密曾在美国革命期间写到,“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的艺术,所以我的子孙后代可以有闲暇来研究哲学和数学。我们的儿子要学习熟悉、哲学、地理、自然史、航海、造船、商业和农业,所以他们的儿子们得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编织和陶艺”[7]。也许现在他们还没有开始学习诗歌而是在编写应用程序,这样的时代还未到来。然而我们无需绝望,我们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认真反思自己的生命和人生,对世界或历史也没有足够的认识,但只要坚持人文教育的理念,这些问题或许都将有解决的一天。
关于人文学科的话题在今日的确被讨论了很多,而作者依然将其对维柯及其《新科学》的思考研究冠之以“人文时空”的名字,可以见出她对维柯理解的着力点在何处。这当然既是维柯思想本身的意义所在,也是研究者在面对维柯时由衷生出的认识和感慨,从而不遗余力地想要将其呈现出来,展示给读者大众,以期引起他们的认同和共鸣。当然,如前所述,面对维柯是不易的,能够选择进入维柯的思想世界是需要勇气的,绝非那些讨巧的文学批评家所能及,只有真正具备一个理论家的素质,才可以在立足整个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上,尽力地进入维柯,也就是我所谓“以维柯的方式重新认识维柯”。生活在这样一个为各种信息所窒息的社会而仍可以孜孜以求着智慧和理想的人,他们是能够纵览全局者,他们能够在恰当的时间运用和处理恰当的信息,以独立的思考来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以为,这是维柯给予我们的信念,也是该书作者给我们做出的榜样。